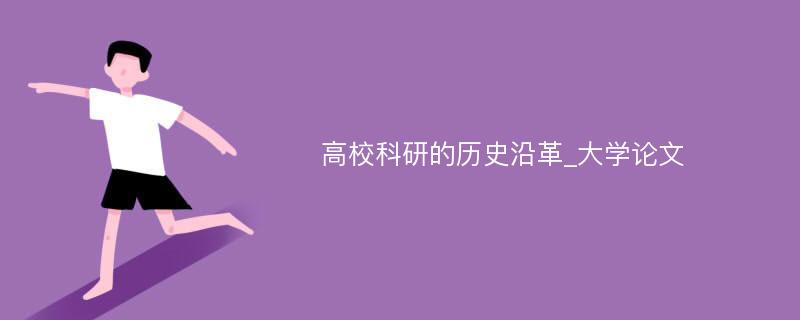
科学研究在大学中的历史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研究论文,学中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608(2006)04-0076-06
科学研究成为现代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中人们的主要活动,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可是在中世纪大学产生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情况并非如此。科学研究是何时进入大学的?科学研究进入大学之后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大学的科学研究史是如何演进的?探讨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认识大学中科学研究的性质、作用以及大学开展科学研究的组织与形式。
一、与教学相结合的研究的发端
“研究活动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认识主要彰显于19世纪的德国大学。到19世纪末,这种认识传播至世界各国,并得到普遍认可”[1] 145。在19世纪的德国,说到将研究作为大学的重要活动,就不得不提及洪堡关于大学的论说。
洪堡对19世纪初期德国大学改革与发展的贡献不仅在于他1809年出任普鲁士的宗教事务与教育局局长,在1810年作为德国大学改革起点与象征的柏林大学的成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更在于他的大学理念、思想影响着德国大学的办学实践。洪堡的大学理念中有两个相互联系的重要的基本观点,即大学是学问的机构,研究是大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其他论述都是由这两点出发,或者说是围绕着这两点而展开的。
关于大学是学问的机构,洪堡在《关于柏林高等教育机构的内部组织与外部组织的理念》中是这样论述的。“与传授和学习既成知识的中学不同,大学的特征在于常常将学问看作是没有解决的问题不断地进行研究。因此在大学中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完全不同于中学,既大学的教师并不是因为学生而存在,教师和学生都为学问而存在”[2] 210-211。洪堡认为,在学问中尚有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没有发现的原理,甚至可以说有些原理也许永远发现不了,正因为如此,“不断地研究、追寻学问是大学必须坚持的原则”[2] 215。从大学是学问的机构之观点出发,洪堡得出的结论是,大学不仅担负传授知识的任务,而且承担创造学问的使命,研究与教学的统一是大学的基本原则。
在大学这样一种学问机构之中,教师与学生都为学问而存在,这就使得教师与学生的关系脱离了传统的样式而发生了某种根本的改变。所谓传统的样式是指,“从教师是真理的拥有者这一前提出发,教师在社会上、组织上占有优越的地位”[3] 99,在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中教师是传授知识的一方。可是在洪堡的大学理念中,教师与学生是学问交流的双方,处在相同的立场或位置上,“各自自主、孤独地从事着学习或研究活动”。洪堡在《柯尼斯堡学校计划》中这样写道:“大学教师已经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教师,学生也不是被动的学习者。学生自主地从事研究活动,教师则对学生的研究给予指导、帮助。因此对当今大学教授的要求是,能够把握学问的统一性,具有创造力。”[3] 104
在这样一种关系中,大学教师的教学目的也发生了变化。按照传统的理解,教学的主要目的是让学生掌握教师传授的知识。可是在作为学问机构的大学中,教学成为促进研究的一种手段。“在自主思考的学生面前进行自由的讲演,这会给讲演者即教师本人带来新鲜的刺激。这种刺激并不亚于从学者团体中所得到的。在拥有众多精力充沛的青年学生的大学中通过不断的讨论学问更加活跃,其发展更为迅速”。[2] 217-218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讲,教学对教师的研究来讲成为必要。
如果我们对洪堡关于大学中的研究之论说做一简要概括的话,其主要内容应是这样几点:第一,洪堡关于大学中研究之论说的基本出发点是将大学看作为学术机构,既是学术机构,研究乃其本意;第二,洪堡是将研究置于与教学的关系中来加以论述的;第三,研究与教学相结合是大学的基本原则,两者的结合体现在一方面通过研究进行教学,研究成为培养学生的主要途径之一,另一方面教学过程即研究过程,教学成为促进研究的一种手段。“研究与教学统一的理念不仅规定了教授的作用,而且意指教学活动必须与研究紧密结合,并且直接建立在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之基础上。大学教师必须不断地进行研究活动,并将从研究活动中获得的见解与成果直接用于教学。更进一步明确地说,开展其成果能够在教育中立刻发挥作用的研究活动,这是大学教师的义务”[4] 16。
洪堡的大学是学问的机构、通过研究进行教学的思想在19世纪德国大学中的具体体现为:
1.哲学院的地位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当时的德国大学一般拥有4个学院,即哲学院、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哲学院取代了一直以来神学院的主导地位,立于大学学问的顶点,成为综合大学的核心。哲学不仅有助于人类伦理的确立与自我实现,而且以它的批判、形成规范的功能促进其他学问的发展”[5] 190。哲学院在19世纪德国大学中的地位,从教授的数量上也可以反映出来。据统计,1840年、1870年、1892年德国大学中正式教授的数量依次为,哲学院270人、383人、519人,神学院120人、130人、131人,法学院108人、126人、148人,医学院135人、166人、211人。哲学院的教授数量不仅远远多于其他3个学院(1892年哲学院的教授数量比其他3个学院的教授数量总和还多),而且增长幅度也是最大的。哲学院的强大使得德国大学染上了浓厚的理论色彩,人们甚至认为,“整个德国的学者荟萃的大学院,竟成为哲学院的一个附庸”。
2.大学的教育由“实践的教条主义”转为“理论的学术研究”。这不仅体现在哲学教育上,更体现在神学、法学、医学的教育中。例如,柏林大学所实施的法学教育不是“风靡18世纪的功利主义的法学教育”,而是“不为功用、实际应用所累的高级教育,即以解决学问问题为目的的超俗教育”[7] 285。“在18世纪,基本教课内容是教条主义的实践,从传教士或法官等职称就可直接知道它们的性质。但是现在看来最重要的,是训练历史研究的能力,在可能时,并包括调查研究和来源批判的科学研究”。大学教授对实践职业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过去,“神学教授保持基督教会的职务;哲学家常常从事于教师或学校指导员工作;法理学家常常成为某一审判委员会的成员;最后,医学教授当然是开业医师。这些惯例,现在虽然尚有一部分残留,特别是医学院里,但大体上大学教师为了纯科学的钻研,已逐渐放弃主动的实践”。
3.研究班(seminar)的教学形式成为大学教育的突出特征之一。研究班的“目的不只是传授已经获得的知识,而且要引导学生进入科学工作,不只是传播知识本身,而且要传授知识如何求得的法门”。虽然研究班早在18世纪初期的哈雷大学、哥廷根大学就已出现,但是在18世纪大学的研究班里也只是“向学生传授一些被认为有用的不成体系的实务知识”。而在柏林大学的研究班上,“是让学生参加教授的研究活动,是以使学生习得教授的思想、教养为目的。因此,神学的研究班不传授对神职人员有用的实务知识,而讨论哲学、历史学、东方学。语言文献学的研究班则成为培养古典学者的温床”[6] 286。
总之,“到19世纪70年代左右为止,全世界能够训练学生从事科学、学术研究的机构,实际上唯有德国的大学”[1] 33。当时的德国大学“以科研作为首要的成分,教授的作用在于把科研和教学结合起来——科研活动十分恰当地成为一种教学的模式。学生的作用就是把科研和学习结合起来——科研活动转变为一种学习的模式。因此科研使教授和学生定向,把教学和学习合拢来成为促进知识的一个无缝的承诺之网,铸成了一个紧密的科研——教学——学习联结体”。[7] 1
二、研究与教学相结合的美国模式
洪堡提出大学是学问的机构、通过研究进行教学思想的19世纪初期,大学中的学问还是以人文学科、哲学为中心。大学研究与教学的人文性、哲学性是洪堡思想的实践基础。“因此教学与研究的结合被认为是,学者对各自领域的权威传统加以解释,在传统上加上自己的创造贡献,并提出新问题,或是以新的形式重组传统,给传统增添新的色彩”[1] 152。当时,“在德国的大学实验科学还不被重视,人们仍然主张应以哲学的、思辨的方法对待自然科学,采取了浪漫的‘自然哲学’立场”[1] 153。
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实验研究逐步进入大学,但由于实验最初“只是对大学没有多少用处的培养药剂师的职业课程,因此被看作是教师个人的行为。吉森大学的李比希研究所成立之初就是如此”[1] 154。不过,随着大学对具有研究能力的教师之需求的增加和化学、物理学、生理学等自然科学的长足的发展,实验研究逐渐在大学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例如,在柏林大学哲学院,1820年数学、自然科学类课程只占课程总数的约12%,而到1830年,这些课程所占比例已经上升到53%[6] 412),李比希的化学研究所后来成为许多大学模仿的样板。李比希对研究所的研究与教学有过这样的描述:“普通概念上的实验室教育,在这所教室里只是由熟练的助手教给初学者的,而我负责指导的学生是根据各自情况来学习。具体方法是我给每个学生以研究专题,并检查他们实践的情况。那如同一个圆的半径有共同的中心一样。我没有对学生进行一般定义的那种指导,而是每天早晨听取每个学生前一天研究进展的情况以及对自己研究工作的见解。最后我对他们表示赞成或反对。让每个学生寻找自己的路是必要的。同时各个学生在共同的研究生活和不断交往中,以及参加所有研究生的工作中相互取长补短。”[8] 62
但是,在研究愈来愈专门化之后,人们发现并不是所有学科的研究都能与教学相结合,都能对培养专门人才有所作用。“特别是在物理学科产生出一些新的领域,这些新领域的知识对于想成为这些领域的研究者以外的人来说,过于专门化。在大学中,物理的实验教学虽然晚于化学和生理学,直到19世纪60年代才真正开始,可是在19世纪末物理已经成为实验科学中最富有知趣的领域。尽管如此,与化学和生理学不同,除了想成为物理研究者之外,高深的物理研究对其他的职业人才培养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作用”[1] 160。由此,虽然研究与教学结合促进了19世纪德国科学的发展,研究与教学结合的理念在德国大学扎下了根,但是在实践中愈来愈高度专门化的研究和并不需要太多高深学问的职业人才的培养之结合出现了问题,在大学之外一些独立的专门研究机构开始出现。
当欧洲出现洪堡的理念与大学实践不太合拍之状况的时候,大洋彼岸的美国产生出研究与教学相结合的新的模式。
19世纪下半叶在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一时期所发生的诸多改革奠定了美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基础,换句话说,美国大学的现代化开始于19世纪下半叶。影响19世纪下半叶美国大学发展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1862年由林肯总统签署实施的有关赠地办农业和机械工程学院的莫里尔法,另外一个是19世纪初期改革之后形成的德国大学模式。前者引导美国大学走上为社会发展服务的道路,后者给美国大学制度染上了高深学问的色彩。当时,德国大学模式对美国大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1.系的体制就是根据德国讲座制度的概念而建立的,大学的学术工作是根据学科来划分的。2.科学研究越来越被强调为大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博士学位被确定为大学教育的顶点。3.大学与国家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政府对科学研究的投资更普遍了。4.随着大学自主权的扩大和可得到的科学研究资金的增加,大学教授的声誉也提高了。”[9] 32而1876年成立的约翰·霍布金斯大学更被看作是德国大学的翻版,它被人们称为“巴尔的摩的哥廷根大学”。约翰·霍布金斯大学成立的意义在于它将研究与研究生教育结合起来,开创了研究与教学结合的美国模式。首任校长吉尔曼在就职时这样阐述了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的目的,即“促进研究,培养青年人,使作为研究对象的各门学科得到发展,为了社会的进步”[10] 516。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的成立在当时的美国大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紧随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科学研究与研究生教育相结合的理念,19世纪90年代其他一些规模较大的综合大学也纷纷成立了研究生院。这些大学依靠所拥有的财产和学费收入为学校规模和完成使命提供基础支撑。这其中既有斯坦福(1891年)、芝加哥(1892年)这样的包括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的新设大学,也有哈佛、哥伦比亚那样的历史悠久的私立大学,还有威斯康星、密西根、伊利诺依那样的依靠1862年和1890年莫里尔法规定的政府补助金、1887年哈奇法规定的实验农场补助金而诞生的赠地大学。到1900年,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已经增加到14所,授予博士300人”。[11] 303
用博士制度培养研究人员美国并不为先,在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已经盛行,据统计,1820年到1849年的30年间,仅柏林大学就授予博士学位3458人[8] 66。不过德国大学的博士培养没有固定的年限,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个教育阶段。美国的制度创新在于,在综合大学中建立了研究生院,研究生培养成为一种教育制度,它与本科教育之间有了明确的区分,而且在研究生教育中实现研究与教学的结合。诚如伯顿·克拉克所言:“在学校层次,实现教学与研究和学习统一原则的最重要的有利条件,是正式建立一个研究生教育层次。从对美国研究生教育的分析可以看到,研究生院已经是美国大学使教学和高级学习具有科研基础的能力的结构上的核心。”[7] 259研究生院成为研究者的培养机构,研究则是研究生教育的主要方式和途径。美国的主要在研究生教育阶段实现研究与教学相结合的模式是对洪堡理念的发展,它明确了研究与教学相结合在大学实践中的局限性或条件性,即这一原则仅适用于部分大学的高层次教学与学习。
三、与教学分离的研究的发展
无论是洪堡的理念,还是19世纪德国的实践,或是美国的模式,大学中的研究活动是在与教学活动的结合过程中发生的,研究是培养人才的需要,培养人才是研究的基本出发点。这种研究与教学结合的状况到20世纪40年代发生了某些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一时期,研究生院的巨大的研究能力被动员参加到一些研究开发项目中,例如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研究开发项目——原子弹的研制。研究经费急剧增加,同时用于高等教育的支出也有大幅的增长(见表1)。大学内设置了从未见过的大规模研究所,这些研究所虽然不完全被大学所包容,但是它们处于大学的管理之下,例如伯克利的劳伦斯辐射研究所、芝加哥的阿尔贡研究所。这样的状况改变了大学教师和行政管理者的视野与观点,开展与教学没有直接关系的研究被看作是大学可以发挥的正常作用,甚至是主要的作用”。[1] 176
表1 美国高等教育、研究开发的经费支出及其占GNP的比例
(单位:10亿美元)
年度
GNP高等教育 研究开发
支出
占GNP之比 支出
占GNP之比
1920
88.9
0.2160.24%
1930
90.4
0.6320.70%
1940
99.7
0.7590.76% 0.340 0.34%
1950 284.8
2.6620.94% 2.800 0.98%
1955 398.06.279 1.58%
1960 503.7
6.6171.31% 13.7302.73%
1965 684.9 15.2002.22% 20.4392.98%
1970 974.1 24.9002.56% 26.0002.66%
资料来源:Joseph Ben David著、天城勳,译:《学問の府》,サィマル出版会,1982年,第177页。
可以这样认为,在20世纪40年代之后,首先在美国的大学中,研究活动发生了变化。那些以培养人才为基本出发点、与教学紧密结合、自由探究、小规模甚或个别式、传统的科学与学术研究依然存在,同时出现了为了教育之外的某个目的、与教学没有什么关系、有明确的组织目标、大规模的科学研究。二战期间的“原子弹研制”(又称“曼哈顿工程”)是典型的事例。该项工程从1942年开始至1945年结束,耗资20亿美元,参与的研究人员上千人,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一批一流大学作为工程的基础与核心,如进行气体发散研究的哥伦比亚大学,进行电磁分离和钚研究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进行武器理论和链式反应研究的芝加哥大学,以及提供辅助数据的明尼苏达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哈佛大学、康乃尔大学等[12] 60。
大学研究的大规模化、社会化(这里的社会化即包括大学研究目的的社会化,也包括研究内容、研究组织的社会化)给大学研究带来的另一大变化是研究经费的急剧增长和研究经费来源的改变。例如,美国大学研究经费的主要来源经过了由个人、慈善基金会到企业再到政府这样一个转变的过程。“最初,支持学术研究的外部资金主要来自从事慈善事业的基金会,企业的作用不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政府开始介入之前,基金会与企业的影响一直没有衰减”[4] 317。而在支持大学研究的基金会中,约翰·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安德鲁·卡内基基金会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例如,193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的研究资助经费占所有基金会研究资助经费总额的比例,社会科学为64%,自然科学达到72%。[4] 318从二战开始,出于军事的需要,美国政府开始有计划、大规模地支持大学开展目的明确的科学研究,政府的科研经费逐渐成为大学研究经费的主要来源,大学的研究活动愈来愈依赖于政府的支持。
表2提供了从20世纪70年代初至90年代末美国大学各学科领域科研经费中联邦政府资助所占比重的情况。虽然在80年代的初、中期联邦政府的资助比重有所下降(那恐怕主要是里根政府的保守主义政策所至),但是到90年代末联邦政府资助占大学科研经费总数的比例仍然保持在约60%。而自然科学的一些领域联邦政府资助经费的比例达到70%左右,这体现出大学科研在经费上对政府的依赖程度。
表2 分领域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经费占大学研究经费的比例(%)
年度 物理科学 计算机科学 环境科学 生命科学 心理学 社会科学
工学 总体
197381.8 69.9
75.2 66.3 79.5 57.3 71.5 68.8
197680.5 74.0
73.4 65.7 76.2 52.7 67.3 67.4
197981.5 70.9
72.6 64.1 72.3 53.0 68.7 67.1
198278.9 74.2
70.1 62.4 68.1 45.6 67.2 65.1
198577.5 69.7
67.2 60.4 66.9 40.1 61.2 62.6
198676.4 72.4
66.6 59.3 67.0 37.4 59.6 61.4
198775.2 69.1
65.0 58.8 66.1 33.6 58.8 60.4
198874.5 70.8
65.9 59.6 65.9 34.2 58.7 60.9
198972.7 68.5
64.8 59.3 65.5 33.5 57.8 60.0
199072.8 66.5
63.8 58.3 64.8 32.2 57.4 59.2
199171.4 67.0
62.7 57.2 65.8 33.7 56.4 58.2
199271.8 68.4
63.7 58.0 65.4 34.5 57.2 58.9
199371.0 69.7
66.0 58.9 67.0 37.7 58.9 59.9
199472.0 71.4
67.4 58.7 67.6 37.7 59.6 60.2
199572.8 70.5
66.9 58.3 67.8 38.2 59.9 60.1
199672.4 72.5
67.3 58.1 68.3 38.8 60.3 60.0
199772.1 71.5
67.2 57.9 69.6 37.4 59.4 59.6
资料来源:宫田由起夫:《アメリカの産学連携》,东洋经济新报社,2002年,第61页。
上述大学研究活动在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变化反映了现代科学发展的基本特征,即科学发展进入了所谓的“大科学”时代。诚如美国学者普赖斯所说:“不仅现代科学硬件如此光辉不朽,堪与埃及金字塔和欧洲中世纪大教堂相媲美,而且用于科学事业人力物力的国家支出也骤然使科学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环节。现代科学的大规律性,面貌一新且强而有力,使人们以‘大科学’一词来美誉之。”[13]“大科学”是与“小科学”相对而言。所谓“小科学”,一般指“历史上那种以增长人类知识为主要目的、以个人的自由研究为主要特征的科学”。“大科学”则是“规模巨大,拥有高级技术装备,并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产生重大影响作用的现代自然科学”。也可以说是“涉及学科多,参加人数多,耗用资金多,且需要时间长的大型科学项目”[14]。“大科学”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研究内容的综合性,研究内容涉及多个学科;研究活动的集团性,研究需要多学科、多部门人员的共同参与;研究组织的系统性,研究活动为一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精密管理;研究经费的巨大性,一个“大科学”项目往往需要耗费巨额的研究经费。
毫无疑问,拥有众多学科、众多研究人员的大学是“大科学”研究的主要力量。大学的研究在被纳入“大科学”体系之后,研究的目的与“小科学”时代相比发生了变化,研究(准确地说应该是部分研究,因为即使在“大科学”时代,那些被称作“小科学”的研究依然存在)也就开始远离教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