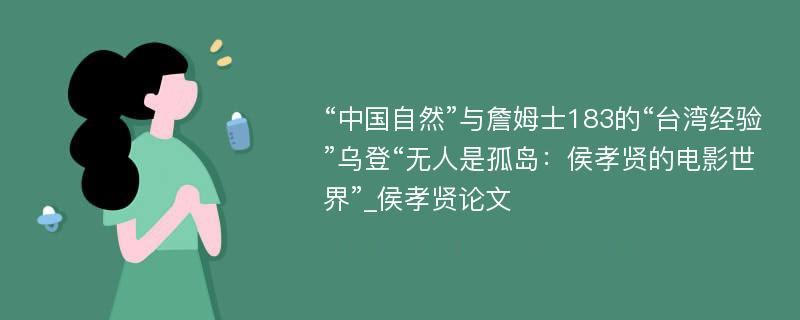
中国性与“台湾经验”——评詹姆斯#183;乌登《无人是孤岛:侯孝贤的电影世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詹姆斯论文,人是论文,台湾论文,孤岛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已成为重要的学术方法。在此背景下,海外电影研究很少局限于文本的艺术性,而越来越强调电影作为社会文本、文化文本的属性,重新回到了宏观的外围研究。侯孝贤电影因敏感的政治议题、突出的美学形式,成为文化研究的最佳文本之一。美国电影学者詹姆斯·乌登的《无人是孤岛:侯孝贤的电影世界》(黄文杰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以下引文凡出自该著者均只标注页码)是近年的新作,表现出较强的专业性和理论深度。正如作者所说:“这本专著的目的,不仅是提供一个侯孝贤直至今日的创作生涯的概括,而且试图解释它为什么会以其特有的方式呈现的大量原因。”(第14-15页)他不愿意归纳侯孝贤特有的美学方式,更不打算概括他的创作历程,而是要解释他为什么能够成为侯孝贤的大量原因。这揭示了詹姆斯·乌登的学术雄心。从作者介绍得知,他为了写作该书,长期居住台湾,并多次采访导演及其合作者。确实,该专著提供了访谈侯孝贤及相关人员的第一手材料、香港学者的英文研究资料,运用定量的研究方法,分析整理电影文本及镜头语言、镜头时数等重要数据,鲜活的经验、异域的学术理论及其方法,对国内侯孝贤乃至华语电影研究来说,都具有较强的借鉴价值。 乌登的论著虽然存在镜头数量、长度的定量研究(文本内部的形式研究,这种研究方法被译者赞许推崇),但就篇幅与价值倾向看,仍然属于文本外部的文化研究;更确切地说,它是电影的文化政治学研究。最明显的标志是:该论著的核心议题在于否定侯孝贤电影被中外学界公认的中国性,而极力强调所谓的“台湾经验”。对于这一话题的特殊意义,作者有着明确的认识:“这不是一个形式主义的学究式问题,而是充满着深刻的政治和文化的意涵”(第296页)。在我看来,这种囿于特殊倾向与立场的文化政治研究,导致了一系列的缺点,如限制了对侯孝贤电影其他论题的挖掘;在具体行文中,首尾处纠缠于非/反中国性的“台湾经验”,主体论述却时常与这一核心议题错位,等等。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清理该论著关于侯孝贤及其台湾电影史料的缺陷,而是认为,这种细节真实与整体谬误的文化政治学研究,在海外华语电影研究中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值得我们认真地分辨与反思。 一、“台湾经验”:非/反中国性的文化政治 在台湾文学及其电影研究中,“台湾经验”并不构成比地域经验更高阶的“中国文化”概念,相反,它以非此即彼的姿态表明自身的政治立场。因此,这种特殊的内涵根本不同于地域文学艺术研究通常所谓的“在地经验”(local experience)。它根源于台湾“民主运动”,是一个为了争取政治独立与国际地位而生造出来的文化概念,存在显见的非/反中国性的政治内涵。乌登对侯孝贤电影的“台湾经验”研究也遵循这一基本的构架。一方面,他坚决否认侯孝贤电影的中国性:“说侯孝贤的电影很中国,等于什么也没说。”“如果说中国文化对侯孝贤电影有任何意义的话,那么这种意义也在于中国文化在台湾约从1947年(和更早)到今天是如何过时的”(第11页)。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台湾对侯孝贤的决定性作用。“离开台湾,侯孝贤的电影就是不可想象的”(第11-12页)。“最重要的,本书试图表明在侯孝贤的创作生涯中,台湾是多么的不可或缺”(第15页)。“侯与台湾岛是不可分割的,没有彼此不可想象”(第345页)。在这种两元对立的话语体系中,侯孝贤电影的政治意义陡然倍增:说侯孝贤作品具有中国性,就意味着否定他的台湾经验;具有台湾经验,就意味着他反中国性的特征。 面对“如果我们问影评人和学者,谁是今日世界最中国的导演,毫无疑问侯的名字会经常跳出来”(第295页)。这样一个海内外学界公认的结论,乌登采用了几近全盘否定的方式(他相对推崇香港学者叶月瑜的侯孝贤电影研究,原因很简单,因为后者的华语电影研究也存在非/反中国性的学术取向)。他首先否定戈弗雷(Godfrey Cheshire)、傅东(Jean-Michel Frodon)、班文干(Jacques Pimapaneau)、波德维尔(David Bordwell)等海外学界那些肯定侯孝贤与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其中也包括乌登自己之前认为侯孝贤的历史态度与艺术直觉都非常“中国化”的看法),他认为这些都是文化本质主义渗透后的大同小异的论述(第2-3页),凡是从总括性解释文化通常是肤浅的(第14页)。继而,乌登也否定中国大陆学界的侯孝贤研究,因为后者总抱有不同的政治动机,“有意无意地与官方政策相吻合”,研究侯孝贤意味着提倡“大中华”的概念,因而存在宣扬民族主义的假定。如针对倪震提出侯孝贤电影表达了儒家精神,他认为:“这种陈述并不像它看起来的那么单纯,事实上包含了一些政治性的弦外之音”(第7页)。对台湾学界的侯孝贤研究,乌登也不尽然认同。如在他看来,台湾著名电影人焦雄屏用中国传统文化来解释侯孝贤,只不过是因为她肩负向海外推介台湾电影的使命,从市场的角度“吊胃口”。退一步说,“如果她真的信任侯氏的‘中国性’,那么充其量只是一种‘偏颇的解释’而已”(第12页),也就不值得重视。乌登发挥了侯孝贤长期合作者、编剧朱天文的看法(朱认为,“考虑到中国文化本身的复杂性和矛盾之处,把侯的风格界定为中国的,是非常困难的”),这使侯孝贤与中国性“偏得更远”(第12页)。该书的引注表明,这是朱天文接受乌登采访时的论断。我们姑且不论那是否是成熟的表达,单就此而言,她也没有否认侯孝贤风格与中国性的关联,而是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复杂性与矛盾处,所以将侯孝贤界定为“中国的”“非常困难”。甚至侯孝贤自己的说法也被乌登推翻。如侯孝贤在多个场合宣称自己既有中国人的文化因素,也是台湾导演的身份(第12-13页)。乌登的解释是,这似乎体现了侯孝贤受访时的灵活性。 那么,乌登是怎样从理论上反驳侯孝贤的中国性的呢?主要有两个层面: (一)历史文化的外围研究。他提出,认为侯孝贤电影具有“中国风格”的研究,就是“暗中假定一种本质的、统一的、共时的观念”(第8页),直接为之扣上了本质主义的帽子。然后,他以中国文化处于发展变化中为由,认为这个概念是空洞的。“中国文化及其儒家传统”存在前汉/后汉、佛教引入、南/北、高雅/大众等众多差异。儒家思想在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之前,只是一种“思想混合体”的组成部分(第8页),从汉朝到隋朝建立遭遇了道教复兴与佛教涌入的围攻。他用道家文化对中国书法、山水诗、画等影响,描述中国艺术传统的多样性。他“离题描述了中国思想与艺术的简短历史,目的很简单:只不过为了说明,说侯孝贤的电影很中国,等于什么也没说”(第11页)。也就是说,乌登用中国文化存在发展、儒家文化吸纳其他学派思想等理由,轻松地否认了具有本质规定性的中国性。 (二)电影文本的内部研究。乌登在描述完侯孝贤创作经历后,更在第四章专辟一节来总结侯孝贤电影不具中国性。其理由如下:1.长镜头不是中国电影传统,因此不能证明侯孝贤的中国性。“在整个电影史上长镜头运用得比较广泛,不但在欧洲的艺术电影中,甚至罕见地出现在最近的好莱坞影片”(第296页)。2.侯孝贤电影的场面调度强调复杂的立体视觉,布光“与日俱增的大胆”,然而,中国电影的场面调度“相对扁平”,布光“缺乏明暗对照”(第298页)。3.远距、吃饭等场景、抒情诗意大过于叙事等特征,也难以成为侯孝贤中国性的证据,因为他在后期创作中(如《海上花》)改变了远距长镜头,而且也没有从文化的角度解释大量吃饭场景,所谓的抒情诗意在世界影坛上也不是独一无二的(第299-300页)。4.认为侯孝贤电影具有中国性,意味着“在文化上不够特别”,反而取消他的独特性,降低了艺术价值(第300页)。 我们认为,对于侯孝贤电影非/反中国性的论题,乌登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尴尬。从写作体例来看,《无人是孤岛》的外部/历史语境的阐释与内部/文本故事的分裂是明显的。在诸多的文本细节上,很难避免侯孝贤电影作品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大陆存在着割舍不断的关联事实,如《童年往事》对广东梅县的乡愁、《悲情城市》潜在的大陆形象、《好男好女》中回大陆参加抗日战争的情节、《海上花》的地点发生在上海租界,等等。为了证明台湾比大陆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他认为台湾保存了中国传统文化,“想想本土宗教在台湾的复兴,也想想台湾保存了多少在大陆‘文革’中已经丧失的传统文化,很多人认识到,过去的大部分仍是台湾今天的一部分”(第345页)。既然台湾保存如此多的传统文化,那么,又怎能认为台湾经验是如此的非/反中国性、以至于两者“敌对”(第343页)?因此,无论他怎样分辩说外省人第二代的乡愁荡然无存(如《童年往事》),或仅仅是“想象的”文化中国(如《海上花》),还是来自大陆/外省人的压迫(如《悲情城市》),在侯孝贤的创作中包含如此复杂情绪的中国形象,已然清晰地表明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血脉命运的关联。就他以发展变动为由否认“中国文化”概念来说,同样是论证不足。从哲学上说,任何一个事物、现象、观念都不是静止的,而是一种“是其所是”的存在,使它成为自己的存在,经历了肯定—否定—肯定的否定辩证,产生出黑格尔意义上的生气贯注的观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它之所以仍然是其所是,就是因为存在某种难以改变的内在规定性。中国性同样如此。一方面它确实存在复杂的差异性,在传统/现代、本土/全球、现实/理想等不同维度之间充满张力,但另一方面,这种差异性始终受制于内在的规定性,从而构成了一个整体性的中国概念。侯孝贤具有中国性,并不意味着他成为同一、本质、僵化的中国性的表征,而是说,他以某种差异性的文化经验、美学形式(道家文化及其美学形式),丰富、补充了具有内在规定性的中国性。 乌登从内部的文本研究得出的非中国性,更缺乏足够的学理性。我们以长镜头语言为例。他从电影语言(如长镜头、景深构图、富有层次的布光等)具有世界共性的角度来证明侯孝贤电影与中国艺术传统相悖逆,因而并不存在中国性。我们知道,电影语言与自然语言不同。自然语言作为族群、地域、民族、国家等的天然屏障,能够区分文化的他者;电影语言是一种次生性语言,建立在光学镜头、剪辑、冲印等媒介技术基础上,长镜头、场面调度、景深镜头、蒙太奇、剪辑等意义表征,是在西方电影(包括欧洲艺术电影和美国商业电影)大量实践中逐渐约定俗成,并在新的媒介技术支持下,不断出现新的语言形式,呈现出开放的未完成状态。换句话说,电影语言是以现代影视技术为前提,人类共同参与、到目前仍然在不断挖掘开发的功能性语言,它根本就没有自然语言所具有的标识具体族裔、民族、国家的作用。我们不可能因正反打镜头、平行蒙太奇在美国电影中确立,就认为凡是使用这种镜头语言的均是美国电影。不仅如此,电影作为西方舶来品,是在欧美现代性语境中发展并丰富起来的,而非中国传统艺术之一种,因此中国电影缺乏中国书法、山水画、文人画等那样足以区分他者、标识中国身份的语言和艺术形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电影语言缺乏特殊的内涵,也不意味着中国电影理当没有自身的表征符号。文化研究揭示出语言、言语、话语的区别,即在语言的具体使用中(言语),出现福柯所说的“可个体化和被调节的实践”的话语①。语言媒介不仅能够指涉客观事实,同时也具有表现特殊情感效果的功能,这种特殊效果产生于话语的个体实践。也就是说,镜头剪辑、长镜头、静止镜头、全景镜头等构成抽象的电影语言体系,然而,一旦具体到电影作品,在导演的操作实践中就成为特殊的言语。任何一个导演使用长镜头等抽象语言,都是已被调整后的个体化实践。正如乌登概括的那样,沟口健二、安哲罗普洛斯、杨索、张艺谋、贾樟柯、洪尚秀等都大量使用长镜头,但是,此长镜头非彼长镜头,任何导演的长镜头使用均存在自身的独特性。每一个镜头的意义不仅关涉长短、运动、节奏、距离、构图等视觉层面,更取决于拍摄对象、演员表演及其由此传达的意义、情韵、价值等。与自然语言的能指、所指存在相对固定的关系相比,镜头语言的能指与所指更具自由性、特殊性。个人一旦使用某种镜头语言,不仅与理想中作为抽象规则的语言形态存在差异,也区别于他人的话语使用。因此,长镜头只是镜头形式的概括,并不能说明镜头所呈现的内容。不同导演使用长镜头呈现不同内容,这种质的区分不能被镜头语言的同一名称所抹煞。我们不可能说,张艺谋使用长镜头拍摄的《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与贾樟柯使用长镜头拍摄的《小武》、《站台》、《三峡好人》等,就等同侯孝贤的《悲情城市》、《戏梦人生》、《海上花》。试想,如果真如乌登所说,他所列举的前三个理由岂不是从语言的共性彻底取消了侯孝贤的独特性?不仅侯孝贤没有独特性,任何导演都没有独特性,欧洲艺术电影与美国好莱坞电影也没有区别,因为所使用的镜头语言都能在其他导演及作品中找到。这种论断岂不荒谬? 二、宏观政治与微观政治 虽然对侯孝贤作品作如此政治学分析,乌登也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即便在《悲情城市》这样明确表现“二二八”事件的文本中,侯孝贤也常常因为他的政治矛盾和逃避而受到“统派”和“独派”的双方批评,甚至很少有人能够指出侯孝贤在台湾真实的政治光谱中的位置(第31页)。我们认为,现实中截然对立的“统”“独”双方均指责侯孝贤回避政治,这是由于文本虽然表现了政治事件,却又缺乏确凿的政治立场、态度所致。他既不是“统派”传声筒,也不是“独派”的鼓吹者,这正是侯孝贤遵循艺术本体性的结果:进入文本的政治已不是现实的政治,它不过是一种经由艺术过滤、体现艺术原则的情绪与气质。可以肯定地说,电影艺术以个体形态、日常生活表现出的微观政治,根本有别于宏观的政治立场或态度,存在着混沌的多义性。关于宏观与微观两种政治形态,衣俊卿作了如此区分:“所谓宏观政治是指国家制度的安排、国家权力的运作等宏观的、中心化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而所谓微观政治是指内在于所有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层面的弥散化的、微观化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②如果说政治的核心是权力和控制,那么: (一)微观政治意味着权力和控制从国家权力机器、社会机制更深刻地演进到个体的日常生活。“人是一种政治的动物,人的社会关系首先就表现在它是一种政治关系。这种政治关系就是一种控制和被控制、主宰和被主宰、主人和奴隶这样的关系,这种关系是辩证的。”③但凡在社会/日常生活中存在控制和被控制等权力关系,就是微观政治所在。因此,电影等大众/社会文本在微观政治学研究中越来越重要,不仅侯孝贤电影挟带了复杂的微观政治意义,李安、张艺谋、陈凯歌、贾樟柯等华语电影在这种研究方法中也存在广阔的阐释空间。但客观地说,相对李安研究之于离散批评与后民族主义批评、张艺谋研究之于后殖民批评与东方主义等研究的丰厚程度,侯孝贤及其电影研究仍嫌薄弱。这与侯孝贤及其整个台湾电影研究长期依赖并受限于宏观政治话语及其思路有密切关系,质言之,它尚未进入文本的微观政治学研究。侯孝贤在论述自身创作的“沈从文情结”以及文本中广泛存在的生活现象、中国想象、政治事件及黑帮时,很容易成为“统派”、“独派”等生拉硬扯维护自我利益的注脚,乌登的侯孝贤研究也不例外。最明显的例证是,他所推崇的侯孝贤的世界观、云块剪辑法、自然观等,并没有得到系统的阐释,尽管他已经认识到《戏梦人生》“它起落流动的自在,它始终如一的静止”,是最节制然而也最深刻的哲学表述之一(第235页)。因为如果再深入下去,侯孝贤和他的电影就与中国传统的道家文化及其美学精神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侯孝贤电影的中国性核心就在于接续了对中国传统艺术影响最深的道家文化。这种结论显然不是强调台湾经验、否定中国性的乌登所乐意看到的。相反,他却在《海上花》为什么没有出现“台湾”的问题上,花费了大量的笔墨(该节共一万字左右,其中五千多字论证该问题,其他内容是镜头、布景:灯光等纯粹形式的分析)来解释原本再正常不过的创作现象(而从世界范围看,任何导演都不会自我限定只拍摄一个固定的城市)。在乌登看来,这个问题之所以如此重大,原因在于“对某些人来说,侯似乎已经抛弃了台湾,而钟情于大陆”(第266页)。然而,辩解的结果是:“不过,不可否认这部电影对很多观众来说还是非常中国化的。”于是,作者只能以“这部电影在形式是如此的完整,它的美学外观是如此的引人注目,以致观众很容易忽视这部电影到底在讲什么”(第278页)来回避中国性问题。也就是说,他最后也未能反驳影片“还是非常中国化”,只能以美学形式的显著,从武断揣测观众的主观角度(然而他凭什么认为观众“很容易”忽视影片的故事内容?)草草抛开了难以自圆其说的《海上花》的非中国性。在我看来,这是明显受制于宏观政治、勉为其难地缝合客观/文本与主观/意识形态裂缝的阐释现象。这种无效的研究制约了乌登的侯孝贤电影研究的深度与丰富。 (二)与固态的宏观政治相比,微观政治是一种弥散化的气体状态,它取消了规定性本质的固定特征,更多以变动不居的面貌示人,它尤其置身于电影艺术的另一个场域中,融合在个体行为、事件中,人物的经历、情感、命运成为微观政治的表征,叙事视角、人称、频率也隐含着微观政治的意义,意象、文化逻辑、思想观念等更是微观政治的表达路径。“文本的开放性保证了文本意识形态的多元性和丰富性。文学使意识形态超出了居于主流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束缚,把生活中的各种意识形态都纳入其中,经过文本的熔铸与重构,从而产生新的意识形态。”④在微观而复杂的文本世界中,我们不能因为《童年往事》讲述了来自父亲、母亲及祖母的死亡,就认同乌登所说的,“这是一道遗忘的弧线,日渐淡忘大陆”(第136页)。影片虽然叙述了年长者的死亡,但重点在于懵懂少年的成长记忆与经验;强调的是阿孝对生死的直观感悟,而不是外省人的身份政治。我们也不能说《悲情城市》由于从宽美/本省人的视角叙述“二二八”事件,就是“明显照顾本省人而非大陆新移民的声音失调”(第232页)。事实上,叙述视角的选择,不仅受限于叙述对象,而且与导演追求的叙事主题、叙事效果相关。吴宽美的画外音一方面有利于影片对“二二八”事件的外在观察与真实还原,另一方面,对于文本形成特殊的叙述效果(历史事件的旁观叙述)、美学形式(克制、隐忍)具有十分重要的功能。我们也不能由于《戏梦人生》“既不理想化地描述日据时期,也不严厉地抨击它”,就认为“侯的作品表达了一种矛盾的复杂性,一种混血感,以及一种总体上犹豫得多的身份”(第213页)⑤。当然更不能简单地由于《好男好女》在“大陆审讯”的场景中表现了钟浩东与大陆人之间存在语言障碍,就说“它进一步强化了侯自在《儿子的大玩偶》中使用台湾话以来对国民党统一语言意图的颠覆”(第254-255页)。我们认为,电影文本的微观政治研究远非如此简单。在独立自足的文本世界中,众多符号表征及其意义体系互相影响,程度不一地发挥作用;文本的微观政治意义,反而更需要整体性的考量。如我们长期关注《悲情城市》,却忽视了《好男好女》对“二二八”事件的表现。后者描述了在“白色恐怖”时期钟浩东私下办《光明报》,公开谈及“二二八”事件;他认为,外省与本省人的冲突仅仅是表面现象,地主阶级的剥削、战争导致底层群体的贫困,才是导致事件产生的真正因素。从这一人物的重要性来看,乌登也承认钟没有任何“人性缺陷”,是“政治圣徒”形象,是理想式的英雄人物(第255-256页),那么,这种意见更值得我们认真对待。乌登的论断之所以单薄、武断,就在于他忽视了错综复杂的文本结构及其意义的表征符号,用抽象的宏观政治观念压倒了文本细节的微观政治意义。“统派”与“独派”对侯孝贤的指责,就是用现实的意识形态/宏观政治强行整饬文本意识形态/微观政治。乌登强调侯孝贤电影的台湾经验而否定中国性,与此理相同,不过是以学术研究的方式表明自身的政治立场而已。 (三)与宏观政治难以消除的他者不同,电影艺术的微观政治是内在于生活中的形态,是从独立自足、自成体系的内部中延伸出来的。相对于宏观政治抽象的理性与外在的他者,微观政治一方面能够渗透到生活、艺术等其他领域,作用于个体的微观方式,从生活的内部强调“日用而不知”的普遍形态,从人物的内部强调情感,故而感人至深、影响人于无形之中;另一方面,这种观念是特殊人物在复杂的生活中的合理延伸,在不同观念碰撞与竞争中的自我选择,而非外在意义的强加。换句话说,叙事不仅是人物生命的隐喻(情节是人物性格的形成史),也是意义生产的隐喻(意义在内在的否定辩证中得以完成);微观政治借助电影叙事对人物的人生重构、生命重释传达出来。因此,这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电影中人物与生活、人际关系、社会环境之间的感性关联,以及关注具体人物、特定身份所携带的微观政治意义,否则就很容易陷入以外在宏观的政治观念强行解读文本的误区。如乌登在分析《童年往事》时,认为“陈诚之死象征着1950年代紧张时期的真正结束,也代表了台湾向快速发展和外向型经济的转型。这一历史背景强调侯在青少年时期完全认同台湾”(第136页)。然而,尚未长大成人的阿孝不可能对台湾政治及社会有如此宏观理性的认知,就连他对祖母、父母亲与生活环境也是迷惘懵懂,何以能在表征时间流逝的广播声中“完全认同了台湾”?再如,乌登认为《悲情城市》的林家有黑帮、医生和知识分子,就是揭示了“大中华”概念如何在台湾失落(第186页)。我们认为,侯孝贤以各种不同的职业与身份(尤其是与黑帮关联、在东南亚参战、到大陆做翻译等)组建林家,突出的是它在当时台湾社会的代表性,有意将林文清设定成聋哑的摄影师,而不是吴宽荣那样投身于政治的知识分子,就是强调一个再寻常不过的台湾家庭如何受到“二二八”事件的灭顶之灾,以这一重大而痛苦的历史事件凸显了个体命运的悲欢离合、生离死别。质言之,影片的落脚点是个体生命在政治运动中的沉浮、痛苦与死亡。因此,乌登从林家受伤害、被镇压的历史遭遇,突然跳升到“大中华”这个概念在台湾失落的论断,在微观与宏观、具体人物与抽象概念之间缺乏必要的关联(《悲情城市》本身就没有出现整体性的“大中华”概念,又何谈失落?)。综观侯孝贤的电影,人物身份均缺乏显见的政治性,就是为了抵消影片讲述故事时代及其环境、事件的政治意义,林文清如此,经历了日据时期的李天禄同样如此(如当日本军官要求他加入木偶宣传队时,他直言不讳地问“有什么待遇”。对挣扎在生死之间的普通人来说,宏观政治强调的民族大义、敌我关系过于遥远)。因此,乌登的文本阐释是一种外在于日常生活的理性抽绎,并不是研究具体人物生活处境中支配与被支配等权力关系的微观政治研究。 概言之,乌登的《无人是孤岛》显示出宏观政治对微观政治的强行介入与整合,后现代学术背景下微观政治学的困境就在此。一方面,人们敏感于权力与控制,权力已经扩散到日常生活的微观形态,“个人即政治”成为一种彰显权利与自由的口号;但另一方面,又不断地遭遇到宏观政治粗暴地强行介入与曲解,促使原本复杂的微观形态重新纳入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由此艺术文本与政治文本的属性混淆,政治论断难以获得足够的文本支持,艺术分析也遭遇政治思路的干扰。在我看来,我们应当避免以现实中某种确定的政治观念与原则直接界定电影文本中的微观政治现象。文本的自足空间,使得微观政治意义无比丰富且复杂。而且,但凡在文本中发掘政治内涵,也需要外在/内在、宏观/微观、政治/艺术等多维度的综合考虑。“微观政治哲学在政治现象和政治事务的视野中,充分重视各种边缘的、微观的、多形态的、多元差异的政治权力的地位和作用,形成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政治理解模式。”⑥也就是说,在艺术文本中,微观政治是一种内在的真实意义,形成于具有特殊身份的人物经历否定的辩证与曲折的生活的过程。它不能纠缠于边缘的、微观的具体权力,或者以孤立的片段、个案、细节独立生发出意义,更需要与宏观政治学联系,从微观到宏观的循环往复中产生出来。 三、过度阐释的有效与无效 在文化研究中,过度阐释乃至于误读都已成为文本解读的方式,如乔纳森·卡勒为过度阐释的积极辩护⑦。但是,过度阐释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底线与原则,并非所有的潜在意义都是有效的。何谓“过度”,争论历来激烈。我们认为,阐释是否过度,归根到底取决于阐释出来的文本意义、论述方法。伽达默尔说得好,在文本中发掘意义是可理解的,更重要的是,“作为这种可理解的东西,它本身不会促使人回到他人的主观性中去”⑧。可理解(或者说是有效)的阐释,是以意义的客观性(文本的依据)、说服力(话语逻辑)为前提;纯粹属于他人的主观性意义就是一个不可理解的无效阐释。具体到乌登的这部论著,明显存在从宏观的、外围的政治意义阐释文本,即历史的“后见”。在文本中寻找与某种政治观念相匹配的细节,用后来的社会发展解释文本现象,甚至赋予文本人物、情节、结构的政治意义,很容易出现牵强附会的主观性。比如乌登从《童年往事》的死亡现象归纳出“遗忘的弧线”的意义。“侯之前的电影遵循年纪最小的角色不断发展的意识的弧线。在这里相反:这是一道遗忘的弧线,日渐淡忘大陆。……这条遗忘的弧线也传达出影片的历史感。对侯的家人来说,他们只在乎私人的、家庭的历史事件”(第135页)。毫无疑问,《童年往事》“只在乎”私人的、家庭的事件,但这与人物“非政治化”的身份设置相关,取决于影片创作的目的(落脚点在于经历亲人相继离世,在生死之间的个体成长与感悟,而不是描述宏观政治生活及其政治意识的产生)。这种“只在乎”个体、家庭(融入在地生活及其经验)并不处于非此即彼的二元选择,因此不会构成反中国性的政治意义。如此,乌登所谓的“日渐淡忘大陆”自然也就无从谈起。再如对1965年的“陈诚之死”的过度阐释。乌登认为,它“象征着1950年代紧张时期的真正结束。陈诚葬礼那天,他和他的朋友们甚至在打台球,表明无惧失礼,而且满不在乎地和气愤于他们行为的老兵们打架。慢慢地,不知不觉地,大陆渐行渐远,而台湾经验悄悄地取而代之”(第136页)。在他看来,陈诚葬礼的意义不仅仅是借助广播的声音传达确凿的时间及社会背景,而且代表台湾社会紧张时期的真正结束、经济腾飞时代的到来,这显然是从历史后来者的视角强行阐释的结果(身处时代之中的普通人对此难以察觉,而且,这种信息在后面剧情中也没有任何表现)。他进而认为,陈诚葬礼之后的黄金时代,就是第二代外省人隔断大陆关联的表征,他们“无惧失礼”的潜在意义是“大陆渐行渐远”、“台湾经验取而代之”。这种过度阐释的“不可理解”,不只是因为它是一种脱离了文本语境的历史“后见之明”,而且缺乏必要的论述逻辑与说服力。作为对立面,“一群老兵”气愤于他们的行为,这是否从数量、群体、情节功能上,表明与大陆的血脉关联已成为台湾社会的基本记忆与经验?这个一旦“失礼”即起冲突的细节,恰恰表征了台湾政治及其社会的复杂性,即便是第一代外省人相继死亡,关于大陆的经验及想象已经顽固地沉淀在台湾社会的集体记忆中,否则又怎会打架?乌登由此阐发的台湾经验对大陆记忆的取而代之,只是纯粹的主观性意义,难以令人信服。 伽达默尔特别强调阐释文本的一致性,这也成为构成有效性的要求。他明确地说:“诠释学历来的任务就是,把没有出现的或被干扰的一致性建立起来。”⑨这是因为艺术文本的思想观念、政治立场、美学形式在具体符号表征(叙述活动)中显示出来,这种文本的一致性总是缺席(没有出现)的在场(仍能积极发挥作用)。“干扰”源自于人物表象活动、情感宣泄、事件演绎等具体符号“自然流露”的感性原则。排除干扰,就是从这些感性多义的具体符号(完成的文本状态)还原到“一致性”(始初的创作心理及其主观意图)。我们不妨再回到乌登对《童年往事》死亡现象的过度阐释。它不仅缺乏文本相继的细节依据,甚至与显在意义相违背。在结尾时,作为导演也是局中人的画外旁白,特别指出“直到今天常常想起”陪伴祖母寻找“大陆”的那个下午。基于个体记忆、建构文本的一致性呼之欲出,然而仍然被乌登主观地阐释为“遗忘大陆”的政治意义。他对《海上花》的阐释更为随意。面对文本如此显见的中国性,他以上海与台湾均是港口城市、“台湾是一个隐喻”等为由,勉为其难地论证台湾仍然在影片中存在(如妓院经验、在台湾搭景等),最后的结论是:“与其说它证明了传统中国文化,不如说证明了一个总是处于中国阴影之下的岛屿,却创造了中国的另一个版本,一个较难预测却有趣得多的版本。”(第300-301页)在这个根本没有台湾形象的电影文本中,又如何证明台湾总是处于“中国阴影”之下?在侯孝贤受到韩子云、张爱玲、阿城等大陆三代小说家启发帮助中,又怎能说创造了不同于传统中国文化、而且很难预测更有趣的“另一个版本”?这种阐释不止是缺乏文本的一致性,而且是完全不顾文本一致性的主观臆测了。 过度阐释的有效性还要求:所阐发的意义具有清理、修正“前有”、“前见”及其“前把握”的功能。“解释者并非从自身业已具有的前意见出发走向‘文本’,而是检查本身具有的前意见是否合法,亦即检验它的来源和作用。”⑩如果仅仅是重复业已具有的“前意见”,那么这种阐释就没有什么意义。正是由于察觉到文本的“前见”存在某种缺陷,阐释者重新寻找意义表征,发掘文本的空白、连缀文本片段的潜意义以及缺席的一致性,这种新意义修正了“前见”,从而构成了有效的阐释活动。如上所述,乌登在《童年往事》、《悲情城市》、《戏梦人生》、《好男好女》中都以宏观的政治观点、历史的“后见”阐释人物的日常生活,用边缘的“台湾经验”进行非/反中国性。这种后现代思潮背景下的反国族态度,早已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主流话语,因此,乌登对侯孝贤的文本作出这般的政治阐释,不是纠正某种“前见”、“前有”(“台湾经验”的非/反中国性),反而进一步加强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前见”。这种过度阐释也就成了一种无效的重复。 乌登的论著充满了矛盾:既强调历史、政治、文化的外围研究,也突出表现出技术主义的研究倾向(如根据长镜头、镜头时数、场面调度等对侯孝贤电影艺术价值的判断);既极力突出“台湾经验”的非/反中国性,否认中国文化对侯孝贤的影响,也不得不面对电影文本俯拾皆是的海峡两岸历史与现实的关联;既想单独凸显电影文本的政治特征,但又察觉到侯孝贤的政治、历史、人性等主题,背后存在一个更深刻的世界观。这些矛盾论述源于作者自身的政治倾向:如此不合情理地强调“台湾经验”,就是为了否定中国性。然而,他把所谓“台湾经验”笼统地界定为:“在台湾,流动的共同的经验压倒所有固定的经验,这不是理性思维的产物,而是台湾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事实”(第24页)。似乎只要表现了台湾日常生活的电影就具有“台湾经验”,这又缺乏政治意义上的实质内容,使得论著的政治意图落在空处。事实上,任何研究侯孝贤的学者(无论境内外)都不会否认台湾对于侯孝贤创作及文本的重要性,但并不是有了台湾的生活经验就必然非/反中国性。试想,在当下华语电影导演中,如果连侯孝贤这样一以贯之、且具有如此鲜明的道家文化理想及其美学特征,都被研究者认为不具有中国性,那么还有谁具备呢? 注释: ①参见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96页。 ②⑥衣俊卿:《现代性的维度》,黑龙江大学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88页,第90页。 ③《邓晓芒讲黑格尔》,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0页。 ④杨建刚:《文本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对话中的一个关键问题》,载《文艺研究》2010年第1期。 ⑤乌登在分析《戏梦人生》对日据时期的态度时明显存在矛盾,他一方面认为侯孝贤对日据时期比王童的《无言的山丘》要复杂得多,提到中国台湾人面对日本人的统治现实所做的顺从和妥协,并有历史资料,表明“侯的版本更接近事实”(第213页),但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侯孝贤追求“自然”的道家美学对这个敏感内容的影响,“不带任何惯常判断和过分期待地看世界,甚至是历史世界”(第214页)。 ⑦乔纳森·卡勒:《为“过度诠释”一辩》,艾柯等著《诠释与过度诠释》,王字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⑧⑨⑩伽达默尔:《论理解的循环》,《诠释学: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71页,第72页,第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