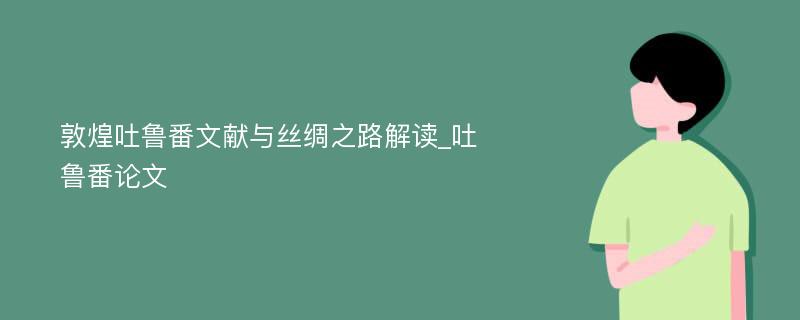
《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读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吐鲁番论文,敦煌论文,丝绸之路论文,文书论文,读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期以来,结合中外史料探讨丝绸之路与文化交流的力作,实在并不多见。姜伯勤先生的《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将这项课题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该书通过对隋唐时期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文化交流进行新的构架和研究,至少在以下五个方面作出了贡献:
(1)与日本学者冈崎敬等相呼应,姜先生阐发了“白银之路”、“香药之路”、“法宝之路”等概念。他据吐鲁番文书和新疆地区发现的一批萨珊波斯银币,认为高昌(西州)曾是银钱流通区;由于中原地区不以银币为通货,这些银钱实为波斯银币、粟特银币和克什米尔等地的西域银币;在高昌,一般都以波斯银币为标准货币。这说明,从中国通往波斯的丝绸之路,也即从波斯通往中国的一条“白银之路”(第30页)。他还详考了文书中有关香药以及香药文化之记述,认定“佛教传入之路,也是一条(由印度到中国的)香药传入之路”(第131页)。
(2)深入探讨了吐鲁番地区国际标准通货和使用货币之演变问题。他认为,北周至唐初(约557—630年),拜占廷金币实际上成为高昌的国际标准通货(第10—13页);4—7世纪,从波斯以东到中国河西走廊,流行银通货。唐初至开元年间(约630—741年),曲氏高昌以波斯银币为标准货币(第30页);但自武周以后,银钱逐渐不见于文书记载,这说明铜钱和帛一起成为敦煌、吐鲁番地区的货币形式(第202页)。在整个7世纪,西州直至西边的安西、疏勒一带,在货币流通方面,钱帛兼行;而钱货方面,又是银钱与铜钱兼行(第199页)。他还分析了敦煌、吐鲁番地区受波斯及粟特影响而流通银币之原因(第201页)。到唐开元时期,银钱表面上从流通中消失(第34页)。他还研究了7—8世纪之交敦煌、吐鲁番的铜钱使用及外流问题,得出了该时期粟特地区铜币流通兴盛的原因之一是中国铜钱外流到该地区的结论(第202页)。
(3)挖掘出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有关“波斯”和“波斯军”的记载,拓展了中国与波斯关系史的研究领域,并提出了“敦煌与波斯”这样一个饶有趣旨的课题。关于萨珊朝灭亡(651年)后中国与波斯人的关系,学者一直注意不够。姜先生从80年代中期开始注意此课题,并探微入渐,成果斐然。他对此项课题的研究,至今仍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他结合中外考古资料对“波斯锦”和“胡锦”的研究,也颇具心得和特色。他认为,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唐代联珠猪头纹锦式样应与萨珊波斯人的琐罗亚斯特教(袄教)的观念有关(第75页)。关于敦煌莫高窟各种联珠纹图样所受萨珊风格之影响,前人著述不少。姜先生结合国外考古和研究成果,进一步充实了这项研究成果的内容(第77—82、206—226页)。他认为,敦煌文献中的“胡锦”、“番锦”,既有境外输入的,也有汉地生产的;粟特人在胡锦生产技术输入汉地的过程中,起了中介作用。
(4)探讨了敦煌、吐鲁番的粟特人之经济活动、社会生活和宗教信仰。日本学者池田温曾作《8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1965年)、《吐鲁番汉文文书所见的外族》(1978年),山田信夫作《突厥族与粟特商人》(1971年),护雅夫作《丝绸之路与粟特人》(1979年);中国学者夏鼐、唐长孺、马雍、朱雷等也分别针对新疆出土的古代丝织品和钱币、唐西州诸乡户籍帐、“萨藩”问题及曲氏高昌的“称价钱”做过专题研究。姜先生在这些中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高昌粟特人及其活动情况,认定高昌也存在粟特人聚落;这些粟特人分为入籍和未入籍两种,他们各自有不同的义务和权利;他们都对东西贸易和文化交流起了巨大的中介作用,对敦煌、吐鲁番和粟特地区货币的演进也起了很大作用。他们既促使敦煌、吐鲁番地区采用银本位制,又促使粟特地区采用铜钱。
(5)在史料利用和研究方法上有较大突破。姜先生对日本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非常熟悉,并充分吸收了日本学者羽田亨、池田温、白鸟库吉、护雅夫、伊藤义教等人的研究成果。他还使用了国内学者极少利用的塔吉克斯坦《穆格山粟特文书》,前苏联的考古成果和钱币资料,以及北高加索阿兰(Alan,即奄蔡)地区所出汉文文书,并且利用了部分欧美学者的研究成果。在研究中,他注重以出土文书与其他考古发现相参证,以地下出土文物与史籍相参证,力图把敦、吐地区的商业贸易和文化汇聚,置于整个东西方社会政治发展和历史背景中去考察,使敦煌、吐鲁番一时、一地、一事的研究具有了国际意义。这对于专治中国史的中国学者来说,尤为难能可贵。
姜先生的研究,为学者们提出了许多尚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笔者提出以下问题讨论:
首先,北周至唐初,高昌采用银钱本位的原因究竟有哪些?拜占廷金币是否如姜先生所称已成为高昌的国际标准通货?显然,仅据“金钱”成为该时期高昌虚构的随葬物,以及高昌发现了几枚拜占廷金币,尚不足以说明拜占廷金币已成为该时期高昌的“国际标准通货”。
其次是铜钱取代银钱之原因。我们应当充分重视以下两个因素:一是阿拉伯人在8世纪初最终征服河中和粟特地区后,这些地区的银币铸造权收归阿拉伯倭马亚朝廷和阿拔斯朝廷,这些地区仅有铜币铸造权。到公元822年中亚塔赫尔王朝(822—873年)建立,上述地区又恢复了银币铸造权。不过,这些地区直到10世纪末均没有停止银本位制。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记载,回历211—212年(公元826—827年),河中、粟特、呼罗珊各地税收和买卖均以银币(迪尔汗)为本位计算;古达玛的《税册》也证实了这一点[①a]。二是,据美国学者费叶(R.N.Frye)研究,中亚萨曼王朝(874—999年)时期,在东突厥斯坦没人愿用银币做交易,人们与来自萨曼王朝的商人做生意主要是物物交易;而在伏尔加河和东欧地区,萨曼银币既作为货币来使用,又以其银的含量而作为商品出售[②a]。考古材料也支持费叶等的结论。在碎叶故址(阿克·贝欣)未发现8世纪中叶后的钱币;在伏尔加河流域、波兰和斯堪的那维亚则发现了大批萨曼王朝银币[③a]。看来,高昌(西州)废用银币还有本地的其它因素,这尚待学者们做进一步研究。至少,高昌银钱被中亚各族拒绝使用,是高昌银钱渐废的原因之一。至于敦煌、吐鲁番所使用的银钱是否在本地铸造,有多少在本地铸造,银钱成色是否有降低过程,也亟待文献和考古发现来解惑。只有铸银币地点及银币成色问题真正得到解决,这两地银钱兴废的原因才能探讨清楚。
必须指出的是,从武周到天宝年间,敦煌、吐鲁番地区仍广泛使用练绢作为一般等价物;该时期记载以练绢购买马、骆驼、牛、奴婢等的文书在14件以上。据赵丰研究,在这个时期铜钱贬值率达43%;铜币在当时称不上是硬通货,只能用于小买卖;在开元、天宝年间(713—756年),绢练在敦煌和吐鲁番地区充当主要货币[④a]。这在《册府元龟》和《唐会要》中都有明确记载。显然,敦、吐地区钱币的流通变化,与唐朝政府和中国内地的关系要更紧密些。从穆斯林著述看,唐朝铜钱并未大量外流到中亚,中亚考古材料也未见唐铜钱之大量发现。
第三,关于粟特人之研究,尚有以下课题有待深入研究:敦、吐地区的粟特人与灵州、夏州南境的六胡州之粟特人比较研究(如两地粟特人定居原因之异同、他们对商业贸易作用之差异、权利和义务之区别、汉化程度之大小,等等),定居(入籍)粟特人与当地汉族居民的权利和义务之差异,中国内地是否存在粟特人聚落,粟特人分布点与丝绸之路走向的关系,等等。这些子课题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透过粟特人在中国活动之表象,揭示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担当者”的粟特人在隋唐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以及粟特人的活动对中国和西域地区历史发展的影响。
显然,在隋唐丝绸之路上,充当文化交流使者角色的不仅有粟特人,还有波斯人、阿拉伯人、突厥人等。后三者在敦煌、吐鲁番如何活动,他们与粟特人有什么不同,他们的作用如何,都有待学者们做进一步研究。
第四,必须充分利用中国西部地区出土的大批粟特文书。这些文书,有商业文书、佛经、摩尼教和基督教(景教)文书。利用这批粟特语文书,必可使有关课题研究深入一大步,揭示出敦煌各种宗教所包含的伊兰因素。诚如姜先生所指出的,要研究敦煌宗教中的伊兰(中古伊朗)因素,“不仅要研究祆教、摩尼教、景教,更要研究敦煌大乘佛教中,如无量光明阿弥陀佛、西方乐土、弥勒和观世音崇拜,如何为伊兰思想所浸透。”[⑤a]
第五,必须注意的是,“粟特”(地区)、“粟特人”概念,在中古时期的汉籍及穆斯林史籍记述中是有差异的。中国史家一般均认定唐代中亚昭武九姓为粟特人,昭武九姓存在区域(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为粟特地。《大唐西域记》卷一记云:“自素叶水城至羯霜那国(即史国,今撒马尔罕以南之萨赫里萨布兹——引注),地名窣利(即粟特——引注),人亦谓焉。文字语言,即随称矣。”《新唐书·康国传》云:“羯霜那,居独莫水南,……南四百里吐火罗也。有铁门山,……为关以限二国”。由此可见,唐代中国人眼中的粟特,其地域从碎叶直至史国南界的铁门关,布哈拉地区(安国)并不包括在其内。而在中古穆斯林舆地文献中,“粟特”(地)的概念要狭窄得多。
据伊斯塔赫里(IstakhrTī,10世纪上半叶人)记述,粟特地仅包括布哈拉东部之地,即从代布西亚(位于布哈拉以东22法尔萨赫,约合137公里;此地东至撒马尔罕17法尔萨赫,约合106公里[①b])到撒马尔罕之地;不过,布哈拉(安国)、渴石(史国)和纳塞夫(即《新唐书·西域传》之那色波,亦曰小史,今布哈拉东南之卡尔希)也可包括进粟特[②b]。雅古比(Ya′Kübī,卒于公元897年,著有《诸国志》)则把渴石、纳塞夫、撒马尔罕地区称作粟特,但布哈拉不包括在粟特之内;他时而把撒马尔罕作为粟特首府,时而又把渴石作为粟特首府[③b]。马合木·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约成书于11世纪70年代)则认为,粟特位于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之间[④b]。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在《道里邦国志》(定稿于约公元885年)中,则把粟特、撒马尔罕、拔汗那(费尔干纳)、突厥诸城镇、渴石、纳塞夫都视作粟特地,而把布哈拉、东曹国和石国都排除在外。看来,在中亚穆斯林眼中,撒马尔罕以东诸地(如石国、东曹国)往往不包括在粟特地区之内。这种概念上的不同,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来华粟特人不同群体(如安、康、史与石、曹姓)之间的差异。
姜先生在书中第44页,特意加注说明孙继民最新研究成果(1990年1月)对自己观点的修正,严谨治学之风令人叹服。笔者冒昧提出,书中第55页所言中亚诸王朝兴废年代有误。呼罗珊和河中最早建立的波斯人(伊朗语族人)王朝——塔赫尔王朝建于公元822年,而非820年(也有学者认为该王朝建于公元821年);萨曼王朝存在时间为874—999年,而非900—990年(书中第56、271页又称,萨曼王朝灭亡于1002年之前三年,即999年)。
《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姜伯勤著。
18万字。文物出版社1994年2月版。
注释:
①a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古达玛:《税册及其编写》,中译本,宋岘译,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38—42、258—259页。
②a 费叶:《伊斯兰伊朗和中亚》第6章,1979年英文本。R.N.Fryeed.,Islamic Iran and Central Asia,Chap.XI.London,1979.
③a 《剑桥伊朗史》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第4卷,伦敦,1975年版。
④a 赵丰:《唐代丝绸与丝绸之路》,三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8—208页。
⑤a 《敦煌与波斯》,载《敦煌研究》1990年第3期。
①b 里程数根据《道里邦国志》,参见前引中译本。
②b 《阿拉伯舆地丛书》Bibl.Geog.Arab.,第1卷,荷兰莱顿,1870年,第314—316页。
③b 同上丛书,第7卷,1892年,第293、299页。
④b 《突厥语大词典》第1卷。引自《伊斯兰百科全书》英文本,第1版,第7卷“Soghd.”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