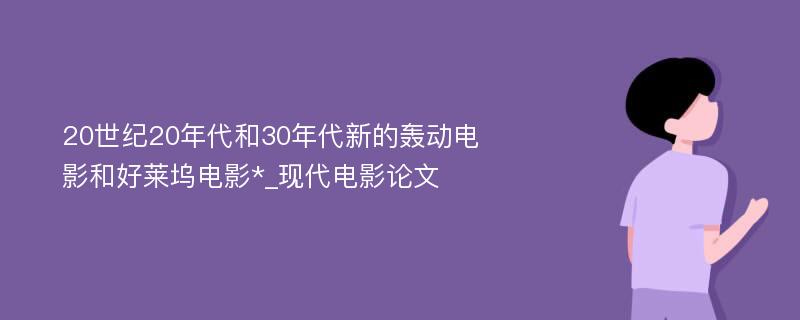
新感觉派和二三十年代好莱坞电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二三论文,好莱坞电影论文,新感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曾经有论者断言:“1922年而后的小说史,即《尤里西斯》问世后的小说史,在很大程度上是电影化的想象在小说家头脑里发展的历史,是小说家常常怀着既恨又爱的心情努力掌握20世纪的‘最生动的艺术’的历史”〔1〕。即使这个概括有些绝对,但随着电影在20 世纪成为最流行的艺术,它对现代小说的影响却是低估不了的。20世纪的现代小说大师——卡夫卡、乔伊斯、吴尔芙、福克纳、海明威、帕索斯和法国新小说家们都在自己的创作中,为现代小说艺术如何能够既吸收进电影的技巧而又不牺牲它自己的独特力量的探索上,留下了各自的经验和教训。可以说,在今天若不了解电影艺术的种种技巧实验和追求,也很难理解20世纪现代小说发展的种种技巧实验和追求。
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上海文坛以其“簇新的小说的形式”而“盛极一时”,造成“一时的风尚”的新感觉派对“各种新鲜的手法”的尝试,有研究者追根溯源到日本的新感觉派,把刘呐鸥翻译的日本短篇小说选《色情文化》称为“中国新感觉派文学的始祖”〔2〕, 也有论者进一步顺藤摸瓜到日本新感觉派的源头——保尔·穆杭(Paul Morand),更有印象主义、未来主义、表现主义和立体主义混合物的多种说法。尽管以前也有人指出过新感觉派对电影技巧的借鉴,但一般都是点到为止,没有对这一现象展开详细的研究。事实上,电影对中国新感觉派的影响不仅仅限于个别的手段和技巧,而且涉及到题材内容以及现代小说的整体范式带有根本性变化的某些特征,显示了20世纪现代小说艺术实验和发展的一种趋向。它不仅是这一流派的一个重要现象,甚至是在现代小说发展中带有标识性的一个重要的文体现象。
女体和叙述者作为“看”的承担者
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新感觉派的全盛期也正是电影“在上海市民的娱乐生活中占了最高的位置”〔3〕时期。 根据《上海研究资料续集》有关上海电影院的发展的记载:“一九二八——三二年间,电影院的生长,有非常可惊的速度。”〔4〕因此, 这一时期被标识为“膨胀期”。1931年3月16 日《文艺新闻》创刊号就曾以大幅标题报道:“都市化与近代化的上海人之电影热,文章分析说,“上海在外国人的经营下,一切都倾近于都市化与近代化一般的社会人士,除跑狗、赌博、嫖妓等不正当游冶外,极少娱乐便利,于是促成了电影爱好之速度的发展。”这股电影热使上海电影院到30年代中期已成为“每日百万人消纳之所”〔5〕!电影的魔力和电影在上海市民生活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根据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的描述,“中国的电影事业不是从自己摄制影片开始,而是从放映外国影片开始的。”〔6 〕这首先因为电影放映事业相当一段时间操纵在外国人手中,从1908年西班牙商人雷玛斯(A.Ramos)在上海正式修建起第一座电影院虹口大戏院, 到1925年英美烟草公司垄断中国电影市场,上海第一轮影院几乎全部操纵在外国商人手中,甚至直到1932年后,经过“一二八”战火的毁灭,上海剩下的影院仍大多数是外国商人经营的,这些影院都拒绝放映中国影片,专门放映外国片。其次,中国电影制造业也无力竞争,与外国影片相抗衡。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在电影工业的世界竞争中赢得了垄断的地位,它在制片业和放映业所投的资金超过世界各国投资的总和,几乎在所有国家里至少垄断了半数的上映节目,在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英国,美国影片所占的比例甚至达到百分之九十〔7〕。 中国也不例外,美国片“几乎独占了当时和以后中国的全部银幕”〔8〕。 由此不难想象美国电影文化对当时上海市民生活以及对二三十年代上海特殊的文化环境的形成会起到多么巨大的影响作用。
其时新兴的好莱坞,以大企业的方式加以开拓的金矿是“性感”和百万富翁的豪华景象,除极少数外(如卓别林的作品),“大部分影片的内容,多是大同小异,千篇一律的逃不出恋爱与情感作为故事的主题”,“极尽罗曼司、妖媚与美丽”之能事〔9〕。30 年代美国向中国大量倾销的正是这类典型的好莱坞传统片,在相当一个时期里“握着我国电影企业最高的权威”〔10〕,这与30年代逐步发展起来的左翼电影形成尖锐的对立,就连《良友》画报这样的通俗杂志也注意到其间的差异,而刊载短文《电影的两面:麻醉的与暴露的》说,美国片把“一切麻醉的、享乐的表现方法,尽量地搬弄出来,铺张华丽,推陈出新,极声色之娱”;而中国片却“大都趋向于摄制描写人间流离颠沛,生活痛苦的影片”。〔11〕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这个对立终因对茅盾《春蚕》改编成电影的评价问题,引发起著名的持续时间达两三年之久的“硬性电影”与“软性电影”之争,而“软性电影”论者的主要代表人物即新感觉派的中坚分子刘呐鸥、穆时英,以及和刘呐鸥共同主编《现代电影》,并在《无轨列车》上发表过《爱情的折扣》、《憧憬时代》等短篇小说的黄嘉谟。
在这次论争中双方都发表了比较系统的理论文章,涉及到文艺的本质、功能以及题材和形式等一系列的重要论题,这些无关本题略而不论,但从“软性电影”论者所持的观点来看,他们对美国“极声色之娱”的影片是持接受态度的。“硬性电影”论者认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欧美帝国主义的影片以文化侵略者的姿态在市场上出现,起的是麻醉、欺骗、说教、诱惑的作用”,除“色情的浪费的表演之外,什么都没有”。〔12〕而以“美的照观态度”,主张“寻找纯粹的电影事件”〔13〕的“软性电影”论者恰恰相反,认为“电影是给眼睛吃的冰激淋,是给心灵坐的沙发椅”〔14〕,“现代观众已经都是较坦白的人,他们一切都讲实益,不喜欢接受伪善的说教。他们刚从人生的责任的重负里解放出来,想在影戏院里找寻他们片刻的享受。”〔15〕而美国片正可以叫一般的观众享受短时间的声色之娱。可见,争论双方虽然对美国影片的性质达成了共识:“声色之娱”,但对此所持的态度却根本不同。
好莱坞传统片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把女人形象通过电影的特殊技巧,特写的分解、不断变换的视点、俯仰的角度及风格化的模式造成一个完美无缺的产品,使女体本身成为影片的内容和表现的对象,成为影片被看性的内涵和色情的奇观。好莱坞风格的魅力正是来自造成这种视觉快感的种种娴熟技巧和令人心满意足的控制。这也无怪“硬性电影”论者认为这类的电影不过是“拿女人当作上海人口中的‘模特儿’来吸引观众罢了。自然观众们简单说一句,也只是看‘模特’——女人——而不是看电影”。〔16〕《无轨列车》从第四期至第六期曾连载过《影戏〔17〕漫想》一篇长文,电影让作者最先想到和谈到的问题就是“电影和女性美”。文章说:“银幕是女性美的发现者,是女性美的解剖台。”甚至认为“全世界的女性是应该感谢影戏的恩惠的,因为影戏使她们以前埋没着的美——肉体美,精神美,静止美,运动美——在全世界的人们的面前伸展。”好莱坞电影对女体的发现,以及它对女体所造成的一种观赏及快感的价值和魔力使展示女体美至少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上海成为一种文化时尚和潮流的重要的刺激条件之一。
新感觉派的成员在当时可以说都是影迷,是都市娱乐活动的积极参与者,穆时英曾写过一篇短文《我的生活》描述自己“公式化了的大学生的生活”说:“星期六便到上海来看朋友,那是男朋友,看了男朋友,便去找个女朋友偷偷地去看电影,吃饭,跳舞。”〔18〕徐霞村在一致戴望舒函中谈自己“晚上的时间多半是消磨在电影院,戏院,和胡同里面”。〔19〕施蛰存回忆他和刘呐鸥、戴望舒的一段生活时也曾谈到,他们每天晚饭后就“到北四川路一带看电影,或跳舞。一般总是先看七点钟一场的电影,看过电影,再进舞场,玩到半夜才回家。”〔20〕刘呐鸥更热心于电影艺术的研究,施蛰存曾在《文艺风景·编辑室偶记》中介绍,刘呐鸥“平常看电影的时候,每一个影片他必须看两次,第一次是注意着全片的故事及演员的表情,第二次却注意于每一个镜头的摄影艺术,这时候他是完全不留心银幕上故事的进行的。”〔21〕根据1933年11月1日《矛盾月刊》2卷3期上发表的“矛盾丛辑预告”, 刘呐鸥曾准备写过一本《刘呐鸥电影文论集》,也许这本书未能面世,但至少可以证明,那时刘呐鸥对电影的技巧已有相当的心得。这从他发表的一系列有关电影艺术的文章来看,也可证明这一点。
中国的新感觉派作为好莱坞的影迷和“软性电影”的倡导者,既是从好莱坞电影文化所造成的时尚中脱颖而出的,又是这股潮流中的一朵浪花。“趋重”对女体的新感觉也是他们创作中的显著特征之一。尤其是穆时英的小说,他的《Craven“A”》、《黑牡丹》、 《白金的女体塑像》、《墨绿衫的小姐》、《红色的女猎神》等基本上是以描写女体,或者说是女性形象的性魅力为题旨的。另外如《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某夫人》、《骆驼·尼采主义者与女人》、《五月》、 《PIERROT》等则进一步把对女体的观赏和叙事相结合,女体成为并列主题,或是重要的描写对象之一。《Craven“A”》开篇即以差不多整整4页的篇幅描写女主人公Craven“A”的肖像和体态,以对丰腴的, 明媚而神秘的自然风光的恣意描摹暗示着女体的形貌,蕴藏着对女体流动而精细的感觉。著名的《白金的女体塑像》更赋予女体以美的力量,让“反映着金属的光”,“流线感的”白金的女体如闪光的太阳,使过着鳏夫的生活,生命已机械化了的医师获得了对生命的感觉和充满生命感的世俗生活。其他的新感觉派的成员,如“追随了穆时英而来”,“属于新感觉主义”的黑婴的创作竟被当时的批评家如同批评美国片一样,说成是“除了看到一副美丽的表皮外,至于内实,大概是很空虚的”!〔22〕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其中对女性的描摹也成为他“都市风景线”里的重要一景。如果进一步把穆时英在小说里对女性的描摹同他在一些影评文章中对好莱坞女明星魅力的阐述对比一下,可以更确凿地找到穆时英接受美国电影影响的证据。
穆时英曾写过一篇系列随感式文章《电影的散步》,从1935年7 月17日至28日在上海《晨报》上连载了8次之多, 其中就有两篇文章《性感与神秘主义》、《魅力解剖学》专门讨论好莱坞女明星的魅力问题。他写到:“好莱坞王国里那些银色的维纳斯们有一种共同的,愉快的东西,这就是在她们的身上被强调了的,特征化了的女性魅力。就是这魅力使她们成为全世界男子的憧憬,成为危险的存在。”〔23〕他还分析说:“女星们的魅力都是属于性的”,“就是一种个性美和性感的化合物”〔24〕。穆时英对那时期当红的女明星们熟悉得已达到如数家珍的程度。他把她们分成两类,第一类以嘉宝(Greta Garbo)、 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朗白(Carole Lombard)、克劳福(Joan Crawford)为代表,其特点是“永远是冷静的,她不会向你说那些肉麻的话,她不会莫名其妙地向你笑,甚至于连看也不看你一眼。可是你却不能离开她。你可以从她的体态,从她的声音里边感觉得在她内部燃烧着的热情”;〔25〕另一类以梅惠丝(Mae West)、琴哈罗(Jean Harlow)、克莱拉宝(Cl ra Bow)、罗比范丽(Lupe Velez)为代表, “这一类的女子是开门见山的女子,一开头,就把一切都拿了出来,把全部女子的秘密,女子的热情都送给了你。她们是一只旅行箱,你高兴打开来就打开来,你可以拿到一切你所需要的东西。第一次你觉得非常满足,可是满足了以后,你就把她们忘了”。〔26〕穆时英把前者的特征概括为“隐秘地、禁欲地”;后者“赤裸裸地、放纵地”,并认为“她们是代表着最现代的女性的魅力的两种型的”。〔27〕穆时英笔下的某些女性也正是按照这两类模式塑造出来的。如《Craven“A ”》的女主角余慧娴就属于后一种模式,被男人比作“一个短期旅行的佳地”,这与“一只旅行箱”比喻的暗示毫无二致,其性格命运也雷同。《白金的女体塑像》中的女客属于前一类,她始终“淡漠地、不动声色”,“没有感觉似地”在医师面前做了一个“没有羞惭,没有道德观念,也没有人类的欲望似的,无机的人体塑像”,可却在医师的内心激起了“像整个宇宙崩溃下来似地压到身上”的震撼。
更有意思的是,穆时英不仅在小说里描述他的女主人公如何模仿电影女明星的表情和做派,文艺家们如何在沙龙里谈论嘉宝的沙嗓子,大众崇拜和弗洛依德主义,甚至他对自己小说女主人公肖像的描绘也模仿好莱坞的女明星。他曾把好莱坞女星们的特写抽象化,得出一个“神秘主义的维纳斯造像”:
5×3型的脸。羽样的长睫毛下像半夜里在清澈的池塘里开放的睡莲似的半闭的大眼眸子是永远织着看朦胧的五月的梦的!而且永远望着辽远的地方在等待着什么似的。空虚的、为了欲而消瘦的腮颊。嘴唇微微地张开着,一张松弛的,饥渴的嘴。〔28〕我们再来对照一下穆时英对自己的小说女主人公肖像的描绘:
一朵墨绿色的罂粟花似地,羽样的长睫毛下柔弱得载不住自己的歌声里面的轻愁似地,透明的眼皮闭着,遮住了半只天鹅绒似的黑眼珠子…
——《墨绿衫的小姐》
她绘着嘉宝型的眉,有着天鹅绒那么温柔的黑眼珠子,和红腻的嘴唇,穿了白绸的衬衫,嫩黄的裙。
——《骆驼、尼采主义者与女人》
画面上没有眉毛,没有嘴,没有耳朵,只有一对半闭的大眼睛,像半夜里在清澈的池塘里开放的睡莲似的…
——《五月》
仅举几例不难证明,穆时英是以好莱坞那些维纳斯们来设计他的女主人公形象的,甚至可以想象,也许年轻的穆时英的某种创作冲动和激情也同样来自这些“银色的维纳斯”——用文字来表达银幕上的维纳斯的女性魅力所带给他的“憧憬”和震撼。无独有偶,刘呐鸥也曾以电影女明星来概括最新型、最摩登的现代女性的特征。〔29〕从感觉上说,新感觉派的很多小说尽管缺乏电影情节的完整性,但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一些电影片断,沈从文就曾说过穆时英的某些作品是“直从电影故事取材”〔30〕,特别像刘呐鸥的《赤道下》描写蛮荒部落的风光和土著人的习俗以及发生在其中的一对都市男女和未开化的兄妹之间,一段带有原始性的性爱故事,非常吻合好莱坞诸如《蛮荒双艳》、《蛮荒天堂》之类表现文明人与野蛮人之间的对立和沟通的路数以及展示奇风异俗的兴趣。
也许这样的假设过于大胆,但二三十年代的欧美电影的确深刻地改造了人们,包括作家在内的思想观念、审美情趣、观察事物的方式和接触外部世界的习惯等等方面。过去一向为我国传统服装所遮掩,也为传统的审美标准所不容的女性肉体的性感特征,随着对好莱坞女星们风格化的形体的接受和其观赏价值的发现,而成为“现代女性”、“近代都会的产物”的标志,也成为穆时英、刘呐鸥等新感觉派所捕捉到的“战栗和肉的沉醉”的美的象征,也即刘呐鸥所说的“内容的近代主义”。所以他们笔下的女性一反中国传统的女性形象而更西化,或者说好莱坞化。“弱不禁风”被健康和“肌肉的弹力”,“杨柳细腰”被“胸前和腰边处处丰腻的曲线”,“温柔含蓄”被大胆和挑衅,”樱桃小口”被“若离若合的丰腻的嘴唇”所取代。
美国女权主义者劳拉·穆尔维曾结合弗洛依德和女权主义观点分析好莱坞传统电影是怎样结构影片形式,男性视觉快感如何在电影中占支配地位的。她认为,好莱坞传统片所构成的观看方式和看的快感的方式给予影片以特有的结构方式,使被展示的女人在两个层次上起作用:作为银幕故事中人物的色情对象和作为观众厅内的观众的色情对象,从而使一种主动与被动的异性分工控制了叙事的结构,即把女人置于被看的位置,男人做了看的承担者。〔31〕这种结构影片的形式也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穆时英、刘呐鸥一些小说的潜层的叙事模式。从小说的表层故事看,穆时英、刘呐鸥笔下的那些具有欧风美雨特征的女性一改为男人所玩弄的地位而玩弄男性,为男性所抛弃的命运而抛弃男人,如穆时英《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中的蓉子,无聊时把男人当作“辛辣的刺激物”;高兴时把男人当作“朱古力糖似的含着”;厌烦时男人就成了被她“排泄出来的朱古力糖渣”。刘呐鸥《游戏》里的她,把爱和贞操给了自己的所爱,但论到婚姻时,却要和她的所爱“愉快地相爱,愉快地分别”,去嫁给一个能为她买六汽缸“飞扑”的富商。《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中的H和T都因未能领会女主角从来“未曾跟一个gentlmen一块儿过过三个钟头以上”的恋爱方式,不知珍惜时间,而被女主角嗔怪:“你的时候,你不自己享用”,无可挽回地无情地遭到淘汰。但是由于这些女性都被组织在主动/看、被动/被看,女人作为被看,男人作为看的承担者的结构模式中,这就使得她们主动地选择和抛弃男人的行为实际上是为更深层的为了男人的目的——观看的主动控制者的视线和享受而展示的。在这类小说的结构中,一般都只有男女两个主人公,其他人物都属于群像式背景衬托,男人作为主动的聚焦者、叙述者,女主人公只有在聚焦者视线的注视之下和叙述者的感觉之中才得以凸现和清晰,无论她如何行动都无能摆脱这种观赏者的视线和被描述者的地位。所以,那些男主人公们尽管得不到这些女主人公们的爱,但他们再不象郁达夫的抒情主人公们那样自怜和感叹,女人的放荡和妖冶都不过是他们观赏中的美景和奇观,一切失落和怨仇被这种观赏而中断或淹没,分手也只不过是作为“看”的聚焦行为的结束。叙述者不再有着“抒情”的功能,而是“看”的承担者,起着描写“看”的对象的作用。通过对聚焦对象的描写和叙述,使女体成为叙述者本身和读者共同的欣赏对象。
电影摄影机镜头对女体的解剖式分解式的展示技术也给文学的描写方式带来了显著的变化。比如刘呐鸥的《游戏》通过男主人公的视线对女主人公形象的展示:
他直起身子玩看着她,这一对很容易受惊的明眸,这个理智的前额,和在它上面随风飘动的短发,这个瘦小而隆直的希腊式的鼻子,这一个圆形的嘴型和它上下若离若合的丰腻的嘴唇,这不是近代的产物是什么?
很明显,这样的描写也只有电影特写镜头和镜头的不断推移,才能如此冷冰冰机械地切割展览人的身体器官。
再比如穆时英对Cr ven“A”眼睛细部的刻画:
她有两种眼珠子:抽着Craven“A”的时候, 那眼珠子是浅灰色的维也勒绒似的,从淡淡的烟雾里,眼光淡到望不见人似地,不经意地,看着前面;照着手提袋上的镜子擦粉的时候,舞着的时候,笑着的时候,说话的时候,她有一对狡黠的耗子似的深黑眼珠子,从镜子边上,从舞伴的肩上,从酒杯上,灵活地瞧着人,想把每个男子的灵魂全偷了去似地。
在电影时代之前,人面对活人的描写恐怕是不可能如此没有距离感地描写眼珠子色彩的变化,也不可能如此不动声色地盯视和放大眼部细节而不受到对方对被看的察知和反应的逼视的。也很明显,穆时英的这段描写是出于对电影的特写和叠印技术的搬移或说是模拟。电影给人们留有的对无数影片和镜头的记忆,为文学带来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变化,即作者描写人物时,有时会自觉不自觉地不再面对活生生的人,而是对于银屏上的影象的记忆。穆时英和刘呐鸥的某些创作可以让我们感觉到这一点,阅读这些作品正像我们看一张照片而不是一副画,看一段生活的实拍录象而不是身临其境的感觉一样, 缺乏的也许就是本杰明(Walter Benjamjn)所说的“气息”。这种“气息”的经验是建立在人与人的活生生的交流、对视、看与回看的反应能力之上和关于一个活生生的人的不期然而然的感知、回忆和联想之中,是人的影象和相片之类性质的东西所不能具备的,因为这些机械复制品只能“记录了我们的相貌,却没有把我们的凝视还给我们”〔32〕。当然,这并不是说穆时英、刘呐鸥等的作品完全是对机械复制品的再模仿,但电影艺术的确给他们的创作留下了鲜明的烙印。沈从文曾批评穆时英的作品“于人生隔一层”,仿佛是“假的”,是“假艺术”,〔33〕尽管有些苛刻,但也许这样的指责正是因为穆时英笔下的一些人物缺乏一种活生生的“气息”,而缺乏一种“真实感”所致。
都市风景和小说形式的空间化
中国新感觉派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对都市景观的展示。刘呐鸥非常准确地把自己唯一的短篇小说集题名为“都市风景线”,穆时英则通过他的人物之口把自己的创作角色定性成都市的“巡礼者”。这说明他们对都市的把握是自觉地从“外观”和“现象”入手的,这样的创作意图使他们的小说性质内在地更接近以画面、物象,或说是影象为“现实”的电影本质,而电影技巧又似乎是“特别适用于对一座大城市做全景式观察的了”〔34〕。关于这一点刘呐鸥更是心领神会,他在1933年4 月发表于《现代电影》1卷2期上的《Ecranesque》一文中说:“最能够性格的地描写着机械文明底社会的环境的,就是电影。”甚至有论者认为,“近几十年发展起来的沸沸扬扬的大城市生活新方式和新特点只有电影能够记录下来和做出灵敏的反应。”〔35〕事实上,早期电影也确实曾经把“大都市外貌”作为重要的主题,二三十年代的电影界曾出现了相当一批以反资本主义的浪漫精神表现城市生活的影片,以电影特有的纷杂手段表现城市生活的纷杂。电影这种内容特征和技术特性,当年已敏锐地引起不少小说家和批评家的关注。中国早期电影批评家尘无曾专门著文探讨“电影和都市”的关系,认为“电影是都市的艺术”,这不仅因为“都市的物质建筑”和“大量的直接消费者”,更因为“都市生活的复杂和都市情调的紧张,也恰恰适合电影的表现”。〔36〕楼适夷在他颇染新感觉派作风的《上海狂舞曲》〔37〕中,深有感触地写到:“都会风景恰如变化无绝的Film”。前面已经提到的《影戏漫想》那篇长文,除了联想到“电影和女性美”之外,也联想到“电影和诗”。文章说:“影戏是有文学所不到的天地的。它有许多表现方法:有close —up有fade out,fade in,有double crauk(crank ), 有higo (h )speed,有flash……利用着他们这些技巧要使诗的世界有了形象不是很容易的吗?”刘呐鸥曾翻译过著名的电影理论家安海姆的著作《艺术电影论》,在上海《晨报·每日电影》上连载了三个月之多,其中主要涉及了电影的“立体在平面上的投影”、“映像与实体”、“影片底深度感觉底减少”、“空间时间的连续性底缺乏”、“非视觉的感觉世界底失灭”、“电影底制作——当作艺术手段的开麦拉与画面”、“空间深度减少之艺术的利用”等诸方面的重要问题,其中的一些电影艺术的特征用来概括新感觉派的小说也很恰当。刘呐鸥本人在《现代电影》上发表的《电影节奏简论》、《开麦拉机构——位置角度机能论》、《影片艺术论》等都是有关电影艺术的特性和技巧,学术性很强的文章,这些译作和文章不仅表明刘呐鸥对电影艺术形式已揣摩日久,深得三昧,甚至也可以说是对自己和新感觉派借鉴电影技巧,进行小说实验的一系列技术操作的总结。
电影艺术对刘呐鸥最大的启示是“不绝地变换着的”观点和作为影片的生命的要素“织接(Montage)”。 他的《开麦拉机构——位置角度机能论》、《影片艺术论》对此作了详细的介绍和分析。所谓“观点”即开麦拉(摄影机)的位置,“是指当摄影的时候从一个方向对着摄影对象而停立的摄影机的一个位置而言”,〔38〕一个开麦拉的位置就代表着一种观点。电影艺术就是“不绝地变换着它的观点而用流动映像和音响来表明故事的一种艺术”〔39〕,刘呐鸥认为这种不绝地变换着”的观点是电影艺术“所有特质中最大的一个机能”,并将之称为“是个革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40〕。而所谓织接即现在所说的蒙太奇。刘呐鸥受到苏联导演普道甫金(Poudoukine)的影响,认为织接使相机拍好的软片上的“死的静画”“头尾连接而统归在一个有秩序的统一的节奏之中”,“由在不同的瞬间里,在种种的地方摄来的景况而构成并‘创造’出一种新的与现实的时间和空间毫没关系的影戏时间和空间,即‘被摄了的现实’”,“是诗人的语,文章的文体,导演者‘画面的’的言语”。织接可以使前面所说的“开麦拉”获得“灵魂之主”,它们之间结合的瞬间“能够使物变换其本质的内容,确保其新的价值,给影片以从前所没有的意义”。所以,这种新艺术赋予了人们一种“视觉的教养”,“它使我们的眼睛有学问,提高我们的‘看’的技术,教我们以在一瞬间而理解幕面的象征的意义”。〔41〕的确,中国的新感觉派正是借鉴了电影艺术的特质,利用了电影给以他们和人们的“视觉的教养”,以“不绝地”“变换着”的“流动映像”,织接“人生的断片”,“表明故事”而非叙述故事促成了小说文体的又一次“革命”,使一向以时间和连续性为叙述基础的小说形式空间化。
小说的“空间形式”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学者约瑟夫·弗兰克提出,并由诸多学者进一步充实、发展和完善的。由于这个概念能够为解释现代小说的叙事技巧和认识现代小说的意义提供合适的理论框架而倍受关注,甚至有论者认为,在“为理解伟大的艺术作品而创造出新的可能性”方面,“没有哪一个批评概念能够比它提供更多的东西”。〔42〕“空间形式”概念之所以如此重要,因为它打破了本世纪初兴起的小说实验的文体技巧使评论者“惊慌失措”,引起批评危机的尴尬局面,完成了小说理论从建立在巴尔扎克、狄更斯基础之上的现实主义批评范型向现代主义批评范型的转移。罗杰·夏塔克曾经指出:“20世纪强调的是与早期变化的艺术相对立的并置的艺术。”〔43〕“空间形式”概念正符合20世纪一个新近时期的文学艺术的特征,也是认识中国新感觉派所创造的一种“新奇的”小说类型的合适术语。
小说形式的空间化在本质上是与小说叙述的和连续的趋势相抵触,甚至也是和字词排列在时间上的连续性相抵触的。如何获得小说的空间形式?它的技巧就是“破碎”,“破碎——它导致了所谓的‘空间形式’——已经引起了批评家们的绝大部分的注意”。〔44〕“破碎”首先是情节的破碎,“它的终极形式是生活的片断”〔45〕,而其呈现又最适合被作为“不绝地”“变换着”的“流动映像”来描述的。在这方面,电影以它的特长为小说形式的“革命”提供了可资模仿的榜样。刘呐鸥翻译的安海姆的《艺术电影论》里专门谈到电影“空间时间的连续性底缺乏”问题。文章分析说,“在现实里并没有时间或空间的飞跃。时间和空间有着连续性”,“电影上就不是这样。被摄在片上的时间的断片可以由任意之点切断。它可以马上接上完全在两样的时间内发生的一场景。空间的连续性也是同样可以被中断。”而且,在电影里“全场所底同时发生的事象均可以简单地用构成的画面排成前后关系来表明,使人们由动作的内容知道它的同时性。最原始的方法是利用对白或插入字幕那样的说明文字”〔46〕。电影中表示时间和空间转换过程的诸多技巧,很明显地启发了新感觉派的创作。且不说刘呐鸥的《A Lady tokeep You Company》,被施蛰存称为“小说型的短脚本”,还有叶灵凤的流行性感冒》、禾金的《造型动力学》都把小说写成了分镜头脚本以远景、近景、特写、字幕等等画面形式的呈现来不断的打碎叙述情节的时间流程,以电影化的影象系列取代小说对故事情节的叙述。穆时英的《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上海的狐步舞》等也几乎可以说是不标镜头的分镜头脚本。其每一段落都可视为一个镜头,或系列画面。《夜总会里的五个人》〔47〕全文共排列了491行,其中1至2行为一段的就有366行,占全文行数的75%,而其他段落又大部分是由占3行的段落组成。 段落的密布和小型化直接说明了小说文本的片断性和零碎性,而事实上,即使是较长段落也往往是由密集的零散性的画面系列聚集而成的,比如经常被论者引用的《上海的狐步舞》中对舞会场面的表现:
蔚蓝的黄昏笼罩着全场,一只saxophone正伸长了脖子, 张着大嘴,呜呜地冲着他们嚷。当中那片光滑的地板上,飘动的裙子,飘动的袍角,精致的鞋跟,鞋跟,鞋跟,鞋跟,鞋跟。蓬松的头发和男子的脸。男子的衬衫的白领和女子的笑脸。伸着的胳膊,翡翠坠子拖到肩上。整齐的圆桌子队伍,椅子却是零乱的。
在这一小段中,除第一句是完整的描写性句子外,其他大都仅仅是由定语和主语、形容词和名词组成的,是缺少谓语和宾语的省略句。这种不连续句法本身就造成了描写的中断,而产生类似摄影机镜头的不断叠印显现,变换无穷的万花筒式的空间效果。这样,典型的空间形式小说不再由故事或人物的发展变化的内容组成,而由无数个画面、场景的碎片构成。穆时英在《白金的女体塑像·自序》中就是这样描述自己的创作:“人间的欢乐,悲哀,烦恼,幻想,希望……全万花筒似地聚散起来,播摇起来。在笔下就漏出了收在这本集子里边的,八篇没有统一的风格的作品。”
空间小说情节“破碎”的另一特征是以场景的呈现代替叙述,或说是阻碍叙述的向前的历时发展。这类的小说往往只是由几个大的场景构成,而弃绝了场景与场景之间的连贯性的叙述程序。尽管从场景到场景的跳跃变换上,读者可以猜测到情节的发展和人物的变化,但这种发展和变化游离于叙述过程之外,作者通过对典型的可以作为标识性场景的选择和呈现,使小说具备了电影“永远的现在式”的特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再描写往事,而是把往事也化为场景,像电影的闪回镜头一样,倒退到彼时彼地,以获得现在时场景的直接性。这样的表现方法并不简单地等同于一般小说的倒叙,因为他不再用一大段首尾连贯的回叙来交代往事,而是不断地切出切入,造成场景或场面的间隔效果和非连续性。它的最明显的功效即打断一个故事的时间流,而使观众把注意力集中到一个相对静止的时间领域内各种关系的相互作用上。比如穆时英的《街景》,整个小说由系列的街景的场面组成,一类是发生在现在的街景,一类是作为现在的街景之一——一个老乞丐头脑中所浮现的他经历过的那些“街景”,作者把现在的街景和过去的街景模拟电影技巧交叉剪辑在一起从而造成情节的不断中止而片断性地反复强化了一个乡下人发财梦的破灭,有家归不了的悲剧。徐霞村的《MODERN GIRL》〔48 〕也通过叙述者对被誉为“现代姑娘”几次会面场景的回忆,以具有相同性质行为的并列和重复,创造出关于一个所谓“现代姑娘”不过是“会作新诗”,“法郎士的爱好者”,以此去获得男性的好感,骗取钱财的印象。这种由诸多场景交叉切割,省略叙述过程,有意地使情节支离破碎的小说是电影化的想象带给小说叙事方法的一个显著变化,也是新感觉派极其受影响的一大批创作的突出现象之一。它使前一阶段作为现代小说技巧革新标志的“倒叙”手法,进一步复杂化,或者说遭到淘汰。
小说情节的破碎势必给小说的结构带来新的特点。戈特弗里德·本曾使用了一个桔子的比喻来说明取消了时间顺序的空间化小说的结构:“是像一个桔子一样来建构的。一个桔子由数目众多的瓣、水果的单个的断片、薄片诸如此类的东西组成,它们都相互紧挨着,具有同等的价值。”〔49〕戴维·米切尔森进一步阐明说,这个“由许多相似的瓣组成的桔子”,“并不四处发散,而是集中在唯一的主题(核)上”〔50〕。在这里,构成空间化小说情节的“生活断片”即相当于桔子瓣,它们的结构方式也是夏塔克所提出的“并置”原则,即不分主次、先后或因果的关系并列地置放在一起,文体的整体感依靠各种意象、暗示、象征和各个片断间的前后参照和空间编织而获得。所以“事件的安排显然也不受发展原则的支配。书中的各章是一些块块”,“它们唯一的接触点”〔51〕就是主题。这种结构模式在穆时英的《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上海的狐步舞》中最为典型。《夜总会里的五个人》共分四部分,实际上展现了七个场景。在第一部分里作者并置了五个场景:近代商人胡均益在金业交易所眼看着标金的跌风把八十万家产吹得无影无踪;大学生郑萍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心上人跟着别人走了;曾经美丽得“顶抖的”黄黛西突然意识到自己的青春不再而痛苦不堪;学者季洁百思不解“你是什么?我是什么?什么是你?什么是我?的问题”;一等书记缪宗旦接到撤职书,感到“地球的末日到啦”的绝望。这五个场景相互间毫无联系,作者也有意用空一行的版式来强化这种间隔,但为了将它们组织成一体,作者在这一部分以醒目的标题:“五个从生活里跌下来的人”标志出这五个人不同命运的生活断片的共同性质,以“同类并置”的结构取得了相互的关联。同时作者又在每一场景前,借鉴电影表示同时性的最原始的方法,类似屏幕上的字幕一样,标出时间,为发生在不同地点不同人物,但同一时间的事件获得一个外在的接触点。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前四个场景写的是确切的日期:“一九三二年四月六日星期六下午”,而第五个场景标出的却是个不定日期:“一九×年——星期六下午”,这个不定日期暗示了下面发生的事件的虚拟性,甚至也颠覆了前四个事件的真实性,但突出了星期六下午的特别指认,而使这五个场景具有了一种概括性,它意味着尽管前面所标出的具体时间也许是虚拟的,但“星期六下午”是特别的,在星期六下午发生下面的种种事情是经常性的,这几个片断不过是信手拈来的几个现象而已,正像前面信手标出的日期一样。为了突出星期六的特殊性,作者不惜以一节的篇幅,通过报纸标题、各大建筑物、晚上,是上帝进监狱的日子。”所以,在这不正常的一天发生任何事情都是正常的,甚至就像周而复始的星期六一样是反复不已,接连不断的。接着作者描写了这“五个从生活里跌下来的人”会聚在夜总会通宵达旦,狂饮疯舞,最终胡均益开枪自杀的场景和剩下来的四个人为胡均益送殡的场景。尽管后两个场景以空间的形式展现了情节的发展,但显然这不是作者的兴趣所在,在接近尾声之处,作者用了一个“爆了的气球”的意象,反反复复以细节、以感慨、以叙述者的突然插话,重复了七次之多,而成为一种象征,使整个小说的断片、情节、人物等都获得了聚焦的主题中心点:杯盘狼藉散了的舞会“像一只爆了的气球”,开枪自杀的胡均益是“一只爆了的气球”,而面临绝望境地的失恋者郑萍、失业者缪宗旦、失去青春的黄黛西、失去人生信仰的季洁,他们的希望和幻想难道不也成了“爆了的气球”吗?这“爆了的气球”的意象正是这五个人所代表的都市的生活、都市的人生,甚至可以说是不断膨胀的都市的欲望的预言。黄黛西说:“我随便跑那去,青春总不会回来的。”郑萍说:“我随便跑那去,妮娜总不会回来的。”胡均益说:“我随便跑那去,八十万家产总不会回来的。”都市人无可奈何的命运,正深藏在这无可挽回,“No one can help!”的绝望和悲哀之中。通过不同人的生活片断的并置,以及意象、象征、短语的暗示和明喻,作者为都市生活创造了统一的印象和一幅末世的景观。
《上海的狐步舞》的结构更是纵横交错,既建立在“天堂与地狱”的异类并置的空间对立之上,又有着同类并置的对应关系。灯红酒绿的舞场、饭店、旅馆和建筑这些舞场、饭店、旅馆的工地形成对立;街头娼妓和花天酒地里的淫乱相呼应,发生在林肯路的直接谋杀和建筑工地的间接谋杀相关联,从这些生活片断的对比和对应中可很自然地过渡到小说的主题:“上海,造在地狱上的天堂”。但所谓“天堂”仅指物质环境而言,就人来说,只有生活在地狱中和该下地狱的人们。
通过主题或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广泛的意象网络而建立的空间结构形式的小说意味着“发展的缺乏”,因而“叙述中的‘于是’就萎缩成简单的‘和’”〔52〕,使“文本具备了一种反叙述的近乎固定的性质”〔53〕,带有静止特征的“个人肖像”和“社会画面”就成为它经常性的主题。刘呐鸥、穆时英的作品正是以“都市风景”为主题的,所以尽管他们的小说也有情节、人物和情绪,但不管是人物还是情节或是情绪都不是他们的目的所在,这样,他们的情节缺乏过程和连续性,他们的人物缺乏性格和立体感,他们的情绪缺乏微妙和感染力,一切都仅仅是组成“都市风景”的一个片断、场景或现象。刘呐鸥的短篇小说集《都市风景线》甚至可以作为具有空间形式特征的长篇小说来读,每一个短篇都是这幅社会长卷的一个画面、片断和现象,共同构成了这部“都市风景线”。他们的部分小说不仅与注重情节和人物,以全知全能观点叙事的传统小说相距甚远,甚至同完成了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着眼于表现人物的情绪、感受、注重叙事观点的统一和人物心理为结构中心的五四小说也大有不同,在这里,作者的叙述大都为对每一画面、场景的描写所取代,叙述者的视点、情绪已不再成为文本的统一的来源,反而被中断和打碎;以历时性的情节或心理的发展变化为基础的时间流被不同时空的生活片断的空间编织所代替。所有这些特点足以表明米克·巴尔(Mieke Bal)在《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中的所说, 以“空间联系取代了时间顺序联系”,“事件只依据空间或其他准则(比如联想)来结构的话,那么这一本文就不再适合本书导言中所提出的叙述界说”。〔54〕也就是说,空间形式的小说并不很适于套用一般小说叙述学的理论。
但是,“空间形式”小说如万花筒的片断和破碎的性质以及结构编织特点却与电影多样可变的观点、图象本性和蒙太奇处理镜头的联结、段落的转换的技巧存在着一种对应或同源关系。在刘霓虹灯广告以及具有代表性画面的叠印造成星期六的气氛,以开列节目单的方式加强星期六已经程式化的印象,甚至不忌讳直白而抽象的论说,概括出星期六的性质:“星期六的晚上,是没有理性的日子。/星期六的晚上,是法官也想犯罪的日子。/星期六的呐鸥看来,“除了些形式上及技术上的差别之外,文学和影片在组织法上简直可称为兄弟。”〔55〕本来“空间形式”小说是建立在对普鲁斯特、乔伊斯、福克纳等所创造的现代主义小说范型的分析之上而形成的一个新的批评概念。这些意识流大师尽管大量借鉴了电影技巧,但“他们所开发的经验领域大都是哪怕最灵巧的摄影师也无法进入的”〔56〕精神之巨大的空间。他们以文字的图象、暗喻、象征以及相互的关系,通过对照、并列、编织等类似电影蒙太奇的剪辑手法表现人的思维活动和心理活动,在这方面也许受到弗洛依德的启示:“将思想变为视象”〔57〕,使心理感知作为事物的摄影图象来描述,从而创造出既吸收进电影的技巧又不牺牲深入剖析人的精神意识,发挥无以伦比的语言力量的现代小说范型,把电影化的想象和技巧融会在本质上是文字的表现形式之中和文学地把握生活的方式之中。但刘呐鸥穆时英等只浅尝辄止于从外部的视点捕捉某些五光十色的社会现象的断片,也许他们在某些零碎画面的描写上没有丧失文字的感觉力,但从整体上看,他们的小说缺乏语言文字特有的分析力,内涵力,和理性的力量,造成“深度感觉底减少”。这样,他们的创作难以满足知识分子层对人类的精神和行为的深度探求;而他们对情节、人物的忽视也不能满足一般读者层娱乐消遣的要求,只能以“新奇”的形式引起一时的惊诧和轰动效应。但他们对文体形式的探求毕竟创造了小说文体的一种新的类型,为小说文体在现代的发展显示了一条新路而与西方现代小说实验的一个方面联系在一起。
中国新感觉派与电影的密切关系还突出地表现在以快速的节奏表现现代都市生活,严家炎先生对此早有论及,他精辟地指出,中国新感觉派小说“有异常快速的节奏,电影镜头般跳跃的结构,在读者面前展现出眼花缭乱的场面,以显示人物半疯狂的精神状态,所有这些,都具有现代主义的特点。”〔58〕中国新感觉派之异常重视节奏的问题是因为他们体会到“现代生活是时时刻刻在速度着”〔59〕,现代人的精神“是饥饿着速度、行动、战栗和冲动的”。〔60〕刘呐鸥认为,电影作为一门新兴的艺术,所以能够在现代艺术中占着“绝对地支配着”的位置,就因为“它克服了时间”,于是“电影的造型”便代替了一切“静的造型”,“节奏是电影的生命”〔61〕,也是新感觉派为创造现代小说形式从电影艺术中输入的活力。
刘呐鸥非常认真地研究了电影的节奏问题,他曾在1932年7月1日至10月8日连载于《电影周报》的长文《影片艺术论》, 专门介绍“绝对影片”的作者及其特色一节中,特别谈到电影是“视觉的节奏”问题,认为“把现代用视觉的手段组织成为有节奏的东西”是“绝对影片”的成功之一。他还在另一篇文章中分析说,“节奏是有三个要因的,一是影象Image的映写长度。二是场面的交叉和动作动机motif的交叉。三是被写物,演技、背景等的移动。”〔62〕这三个要因可以说都被中国新感觉派在纸面上横移了过去。刘呐鸥认为,就电影影象的长度来说,“大约在一定的胶片长度内如果镜头的数目少(时间长,音调弱)的时候,全体的氛围气是静的,而如果同长度内的镜头数多(Flash 等时间短,音调长)即影片的氛气便变成动的,活泼,劲力的”。〔63〕文学语言和电影画面具有一定的类比性,镜头、片段、场面、剪辑可相当于字、词、句、句法和语法,这样,语言文字在一定的篇幅内展示的形象越多,当然节奏也就越快。穆时英和刘呐鸥正是掌握了这种类比性,而聪明地将电影艺术技巧运用于自己的创作。短镜头组合、叠印、突切、化、交叉剪辑等都可以在穆时英、刘呐鸥小说文本的省略文体、不连续句法、物象纷呈中找出相对应的技巧。比如穆时英描写舞场外停放着许多汽车等候着接送舞客的场面,把一句话的内容分解成系列物象的排列——“奥斯汀孩车,爱山克水,福特,别克跑车,别克小九八汽缸,六汽缸……”〔64〕这就像拍摄同样的场面,不用一个连续的长镜头的摇镜来表现,而切割成一个个短镜头快速剪辑在一起一样,具有快速的节奏感。就场面的交叉和动作动机的交叉来说,它涉及到小说本文的结构排列顺序问题。如果事件按一条线索的时间顺序来发展,甚至以倒叙追忆大段的往事,其节奏是平稳而缓慢的,但若打乱时间顺序,把不同时间地点的事件交叉剪辑在一起就会产生跳跃的快节奏。穆时英的《街景》、《PIERROT》、《空闲少佐》等都采用了这样的结构方法。 被写物和背景的移动在穆时英、刘呐鸥的作品中也比较多见,比如《上海的狐步舞》有一个片断,刘颜蓉珠从老夫刘有德手里要了钱后,拉着她法律上的儿子,实际上的情夫坐上车,接下来就突兀地描写到:“上了白漆的街树的腿,电杆木的腿,一切静物的腿……revue (轻歌舞剧——笔者注)似地,把擦满了粉的大腿交叉地伸出来的姑娘们……白漆腿的行列。”各种腿的罗列不仅适合坐在轿车里看到窗外近处风景的下部的视野,也创造出背景移动的效果,并且以画面的空间形式暗示了时间上的接续:前段写这对乱伦母子坐上车,这段表现的是他们在车里看到的飞逝而过的风景。但这种联系完全游离于叙述过程之外,只能靠读者自己去领会。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电影对新感觉派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也多是表面化的,但又是非常恰当的。作为中国都市文学的开创者之一,他们把自己在都市中的角色定位在“巡礼者”,这就决定了他们创作的观光和游览性质。这既不同于茅盾以社会剖析者的身份取得对都市的俯视观点,也不同于后来的张爱玲、苏青、潘柳黛等作为都市的居住者,把都市作为生活的空间,有着身在其中的观点。他们不上不下漫游在路面上,视觉不得不为鳞次栉比的建筑群所切割的位置,只能使他们获得关于都市的断片的、有限的偏、重视觉的印象式的经验,所以他们那些较多地模拟电影的小说是具有电影性质的物象或说是图象纷呈,而不象张爱玲的作品是综合着情感、理性的意象纷呈。这种区别就在于物象是平面的,物象即物象,本身并不具有意义,意义的产生依靠和其他物象的关联;而意象是有深度的,本身就蕴涵着意义和情感,所以新感觉派的创作性质正适合电影技巧的发挥和移植,而电影作为一种新的表述媒介也为生存于现代科技世界中的人所获取的新的经验感知能力和方式提供了新的手段。中国新感觉派正是通过借鉴电影艺术和其他现代文学艺术掌握了表述现代空间经验(局部片断)和时间经验(快节奏)的技巧,并非自觉地创造出空间小说的类型。但由于他们对现代性的认识多停留于视觉经验,就不可能在现代的形式及其根源和意识之间建立起深刻的联系,事实上,形式的空间化,不仅是一种技巧的策略,更深层的意义是,它说明自文艺复兴以来,一直以决定论、进化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等“理性”方式组织起来的宇宙观已经破裂,是现代性本身在文化中产生的一种涣散力的主要征象之一。
注释:
〔1〕〔34〕〔56 〕爱德华·茂莱:《电影化的想象——作家和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1989),第5、137、302页。
〔2〕杨之华《穆时英论》,载南京《中央导报》第1卷,第5期, 1940年8月。
〔3〕〔4〕〔5 〕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上海书店,1984)第538、538、532页。
〔6〕〔8〕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第13、12页。
〔7〕参考〔法〕乔治·萨杜尔:《电影通史》第3卷(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第539、54页。
〔9 〕壮游:《女性控制好莱坞——她们主宰着电影题材的选择》,载上海《晨报》,1935年3月4日。
〔10〕何珞:《电影防御站》,《时报·电影时报》,1932年7 月26日。
〔11〕《良友》画报,第86期,1934年3月15日。
〔12〕唐纳:《清算软性电影论》,载上海《晨报》,1934年6 月27日。
〔13〕刘呐鸥:《论取材——我们需要纯粹电影作者》,《现代电影》第1卷第4期,1933年7月。
〔14〕〔15〕嘉谟:《硬性影片与软性影片》,载《现代电影》第1卷第6期,1933年12月
〔16〕尘无:《电影与女人》,载《时报》1932年7月12日。
〔17〕电影的别称。
〔18〕《现代出版界》第9期,1933年2月1日。
〔19〕孔另境编:《现代作家书简》(花城出版社,1982 )第105页。
〔20〕施蛰存:《我们经营过三个书店》,见《沙上的脚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第12页。
〔21〕《文艺风景》第1卷第1期,1934年6月1日。
〔22〕郑康伯:《帝国的女儿》,载《现代出版界》第26、27、 28期合刊。
〔23〕〔24〕〔27〕穆时英:《电影的散步·魅力解剖学》,载上海《晨报》,1935年7月19日。
〔25〕〔26〕〔28〕穆时英:《电影的散步·性感与神秘主义》,载上海《晨报》1935年7月17日。
〔29〕刘呐鸥:《现代表情美造型》,载《妇人画报》第18期。在这篇文章里,刘呐鸥认为,在现代社会的生存竞争中,99%的男子是不能满足征服欲的。累次的失败使他们的心理起了一种变化,他们既喜欢施虐同时也爱被虐。于是他们需要从来所没有的新型女子。这个新型可以拿电影明星嘉宝、克劳福为代表,“她们的行动及感情的内动方式是大胆,直接,无羁束,但是在未发现的当儿却自动地把它抑制着”。使男子享受到双重的满足,这样的女子“在男子的心目中便现出是最美,最摩登。”
〔30〕〔33〕沈从文:《论穆时英》,见《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联合出版,1984)。
〔31〕劳拉·穆尔维:《视觉快感与叙事性电影》,收入《电影与新方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第203页。
〔32〕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三联书店, 1989)第161页。
〔35〕〔匈〕伊芙特·皮洛:《世俗神话——电影的野性思维》(中国电影出版社,1991)第78页。
〔36〕尘无:《电影和都市》,载《时报》,1932年6月12日。
〔37〕载1931年6月1日——8月1日《文艺新闻》第12——22号,因作者生病,小说未能全部刊出。
〔38〕〔39〕〔40〕刘呐鸥:《开麦拉机构——位置角度机能论》,载《现代电影》1卷7期,1934年6月15日。
〔41〕有关“织接”的引文均见刘呐鸥:《影片艺术论》,载《电影周报》,1932年7月1日至10月8日第2、3、6、7、8、9、10、15期。
〔42〕〔43〕〔44〕〔45〕〔49〕〔50〕〔51〕〔52〕〔53〕依次见秦林芳编译:《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第101、70、130、165、142、142、144、143、156页。
〔46〕安海姆著、刘呐鸥译:《艺术电影论》,上海《晨报》, 1935年5月15——16日。
〔47〕根据现代书局《公墓》初版本。
〔48〕载《新文艺》,1卷3期。
〔54〕〔荷〕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第76页。
〔55〕同注释41。
〔57〕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引论》(商务印书馆,1984 )第132页。
〔58〕严家炎:《中国小说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第144页。
〔59〕〔60〕〔61〕〔62〕〔63〕刘呐鸥:《电影节奏论》,《现代电影》第1卷第6期,1933年12月1日。
〔64〕穆时英:《上海的狐步舞》,《公墓》第20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