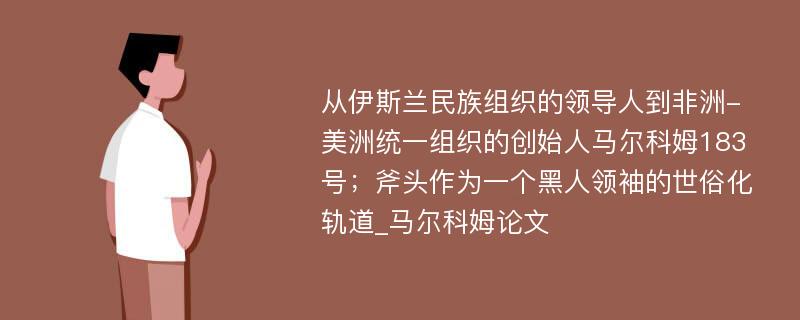
从伊斯兰民族组织的教长到非裔美国人统一组织的创建者——马尔科姆#183;爱克斯作为黑人领袖的世俗化轨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兰论文,教长论文,组织论文,创建者论文,美国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0)16-0056-09
马尔科姆·爱克斯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时期与小马丁·路德·金齐名的著名黑人领袖,被誉为美国黑人“闪光的王子”。他早年曾混迹于街头,后成为伊斯兰民族组织最有活力的领袖,在与该组织毅然决裂后,走出了黑人穆斯林宗教使命与活动的局限,在愈来愈广阔的世俗领域里为所有黑人乃至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奔走呐喊,直至1965年不幸遇刺身亡。马尔科姆·爱克斯因其具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一直是国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和争议的焦点。有学者盛赞马尔科姆·爱克斯是国际主义斗士,也有学者贬低他为种族主义煽动者。可是这种赞扬和贬抑大都以马尔科姆·爱克斯的政治思想为研究对象,而忽略了其宗教意识。少数从宗教角度研究马尔科姆·爱克斯的学者却又忽视了马尔科姆·爱克斯思想的政治内容。实际上,在马尔科姆·爱克斯成为黑人领袖后的经历中,宗教和政治是密不可分的。宗教在马尔科姆·爱克斯早期的思想和活动中曾一度占据主导地位,不过,这一地位最终为世俗政治所取代。可以说,马尔科姆·爱克斯成为黑人领袖之后经历了一个世俗化过程。本文在借鉴和吸收国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相关原始文献的重新解读,试图对马尔科姆·爱克斯的这一世俗化过程加以梳理和阐释。
马尔科姆·爱克斯一生经历了很大的变化,他成为一名黑人领袖以后的变化更是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美国学术界一般以马尔科姆·爱克斯1964年3月与伊斯兰民族组织(the Nation of Islam)决裂为界,把他作为黑人领袖的思想分为早期和晚期两个阶段。实际上,马尔科姆·爱克斯在思想和活动上所发生的变化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并没有完全明确的分界线。换言之,在所谓的早期和晚期之间还存在一个过渡阶段。因此,为更加清晰而完整地层现马尔科姆·爱克斯作为黑人领袖世俗化过程的全貌,本文将其分为三个阶段:早期阶段(马尔科姆,爱克斯加入NOI——20世纪60年代初)、过渡阶段(20世纪60年代初——非裔美国人统一组织成立the Organization of Afro-American Unity)和后期阶段(OAAU成立——马尔科姆·爱克斯被刺)。早期的马尔科姆·爱克斯主要是伊斯兰民族组织内部的一名教长,不参与世俗事务。但后来随着活动经验的增加,马尔科姆·爱克斯的思想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世俗化倾向,其主要的活动也从宗教转向了世俗政治,到1964年6月OAAU成立,马尔科姆·爱克斯作为黑人领袖的世俗化过程最终完成。这样,到他生命的后期,宗教仅仅是马尔科姆·爱克斯的个人信仰,而世俗政治则在马尔科姆·爱克斯的思想和社会活动中占据了主导位置。此时,他才真正成为没有宗教和种族偏见而代表美国黑人大众利益的杰出政治领袖。
一、早期的马尔科姆·爱克斯——黑人穆斯林的宗教领袖
马尔科姆·爱克斯早期的思想主要是伊斯兰民族组织的教义,其有关种族和政治等方面的看法也具有很强的宗教色彩。在社会活动方面,马尔科姆·爱克斯更是以宗教身份示人,主要精力都用于传教活动。可以说,早期的马尔科姆·爱克斯只是一位黑人穆斯林的宗教领袖。
早期马尔科姆·爱克斯尚未形成自己独立的思想,全盘接受了伊斯兰民族组织的领导人伊莱加·穆罕默德传授给他的教义,其思想完全被宗教化。黑人民族的“原初性”与反基督教乃是穆罕默德宗教思想的主要内容。穆罕默德指出,最早的人类是黑人。黑人是最早的也是最后的人类,是宇宙的制造者和所有者,由黑人诞生出了所有其他的人类——棕色人、黄种人、红种人和白种人。通过使用生育控制法的一种特殊方法,黑人制造出了白人[1](p.46)。高加索白人曾经是居住在欧洲山洞里的野蛮人,他们过着茹毛饮血的低等生活。整个白种人就是一个罪恶的种族[1](p.29)。他们只被安拉赋予了6000年的统治时间[1](p.36)。因此,“黑人必须与白人奴隶主分离,这是我们问题的唯一解决之道。根据圣经,这是以色列和埃及人的唯—解决之道,并且它也将是美国黑人奴隶的唯一解决之道”[1](p.49)。不仅如此,穆罕默德十分敌视基督教。他指出,基督教是白人恶魔为了奴役黑人而创建的宗教。《圣经》教会和基督教一直都在欺骗所谓的“黑人”。伊斯兰才是所有黑人的原始宗教[1](p.34)。末日审判正在进行,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将会有一场世界末日的善恶大决战[1](p.22)。届时,基督教和一切白人“恶魔”将被彻底清除。这种宗教观与正宗的伊斯兰教是不相符的,显然有点异想天开,甚至荒诞不经,但却比较符合当时境遇恶劣的马尔科姆·爱克斯的心态,因而被他全盘接受。
根据穆罕默德的教条,马尔科姆·爱克斯相信,世界上最早的人类是黑人,白种人是一个叫雅各布的黑人科学家为反叛安拉而创造出来的。由于白人在黑人民族中惹是生非因而被驱逐到蛮荒的西方。白人进行了血腥的奴隶贸易,对黑人民族实行了残暴的统治,还利用基督教愚弄黑人,教导黑人爱他们的压迫者。安拉的惩罚即将到来,最终毁灭“白人魔鬼”,重新确立黑人民族的正义统治[2](pp.76~79)。生活在美国的这些黑人其实是来自非洲的亚细亚民族的后裔,构成了安拉的选民,承担了毁灭白人文明的神圣使命。真主安拉和他派来的使者穆罕默德发现了他们,并将把他们带回黑人民族最初的家乡[3](p.79)。
马尔科姆·爱克斯不仅相信安拉将毁灭“白人魔鬼”,而且竭力攻击基督教,希望以此吸引更多的黑人参加伊斯兰民族组织。他到处向人们宣讲说,基督教是白人的宗教,是虚伪的宗教,充满了偏见、仇恨、虚伪,并在不断腐化。他断言基督教世界是白人的天堂,同时也一定是黑人的地狱。马尔科姆·爱克斯还极力批判基督教的来世观,说那是白人用来统治和教化黑人的工具。他认为,没有什么天堂和地狱,黑人应该更加关注现世,努力争取现世的自由、平等与公正[4](p.113)。在他看来,圣经的很多教义都被白人篡改了。基督教仅仅表达了白人至上主义,它是用来奴役黑人种族的宗教,而不是旨在维护和平的宗教。因此,马尔科姆·爱克斯认为只有伊斯兰教才是黑人天然的宗教,只有它才能解决美国黑人的问题。
在早期阶段,伊斯兰民族组织的教义当时完全左右了马尔科姆·爱克斯对世俗问题的看法。在种族观上,基于黑人“原初性”的黑人穆斯林的宗教信仰,马尔科姆·爱克斯指出,“黑人是漂亮的”,他们不仅不应为黑肤色感到卑微,而且还应为此感到自豪和骄傲[5](p.103)。至于白人,由于伊斯兰民族组织教义认为白人是反叛安拉的邪恶的创造物,所以马尔科姆·爱克斯断言,白人是魔鬼,天生邪恶,没有道德能力,对黑人做尽了坏事,残忍无比。马尔科姆·爱克斯甚至对白人个体和群体不加区别,他坚信白人是黑人共同的敌人、共同的剥削者、压迫者和歧视者[6](pp.4~5)。马尔科姆·爱克斯尤其痛恨白人自由派,甚至认为美国北方的“白人狐”比南方的“白人狼”更残酷、更邪恶[7](p.65)。
在政治理念上,由于相信美国黑人肩负安拉赋予的毁灭白人文明的神圣使命,马尔科姆·爱克斯不仅倡导对白人“恶魔”实行暴力还击,还鼓吹黑人的暴力革命。他对美国政府的批判和指责也主要是从宗教角度着手的。在他看来:“基督教世界已经不能给予黑人公平。(美国)基督教政府也没有给予那些为他们无偿劳作了310年的2000万前奴隶(公平)……白人基督教徒一直都不愿意承认我们,也不愿将我们当作平等的人类看待。”[8](p.122)此外,马尔科姆·爱克斯对“白人魔鬼”说的教义坚信不疑,竭力鼓吹伊莱加·穆罕默德的回到非洲去或在美国建立“国中之国”(获得土地是最重要的)的主张,其目的是通过种族分离、经济自立以及黑人自己的文化认同与联合,实现与白人的彻底分离。他坚决反对种族融合,认为融合对黑白双方都不好,会破坏双方的种族纯洁[8](p.127)。因此,早期的马尔科姆·爱克斯严厉批判黑人中产阶级,与金等民权领袖以及他们领导的民权运动处于水火不容的状态。马尔科姆·爱克斯认为,这些上层黑人仅仅是“现代版的汤姆叔叔”,他们是“20世纪的家用奴隶”,完全服从白人,是白人用于统治黑人的工具[6](pp.10~17)。
马尔科姆·爱克斯不仅在思想上宗教化,唯伊莱加·穆罕默德的教义是从,而且其早期的社会活动基本上也是宗教性的。他在黑人中大力传播伊斯兰民族组织的宗教教义,为伊斯兰民族组织四处招募教徒,对该宗教组织的发展和壮大做出了引人注目的重要贡献。早在马尔科姆·爱克斯在底特律第一神庙参加伊斯兰民族组织的宗教集会时,他就感到原本不大的神庙尚未坐满实在“让人恼火”[9](p.225)。于是,当马尔科姆·爱克斯后来有机会在芝加哥与穆罕默德面谈时,他就将伊斯兰民族组织的组织规模过小作为首要问题提了出来。马尔科姆·爱克斯认为伊斯兰民族组织的招募方法太消极,应该主动走上街头直接招募。他后来回忆说:“当时神庙的招募态度对我来说似乎就等同于一种坐等的态度……认为安拉将会为我们带来更多的穆斯林教徒。我感到安拉将更愿意帮助那些自助者。”[9](p.225)
这样,早期的马尔科姆·爱克斯就将自己几乎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伊斯兰民族组织的宗教教义传播和组织招募活动之中。为了成功地招募更多成员,马尔科姆,爱克斯对传播伊斯兰民族组织的教义倾注了非同一般的热情。他在1954年给其兄弟的信中写道:“即便是要让这一教义在死者中传播,一个真正的信徒也会毫不犹豫地为此而做出牺牲。因为真正的信徒知道,安拉绝不会使我们劳而无获。如果认为,我们做出任何所需要的牺牲去唤醒逝者的代价未免太大了,那只能证明我们尚未完全相信安拉是最好的回报者。”[10](p.94)马尔科姆·爱克斯的传教热情不仅见之于他的信件,而且见之于他的实际活动。在出狱初期,马尔科姆·爱克斯白天在家具店工作7个小时,晚上下班后仍会不知疲劳地亲自走上街头从事招募活动,寻找一切机会散发各种宣传伊斯兰民族组织的小册子。只要行人稍微停住脚步,他就会继续向其宣传。不仅如此,他还到其他宗教组织内去争取那些游离不定者。在短短五个月的时间里,马尔科姆·爱克斯招募活动的行程就达3万英里,使第一神庙的成员扩大了两倍[9](pp.250~259)。
由于表现突出,马尔科姆·爱克斯从1953年开始被允许在伊斯兰民族组织的宗教集会上公开宣讲。1953年7月,马尔科姆·爱克斯被授予助理教长的职位。此时的马尔科姆·爱克斯称,他是伊莱加·穆罕默德最谦逊的仆人,坚定信奉穆罕默德的一切教条。马尔科姆·爱克斯并不满足于自己在第一神庙取得的成绩,他进一步扩展了自己宗教活动的范围,奔赴外地传教。1954年,马尔科姆·爱克斯奉命前往东海岸传教。他于1954年3月在波士顿成功地创建了第十一神庙。将此神庙交由别人负责后,马尔科姆·爱克斯又马不停蹄地前往费城传教。1954年5月,他在费城建立了第十二神庙,其知名度和地位均大大上升,到6月被穆罕默德指定为哈莱姆第七神庙的助理教长。纽约哈莱姆地区的黑人超过100万,但第七神庙当时的规模非常小,只有一个很小的临街房,其成员甚至不足以装满一辆公交车[9](p.250)。为了争取更多黑人加入伊斯兰民族组织,马尔科姆·爱克斯在哈莱姆的传教活动达到了近于疯狂的程度。他一天有16-18个小时都是在传教,一周7天从未间断。结果,伊斯兰民族组织在纽约市哈莱姆地区迅速发展,其成员人数在全国各州中排名第一。与此同时,马尔科姆·爱克斯还积极在东海岸的其他各州传教。马尔科姆·爱克斯先后在马塞诸塞州的斯普林菲尔德建立了第13神庙,在康涅狄格的哈特福德建立了第14神庙。1955年,马尔科姆·爱克斯又被派往佐治亚的亚特兰大传教,在此建立了第15神庙。1955年5月,马尔科姆·爱克斯在密歇根的兰辛建立了第16神庙。
至1955年底,在马尔科姆·爱克斯的努力下,伊斯兰民族组织的神庙由7个增加至27个,且教徒人数大大增加。对于马尔科姆·爱克斯的成就,连穆罕默德也非常吃惊。他曾不无感慨地说:“感谢安拉赐予我马尔科姆教长。”[11](p.185)1956年之后,马尔科姆·爱克斯主要负责纽约地区伊斯兰民族组织的活动。他仍旧以传播伊斯兰教和发展该宗教组织作为自己每天活动的主要内容。除了这些宗教活动外,此时的马尔科姆·爱克斯基本上没有真正参与世俗政治。正如Louis A.DeCaro所言,马尔科姆·爱克斯在伊斯兰民族组织期间热情和不知疲倦地工作,都是其宗教精神的表现而不是政治活动[10](p.90)。乔治·布里特曼甚至认为,从1952年到1960年期间的马尔科姆·爱克斯是宗教狂热分子。正是由于马尔科姆·爱克斯在这段时期的不懈努力,伊斯兰民族组织从一个偏居一隅的教派发展成为一个新的重要宗教组织。
由此,无论是从思想还是从实际行动上来看,早期的马尔科姆·爱克斯都是一位积极的宗教活动家,而不是政治家。换言之,他只是黑人穆斯林的一位宗教领袖而已。
二、过渡时期的马尔科姆·爱克斯
1961年之后,马尔科姆·爱克斯开始作为穆罕默德的代表参与各种公共活动。随着活动阅历的增加,马尔科姆·爱克斯逐渐形成自己独立的思想和见解,在认识和行动上出现了世俗化倾向。他不再仅仅作为伊斯兰民族组织的教长关注宗教问题,而开始从全体美国黑人的角度关注超越宗教范围的世俗问题,其活动也不再是单纯的宗教活动,而开始与世俗政治有了密切的联系。
马尔科姆·爱克斯在思想上出现世俗化倾向的突出表现是,对穆罕默德的“不参与”政治的政策感到不满,认为只有通过政治参与才能获得自由,所以伊斯兰民族组织应该参与到黑人的斗争中去。穆罕默德却认为,政治斗争仅仅是安拉用来摧毁白人恶魔的工具,而不是最后善恶大决战的前奏,因此伊斯兰民族组织必须脱离政治。此外,他还对伊斯兰民族组织教徒之外的其他黑人缺乏信任。这样,马尔科姆·爱克斯就因为自己的世俗关注而与穆罕默德产生了分歧。
马尔科姆·爱克斯此时的思想变化无疑与民权运动的兴起有很大的关系。20世纪60年代,小马丁·路德·金等人领导的民权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声威遍及全国,而伊斯兰民族组织不参与政治的保守政策则使其影响日渐缩小。马尔科姆·爱克斯自然对其组织在黑人运动中所处的这种地位日益感到焦躁不安,他当时曾明确表示:“就个人来说,我一直认为如果伊斯兰民族组织参与更多的行动,我们将是美国黑人斗争中更为强大的一支力量……我认为,无论黑人在何处献身,在小石城、伯明翰还是其他地方,激进而自律的穆斯林都应该与之并肩战斗。”[9](pp.333~334)1961年5月开始的“自由乘车运动”中,年青的黑、白人学生在南方遭遇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暴行,令国内外震惊。马尔科姆·爱克斯内心难以平静。他认为,当许多非裔美国人和白人为黑人的自由斗争而英勇献身时,NOI不能再坐视不理。面对美国舆论对伊斯兰民族组织的指责,马尔科姆·爱克斯感同身受。他说:“现在黑人社区有越来越多的人指责‘穆斯林只说硬话,却从不行动,除非有人触犯了他们的教徒’。”鉴于伊斯兰民族组织“只说不做”而威信大降,马尔科姆·爱克斯明确指出,NOI如果想继续在美国发展并繁荣,就必须直接参与到黑人大众的运动中去,因为“这种穆斯林‘只会说’的标签很可能会突然有一天使我们与黑人的前线斗争分离”[12](p.271)。
美国黑人运动形势的发展和马尔科姆·爱克斯对穆罕默德不满情绪的逐渐增加,使他的思想出现了明显的世俗化倾向。他曾私下向一些朋友和助手透露:“仅仅依靠请求安拉和‘令人尊敬的穆罕默德’是不够的,是无法解决这些只有凡人才能处理的问题的。”[9](p.247)他在罗彻斯特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那些与他一样日渐不满的人已经越来越少地关注黑人的宗教。因为不论他是卫理公会教徒还是清教徒,是无神论者还是不可知论者,他都处于同样的困境。”[13](p.13)到1963年,这种世俗化的倾向表现得愈来愈明显。马尔科姆·爱克斯不再仅仅宣传伊斯兰民族组织的教义,而是对现实政治问题发表言论。他对当时的抵制公车、静坐等黑人抗议行动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同时也对以金为代表的民权领袖的非暴力不合作战略提出了批评。马尔科姆·爱克斯认为,民权领袖们期望美国政府通过民权法案解决黑人问题,无异于将受害者交至由罪犯掌握的法庭,结果是问题“绝对不会得到解决”[6](p.53)。他说:“事实已经证明这个政府不能或者不愿意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来保护黑人所关注的生命和财产。”[14](p.22)显然,马尔科姆·爱克斯主张采取比民权运动更为激进的抗争行动。正如他后来在自传中所说的一样,“我在1963年越来越少地谈论宗教,我向穆斯林教徒教授社会教条和当前时事政治,我完全不涉及道德主题”[9](p.336)。不仅如此,马尔科姆·爱克斯的活动也不再仅仅限于传教,开始介入世俗事务。他出席各种有关世俗政治问题的辩论,接受各种采访,针对美国的种族关系问题发表看法。1963年11月,马尔科姆·爱克斯在参加北方草根黑人领袖会议时,还积极倡导全世界有色人种学习万隆会议的精神,求同存异,共同斗争。此外,他还私下与卡斯特罗等第三世界的领袖会谈,讨论有色人种的政治斗争问题。
尽管其世俗化的倾向此时已十分明显,马尔科姆·爱克斯早期形成的宗教观念对他的影响仍旧很深。他依然声称自己是穆罕默德的忠实信徒,必须遵守穆罕默德的规定[13](p.13)。协助其撰写传记的Alex Haley就曾指出,到了60年代初,马尔科姆·爱克斯发现自己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他十分渴望更加积极地对现实政治公开直言;另一方面,他又必须服从穆罕默德不参与政治和宗教化的命令[9](p.244)。正是因为对穆罕默德的服从,马尔科姆·爱克斯在1961年5月24日的哈佛法学院演讲中,反复强调NOI是一个宗教组织而非政治组织[7](p.60)。直到1963年12月在加州大学演讲时,他还是以摩西比喻穆罕默德,称他为“现代摩西”,而且对会议不允许他从宗教角度讨论世俗问题表示不满,说,这“正如让鸟飞翔不用翅膀和让马儿奔跑不用腿一样”[7](p.69)。在行动上,由于受黑人穆斯林“不参与政治”的纪律约束,马尔科姆·爱克斯这时从来就没有真正参与,更没有领导过任何民权斗争。
不过,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马尔科姆·爱克斯思想的成熟,他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行动上开始介入政治斗争,并最终克服了黑人穆斯林的宗教局限。1962年4月,几个黑人穆斯林教徒与洛杉矶警方争执时发生冲突,一名教徒被杀,多人受伤。马尔科姆·爱克斯领导与之开展了坚决的斗争,并计划开展直接的反击报复行动,但是遭到了穆罕默德的阻挠和反对。1962年5月,在美国奥利机场的飞机坠毁事件中,121名白人乘客死亡。马尔科姆·爱克斯听到这一消息后十分高兴,在一次公开集会上宣布:他认为这是安拉为了给洛杉矶事件中死去的穆斯兰兄弟报仇而对白人的一次惩戒。而穆罕默德性丑闻事件则对马尔科姆·爱克斯最终摆脱对穆罕默德的盲从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明确指出:“我感觉自己是个十足的傻子,整天四处传教却对自己眼皮子底下的事情置若罔闻,却不知道在我的组织内包括我一直颂扬的人身上发生了什么。我再次有了哈莱姆犯罪生涯中那种被愚弄和被欺骗的感觉。而这对于一名小混混来说最糟糕的事。”[9](p.296)这使穆罕默德的头上的神圣光环最终黯然失色,马尔科姆开始摆脱对他的依赖进行独立思考和行动。而马尔科姆·爱克斯对肯尼迪总统遇刺事件的评论是其摆脱穆罕默德控制的主要标志。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总统遇刺。穆罕默德规定,所有的穆斯林教长都不要针对遇刺事件发表任何言论。12月,马尔科姆·爱克斯在纽约讲话被问及对遇刺事件的看法时,他公开指出这是“罪有应得”[9](p.347)。结果,马尔科姆·爱克斯被禁言90天。最终,马尔科姆·爱克斯于1964年3月8日公开宣布脱离伊斯兰民族组织。他后来曾对此做出解释说:“因为我们不允许参与政治,我们是政治上的虚无主义者,我们处于宗教的真空中,我们是政治上的虚无主义。我们实际上被隔离了,与所有的活动甚至是我们与之斗争的世界隔离了。我们变成了一种宗教政治混合体,不参与任何行动而只是站在旁边谴责每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不采取任何行动,我们就无法纠正任何事情。”正是这种对穆罕默德禁止伊斯兰民族组织成员参与世俗政治活动的不满,导致了马尔科姆·爱克斯与该组织的决裂。他认为:“那些分裂出去的人是这个运动真正的行动主义者,他们十分有思想,想要找到一种能使我们为西半球所有黑人而战的计划”,“这些人想采取行动。这些人想做些事情来消除黑人面临的罪恶。”[7](p.13)
脱离伊斯兰民族组织后,马尔科姆·爱克斯逐渐将宗教和世俗政治分离,把宗教仅仅作为自己的个人信仰,而把世俗政治视为自己的主要关注所在。在1964年3月8日宣布分离的当天,马尔科姆·爱克斯就召开发布会,宣布他将成立两个新组织,一个世俗政治的组织和一个宗教组织[11](p.299)。他还明确表示将与南方及全国其他地方的民权组织合作。马尔科姆·爱克斯就像他在一次采访中所说的一样,正在努力改变方向[15](p.26)。1964年3月12日,他公开宣布:“我将在纽约组建和领导一个新清真寺……我们的哲学将是黑人民族主义……我们中的很多人没有宗教倾向,所以它将欢迎所有黑人参与我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项目,而不管他们的宗教或非宗教信仰如何。”[6](p.21)这个组织就是他组建的穆斯林清真寺有限公司,该组织看上去是一个宗教团体,实际目标却很世俗化。1964年4月3日在克利夫兰谈到这个组织时,马尔科姆·爱克斯进一步指出:“我们是穆斯林,我们的宗教是伊斯兰,这一点是真的,但是我们不会将我们的宗教与我们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民权运动相混淆。我们的宗教将仅限于我们的清真寺之内。当我们的宗教仪式结束后,那么作为穆斯林的我们将参与到政治、经济、社会和市政工作中去。我们准备随时随地以任何方式与任何仍旧侵害我们社区人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邪恶作斗争。”[6](p.38)
1964年4月13日,马尔科姆·爱克斯启程前往麦加进行朝圣,并最终皈依了逊尼派伊斯兰。这次看似宗教性质的行动却有着很明确的世俗目标。美国学者乔治·布里特曼就曾指出,麦加朝圣是马尔科姆·爱克斯必经的一个阶段,这不仅是要为其追随者提供宗教基础,更重要的是要为马尔科姆·爱克斯开展其他活动铺平道路[15](p.31)。马尔科姆·爱克斯本人也讲得很清楚。他说麦加之行使他认识到:“伊斯兰是真正的兄弟宗教”,“但对兄弟之谊的信奉并不会改变这个事实:我也是一个非洲裔的美国人或者说美国黑人,任何宗教都不能使我无视这个社会中严重的种族问题。”[7](p.81)麦加朝圣后,马尔科姆·爱克斯并未立即返回国内,而是前往非洲,与非洲各国政治领袖会谈,讨论美国黑人的种族压迫问题。
麦加之行使他认识到,穆斯林清真寺有限公司并不是他参与世俗政治活动的合适工具。于是,马尔科姆·爱克斯回国后于1964年6月28日正式组建了非裔美国人统一组织。他后来解释成立该组织的原因时曾指出:“我们意识到在这个社会里我们的问题超越了宗教。正因为如此,我们建立了OAAU,社区中任何人都能参与到旨在使我们黑人作为真正的人类被承认和尊重的计划中来。”[7](p.175)他还说:“我们不再特别关注黑人宗教。因为不论他是一个卫理公会教徒还是清教徒,是一个无神论者还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他都处于同样的困境之中。”[7](p.174)显然,该组织是一个完全世俗化的政治组织,就像马尔科姆·爱克斯在1964年6月24日的公开信中所指出的一样,“它(OAAU)的目的就是将所有非裔美国人和组织围绕人权这个非宗教和非地区性的目标团结起来”[15](p.77)。
三、后期的马尔科姆·爱克斯——具有开阔视野的世俗政治领袖
非裔美国人统一组织的成立标志着马尔科姆·爱克斯世俗化过程的最终完成。他曾明确:“之前我主要是被穆罕默德全权指导,现在我是独立思考。”[6](p.226)宗教也不再在他的生活中占有主导地位,只是个人信仰,甚至是展开政治斗争的工具。1964年秋,马尔科姆·爱克斯在OAAU集会上指出:“任何时候,如果我信仰的宗教禁止我为我的人民而战,那么让它见鬼去吧。那正是我成为一名穆斯林的原因。”[16](p.140)显然,为人民而战的世俗政治已成为马尔科姆·爱克斯的主要关注。
马尔科姆·爱克斯思想的世俗化表现在很多方面。首先,他对美国黑人斗争问题有了全新的认识。在现实斗争的方式上,他不再寄希望于安拉通过神圣干预对白人“恶魔”实施“最后惩罚”,而是倡导黑人积极利用世俗政治斗争的手段获取权利。他虽然仍旧没有放弃暴力斗争的策略,但是采取了比过去更为灵活和现实的态度。他也不再仅仅倡导暴力,而是主张采取“任何必要的手段”[14](pp.20-26)。他还充分肯定了黑人选票的重要性,甚至声言:“在这个国家中穷人唯一真正的权力是选票的权力”[6](p.224),“大量黑人投票将改变政府的国内外政策,因此使美国政策革命化的唯一有效的方法是给予黑人投票权。”[8](p.139)他在“选票还是子弹”的演讲中指出,1964美国大选年是革命性的一年,美国黑人要认真运用自己的选票来获取权利[6](p.38)。为此,他积极主张开展选民登记运动,以保证黑人的选举权利。除此之外,他还“准备支持和组织一些政治俱乐部,推选独立的候选人”。在斗争目标上,他则完全放弃了早期建立独立的黑人“伊斯兰国”的主张,也不再提倡建立独立的黑人国家。在1965年1月19日的一个电视谈话节目中,马尔科姆·爱克斯公开宣布:“我不再相信黑人国家,也不再相信在北美建立一个黑人国家,我相信一个社会,在那里,人们能在平等的基础上,像人一样有尊严地生活。”[6](p.197)
在种族观上,马尔科姆·爱克斯最终摆脱了穆罕默德狭隘教条的限制,开始变得更加灵活、开放、理智和务实。1964年初的麦加朝圣之行对他的种族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说:“我绝没有想到穆斯林世界对我之前的想法有这么巨大的影响——当我一想到它我就感到非常震凉。”[6](p.58)麦加之行使马尔科姆·爱克斯认识到穆罕默德的教条与正宗的伊斯兰信仰是不同的,伊斯兰并不仅仅只属于黑人,白人也并不全是所谓的“恶魔”。1964年4月20日,在苏丹的来信中,他具体描述了麦加之行对他的影响和震撼:“那里有数以万计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朝圣者。他们是各种肤色的人,从蓝眼金发到深肤色的亚洲人,但是所有人都参加同样的仪式,展示了团结精神和兄弟之情,而据我的美国经验这在白人和非白人之间是绝不可能存在的。”[6](p.59)马尔科姆·爱克斯在这段时间抛弃了早期敌视所有白人的极端主义态度,不再简单地以种族和肤色作为判断依据。他明确指出:“我相信《古兰经》的教导,一个人不应该按照他的肤色而应根据他的行为,即他对待别人的态度和行动来判断好坏。”[4](p.186)他甚至还进行自我批评:“我过去常常谴责所有白人,可能对一些真诚的白人带来伤害。麦加朝圣使我的精神得到新生,我将谨慎地不谴责任何白人,除非他被证实有罪。”[6](p.58)他开始把白人个体和白人整体区别开来,尽管他依然认为白人作为一个集体对黑人实行了奴役和剥削,但开始承认白人中有些普通大众是善良的。在1964年5月朝圣归来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马尔科姆·爱克斯明确指出,他不再认为所有的白人都是恶魔[9](p.474)。不仅如此,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认可白人参与解决黑人问题。他说:“我们将与任何人、任何群体合作,无论他们的肤色如何,只要他们对采取必要的方法来结束这个国家强加于黑人的不正义真正怀有的兴趣。”[6](p.70)马尔科姆甚至完全摆脱了宗教限制而从美国种族主义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结构中寻找黑人遭受苦难的根源。他认为,美国的资本主义体系决定了种族主义必然存在,只有革命现存的体系才能实现黑人独立和自由。用他的话来说,“这个国家的体系不可能给予美国的非裔人自由。这个国家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体系注定了这不可能实现……如果一只鸡孵出了一个鸭蛋,那它肯定是一只已经革命了的鸡”[6](p.69)。
在对黑人民权领袖的态度上,马尔科姆·爱克斯也一改往日的激烈,主张与一切黑人组织合作,大力倡导黑人团结。他在“选票还是子弹”的演讲中就明确提出:“不论我们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教徒,是民族主义者还是不可知论者或者无神论者,我们必须首先学会放弃我们的不同。”[6](p.25)在1964年12月的讲话中,他更进一步指出:“我认为我们人民的领导者浪费时间彼此争斗毫无意义。我认为,我们如果可以私下里坐下来并消除可能存在的不同然后做一些有益于我们人民的事情,那么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7](p.87)对于金等人的非暴力策略,马尔科姆·爱克斯也不再一味地反对,而是给予一定的认同:“我非常尊敬那些敢于把自己的手捆起来然后走向大街任由暴徒对他施暴的人……并且我不建议谴责COFO和SNCC……我没有批评你或者谴责你,但是我质疑你的策略。我正在质疑你的策略。”[7](p.208)但是,他仍旧反对民权主义者以种族融合为最终目标。他认为融合仅仅是获取黑人自由的一种方法而非最终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马尔科姆·爱克斯思想的世俗化具有视野开阔的特点。和当时很多美国黑人民权领袖不同之处在于,他不是仅仅着眼于美国黑人的公民权,而是追求世界各个种族的普遍人权。1964年3月与伊斯兰民族组织决裂以后,马尔科姆·爱克斯就开始反复强调黑人的人权。他明确提出,我们需要将民权斗争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人权的层次,“我们正为被承认作真正的人而战,我们正为自由人的生存而战。事实上,我们为之斗争的权利远远大于民权,那就是人权”[6](p.51)。在他眼中,美国的黑人问题不仅仅超越了宗教的范畴,而且超越了地域和种族的限制。他认为,美国的黑人问题不仅仅是美国的内政问题,而且是整个第三世界人民的问题。在非洲统一组织的首脑峰会上,马尔科姆·爱克斯指出:“我们的问题就是你们的问题。它不是一个黑人问题,也不是一个美国问题,而是一个全世界的问题,一个全人类的问题。它不是一个民权问题而是一个人权问题。”[6](p.76)马尔科姆·爱克斯认为,黑人不属于美国的公民范畴,而是全世界有色人种的一部分,是全世界殖民地人民的一部分,因为美国对黑人的统治是殖民统治而非政府对公民的正常管理。他公开宣称:“美国是一个殖民国家……是一个20世纪的殖民国家,它是一个现代殖民势力,它一直在殖民2200万美国非裔人”,其实质是“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14](pp.16~18)同时,马尔科姆还努力促使美国黑人的斗争超越美国现有体制,实现国际化。早在麦加之行访问尼日利亚时,他就提出将美国黑人问题提交联合国国际法庭的必要性,并强调了美国黑人成为泛非主义者的必要性。在他访问加纳时,其泛非主义思想进一步发展,他认为加纳的成功是泛非主义的表现,是加维设想的实现。他与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加纳许多权威人士、学生、非洲裔美国人流亡者、中国等国的驻加纳大使会面,讨论第三世界人民的斗争问题。马尔科姆·爱克斯呼吁全世界所有被压迫、被剥削的有色人种团结起来,一致反对欧美等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他大力倡导“泛非主义”。在1964年5月的非洲之行中,马尔科姆·爱克瓶就热情地宣扬:“正像美国犹太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与世界犹太主义者联系在一起一样,非裔美国人成为世界泛非主义的一部分的时刻来到了,即使我们的身体可以留在美国,……我们也必须从哲学和文化上回归非洲并且在一个泛非主义的框架内发展紧密团结的合作关系。”[6](p.63)
马尔科姆·爱克斯思想的世俗化导致他在自己生命的后期几乎完全投身于美国和世界范围内的政治斗争。非裔美国人组织成立不久,马尔科姆·爱克斯即于1964年7月再次前往非洲各国访问。在这次历时数月的外国之行中,他与纳赛尔等多位非洲国家领袖、多国大使以及当地的有色人种领袖讨论非洲裔黑人以及反殖民斗争问题。每到一处,他总是争取一切机会发表演说,努力获得各国人民对美国黑人斗争的国际支持。同年7月7-21日,马尔科姆·爱克斯还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非洲统一组织(the 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首脑峰会。他向大会提交了长达8页的备忘录,陈述美国黑人的悲惨遭遇,大力呼吁非洲国家将美国黑人问题提交联合国大会讨论。他明确指出:“我们在美国的这些人是你们长期走失的兄弟姐妹,我来这里只是想提醒你我们的问题就是你们的问题……为了世界的和平和安全,我恳请非洲独立国家的领袖们提议让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立即对我们的问题进行调查。”[6](p.77)不仅如此,马尔科姆·爱克斯还极力反对美国干涉非洲国家的内政,反对越南战争。在国内,马尔科姆·爱克斯此时与著名民权领袖詹姆斯·法默交往甚密,与金也多次通话探讨黑人斗争问题,在临终前还在努力争取与金当面会谈。马尔科姆·爱克斯甚至亲身参与了南方的民权运动。1965年2月,马尔科姆·爱克斯应SNCC(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之邀,在亚拉巴马州的塞尔玛对年轻的民权主义者做了一次演讲,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总之,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行动来看,后期的马尔科姆·爱克斯已经完全世俗化。美国学者Truman Nelson就认为马尔科姆·爱克斯在两次外国之行后开始获得自我重生,他有了一种新的目标和一种新的政治斗争形式,开始作为革命大众的一员讲话[17]。应该说,马尔科姆·爱克斯的世俗化过程就是他本人成熟和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马尔科姆·爱克斯首先认识到自己原有宗教思想的狭隘性和局限性,继而努力摆脱它的束缚,而最终超越了宗教的限制,成为一名世俗的政治领袖。正是在摆脱了这种狭隘宗教意识的限制后,马尔科姆·爱克斯才最终实现了思想上的飞跃。于是,乔治·布里特曼称赞他是人民解放道路上的革命国际主义者[15](p.39)。布鲁斯·佩里则认为马尔科姆·爱克斯最后成了一位反帝国主义者和反资本主义者,其视野和行动从民族解放斗争扩展到了在全世界为被压迫的人民争取人权的更为广泛的国际主义目标。他称马尔科姆·爱克斯为二战后美国工人阶级中出现的致力于世界革命的杰出代表[7](p.11)。总而言之,马尔科姆·爱克斯后期的世俗化使他的思想超越了当时民权运动的范畴,瞩目于更为远大的目标,从而对当时和此后的黑人斗争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
【收稿日期】2010-07-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