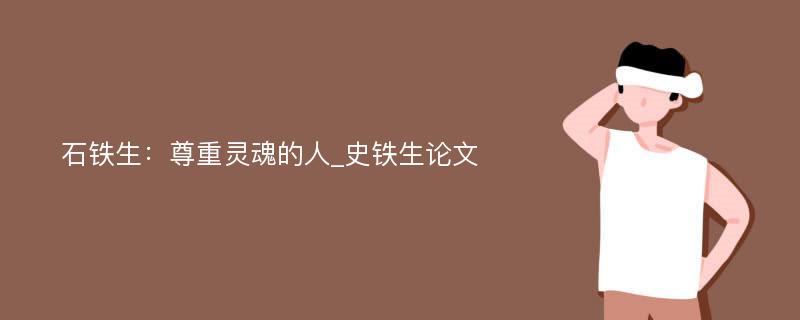
史铁生:一个尊灵魂的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的人论文,灵魂论文,史铁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凌晨三点四十六分,作家史铁生因脑溢血在北京去世。之后一些天,对他的思念和缅怀,一直在网络、报纸和各地自发举办的烛光追思会中蔓延。我从未见过一个当代作家,生前能在读者当中获得如此纯粹的声誉,死后又能在民众当中引发如此浩大的伤怀之情。
我知道这个不幸消息的时候,一个人在沙发上默想了很久,我说不出来是难过还是不舍。我随后编写好了一个短信,准备发给史铁生的夫人陈希米女士,但犹豫许久,还是放弃了。我想,她一定在忙乱着,而且史铁生似乎也不需要这些。他这样一个通达、智慧的人,早已了悟生死,死亡这“必然会降临的节日”,何时来,是以什么方式来,其实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充分向我们展示出了他的灿烂人格——无论他敏锐、深邃的文字,还是他宁静、宽厚的为人,都在述说一个人如何才能有尊严地活着,并如何把自己带到一个高度。
这个高度,是史铁生用文字建构起来的,也是他那种有精神体量的生存所抵达的地方。他给我说过,他喜欢读思想和哲学著作,这决定他的写作,既关注现世,也关注永恒,无论小说,还是散文,他总是持续地在思索人的存在如何才能获得意义的确认。他害怕自己走失,他正视自己的迷茫,并不断地向时间发问,也不掩饰自己渴望获得终极意义上的救援——事实上,唯一能帮助他的只是他自己的思索。他的思索,不像其他一些思想者那样干枯,而是保留了一个作家的感性,甚至他还模仿宗教语体,在作品中用了许多比喻,从而使他的文字散发着浓郁的人间气息。所以,我这几天重读他的著作,感觉他并未离去,他所深思的那些问题,和每一个人都如此切近,且从未过时。我想,只要语言的交流在继续,肉身的隔绝就并不重要,正如我第一次见他是在十年前,这十年来,我们只是偶尔联系、见面,更多的时候,我是在他的文字中与他交谈,但我对他从未有任何的陌生感。所谓的超越性,这也是其中一种吧。
肉身的死亡,“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他并不避讳这点。甚至,死亡对他而言,也未尝不是一种解脱。我见过他做透析时的辛苦,写作的艰难就更是可以想象了。他的生命,似乎是不完整的,时间仿佛也是切碎的——他所能享受的,不过是其中很小的一块。所以,他说自己职业在生病,业余是写作。他活着,照常人看来,就是磨难。疾病、残缺,坐着轮椅频繁往返于医院,身体在快速恶化,死亡的邀约已经发出多次,奇怪的是,我每次见到他,他总是温和地笑着。他的眼神里,传递的从来不是虚无、抱怨,而是相信——相信生命,也相信生命展开的过程。
许多人活着是关心结果,而史铁生看重的是过程。他认为,对付绝境的唯一办法就是重视过程。“一个只想使过程精彩的人是无法被剥夺的,因为死神也无法将一个精彩的过程变成不精彩的过程,因为坏运也无法阻挡你去创造一个精彩的过程,相反你可以把死亡也变成一个精彩的过程,相反坏运更利于你去创造精彩的过程。”“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你能创造这过程的美好与精彩,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你能够镇静而又激动地欣赏这过程的美丽与悲壮。”——在二○一○年的最后一天,这个过程似乎已经结束,但当我看到许多人在烛光追思会中举着史铁生的照片时,我强烈地觉得,肉身的寂灭,不过是一个影儿,灵魂的存在如此真实,它确定是在以别的方式延续着。
过程在到处继续,在人间、在天堂、在地狱——史铁生说这话的时候,是在人间,如今他不过是换了一种存在方式吧;他去了天堂,但我们仍然能在文字中听到他的低语、沉吟。
我把他的书从书架里找出来。其中有一本《灵魂的事》,是我应约帮他挑选篇目并拟定书名的。灵魂的事,对于别的作家而言,或许是一种虚妄,但对史铁生,就不过是他自身的经验而已。因着长年困守于轮椅,空间的延展极度受限,他只能向内心进发,向时间索要生命的意义。“左右苍茫时,总也得有条路走,这路又不能再用腿去趟,便用笔去找。”写作是为了找路,救赎之路,通往内心之路,但在前行的路上,他又不是只重虚无和玄思,直奔彼岸,而是时刻意识到还有一个沉重的肉身——看见此岸的残缺、肉身的苦难,正视人的有限性,才能默想无限和永远。史铁生有一首诗,题目就叫《永在》:我一直要活到我能够/坦然赴死,你能够/坦然送我离开,此前/死与你我毫不相干。/……/此后,死不过是一次迁徙/永恒复返,现在被/未来替换,是度过中的/音符,或永在的一个回旋。
核心的问题,就是:在。如何在?何为永在?经过《我与地坛》的自我省思,《务虚笔记》的深沉思辨,到《病隙碎笔》,它把史铁生的存在之思推向了一个高峰。这本书曾经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二○○二年度杰出成就奖”,它的厚重、深刻、警觉,以及对人生和世界的通透观察,我和评委们都曾为之深深折服。它有力地证明,史铁生不仅是一个文学家,也是一个思想家,更是一个有大质量心灵的人。我当时为他写的授奖辞是:
史铁生是当代中国最令人敬佩的作家之一。他的写作与他的生命完全同构在了一起,在自己的“写作之夜”,史铁生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他睿智的言辞,照亮的反而是我们日益幽暗的内心。他的《病隙碎笔》作为二○○二年度中国文学最为重要的收获,一如既往地思考着生与死、残缺与爱情、苦难与信仰、写作与艺术等重大问题,并解答了“我”如何在场、如何活出意义来这些普遍性的精神难题。当多数作家在消费主义时代里放弃面对人的基本状况时,史铁生却居住在自己的内心,仍旧苦苦追索人之为人的价值和光辉,仍旧坚定地向存在的荒凉地带进发,坚定地与未明事物作斗争,这种勇气和执著,深深地唤起了我们对自身所处境遇的警醒和关怀。
确实,他是当代少有的能把灵魂的力量展示出来的作家。他的写作,是有重量的,有方向的。比起当下许多作家的肤浅和轻佻,你会感觉史铁生和他们完全不在一个世界,甚至不像是同一个人类。《病隙碎笔》作为单篇随笔,在刊物上陆续发表时,当时并未引起多少人的注意,这些思想的碎片,指向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精神疑难,也是作家对自我的一次透彻认知,但真正对他的心语有响应者,寥寥可数。所以,他一直在倾听,在追问,内心的忧思却从未释然过。史铁生说,“作家应该贡献自己的迷途”,看得出,他的内心还有矛盾,文字中也一直背负着重担,他不愿轻易地和现世和解,而是通过一种对有限性、残缺性的省思,为人的存在如何朝向无限和不朽发出了坚定的吁求。
他是一个有自己的写作母题的作家。在他的眼中,书写那些“主要的真实”,才是唯一值得用力的,是任何别的俗世安慰所不能代替的。他为了企及这个写作目标,甚至有意采取了一种带有先锋色彩的叙事探索,而并不在意读者的阅读习惯,尤其是他的两部长篇小说,思力深厚,那种无处不在的超验之问,充满心灵的冒险,也充满诗意。他的语式和时下流行的文学也是不同的,他是在自我追问,也是在寻找一条切近精神本体的道路,进而确证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及其救赎方式。我非常着迷于他所创造的文学世界,但我也知道,他的方式往往是孤寂的,是一般人所难以理解的。上一届茅盾文学奖终评时,很多人都感叹《我的丁一之旅》读不懂——他们只关注小说的趣味性和可读性,而从未想过为史铁生式的精神冥思留一个空间。现在,这个奖将永远错过史铁生了!
我忽然想起,二○○三年非典时期,史铁生来广州领奖,戴着几层口罩,行动不便,身体受苦,甚至在广州的几天时间,他还曾去医院做了一次透析,可他仍然客气地面对每个来访的人,安详而宁静。他上台领奖时,那么多双手不约而同地抬起他的轮椅,场面极为感人,那些在台下注视他的眼神,也都饱含钦佩和痛惜。他这样一个时刻面临死亡威胁的人,却用自己的文字,见证了自己坚韧的生、有幸福感的活着。
在今天这个庸常、实利、娱乐化的时代,我们或许能记住一个作家的文字,但很难在文字中遇见一个作家的人格,更难辨识出这种人格的光辉。史铁生是少数的例外。
他是中国当代最关注内心的磨难,进而到达了一种深渊境遇的作家。他的作品,几乎每篇都带着他的生命体验,也贯注着他的诘问和迷思;通过写作,他拥有了获救之舌,并成功地为自己的心灵创造了一个居所。他是一个真正有灵魂、也是尊灵魂的大作家,他的去世,为中国当代文学写下了悲伤而令人心痛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