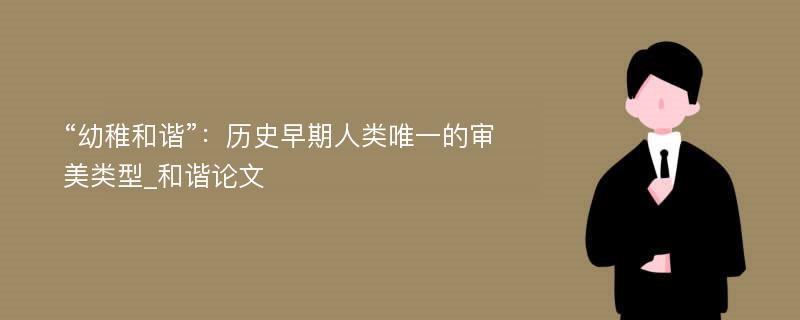
“稚拙的和谐”:史前期人类惟一的审美类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稚拙论文,史前论文,惟一论文,人类论文,和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审美的发生,至今仍是一个不易言说但却又十分诱人的课题。当我们看到山东大汶口出土的那把均衡滢润的玉斧、仰韶文化的舞蹈彩盆、马家窑文化的尖底瓶以及半山类型的涡纹壶和马厂类型的变体蛙纹壶;当我们读到“击石拊石,百兽率舞”①、“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②等记载;当我们仿佛听到“候人兮猗”③那样一声哀婉的歌声,我们的心底总是要发生震颤,我们总是要产生一种探究远古人类审美活动的渴望,我们总是企图对这远古时代遗留下来的至今仍闪耀着美的光芒的事物说出点什么。事实上很多人也已经说出了点什么或者正在说。然而——
审美是人的意识活动。意识是人脑的机能。远古人类的意识,早已随着他们大脑的消失而消失了。人类意识的真正起源问题已经或正在使思维科学的研究者们大伤脑筋。我们只能凭借少得可怜的出土物以及古书上的只言片语再加上人类的理性思维,来对远古人类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起源进行“合理”的推测。但这种推测的合理性到底有多少,连我们自己都心中无底。
尽管如此,由于远古人类创造的独特的美深深地吸引住了我们,所以我们还是要说。虽然我们不可能达到绝对的真理,但却可以接近它。
许多学者从审美发生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史前期人类的审美,有“崇高”(或曰“神秘的崇高”)与“和谐”两种类型。笔者不赞同这种观点。笔者认为,起源意义上(史前期)的人类审美,只有“和谐”这一种类型,并无“崇高”这种类型。下面请听其详:
首先,我们要了解“崇高”这一美学范畴的内涵。“崇高”这一范畴最早是由古罗马的朗加纳斯在《论崇高》中提出来的。他从修辞学的角度,认为崇高体现于一种“措词的高妙之中”。以后,十八世纪英国经验主义者博克,德国古典美学家康德和黑格尔,以及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都对“崇高”进行过论述。其中,博克提出的崇高感是由痛苦或恐惧感转化而来的愉悦感(快感)的观点,道出了崇高感的最本质的特征,也是本文立论的基石。
博克认为,人的所有情感都可以归结为两大类,即自我保全的情感和社会生活的情感。前一类情感,主要与危险和痛苦相关。由于这危险和痛苦与人隔着一定的距离,不能现实地加害于人,于是这种危险和痛苦感就转化为快感。这就是崇高感④。
在自然史上,当第一只猿手敲出第一把石刀,这只猿类的手就变成了人类的手,人类诞生了,人类的意识也就萌芽了。人类虽然诞生了,但却经历了一个极其漫长的苦难的“童年”。在人类的童年时代,由于生产力的极其低下,原始初民在自然力的压迫下痛苦地挣扎。现实在当时无疑是十分可怕的,周围是一个充满神秘力量、充满敌意的世界,似乎每时每刻都可能发生毁灭性的灾难。当时,一切可带来危险的对象无疑都会使原始初民感到恐惧、颤栗。而由于当时人类的思维尚不能把握自然,所以他们还不可能认识到危险的对象与自己的距离。弗雷泽曾把原始巫术分为“顺势巫术”(“模拟巫术”)和“接触巫术”两大类。这两类巫术又可统称为“交感巫术”。两者都认为物体通过某种神秘的交感可以远距离地相互作用,通过一种看不见的“以太”把一物体的推动力传输给另一物体⑤。这就是说,在原始人的思维里,想象与现实是混沌同一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一个东非洲苏法拉地方的卡福人,宁愿受粗木棍或铁棍的痛击,而不愿让诸如芦苇稻草之类空心的东西打到身上,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一个人被空心的东西打过,他的内脏就会萎缩直至死亡⑥。
因此,危险的对象即使在现代人看来不可能对人构成现实的伤害,但在原始人那里,却被认为是实实在在的危险。更何况在人类的童年时期,大自然还频频暴虐地对人类施加现实的伤害呢?洪水猛兽、饥馑瘟疫,时刻都有可能夺走他们的生命,甚至危及他们的种族。所以,在原始初民那里,危险感还不可能转化为快感,危险的对象也不可能转化为被欣赏的、能使人产生间接快感的崇高的对象,它只单纯地引起一种畏惧感,一种惟恐避之而不及的恐怖感。
按照博克的理论,人的第二类情感,即社会生活的情感,主要与爱联系在一起,所产生的是积极的快感,也就是美感。博克所理解的“社会生活”是狭义的,只涉及生理要求或本能方面,它包括异性间的性欲和一般人与人之间的社交要求。但他所说的美感是由爱而引起的一种积极的快感,却是深刻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需要分为三个层次,即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发展需要。在人类发展的高级阶段,这三种需要同时并存,这就决定了人的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并不仅仅局限于单纯的生理要求或本能方面。然而,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原始社会,人的需要则主要体现为生存需要,包括维持自身生存的需要(求食的需要)和维持种族生存的需要(性的需要)。这两种需要是人从猿类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生理本能,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所谓“食、色,性也”⑦;“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⑧,就是这个意思。
日本著名汉学家笠原仲二在《古代中国人的美意识》一书中认为,中国人原初的美意识最早起源于美食和“美色”引起的官能快感。著名的“羊大为美”的观点是众所周知的。笠原仲二通过对中国古文字的考察,证明在古代“美”与“甘”通训,而“甘”的初文作为口中含有美食的形状。他还考察了古代的“色”字,认为“色”的原初意义是“男女交媾”(“色”的初文字形是人在人上,表示男女性器相合),并进而引伸为“性欲”和由此体验出来的美的感受。
笠原仲二的见解是独到的。在灾难深重的原始社会,大自然使原始人感到恐惧和不安,但在求生存的斗争中,当他们啖食甘美的食物,或者性欲得到满足时,最容易产生一种舒适愉悦的感觉,而这种官能的愉悦感就是人类美感的来源。
问题在于,这种生理的愉悦感究竟与动物的生理快感有何区别?或者换句话说,这种动物性的官能快感上升为只有人类才有的美感的标志是什么?
我们知道,由猿到人的转变,其转折性的标志是制造工具。工具是人手的延长,学会了制造工具,无疑大大地扩展了原始人的食物来源。人类最初制造的工具,并不是为了审美,而是为了实用。制造成对称、均衡、光滑的石器总是表现出更大的实用价值,能给原始人带来更多的食物。渐渐地,对称、均衡、光滑等美的形式韵律就在原始人对食物的餍足之后获得了独立。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人类学和进化学的研究则证明,制造工具对于人的生命意义再重大,也很少给人的自身生产的生理过程带来影响,制造工具前的猿的性的生理过程与制造工具后的人的性的生理过程,并没有质的不同(即使是量的变化也是微不足道的)。那么,性的生理快感是怎样上升为美感的呢?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从制造工具这个基本历史事实出发。
恩格斯指出,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⑨人和动物的基本差别之一就是能不能从事劳动,而“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⑩以制造工具为前提的人类劳动,促使人类语言的产生,在语言和劳动的推动下,古猿的脑髓开始转变为人的脑髓,从而促使古猿的心理不断地发生变化,最后变为人类的意识。只有人类意识产生了,人类对性的追求才超出简单的本能性的发泄,而上升为一种对象性的审美行为。
至此,我们已经说明了人类的审美意识来源于“社会生活”方面的情感,更具体地说,来源于“食”、“色”所引起的生理快感。我们也阐明了起源意义上的审美,不可能产生来源于“自我保全”方面情感的崇高感。也就是说,在人类审美的发生时期,只有产生积极快感的“美”这一类型,并没有由引起痛感的对象转化而来的“崇高”这一类型。而在审美的起源时期,美感实质上即是一种和谐感。因为对原始人来说,他们所感觉到的、意识到的世界是狭小的、封闭的、在这个狭小,封闭的世界里,一切能引起他们的快感、并进而上升为美感的对象,对他们来说都是一种和谐的对象,否则就是一种异己的,不和谐的、让人恐怖的对象。《尚书·舜典》中关于“神人以和”、“八音克谐”的观点,可以说是对远古人类美学思想中关于“和谐”观念的最早概述。古希腊自然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等人所表述过的美在于“和谐”的思想,也显然与史前人类素朴的“和谐”观有着历史的联系。
黑格尔在《美学》中把人类史前期的艺术称之为“艺术前的艺术”,归入他所谓的“象征型”艺术。他认为,象征型艺术的特征在于“观念还没有在它本身中找到所要的形式,所以还只是对形式的挣扎和希求”(11)。黑格尔的论述是神秘的,但见解是深刻的。就是说,史前期的艺术形式是粗糙的、不完善的,观念还受到自然材料的束缚,好象是勉强粘附在对象上的,这无疑是十分稚拙的。因此,上面所论述的审美发生时期的惟一的审美类型——和谐,前面应该还要加上一个定语,从而成为:“稚拙的和谐”。
注释:
①《尚书·益稷》。
②《吕氏春秋·古乐》。
③《吕氏春秋·音初》。
④参见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第236-237页。
⑤⑥《金枝》上卷第19-21页、第50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6月版。
⑦《孟子·告子上》。
⑧《礼记·礼运》。
⑨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08、513页。
⑩黑格尔《美学》第1卷第95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1月版。
标签:和谐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