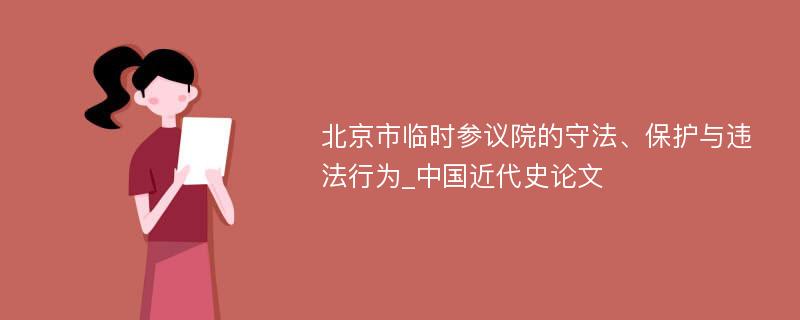
北京临时参议院的遵法、护法与违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参议院论文,护法论文,北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北京临时参议院(1912年4月~1913年4月)作为具有临时国会性质的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在民国初年的政治斗争和立法建制中均扮演着重要角色。而其本身既为遵行法律法规,维护法律尊严进行了积极的努力,亦有未能严格依法行事甚至违反法律法规的不光彩的记录。
北京临时参议院在日常的议事活动中,总的来说是认真遵守有关法律法规,非常注意依法行事的,并为维护法律的尊严,对袁世凯政府的某些违法行为进行了抵制和斗争。
首先,参议院言必称法律,行必引法规,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临时参议院每次议事,如届规定的散会时间而议题尚未讨论完毕,①议长欲继续讨论,均须请议员就是否延长会议时间(多数情况下是延长10分钟)进行表决,待多数同意后方继续开会。
1912年8月中旬,参议院接四川省议会来电称:因蒲殿俊等川籍议员已辞职,补选邓镕为临时参议院议员,邓镕时已在京,请参议院促其赴院。在8月14日的会议上,秘书宣读此电后,即有议员提出,邓镕现为内务部某科科长,依法行政官不得兼任议员。待此情况得到证实后,议长宣布,根据《参议院法》第5条关于“现任行政职员及现任司法职员”不得为参议员的规定,致电四川省议会,说明其对邓镕的选举无效。②
当晚,参议院收到邓镕的来信,称已于本月初辞去在内务部的官职。但参议院致四川省议会的电报业已发出。在8月15日的会议上,议长说明这一情况,经讨论决定,再次致电四川省议会,说明“据邓镕来信,谓行政官已经辞职,现本院正在调查,请其暂缓改选”;同时致函内务部,查询邓镕“是否业经辞职”。③至8月19日,参议院接到内务部的复文,谓邓已于8月3日辞职。④参议院于是通知邓镕8月20日到院与会。⑤
以上两事,北京临时参议院依法行事的精神可见一斑。而且,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严格依法行事,临时参议院还对袁世凯及北京临时政府某些违反或破坏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了抵制和斗争。⑥
北京临时参议院第一次会议的第一件议案,为《大总统咨请将官制通则内务部加次长一人案》。在5月4日的会议上,此案一经宣布,立即遭到众多议员的指责。阮庆澜指责此案“在法律上已不正当”;王振尧则提出,此案为“不照法律之交议”,不能成立,不予交付审查。⑦
为何袁世凯的这一提案受到违法的指责,这还要从南京临时参议院时期说起。3月12日,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各部官制通则》,其中规定,中央政府设10个部,每部设总长一人,次长一人,⑧并于当日电告袁世凯。⑨这是刚刚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组织新的政府的主要法律依据。但袁世凯在随后提交南京临时参议院的组建临时政府方案中,设置了12个部,违反了《各部官制通则》的规定。南京临时参议院3月15日复电袁世凯,重申《各部官制通则》的规定,指出其“拟派国务员与原案员数不符,未便遽付同意,仍请按照本院议决原案所设十部”提出国务员名单,交本院同意。⑩尔后,袁世凯重新提出10部总长人选,交由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表决中交通总长梁如浩未获通过,由总理唐绍仪代理),新的临时政府组成。但在4月9日,袁世凯以大总统令,任命张元奇、荣勋二人为内务部次长,(11)再次违反《各部官制通则》的规定。据称,其原因是原理藩部事宜归并入内务部,“事务既属殷繁,而蒙藏事宜尤非有特别历练之人不足以资熟手,故遂定设二次长,而以久于理藩部之荣勋分任一席,俾其专理边事”。(12)此时南京临时参议院已经休会,待临时参议院北迁重新开会后,袁世凯遂提出这一“咨请”,以使其任命合法化。但袁世凯此项任命已违法在前,“咨请”实属“先斩后奏”,故引起参议员的纷纷指责。虽有议员提出此案违法,不予交付审查,但《参议院法》第39条规定:“政府提出之议案,非经委员会审查不得议决”。(13)为遵守这一规定,参议院仍决定将此案交付法制委员会审查。(14)
在5月8日的参议院会议上,法制委员会提出审查报告。审查报告将此“咨请”改称为《大总统交议修改官制通则案》,否决了袁世凯关于内务部增设一次长的要求,而提出另设一蒙藏事务局。法制委员会委员长张耀曾对审查报告做进一步的说明称:一部设两次长并非绝对不可,“但政府并未分明事务权限……事实上亦并未将蒙藏事务专划归于该次长管理。即该次长专管蒙藏事务,亦必增设蒙务司、藏务司等附属机关。如此则有各司、各科专办蒙藏事宜,即一次长已足辅佐总长,又何必再增设一次长”?而鉴于“蒙藏之文化上、经济上、教育上均不能遽与内地同等,必施以积极政策,以发展蒙藏之事务”,故决定另设蒙藏事务局,直隶国务总理,专司蒙藏事务。审查报告获多数通过。(15)
这是北京临时参议院与袁世凯政府不遵守法制行为的第一次较量。这里的关键不是袁世凯提出的议案有多少道理,而是北京临时参议院要严格遵照法律的规定行事。北京临时参议院依法行事,否决了袁世凯的违法行为,维护了法制的尊严,同时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对行政机构做了调整,既合情理,又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行事,是值得肯定的。
如果说临时参议院这次成功地维护了法律的尊严,那么,围绕张振武案,北京临时参议院对袁世凯及北京政府违法杀人行为的斗争则以失败告终。
8月15日,袁世凯与黎元洪相互勾结,逮捕并随即枪杀了武昌首义的革命党人张振武。这是民国以来袁世凯政府第一次公开违法杀人,引起全国上下的极大震动。北京临时参议院对此事极为关注。8月18日,由参议院鄂籍议员张伯烈领衔,刘成禺、郑万瞻等19人联署,提出《质问政府枪杀武昌首义将领张振武案》。8月19日,参议院破例讨论此质问案(质问案可直接咨送政府,无须经参议院会议讨论)。刘成禺首先发言称:《临时约法》载明,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张振武“既为中华民国之人民,即应享有中华民国人民之权利”,即使罪有应得,亦应捕送审判厅,公开审问,而不能“星夜邀袭,旋捕旋杀”,政府此行为“违背约法”。刘彦认为,“此事体重大,质问恐无效力。不如提出弹劾案,以尽本院保护人民之责”。随后有多人发言亦主张弹劾,并提出不但应弹劾副署袁世凯杀张命令的陆军总长,还应弹劾国务总理与副总统。但《临时约法》规定,弹劾国务员须有参议院“总员四分三以上之出席,出席员三分二以上之可决”,(16)当日出席人数不足约法的规定。议长不得不宣布,“今日限于出席人数,不能表决”,只能要求政府二日内对质问书给予答复,待政府答复不能满意时,再提出弹劾案。(17)
明明是大总统袁世凯下令捕杀张振武,但在参议院一个多小时的讨论中,虽亦有不少激烈言论,但无一人提出应弹劾真正的罪魁袁世凯。从表面上看,当时实行的是责任内阁制,总统对政府行为不负责任,且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只有当大总统“有谋叛行为时”,参议院才可实行弹劾。擅杀首义功臣,问题固然严重,但似乎尚未达到“谋叛”的程度。不过,这都不是不能对袁世凯提出弹劾的真正理由。袁世凯下令捕杀张振武,这实质上是一个政治行为,而非简单的违法问题。而参议院不敢提出弹劾袁世凯,实际上也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不敢和袁世凯决裂,而以法律程序上的问题,来掩饰这种怯懦的心理。(18)用参议员彭允彝的话来说,“政府虽不遵守法律,本院必须遵守法律”。(19)结果是守法的参议院制约不了违法的袁世凯。
8月23日,陆军总长段祺瑞到参议院回答质问。段祺瑞的答复吞吞吐吐,故弄玄虚,称此案“关系民国共和前途甚大,不得不如此办法”;各国公使馆近在咫尺,“恐稍有迟缓贻祸非浅”;而当参议员的追问无法回避时,段即以此案有“关系秘密的地方,此时未便即行宣布”,“政府不能不如此举动……许多话一时不便说明”等等搪塞。议员的质问最后集中于杀人是否合法,称:参议院不问其人其罪是否应杀,“杀人之事,则必要依据法律”,即使张振武应杀,政府“是否应依据法律而杀之”?段祺瑞答道:“现在政府以国家为前提,自不能不以临时之办法,不然于国家大有危险……手续虽有错误,祺瑞身当其咎亦未为不可”。有议员提议,陆军总长既已认错,能原谅政府则无须再诘问,不能原谅,即行弹劾。于是质问结束,段祺瑞退席。(20)
问题拖至8月28日,由张伯烈、刘成禺等12人提出《弹劾国务总理、陆军总长案》。该案把袁世凯不经审判,捕杀张振武的违法行为,归罪于国务总理与陆军总长“辅佐乖谬”,“陷临时大总统于违法地位”,要求免去二人职务。但由于袁世凯的暗中运动,临时参议院几次开会,出席人数均达不到《临时约法》所规定的讨论弹劾案须,“总员四分三以上”出席的要求,此弹劾案终未能讨论通过。拖延既久,此事遂不了了之。参议院此次维护《临时约法》的努力归于失败。
此时的袁世凯,名义上是中华民国的临时总统,实际上是意欲实行专制独裁统治的军阀、官僚,脑子里并没有民主共和思想和依法行事的理念,更不想接受《临时约法》的制约。在这样一个手握重兵,控制着中央政权的军阀、官僚面前,活现出法律的无奈。
北京临时参议院在其议事活动中,也曾出现某些未能遵守法律规定,甚至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况。
在审议一件比较特殊的法律案——《修改约法青海为西蒙古并增加议员案》的过程中,参议院对《临时约法》中关于出席人数的理解有误,并导致出现违反此项法律规定的情况。
《临时约法》第55条规定:“本约法由参议院参议员三分二以上,或临时大总统之提议,经参议员五分四以上之出席,出席员四分三之可决,得增修之。”在5月4日参议院第一次会议上,第3项议程为审议《修改约法青海为西蒙古并增加议员案》。此为大总统交议案。当议长宣布开议第3项议案后,即有议员询问此时参议员是否在《临时约法》规定的4/5以上,议长答称:“出席六十八人,报到者八十人,已在五分四以上”,(21)于是请政府特派员说明此案提出理由。此议案主要内容是将青海、科布多、旧土尔扈特等处改称西蒙古,选派参议员5名;唐努乌梁海附于外蒙古,阿拉善、额济纳附于内蒙古,并相应修改《临时约法》中的有关规定。此议案于南京临时参议院时期即已提出并经审查会两次审查,但由于内容重大且牵涉复杂的历史沿革及民族问题,“均未能深悉底蕴”,故决定待迁至北京后与蒙古议员详细计议后再继续审议。这次参议院会议在听取政府特派员的说明后,决定将此议案交付特别审查。(22)
此后,此议案经特别审查会4次开会审查,又经参议院第9次会议听取审查报告,第10、14、40次会议二读审议。在审议中,议员之间意见分歧很大,虽经多次长时间的辩论,亦未能取得较为一致的意见。在第40次会议进行表决时,原案、特别审查会提出的修正案及议员提出的修改动议,都未能获得3/4多数,而均被否决。《参议院议事细则》第55条规定:修正案及原案皆未获通过,而“参议院议决为不得废弃者,得委员另行起草付之会议”。根据这一规定,第40次会议继续讨论此议案是废弃或另行起草问题。但在讨论过程中,由于一些议员中途退席,议长宣布,“此案法定人数已经不足”,转而审议其他议案。(23)此后,未见临时参议院再议及此案。
在这4次审议中,参议院对出席人数的要求,也均是按照到院议员的4/5计算的。第9次会议开议此案之前,议长宣布现共有议员97人,出席78人,达到了4/5。第10次会议时仍共有议员97人,议长宣布出席人数是84人,达到了法定人数。第14次会议开议此案前,议长称,现在“出席者七十九位,到院者共是九十九位”。这距4/5的法定人数还差一位,故只得先议其他议案。稍后,又有一人到会,达到了4/5,议长宣布开议此修约案。第40次会议开议此案之前,议长宣布:“现在已有八十五人出席,按照一百零六人计算恰足五分之四,即行开议。”(24)
在此修约案的审议过程中,临时参议院对于《临时约法》有关审议修约案出席人数规定的理解是存在问题的。《临时约法》第55条所称“经参议员五分四以上之出席”之“参议员”,是指“总员”,还是指“到院议员”?从以上所述可见,北京临时参议院在审议此修约案过程中的所谓共有议员显然是指“到院议员”。但对照研究《临时约法》中对其他有关会议出席人数的规定可知,(25)《临时约法》在规定出席议员人数须达到的比例时,所用的分母均是“总员”,而非“到院议员”。
此外,修改《临时约法》案是比弹劾总统案更为重大的议案,也是北京临时参议院所审议的最为重大的议案,在议案的提出、出席及表决人数等方面,法律只会规定得更为严格、最为严格,而不是相反,实际上也正是如此。关于弹劾总统案的提出,《临时约法》没有做关于人数的规定,只是《参议院法》第59条规定:“弹劾大总统案,非经参议院[员]二十人以上之连署……不得提出”,(26)但关于修改约法案,《临时约法》第55条规定,要“由参议院参议员三分二以上……之提议”,这显然比对弹劾总统案提出人数的要求要严格得多。那么弹劾总统案的审议尚须有“总员五分四以上之出席”,修改《临时约法》案怎会仅要求到院议员4/5以上出席就可开议呢?由此可见,北京临时参议院对《临时约法》关于审议修约案出席人数规定的理解是错误的,在实践上违反了《临时约法》的规定。(27)
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在议事活动中,亦有不遵守参议院有关出席会议和会场秩序规定的多种情形。
《参议院法》规定:参议院会议时“参议员非有正当理由不得请假”;“参议员不得任意缺席,违者分别惩罚”;“参议员无故缺席连续至五日者,应酌定五日以上之期停止其发言。一月内无故缺席至七日以上者除名”。《参议院议事细则》规定:“会议中议员如有因不得已事故,陈明议长,经认可退席”;等等。北京临时参议院在遵行这些法律、法规方面存在严重问题。
北京临时参议院在其存在的近一年中,共开会128次,(28)到院议员全体出席者无一次;出席人数最多者为7月19日第42次会议,出席99人;(29)出席率最高者为5月23日第10次会议,当时到院人数为97人,出席84人,(30)出席率为86.6%。平日会议的出席率则多在60%~70%,大多数会议有1/3左右的参议员因事、因病或不知因何而不到会。其中仅有个别几次会议,是因某常任委员会有紧急议案需要审查,而在参议院开正式会议的同时开此委员会的审查会,致使出席参议院会议的人数较少。(31)
临时参议院几乎每次会议时,都有一些议员在议事中擅自退席,或到休息厅喝茶休息,甚至有些议员在开议后不久即退席,致使实际在会场的人数往往少于会议速记录上所记载的出席人数。一般情况下,二者相差在10人左右,有时则高达二三十人。如6月11日第18次会议,速记录记载出席者84人,但当会议进行到第三项议程,对国务院官制修正草案是否即开第二读会问题进行表决时,在场议员仅剩56人;(32)7月15日第38次会议,速记录记载出席者90人,但会议中当对吉林省弹劾都督案表决时,在场仅65人。(33)
这种情况在北京临时参议院开院之初即存在,并引起一些议员的不满和指责。在5月28日的第12次会议上,李素针对一些人中途退场的行为指出:“此事关乎个人之名誉,如此殊属不成事体。”刘彦指斥此种行为为“不负责任”,“如此之人实属太无人格,太无道德”,提议将这种人予以惩罚,以后除饮茶、便溺外不得无故离场。孙孝宗则提议会议中间休息一次,此外不准离开会场。(34)但这些指责并未发生任何效力,这些意见也均未能实行,中途退席的情况愈演愈烈,致使由于中途退席人数过多,会议不足法定人数而暂时停议,甚至不得不提前散会的情况频频出现。(35)例如,第41、54、63、64、67、69、92等次会议均因有人中途退席不足法定人数而宣布暂时中止会议,待有人返回会场,达到法定人数后,又继续开会;(36)而第32、120、123、124等次会议则因等人返回无望而不得不宣布提前散会。(37)12月4日第110次会议中人数减至法定之下,且长时间等待无人返回,但预定国务总理、外交总长将莅参议院报告蒙古问题,不能提前散会,只得将正式会临时改为秘密谈话会。(38)
再一种情况是,由于会议要等达到法定人数才能开始,而许多议员又经常姗姗来迟,所以北京临时参议院所举行的128次会议,按《参议院议事细则》规定的时间准时开会者仅有11次,(39)多数情况下延迟15~30分钟开会,延迟一个小时以上的情况亦有十几次之多,而第122次会议竟因等人而迟开了两个小时。(40)
此外,更多次出现因出席人数不能达到法定人数而流会的情况。如前所述,开院初期,多是在规定的开会时间已到而人数不足时,再等上半个小时左右即可人足开会,但至1912年9月以后,开始出现长时间等待,而人数仍不足终未能成会的情况。在9月23日第79次会议上,一些议员提出要整顿出席纪律,并议决只延长开会时间半个小时,至9:30人数不足即散会。(41)但9月24日的第80次会议就延至9:35才开议;(42)9月25日至9:30仍未达法定人数而只得宣布流会;9月26日第81次会议延至9:44方达到法定人数宣布开会,有议员提出已过规定时间,不能再开会,议长吴景濂劝告议员“不要负气”,而继续开会,亦不执行刚刚议决的规则。(43)这样勉强维持了一段时间后,随着秋深日短,迟到的现象又日益严重起来。为此在10月15日的第91次会议上,经讨论并多数议决:修改《参议院法》,将正式会改为每周一、三、五下午1:00~5:00召开;将缺席者的名单列于会议速记录之前,以示惩戒;会议中间休息15分钟,“不能照以前大会方开即陆续退出休息”。(44)经过这样的改动,此后至12月中旬的20余次会议多能在规定时间后半个小时内召开。
但到12月中旬以后,由于一些议员纷纷回籍运动国会议员的选举,在京议员人数大为减少,又致使多次开会未成。在1912年12月25日至1913年3月3日的69天中,参议院仅开成了4次会议,其余10余次均因等待多时而出席者无望达到法定人数而流会。(45)而勉强开成的4次会议中,亦有两次因有人中途退席致使人数不足而提前散会。(46)面对如此严重的出席问题,有关惩罚的规定却未见执行一例。
对北京临时参议院这些表现,社会各界深为不满。《申报》不断指责参议院议员“遂图自便”,(47)“无道德心,无责任心至此”,(48)出席会议“冷淡”,运动选举“狂热”;(49)《大公报》则破口大骂:“参议院议员真无心肝”!“参议院尚知人间有羞耻事耶”!(50)
多次开会未成的直接后果,是使政府已提交参议院而参议院未能开议,或已开议而未能议决,积压在参议院的议案多达50余件。(51)袁世凯政府乘机将一些未开议或未议决的法律、法规议案提回,径以大总统命令的形式公布施行。舆论指责参议院“断送立法权”,造成“共和时代之专制”,(52)“殊于民国前途贻误匪细”。(53)参议院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与威信已丧失殆尽。
关于会场秩序问题,《参议院法》和《参议院议事细则》也都有规定。如前者规定:“参议员于议场不得用无礼之言辞”,“参议员于会议时,有违背院法及议事规则或紊乱议场秩序者,议长得警告制止之”;后者规定:“未通告而欲发言者,须起立呼议长并告自己之席次,待议长许可始得发言”;“会议时无论何人不得喧哗或作赞否声”;等等。
应该说,在多数情况下,北京临时参议院会议尚能按照院法及议事规则正常地进行,争论、辩驳也较有秩序。但在议事过程中,议员之间甚至议员与议长之间语意间的唐突、冲撞经常不断;有些议案,由于议员间分歧较大,讨论中情绪渐趋激烈,于是正常的辩论转为争吵、叫骂,以至拍案、狂呼,整个会场乱作一团,使会议无法进行的情况亦不鲜见。5月23日第10次会议上因《修改约法青海为西蒙古并增加议员案》而发生的冲突就是其中较典型的一例。
如前所述,此修约案涉及的问题确较为复杂,且关系重大,故议员间的分歧很大。这次会议的第一项议程即为此议案的第二读会。讨论中,持不同意见的议员互相反复辩驳,情绪变得激烈起来,会场秩序逐渐失去控制。当日会议速记录的记载是:“二十八号、四十五号与十五号、四十三号互相辩论,同时发言,议场秩序为之大乱”,议长竭力维持秩序,劝说大家:“此事关乎领土甚为重大,应平心静气讨论……维持议场秩序为是”,(54)但已无济于事。《大公报》记者的报道则称:数位议员激烈争吵,会场上“拍掌声、拍案声、呼号声并作”,秩序大乱。(55)《申报》的报道且披露,刘成禺与文崇高坐席相接,二人争辩激烈,刘成禺“即举手作欲击势”,于是平刚、谷芝瑞两个上前各助一方,虽“卒之无一真击人者,然议长已无法维持秩序矣”。(56)在这种情况下,议长不得不宣布:“照院法第八十六条,议场骚扰不能维持秩序时,议长得中止会议或宣告散会。今日本议场按此条规定,宣告散会。”(57)
如果说这次纷扰主要是由此议案本身确实复杂,而部分自视高明正确而又固执褊狭的参议员各持己见,互不相让而起,那么8月28日第70次会议上因《弹劾国务总理、陆军总长案》和《咨请政府查办参谋总长黎元洪违法案》而发生的哄吵与争闹,则主要反映了刚刚改组而成的国民党与共和党之间政见上的分歧。(58)
北京临时参议院会议出席情况方面的上述问题,反映了部分议员的散漫作风和自私、不负责任的个人品德;而参议院不能有效地制止或解决这些问题,说明参议院有关规定的空疏、不健全,更表明参议院缺乏严格遵行这些法规的精神和具体措施。会场秩序问题则说明部分参议员激烈而褊狭的心态,以及议会政治训练的缺乏。
有关法律、法规能否得到遵守和维护,并非简单地只是法律本身的问题,其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民素质密切相关,更与社会政治有着直接的关系。在刚刚推倒封建帝制,共和肇建的民国初期,可以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国民素质的程度,还没有为实行民主与法制提供充分的条件,特别是由于以袁世凯为首的军阀、官僚控制了中央政权,更是给推行法制造成巨大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北京临时参议院为遵行法制,维护法律尊严所进行的努力就显得尤为可贵;而其未能正确严格地依法行事甚至违反法律法规的不光彩的记录,则使人们从中看到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法治社会转型过程的艰难与复杂。
注释:
①《参议院议事细则》规定:“除星期六及星期日外,每日上午九时至十二时为寻常会议时间。”《政府公报》第22号,1912年5月22日。本文所引《参议院议事细则》,皆据此《政府公报》,以下不一一注明。
②《参议院第六十次会议速记录》,《政府公报》第127号,1912年9月4日。
③《参议院第六十一次会议速记录》,《政府公报》第129号,1912年9月6日。
④《参议院第六十三次会议速记录》,《政府公报》第131号,1912年9月8日。
⑤《参议院第六十四次会议速记录》,《政府公报》第132号,1912年9月9日。
⑥只能说北京临时参议院对袁世凯及临时政府“某些”违反和破坏法律的行为进行了斗争,尚有某些违反和破坏法律的行为,未见临时参议院采取任何行动。如:《临时约法》规定实行责任内阁制,根据内阁制的原则,北京政府国务总理的人选由总统提名,但国务总理经参议院通过后,内阁成员由国务总理遴选,但北京临时政府自唐绍仪开始的各届内阁,实际上和表面上均是由总统袁世凯在决定人选;袁世凯违背与南方关于王芝祥为直隶都督的约定,改委其为南方军队宣慰使,不顾国务总理的反对将未经内阁副署的任命状交给王,这直接违反了《临时约法》关于大总统命令须由内阁副署的规定;等等。
⑦《参议院第一次会议速记录》,《政府公报》第10号,1912年5月10日。
⑧《参议院议决案汇编》,甲部一册。
⑨《致袁大总统议决各部官制通则电》,《参议院议决案汇编》,甲部二册。
⑩《致袁大总统请照议决各部官制通则另将拟派各国务员交院同意电》,《参议院议决案汇编》,甲部二册。
(11)《申报》1912年4月11日,“大总统命令栏”。
(12)《内务部用两次长之原因》,《申报》1912年4月16日。
(13)本文所引《参议院法》,皆据《中华民国史档案史料汇编》第2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以下不一一注明。
(14)《参议院第一次会议速记录》,《政府公报》第10号,1912年5月10日。
(15)《参议院第三次会议速记录》,《政府公报》第12号,1912年5月12日;《参议院第四次会议速记录》,《政府公报》第14号,1912年5月14日。
(16)本文所引《临时约法》,皆据《中华民国史档案史料汇编》第2辑,以下不一一注明。
(17)《参议院第六十三次会议速记录》,《政府公报》第131号,1912年9月8日。
(18)参见胡绳武、金冲及《辛亥革命史稿》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第348页。
(19)《参议院第六十三次会议速记录》,《政府公报》第131号,1912年9月8日。
(20)《参议院第六十七次会议速记录》,《政府公报》第138号,1912年9月15日。
(21)根据《临时约法》第18条的规定,北京临时参议院共有议员126人。而实际上在其存在的近一年中,在院议员,即所谓“报到者”最多时为117人。5月4日,北京临时参议院刚刚开幕,故“报到者”仅80人。此中具体情况见拙作《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人数及变动情况考》,《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
(22)《参议院第一次会议速记录》,《政府公报》第10号,1912年5月10日;《参议院审查〈大总统交议修改约法青海为西蒙古并增加议员案〉报告》,《政府公报》第22号,1912年5月22日。
(23)《参议院第四十次会议速记录》,《政府公报》第94号,1912年8月2日。
(24)分别见《参议院第九次会议速记录》,《政府公报》第24号,1912年5月24日;《参议院第十次会议速记录》,《政府公报》第26号,1912年5月26日;《参议院第十四次会议速记录》,《政府公报》第40号,1912年6月9日;《参议院第四十次会议速记录》,《政府公报》第94号,1912年8月2日。
(25)例如,《临时约法》第19条第11款规定:“参议院对于临时大总统,认为有谋叛行为时,得以总员五分四以上之出席,出席员四分三以上之可决弹劾之”;本条第12款规定:“参议院对于国务员,认为失职或违法时,得以总员四分三以上之出席,出席员三分二以上之可决弹劾之”;第29条规定:选举总统时“以总员四分三以上之出席,得票满投票总数三分二以上者为当选”。
(26)《中华民国史档案史料汇编》第2辑,第127~128页。
(27)此后民国第一届国会的各种会议(参众两院各自的会议、两院会合会、宪法会议、大总统选举会等),在计算出席人数时,均以两院各有议员274、596人或总员870人作为依据,尽管到国会报到的议员从没有达到过这样的数字。此亦可为证。
(28)这里指参议院正式会议,此外,尚有开幕式、闭幕式、参议院全院委员会会议、各常任委员会会议、秘密会议、谈话会等等,不在本文论述范围之内。
(29)《参议院第四十二次会议速记录》,《政府公报》第96号,1912年8月4日。
(30)《参议院第十次会议速记录》,《政府公报》第26号,1912年5月26日。
(31)有几次会议是因为党派政争,影响到出席人数,似属别类问题。
(32)《参议院第十八次会议速记录》,《政府公报》第49号,1912年6月18日。
(33)《参议院第三十八次会议速记录》,《政府公报》第92号,1912年7月31日。
(34)《参议院第十二次会议速记录》,《政府公报》第35号,1912年6月4日。
(35)《参议院法》第33条规定:“参议院非有到院议员过半数之出席,不得开会。但临时约法及本法关于出席员数有特别规定者,从其规定。”
(36)见以上各次会议速记录。
(37)见以上各次会议速记录。其中第32次会议的情况是,上午审议《国会组织法大纲案》至午未毕,因此议案紧急,下午继续开会,至5时半因人数不足而散会,与其他几次有所不同。
(38)《参议院初四日议事纪略》,《大公报》1912年12月6日。
(39)即第1、2、4、11、14、15、25、26、30、42、46次会议。见以上各次会议速记录。
(40)《参议院第一百二十二次会议速记录》,《政府公报》第331号,1913年4月8日。
(41)《参议院第七十九次会议速记录》,《政府公报》第165号,1912年10月13日。
(42)《参议院第八十次会议速记录》,《政府公报》第171号,1912年10月19日。
(43)《参议院第八十一次会议速记录》,《政府公报》第173号,1912年10月21日。
(44)《参议院第九十一次会议速记录》,《政府公报》第227号,1912年12月14日。
(45)见《申报》、《大公报》此期间的有关报道。
(46)见《参议院第一百二十三次会议速记录》、《参议院第一百二十四次会议速记录》,均载《政府公报》第331号,1913年4月8日。
(47)《参议院之暮气》,《申报》1912年12月10日。
(48)《参议院之残局观》,《申报》1912年12月26日。
(49)《参议院竟无法开会耶》,《申报》1913年1月12日。
(50)此为《大公报》两件报道的标题,分别见《大公报》1912年12月30日、1913年1月22日。
(51)《参议院延误议案之罪状》,《大公报》1913年3月10日;《呜呼末路之参议院》,《大公报》1913年3月23日。
(52)《论参议院之断送立法权》、《闲评一》,《大公报》1913年1月10、22日。
(53)《参议院之残局观》,《申报》1912年12月26日。
(54)《参议院第十次会议速记录》,《政府公报》第26号,1912年5月26日。
(55)《参议院纪事》,《大公报》1912年5月25日。
(56)《参议院之第一次轰天雷》,《申报》1912年5月29日。
(57)《参议院第十次会议速记录》,《政府公报》第26号,1912年5月26日。
(58)关于此次会议上发生争闹的情况,胡绳武、金冲及著《辛亥革命史稿》第4卷中有详尽的记述,见该书第356~359页。
标签:中国近代史论文; 袁世凯论文; 历史论文; 申报论文; 法律论文; 北洋军阀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辛亥革命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