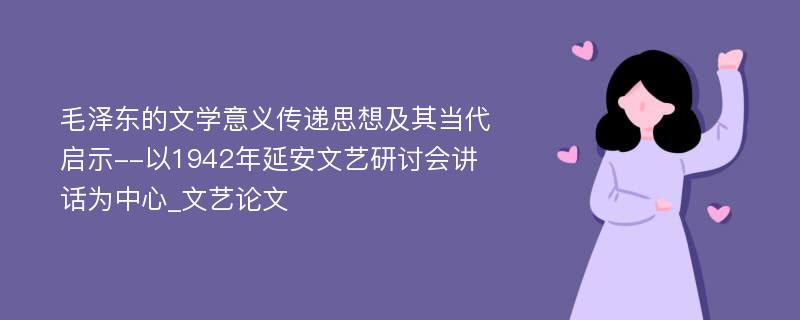
毛泽东文艺意义调度思想及其当代启示——以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论文,延安论文,座谈会上论文,启示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5)05-0009-06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5.05.002 文艺是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制造和传达意义的事业。文艺文本的意义,具有鲜明的主观性和可调控性,可按主体需要进行意向性设计和调控。若把这种意向性的意义设计和调控过程谓为意义调度,那对这一调度过程中的具体机制、方式方法进行规定,就能保证生产出符合主体意向的意义文本。就此而言,系统分析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的文艺意义调度思想,不仅有利于更深刻地理解1942年后中国革命文艺意义生产的内在机制和规律,而且可为推动当下中国文艺价值建构的健康发展提供重要启示。 1 革命文艺意义生产的首要原则及其实践路径 制约文本意义生产的首要因素,是创作主体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态度——对“何为文学”及“文学何为”的根本看法和观点。无论中西,自古就有功利主义和审美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传统。功利主义强调文学对非文艺事业的服务与配合,审美主义偏向对文学自身审美意味的传达。前者强调实际利益的寻求或满足,后者强调纯粹艺术的创造或享受。从《讲话》的基调来看,毛泽东秉承的自是前者而非后者。他开门见山地指出座谈会的目的,是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1]847。这种将文艺当作其它工作的协助以达到特定政治目的的功利主义文学观,贯穿《讲话》的始终。针对有人用功利主义的名义贬低革命文学价值的作法,他甚至坦率地说:“我们的这种态度是不是功利主义的?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而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1]864 历史地来看,毛泽东这种“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功利主义观念,既与中国古代文以载道、征圣宗经的观念一脉相承,也是晚清文学改良观和“五四”文学启蒙论的发展,但更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倾向性和文学革命工具论思想的继续。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创立者,马克思丝毫不掩盖自己文艺思想的倾向性:“我绝不反对倾向诗本身。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和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都是具有强烈倾向性的诗人,但丁和塞万提斯也不逊色。而席勒的《阴谋与爱情》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现代那些写出优秀小说的俄国人和挪威人全是有倾向的作家。”[2]385这里所谓倾向性,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指文艺的政治功利性,或者说文艺服务于政治的程度或方面。正因为此,马克思和和恩格斯都特别强调文艺作品的实际政治效果。马克思说,狄更斯、萨克雷、勃朗蒂等“现代英国的一派出色的小说家,以他们那明白晓畅和令人感动的描写,向世界揭示了政治的和社会的真理,比起政治家、政论家和道德家合起来所做的还多”[3]686。恩格斯则说,德国画家许布纳尔的油画《西里西亚织工》,“从宣传社会主义这个角度来看,这幅画所起的作用要比一百本小册子大得多”[4]590。至于列宁,更为明确地提出文学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5]93毛泽东的功利主义文学观,显然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关思想的发展。在《讲话》中,他甚至直接引用了列宁的上述观点[1]854。 但功利与非功利或者功利与审美、功利与艺术,并非绝然对立的两面,而是文艺固有的两种性质:“文学的这种无功利性背后又总是存在着不可否认的功利考虑。文学直接地是无功利的,但间接地或内在地却又隐伏着某种功利性。”[6]66也因此,历史上的功利主义者并不排斥艺术,审美主义者也同样强调“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对此,毛泽东也深以为然:“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1]869-870也就是说,虽然政治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念意味着革命文艺的意义生产必须指向对政治事业的配合,任何淡化、消解政治或者仅以审美作为文艺终极目的的做法都必须予以排斥,但这并不代表对审美性和艺术性的拒绝。换言之,是政治还是审美,作为意义生产的两种基本指向,在写作设计时或许有主次先后之分,但实际的文本中却应是辩证统一的整体。 不过,毛泽东文艺意义调度思想的特别之处,不在于其政治功利主义或政治与艺术必须辩证统一的观念,而在于从文学实践的角度,深入分析了政治与艺术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及其解决方法:“又是政治标准,又是艺术标准,这两者的关系怎么样呢?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1]869这里提出了政治和艺术“两个标准”并对之做了轻重高下的区分,这和其“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的告诫一起,便可引申出革命文艺意义生产的一个重要法则:应尽量追求政治正确性与审美艺术性的有机统一;若二者发生冲突则必须遵守政治正确性大于或者优于审美艺术性的要求;至于只问艺术、不问政治正确性的极端做法,则是完全不能允许的。这比起笼统的“文学为政治服务”的观念,显然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除了“两个标准”以及“政治标准第一”的原则,毛泽东还从“效果与动机”的角度对如何落实政治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念进行了更具可操作性的阐述。“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为个人的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1]868如果说动机是从作者角度考虑问题,效果则主要着眼于读者立场,那这里的论述显然兼及了动机和效果、作者和读者两个维度。但仔细揣摩,其暗含的重心却是对效果和读者的强调:“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1]868这种以政治效果作为检验政治动机唯一标准的思想,再次显现出毛泽东文艺思想中那种“读者本位的文学立场”[7]。这种立场要求作家写作时必须时刻考虑到可能读者的存在,考虑到作品对他们的教育意义和政治影响,从而不断调整规划自己的创作:“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总结经验,研究方法,在创作上就叫做表现的手法。”[1]874这样,“文艺为政治服务”就由外在的抽象指令内化而为文学实践的一个具体环节,显然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和实践品格。 政治功利主义本是马克思主义和此前左翼文学固有的传统,走人革命文学阵营的人,都怀着强烈的用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动机。但正确的文学观念并不能自动保证观念的必然落实,良好的动机也不意味着良好效果的必然取得。因为从观念到文本,从动机到效果,显然还有许多的中间环节。事实上,左翼文学尤其是1942年前的延安文学实践中,虽然作家们都认同文学为政治服务的观念,在意义的生产上却出现过较为混乱的现象。比如同是文学功利主义信仰者的王实味等人,却极力倡导非阶级化的“永恒的人性和爱”。这类自反现象说明,问题的关键与其说是作者们没有树立文学为政治服务的观念,毋宁说是没有找到如何落实这种观念的正确方案,因而在把抽象观念变为文学实践的过程中误入歧途。而《讲话》指出的“政治标准第一”以及用效果预测来反向调整创作实践的意义生产原则,显然可以有效规避这一歧途——比起主观世界的复杂多样和审美趣味的人言人殊来说,外在世界的政治标准和政治效果确实要相对客观和容易把握得多。也因此,《讲话》发表后,革命文艺意义生产的“混乱”局面便迅速结束,并由此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强调政治艺术两个标准和政治标准第一,并以社会效果的预测反向指导文学创作,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品格,是毛泽东对中国传统以及马克思主义文艺政治功利主义观念的进一步发展,也是毛泽东文艺意义调度思想的首要原则。“文革”结束后,这一原则在所谓“去政治化”的呼声中一度受到反思和批判。随着时代的变化,给文学和政治进行一定程度的松绑是必要的,但松绑并不代表弃绝政治。毋庸讳言,“文革”后的去政治化思潮在某种程度上为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但也带来了不少问题:对功利维度的放弃,使部分作家打着艺术的旗号走入了个人探索的死胡同;对社会效果的漠视,则使部分作家陷入了商业主义的泥淖;还有部分作家从个人化的井口进去,却从欲望化的井口钻了出来,把写作变成了取悦读者本能的商业化行为。如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美女写作和身体写作就是如此。就此而言,在一定程度上重温毛泽东意义调度思想的首要原则,重拾文学的政治维度,重申社会效果对写作的规范调整功能,不啻是纠正当代文学发展偏差的一剂良药。 2 革命文艺的基本价值轴线及其设定 以政治效果的预测来反向调整和规范创作主体的文学行为,已提供了把外在政治要求引入内在文学实践的可能性。但政治的要求往往是抽象的,而文学则是形象的表达。在形象性的文学文本中,又如何才能保证政治的正确呢?有学者指出,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对古希腊神话深层二元结构的挖掘,其实就是寻找文本意义生成机制的行为。因为找到文本背后的二元结构,神话的意义也就不言自明,而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理论在本质上也是通过寻找二元结构的方式来发现文本的深层意义[8]178-183。这也就是说,文本的意义效果其实主要来自文本深层各种价值观念的“二元对立”,如自然/文明、道德/欲望等,它们就像文本价值生产的中心轴线,只有围绕它,意义才能得以建构和显明。当然,文本中的价值轴线或许有多条——条数越多意义越复杂,但总有一条是最基本的。正是这条最基本的价值轴线,决定着文本意义生产的总体方向。毛泽东发表《讲话》的时代,法国的结构主义尚未登场,但《讲话》对人性/阶级性的分析,却具有明显的为革命文艺确定基本价值轴线的结构主义意味。 关于人性与阶级性,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世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阶级使社会分化为许多对立体,阶级消灭后,那时就有了整个的人类之爱,但是现在还没有。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1]871人犹如此,文学亦然:“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相互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1]865历史地来看,这种对阶级性的强调,对普遍人性的批评,无论是使用的概念还是观点,显然都是对左翼话语的延续。左翼时期,针对梁实秋等人主张的文学只应表达“普遍永恒的人性”说法,鲁迅曾说,“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9]195作为作家,要想写出没有阶级性的作品,那无异于痴人说梦:“生在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予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10]336 但毛泽东对于左翼话语,不仅有延续,更有改写。在鲁迅等人看来,普遍人性虽然应该批判,却是存在的:“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情感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11]126-127也就是说,鲁迅对阶级性的强调,是以承认具体人性的存在为前提的。而毛泽东则认为所谓普遍人性不过是超阶级人性、抽象人性的同义语:“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1]870不难看出,作为与阶级性相对的普遍人性概念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一个花招,世间真正存在的只有不同阶级的“具体的人性”,而这种“具体的人性”其实就是阶级性。因此,无产阶级的人性也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资产阶级的人性则等于资产阶级的阶级性。 这样,经过毛泽东改写后的人性/阶级性话语,就发展为无产阶级人性(阶级性)/资产阶级人性(阶级性)的二元对立。就具体内涵而言,前者指向大我化的斗争、抗争、集体主义,后者表现为小我化的个人主义和个人欲望。这与《讲话》强调的“二元性人物角色模式”相结合[7],就必然形成这样的意义调度原则:在整体的“我们”和“他们”的对立中,着力突出二者之间阶级性的对抗与冲突,凸显我们的阶级性——大我的道德主义和不屈的抗争精神,强化他们的阶级性——小我的欲望化、残忍化、反动化;而在我们内部,则按照先进性的程度分别凸显其阶级性的强弱,如落后分子对应小我、积极分子对应从小我走向大我、先进分子则对应完全的大我。这种共时性的意义结构再和历时性的情节演变相结合,则表现为:我们和他们的斗争,其实就是小我和大我的斗争,就是两种人性或曰阶级性的斗争;我们内部三种人物的矛盾冲突,也是小我和大我的冲突。这样,整个文本的意义生产就能始终围绕着阶级/革命展开,而不可能溢出政治革命的轨道。 以今天的眼光观之,把所有人都必然具有的小我化欲望追求窄化为资产阶级特有的阶级性,把大我化的道德追求和抗争精神等同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并要求任何文艺的意义产生都必须围绕二者间泾渭分明的对抗展开,或许有简化文艺意义生产多重可能性的倾向。但这是当时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下的必然产物,而且小我与大我或日本我和超我的冲突,本是人类作为存在的最基本矛盾,毛泽东对人性/阶级性也即小我/大我这一基本价值轴线的阐释,其实切中了人类文艺意义生产的核心肯綮,具有超越具体时代的普遍真理性。一个令人痛心的事实是,“文革”后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的当代文学,由于对阶级性话语的盲目放逐以及商业主义大潮的裹挟,部分作家以贩卖个人隐私相号召,只知一味自然主义地描绘小我化的肉欲、物欲和权欲及其相互冲突,最终滑入了本能化写作的陷阱。在此语境中,我们若能够扬弃毛泽东人性/阶级性话语中阶级性的时代烙印,将小我与大我的矛盾由两个阶级代言人间的外在对抗,内化为具体个人生命内部的人格冲突,并积极揭示其中的辩证法,或许可以帮助当下文学走出本能化困境,重新找回个体与社会、与时代的复杂联系。 3 革命文艺的价值意向呈示机制及其辩证把握 围绕人性/阶级性的价值轴线,可保证文本的意义生产在政治的轨道上运行,却不能天然保证其政治上的正确和效果上的不出偏差。因为文本的最终意义效果,除了价值轴线的设定之外,还与具体的价值意向呈示机制有关。就此而言,《讲话》中有关歌颂/暴露的讨论,其实正是对革命文艺价值意向呈示机制的说明。 歌颂与暴露,本是文艺史上两种常见的价值意向呈示机制,无所谓好坏优劣。古往今来的伟大作品,有的以歌颂见长,有的以暴露出彩。究竟是歌颂,还是暴露,究竟歌颂什么,暴露什么,完全取决于作者的价值态度和审美考量。但非常时期需要非常的措施,为保证革命文艺政治功效的正确,毛泽东不得不对歌颂什么、暴露什么进行具体的论述。他说:“对于敌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鼓励抗日军民同心同德,坚决地打倒他们。对于统一战线中各种不同的同盟者,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有联合,有批评,有各种不同的联合,有各种不同的批评。他们的抗战,我们是赞成的;如果有成绩,我们也是赞扬的。但是如果抗战不积极,我们就应该批评。如果有人要反共反人民,要一天一天走上反动的道路,那我们就要坚决反对。至于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人民也有缺点的。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只要不是坚持错误的人,我们就不应该只看到片面就去错误地讥笑他们,甚至敌视他们。我们所写的东西,应该是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1]848-849 这段话的要旨有三:对“我们”或曰“自己人”要歌颂;对“敌人”要暴露;对“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或者说“朋友”则视实际情况灵活决定。“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们是否废除讽刺?不是的,讽刺是永远需要的。但是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1]872这种不是歌颂就是暴露的二元对立化的思维方式,也许淡化了文艺作品价值内涵上本应有的复杂性、模糊性和暧昧性,却是保证意义调度始终正确的最有可操作性的方式。因为在阶级性/人性的价值轴线已然确定的前提下,歌颂什么和暴露什么已是不言而喻:歌颂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大我的集体主义道德、敢于反抗不妥协的斗争精神;暴露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人性——虚伪、残忍、腐朽、反动,以及小资产阶级的人性——贪图享受、好逸恶劳、自我清高等。明白了这一点,作家就能在人性与阶级性的对立中予以正确取舍,并通过主人公的设置、故事或人物命运的结局、叙述者的干预等叙事手段来传达或暗示,从而避免政治效果上的错误。 一个基本按照人性/阶级性的价值轴线组织意义,却在最终效果上犯了政治错误的例证是建国初期的电影《武训传》。该片讲述清末一个名叫武训的人行乞兴学的故事,其意义建构显然也是围绕人生/阶级性组织起来的,但在歌颂与暴露的对象问题上却出现了偏差。按照《讲话》论述的价值呈示逻辑,武训作为无产阶级的形象,自然是要歌颂的,但要歌颂的应该是其阶级性——为大众利益敢于反抗敢于斗争的精神,而不应是其所谓泯灭阶级界限的普遍的人类之爱。满清皇室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言人,本该是暴露讽刺的对象,影片却赋予其正义主持者的形象。这就难怪毛泽东要亲自对之进行批判了:“《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12]46-47这表明,《武训传》的问题,不在于没有按照人性/阶级性的轴线进行意义调度,而在于对歌颂/暴露这一价值意向呈示机制的把握出了问题。 毛泽东对歌颂和暴露的阐述,源于其强烈的阶级爱憎和对剥削与被剥削阶级极恶与极善的道德判断。这种善恶分明的道德态度,既是战争年代的特定革命需求,也是任何时代都必须保有的核心价值理念。“文革”后文学,在坚守这一基本原则的大前提下,曾出现过善恶判断模糊化、价值意向复杂化的探索。如韩少功《爸爸爸》中的丙崽,就很难用传统的善恶观念来概括,价值意向也很难说是单纯的歌颂或暴露。但因为西方思潮和中国商品经济的影响,这类严肃的价值探索在进入1990年代后,却在许多作家的笔下变成了善恶的无边界化和道德的无底线化——当今倡言解构的许多影视作品尤为明显。笔者以为,若把作家的善恶判断看作一个河床,毛泽东强调的歌颂与暴露则好比河床的两岸。要求价值建构的河水只能紧贴河岸而非在河中自由流淌,自会带来意义河流的枯竭。但让价值建构的河水完全不受河岸的束缚,甚至任其冲出乃至冲垮河岸,则必然造成意义泛滥的灾难。就此而言,重新修复歌颂与暴露的河岸,让中国文艺的意义之河能更加自由有序地健康流淌,实是毛泽东《讲话》留给当今文学的又一份重要启示!标签:文艺论文; 政治论文; 功利主义论文;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文; 毛泽东论文; 无产阶级政党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延安时期论文; 当代作家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人性论文; 文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