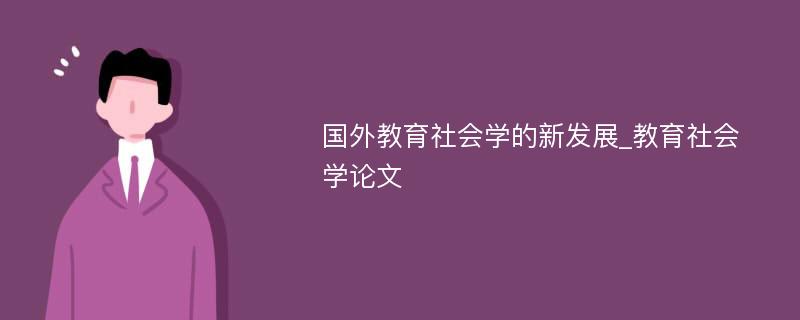
国外教育社会学的新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新发展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5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3-7667(2002)12-0001-06
教育社会学的奠基者可追溯到马克思、韦伯、涂尔干。从诞生开始,它就是教育学科群中最具思想活力、提供批判反思并指引路标的“母学科”之一。1971年以来,这一领域涌现出诸如艾坡(Apple)、伯恩斯坦(Bernstein)、吉鲁(Giroux)、瑞威(Renway)、赖塞尔(Lather)、麦克赖恩(Maclaren)、威克斯勒(Wexler)、威蒂(Whitty)、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等杰出社会科学家,[1]他们对教育问题与实践的关注与探究,并使“教育研究”不再划地为牢地限制在贴着教育学家标签的狭小圈子中。
一、“建构”取代“接受”
一个研究者进入问题时,“问题”之于他(她),究竟是"Take"还是"Make"?这并不是一个语言游戏,而研究问题的转折——借用鲍尔的话,研究取向中解释主义取代了自然主义。[2]
"Take"(接受)的对象一定是外在的——与“你”(准确地说,是研究者,研究者的面具罩在你的头上,你之为你的一切,成长背景、生活世界都不重要)无关的事实,客观的事实——任何眼睛看起来都一样。这个"Take"所针对的是自然事实,准确地说是物理事实,象桌子、凳子一样没有生命的东西。其实,自然事实也不等同于物理事实,向日葵可谓是自然事实了吧?在梵高的眼里与画中,向日葵充满着生命、激情,我们从梵高的眼中甚至能看到向日葵周遭的阳光、风影、干湿,看到透明的、流动的空气,看到画家的性情与生命。梵高是在“建构”向日葵而非照相式的呈现(Take)——“正是这有生命的、流动的、充实的空气对画面中的物体起了作用”。[3]而建构所强调的就是“你”——“研究者”,“研究者”开始向生活中的“你”回归,虽然研究可以重塑“你”的生活世界,但你的生活、你生活中的问题关怀凌驾在学科戒律之上,主导着“你”的探究之眼。
对同样一个问题,接受与建构的研究策略与问题意识均有诸多差异。接受及其后的自然主义研究传统所关心的是各种变量、变量之间的关系。自然主义的传统企图将社会世界等同于自然世界,并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与视角——相关性分析、现场实验、机率大小等等,移植于社会科学的研究之中;用量的方法致力于“寻找”人的行为与社会变量之间的关系“事实”——客观的、外在的事实,寻找超越情境而存在的规律性认识。自然主义取向的研究在教育学中的应用,在美国被称为“教育的社会学”(Educational Sociology),譬如科尔曼(Coleman)与布劳(Blau)的研究;在英国则是政治算术("Political Arithmetic")的传统,区别于“教育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4]我们以“教育机会均等”这个重要的教育社会学问题来分析两者的路数有何不同。
“教育的社会学”(Educational Sociology)所关注的是工业化民主社会中教育机会与社会流动之间的关系——艾坡(Apple,1996)将其表述为社会分层与所达成的地位之间的关系,即社会出身——先赋地位(社会阶层、经济地位、性别、种族等)与后致地位——尤以教育成就为代表之间的关系。他们将教育视为一种补救,教育对既有的不公平的社会秩序进行重新洗牌,学校教育能够为弱势群体提供补偿性援助,使他们能在一个更为公平的起点上开始其职业、文化与社会历程,因而学校被视为一个生产民主与公平的社会建制。其中最新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穆勒(W.Muller)与卡尔(W.Karle)的《欧洲教育体系的社会选择》,多尔·伯拉特(M.Duru-Bellat)的《法国中等学校中的社会不平等:从数字到理论》等。[5]
一币两面,“补救”的社会学又有一美誉——“黑箱”的社会学,只关心教育的投入与产出,忽视——严格地说是其研究方法上不能涉入学校内部的教育教学过程。
建构及其后的解释主义教育社会学从自然主义视为当然、准确地说视为禁区处起步。对教育社会学中自然主义传统的批判始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主要有三个不同的来源——新马克思主义、互动理论和知识社会学,依照“敌人的敌人即为朋友”的简单分界,它们常被笼统地视为一类,并被冠以“新教育社会学”(the New Sociology of Education,NSOE)。[6]而新教育社会学(NSOE)的核心就在于坚持不断地建构(Making)问题,而非简单地从政策制定者与实践者那里接受(Taking)任务。“教育的机会均等”这样一个在结构功能主义传统下被表述为事关教育的投入与产出的经济学命题,被解释主义者转换为这样一个问题域:在时间滴滴哒哒的流逝中,学校这个黑匣子究竟发生了什么?
“教育机会均等问题”在扬(M·Young)那里就成了“知识与控制”的问题。[7]教育机会均等后面是教育公平与教育民主这样一些核心价值,其后又是所建构出的“贫困”概念。在英国20世纪50~60年代,“贫困”的内涵逐步由经济意义转变为文化意义,贫困者逐渐由物质上的赤贫者被建构为文化上的匮乏者——布迪厄所贡献出的文化资本成为一个重要的解释视角,而优良合理的教育应该成为“补救”文化匮乏者的利器,教育机会均等成为建设民主社会的重要途径。随着对教育机会均等的关注,学业失败者、学业能力欠佳者开始吸引教育研究者乃至公众的眼球,并被建构为一个教育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最初是从功效观出发,认定其为“教育浪费”;随着探究的深入,这个问题逐步被转换为不同的表达、不同的关注兴趣乃至不同的研究域。学业失败者的特征首先被描述成心理特征,诸如智力商数、学业能力等等;其后学业失败者的特征又与一组社会变量相关连,诸如家庭、阶级、族裔乃至性别,学业失败者与社会中弱势人群相关连。此类研究后面隐蔽着歧视、排斥甚至压迫——社会的等级秩序再制于学校对学生的分类过程中。
我们的疑问是“学业失败者”过去怎么不成为“问题”?是过去没有学业失败者吗?非也。学校是现代社会的人才编码场,学校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对各色人力进行分类、塑造,在强筛选、强分类的教育观下,教育的一个职能就是分层与淘汰,学业失败者自然在教育决策者、实践者与研究者的视线之外,或隐匿不现或视而不见。由此看来,“学业失败者”的产生与建构应了福柯(Foucault)的一句话:从隐匿到可见,从命名到定义,从描述到治疗,都是社会建构(Making)的过程。
直到扬等知识社会学家开始追问:学校中的分类标准由谁制定?学校中的知识代表谁的利益?在何种利益角逐中,谁被界定为“学业失败者”——社会中的弱势人群?课程——Take取向下的“法定文化”才从超越种种利益之上的Given(被赋予的、给定的)知识被还原为一种社会组织中的知识,课程这只旧时王孙燕不得不落入寻常百姓家,课程是“做”出来的“社会建构”或“社会建制”。扬与艾坡[8]用不同的语句指出:课程是经由意识形态(既包括政治的意识形态,也包括科技的意识形态)所界定的知识、所选择的知识、所分配的知识,所实施的知识。无论是正式的官方课程还是非正式的潜在课程,这些课程无论假借圣谕的权威,理直气壮地“替天言道”,还是假借科学的魅力,将自己转换为客观、中立、远离是非利益的“真理”,都被挑破了面纱,被迫承认其情境性。知识也罢、课程也罢,都是置身于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情境中的一种建构,甚至是复数利益群体之间相互角逐、相互妥协的社会建构。课程在此早已不是一种天赋的(Take)的客观事实,而是一个人为的(Make)社会建构。当利益、权力这类社会控制凸现出来时,“更有成效地传授知识”被转换为“更公正、更合理地传授知识”这一事关社会公正的价值问题。
我们略为回溯一下20余年间建构派新教育社会学的发展轨迹。其核心兴趣是教育的传递过程:新马克思主义讨论着学校经验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即学校与教室再生产着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其中最重要的贡献当为鲍尔斯(Bowles)与金蒂斯(Gintis)1976年提出的“符应原则”与莫尔(Moore)的《符应原则与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社会学》;互动理论与学校人种志研究则揭示着教师与学生的社会身份的建立过程,揭示着教室中的社会控制与社会选择;知识社会学则将学校中的知识与学科从教室中置换到社会文化背景之中,课程与教学都是社会的建构。知识社会学进而责难自由主义的知识观与教学观,认为知识内部有着明确的等级差异——精确知识的地位、尤其是可概括为数字的知识地位最高;可以用文字表达出来的知识的地位高于口述的、民间流传的知识;远离生活的知识即与个人生活距离较远的知识地位高于日常生活中的知识;教学中倡导个人化的学习,而合作学习得来的知识地位就较低,这就是知识的层级化(Knowledge Stratification)。[9]课程、课堂教学——看似中立的学校知识场已成为不同利益群体的角逐场,文化实践中包含着权力斗争,教育中充满着不平等与压迫。吉鲁(Henry A.Giroux)等提出将文化学转换为政治学,弗莱雷(P.Freire)等学者提出学校教育学应该是“可能性的”学校社会学,教师应该勇敢地成为“解放者”与“转化型的知识分子”——这是一种新型的文化政治或吉鲁所说的“跨越边界”。[10]
同时,新教育社会学是一种根本性的革命而非修正性的改良,其间有一些里程碑式的研究值得再提。70年代后,教育中批判性的研究谴责教育再制着社会的不平等,在资本主义体系下充任着压迫的社会体系。美国鲍尔斯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欧洲伯恩斯坦的《阶级、符号与控制》,布迪厄与帕森斯(Passeron)的《社会的再制:教育与文化》皆在讨论着教育,通过其空间与时间的组织,对课程知识的选择,对居统治地位的文化与语言的传递,有效地维持着阶级的边界,学校被视为传递社会控制的“隐性课程”。用阿图塞的术语,这是“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其功能在于再制等级秩序。70年代晚期,另外一些研究凸现,开始关注资本主义学校中学生的抵抗力量,抵制论中最为突出的当属威尔斯(Willis)对英国劳工阶层子弟的研究:《学习成为劳动者》。[11]新教育社会学在美国的研究者主要是艾坡、吉鲁和威克勒斯(Wexler),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将马克思主义、互动理论与知识社会学熔合并铸就了一套新的、多元的批判性工具。教育社会学中纯粹的理论急速减少,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学科跨界、观念变化。到了90年代后,批判的传统与后现代的发展集中在教育政策分析和教育改革领域。
相应地,接受与建构取向之后也预示着教育社会学在方法论与研究技术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接受后多为量的研究与实证主义的传统,建构后多为质的研究与解释主义传统。塞拉(Searle)1999年说:社会研究中实证主义取向是乐观的,所强调的观念实体具有理论普遍性,研究所根植的世界独立于人类的关怀之外——尽管这个世界由人的劳动所创造。相反,质的研究承担着双重责任——真实性(发现与再现行动者的意义)与建构性(社会行动者的观念是社会世界的解释)。研究社会生活最重要的是理解人们赋予其行为的意义,理解与共享社会世界之于他人的意义。最好的理解建立在对所研究的生活情境的熟悉与持续参与上。再具有独创性的理论,再科学化的观察者,无论进行多么细致的研究都无法代替对研究之下正在进行的生活本身的熟悉。[12]
Make后的努力正如曼罕(Mehan)所说的是一种“社会行动、文化传递与建设性的活动”,它与人亲密互动,密切地观其言察其行,以描述日常生活中细微的矛盾与细微的差异。它同样为20余年间所活跃的不同理论与认识论所共铸:符号互动理论、人种志研究与现象学等,为获得更多的普适性与大众性,还将实证主义的逻辑性接纳其中——以回应对其“太软”或“太随意”的批评,同时也在接受与包容女性主义与后现代的冲击。如同一场学术接力赛跑,到目前为止,新教育社会学在其活跃期所呈现出的最后一个角色是反省性角色——新教育社会学将工作的基础更多地放在自我批评上,而下一棒——女性主义研究的活跃将承继着批判的传统并开启新的方向。[13]
二、研究者是谁?
如果说在新马克思主义与新教育社会学盛行的20世纪70年代、80年代(早期),教育社会学中充满着阶级、阶级再制与阶级抵抗这类术语,随着有性的(女性主义)与有色的(种族的)研究者的活跃,批判话语从宏大的经济、阶级这类“大词”(Big Words)转换为研究者的身份、研究者的立场等充满着微观政治学色彩的“小概念”。“研究者是谁”——立场理论(Standpoint Theories)开始活跃,并主导着80年代后的发展。
在以往的社会学与教育社会学生产中,充满着学科的微观政治学,有人称之为“社会学系研究生的隐型课程”,隐型课程有两种,其一为弱形式,它界定与控制着“像一个社会学家”,即在具体的方法、主题、关怀与旨趣上对学生进行社会学专业化,也即布迪厄的“惯习”;其二为强形式,在社会学的研究过程中再制既存的权力层级化与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其中白人男性学者居重要地位;而女性、少数民族这些社会边缘群体,被排斥于知识生产领域之外。[14]许多人甚至认为女性研究仅是针对父权制的狂躁的报复而非合法的学术探讨。在此类学科戒律下,研究者所身居的社会位置、他(她)的生活世界所赋予其独特的问题意识是不重要的。教育社会学也不例外:对于一个具体的研究者来说,不管身处于多么边缘的情境,有多么真切的现实关怀,但一走入学科体系,就需要采用主流的、官方的语言、问题与思维,——准确地说,将自己处理成一个抽象的“人”,一个虚假的、被异化的“人”来进行学术操作,热的问题关怀常被冷的学术技术所肢解。艾德兰·莫兰就说:社会学者尤其是科学的社会学者常是一群精神分裂的人。[15]
然而,教育是人的实践,教育学是人的科学,人有其生活与立场,有其生命痛痒亲切的所在。科学化的努力只会使研究者远离行动与实践,并建构出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教育学这样有关人的实践的学科可以高居(远居)于人之上(之外),并保持所谓中立的立场吗?——这种理性主义的进步论调不仅是危险的,也是一种蓄意的欺骗。不独研究者的身份被架空,教育的实践者亦被架空了。
鲍尔指出近些年来如日中天的管理学就是一种道德技术,[16]由于管理学的介入,办学如同办工厂,在市场竞争的逻辑牵引下,教师基本上失去了对教学环境的控制,矮化为技工。不独教师被架空,更为严重的是教育中的人也被架空了。
福柯指出,管理学是一种道德技术或权力技术,管理学使学校更像边沁的“全景敞视主义”的现代版本。它引入一对“天眼”,个人的一切都纤毫毕见;它引入效率与规训,个人的每一个行动都成为最节省、最经济的塑造。校长和教师都仅关注技术与能力,学校复杂、纵深的背景被简约为客观的效率——教育非人化了,教育也反社会化了。集中体现为两点:其一,学校中的知识即课程与教学日渐远离教师与学生的具体生活,自称其为客观知识,是与具体人不关联的、不容怀疑的外在知识,学生只需学习与掌握它们就可以了;其二,学生的日常生活世界被忽视了,家庭与学校两个世界被认为是同质的。学生如同孙悟空,从石头缝中蹦出来——学生文化、学生的家庭文化、家庭文化背后的阶级文化都被忽视了。教育中的人被架空了。
如此之多的“被架空”的必然结果是,教育研究被架空了。女性主义就批判教育研究被雄性化(Maleable)——即被权力化与庸俗的权威化了。刻板的技术简约主义使教育远离无家可归者、失业者、贫困者,教育可以为社会中的高地位人群锦上添花,却不肯为弱势人群雪中送炭;教育研究远离种族主义、制度混乱、社会隔离与社会融合这类真切的现实议题,或只顾大而空泛的“应然”理念,或一味钻入琐屑的细节之中。
立场理论从一种批判的理论更多地转换为一种批判的工具。它首先是一种被压迫者的声音,被压迫者、被歧视者开始尝试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表述自己的声音——在以往的主流教育社会学中被消匿的声音。有色人种、女人、同性恋、有障碍者开始重新划定其疆域,挑战教育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分析工具甚至研究传统。
首先,立场理论挑战着本质主义。[17]立场理论强调研究者的立场,知识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知识的生产者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如何?传统的认识论认为知识与认识者自身的位置无关,知识是外在的、等待着被发现的事实。晚近尤其是在女性主义、后现代的研究域中,知识是建构出来的。立场理论质疑认识上的特权主义,男性白人在所生产的理论中凝冻着其自身的特权,他们凭借认识上的霸权、出版上的霸权,将建基于其立场上的特殊主义的认识转换为普遍主义的叙述,并采用去立场化、去价值化、去情境化的策略,驱逐来自不同立场的其他声音。
立场理论宣称其理论的发展来源于研究者所身处立场的差异性,女人的天地不同于男人,女人的社会位置不同于既往生产知识特权者的位置,因而,女人的研究视野能够引导知识的生产与对社会实体的新解释。哈丁(Harding)从女性的生活引发出这样的疑问:“谁的科学?谁的知识?”,知识根植于不同的主观情境与社会情境,研究本身体现出社会的价值诉求与政治诉求。[18]知识总是落座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甚至是个人境遇的某种表达,任何表述都有其局限性,也都有其背景性。唯此,表达才是真实的,也才是真诚的,水一般清澈的日常生活中才有那么多常人难以觉察、难以置信的诡秘。在黑泽明执导的《罗生门》中,每个人的解释在其个人情境中都是真实的表述,本质主义的犯罪观被重新解释了——谁是谁非,一个客观的事实不再存在,而是借助权力,某些特殊的话语能否转换为公众的意识;或许是特殊的话语之间彼此协商、沟通,并达成共同接受的一种解释。
女性主义研究者进而开始质疑本体论,并将新的本体主义感觉论带入教育社会学和社会生活、社会活动的新领域——将特殊的性别与情感带入研究领域之中,女性主义开始了其身份政治。女性主义赋予学校性别的视角与框架,认为学校的场域极大地忽视着女性独特的经验,在教育目标上、学校评价上以及课程与知识上,教育都再制着男性与女性的区隔与对立,将女性定义为“非男性”——男人的指标成为人的常态指标,女性在此指标体系下永居劣等。女性主义批判的锋芒甚至直指马克思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认为仍然是观念上的“父权制”。[19]女性主义正是从询问性别本质为何这样一些基本问题开始,扩展到询问社会身份本质,开始消解本质主义。
其次,立场理论还挑战着研究的过程与方法。女性主义活跃在文学、法律、大众文化、自然和社会科学话语中,女性主义挑战着这些学科的“科学集体无意识”,既包括研究过程本身——生产学术的模式,也包括研究的主题——研究者的悖论——寻找研究者的主观性。[20]哈丁1986年指出,社会学研究如同“手工劳作”,而非现代科学研究中盛行的工业化与科层化的模式。女性主义从最根本上挑战着男性研究中的“上帝之眼”。[21]
在对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反省上,莫蕾(L.Morley)1996年发表了《与父权制协商:女性研究的挑战》,指出许多研究都是所谓“强奸研究”(Rape Research)。女性在参与父权化的研究中被视为可以被任意剥削、任意闯入的客观对象,研究者为了自己的专业声誉与职业发展可以任意闯入女性的生活之中,却从不反省这样的研究过程对参与者有什么伤害。[22]女性主义在对父权化的研究批判中,呈现出多元的认识论,她们还试图用协作的、参与的、合作的新型研究风格来替代男性化的研究风格——个体主义、竞争主义与主客对立的研究风格。赖塞尔称其为“女性主义人种志研究”,她们致力于让沉默的、受压迫的人发出声音来。相应,也有声音用苏格拉底的对话法或精神助产士(催生婆)来寄托对女性主义人种志研究的期许,每一次询问既是话语,更是新的实践。[23]
值得重视的是,立场理论并非一个整合的理论,在强调研究者立场这一策略下,各种立场的研究者之间也充满分歧与冲突。譬如,主流的女性主义与同性恋、有色人种主义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然而,女性主义的普遍性的政治诉求,女性所共享的诸多经验超越了种族与阶级性、年龄与文化背景,因而,迥异的女性经验被笼统地归类于“女性经验”的框架之中,将女性研究者视为一个共同的“阶级”或享有一个“背景”。
再次,立场理论的实践还有效地挑战着教育社会学中的传统并重塑着教育社会学的未来。教育社会学中盛行着西方中心主义,欧洲尤其是来自昂格鲁·萨克逊森的哲学传统、内容与目的,确定着教育社会学的发展;教育社会学主流声音多来自法国、德国、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经济上的优势帮助它们攫取智识上的霸权。艾恩奇(Lynch)以爱尔兰为个案探讨高等教育中的平等问题时,发出这样的感慨:小国家要开启自己的理论传统、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是多么艰难![24]
从全球化的视角来看,文化市场的开放并非无条件的,政治与经济的殖民者常常也成为文化上的殖民者。社会学是一种具体社会历史情境中的话语,各个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与经济发展又多么不同!近20年来,全球民主化日益高涨,官方的社会学对本土——具体情境中的社会思想的符号暴力受到一系列的挑战,尤其是女性主义理论与研究——她们(他们)之后的立场理论的挑战,让研究者——具体的、真实的、丰富的人回到研究中。研究过程也罢,理论假设也罢,都要体现人的情感、人的思想。多元化、本土化、个人化体现在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之中,教育社会学呈现出戴维斯(Davies)所谓的“做社会学”(Doing sociology)的迥异风格。[25]结构化的、外现的sociology——其中的学科界限、学科戒律逐渐淡化,重要的是doing之发出者——人的意志、doing之过程——个人化的风格、doing之结果——融入本土生活,“这一个”教育社会学而非“那一个”——美国的或英国的教育社会学。不同地域的教育社会学纷纷出现风格迥异、思路同构的“本土化”倾向——即鲍尔所言:教育社会学的流变是一系列能动的、本土化的建设。[26]
立场理论中所凸现出的个体性、多样性与差异性,既是大理论、大叙事的终结,又是新的开始,后现代理论在教育研究中蔚然兴起。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总结:20年前,教育社会学用新马克思主义所酷爱的再制、权力等概念与结构功能主义做周旋;20年后,立场、身份与差异——教育社会学中日渐盛行的后现代话语,用不争之争的策略走出了后实证主义的阴影。教育社会学从“新”走到“后”,人——具体生活中的人终于回到了学科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