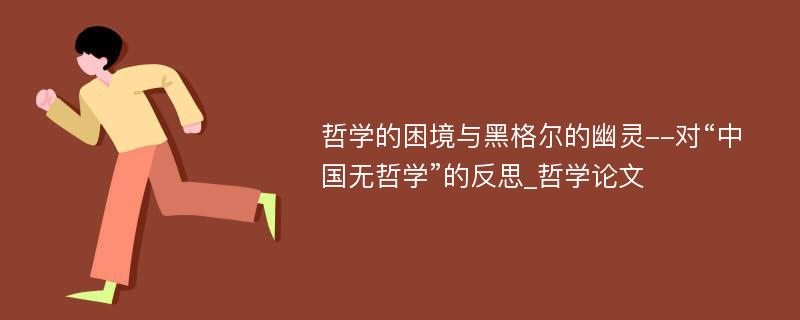
哲学的困境和黑格尔的幽灵——关于“中国无哲学”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黑格尔论文,哲学论文,中国论文,幽灵论文,困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从“名实之辩”看中西转换
近代西学东渐,中国的思想文化和学术界涌现了一批外来名词。如果这些名词所反映的对象中国本来没有,完全是从西方传来的,一般不会引起争议。如果指称中国固有的事物,争歧往往不断,并常常困挠我们。这里,我们首先遇到的是一个逻辑困境,按照中国的术语,是一个“名实”关系问题。也就是说,这些西来的“名”,究竟能否正确地反映中国的“实”?
近代中国出现的一些“名实之辩”,往往是跟中西文化碰撞中对西方一些名词的汉译解读直接相关。如,“中国宗教是不是宗教”、“中国哲学是不是哲学”等问题的提出,其根本症结就在于用“宗教” (religion)和“哲学”(philosophy)这两个本于西方的“名”来指称中国的“实”。荀子说“约定俗成”谓之“名”,一个名词能否通行,有时并不仅仅取决于它能否正确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还取决于经验和习惯。以“实”定“名”和以“名”指“实”是概念与实体之间的一种基本关系,从逻辑学上说,概念如不能正确地反映客观对象的本质属性,那就是一个虚假概念。然而,在不同的文化系统乃至同一文化系统中,不同的“实”可能有不同的“名”,说穿了,“名”只是“实”的一种符号表征而已。归根到底,“名”是次要的,“实”的自身状况才是关键所在。
就“实”而论,它必然是具体的,人有我有,就可以从意义上翻译其“名”,这叫译词。所谓译词,即不同语言系统中在意义上能够通约和通释的词汇。所谓借词,即整体借取、整体移植的外来词汇。诸如“迪士科”、“沙发”、“沙龙”等等,皆属借词。在缺少可比性前提下使用译词遇到困难或准确度欠佳的时候,借词往往更能准确地反映实体的本来面目。
另有某些“实”,人有我也有,虽然彼此仍具有大致相同的本质属性,但却打上了深厚的不同民族和文化的烙印,差异性明显,音译不利于消化和吸收,通常也可用意译。但由于缺少现成的能准确表达实意的译词,需要摹实取名,创出新的词汇;或是加上限定词,以标明特性。
中西方之间,如果只关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极易自我设限。当然,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人有我无”的窘境时有发生,这些都完全可以通过借鉴、沟通、学习而达到理解与分享。今人往往拘泥于西方标准理解中国文化,这种情况不仅可以发生在哲学身上,也可以推演到其它学科身上。如果按照学科的西方之“实”来审视中国之“名”,我们不可避免地会跌入“名”、“实”淆乱的困惑之中。
中西哲学之间的学术转译、通约和交流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比较哲学研究的过程。一般来说,“人有我有”就得比较,从比较中找到双方的共性作为共同的标准,应避免在价值判断上以一方剪裁另一方。比较研究的目的是取长补短,促进交流,共同发展。因此,对于“人有我无”的东西,要么舍弃,要么“拿来”。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始终存在着一个合理性的问题,却从来没有一个“合法性”的问题,因为判断一个学科能否成立的标准,最终还是依学理和客观需要而定,而不是依先定之“法”和人为预设而定。说一个学科的存在是否具有“合理性”则可,说是否具有“合法性”则不可——那是误用了“合法性”这一术语。
一个文化势位高的民族,在翻译外来语言时必然译词多于借词。相反,则是借词多于译词。如果在文化势位上以畸低对畸高,处于一种极不对称、极不平衡的地位,在强势文化和语言霸权面前,本民族的语言就有可能处于丢失、灭绝或者最终被外来语言吞噬的危险。此种情况的出现便意味着这个民族尽管形式上还存在着,但事实上已经消亡了。所幸的是,中国文化是一个有着五千年传承的高势位文化,历史上在与境内外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中,多是用译词解读外来文明,并通过这种意译的方法,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并把它转化为自己文化中的有机部分。如中世纪对佛教文化的吸收和近代对西方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吸收,既反映了我们文化底蕴的深厚,又反映了我们的文化具有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
二、“黑格尔标准”和“西方主义”
“中国有没有哲学”跟“中国有没有科学”一样,也是一个沉寂了几十年的老话题。旧话重提,虽无新意,但仍能吸引不少人的眼球。应该承认,这个问题的内在原因复杂,甚至深刻,因为它透露了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当今社会的价值危机,尽管这种危机的深层原因并不在于“名”、“实”之辩,也不在于中西之异,但要清算这一问题,则并非易事。
争论中国有无“哲学”之“名”并无意义,关键在于中国有无philosophy之“实”,这才是问题的核心。人们只知道日本人西周氏在1837年首创“哲学”一词翻译中国传统的儒、释、道的“义理之学”,而不知早在数百年前,西方人便认定中国的“义理之学”就是西方的philosophy!早在16世纪,西方人就“发现”了中国哲学,这早于日本人西周氏把philosophy翻译为“哲学”近三百年。无论是16世纪的利玛窦把中国的“易学”翻译成philosophy,还是19世纪的西周把philosophy翻译成“哲学”,都说明在中国的确存在着philosophy这一基本事实。philosophy在两个文化系统中不可能完全等同,必然表现出个性化的差异,但就其一般的本质属性来说则没有什么不同。为了避免“惑于以名而乱实”或“惑于以实而乱名”,今人在讨论哲学史上的问题时,必须标以“中国哲学”和“希腊哲学”以示区别。
有必要提请大家注意的一个现象是:每当有人出来说“中国没有哲学”时,总要抬出黑格尔。足见黑格尔的影子——或者说黑格尔的幽灵一直在中国哲学界上空徘徊——跟它同在的就是挥之不去的“西方中心主义”。可是,黑格尔从来没有说过“中国没有哲学”这句话。相反,他认为中国有一种自己的哲学。他认为孔子算不上是一个“思辨哲学家”,在他那里只“是一种道德哲学”(实际上袭用了利玛窦的说法),说“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然而,他没有否认“道德哲学”也是哲学。黑格尔更没有说《易经》、《老子》和朱熹“理学”不是哲学。当然,黑格尔认为中国哲学概念缺少“规定性”,或者说缺少确定性,甚至说中国哲学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排除这些西方主义的偏见之外,我们发现黑格尔不得不承认中国有哲学这一事实。
黑格尔在考察世界上各种哲学体系时,无法掩饰其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情结。他以希腊哲学的传人自居,黑格尔出于情感上的需要,自然会以“希腊标准”裁判一切。恩格斯、丹皮尔、罗素等人在提到希腊哲学从公元3世纪到10世纪湮埋了数百年后重新被发现的这段史实时,无不对阿拉伯人在哲学上的卓越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然而黑格尔却说:“关于阿拉伯人,我们可以这样说:他们的哲学并不构成哲学发展中的一个有特性的阶段;他们没有把哲学的原理推进一步。”
遗憾的是,“黑格尔标准”和“西方中心主义”仍然是一些人最常用的裁判一切的尺度。
三、“否定之否定”——形而上学的怪圈?
黑格尔的幽灵并没有阻挡住19至20世纪以来哲学王国领域的多元化拓展和哲学定义的多样化趋势。Philosophy在今天的西方早已不只是停留在“爱智学”的层面或向度上了,它的多次危机促使其在内涵与外延两方面屡获突破,“爱智”的初衷一如孩提时代一抹淡淡的梦痕仅残留在哲学发展的轨迹上。我们无法历数现在世界上到底有多少哲学的定义(罗素说过:“有多少哲学家就有多少哲学。”),我们要说,把哲学仅仅定格为“爱智学”的原始含义,早已是很不合时宜的了。
事实上,“爱智学”在公元3世纪就已经中断了。即使在笛卡儿时代,对于希腊的形而上学本体论也不全是一种认同的态度,拒斥形而上学的思潮与欧洲进入哲学时代同期而至。黑格尔哲学表现出了对康德的某种反动,但却开始了对希腊形而上学精神的复归。正是黑格尔本人,营造了“哲学是什么”或“什么是哲学”的理论困境。
对黑格尔哲学采取“拒斥”态度是整个19世纪至20世纪欧洲哲学的主流,它们展现了强大的阵容,这就是影响至今的实证主义的各种流派。从孔德、斯宾塞的实证哲学到维也纳学派的分析哲学再到美国的实用主义,把科学主义引入哲学,在“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下反思传统,一时形而上学成为强弩之末。按照“拒斥形而上学的”论点,黑格尔哲学也不是哲学。在形而上学那里,无本体论便无哲学,但传统本体论仅仅是一种逻辑建构,而实证主义者坚持认为本体应该是可以实证的,不能被实证的本体尽管逻辑上可以自足(如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但在实际上不能成立。这样,黑格尔哲学在实证哲学面前自然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合理性,按时髦的话语说,即失去了“合法性”。即使师出于黑格尔学派的马克思,也声称自从近代自然科学诞生之后,作为“科学的科学”的哲学已经死亡——恩格斯宣称:费尔巴哈是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德国古典哲学已经终结,代之而起的是分门别类的实证科学。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愧为伟大的哲学家,但他们从来没有宣称他们的学说是“哲学”,按照恩格斯的说法,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只能属于科学。
对形而上学的这种大颠覆实际上是对黑格尔哲学标准和哲学定义的大否定,也是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大否定。
从尼采“上帝死了”到海德格尔的“诗意的栖居”,再到当代德里达对“语言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消解,实际上开显出一种“文化哲学”的发展趋势,科学主义被当作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必然结果加以批判,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深陷空前的危机,其阵容可谓溃不成军。然而,“哲学”这一概念的躯壳仍在被袭用。遍观当代哲学界各种流派,谁也不会因为拒斥形而上学和本体论而被认为“不是哲学”,更不会遭遇到“不是哲学的哲学”之“合法性”的质疑。如今,就像人们没有理由斥责马克思、孔德、尼采、本格森、海德格尔、福柯和德里达的哲学“不是哲学”一样,人们更没有理由斥责《易经》、《老子》、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中的形而上学的本体论“不是哲学”!
科学是知识论的产物,现代科学是知识论发达的产物,科学的使命就是要去穷究具体实体的奥秘,在科学原理的指导下产生了日新月异的技术。但是,现象和物质世界是无限的,科学的使命也是无限的。无限地去接近绝对真理又不可能穷究所有的真理,在科学的触角抵达不及或暂时无法触及和无法解释的领域,便是神学自由翱翔和大展身手的天地。换言之,一切可以证实或证伪的理论是科学的真理,一切既不可证实又不可证伪的理论便是神学的领地。科学给人们提供源源不断的便利,是天字第一号的理性工具,因而倍受青睐;神学拯救着人们的灵魂,向人们提供进入天堂的廉价门票,同样具有实用的价值。唯独哲学,把科学和神学丢弃的不毛之地捡拾过来,开垦出来的却是一块空灵世界,其贫困、无用和无奈,怎能不导致对其“合法性”的质疑?
然而,正像冯友兰先生曾经指出的那样,传统的形而上学被否定之后,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遂成为当代文化思潮的主流,而关于人类安身立命的大道理却没有人讲了,因此,他呼唤“重建形而上学”。于是,在一片“哲学的终结”、“哲学的解构”声浪中,黑格尔的幽灵渐渐遁去却又悄悄而来。人们突然意识到,正是黑格尔的幽灵,或者说正是“逻各斯中心主义”使得当代哲学至今并没有走出从反形而上学到不得不回归形而上学的画地为牢的百年怪圈!不过,新世纪的形而上学将不再是“黑格尔标准”的思辨哲学了,而是一种维柯(18世纪意大利哲学家)式的“人类形而上学”或曰“文化哲学”。可见,所谓“文化哲学”,正是这样一种立足于人类的类存在,以超越思辨哲学的先验论域,站在高起的历史和人文精神的平台上,用更加广阔的文化视野和更加真切的人文关怀,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及其生存境遇作出深刻的透析,并给予理论总结。因此,“文化哲学”亦即“人类的形而上学”。
从“理性形而上学”到“拒斥形而上学”再到“人类形而上学”,近二百年的西方哲学发展史走出了一个形而上学“否定之否定”的圆圈,这是一个螺旋发展、无限向上的圆圈,21世纪的世界哲学,正在展现一种哲学家模式大转型的圆圈,21世纪的中国哲学,必将被定格在这个转型圆圈的至高点上!
摘自《文史哲》(济南),2005.3.18~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