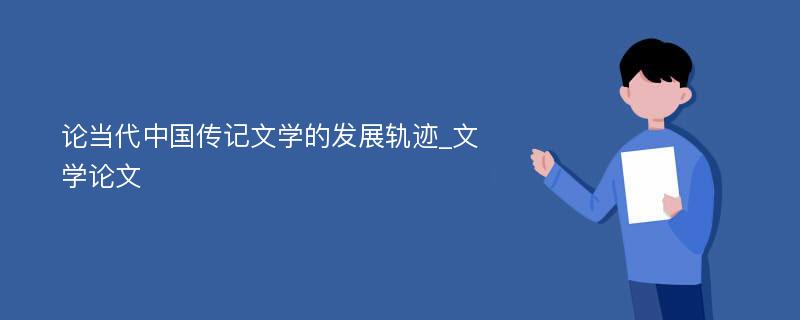
论中国当代传记文学的发展轨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记论文,轨迹论文,中国当代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657(2002)05-0008-08
中国当代传记文学,是指新中国以来创作的,艺术地再现真实人物生平及个性的文学 样式。伴随着人民共和国53年的风雨鸡鸣和沧桑记忆,传记文学在承传与变异、认同与 超越、写人与造神、歌颂与批判的两难选择中,上下求索,多方参照,几度坎坷,几度 辉煌,走过了一条极不平坦的发展道路,终以多元开放的创作态势构成一个色彩斑斓的 艺术世界,融汇到汪洋恣肆的世界传记文学大潮之中。
纵观建国53年传记文学的发展轨迹,我们认为,大致可以划分为“建国17年”、“文 革10年”、“新时期13年”、“后新时期11年”以及“新世纪2年”五个段落来考察。
建国17年(1949-1966):传记文学的初步繁荣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也为当代传记文学创作的发展开 创了无限广阔的前景。从1949年到1966年的17年间,除译传外,我国内地共出版人物传 记500余种。传记创作获得了较大发展,从而形成了一种初步繁荣的局面。
建国之初,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已是不容置疑的方针政策,具有 悠久历史传统的传记文学对此较早地做出了积极的响应。1949年8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印行的《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萧三),迅即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很快被译为英 、德、日、法、捷克、匈牙利等多种文字,对树立革命领袖的权威形象,起到了明显的 推动作用。从1949年到1956年,当代传记文学初具规模,革命英雄传记大行其道,引人 注目的便有:梁星的《刘胡兰小传》、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周而复的《白求恩 大夫》、林音频、刘树墉的《郝建秀》、叶坪的《伟大的方志敏》、苗培时的《矿工英 雄马六孩和连万禄》、丁洪、赵寰、董晓华的《真正的战士——董存瑞的故事》、高玉 宝的《高玉宝》、雷加的《海员朱宝庭》、柯蓝、赵白的《不死的王孝和》、韩希梁的 《黄继光》、以及建国后第一部集体创作的、规模宏大的传记文学《志愿军英雄传》等 。这些传记作品尽情讴歌工农兵英雄模范人物,反映了新中国蓬勃向上的时代风貌。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同年秋,中国文联机关刊物《文艺报》编辑部专门召开了“传记文学创作问题”的座 谈会,用以推动传记文学的发展。从1957年至“文革”发生前的十年间,革命回忆录这 种新兴的史传文学形式在一段时间内得到了蓬勃的发展。《星火燎原》与《红旗飘飘》 这两套大型丛书,集结了当时最有代表性的短篇回忆录。其它如陶承的《我的一家》、 缪敏的《方志敏战斗的一生》、杨植霖等的《王若飞在狱中》、黄钢的《革命母亲夏娘 娘》等一批优秀中长篇传记作品,也都传诵一时,深受欢迎。但是,这种欣欣向荣的发 展不久便遇到了挫折。1962年,康生一伙以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为名,诬陷长篇 传记小说《刘志丹》为“反党小说”,致使作者李建彤遭到残酷迫害,株连上万人,造 成古今稀有的大冤案,于是革命的史传文学创作便偃旗息鼓,无人问津了。
历史总是曲折地发展着。1963年,共和国一个普通士兵——雷锋的名字响彻神州大地 ,中国青年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推出《雷锋小传》(陈广生)。这本英雄传记随着毛泽东 等革命领袖为雷锋同志的题词而家喻户晓,颇具轰动效应。
在英雄传记的主潮之外,17年的传记文学还有非主流的传记值得一提,如冯至的《杜 甫传》、朱东润的《陆游传》、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溥仪的《我的前半生》 、马可的《冼星海传》等,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传记文学的人物画廊。
综观建国17年的传记文学,承续了五四以来现代传记文学“新民”与启蒙的优良传统 ,其主题大多是单一、明朗的,带有明显的政治功利性和鲜明的时代特征;题材内容以 反映已经逝去的革命历史或正在进行的现实斗争为主;传主以革命先烈、当代英模居多 。不少作品在史实求真的基础上还颇有文采。这些英雄传记,发行量大,读者众多,它 配合当时的政治形势,宣扬共产主义、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集体主义思想,凝聚 民族向心力,发挥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如《把一切献给党》出版不到一年,就四次 印刷,印数达200万册,至60年代中期,累计印刷1000多万册,并被译成多种外文读本 ,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这一时期的传记文学的主要缺陷是:还存在着传主 类型较为单一、题材狭窄的毛病;不少作品艺术粗糙,创作上出现了公式化、概念化、 简单化的倾向,传主形象失之片面,个性模糊,只见叙事,而不见闪动鲜活的人性的身 影;有的传记自觉不自觉地拔高、神化,甚至人为地造假失真。
“文革”10年(1966-1976):传记文学的停滞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 ·一六通知》。以此为标志,我国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 年“文革”,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传记文学创作事业也受到了严 重的摧残。在这场浩劫中,林彪、“四人帮”以文艺为篡党夺权的突破口,疯狂推行封 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他们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准以任何艺术形式表现真人真事 。“旗手”还下达了这样一道懿旨:“……就是刘胡兰,也还是不要写真人真事!”这 样一来,所有以前歌颂真名实姓的英雄传记便统统被封杀,为老一辈革命家写史作传的 作品,自然更是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作家马烽1964年就完成了《 刘胡兰传》的初稿,当时,中国青年出版社曾排印了数百册样本,分送给刘胡兰烈士的 家乡云周西村党支部、文水县委会、山西省委、原晋绥边区的领导人,以及烈士生前友 好和有关单位征询意见。各级领导和熟悉刘胡兰生平的同志,在百忙中对传记进行了审 阅,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作家也据此进行了修改,之后出版社又重新付排,并已打出 了清样,但难逃夭折的厄运。[1](P405)
“文革”十年,“左”的思想泛滥到各个领域。许多传记作家横遭迫害,传记文学创 作与出版呈现一派萧条荒凉的景象,这是传记文学的停滞期。“四人帮”一方面不准他 人立传,另一方面又大搞阴谋文艺。在传记写作中,根据政治运动的需要而篡改史实, 以服务于现实斗争的情况时有发生,如为配合“四人帮”的评法批儒而出版的几本颠倒 是非、歪曲历史的人物传记小册子:《孙丘反动的一生》、《孔家店的二老板孟珂》等 ,又如“石一歌”的《鲁迅传》、《鲁迅的故事》等。
但本时期的传记写作仍出现了一种罕见的文学现象——“潜在写作”。“潜在写作是 指作家不是为了当时公开发表而进行的写作活动。”[2]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能看到的在 “文革”中写作,可以称为传记文学的作品有两部,一部是剧作家陈白尘的《牛棚日记 :1966-1972》,一部是传记文学家朱东润的《李方舟传》。这两部写于“文革”之中 的“地下书”,作者生前都未能亲见它们的出版。
从1966年9月11日被关在中国作协的“牛棚”起,陈白尘便开始写日记,且从此没有中 断。整整七个年头,每逢夜深人静之时,他便偷偷地坐起,用着只有他自己能够看懂的 符号以及各种各样的缩写,记录下那个恶梦一般的时代。1973年,陈白尘终因心脏病频 发而被“恩准”回南京治疗,在那段隐姓埋名的日子里,他重新翻出这摞日记,将那些 符号、缩写“翻译”成文且整理成篇。这些曾经冒着生命危险写下的“实录”,记载的 是那一段曾令人迷惘、令人痛心的历史,值得人们再去细细地咀嚼。
《李方舟传》“这本书的写定,是在波涛汹涌的‘文化大革命’中进行的”。[3](P10 8)朱东润夫人邹莲舫女士在“文革”中不堪折磨,以死相抗。为怀念亡妻,寄托幽思 和孤愤,朱东润采用托名的形式,“在惊涛骇浪中写成”了这部特殊的传记。迫于时势 ,书中的人名、地名都用了隐语。
新时期13年(1977-1989):传记文学的复苏与振兴
新时期的传记文学,经历了一个相对冷寂——复苏——振兴的全过程。人们记忆犹新 ,当粉碎“四人帮”的头几年,传记文学园地还相对冷清,仅仅再版了《刘胡兰传》、 《未完成的画》、《闻一多传》等几部旧作,和《梅尧臣传》、《任弼时》、《随卫敬 爱的周副主席》、《高士其爷爷》等几部屈指可数的新传。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 国传记文学创作逐渐走出低谷,出现了一批瞩目之作。直至80年代中期,随着纪实文学 潮的到来,传记文学创作呈现一派兴盛景象,不但数量多,质量也很高。以刘白羽、何 晓鲁、铁竹伟、郭晨、张俊彪、权延赤等为代表的领袖/将帅传记文学,以林非、刘再 复、肖凤、凌宇、林贤治、李辉、石楠、廖静文、赵云声、倪振良等为代表的文学家/ 艺术家传记文学,以徐铸成、叶永烈、泰栋、罗岩等为代表的恶人传记文学,共同组成 了新时期传记文学最亮丽的名人风景线。
传记文学在新时期为什么会得到蓬勃发展?究其实,是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的旷世 伟业,为中国有良知、有志气和有才能的传记作家提供了创造优秀精神产品的丰厚土壤 和用武之地,他们得以冲破思想的牢笼和创作的禁区,才创作出了一大批无愧于时代的 优秀之作。
新时期传记文学的第一个热点是领袖/将帅传记文学。由于诸多原因,过去我们较难读 到由中国人自己撰写的描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传记, 这种现象,在新时期已不复存在。老作家刘白羽的《大海——记朱德同志》,以饱蘸激 情的笔触写出朱德上下求索,由农民到旧军官到共产主义者的升华,清晰地描绘出朱德 革命思想发展的轨迹。苏叔阳《大地的儿子——周恩来的故事》,以较大的篇幅描绘了 周恩来少小立志、胸怀天下的故事,给“振兴中华”的青少年留下深刻的印象。权延赤 《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等传记,则成功地完成了领袖由“神”向“人”的还原。作品鲜 明突出的特色,“就是一反过去政治化或泛政治化、单从社会变革或党性阶级性角度写 人的叙事模式,首先把领袖还原为一个具体的人,当作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个体来塑造; 着重表现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精神情感世界,从人的基点上透视,寻找内在的审美价值。 ”[4]
将帅传记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的,首推军队女作家铁竹伟写陈毅在“文化大革命” 中的断代传记文学《霜重色愈浓》。作品真实、准确、形象地再现了“文革”的历史, 讴歌了陈毅元帅在极其严峻的考验面前,光明磊落,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无产阶级革 命家的崇高品格。这部作品与另一位军队女作家何晓鲁的《元帅外交家》,以及她俩合 写的《一个人和一个城市》一起,组成“陈毅文学传记”三部曲。接下来,点点以自己 父亲罗瑞卿大将为传主,向人们坦诚率真地再现了那《非凡的年代》。此外,写其它老 一辈革命家的传记作品,产生较大影响的还有郭晨的《巾帼列传》、张俊彪的《血与火 》、王朝柱的《李大钊》、柯岩的《永恒的魅力——一个诗人眼中的宋庆龄》、王观泉 的《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等。这些作品不仅使老一辈革命家的彪炳业绩德 厚流光,也为传记文学增添了新的色彩。
新时期传记文学的另一个热点是文学家/艺术家传记文学。过去无人敢为“臭老九”立 传,而在新时期,一批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也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传记文学的舞台,真 正是“人类的群星闪耀”!以文学家为例,就有林非、刘再复的《鲁迅传》、肖凤的《 萧红传》、《庐隐传》和《冰心传》,田本相的《曹禺传》、凌宇的《沈从文传》、林 贤治的《人间鲁迅》(第一部、第二部)、桑逢康的《感伤的行旅——郁达夫传》、柯兴 的《风流才女——石评梅传》、李辉的《胡风集团冤案始末》等。以艺术家为例,就有 廖静文的《徐悲鸿一生》、石楠的《张玉良传》、倪振良的《赵丹传》、赵云声、冼济 华的《话剧皇帝——金山传》、郑理、佳周的《李苦禅传》、纪宇的《青铜与白石—— 雕塑大师刘开渠传》等。
在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还欣喜地发现,新时期还开始大量涌现了建国17年所从未有 过的传记文学新品种——恶人传。这类反派人物的荣辱兴衰,往往折射出时代和社会变 幻的风云。老报人徐铸成的《杜月笙正传》(1981)首开先例,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了流氓 大亨杜月笙“这一个”的独特个性,继而他又用《哈同外传》(1982)为一个外籍“闻人 ”立传。这两本为反派人物立的传记,使人们有理由相信,在不久出现的传记文学作品 中,将会看到更丰富的、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
人们的愿望没有落空。1985年,《魂断武岭——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日子》(泰栋、罗 岩)面世,作家将镜头直接对准了独夫民贼蒋介石,揭示了他几十年来与人民为敌,逆 历史潮流而动的悲剧性结局。1988-1989年,叶永烈以《“四人帮”兴衰》——《蓝苹 外传》、《张春桥浮沉史》、《姚氏父子》、《王洪文兴衰录》等四部长篇,揭示“文 革”秘史,大大拓展了传记文学的题材领域。
新时期13年的传记文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打破了 几十年来我们自己手造和心造的各种框框和思想牢笼,许多禁区已经突破,在题材方面 有了新的拓展,传主类型日益丰富,结束了建国17年英雄传记一统天下的尴尬局面。我 们的传记文学,不仅写了无产阶级革命家、文学家、艺术家,而且还写了科学家(如吴 崇其、邓加荣的《林巧稚》)、学者(如杨建业《马寅初传》),甚至还写了蒋介石、“ 四人帮”等一些反面角色。2、传记创作不仅注重了真实性,而且文学性也有了很大的 加强。开始注意对人性的发掘。注意从兄弟文学、艺术中借鉴吸取许多表现手法,如小 说的细节刻画、心理描写,散文的抒情联想,诗歌的意境创造,电影的剪辑手法等等。 多种手法的引进,增强了传记文学的文学性。3、传记创作蔚为大观,无论在数量质量 上还是社会效果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况。这一时期,据说出版了各类长篇人物传 记3000余种,被后来人们誉为“传记艺苑常青树”的三大传记刊物——《人物》(1980) 、《传记文学》(1984)、《名人传记》(1985)也相继创刊,发表了大量的中短篇人物传 记。4、传记文学的理论研究开始提上议事日程。如《人物》杂志在1981——1982年展 开了“关于传记作品的写作问题”的讨论,《传记文学》开辟了“传记创作研究”栏目 ,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等相继召开传记文学研讨 会、座谈会等。
这一时期的传记文学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概而言之,则是“四多四少”:“即宣传革 命家、军事家、文学家多,宣传科学家、教育家、企业家少;介绍大人物多,介绍小人 物少;介绍外国古代近代人物多,介绍我国当代人物少;介绍盖棺论定者多,介绍活着 的人少,许多青年崇拜的同龄杰出人物更少。”[5]
后新时期11年(1990-2000):传记文学的崛起与嬗变
20世纪90年代,随着“大众传媒的崛起,消费浪潮的出现,‘冷战’后世界格局的转 换带来的新的全球化进程使中国文化进入了一个‘后新时期’。”[6]转轨换型的市场 经济社会里,名人无疑是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名人传记自然也成为非虚构文学中最受 欢迎的体裁。连不写传记文学的作家陈建功也感慨系之:“我以为我们的诗歌和小说创 作的确面临着一些还待解决的严峻问题;而相比之下,作为跨越于史学与文学之间的文 体,传记文学则正充分显示着它的文体上的优势,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的确呈现出比 其它文学品种更为生气勃勃的前景。”[7]这就是:传记文学的崛起与嬗变。
后新时期的传记文学热点不断,高潮迭起,真正呈现出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多元化 艺术格局。可以说,任何一种类型的传主包括革命家、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文学 家、艺术家、学者、企业家、科学家、英雄、恶人、明星乃至平民都有人写,一个作家 写作多部传记,一个传主拥有多种传记的现象屡见不鲜,这里只能择其要者谈谈。
领袖/将帅传记文学仍然是这一时期的“领衔主演”。毛泽东、周恩来的传记多得不可 胜数。继新时期将领袖由“神”还原成“人”后,这一时期不断走向深化。或选取传主 的早年或晚年的政治生涯,再现一代伟人为寻求真理锲而不舍,为实现理想奋进不息的 生命轨迹,如《早年周恩来》(庞瑞垠)、《周恩来的最后十年》(张佐良);或截取传主 政治生涯的某一中段聚焦,再现传主所经历的时间激变的风雨云烟,如《开国领袖毛泽 东》(王朝柱)、《渴望真话——刘少奇在1961》(张步真);或叙写领袖的日常私生活, 以文学——人学的目光,透视传主包括爱情、婚姻、家庭在内的多元生态,如《李敏· 贺子珍与毛泽东》(王行娟)、《朱德和康克清》(纪学);或把目光投向领袖的文化心理 结构,从开阔遥远的文化视角来剖析领袖作为诗人、作为文化人一生的心路历程,如《 文人毛泽东》(陈晋)、《诗人毛泽东》(刘汉民)。特别是由领袖的子女所写的一批传记 作品的出版,更使领袖传记文学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代表作有毛毛所写轰动海内外的 《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及续篇《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辽宁人民出版 社的《父辈丛书》等。后新时期将帅传记佳作引起读者的共鸣与兴趣的,先后有尹家民 的《风流大将军》(陈赓传)、董保存的《谭震林外传》、陈廷一的《许世友传奇》和东 方鹤的《张爱萍传》等。描写其它革命家的传记中,金凤的《邓颖超传》、忽培元的《 群山——马文瑞与西北革命》颇为感人。另外,当代国际政坛风云人物也大量进入我国 作家的视野,粗略统计,这方面的传记近百种之多。
企业家或实业家传记是这一时期传记文学的重要收获。经过改革开放十来年的思想和 精神准备,我们不再忌讳有人扣“为资产阶级树碑立传”的“左”的帽子。不少思想敏 锐的作家迅速调整视角,为人们重新认识现代资本家、重新认识现代资本主义写下了新 的篇章。于是,《中国大资本家传》、《中国红色资本家丛书》、《十大富豪传奇》、 《世界华人精英传略》等丛书应运而生;桑逢康的《荣氏家族》、王慧章的《王光英传 》与夏萍的《李嘉诚传》、《曾宪梓传》结伴而至。这些传记以真实准确的史料为依据 ,运用文学手法,通俗、生动地描绘了民国、港、澳、台、海外华人有代表性的工商巨 子、富豪大亨的创业历程、生财之道、人生百态,使很多读者受到了鼓舞和启发,也给 很多人带来了新的梦想。此外,内地当代企业家《贝兆汉传》、《中国女杰刘志华》、 《国药冯》、《农民企业家》等同样成为人们模仿的对象。
与商界成功人士同时保持高频率“出镜”率的是一拨科学家的联袂亮相。几年前寥若 晨星的科学家传,伴随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和“科教兴国”的战略日益 深入人心,如鱼得水,得到长足的发展。作家们将目光投向因特殊时代原因而长期默默 无闻、不为人知的中国当代科学家群体,从此,这些赫赫有名却长期隐姓埋名的人物, 撩开神秘的面纱由幕后走上了前台。在描写“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传中,我们可以读 到王淦昌、邓稼先、钱三强、钱学森、王大珩、彭桓武、任新民、孙家栋、王希季、陈 芳允、杨嘉墀等人为传主的多部传记作品。90年代末的《中国国防科技科学家文学传记 丛书》与新世纪初的《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丛书相映成趣,让人们走近科学家的同时 ,充分领略了科学家迷人的风采。“863”高技术科学家也成为新的文学传主,如徐光 荣的《科技帅才蒋新松》、聂冷、庄志霞的《绿色王国的亿万富翁——杂交水稻之父袁 隆平传》。这类传记以呼唤国家意识的复苏与重构,引起国人的广泛关注。此外,描写 传统科学家的传记作品,同样受到读者青睐,如数学家王元写的数学家《华罗庚》具有 不同寻常的特殊价值。
包括文学家、艺术家、学者在内的文化名人传记长盛不衰,无疑是这一时期的佼佼者 。其艺术生命力,或许将胜过同时期的领袖/将帅传记。多年来致力于《中国现代作家 传记丛书》出版的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功不可没,这一时期陆续推出了《沙汀传》(吴 福辉)、《周作人传》(钱理群)、《丁玲传》(周良沛)、《田汉传》(董健)、《胡风传 》(梅志)、《艾青传》(程光炜)、《萧红传》(季红真)等15部,描述了这一代的知识分 子在家园剧变、时代的颠沛流离中人生的抉择、心灵的探求与时代、命运的关联。上海 文艺出版社的《世纪回眸·人物系列》,以评析知识精英作世纪回眸,大多达到对一个 世纪的整体反思,从而启迪我们有更多的理性来抉择21世纪的路该怎样走下去。其中王 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最具轰动效应。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文人传记,还 有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蔡德贵的《季羡林传》、徐开垒的《巴金传》、 金梅的《傅雷传》、张毓茂的《萧军传》、宋益乔的《徐志摩传》、戴光中的《胡风传 》、沈卫威的《情僧苦行:吴宓传》、郑恩波的《刘绍棠传》、孙见喜的《贾平凹之谜 》等。艺术家传记涉及到的传主包括美术家、音乐家、电影表演艺术家、相声艺术家、 导演、喜剧演员、京剧泰斗、摄影大师等等。作家们力图走进历史的深处,感受艺术家 多姿多彩的人生,如《圆了彩虹——吴冠中传》(翟墨)、《人在漩涡——黄苗子与郁风 》(李辉)、《贺绿汀传》(史中兴)、《马三立别传》(刘连群)等。
明星自传的“火爆”,是后新时期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当红明星人气极旺,包括电 视节目主持人、影视明星、歌星笑星、球星棋手等等,他们纷纷动笔讲述自己的故事, 其书频频走红市场。或真实坦率地展示自我的内心世界及成长经历,多少给人一些启迪 ,或自恋自夸,展示欲望、隐私,可谓毁誉参半。与明星自传的呼啸而来又呼啸而去有 所不同,悄然兴起的文化名人“口述自传”似有后来居上之势。继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推出萧乾、侯波、徐肖冰、朱正、何满子等人的口述传记之后(另有华君武、贾植芳 、陈明、李锐等人的口述传记即出),我们又看到华艺版的《我的人生——浩然口述自 传》等数种。这些传记口述个人身世,鲜活地映现时代变迁的历史,从中可以让人领略 20世纪中国的风云变幻,并欣赏到许多生动感人、鲜为人知的画面。
世纪之交的传记文学出现了一个新的亮点——平民传记。作为被“遮蔽的历史”的发 掘,平民传记诉说小人物的艰难困苦,赞颂小人物的美德懿行,同时也不回避小人物的 缺憾与丑陋,具有名人传记不可取代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不仅一些作家、记者深入 到生活的底层、中国的民间去寻找当代中国的生命力,为小人物树碑立传,如刘心武的 《树与林同在》、陈丹燕的《上海的红颜遗事》,而且许多普通人自己也用《我是×× 》、《我家》、《我的母亲》奏响悲喜交加的人生乐章。
后新时期的11年,传记文学不断走向成熟,进入了传记的“黄金时代”。它具有多元 、开放、众声喧哗的时代特色。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传记文学也与时俱进,“历经 了一个由偶像到凡人,由单一到多元,由倚重传奇色彩到关注精神内涵,在持续中发展 ,在发展中超越的转变。”[8]我们涌现了一支规模可观的传记文学作家队伍,成立了 自己的研究团体——中国传记文学学会(1992)和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1994)。为繁荣我 国传记文学创作,促进传记文学的发展与对外交流,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于1995年和2000 年先后举办过两届中国优秀传记文学作品奖的评选活动,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则每年都 举行一次研讨会。不少高校还成立了传记文学研究中心,开设传记文学课程,培养硕士 博士生。传记创作与出版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与以往相比,表现了一些崭新的特点, 如向系列化、集团化发展,精品化水准有所提高,传记形式在嬗变中不断丰富,传记文 学的文体建构卓有成效,作品的数量无疑大大超过前40年的总和。传记类期刊已多达十 余种,发表的园地日益扩展,在任何一种文学报刊上,传记文学都占据着相当重要的版 面。传记业已成为小报连载及“文摘”、“周末”报刊的最佳资源。传记文学的读写热 潮,直接引发了传记文学的理论研究与批评的繁荣,涌现出了一大批传记文学研究论文 与专著(笔者将另文论述)。
但无庸讳言,对于风头正劲的传记文学来说,良莠混杂,繁荣的背后还潜藏着不少隐 忧。不可忽视的是以下四种不良倾向:一曰胡编乱造,二曰暴露隐私,三曰欺世盗名, 四曰轻率取巧。[9]或如其它论者所论述的那样,“我国的传记文学界还存在着媚俗化 、克隆化、快餐化、工具化和不真实的病症”。[10]这些弊病都是需要努力匡正的。
新世纪2年(2001-至今):传记文学的新走向
2001年,历史已跨入21世纪。在全球经济和政治、文化发展新趋势的有力推动下,中 国当代的传记文学也在出现新走向。一是大传/全传方兴未艾,全景式、大容量再现历 史沧桑。世纪之交,“全传”、“大传”已开始出现,如陈廷一的“宋氏三姐妹全传” 和《查理·宋大传》。新世纪伊始,团结出版社便推出一套“民国人物大系”丛书,以 “大传”命名的包括《孙中山大传》、《蒋介石大传》、《张学良大传》、《宋美龄大 传》、《蒋经国大传》等,力求全面、客观、公正、形象地评述传主的一生,生动、完 整地再现这些20世纪中国极富传奇色彩的风云人物的独特风采。不以“大传”、“全传 ”命名的有《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大陆版(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用百章篇 幅写百年人生,图文并茂,相得益彰。这些传记充分利用近年来海内外“解密”、公开 的各种历史档案,挖掘出许多以前人不知晓的或不便披露的历史材料,较好地表现了特 殊环境特殊人物性格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少则50万字,多则150万字,贪“大”求“全 ”是其一大特色。如《顾准全传》、《梅兰芳全传》、《屈原全传》等,也有一些新的 发现。二是将“冷门”变为“热点”,成为某一方面的填补空白之作。如《扬州八怪传 记丛书》和《犹太名人传丛书》。
其它类型的传记文学平稳发展,产生较大社会反响的作品有:《敦煌守护神——常书 鸿》(叶文玲)、《徐志摩传》(韩石山)、《鲁迅与我七十年》(周海婴)、《舒芜口述自 传》(舒芜、许福芦)、《末代皇帝最后一次婚姻解密》(贾英华)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元 帅传记丛书》等。
21世纪的传记文学将走向何方?虽说机遇与挑战并存,希望与危险同在,但我们坚信, 一个曾经诞生过司马迁这样人类史上最辉煌的传记作家的民族,一定会用新世纪的眼光 ,科学地、历史地、哲学和人性地发掘被“遮蔽的历史”,写出更多具有生命力的史诗 式力作,再创传记文学的辉煌。
收稿日期:2002-07-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