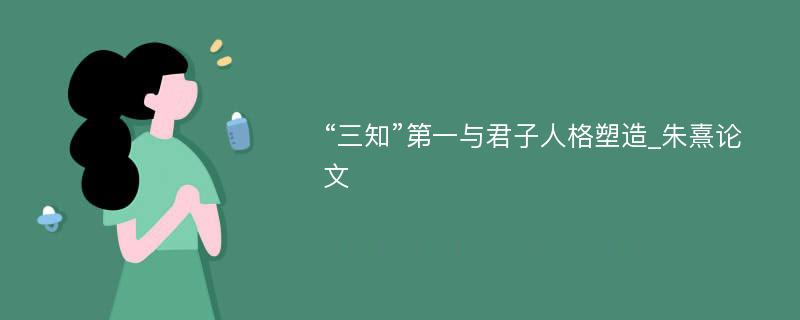
“三知”为先与君子人格的塑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先论文,君子论文,人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73(2012)02-0017-07
儒家的修身处世,突出的是人生修养的实践,重心是放在“行”上。但对清初朱学来说,“行”固然重要,却须有先后次序之分,首先关注的应是知的方面。信守程朱的康熙明言:“每念厚风俗必先正人心,正人心必先明学术。”而康熙眼中的学术,核心就是《四书》,为此,特敕臣下编撰《日讲四书解义》(下简称《四书解义》)以彰其学,其中又尤为突出《论语》的地位,称“天德王道之全,修己治人之要,具在《论语》一书”[1]1-2。在这里,“修己治人”也就是修身处世,其精要都浓缩于《论语》之中。然而,《论语》涵盖范围很大,如何下手才不至于走偏呢?《四书解义》以为,全部《论语》的最后一章给出了答案:
“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此一章书,是孔子言圣学之始事也。孔子曰:修身处世之道固自多端,然其要有三:知命、知礼、知言而已。……《论语》以是终篇,诚示人以修己处世之要道,必自知入矣。盖惟精之功先于惟一,格致之学先于诚正,故朱子曰:论轻重,行为重;论先后,知为先。譬如行路,目先见而后足履之,庶无冥行倾跌之患。否则伥伥其何之矣。奈何后之儒者,混知行为一途,而不以讲学明理为急务哉。[2]326-327
以知命、知礼、知言的“三知”为修身处世的要道,真实反映了康熙帝“孳孳求治,留心问学”的以程朱知先行后观为指导的治学思想。其所批评的混知行为一途的后儒之言,显然是明末流行的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王学既倡知行合一,其“不以讲学明理为急务”便属自然,从而招致站在朱学立场的康熙君臣的深为不满和严厉批驳。
一、修身处世为何以“三知”为先
《四书解义》批驳知行合一而倡知先行后之语,如果不谈社会层面的因素,大致反映了清初朱学对知行合一实际取消了知对行的指导作用这一关键性问题的某种自觉。《大学》云:“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本末先后在任何事物和活动都是客观的存在,而知道这一先后并用以指导自己的修身实践,是接近和把握道的根本途径,所以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如果不然,不问方向道路而盲目修身,结果只能带来人心迷惘、冥行倾跌的祸患。所以,清初朱学要求重新回到程朱先知后行的理路,强调修身必须以知为先。那么,这一认识是如何展开的呢:
首先,从总体看,《四书解义》以《论语》终篇之“三知”为纲领,强调“知”为圣学之始事。既是“始事”,固然不涵盖修身处世的全过程,它主要是针对其“入端”,即解决儒者修身自何处而入的问题。就此而言,《论语》以“三知”终篇,是真实反映了孔门师徒治学意向、旨趣的某种必然,还只是不同弟子汇编孔子言语的一种偶然结果,在不同学者存在意见的分歧。但就目前的资料,汉学的考据无法恰当解释为何有这样碰巧的偶然,那就不妨借助于宋学的义理分析,假设它反映了《论语》编者的“深意”,即揭示孔子始终强调的对君子人格塑造的要求。
朱熹在《论语集注》的最后,引尹氏(焞)之言终篇,尹氏曰:“知斯三者,则君子之事备矣。弟子记此以终篇,得无意乎?学者少而读之,老而不知一言为可用,不几于侮圣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3]195显然,朱熹是认同尹焞所说的。孔子一生,叙说君子之事不少,其提出的要求也不尽相同,但从程朱的角度,根本的问题是“三知”,“知斯三者,则君子之事备矣”。弟子所以记“三知”以终篇,就在于如果不能知命、知礼、知言,则根本阻断了进入圣学的门径,儒者修身以成为君子自然变得不可能。
《论语》一书,儒者固然从小熟读,但是,《论语》揭示的修身之要即塑造君子人格,却不是人人都能明白的。“三知”中只有第一“知”——“知命”直接联系着君子,但后面的“知礼”和“知言”,实际上同样属于君子应有的品格,目的都在突出君子的人格塑造。在朱熹之后,朱学的后裔对此都有自觉的体会,并继续朱熹的理路,将《论语》末章与首章论君子结合起来①。如蔡沉长子蔡模称:“《论语》首章,末以君子言;末章,首以君子言。圣人教人,期至于君子而已。详味两章语意,实相表里。学者其合而观之。”[4]528明胡广等编《四书集注大全》,于注文下凡训释一二字或二三句者,多取新安陈氏(栎)说。陈氏曰:“《论语》一书,夫子以君子教人者多矣。首末两章皆以君子言之,记者之深意。夫子尝自谓不怨天、不尤人;人不知而不愠,不尤人也;知命,则不怨天,且乐天矣。学者其深玩潜心焉。”[5]
《论语》首章末句为“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首章末句与末章首句均论君子,塑造君子的心愿可谓贯穿孔子的一生。弟子强调两章前后相表里的“深意”,被归结为天与人双方的知行关系:在人一方,是人不知我而我不怨人;在天一方,则是我知命则乐天。双方的共性,一是知在行先,二是我皆不怨;而个性或特殊的方面,是首章的君子已是“成德之名”(朱熹语),修身臻于完善,属于现实的存在,是以德备来见证其知尽;而末章则在强调修为君子的必要条件,君子的人格还只是可能,这就必然要求以知为先导。但双方又不是截然分割的,首末章必须合而观之,这就需既讲以知为先,又应将知行贯通起来。
其次,以知为先的修身处世之道,无疑包含有多方面的内容,但关键的问题在找准进入的端口。“三知”所指是大的方向,人的修身活动应当以此为开端而进一步落实。故对理学至关紧要的惟精惟一之功、格致诚正之学,其实都有先后之别。精察先于专一,格致先于诚正,不精察则专一无根,不格致则诚正盲目。明末王学的失败,不是不讲修身,而是没有方向指导,结果荡佚礼法,后果不堪回首。
在朱熹,人心道心杂于方寸之间,要治之必须要先知道从何下手,所以君子的修身,首先是精察何为道心、何为人心,何为天理、何为人欲,明确将双方区分开来而不混杂。接下来,才能坚守本心之正而始终不离,所以精察要先于专一②。而格物致知先于诚意正心,在《大学》已是明文,先有物格知至,再有意诚心正。所谓“欲诚其意,先致其知”;“知至而后意诚”。所以是如此,“盖心体之明有所未尽,则其所发必有不能实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6]8。人只有通过格物致知的活动充分明理,才能恰当分辨天理人欲,心之所发便能专一于天理,本心充实而不自欺。朱熹强调:“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后有以见其用力之始终,其序不可乱而功不可阙如此云。”[6]8诚意正心的践行必承格物致知而来,这一用力之始终必须要认清,前后次序是不可颠倒的。当然,对于已明之理则需要体验扩充,存养不懈,使正心修身之功臻于圆满。
但以致知为进德之基的君子修身之方,在后来却受到王守仁知行合一说的严重冲击。王守仁以知行合一批驳朱熹的知先行后无疑有自身的价值,但也带来了不少的问题。明末清初,王夫之对朱熹的知先行后和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进行总结,认为:“盖云知行者,致知、力行之谓也。唯其为致知、力行,故功可得而分。功可得而分,则可立先后之序。可立先后之序,而先后又互相为成。则繇知而知所行,繇行而行则知之,亦可云并进而有功。”[7]王夫之显然是折中了朱王双方,肯定知与行有先后之序;但既然知与行是相互为成,先与后又不能截然对待,所以王学的知行并进(合一)而有功也有自己的意义。这就既有别于朱熹的知先行后,也不同于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当然,王夫之面临的是明末王学泛滥、学术空疏的流弊,所以他的主要矛头还是针对王守仁的知行合一的。在王夫之眼中,知行合一所以不对,原因就在它实际上是“销行归知”、“以知为行”:“以知为行,则以不行为行,而人之伦、物之理,若或见之,不以身心尝试焉。”[8]因为知行合一,在逻辑上就不存在知外之行,对外于人之人伦物理,如以见之即行,身心投入的具体实践也就从根本上被取消了,结果造成以不行为行的恶果。
王夫之的批评对否暂且不论,但他的批评重在针对以不行为行、销行以归知的弊病却是无疑的,即认为王学于人伦物理是有见而不行。然而,与王夫之处于同一时代的清初朱学,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即王学的混知行为一途,问题不是在取消行,而是在不知理,不以讲学明理为急务,即属无见而冥行。之所以如此,在于双方面临和要解决的问题不同:为明亡痛惜的王夫之面临的,是知行合一造成对知与行双方各自的角色、特点、功用不分,结果导致以知为行而取消行,儒者的修身治世也就从根本上被瓦解;而清初朱学是站在道统传承者的立场上看待前朝学术的利弊,目的在“阐发义理,裨益政治”,突出的是“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1]1。清王朝统治的正统需要利用朱学的道统来阐明其合法性。所以,认识朱学阐扬的天德王道并为君子的修己治人提供依循的指南,自然就成为优先的任务。
当然,强调知为先并非不重视行,事实是,强调知为先本来也是因为重视行。倘目不先见,则或者无所适从而不知从何下脚,或者盲目行动而最终招致祸患,也就根本断送了塑造君子的可能。同时,在朱熹,知先行后并不是一绝对原则,它需要与行重知轻相互补充。所谓“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2]327,在这方面朱熹有不少的论述。可以说,知行并重是朱熹知行关系论的总原则,他的全部知行思想,都是这一原则的具体阐发和运用。然而,清初朱学虽然总体上继承了朱熹的思想,却在继承中又显示出自己的特点,即将朱熹的先讲先后、后说轻重的重点落在轻重上,改成了先讲轻重、后说先后而将重点落在先后上,从而将讲学明理、克服冥行倾跌之患放在了问题的首位。
二、“三知”为先如何能塑造君子
“三知”均为君子人格塑造所必需,但“三知”之间又各有自己的特点和要求,故需要予以具体的分析。
首先,先知命方可能为君子。“三知”之中,“知命”于君子最为紧要,因而被位于“三知”的首位。《四书解义》对于《论语》“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的解释,突出的是尽人事以听天,并以理学的义利之辨划分君子与小人。其言曰:
盖人之有生,吉凶祸福皆有定命。必知命而信之,尽人事以听天,乃能为君子。若不知命,则不顾义理,而见害必避,见利必趋,徒其守,而陷于小人之归矣,何以为君子。此命之不可不知也。[3]195
如此论说的根据,源于朱熹《集注》中所引程子之言。程子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则见害必避,见利必趋,何以为君子?”以“知有命而信之”解“知命”,突出了理性自觉的价值。君子信奉命,是因为他首先认识到“有命”,进而悟得命之必然在根本上成就了君子的人格。相形之下,小人因达不到这一理性的高度,所以他们既不知命也不信奉。
那么,何为“命”呢?朱熹以为:“此只是气禀之命。富贵、死生、祸福、贵贱,皆禀之气而不可移易者”。[10]79又说:“盖学者所以学为君子者,不知命则做君子不成。死生自有定命,若合死于水火,须在水火里死;合死于刀兵,须在刀兵里死,看如何逃不得。此说虽甚粗,然所谓知命者,不过如此。若这里信不及,才见利便趋,见害便避,如何得成君子!”[11]“命”既然源于气禀,便与人体同在,人不可能“移易”自己的身体,也就不可能移易命。形象地说,死于水火的就不会死于刀兵,所以叫做“定命”。君子面对定命不会逃避,而是认知其为何逃不得的道理,从而自觉顺命。朱熹强调,此解虽不够精细,但道理并不错,君子价值实现的关键就在这里。而小人之所以是小人,就在于趋利避害,唯利是图。显然,知命的内涵打上了理学义利之辨的烙印,“知命”需要明辨义利,义以为上。
朱熹以气禀之命解“命”,可以回溯到子夏所闻知的“死生有命”之命。在孔子师徒,“死生有命”是联系着“富贵在天”的,所以二者又有关联:“命禀于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为而为,非我所能必,但当顾受而已”[12]134。“非今所能移”与“非我所能必”在客观必然的层面可以相通,但人对此必然,又不是完全被动。例如对于无兄弟的担忧,他可以“修其在己者”即内在仁德,“持己以敬而不间断,接人以恭而有节文,则天下之人皆爱敬之如兄弟矣”[12]134。“兄弟”从无到有,必然在这里已转化为自由。朱熹此解,实际上已融入了“知礼”、“知言”的成分。在整体上便是五百年后的清初朱学所陈述的尽人事而听天命。君子的修身处世,只有了解其所面临的命运,才能安下心来践履人事而等待天命的降临。从孔子到朱熹,都认为认识自己的命运并充满信心地迎接即将到来的吉凶祸福,是成就君子必须的要件。
在这里,与人事对应的天命,并不等同于命,但二者毕竟又有关联。朱熹分析“死生有命”与“天命谓性”二“命”的不同时说:“‘死生有命’之‘命’是带气言之,气便有禀得多少厚薄之不同。‘天命谓性’之‘命’,是纯乎理言之。然天之所命,毕竟皆不离乎气。”[10]77气禀之命构成人的生命基础,天命之命奠定了人的价值根源。但天命所命不能脱离开气禀生命,“纯乎理”者内在于人“命”之中,成为人生而所具的仁义礼智。由于仁总四德,包义礼智,所以可说:人者,仁也。君子既以仁德为质,故“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念兹在兹,怀仁不二也。不过,如果严格按“无终食之间违仁”的要求来衡量,又似乎过于严厉,因为即便颜回也只能“其心三月不违仁”(《论语·雍也》)。倘若此,则圣人门下无一人可谓君子也。
到宋明,理学家对这一过分严厉的标准进行了重新解释。周敦颐首先提出了“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的阶梯性渐进的模板,肯定颜渊的“不迁怒,不贰过”和“三月不违仁”乃是“大贤”。希望学者能够“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志伊尹之志”,就要辅君惠民行仁德善政;“学颜渊之学”,则需克己复礼而心志于仁。二者形式上虽然有别,目的却完全一致,中心都是同一个仁德。若真能如此,其结果将是十分令人欣慰的,所谓“过则圣,及则贤,不及则亦不失于令名”[13]。超过“大贤”便进于圣,不及于贤也是在进达贤的过程中。对此,孟子曾以“立命”的境界来加以概括,所谓“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君子修身由知天而事天,将知觉所体验的仁义本性落实于实际的践履,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换句话说,知命是在立命的践履中得以落实的。
孟子论“知命”突出了主体的选择,并将正与非正的价值内涵添加进“命”的概念中。“正命”是君子追求的目的,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朱熹发挥说:“人物之生,吉凶祸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为正命,故君子修身以俟之,所以顺受乎此也。”[14]朱熹在这里仍然是将天与命结合而论的,“命”既然是由“天”赋予,人就不可能干预;那么,不是由人的行为招致,而是自然到来的吉凶祸福之命便是正命。君子的知命,实在于知此正命,从而引导自己的修身。因而,知命不仅应知道“命”是什么,更在于知道如何对待“命”。所谓顺命,也就不是逆来顺受,而是在知觉所命的前提下谨守正命,君子人格就此而得以树立。
其次,必知礼方能规劝人生。人生活于社会之中,而社会是由一定的规范即礼来维系的。孔子所以说“不知礼,无以立”,从朱熹到《四书解义》的解释是:
至于礼者,可以消非僻之心,振惰慢之气,知之则德性坚定,威仪检摄而有以自立。若不知礼,则耳目手足惶惑失措,无以持身而自立矣。此礼之不可不知也。[2]327
君子的修身成人,礼是最根本的保障。礼对于“成人”的功用,主要表现有二:一在于有德性,二在于有礼仪,而这两方面都是由知礼来提供的。知礼则德性坚定,而不会生放荡邪僻之心;以礼仪来整肃己身,则不会有懒惰散漫之举。人的举手投足、持身践履,实际上都不可能离开礼而行。所以,《礼记?礼器》说:“礼也者,犹体也。体不备,君子谓之不成人。”(《礼记·礼器》)礼可以与人的身体相比:身体发肤、骨肉、筋脉不备,则不成其为人;人不备礼,同样也不能成人。显然,所谓不备礼的不成人,不是自然人,而是社会人,“成人”乃是指成就君子人格。
礼既然维系着人的日常生活践履,所以圣人教化尽管多方,然无不以礼为准绳:“六经其教虽异,总以礼为本。”[15]那么,知礼就是人立足社会所必需,只有知礼,才能安定和规范人生。为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而操劳一生的孔子,因而要求“克己复礼”,希望通过不同个体对自己行为的自觉约束来回复到周礼的规范,这刚好表现了修身与处世的统一:“复礼”的内涵在“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色人等都需要合乎等级名分的规范;而在己身的修养,便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以礼自律。在此基础上,如果人人都能够约束己身并以践行礼为己任,天下便会是一个仁爱和睦的社会。所谓“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在此意义上,“克己复礼为仁”表达的是儒家修身处世的理想。反之,人若“不知礼,则耳目无所加,手足无所措”[3]195。人不知礼,则既不能端正自身,更不能矫正社会,完全失去了在社会立足的资格。
落实到每一个体,人之循礼,有自内而外的仁德的扩充推广即立足性善的适宜,用理学的话语,就是发而中节,行为自然符合礼;也有从外而内的以圣人教诲和国家礼法来规劝即立足性恶的教化,己身在意志作用下遵守礼。但不论哪一条道路,目的都在使己身能够立足于社会。可以说,自大道既隐、天下为家以来,儒家圣王前后相传,未有不谨于礼者。所以,知礼不但是君子所必须,而且是非常急迫的任务。孔子在答子游“如此乎礼之急也”之问时强调说:“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礼记·礼运》)礼本于天道,礼对于人之重要和急迫,就如同老鼠有自己的身体一样,是得之则生、失之则死的,具有与生命同在的价值。所以要学为君子,必须要先知礼。
当然,由于礼本身的复杂性,所谓“礼有大,有小,有显,有微,大者不可损,小者不可益,显者不可掩,微者不可大也”(《礼记·礼器》)。所以,对于学礼的君子来说,是否已经知礼,并不容易简单给出答案。在《礼记》中,孔子曾说自己不知礼,这固然是谦逊之辞,但从随后的陈述来看,更主要是为突出礼之极端重要性和涵盖的广泛性,无处不有礼也。至于何人才能被许为知礼,可以参看孔子对他人的评价:鲁国大夫穆伯死了,他的妻子敬姜治丧时白日哭;可是到给他们的儿子文伯治丧时,敬姜却是白日和夜晚都哭;同时,敬姜还能够注意避嫌和分别上下,能够公正地议论其子与媳的德行,所以获得了孔子“(敬姜)知礼矣”的评价。鲁国执政者季氏主持祭祀,因耗时太长弄得参加者倦怠不堪,行为不敬;后来再有祭祀,子路参与组织,时间和程序都安排得当,祭礼顺利完结,孔子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谁谓由也而不知礼乎!”子路是知礼的。那么,知礼是既不易也易的,关键在顺天道,适人情,行为中节也。
第三,须知言才能明白事理。与知命、知礼立足于生命和礼法相比,知言显得不是那么要紧。然而,知言为何又能与知命、知礼并立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命、礼的重要性是借助于言才得以彰显的。同时,知命、知礼的突出“知”,是落实于“为”、“立”的践履的,相互间的关系,可以用朱熹的“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来概括;只有知言的“不知言,无以知人”是双重的重知,故又显示了与知命、知礼不同的特色。
为何“不知言,无以知人”?因为“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3]195。言从心生,人之邪正一定会从言语中表现出来,故可以通过言去了解其实。孟子对“知言”的阐释,是:“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孟子·公孙丑上》)如果说知命、知礼是知道其是什么和怎么做的话,知言则不是知道言是什么和怎么做,而是在知晓言本身的问题在哪里并针对性地予以纠正。如果不纠正,偏邪不正之言必然会损害政治,危害日常事务活动。孟子的叙说本身就是言,相信后来的圣人一定能知晓孟子这里的自我期许之言。
不过,从孔子到孟子,知言都是限定在言本身而论。朱熹阐释孟子的知言,却联系到了他所着意的天理。所谓“人之有言,皆本于心”;“知言者,尽心知性,于凡天下之言,无不有以究极其理,而识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16]。知言实质上是要知心性,对天下之言要能够深入其内,穷究其理,从而找出人之是非得失的原因以便于纠正。清儒强调说:
至于人之邪正,已之取舍系焉,不可不知,而其要在知言。盖人心之动,因言以宣,即其言语之当否,可以知其心术之邪正。若不知言,则邪正何由而辨,无以知人而定取舍也。此言之不可不知也。[2]327
已之取舍既系于人之邪正,也就必然需要清楚的了解。如不知言,则不辨邪正,从而无法恰当地了解人而给予正确的取舍,所以言不可不知也。
知言的重要性无可置疑,如何恰当知言则体现了自己的修养水准。要提高自己的修养水准并修成君子人格,最好的途径就是学《诗》:“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也。孔子对于培养自己的下一代,有所谓过庭之训,但内容不过就是学《诗》以言,学《礼》以立。孔子曾云:“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这里固然对诵《诗》三百而不能从容行政和出使四方提出了批评,但之所以将双方联系在一起,正是表明在孔子心中,双方是应当理想地融合为一的。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受命者要圆满完成交办的任务,适时地诵引诗篇是必备的才能。朱熹发挥说:“《诗》本人情,该物理,可以验风俗之盛衰,见政治之得失。其言温厚和平,长于风谕。故诵之者,必达于政而能言也。”[17]《诗》作为人情物理的恰当概括,为从政者提供了最充分的资源和最活泼的形式,所以能诵《诗》者理当善于言辞并从容行政也。否则,根本不具备君子的品格。
诵诗与践礼,在孔子的生活中是经常涉及的问题。《礼记·礼器》记述孔子之言曰:“诵《诗》三百,不足以一献;一献之礼,不足以大飨;大飨之礼,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飨帝。毋轻议礼!”礼(祭祀)有小有大,孔子这里不是说祭各路小神的一献之礼都比知诗重要,而是说,即便能诵《诗》三百即已知诗能言,但如果不知礼,则不足以承担一献之礼的职责。所以,如果不学礼,就不能轻率地去议论礼。在这里,无疑表明了行重知轻的关系,但行重不等于是知礼重、知言轻,因为礼与言都各有其知与行的问题,知礼、知言都需要落实于行上。诵《诗》三百而通达行政,知晓礼仪而酬酢适宜,是学为君子互不可缺的要求。
三、“三知”相互促发以塑造君子
知礼与知言相衔接,而与知命同样不可分。“三知”作为修身处世的要道,共同作用于君子人格的塑造,相互发明,缺一不可。其间的关系,朱熹高徒黄榦认为:
知命知其在天者,知礼知其在己者,知言知其在人者。知天则利害不能动乎外,而后可以修诸己;知礼则义理有以养乎内,而后可以察诸人;知天而不知己,未必能安乎天;知己而不知人未必能益乎己。[5]527
中国哲学通常被概括为天人之学,但这一概括也有不足,那就是天与人都是他者,“我”或“己”的主体处于什么位置呢?其实天与人之间应当有一中介,那就是“己”,己是天命(性)与人性(命)的统一体。朱学弟子对此已有充分的自觉,所以以“己”来联系和贯通天人。在黄榦,君子既知在天者为命,故利害得失不能扰动我心,而能专心于自我的修养;而礼虽表现为外在的行为规范,根子却在内在仁义的发而中节。同时,行为的合礼源于内心存养的切实,以内在义理为基准,才能通过言语去考察他人。所以,“三知”实际上是相互依赖的:不能知己,内在义理不能得以体验扩充,人就必然为利害得失所动而不能安乎天;不能知人,意味己之内在仁德、义理存养有失,故而无法判定是非正邪。
那么,要成为君子,就不仅是内在的仁德存养,君子之事,是将独善其身与兼善天下联系在一起的。朱熹另一高弟辅广说:“知命则在我者有定见,知礼则在我者有定守,知言则在人者无遁情。知斯三者,则内足成己之德,外足尽人之情,故君子之事备。”[5]527命虽然属于客观必然,但知命意味着主体能够把握自身的命运,不会为任何事物变化所迷惑;知礼则我心有确定的志向和操守,应事接物无不适当;知言则能正确地辨别人情世故,知善知恶,尽己尽人,成己成物,君子之事因而完备。那么,人之行为既不能逃过我之明鉴,世间善恶褒贬得当,正义得以弘扬,天下太平也就在不言之中了。用元代朱熹后学胡炳文的话来说,就是“学始于致知,终于治国平天下”也[5]527。
当然,就宋代理学来看,重视“三知”对君子人格塑造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朱熹一派。事实上,其他诸家对此也是非常看重的。例如湖湘学派代表张栻便认为:
此所论命,谓穷达得丧之有定也;不知命,则将徼幸而苟求,何以为君子乎?知命则志定,然后其所当为者可得而为矣。礼者所以检身也,不知礼则视听言动无所持守,其将何以立乎?知礼则有践履之实矣。知言如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之类,不知言则无以知其情实之所存,其将何以知人乎?故知言则取友不差矣。此三者学者之所宜先切要之务,必以是为本而后学可进,不然,虽务于穷高极远,而终无所益。门人以此终《论语》之书,岂无旨哉?[18]
张栻综论“三知”的意义及其相互关系,可以与朱学一系相互发明:知命则心志有定,不作非分之举,君子事业可以期待;知礼则行为举止中节,人能实在地立足于社会;知言则能通达人之真情本性,择人取友识见不差。学者学为君子,“三知”实乃其根基,只有此基础奠定实在了,探求天命性理的“高远”才不致有蹈空堕虚之嫌③。由此,“三知”所知与理学家着意的理气性心之辨并不相同,它是侧重于形下的日常生活实践的。联系儒门后来的空谈心性之弊,《论语》编纂以“三知”终篇,或许的确有其深意所在。
[收稿日期]2011-12-15
注释:
①事实上,不只是朱熹,理学的其他大家如张栻等,同样也是将首末两章论君子联系起来考虑的。
②参见朱熹:《中庸章句序》。
③朱熹于此实际上也有警觉。他曾称:“盖此章所谓理,止指礼文而言耳。若推本言之,以为理在其中则可,今乃厌其所谓礼文之为浅近,而慕乎高远之理,遂至于以理易礼,而不复征于履践之实,则亦使人何所据而能立耶?”见《论语或问·尧曰》,《四书或问》第41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标签:朱熹论文; 论语论文; 儒家论文; 君子论文; 读书论文; 孔子论文; 国学论文; 知礼论文; 知行论文; 宋明理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