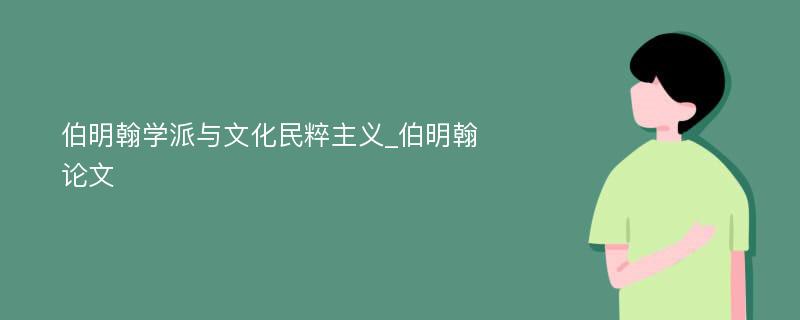
伯明翰学派与文化民粹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伯明翰论文,学派论文,主义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9]03—0018—06
“文化研究”是当前国际学界最热门的研究思潮,作为“文化研究”思潮始作俑者的伯明翰学派也因此成为近年来国际学界关注的焦点。然而,2002年6月,该学派大本营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却突然遭遇了被关闭的噩运。这在国际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成为当年国际学界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关闭当然有着许多现实的原因,如经费紧缺、研究人员不足等等,不过其更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它理论上颇难逆转的困境。这一困境被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是由其日益强烈的“文化民粹主义”倾向造成的。本文将着力考察伯明翰学派“文化民粹主义”倾向的具体表现、形成原因以及理论局限,并对当代文化研究如何避免文化民粹主义做出初步的思考。
何为文化民粹主义?文化民粹主义的概括参考了政治学意义上的民粹主义,但与后者又不完全相同。政治学意义上的民粹主义出现在19世纪中后期的俄国,是当时俄国知识分子为反抗沙皇暴政而提出的。这种民粹主义的英文表达方式不止一种,最常见的是“populism”,可以直译为“民众主义”,强调民众代表了最先进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能够作为改革社会的先锋力量。与此相应,文化民粹主义也是由知识分子提出,也刻意尊崇和抬高民众的能力,只不过与民粹主义强调民众的政治先锋意义不同,文化民粹主义强调的是民众的文化先锋意义。所以,麦克盖根说,文化民粹主义就是“由一些通俗文化专业学人所作的知识分子式的界定,认为普通百姓的符号式经验与活动比大写的‘文化’更富有政治内涵,更费思量。”① 由此可以看出,文化民粹主义实际体现了三大特点:第一,文化民粹主义着力无限度地尊崇并抬高民众符号经验与文化活动的地位;第二,文化民粹主义力图摒弃精英文化的教化与影响;第三,文化民粹主义具有相当程度的空想色彩。
伯明翰学派的文化民粹主义起源于该学派学术领袖雷蒙德·威廉斯的平民文化观。理查德·霍加特紧随威廉斯其后从文化生产角度强化了其文化观中的平民意识,形成了文化生产角度的民粹主义;而约翰·费斯克则在斯图亚特·霍尔的带领下,从文化消费角度强化了威廉斯文化观中的平民意识,形成了文化消费角度的民粹主义。文化生产民粹主义与文化消费民粹主义由此构成了伯明翰学派文化民粹主义的两种主要表现形式。
文化生产民粹主义主要体现为从文化生产的角度张扬与尊崇民众的文化经验与文化活动,贬低精英文化的价值。霍加特分析了阅读报纸、郊区旅游、酒馆闲聊等大量20世纪30年代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与娱乐方式,并对这种文化大加称赞。他认为只有这些与工人阶级生活有机关联,由工人阶级亲身创造出来的文化才能够真正体现民众的观念、意志与情感,才是“真正的人民的世界”,是“理想文化”②。霍加特特别强调民众创造对于文化的意义,因此他对非民众创造却貌似民众创造的商业文化深恶痛绝,并做出了激烈的批判:以时尚读物、牛奶吧、电子游戏厅等面目出现的所谓“大众文化”绝不是民众的文化,它为了自己的商业目的不择手段,无时无刻不在欺骗、控制与强迫民众,“最后就是D.H.劳伦斯所形容的‘反生活’,充满了腐败堕落,不正当的诱惑和道德沦丧。”③ 很明显,霍加特追求的理想文化就是一种纯粹由民众生产、创造的文化,他将毕生精力都放在为这种文化争取合法权利上。因此,他必然对同这种文化相对立的精英文化持贬低的态度。霍加特以批判的口吻指出,工业社会中的文化并不是如精英文化暗示的那样,是一种特权,由某些文化精英守护并“自上而下”地传播。实际上,精英文化已经退出了工业社会文化生活的中心,对于后者已经没有决定性影响。
文化消费民粹主义则主要体现为从文化消费的角度张扬与尊崇民众的文化经验与文化活动,贬低精英文化的价值。霍加特强调民众通过掌控文化生产来创造纯粹、理想的民众文化,而费斯克则更加关注文化的消费领域,主张民众通过对不同类型的文化原材料的消费与解读,“再生产”出理想的、纯粹的民众文化。费斯克将此称作“符号的游击战”。费斯克对民众能力的信任与尊崇显然更甚于霍加特,因为在他这里,民众的力量似乎更强大,他们不需要刻意生产和创造自己的文化,只需要在文化消费中运用一定的策略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解构主流文化,建构自己的文化。这就进一步夸大了民众在文化活动中的能动性,也进一步加深了伯明翰学派的文化民粹主义倾向。既然费斯克对民众的文化创造能力如此自信,那么他对于同民众文化相对的精英文化自然是不遗余力地进行贬低。费斯克指出,“高雅文化”只是资产阶级为了进行文化统治而通过制度刻意抬高的文化,实际上,“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之间并没有实质性差别,只是不同种类的文化而已④,“高雅文化”并不比“通俗文化”更高明。费斯克理论中流露出的文化民粹主义倾向实际上要大大强于伯明翰学派的其他理论家,以至于有的学者建议不将他当作伯明翰学派的成员来看待,不过这一看法并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同。学界普遍认为,虽然费斯克与其他伯明翰学派的成员相比,对民众能动行为的强调要更激烈,但他的观点毕竟还是从伯明翰学派相关学者的理论中生发出来的,所以他还应该属于伯明翰学派。这样,我们还是采取尊重学界普遍看法的态度,将费斯克当作伯明翰学派后期的重要代表,将他的理论作为伯明翰学派文化民粹主义在后期发展的主要范例。
文化民粹主义的倾向能够在伯明翰学派内部生成,当然有上文提到的学理方面的原因,但也不可忽视其社会背景方面的原因。以霍加特为代表的文化生产民粹主义,随着伯明翰学派的诞生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当时的英国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较二战前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的迅速复苏与持续发展使得英国社会的商业色彩愈加浓厚,商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各阶层在商业平台上的平等交流,从而冲击了英国社会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度,为整个社会生活带来了民主的气息。在这种民主气息的催化下,英国的工人阶级与平民阶层迅速崛起,开始努力争取自己在政治、文化上的一系列权利。与此相应,代表工人阶级与平民阶层政治倾向、文化趣味的通俗文化也开始蓬勃发展。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与文化背景下,威廉斯才提出了具有浓厚平民色彩的文化定义:“文化是整个生活方式”,“文化是平常的”。他希望通过对文化概念的重建来对抗以利维斯主义为代表的精英主义文化观念,并进而为工人阶级与平民阶层进行政治、文化上的代言。霍加特积极响应威廉斯的提议,专门写作了《有文化的用途》一书为“文化是整个生活方式”做出了实例论证,并在自己浓厚的工人阶级生活“怀乡症”的驱使下,对民众的文化生产活动做出了过度张扬,对与民众文化生产活动相对的精英文化生产活动进行了刻意贬低,由此产生了以他为主要代表的文化生产角度的民粹主义。
以费斯克为代表的文化消费民粹主义是伯明翰学派发展到相当程度的产物。就社会背景而言,文化消费民粹主义产生的社会背景同伯明翰学派发展初期的社会背景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20世纪70年代,整个西方社会的商业化程度较战后初期深化了许多,这种深化在文化生活方面产生了两方面后果。一方面,西方社会随着商业化程度的加深,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物质财富。这些物质财富促进了社会各项公益事业,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发展。由此,民众的文化素质得到了普遍提高,文化权利也得到了基本保障,完全有能力来接受和消费文化。另一方面,西方社会商业化程度的加深也将文化生产进一步纳入了工业生产的轨道,民众由此进一步丧失了文化的生产权,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被动接受和消费文化工业生产的产品。这两方面后果直接导致西方社会的文化生活从文化生产时代迈入了文化消费时代。社会背景的变化再加上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和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等外来理论的冲击,伯明翰学派的研究思路必然要发生转变,这一转变首先体现为该学派内部学者E.P.汤普森对该学派初期主要概念“文化是整个生活方式”的质疑。时代的变化与外来理论的冲击使得汤普森不禁对伯明翰学派初期文化观的合理性产生了担忧。他明确指出“文化是整个生活方式”在表述文化性与平民性方面的模糊不清,希望通过修正定义的方式来巩固伯明翰学派在初期提倡的文化观。面对汤普森的质疑,威廉斯采取了一系列补救措施:他首先吸收了使伯明翰学派备受冲击的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与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将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础—上层建筑”模式改造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然后以此为出发点重新解释了“文化是整个生活方式”。文化由此从“整个生活方式”变成了“社会存在”为“社会意识”“设定限制和施加压力”的过程,进而被转换为“社会秩序得以传达、再生产、体验和研究”的“符号系统”⑤。同“文化是整个生活方式”相比,修正后的文化概念显然强化了文化的符号性与平民性,弥补了汤普森质疑的缺点。然而,在弥补缺点的同时,该概念却出现了两个新特点:首先,该概念更关注文化的消费领域。当文化被认为是“整个生活方式”时,文化很明显与日常生活是融为一体的,民众就是文化的生产者;而当文化被认为是一种“社会秩序得以传达、再生产、体验和研究”的“符号系统”时,民众与文化生产之间则出现了距离,民众主要体现为具有符号能力从事文化消费的功能存在。该概念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特点,同威廉斯对结构主义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吸收有莫大关系:通过吸收结构主义对不同社会因素之间进行平等“结构”的主张,威廉斯消除了他所厌恶的“基础—上层建筑”模式过度二元分立的弊端,但同时也强化了他对文化的精神维度的关注;而在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影响下,威廉斯更加强调文化作为一种符号解读行为对日常生活的结构功能。这两种理论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使威廉斯新文化观念强调的重点从文化生产领域转向了文化消费领域。其次,该概念更突出了民众在文化生活中的能动作用。威廉斯的修正虽然没有明确表示出对民众的尊崇,但结构主义对社会意识与经济基础之间平等地位的解释却激发了威廉斯对社会意识的关注,进而更加强调文化主体“再生产、体验和研究”的能动行为。而随后所吸收的强调意识形态斗争的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则进一步强化了威廉斯对文化内涵的社会意识以及随之而来的民众能动作用的关注。威廉斯文化概念的新特点很快被伯明翰学派中期的重要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察觉,并加以强化。霍尔由此成为威廉斯后期重要的理论同盟军。同威廉斯一样,斯图亚特·霍尔也通过参考结构主义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方式来考察文化。虽然他认为自己是在综合考察以前期威廉斯为代表的“文化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基础上寻找“第三条道路”,但实质上,他对文化的理解更偏向于“结构主义”。他比威廉斯更彻底地解构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础—上层建筑”模式,提出文化研究问题的关键并不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也不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关系,而是社会个体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他将现实生活中社会个体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称为“接合”关系。他解释说:“接合是一种连接形式,它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统一两种不同的要素。作为一种关联,它并非总是必然的、确定的、绝对的和本质的。”⑥ 简言之,接合就是一个在各种要素或组成部分之间建立关系的实践活动。这样,文化就体现为社会个体与意识形态之间自由接合的动态过程。在霍尔这里,意识形态的选择权、文化的仲裁权实际上完全交给了社会个体。由此可见,无论是对文化消费领域研究的介入还是对民众能动作用的强调,霍尔都比威廉斯要强烈。这样,后期威廉斯对文化消费领域的关注与对民众能动作用的强调,加上霍尔后来的推波助澜,必然会在伯明翰学派内部催生出从文化消费角度明确张扬民众强大能动力量的文化观念,这就是费斯克的文化消费民粹主义。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化生产民粹主义与文化消费民粹主义形成的过程中,虽然威廉斯毫无疑义地为它们提供了理论基础,成为促成它们在伯明翰学派内部生成的主要学理原因,但他本人对文化的理解却并非文化民粹主义。实际上,威廉斯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落入文化民粹主义的陷阱:在伯明翰学派发展初期,威廉斯最早明确提出了“文化是整个生活方式”的定义。然而,他还同时指出,“文化是整个生活方式”只是理解文化三方面含义中的一个,其他两方面含义包括,文化可以“用来描述18世纪以来思想、精神与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⑦;文化可以“用来描述关于知性的作品与活动,尤其是艺术方面的”⑧,这两个关于文化的定义主要将文化看作是精英文化。要想完整地理解文化,需要将这三个方面综合起来。可见,威廉斯在注意肯定民众文化活动能力的同时,还承认了精英文化作为文化的合理性。他提出“文化是整个生活方式”的目的只是为了冲破从前单纯从精英文化角度来定义文化的狭隘,将民众的文化经验与文化活动也纳入对文化的理解,进而肯定和承认民众在文化生活中的平等权利,而不是为了特别尊崇与抬高民众的文化经验和文化活动。同样,在伯明翰学派发展的中后期,威廉斯也没有特别去夸大与提高民众的文化能力。文化是“社会秩序得以传达、再生产、体验和研究”的“符号系统”,虽然在“文化是整个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加强了对民众能动性的关注,但还是将民众作为拥有同一价值取向的某个阶层来看待,并没有刻意强调每个社会个体特殊、独立的意图与意志。这与霍尔将社会意识的选择权完全交给社会个体的做法相比,显然更客观,更冷静,也更远离文化民粹主义。
文化民粹主义的形成当然有着可以理解的客观原因,但它带给伯明翰学派的理论局限却是致命的。它潜滋暗长,不知不觉地侵蚀了伯明翰学派的理论肌体,最终将这一学派及其学术研究引向了衰败:首先,文化民粹主义对民众符号经验与文化活动的盲目尊崇与抬高致使伯明翰学派丧失了真正的批判精神。我们知道,有距离地反思、批判现实一直是学术研究的基本社会价值之一。而学术研究确立批判精神的关键则在于对一种理想价值的合理预设。只有在合理预设的理想价值的参照下,才能映射出现实生活的不足,进而形成学术研究明确的批判立场。如果这种预设的理想价值是不合理的,那么批判的立场也就无从谈起了。从表面上看,伯明翰学派并不缺少批判:霍加特、费斯克等学者对精英文化无不展示出了鲜明而激烈的批判姿态。然而,这种批判的预设价值前提却十分薄弱,甚至可以说不堪一击。伯明翰学派批判精英文化的预设价值前提就是文化民粹主义所极力称赞的民众符号经验与民众文化活动,而现实生活中的民众符号经验与文化活动却并不符合理想民众文化的标准:第一,民众创造、生产的文化绝非理想的民众文化。如前所述,霍加特对民众自身创造、生产的文化推崇备至,称其为“真正的人民的世界”、“理想文化”,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毋庸置疑,这种文化可以充分表达民众自身的观念、情感、意识。然而,一方面民众自身的素质有限,他们创造、生产的文化的品质并不高;另一方面民众在创造和生产这种文化时是随意的、非理性的,从没有认真考虑过所创造和生产的文化对自身会有什么作用。这就造成了民众创造、生产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缺少对民众的有益影响,甚至可以说在客观上还形成了民众接受教育、提升素质的障碍。有趣的是,民众创造、生产的文化的不足却恰恰是精英文化的长处。可见,即使是在为民众争取文化权利的角度上,霍加特所推崇的这种文化同精英文化相比,也不具有更多优势。可以说,它并不是一种理想的民众文化形式。第二,民众通过消费“再创造”、“再生产”的文化也不是理想的民众文化。虽然以费斯克为代表的后期伯明翰学派学者主张民众可以通过文化消费和文化解读来重构主流文化的符号体系,用主流文化的原料“再创造”、“再生产”民众自己的文化,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一主张却很难实现。原因在于:其一,民众的素质虽然在战后有所提高,但就普遍意义而言,民众在抵抗社会控制和利用主流文化的原料生产自己的意义方面还缺乏真正的自主性和创造性。除了相关于家庭、氏族与地方社群的风俗习惯等传统以外,民众没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与价值,实际上他们缺乏建立自己独特文化、价值的头脑⑨。其二,即使民众能够拥有“再创造”、“再生产”自己文化的独立意识,它再生产的原材料也还是主流文化提供的,这就使它的“再创造”、“再生产”很受局限,并不能够真正贡献出有冲击力和独立意志的民众文化:民众反抗的原材料主要是由商业社会提供的,他们难以自发地用他们自己制造的原材料来创造文化,主要通过拼贴式的“符号游击战”进行反抗,这本身大大限制了民众反抗的彻底性⑩。其三,即使民众可以通过自己的策略和技巧巧妙躲过各种主流文化的控制,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理解和重构这些主流文化,“再创造”、“再生产”出具有民众独立意识的文化,我们又如何来判定呢?当我们看到一种通过“拼贴”的方式创作出来的文化时,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反抗主流文化的民众文化,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反过来说,那正是资本主义社会主流文化,尤其是商业文化标新立异和哗众取宠精神的体现,从而是主流文化预谋已久的收编策略呢?在发达工业社会强大的文化控制下,这实际上也不是不可能的:“作为抵抗的亚文化与作为领导权一部分的商业文化之间的界限实际上很难划定”(11)。既然现实生活中民众的符号经验与文化活动并不符合理想民众文化的标准,那么,强行为民众的符号经验与文化活动贴上理想的标签,制造一种空洞的价值预设,并以此为出发点和立足点来批判现实,必然是缺乏力度、缺乏深度且无法令人信服的。这也是霍加特与费斯克等学者对精英文化的批判虽然鲜明,虽然激烈却仍被学界诟病为苍白无力的主要原因。文化民粹主义就这样通过对民众符号经验与文化活动的盲目尊崇与抬高剥夺了伯明翰学派真正的批判精神。
其次,文化民粹主义对精英文化的批判与贬低致使伯明翰学派忽视了文化的精神内涵及其教化功能。这种忽视直接导致了当代学界对伯明翰学派文化观念合理性的质疑。实际上,文化的精神内涵和教化功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构成了学界理解文化的必要因素。我们知道,文化概念的提出主要是为了反抗文明概念对“物化”行为的强调。因此,文化概念在形成之初特别强调文化的精神内涵和陶养功能,如18世纪的思想家赫尔德指出,各民族、各时代的文化以不同的形式“表现了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文化中最内在的精神”(12)。后来的思想家、理论家虽然讨论文化的侧重点不同,但都十分重视探讨文化的精神内涵和陶养功能:伏尔泰指出,文化的发展就是人类理性的发展,文化的使命就是陶养性情,使人能够根据自己的自然本性的要求和需要而生活。康德在伏尔泰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了对文化在理性角度的概括:“有理性的实体为了一定的目的而进行的能力之创造”(13),文化的价值就在于完善内在人格。卡西尔虽然不再强调文化的理性内涵,但他坚定地认为文化内涵了一种心灵性、精神性的东西,人类可以通过文化达到“自我解放”。马尔库塞认同于卡西尔,也认为文化内涵的就是与“物化”相对的人性精神,文化能够带领人的心灵走向真正的解放。直到伯明翰学派诞生之前的20世纪初,以马修·阿诺德、T.S.艾略特和利维斯为代表的英国文化主义也还是在以反抗“物化”的文明为己任,强调文化崇高、伟大的精神内涵以及文化教化民众的功能。而伯明翰学派的文化民粹主义者却将这种对文化的理解仅仅看作是对精英文化的概括,并没有认识到它对解释文化本身的重要性。因此,他们在理解文化时,为了鲜明地对抗精英文化,就着力强调文化的日常性以及民众自身的文化创造能力,而刻意忽视文化本来就蕴含的精神内涵与应有的教化功能。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况在前期的霍加特那里并不十分严重。虽然霍加特也强调文化的日常性,也强调民众超越于资产阶级的文化创造能力,但他一方面还承认文化内涵了某种意义,他曾以《派格报》为例分析了民众文化内涵的“日常”、“惊奇”和“道德”意义;另一方面也没有特别无限度地夸大民众的文化创造能力,只是对民众的文化创造能力作出了充分肯定。情况在后期的费斯克那里才开始变得严重。费斯克虽然在解释文化概念时也指出文化内涵了对意义与快感的流通,但他无限度地夸大民众文化“再生产”、“再创造”的能力,却有主张阐释无限制之嫌。当意义可以被无限制地阐释时,也就不存在什么稳定的意义了,也就是说意义本身被消解,失去了意义。当费斯克消解了意义本身时,他也就彻底消解了文化的精神内涵以及随之而来的教化功能。
最后,文化民粹主义阻碍了文化研究对社会生活的真正介入。伯明翰学派一直努力将文化研究对社会生活的介入建设成为自己的研究特色。在该学派发展初期,威廉斯不但力图使文化理论平民化,而且还努力对现实政治、文化教育做出实际的介入和干预。霍加特走得比威廉斯更为极端,他试图通过控制传播媒体与教育社会个体的双重方式挤压精英文化,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真正民主”的、理想的民众文化;这种设想比起威廉斯来更加缺乏实际操作性。在费斯克的理论视野中,民众只要成为一个狡猾的读者、能动的受众,就可以对社会权威和既定秩序做出想象性的抵抗。这种理论显然缺乏对现实生活真正的介入和批判。在费斯克时代,文化研究已经演变成大学课堂上传授的时髦知识和精致的操作程序;文化研究完全变成了脱离社会生活的学院式空想;文化研究学者从而逃避了应当担负的社会责任。
由于文化民粹主义的局限,伯明翰学派后来逐渐丧失了真正的批判精神,忽视了文化的精神内涵与教化功能,并由此失去了真正介入社会生活的能力。该学派随之也慢慢走向了衰落。伯明翰学派的衰落为当代文化研究的发展、走向敲响了警钟,如何避免落入文化民粹主义的陷阱由此成为当代文化研究学者密切关注的问题。本着“解铃还需系铃人”的原则,我们可以针对伯明翰学派文化民粹主义形成的原因,尝试为当代文化研究的发展路向提出建议:首先,当代文化研究需要确立一种多元的文化观念。文化民粹主义产生的最初理论原因就在于将具有平民色彩的文化观念当作了理解文化的唯一途径,从而造成了对民众文化活动的过度尊崇与抬高。在现实生活中,文化从来就不可能仅体现为一种单一、纯粹的文化形式,它总是一种包括民众文化、精英文化等各种文化形式在内的混合体。这样,在理解文化时,我们也一定不能对现实生活中的某一种文化形式,无论是精英文化还是民众文化,做过度的尊崇与抬高,而要将精英文化、平民文化都看作是多元文化中的不同文化形态,承认它们各自存在的合理性,从而确立一种多元的文化观念。威廉斯在伯明翰学派建立初期分别针对不同文化形态而总结文化概念的做法就很具有参考意义。其次,当代文化研究需要对文化生产领域保持密切关注。文化民粹主义在伯明翰学派后期被强化的主要理论原因就在于,在理解文化时,彻底抛弃了对文化生产领域的关注,将注意力完全放到了考察文化消费领域上。仅仅从文化消费的角度来考察文化,就对文化产生的原始动机和阐释的最大限度缺乏了解,从而容易无限度地夸大文化消费者的文化活动能力,陷入更深一层的文化民粹主义。霍加特和霍尔因此后来都对完全抛弃了将文化观念与文化生产领域密切结合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表示出了不同程度的后悔:霍加特对抛弃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的伯明翰学派的所谓“葛兰西转向”提出了激烈的批评,认为伯明翰学派应该一直保持对文化作为“整体的生活方式”的理解,而不应该有任何实质性的理论转向。霍尔更是对自己抛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表示了深深的自责,将此描述为一种“理论化的失败”,“使得更弱的、观念上贫乏的范式得以继续流行,主宰着这个领域。”(14) 正是在这一基础上,麦克盖根指出:“文化研究从文化的政治经济学中的脱离,迄为该研究领域之最自残特征之一。”(15) 最后,当代文化研究需要时时注意保持同现实生活的互动关联,避免陷入纯学院化的研究。学术研究只有与现实生活保持时时互动的密切关联,才能够拥有长久的生命力和社会价值。文化民粹主义之所以能够出现在伯明翰学派内部,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相关学者忽视了研究与现实生活的时时互动,致使研究有时同现实生活脱节。这样,就会不自觉地出现某些偏差和谬误。比如霍加特虽然注意从考察现实生活的角度来得出结论,但他在考察现实生活时过分执着于“文化是整个生活方式”的平民立场,致使在理解现实时缺乏客观的态度,夸大了民众自我生产文化的能力,所以才造成了研究的民粹主义倾向。同样,霍尔、费斯克虽然不缺乏对现实生活的考察,但他们考察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得出结论,而是为了确证已经通过学理推衍而得出的结论。这种学院化的研究方式最终导致了夸大民众能动消费能力的民粹主义的产生。而时时注意保持同现实生活互动关联的威廉斯就没有落入文化民粹主义的陷阱。威廉斯总是在进行理论考察之后,再回到现实生活的层面对自己的理论观念进行检验,并及时修正其中脱离现实生活的学院化因素,无论是他在前期定义“文化是整个生活方式”时,还是他在后期定义文化是“社会秩序得以传达、再生产、体验和研究”的“符号系统”时,都是如此。
需要指明的是,虽然伯明翰学派的理论曾一度陷入困境,但这并不意味着该学派理论生命的结束。如果我们能够有效纠正其文化民粹主义的弊端,该学派的理论应该能够在当代文化研究中继续发挥积极、重要的作用。
收稿日期:2009-01-06
注释:
① 吉姆·麦克盖根:《文化民粹主义》,桂万先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② Graeme Turner,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An Introduction,London:Routledge,2003,p.239.
③ Richard Hoggart,The Uses of Literacy,U.S.A.New Jersey New Brunswick:Transation Publishers,1998,p.263.
④ Pierre Bourdieu,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p.6.
⑤ Raymond Williams,Culture,Fontana New Sociology Series,Glasgow:Collins,1981,p.13.
⑥ David Morley and Kuan- Hsing Chen,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1996,p.141.
⑦⑧ Raymond Williams,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90,p.90.
⑨ 阿兰·斯威伍德:《大众文化的神话》,冯建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00页。
⑩ John Storey,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 :An Introduction,Pearson Education Asia Limited and 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4,p.10.
(11) Simon During ,The Cultural Studies Reader,London :Routledge,1993,p.357.
(12) 曹卫东、张广海:《文化与文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13) 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宗白华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53页。
(14) Iain Chambers and Lidia Curti ,The Post - Colonial Question :Common Skies,Divided Horizon,London :Routledge,1996,p.258.
(15) 吉姆·麦克盖根:《文化民粹主义》,桂万先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页。
标签:伯明翰论文; 民粹主义论文; 精英文化论文; 精英主义论文; 消费文化论文; 消费社会论文; 活动理论论文; 经济学派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精英阶层论文; 结构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