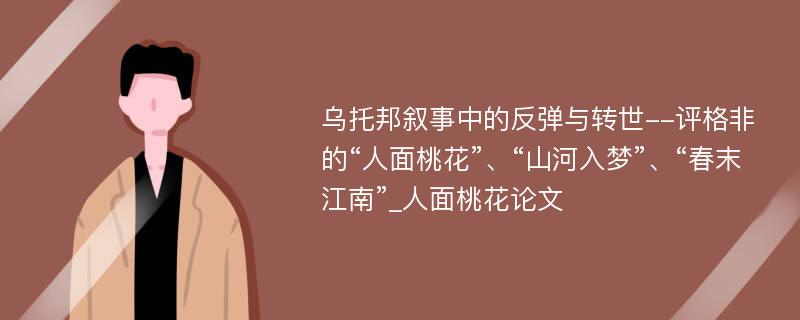
乌托邦叙事中的背反与轮回——评格非的《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乌托邦论文,人面桃花论文,江南论文,山河论文,评格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格非的《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以其举重若轻的百年中国叙事,从清末民初一直写到新的世纪转折,隐喻了一个古老民族在寻求新生的过程中的世纪性孤独,轻灵中透出沉重,浪漫中散发出宿命的气息。对于格非来说,从《人面桃花》(2004)到《山河入梦》(2007),再到《春尽江南》(2011),这绝不仅仅是一次叙述的历险,更是一次漫长的精神苦旅。在将近十年的写作时间里,格非要经受住的是参透百年历史迷雾后的悲凉,准确地说,他要直面我们民族百年乌托邦冲动中背反与轮回的挣扎和洗礼。这是一种灵魂的煎熬,而作为煎熬的馈赠,则是参透历史悲凉后的平静,一如《春尽江南》附录的《睡莲》诗中所描述的那样:“事物尚未命名,横暴尚未染指/化石般的寂静。”
在中外文学史和文化史上,乌托邦叙事由来已久,这得归因于人类集体无意识中永不衰竭的乌托邦冲动。古代中国的乌托邦叙事带有浓郁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可以说是对孔子的“大同世界”的文学写照。而在西方,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莫尔的《乌托邦》和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再到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同样性质的乌托邦叙事一直不绝如缕。然而,进入20世纪以来,西方文坛出现了所谓“反乌托邦三部曲”,扎米亚京的《我们》、奥维尔的《1984》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它们以其强烈的现代主义乃至解构主义的叙事方式彻底颠覆了古典的乌托邦理想及其叙事模式。从乌托邦叙事到反乌托邦叙事,显然,20世纪是人类乌托邦冲动及其叙事的历史分水岭。然而,具体到20世纪的中国却有所不同。作为一个后发性的现代化国家,传统中国在向西方现代化认同的现代性进程中无法与20世纪西方的反乌托邦叙事保持同步,相反,传统的乌托邦冲动及其叙事模式在20世纪的中国文坛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这在1949年以后的“50—70年代文学”中表现得至为明显,以柳青的《创业史》和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为代表的“红色经典”长篇小说即是明证。直到20世纪末期的中国文坛,才出现了以阎连科的《坚硬如水》和《受活》为代表的激烈的反乌托邦叙事作品。如果把阎连科的反乌托邦叙事与柳青和浩然等人的乌托邦叙事加以简单对照,不难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二元对立的绝对主义思维定势,前者是后者的反题,后者是前者解构的对象。事实上,如何看待20世纪中国的乌托邦冲动及其叙事,并非是一个简单的非此即彼的立场问题,虽然一个作家在乌托邦叙事中择定一种明确的价值立场进行叙述要便利和容易得多,但我们不能忽视历史及其本身隐含的历史文化心理结构的复杂性和多元性,而且在很多时候面对着历史,我们是无法做出简单的价值判断的。这意味着还存在更复杂和更客观的书写20世纪中国乌托邦冲动的叙事形态。
在我看来,格非的《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正好提供了一种客观而复杂的20世纪中国乌托邦叙事形态。格非并没有轻易地落入乌托邦叙事与反乌托邦叙事二元对立的叙事陷阱中,他的叙述立场显得高远而超拔,这是一种俯视历史的悲悯情怀,已经超越了简单的道德价值评判。不难看出,传统的乌托邦叙事大抵遵循传统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叙事成规,其中,浪漫主义是主导,现实主义是表象,这在所谓“革命现实主义”叙事或者毛泽东倡导的“两结合”叙事中表现得很分明。而在现代的反乌托邦叙事中,现代主义的荒诞叙事与后现代主义的叙述游戏占据了主导位置,这在西方的“反乌托邦三部曲”中表现得极其强烈,同样,在阎连科的所谓狂欢化叙事和荒诞现实主义叙事中也留下了深深的印痕。而我要说的是,在格非的乌托邦叙事中我们已经看不到乌托邦与反乌托邦之间的截然界限,作者对乌托邦冲动的情感和态度不是简单地溢于言表,而是隐含在叙述的深层,而且作者的情感价值立场是复杂而冲突的,由此带来了格非的乌托邦叙事中的多种声音,类似于巴赫金所说的“复调小说”。之所以出现这种叙述效果,得益于格非没有简单地像自己早期的先锋小说那样径直采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叙事策略,而是转向了寻找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相结合的新的叙事形态。这是一种叙述的回归,但绝不是简单的回归传统,而是谋求传统的现实主义与现代的现代主义之间的叙述融合。正如格非所言:“这种回归是建筑在对传统现实主义及现代主义小说全面考察的基础之上的,并非意味着对过去的简单重复……越来越多的作家在传统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选择了一条谨慎的中间道路。我认为,这条道路至少在目前是可行的。因为他们一方面使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中的过时成分得以消除,同时,又避免了小说最终走向分裂。”①格非之所以选择这样一条“中间道路”,还因为他后来逐渐意识到,也许并不存在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截然界限,实际上二者之间常常是彼此交融的,现实主义中有现代主义因素,而现代主义中有现实主义因素,前者如老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福楼拜的小说,后者如卡夫卡和普鲁斯特的小说,他们的小说中都包含了各自的所谓对立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格非不认为自己的小说创作存在着所谓前后期的“断裂”,而是更多地强调自己小说的连续性。②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格非的小说创作历程中真的并不存在叙述转型的问题,实际上他早年就经历过“从规矩到乱的过程”,③即摆脱传统现实主义叙事成规、走向先锋派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叙述策略的过程。以此观之,则新世纪以来,格非又经历了反向的“从乱到规矩的过程”,这就是格非在《人面桃花》三部曲中所实现的小说叙述回归,但绝不是简单地回归传统的现实主义,而是谋求传统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艺术视域融合。
唯其追求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叙述融合,格非的乌托邦叙事才具有所谓“向内转”的倾向。对此,格非的解释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叙事方面更加“内在”,不像先锋时期那样直露地做形式实验;一个是作者开始注重吸收传统叙事资源,向内而不是向外拓展。④格非想以此划清他的“向内转”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艺界的“向内转”思潮之间的界限。实际上两种“向内转”之间并非没有联系,格非在《人面桃花》中对人物的心理世界的挖掘是颇见功力的,而且“小说当中涉及的人物也好,历史事件也好,都与历史关系不大。写的都是我的感觉,我的经验。这些人物也是‘我’。比如说秀米这个人物,我对她给予了很大的同情,她的感觉也是我的感觉”⑤。转向人物的内心,最终转向作者的内心,凸现人物(作者)在百年乌托邦冲动的背反与轮回中的心理困惑和精神痛苦,这就是《人面桃花》三部曲“向内转”的深层意义之所在!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格非为什么要在关于《山河入梦》的访谈中这样说:“伟大作品拥有顽固的记忆力。作家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个记录者。他们用文学的方式记录永不磨灭的人类心灵史。”⑥
二
《人面桃花》第一部问世后好评如潮。人们都相信曾经的那个先锋作家格非在沉寂多年后又回来了,而且是以一种更为老到的姿态强势回归,这就是前面所说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相融合的叙述姿态。关于《人面桃花》的评论焦点,几乎都集中在所谓乌托邦叙事上,作者在访谈中对此也做过明确的表述。他说: “我所关注的正是这些东西——佛教称之为‘彼岸’、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的完全平等自由的乌托邦,《人面桃花》中讲到的桃花源也是这么一个存在于想象之中的所在。”⑦然而,关于《人面桃花》的乌托邦叙事研究依然有待进一步深化,我们需要做的是立足文本的叙述结构去破译乌托邦叙事的策略和意图。
首先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部长篇小说中有两种不同性质的乌托邦形态:一种是王观澄所创建的以花家舍为载体的古典形态的江湖乌托邦,一种是陆秀米所创建的以普济学堂为代表的现代形态的革命乌托邦。关于这两种形态的乌托邦叙事占据了这部长篇的绝大部分篇幅,而女主人公陆秀米的人生历程恰好把这两种形态的乌托邦叙事贯穿了起来。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小说中两种不同形态的乌托邦叙事也凝聚了各自不同的群体成员,亦可谓之为精神家族。从古典形态的乌托邦来看,陆秀米的父亲陆侃无疑属于这一精神阵营。陆侃饱读诗书,学优则仕,然而仕途并不通达,罢官后在普济筑屋隐居,怡然自乐。但陆侃心中一直有着难解的桃花源梦想,他时常对着据说是出自韩愈手笔的《桃源图》发呆发痴,他想在普济重现陶渊明的世外桃源的现实图景,他甚至构想建筑一条风雨长廊把普济的住户联接起来,让老百姓不惧风雨、安居乐业。在普济人的眼中,陆侃就是一个疯子,他的妻子和女儿还有家佣,全都把他看做疯子。疯子是孤独的,因为他有着常人难以理会的超越现实的冲动,这种冲动常常就是西方人所谓的乌托邦冲动。在常人那里,这种乌托邦冲动往往被压抑在潜意识域,而在疯子或先知这里,这种冲动时刻在寻觅着对象化或现实化的契机,这就是常人与疯子的一大区别。疯子陆侃的离家出走,给女主人公秀米的人生带来了重大转折,因为革命党人张季元随即住进了普济秀米的家,他是秀米的母亲的情人。在很大程度上,张季元充当的是陆秀米的“代父”角色,他的到来改变了秀米的人生方向,他给秀米带来了现代的革命乌托邦冲动。张季元是清末革命党组织——蜩蛄会的核心成员,推翻封建专制的腐朽清王朝,建立现代的民主自由世界是他那一类人的桃源梦想,小说中的薛举人薛祖彦、小驴子周怡春,包括女主人公陆秀米等在内,都属于这个乌托邦家族的精神成员。不过对于秀米来说,她一开始并未明确地接受“代父”张季元的革命乌托邦冲动的影响,她对张季元的恋父冲动更多地表现为她与母亲梅芸之间的暗中情感较量。转折发生在秀米被劫掠至花家舍以后,她在花家舍这个土匪窝子里面居然看到了父亲理想中的桃源梦境全部得以实现了!在花家舍里,包括总揽把王观澄在内,其他五位爷都是很有些来历的人,有的从文、有的习武,他们把花家舍经营得像一片世外桃源,让来者无不叹为观止,但对于知情者而言,花家舍就是一个土匪窝,就是一个江湖世界,其中充满了刀光剑影和尔虞我诈,充满了血和泪。花家舍其实是一个人间天堂的幻影,看似美妙无比,实则隐藏着巨大的灾难和危机。秀米在花家舍惨遭蹂躏、九死一生的经历使她最终放弃了父亲陆侃的古典乌托邦理想,而走上了“代父”张季元远走东瀛,致力于反清抗暴,建构现代革命乌托邦的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格非在《人面桃花》中不仅写出了古典江湖乌托邦的破产,而且也写出了现代革命乌托邦的危机。秀米自日本归来后继承了张季元的遗志,她在普济一带神出鬼没,仿佛当年的张季元再世重生。她领导成立了普济地方自治会,在一间寺庙里设立了育婴堂、书籍室、疗病所和养老院,然而一切如同虚设,她牵头的水渠工程甚至还差点给普济带来灭顶之灾。自治会计划受挫后,秀米又办起了普济学堂,自任校长,直接致力于反清革命活动。正如陆家的老管家宝琛所察觉到的那样,他对老夫人说: “你说她走了当年陆老爷的老路,我看不大像,照我看,她是把自己变成了另一个张季元。那个死鬼,阴魂不散!”确实如此,秀米就是另一个张季元,她心中涌动的是张季元式的现代革命乌托邦冲动,而不是陆侃式的古典江湖乌托邦冲动。秀米无意于相忘于江湖,过那种隐居般的桃源生活,她需要的是介入,介入到改变现存社会秩序的乌托邦进程中。这意味着暴力革命,秀米也确实卷入了革命的暴力之中,她甚至因为沉迷于暴力革命而忽视了基本的亲情伦理,母亲和儿子的死在不同程度上她都难辞其咎。这不禁让读者想起了书中张季元的一则日记,日记中记载了蜩蛄会成员在夏庄薛宅中商定的《十杀令》,中间竟然有“妓女杀”、“缠足者杀”、“媒婆、神巫、和尚、道士皆杀”等条款。由此可见现代革命乌托邦冲动非理性的另一面。我们甚至可以说,此时的革命乌托邦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关于乌托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德国学者曼海姆有过十分精辟的阐述,有研究者则做出了极为简洁的归纳,即意识形态是“指导维持现存秩序的活动的那些思想体系”,乌托邦是“往往产生改变现存秩序活动的那些思想体系”。⑧这种归纳虽然点明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之间的区别,即对立关系,然而却忽视了两者之间还具有内在的同一性和相对性,即乌托邦与意识形态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正如曼海姆所说:“在一定的情况下,什么表现为乌托邦,什么表现为意识形态,本质上取决于人们运用这种标准来衡量的现实的阶段和程度。显然,那些代表了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秩序与思想体系的阶层,会把他们所具有的那种关系结构感受为现实,而被迫反对现存秩序的集团则对他们所力争的和通过他们而实现的社会秩序的初次感到兴奋。一定的秩序的代表,会把从他们观点来看在原则上永不能实现的概念叫乌托邦。”⑨既然乌托邦和意识形态是可以相互转化的,那就意味着乌托邦冲动在现实化的进程中隐含着与生俱来的悖谬性。而格非在《人面桃花》中正好揭示了古典与现代两种乌托邦冲动的悖谬性,这是一种历史的两难,如同二律背反,无法摆脱,散发出历史的宿命气息。从古典形态的江湖乌托邦来看,陆侃的桃源情结属于原发性的乌托邦冲动,它是中国传统士人力图逃避或者改变现存社会秩序的一种潜在心理诉求,然而,一旦这种潜在的心理诉求或者文化冲动诉诸于现实社会进程,即由王观澄为代表的花家舍人逐步变为现实,原先的不确定的乌托邦冲动就衍变为凝固的意识形态了。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是对乌托邦的反动。于是我们看到在《人面桃花》中,花家舍被掀开了诗意温情的面纱,而裸露出暴力和杀戮的真相。不仅古典的江湖乌托邦存在着这种历史的悖反,现代的革命乌托邦也不例外。当陆秀米继承了张季元等人的遗志而投身革命后,革命先辈的乌托邦冲动便开始在现实的革命进程中流露出了意识形态的本质。
尤其是当我们看到正是革命党人“小驴子”周怡春策划了花家舍的内部暴力事件时,两种乌托邦之间的精神同一性可谓一目了然。无论是古典的江湖乌托邦还是现代的革命乌托邦,当它们走向现实社会进程的时候,其自身的历史背反如出一辙。而且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二者会呈现出合流或合谋的倾向,即如《人面桃花》中的乌托邦叙事所暗示的那样,现代的革命乌托邦与古典的江湖乌托邦之间不仅同构而且同质,于是革命乌托邦也就褪去了现代色彩,演变成了新古典主义的乌托邦。这当然是一种历史的轮回,而不仅仅是我们习惯上所说的辩证螺旋式的上升。小说中关于乌托邦叙事的历史轮回还借助于几个颇有些神秘性的物件或意象给予了暗示。一个是花家舍,它在小说中反复出现,沟通了古典的江湖乌托邦与现代的革命乌托邦之间的精神渊源。二是金蝉,它是小说中革命党人之间传递的信物,女主人公秀米的一生与金蝉有着不解之缘。当初张季元在临难逃亡前第一次赠给她金蝉,这是两人之间革命乌托邦冲动传递的精神信号。第二次是在花家舍被困期间,老尼韩六送金蝉给秀米,在某种意义上唤醒了秀米内心的革命乌托邦冲动。第三次是“小驴子”送金蝉给秀米,此时秀米在革命失败后闭门禁语,她拒绝“小驴子”的来访,这意味着革命乌托邦冲动在她的内心深处已寂灭。丧失了革命乌托邦意义的金蝉不过是一个无用的空壳而已,它在灾难的岁月里只能被废弃。小小的金蝉脱壳,恰好隐喻了秀米追逐乌托邦的迷幻人生。还有一个在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意象是瓦釜,它其实是一件古老高妙的乐器,这是父亲陆侃的遗物,晚年的秀米在瓦釜里逐渐融化的冰花中仿佛看到了自己的过去和未来,远去的父亲陆侃和遗失的儿子谭功达正在向她走来。秀米就在这种幻觉中死去,她无法拯救自己,除了弥合自己内心的创伤,她无法阻止自己精神密码中的乌托邦冲动开始再度轮回。
三
关于《人面桃花》和《山河入梦》的创作动机,格非这样说道: “一部小说的动机往往来源于一个简单的比喻。我在写《人面桃花》时,无意中想到了冰。在瓦釜中迅速融化的冰花,就是秀米的过去和未来。这个比喻是我的守护神,它贯穿了写作的始终,决定了语言的节奏和格调,也给我带来了慰藉和信心。那么,什么是《山河入梦》的比喻呢?我想到了阳光下无边无际的紫云英花地。假设,花地中矗立着一棵孤零零的苦楝树;假设,一片浮云的阴影遮住了它。望着这片阴影,姚佩佩在心中许了一个愿,闭上了眼睛。不管姚佩佩如何挣扎,那片阴影永远不会移走,因为它镌刻在她的心里。为什么我的内心一片黑暗,可别人的脸上却阳光灿烂?这是姚佩佩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⑩在我看来,《山河入梦》中的这个核心比喻或者中心意象具有双重性,阳光下苦楝树的阴影遮蔽了一片紫云英花地,简言之,阳光与阴影,各自象征着一种乌托邦冲动,构成了这部长篇小说中乌托邦叙事的分裂、冲突与背反。
与《人面桃花》把故事时间选定在清末民初不同,《山河入梦》的故事时间主要被安排在新中国建立后的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广义上就是人们习惯上所说的“十七年时期”。这个时期产生了大量的“红色经典”,尤其是农业合作化题材的长篇小说中普遍具有乌托邦叙事的特征。但《山河入梦》并没有简单地重复当年的革命浪漫主义形态的红色乌托邦叙事,而是以冷峻的历史眼光回望那一段乌托邦冲动的历史,不仅写出了那种充满了“大跃进”精神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冲动的历程,而且揭示了被共产主义乌托邦冲动所压抑或遮蔽的另一种人道主义或自由主义的乌托邦冲动。如果借用那个年代的习惯用语,那么前一种属于红色的乌托邦冲动,拜太阳或阳光所赐,而后一种属于灰色的乌托邦冲动,带有所谓不可见人的“小资情调”,只能存在于阳光下的阴影中。这两种乌托邦冲动在小说中分别由男女主人公谭功达和姚佩佩来体现。值得指出的是,格非在《山河入梦》中的乌托邦叙事是充满了矛盾和缠绕的,作者既写出了红色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冲动与灰色的自由主义乌托邦冲动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又写出了红色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冲动内部的裂隙和矛盾,还写出了两种不同性质、不同色彩的乌托邦冲动之间的融合和交集。这种种矛盾和冲突着的乌托邦叙事,在小说中主要借助于男女主人公谭功达和姚佩佩的凄凉的爱情故事和不幸的人生遭遇来完成。
从红色乌托邦来看,一切都离不开谭功达,他是小说的男一号,也是小说中乌托邦叙事的关捩和纽带。谭功达是陆秀米之子,长大后投身革命,建国后出任梅城县县长。按照新的建制,在梅城县和普济乡,到处都有关于陆秀米的传奇人生故事在流传。生性敏感的谭功达多少年来在内心中一直有一种隐隐的恐惧,不管自己如何挣扎,他终将走到母亲的老路上去,无可逃遁。这是无可选择的命运,更是历史的圈套和轮回。事实上,革命成功后的谭功达确实沉浸在了天下大同的桃源梦中,他要做的就是把母亲陆秀米乃至外祖父陆侃的桃源梦接续起来,这是超越时空的精神链接,显示了20世纪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乌托邦冲动的超强力量。正如谭功达革命年代的文书高麻子乡长在匿名书中所言:“公主梅城县政,不思以布帛菽粟保暖其身,而欲汲汲于奇技淫巧、声光雷电,致使道有饿殍,家无隔夜之炊。民怨鼎沸,人心日坏。造大坝,凿运河,息商贾,兴公社,梅城历来富庶之地,终至于憔悴殆尽。为公思之,每恻然无眠。须知梅城小县,非武林桃源,不能以一人之偏私,弃十数万生灵于不顾。退社之风,盖有源于此。人事天道,自有分界。人事所不能,待以天道而已。夫人定胜天者,闻所未闻,非愚则妄,不待详解。至若共产主义于一九六二年实现,则更是荒诞不经,痴人说梦。”高麻子是谭功达的诤友,他对李自成和朱元璋的一番明辨,其意在于使谭功达幡然悔悟,不再执迷于天下大同的桃花梦。可惜谭功达并未清醒地意识到正置身于一个“天下山河都入梦中”的时代幻境之中。他还请人画了一张梅城规划图,技法精湛、出神入化,名曰《桃源行春图》。正当他雄心勃勃地准备实现自己的桃源梦时,他力主修建的普济水库崩溃,因情节严重他被撤职反省。然而,谭功达并未因此而从红色的乌托邦迷梦中醒来,在被边缘化的日子里他仍然坚守着自己的共产主义大同理想。如果借用曼海姆的观点,此时的谭功达依旧在拒绝让个人的乌托邦冲动意识形态化,他顽强地守护着内心中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理想,而无视现实中共产主义乌托邦已经陷入了意识形态困境。比如在郭从年领导和主宰着的花家舍人民公社里,尽管道不拾遗、秩序井然,然而掩盖不住社员内心的忧戚,因为他们的人身自由遭到限制,神秘的101组织暗中监控着花家舍所有人的生活。就连临时寄居在花家舍的谭功达的一举一动也遭到了严密监视,他与姚佩佩的通信也无任何私密可言。知道了这一切后的谭功达十分恐惧,郭从年和他的花家舍共产主义乌托邦在谭功达的心目中是彻底地坍塌了。然而,谭功达虽然抛弃了这种完全意识形态化了的红色乌托邦,但他内心深处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冲动至死未泯,他临死前还念念不忘他的“梅城规划草图”。
在《山河入梦》中,与红色乌托邦叙事相对立的是灰色乌托邦叙事。姚佩佩是灰色乌托邦叙事的主人公,她内心深处永不磨灭的是一种人道主义—自由主义乌托邦冲动。这种乌托邦冲动与那种意识形态化或者体制化了的红色乌托邦秩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甚至可以说是背道而驰。而怀抱着这种另类乌托邦冲动的姚佩佩,在艰难苦恨的人生坎坷中始终痴心不改,执意向着自己内心中的乌托邦境界进发。姚佩佩出生于政治问题家庭,父亲在建国初被镇压,母亲自缢身亡,她像一棵苦楝树一样孤零零地生存在阳光普照的大地上。孤独的姚佩佩渴望自由,但就连一点微薄的人道尊严竟也难以实现。她一直觉得自己生活在黑暗中,她内心的黑暗无边无际,她短暂的一生始终在追求着光明而不可得。她深爱着谭功达,但这个迟钝的中年男人一再与她失之交臂。她唯一可以说上话的女友是汤碧云,但正是汤碧云狠下心出卖了她。她被金秘书长强暴后复仇成功,但因此而成了被通缉的杀人犯。她在逃亡中历经劫难,但最终鬼使神差地回到了起点,自投罗网。姚佩佩死了,带着她永难实现的自由主义乌托邦梦幻死了。但她在逃亡中写给谭功达的书信产生了奇妙的效果,阅读姚佩佩的书信,谭功达觉得自己的身心与姚佩佩已合为一体。所以小说的结尾专门写到了谭功达在弥留之际与姚佩佩在幻觉中重逢,那是一个“没有死刑、没有监狱、没有恐惧……没有烦恼”的世界,共产主义乌托邦与自由主义乌托邦在那里仿佛不再是两难选择,而是融为了一体。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格非为什么对姚佩佩如此的偏爱,正如他所说:“我想《红楼梦》里面最能表达作者内心的不是贾宝玉,而应该是林黛玉。在《山河入梦》里,姚佩佩在相当程度上隐含了作者。”又说:“其实姚佩佩的身上,更多地寄托了我的情感和我对这个世界的思考,她身上当然有我自己的观念和情感。谭功达是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但写出谭功达之后,我立刻感到了不满足,觉得他不足以表达我的内心,便想到了姚佩佩,写着写着对这个人物的感情就超过了谭功达,就发现自己跟她之间那种深切的关联。”(11)格非说的是实话,对于他来说,与谭功达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冲动相比,姚佩佩的自由主义乌托邦冲动更能与他心心相印。而且遥想那个战天斗地的红色年代,格非的人生遭遇与姚佩佩之间也并非没有关联,因为他的祖父当时因为政治问题而坐监,这种阶级成分问题曾经长期困扰着少年时代的格非。(12)由此我们发现,作者与女主人公之间不仅有着内在精神自传上的同一性,而且还有外在生活自传上的相似性。
四
《春尽江南》是格非的《人面桃花》三部曲的收官之作。这部书让我想起了格非早年的另一部长篇小说《边缘》。在《春尽江南》中,作者主要就是站在“边缘者”的立场上讲述我们这个时代的故事。我们这个时代一直被主流媒体称作“盛世”,我们这个时代的大街小巷也一直流行着“春天的故事”。格非显然没有那么乐观,他要做的就是从一个客观冷静乃至有些戏谑的叙述者角度,来透视我们这个习惯于以“春天”命名的时代里所隐藏的真相,当然包括社会众生相,但更重要的是一个时代的精神真相和心理潜影。唐人杜牧有诗云“秋尽江南草木凋”,折射了晚唐的衰飒和没落,而格非以一字之易,其“春尽江南”的中心意象,显然也包含了作者对于我们这个所谓盛世的末世情怀。书中的主人公谭端午一直喜欢阅读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据说就是一本“末世之书”,这应该不是偶然的。格非能在盛世中怀抱末世之感,是因为他看透了百年中国乌托邦冲动中暗含的循环和轮回,时空在流转,而精神总是跌入深渊。早在关于《山河入梦》的访谈中格非就明确地说过: “是的,我是一个宿命论者。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是一个预言家,对未来我们早就心知肚明,可是有些人装作看不到,自我麻痹,时间久了就是真的麻木了。”他同时又为自己辩解: “我常说,悲观就是乐观。……悲观是乐观的前提,要有勇气看到悲观的东西,并且有能力去承受。”(13)所以,我们可以说,格非的《人面桃花》三部曲是悲观之书,也是乐观之书,乐观来自于悲观,正如希望来自于绝望。
尽管叙事背景已转换至“改革开放”年代,但《春尽江南》在精神脉络上依旧与前两部紧密相连。谭端午、庞家玉、王元庆、绿珠、陈守仁,在这些主要人物的心灵深处,其实都涌动着乌托邦的冲动,只不过与陆秀米、张季元、谭功达、姚佩佩等人相比,他们的乌托邦冲动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呈现出了新的形态而已。显然,新的乌托邦形态并未完全割断与旧有的乌托邦形态之间的联系,就连谭端午那絮絮叨叨的母亲,也就是谭功达的遗孀张金芳也看出来了,她的两个儿子都有点疯疯癫癫、与众不同,区别在于,王元庆更像死去了的老鬼谭功达,而谭端午的身上似乎有着姚佩佩的精神血液。也许老太太朴素的直觉并不错,但毕竟是置身在一个所谓以新见称的时代里,谭端午和王元庆们的乌托邦冲动必然带有属于这个新时代的色彩和特质。从书中反复出现的关于“春尽江南”的写景描摹文字来看,“春”的象征意义不言而喻,它指涉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改革开放进程,简言之,即现代化神话。从80年代跃进到90年代以后,古老的中国已经正在现代化的高速路上飞奔。如果说80年代的现代化暂时还未大规模地暴露其流弊的话那么90年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就已经深深地酿成了大部分人的心理隐痛了。换句话说,如果说现代化或现代性在80年代还属于神话或者乌托邦的范畴,属于民众满怀期待要实现的理想,那么,经过90年代和新世纪的大规模的现代化扩张之后。现代化或现代性业已成了一种主流意识形态,丧失了其早先作为乌托邦思想和冲动的反抗性,由此也沦为新的乌托邦思想和冲动所要反抗的对象。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谭端午和王元庆们要反对自己的时代,为什么他们置身在一个春天的盛世里却有着秋天的悲凉,因为他们怀抱着另一种乌托邦冲动,这是对曾经的现代化乌托邦冲动沦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反抗。他们对时代的疏离、拒绝和反抗,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反现代化,其实质是对现代化或现代性的反思,由此形成了与主流的现代性意识形态相对抗的另一种乌托邦思想和冲动,即新保守主义或新传统主义乌托邦。
不难看出,《春尽江南》中的几个主要人物都经历过由现代性追求转向新保守主义的精神嬗变。男主人公谭端午的人生转折发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主要是80年代末的那次政治事件改变了他的精神航向。作为知名诗人,谭端午在80年代以现代性的名义疯狂地追逐着爱情和政治,这个时期的谭端午确实与他父亲谭功达当年心爱的女人姚佩佩在精神上一脉相承,他们追逐的都属于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的激进乌托邦。小说中重点暗示了诗人海子之死对于谭端午那一代人精神转折的象征意义。在遭受政治和人生挫折后,谭端午返回原籍,进了鹤浦市方志办公室任闲职。从此,他开始了另一种人生状态,用妻子庞家玉的话来说,谭端午过着一种“正在一点点地烂掉”的生活,而且乐此不疲。他陶醉在各种西方古典音乐中,他对工作和婚姻没有任何的激情,他在小说中自始至终都在读欧阳修的那部《新五代史》。他不仅厌倦了政治和婚姻,他甚至对消费主义时代的欲望消费也丧失了兴趣,这与他当年的诗友徐吉士形成了分流,后者由80年代的自由主义乌托邦直接滑向90年代以来的欲望化漩涡,而谭端午选择了疏离和对抗,所以他在妻子的心中定格为了一个“当代隐士”,这与小说中的那座招隐寺不谋而合。在漫长的《新五代史》阅读中,谭端午对欧阳修的忧世伤生感同身受,尤其是对书中频繁出现的“呜呼”二字心有戚戚,显然他在这部“衰世之书”中看到了我们时代的另一精神面影。他对钱穆和陈寅恪关于《新五代史》的赞语深以为然,恨不能像欧阳修那样“用一本书的力量,使时代的风尚重返淳正”。小说附录的那首诗《睡莲》,既可以视为谭端午对死去的妻子庞家玉的和解与呼唤,也可以视为作者对我们这个腐烂的时代的招魂和抗议。有意思的是,当庞家玉认为谭端午“正在烂掉”的时候,其实她不知道她说的正是她自己。庞家玉原名李秀蓉,在叫做李秀蓉的80年代里,她和谭端午一样是个有浪漫情怀的青年诗人,但在90年代以来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她在现代化的神话或意识形态里越陷越深,她由诗人摇身变成了律师,她与谭端午的价值立场越来越远,为了迎合这个时代的需要,她甚至不惜奉献自己的肉体,她对儿子学习的苛刻要求更体现了她与这个时代的合谋。只有当死神提前来到她面前的时候,庞家玉才幡然悔悟,她决意听从内心声音的召唤,抱病出走西藏。西藏在庞家玉的心中意味着乌托邦,那是一个也许还没有被现代化污染的地方,她在最后时刻与谭端午的精神终于息息相通。还有谭端午同母异父的哥哥王元庆,这个在市场经济年代发迹的老板,突然斥资几千万元建了一个“城市山林”别墅群,其实就是一座精神病院,而他自己成了第一个住进去的精神病人。显然,王元庆的精神裂变中隐含了他对现代化神话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拒绝和反叛。他在精神病院中还念念不忘地要在花家舍里建成一座传统书院,而事实是,花家舍被他的投资合伙人张有德改造成了一座销金窟,在那里成天上演着花家舍历史上各种传奇人物的搞笑故事,曾经的乌托邦历史就这样被消费和消解了。
在《春尽江南》中,与其说花家舍是乌托邦,不如说“城市山林”那座精神病院更像是乌托邦。新世纪的花家舍已成了温柔富贵乡,是消费主义的天堂。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个时代里乌托邦与意识形态之间合谋性的融合。同样,陈守仁的别墅“呼啸山庄”,还有谭端午和绿珠时常光顾的“荼蘼花事”,都不是纯粹的乌托邦,因为市场经济时代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完全渗透其中。即使是谭端午的红颜知己绿珠一直恋恋不舍的那座“香格里拉乌托邦”,最后也被她亲身证明不过是另一个被改造过的花家舍而已。这意味着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有纯粹的乌托邦,真正的乌托邦是一种精神、一种理想、一种冲动,它必须处于待定和未完成的状态,一旦现实化和对象化,它必然沦为固化的意识形态,从而成为新的乌托邦所反抗的对象。这就是乌托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悖论。在《人面桃花》三部曲中,格非不仅向我们揭示了百年中国乌托邦进程中的历史悖论,而且暗示了这种历史悖论中无法摆脱的集体无意识力量,因为乌托邦也好,意识形态也罢,其本质都属于集体无意识范畴。(14)然而,格非在《春尽江南》中所凸显或流露的新保守主义或新传统主义姿态,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乌托邦冲动或集体无意识,难免会遭到误解。事实上,新传统主义并不意味着完全回归传统,而是指向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如格非所言:“我们今天重新谈回到传统,谈到对传统的认知。谈到对中国传统资源的一种认可,一种继承,它本身也是一种意向,实际上是回不去的。而传统价值我觉得也是有道理的,有必要的,不是说要将我们现在的维度整个抛掉……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误解,没有这回事。”(15)这虽是谈的关于中国传统叙事资源的话题,但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同样适用。新传统主义或新保守主义并不完全拒绝现代性维度,它要表达的是对单一现代性神话的超越,它最终指向的是民族文化和文艺的复兴。
注释:
①格非:《小说的十字路口》,《塞壬的歌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51页。
②⑤⑦(15)格非、于若冰:《关于〈人面桃花〉的访谈》,《作家》2005年第8期。
③(12)格非、任赟:《格非传略》,《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4期。
④张学昕、格非:《文学叙事是对生命和存在的超越》,《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5期。
⑥(11)(13)格非、王小王:《用文学的方式记录人类的心灵史——与格非谈他的长篇新作〈山河入梦〉》,《作家》2007年第2期。
⑧路易斯·沃思:《序言》,见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4页。
⑨(14)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00、41页。
⑩格非:《山河入梦》,作家出版社2007年版,封底文字。
标签:人面桃花论文; 格非论文; 春尽江南论文; 山河入梦论文; 乌托邦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共产主义社会论文; 文学论文; 共产主义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