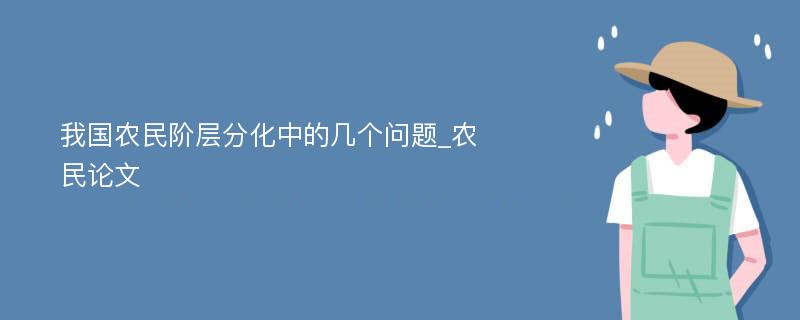
中国农民阶层分化中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问题论文,阶层论文,中国农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农民的基本情况怎样,直接、间接地决定着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心理特质。不了解中国农民,就不了解中国社会,农民的状况构成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之一部分。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以“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为其终点。当代中国农民的重新分化正是在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发生的。这支庞大队伍的重新解体,引起了社会各门学科的关注,在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上产生了许多分歧。本文试就中国农民阶层分化问题作一论述。
一、农民分层研究的指导理论
在当代学术界,分析和研究社会结构,主要有两大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层理论和西方的社会分层理论。究竟哪种理论更适合于作为农民阶层分析的指导理论,主要有三种看法。
第一种观点认为,在分析农民的阶级属性时,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而在进行阶级内部阶层分析时,则可吸收西方的社会分层理论。因为我国还是一个有阶级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差别和阶级之间的利益矛盾,所以还需要以阶级分析理论作指导;但同时,农民内部的阶层分化现象日益突出,西方社会分层理论在分析和认识社会阶层结构方面有其合理性,可以借鉴吸收。
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阶层分析理论。西方社会分层理论不能作为我们的指导理论,它本质上不是一门科学理论,因为它掩盖和抹杀了阶级的本质特征。我们应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的同时,根据变化发展了的社会条件,研究、概括、说明新的问题,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阶层论。
第三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在我国现阶段有很大局限性甚至已不适用;应以西方社会分层理论来指导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分层研究。认为在剥削阶级已被消灭的我国现阶段,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不是对抗性的而是非对抗性的,不是阶级关系而是阶层关系,用阶级观点难以解释其中许多问题,因而,西方社会分层理论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笔者认为,农民分层的指导理论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层论,而不能是其它什么。
1、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是正确揭示社会阶层分化及其内在规律的理论。
只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正确地揭示了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动力和源泉;揭示了社会各阶级阶层在社会发展和进步中的地位和作用;揭示了阶级的起源、性质、各阶级利益冲突的实质和阶级消亡的条件;阐述了阶级和阶层的划分标准。在剥削阶级被消灭以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阶级之间的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但阶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剥削阶级的消灭,并不意味着阶级的消灭。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但绝不是他的陪葬者。无产阶级不仅与资产阶级相联系,更重要的他是现代大工业的产物。同样,农民阶级也不可能是地主、富农阶级的陪葬者,传统农民是与农业尤其是传统的落后的农业相联系的。我国农民是从传统农业开始走向现代农业的新型农民,与传统农民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只有在农业也成为一种与工业没有任何本质区别的现代生产部门时,农民才和工人溶为一体。“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①
2、马克思主义的阶层分析理论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阶级内部的阶层分化现象不是现阶段我国农民阶级所特有的,历史上的一些基本阶级都曾发生过阶层分化现象。经典作家对此都有过系统的论述,这集中体现在《资本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等著作中,并不是如一些人认为的经典作家只注意阶级分析,很少或忽略了阶层问题的研究。这至少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分析理论缺乏全面了解的一种表现。尤其是列宁和毛泽东,正是因为他们对社会各阶层所作的详细调查研究,才制定了科学的农村阶级路线,从而在根本上保证了革命的彻底胜利。他们关于阶层论的一些思想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
3、西方社会分层理论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应该清楚地看到,西方社会分层理论有很大的局限性。西方许多社会学学者提出的各种分层指标,不能反映也未能真正反映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实质。它们最多只是对社会不平等现象的一种描述,不能用来分析阶级社会的基本社会结构,更不能用它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西方社会学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马克斯·韦伯所提出的一套社会分层理论及体系,完全是直接针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它直言不讳地表示就是要用分层方法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用社会分层来抹杀阶级的界限,并且曲解、诋毁和攻击马克思主义。他的思想也一直为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反对马克思主义时广泛利用。但是马克思主义既不害怕批评,也不拒绝“拿来”。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在论战中发展的,在吸收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对待社会分层理论同对待资产阶级其它学科一样:“注意它,利用它,批判地对待它,不放弃自己完整的和确定的世界观。”②
总之,我们并不能因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没有对当代中国农民的阶层分析而断言马克思主义“过时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任何一门学科都具有理论指导意义,这是不言而喻的。所谓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指不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和基本观点,当然也不能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所谓发展马克思主义,正是指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认识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给予符合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新解释,以充实、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
二、当代中国农民各阶层划分的标准
当代中国农民和以前的农民既存在许多相同点,也有其不同的个性。根据研究的目的和要求,无论从共性或个性中抽取一个因子作为标准,都可以将其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或层次。例如:按文化水平,可以把农民分为文盲和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和高中以上几类。在农民队伍中存在一支庞大的文盲半文盲阶层。按劳动力状况,可以把农民分为标准劳动力、半劳动力、辅助劳动力和失去劳动能力的四类,这是我国在“工分制”时采用的一种划分标准。按兼业可以把农民分为纯农业、第一类兼业、第二类兼业和非农业兼业等四类。按所有制性质,可以把农民分为全民、集体、个体和外资外企四类,等等。从不同的角度把握农民各阶层的特点,这种分类是必要的。如果把上述的几个单因素标准结合起来,就可以把农民分为许多更细小的群体和层次。但如果理论的行程到此为止,那么这种分类研究还只是处于一种浅层次的抽象,还不能完全把握和揭示某些农民虽然从个别特征看来所具有的表面差别而在更深层次上所表现出的共同的本质上的一致性。因此综合因素分层更为重要。围绕这一点,理论界又提出了许多新的划分标准和具体的分层。笔者认为,对当代中国农民的分层研究,必须要跳出传统思维的框框,但又不能完全与历史割断,而必须是在经典作家阶级阶层划分标准上的继承和创新。这是因为:第一,对当代农民的分层研究不再是为了重新划分农民各阶层的社会成份,不再是为了重新分配土地,而是要明确各阶层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列宁对俄国农民的分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着不同的目的,使用了不同的划分标准,对我们颇有启发。他在研究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后的农民分化,主张“必须把经营的规模和类型作为分类的根据”③;而在分析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政治和经济时,又把农民分为“劳动者农民和私有者农民,即种地的农民和经商的农民、劳动的农民和投机的农民”④。分类的目的不同,标准也应不同。第二,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出现的许多新的职业位置不可能再重新构成一个新的阶级,因为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如果在社会主义进程中还会产生新的阶级(不管是新的剥削阶级还是新的劳动阶级)都与社会主义运动的目的相悖。农民的分化不再具有两极分化性质。分化的性质不同,分化的特点不同,农民队伍具体构成不同,所以分层标准也应不同。我主张以农民在商品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兼考虑职业特点和财产占有关系作为新的分层标准,这主要是由当代中国农民的特点、分化的原因和研究者的主要目的所决定的。当代中国农民作为独立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决定了必须从商品经济的新角度去重新认识农民。商品经济愈发展,社会分工愈细,农民分化的速度也就愈快,形成的新的社会阶层也就愈多。每个阶层在商品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明显不同的,他们各有其功能和位置。
需要说明的有两点:一是这种新的标准,新的分层法并不排斥别的标准和方法。借助于其它一些分层法可能会更清楚地阐明问题。二是农民在商品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不等于剥削和被剥削、奴役和被奴役的关系,前者只是指经济地位、作用和功能不同,而不包含有人身依附和强制关系。虽然因经济地位的不同可能会导致后者关系的形成,但二者毕竟不能直接划上等号。第三,从社会角色理论可知,许多农民在商品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多重化的,为了确定和分辨主次,轻重,还必须尽可能地进行定量分析,把定性和定量结合起来。一种有效的定量分析法是模糊社会分层法。模糊社会分层借助模糊数学解决了阶层的隶属度问题,也即阶层的模糊性问题。但这种方法本身不能把社会分成哪些阶层,而是首先要研究者确定社会分为哪些阶层,然后才能借此方法确定被调查者属于哪个阶层。而且模糊集合中隶属函数值的具体确定具有很大的主观成份。因此,模糊评判方法只能作为社会分层的一种辅助手段,而不能成为主要分析手段。
三、当代中国农民的分化率指标及其粗略估计
当代中国农民分化的规模、速度和流向情况怎样,很难用一个具体指标来衡量;而且还存在统计口径和交叉阶层、边缘阶层和模糊阶层的归类问题。为了能从宏观上把握当代中国农民的分化速率,只能用一个指标系从不同的侧面来描述。
首先我们假定存在农村(乡村)总人口(含镇)>农村(乡村)总人口(不含镇)>广义农业人口>陕义农业人口>农村劳动力>乡村劳动力>广义农业劳动力>第一产业劳动力>狭义农业劳动力>种养业劳动力。
第一,城镇化水平和速度。1980年市镇总人口1914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19.4%;1989分别为23368万人和21.00%;10年仅提高1.6%个百分点,城镇化的速度实际上是很慢的。城镇化的水平和速度并不能准确地反映农民向城市的转移规模和速度,因为构成城镇总人口增长的主体是城市自身的积累人口。只有其中的机械增长部分才能大体上反映农民的转移情况。城市化增长速度等于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减去农村人口增长速度。由此可以派生出:(1)城镇每年新增人口中机械增长率;(2)城镇每年新就业中吸纳农业劳动力规模和速度,这个指标比较重要,1980~1989年城镇新就业人口中来自农村的劳动力为1240万人,占总数7604.7万人的16.31%。而专家预测1990年前我国农业人口转移规模最低方案为6857万人,年平均转移857万人,超过实际数字。这说明人们对城市的吸纳能力和速度期望值过大;低估了城市自身存在的失业人口对农民进城的影响,等。
第二,农民流动、迁移和离土规模和速度。迁移和流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区别的关键在于流动者是属常住人口变动还是属现住人口变动,若是前者则为迁移;若属后者则为流动。从广义上讲,迁移是指人口永久性或半永久性的住所变更,而流动要比迁移广得多,其量也大得多。从类型上看,迁移有阶梯式迁移、逐级迁移、链式迁移、强迫迁移、自愿迁移、直接和间接迁移、计划性迁移等,迁移率等于一定迁移时间间隔内某一人口的迁移者数量与此间的该人口平均人口数之比。流动类型有地域间流动和社会流动两大类。其中地域流动有:钟摆流动、周期性流动、季节性流动、“盲流”等;社会流动又分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迁移和流动往往是交叉的、并发的。农民由农村直接迁入城镇的年有效迁移量等于城市人口的年机械增长量;它仅构成农民年流动量的一部分。农民在农村区域内部的流动,不能改变农民的总量,而只会改变农村的人口密度和劳力配置。
与流动迁移相近的另一个概念是农民的离土率。广义的离土是指一定区域的农民离开他所定居的土地,进入城镇和到它乡从事农业和非农业活动,即流动总规模;狭义的离土仅指前半部分,相当于城市机械人口量,即迁移规模量。无论是迁移、流动还是离土,速度越大,流量越大,农民的分化和非农化速度也就越快;反之则反。
第三,农业或第一产业社会劳动者变动规模和速度。1980年农、林、牧、渔、水利业即第一产业社会劳动者人数为29181万人,占社会总劳动力的68.89%;1989年分别为33284万人和60.16%,10年下降了8.73个百分点,相应地二、三产业的社会劳动者人数上升了8.73个百分点。农业劳动者占工农业劳动者总数的百分比由1980年的81.3%下降到1989年的77.5%;下降了3.8个百分点。乡村总劳动力1980年为31836万人,占全国总劳动力的75.15%;到1989年分别为40939万人和73.99%;仅下降了1.16个百分点。在乡村劳动者内部,1980年第一产业劳动者为28334万人,占乡村总劳动力的89.0%;1989年分别为32441万人和79.24%,下降了9.76个年百分点;工业、建筑业(即第二产业)劳动者人数由1980年的2225万人,占总数的7.0%,上升到1989年的4758万人和11.62%;交通运输、商业饮食、文化教育等第三产业从业人数由1980年的1277万人,占总人数4.0%,上升到1989年的3740万人和9.14%。可见各种不同统计口径反映的农业就业份额下降速度是不一样的。在乡村劳动力就业结构中,最有特色的是乡镇企业劳动者这个阶层的崛起和发展。1980年全国乡镇企业的职工总人数为2999.67万,其中农业为456.07万人,占总数的15.2%;工业1942.30万人,占64.8%,建筑业334.67万人,占11.1%,交通运输业113.56万人,占3.8%;商业饮食业153.07万人,占5.1%。1989年,乡镇企业职工总数达到9366.78万人,其中农业239.30万人,占2.6%;工业5624.10万人,占60.0%,建筑业1403.73万人,占15.0%;交通运输业699.37万人,占7.5%,商业饮食业1400.28万人,占14.9%。可见乡镇企业职工主体是乡镇工业工人;从事农业的职工下降了12.6%,所占比例极少。乡镇企业的发展成为农民分化的主渠道,一个最有力的支点。
第四,其它相关指标。农民的分化受农业劳动生产率、粮食商品率、收入水平和文化水平等因素的制约非常明显。根据中国农村产业结构研究报告,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增长1%,农业劳动力转移增长率为2%。这意味着每增加一个单位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只能转移出去两个劳动力。1978年年均每一农业劳动力提供的农业净产值为343元,1980年为457元,1988年为1194元,以1978年为基数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2.48倍,相应地农业劳动力转移增长率为4.96倍。由于统计口径问题,我们实际上很难以1:2的比例推算出1988年我国累计已转移出去多少农业劳动力。
粮食商品率在农业国工业化过程中对农民的分化转移制约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1978年平均每一个农业劳动者提供的粮食产量为1059公斤,1980年为1106公斤,1988年为1232公斤。粮食净商品率一直在15~20%之间波动。按人口平均占有的粮食1978年为318.5公斤,1980年为326.5公斤,1988年为362公斤,最高水平的1984年为395.5公斤,人均占粮400公斤一直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在国民经济不能高度工业化下,农业不能为非农业人口提供足够的粮食,而工业又不能通过贸易或其它渠道为非农业人口提供足够的粮食时,粮食商品率的高低既是非农业人口增长的因素,又是它的限制因素,如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作用一样。
另据一些抽样和典型调查,收入水平和文化水平的高低与农民的分化流动呈强正相关。收入水平越高,农民的非农化速度越快,文化水平也起着同样的功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农民的分化流动伴随着农村的文化高流失率,它既是农村生产要素的一种损失,同时也表明只有具备能适应城市最基本生活和工作需要的劳动力才能被城市所接纳,并稳定地沉淀下来。从另一个角度看,它是农民支援现代城市发展的一种人力资本贡献和农业发展的一种自我牺牲。
此外,农民的分化流动迁移还受到其它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制度因素如户籍制度;心理因素如安土重迁的小农思想意识等等。这些因素更难定量化研究。总之,建立一套科学的实际可行的农民分化指标体系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全面地准确地记录下当代中国农民的分化实况,不仅是经济实证研究的基本内容,而且是界定农业国工业化进程阶段的必不可少的最有力的依据之一。
注释:
①④《列宁选集》第4卷,第11页,第90页。
②③《列宁全集》第3卷,第581页,第85页。
标签:农民论文; 社会分层论文; 中国的人口论文; 农村人口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