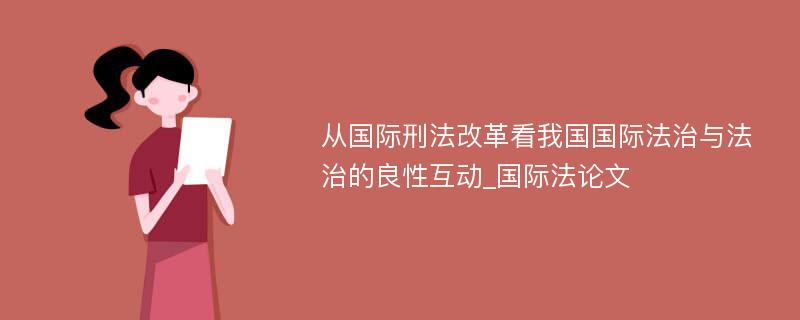
论国际法治与中国法治的良性互动——从国际刑法变革的角度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治论文,国际论文,互动论文,刑法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刑法的变革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国际社会的巨大变化对以控制国际犯罪为主要任务的国际刑法不断提出新的挑战。一方面,随着冷战的结束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经济领域的犯罪日益突出。另一方面,随着高科技的发展以及网络技术在国际社会的广泛使用,危害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国际犯罪更加复杂。(注:例如网络恐怖主义(Cyber Terrorism)就是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新型恐怖主义犯罪。据有关资料,美国安全和情报研究所的Barry C.Collin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最早使用网络恐怖主义一词。参见周文博士著:《网络犯罪的法律控制——国际法与比较法研究》,载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5月,第18-29页。)
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在1993年提交给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一份报告中指出,跨国有组织犯罪(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是国际社会在21世纪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委员会强调,不应将有组织犯罪这一现象视为一种模糊的罪恶或暂时的威胁,而应将其视为有形的非法企业(atangible illicit enterprise)或有组织的犯罪企业(the organized criminal enterprise)。为了适应获取最大利润的需要,许多跨国犯罪集团和国际犯罪组织,在组织上仿照公司和跨国公司进行调整。犯罪组织不仅内部有严密的分工,有采购、生产、运输、销售和财务等各个部门,而且进行国际分工,在相关的国家建立分支部门。与一般的跨国公司不同在于,犯罪组织不仅有“执行部门”,而且使用种种非法手段维持犯罪组织的运转。在使用传统犯罪手段的同时,有组织犯罪更多地依赖于对合法手段的非法操纵,利用合法的市场、合法的企业进行非法活动。有关的调查资料表明,有组织犯罪已形成了一个地下经济体制,这个地下经济体制的总产值和纯利润已对有关国家的合法经济造成威胁。在有的国家,有组织犯罪所操纵的企业和经济部门已达到惊人的程度。有组织犯罪所拥有的企业在商业竞争中往往挤垮合法的竞争者。这不仅因为其他的企业要考虑成本、利润、税收和银行贷款等因素,还因为有组织犯罪在需要时采取各种非法手段包括暴力手段对付竞争者,迫使合法的竞争者破产,从而使犯罪企业获得更多的利润。
跨国有组织犯罪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有组织犯罪与跨国洗钱相互交织,“跨国洗钱”已成为维系跨国犯罪和有组织犯罪的“生命线”。联合国秘书长在1993年的一份题为“有组织的犯罪对整个社会的影响”的报告中,披露了国际信贷和商业银行洗钱200亿美元这一惊人的事实。(注:The Impact of Organised Criminal Activities Upon Society at Large:Report of the Secretary General.UN DOC.E/CN 15 /1993/3;11 January 1993,p12.)国际信贷和商业银行(BCCl)是Agha Hasan Abedi于1972年在卢森堡注册的一家国际性银行。到1991年,它在73个国家设立了430个分支机构。随着BCCI多起犯罪事件露出水面,最引人注目的不是银行已经被迫停业,而是银行长期的犯罪经营所暴露出来的各国监管体制和国际控制犯罪问题。有关资料表明,BCCI不仅仅建立在为一切客户,包括为毒品贩运者、独裁者、恐怖活动者、欺诈者保密和欺诈的基础上,同时它也将秘密和欺诈作为银行服务的一个必要部分。自称为世界发展之目的而创设的一家银行,到它倒闭之时止,在银行业中已经作为“国际欺诈和犯罪银行”而名声在外了。
BCCI通过一系列手段来从事或帮助各种犯罪,包括利用空壳公司、离岸金融中心和银行保密天堂,以及分散公司结构等。虽然BCCI的总部在卢森堡,但其经营的全球范围使单一国家的管辖或规则难以有效控制。BCCI利用鳄鱼岛和荷兰安替列斯群岛创设了许多前台公司,这些公司为BCCI的储户和行为提供了一堵秘密的保护墙。该银行利用有关国家监督系统相互阻隔的问题,将其有关信息分别报告给不同国家的审计员,其中任何一国都无法看到银行行为的全部,从而也无法获得该银行参与协助洗钱、欺诈和腐败的真实信息。正如有关报告所揭示的,或许关于BCCI最令人不安的是,它“并非一个单独的现象,而是一个与国际金融社会同时存在且不断发生的问题。由于国际金融交易超乎想象的规模,欺诈的机会同样巨大,回报丰厚,而反欺诈的保护机制还远远不够”。(注:The Impact of Organised Criminal Activities Upon Society at Large:Report of the Secretary General.UN DOC.E/CN 15 /1993/3;11 January 1993,p12.)
国际社会面临的另一个棘手问题是,腐败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已发展为影响所有社会和经济的跨国现象,并与有组织犯罪、洗钱犯罪和其他经济犯罪紧密联系。(注:2003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序言明确指出,本公约缔约国,关注腐败对社会稳定与安全所造成的问题和构成的严重威胁性,它破坏民主体制和价值观、道德观和正义并危害着可持续发展和法治,确信腐败已经不再是局部问题,而是影响所有社会和经济的跨国现象。)联合国在1995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政府官员受贿是一个日趋严重的问题。报告列举的一份统计资料表明,军火商为出售武器和电信设备向政府部长和有关官员行贿,每年使有关国家损失45亿美元。在1988年至1992年世界十大军火商获得的合同中,贿赂占总额的15%。在腐败官员的庇护下,利用“银行保密和公司保密”从事非法和犯罪活动的公司犯罪也愈演愈烈。(注:Tax Havens:Releasing the Hidden Billions for Poverty Exadication,June 2000.http://www.oxfam.org.uk.)
许多资料说明,经济全球化如同一柄双刃剑,它在加速全球贸易自由流动、增加人类财富的同时,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有组织的国际犯罪、国际经济犯罪、网络犯罪、恐怖主义犯罪和洗钱犯罪等各种传统的犯罪和现代的犯罪交织在一起,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发展的严重威胁。(注: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就曾明确指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使跨国犯罪构成对国家安全、经济发展、民主和主权的新威胁。http://www.un.org/chinese/events/palermoconvention/main.html.)
为适应控制国际犯罪的新要求,国际社会订立了一系列创新性的国际刑法公约,以期建立控制国际犯罪的新的规则和制度,完善控制国际犯罪的国际法律合作机制。这些公约包括第一个有关控制“洗钱”的国际公约——1988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第一个以“补充性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国际公约——1998年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一个以刑法保护整体环境的国际公约——1998年欧洲理事会保护环境的国际公约;第一个控制恐怖主义融资的国际公约—1999年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第—个控制跨国犯罪的全球性、全面性的国际公约——2000年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第—个控制网络犯罪的国际公约——2001年欧洲理事会关于网络犯罪的国际公约;第一个反腐败的全球性的国际公约——2003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上述这些国际刑法公约的缔结、生效和实施有力推动了国际刑法在多方面的变革和发展。(注:上述国际刑法公约大多是在联合国主导下形成的全球性的国际刑法公约,1998年欧洲理事会保护环境的国际公约和2001年欧洲理事会关于网络犯罪的国际公约虽是欧洲理事会主导形成的,但在制定中吸收非成员国参与,并对非成员国开放。欧洲理事会自1990年《关于洗钱、搜查、扣押及没收犯罪收益的公约》开始,公约的标题中已不使用“欧洲”这个词语,以便欧洲理事会以外的国家也能参加。)
这一阶段,国际刑法的突破和创新突出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建立通过控制洗钱来控制犯罪的国际法律合作新机制。
1988年12月19日在维也纳通过的《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以下简称“联合国禁毒公约”)是国际社会第一个控制洗钱的国际公约,该公约所确立的控制洗钱的法律措施与机制对于控制毒品犯罪、跨国有组织犯罪、国际经济犯罪均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注:参见邵沙平等著:《控制洗钱及相关犯罪法律问题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国际社会从20世纪初,就开始了预防、禁止和惩治国际毒品犯罪的国际合作。但国际实践证明,打击犯罪行为的传统国际法律合作措施不足以对付在经济全球化情势下的国际贩毒活动。在追逐非法经济利益的国际犯罪活动中,犯罪收益的转移已成为一个“关键点”。贩毒者从贩毒活动中获得的犯罪收益,通过洗钱得到伪装,并成为对抗合法社会的重要“武器”。有组织犯罪的上层人物,虽然控制着从国际毒品贩运中获得的巨额利润,但很少进行具体的生产、制造以及贩运毒品的活动。而以往国际公约有关犯罪的规定都没有触及到隐瞒或掩饰犯罪收益的洗钱活动,因此依原有的规定难以惩治有组织犯罪的上层人物,也难以遏制愈演愈烈的国际毒品贩运活动。为切断维持国际毒品贩运活动等国际犯罪活动的“生命线”,1988年联合国禁毒公约对“洗钱”通过法律措施予以控制。联合国禁毒公约明确规定了毒品洗钱的犯罪行为,要求缔约国将“洗钱行为”规定为其国内法上的犯罪,明确规定将“没收犯罪收益”作为一种制裁措施。为有效识别、扣押和没收犯罪收益,联合国禁毒公约扩大了传统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范围,使调查取证扩大到银行、公司等金融单位。公约明确缔约国不得以保守银行秘密为由拒绝提供公约所规定的相互法律协助,从而促使各国对传统的国内银行保密法进行改革以适应控制洗钱犯罪的要求。(注:参见1988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第7条的规定。)
自1988年联合国禁毒公约开始,通过控制洗钱来控制犯罪的新思路和法律措施反映在一系列国际公约和国内法中。1999年禁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公约、2000年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2003年联合国反腐败禁止的公约,进一步确立和发展了联合国禁毒公约所开创的新机制。(注:陈道丽博士认为1999年禁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公约已将国际法上洗钱犯罪的范围从犯罪收益扩大到恐怖主义融资,并在国内率先提出新的洗钱定义:隐瞒犯罪收益的来源和性质,或者隐瞒恐怖主义融资的流向,并使之表面合法的一种活动和过程。参见陈道丽著:《金融机构反洗钱法律制度一国际法与比较法研究》,载武汉大学法学博士论文2004年5月。)
第二,建立打击跨国犯罪的国际法律合作的新机制。
国际社会打击跨国犯罪的国际合作由来已久,从国家间的双边合作逐渐扩大到国际多边合作。20世纪初成立的国际刑警组织(the International Crimihal Police Organization),已成为国际社会与国际犯罪和跨国犯罪作斗争的有效工具。联合国成立后,在联合国,的推动下国际社会形成了一系列控制国际犯罪的国际公约。尽管国际社会打击跨国犯罪的国际合作不断扩展,但这种国际合作或者局限于某一特定领域,或者主要是通过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方式,局限于程序法方面的国际合作。为了适应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需要,1990年在哈瓦那召开的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提出了联合国控制有组织犯罪国际合作的战略原则。大会通过了《预防和控制有组织犯罪准则》,要求各国在刑事立法、侦查、执法等方面进行国际合作,不断探索可预防或尽量减小有组织犯罪。1992年联合国成立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以促进和加强全球一致行动控制跨国有组织犯罪。
2000年11月15日,联合国大会第55届会议通过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该公约于2000年12月12日—15日在意大利巴勒莫召开的高级别签署会议上开放签署,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和广泛接受。(注:中国、美国、俄罗斯以及欧盟等124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在会议期间签署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该公约于2003年9月29日生效,我国于2003年9月23日向联合国交存了批准书。)2000年公约以一个单一公约的形式使控制跨国犯罪的法律规则系统化,力图改变仅针对某一类犯罪所拟定规则带来的局限性,并使国际社会在控制跨国有组织犯罪方面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公约巩固和扩大了1988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1990年《欧洲理事会关于洗钱、搜查、扣押及没收犯罪收益公约》等国际公约所拟定的有关控制犯罪的新的法律措施和国际合作机制,是控制跨国犯罪的国际合作的新的历史里程碑。
长期以来,国际社会控制跨国犯罪的国际合作主要是在程序方面进行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与合作,有关控制跨国犯罪的国际法原则、规则和制度主要关于管辖领域的协调和程序领域的合作。国际刑法领域的国际公约一般只对国际犯罪的实体法问题作出规定,有关控制跨国犯罪的实体法问题,一般由国内法予以规定。公约所构建的控制跨国犯罪的国际法律合作机制开辟了国际法律合作的新领域,使控制跨国犯罪的国际法律合作扩展到实体法领域。在控制犯罪方面,传统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刑法措施,有关控制跨国犯罪的国际法原则、规则和制度也主要与刑法措施有关。1988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提出了以刑法措施为主,辅之以其他措施控制犯罪的新思路。1990年《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40项建议书》提出了有效实施1988年联合国禁毒公约的新措施——扩大金融系统在控制洗钱中的作用。(注: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the 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on Money Laundering,简称FATF)是1989年建立的专门致力于控制洗钱的国际组织。FATF在1990年提出了控制洗钱的40项建议,后不断予以补充和修改。2003年6月20日,为了适应国际社会打击恐怖主义融资、反腐败和控制法人犯罪的需要,FATF对1996年40项建议进行了重大修改。根据FATF的评估,“1996年反洗钱40项建议书”已经被130多个国家接受,成为反洗钱的国际标准。See FATF,The Forty Recommendations,20 June,2003.)欧洲共同体《1991年防止使用金融系统洗钱的指令》规定了控制洗钱的金融和行政法律措施。2000年公约吸收和发展了上述创新性的规定,采取刑事、金融、行政等多种措施控制跨国有组织犯罪,将控制跨国犯罪的国际合作从单一的国际刑事合作发展为刑事、行政、金融多重合作机制,形成控制跨国犯罪的国际合作的综合法律机制。
第三,建立控制法人犯罪的国际法律合作的新机制。
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法人所进行的国际犯罪的危害性逐渐为国际社会所认识。(注:例如OECD从2000年开始起草一个有关法人犯罪的报告。该报告指出,几乎每一种经济犯罪都与滥用公司实体有关。)法人所进行的国际走私、国际欺诈、跨国洗钱、跨国贿赂等国际性、跨国性经济犯罪与跨国有组织犯罪、网络犯罪、国际恐怖主义犯罪交织,严重破坏了国际社会正常进行国际经济交往的基础——国际和平与安全,严重破坏了国际经济交往应遵行的基本准则和法律秩序,严重危害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对国家主权和全球经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传统国际法有关犯罪主体主要是自然人的理论,显然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情势下控制国际犯罪的要求。
为适应控制法人犯罪的需要,近年来的一些国际刑法公约不仅明确规定法人的责任,而且在有关规定上一脉相承。(注:这些国际刑法公约包括2003年《联合国反贪污腐败国际公约》、2000年《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1999年《禁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公约》、1998年《欧洲理事会保护环境的刑法公约》。)例如1999年《禁止资助恐怖主义公约》公约第5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根据本国法律原则采取必要措施,以致当一个负责管理和控制设在其领土内或根据其法律设立的法律实体的人在以该身份犯下了公约第2条所述罪行时,得以追究该法律实体的责任,这些责任可以是刑事、民事或行政责任。承担这些责任不影响实施罪行的个人的责任。1999年公约关于法律实体责任的规定,是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新措施。(注:参见邵沙平著:《控制恐怖主义犯罪与国际法律合作—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向》,载《求索》2002年第1期,第42-46页)
2000年《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第10条规定,各缔约国均应采取符合其法律原则的必要措施,确立法人参与和实施公约所规定的犯罪时应承担的责任。在不违反缔约国法律原则的情况下,法人责任可包括刑事、民事或行政责任。法人责任不应影响实施犯罪的自然人的刑事责任。公约强调指出,各缔约国均应特别确保使参与和实施犯罪的法人受到有效、适度和劝阻性的刑事或非刑事制裁,包括金钱制裁。2003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26条也明确规定了法人责任。(注:根据该公约规定,各缔约国均应当采取符合其法律原则的必要措施,确定法人参与根据本公约确立的犯罪应当承担的责任。在不违反缔约国法律原则的情况下,法人责任可以包括刑事责任、民事责任或者行政责任。法人责任不应当影响实施这种犯罪的自然人的刑事责任。各缔约国均应当特别确保使依照本条应当承担责任的法人受到有效、适度而且具有警戒性的刑事或者非刑事制裁,包括金钱制裁。从该公约有关法人责任的规定,可以看出与2000年公约规定完全相同。)
第四,建立通过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国际刑法的国际法律合作新机制。
在国际刑法的实施方面,缺乏国际刑事法庭一直是个重大的缺憾。有关资料表明,没有一个国际刑事法院作为一种实施机制来处理个人的责任问题,灭绝种族行为和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往往不受惩罚。在纽伦堡审判后的50年,发生过许多犯了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而没有被追究个人责任的事例。前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何塞·阿亚拉—拉索对这种现象的说法是,杀害了10万人的人,要面对审判的机会还不如杀害了一个人的人。国际社会不断发出呼声要求改变这种情况,建立国际刑事法院。
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指出,将近半个世纪以来……几乎从联合国成立以来,联大就认识到有必要设立一个国际刑事法院,来起诉和惩罚应该对种族灭绝罪行负责的人。许多人以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种种耸人听闻的惨事……集中营、残酷暴行、集体灭绝、大屠杀等,永远不会再发生了。但是它们还是一再发生了:在柬埔寨,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在卢旺达。我们这个时代……甚至就在九十年代里,我们看到,犯罪者的邪恶是没有极限的。 “种族灭绝”已经进入了我们时代的词汇,针对这个残酷的现实,我们必须付出历史性的回应。(注:参见http://www.un.org.)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在惩治国际犯罪方面呈现了新的局面。1993年由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第827号决议设立“前南国际法庭”审理自1991年以来在前南斯拉夫地区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个人。1994年由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995号决议设立“卢旺达法庭”,审理在卢旺达境内的武装冲突中犯有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个人。
1998年7月17日,联合国设立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全权代表外交会议在罗马通过了《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规约已于2002年7月1日生效,一个常设的国际刑事法院已经建立。国际刑事法院成立后,不仅将改变目前审判国际犯罪完全依靠各国国内法院的单一审判格局,还将对21世纪的国际法律秩序和国际刑事司法制度产生重要影响。
二、国际刑法的变革对全球法治的影响
如前所述,国际刑法的一系列制度性的变革和发展都是通过缔结国际刑法公约来实现的。这些国际刑法公约的缔结、生效和实施不仅对国际刑法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也对21世纪的全球法治产生深远影响。
本文所谈的全球法治,包括国际法治和各国法治。一般来说,国际法治,是指约束国际法主体的法治。这种法治是建立在国际法基本原则基础上的法治,是国际法意义上的法治。各国法治,是约束各国国内法主体的法治。这种法治是建立在各国宪法原则基础上的法治,例如中国法治,是建立在中国宪法基础上的法治,美国法治,是建立在美国宪法原则基础上的法治。这种法治是国内法意义上的法治。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国际刑法的变革使得国际法治和各国法治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国际刑法不同于一般国际法的突出特点就是法律关系的主体包括个人。国际刑法的这种特点是由国际刑法的目的和任务决定的。国际刑法的主要任务是控制国际犯罪,是要维护国际社会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而要控制国际犯罪,国际社会就需要形成共同的认定国际犯罪的“标准”,形成专门的管辖和处罚国际犯罪的法律机制。传统国际法是规范国家行为的,而国家不被认为可以从事犯罪行为;传统国际法是规范国家行为的,对于个人的犯罪行为属于国内法处理的问题。国际刑法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和完成自己的任务,就必须突破国际法的传统模式发展。
国际刑法的变革从多方面对传统国际法进行突破:
第一,观念和理论上的突破。国际社会要适应控制国际犯罪的需要,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在发展国际刑法方面就必须突破传统国际法的思维定式:例如,国际法的“软法”性质;个人不能作为国际法主体;国家破坏国际法的行为不构成犯罪行为等。
第二,规范上的突破。这种规范的突破,表现在规范的内容、规范的对象以及规范的性质等多方面。例如,许多国际刑法公约都直接规范个人的行为,许多国际刑法公约明确规定个人构成国际犯罪应承担的责任、在刑事诉讼中应享有的权利以及各种保障措施。这里所说的个人,是从事国际犯罪行为的所有人,包括国家元首和政府官员。而依据传统国际法,国家元首、政府高级官员以国家名义从事的行为不承担国际法上的个人责任。因为传统国际法只约束国家,不约束个人。国际纽伦堡法庭宪章和法庭判决明确宣示:凡犯有国际法认定之罪行者应负刑事责任,并受到惩处;不违反所在国的国内法不能作为免除国际法责任的理由;被告的地位不能作为免除国际法责任的理由;政府或上级的命令不能作为免除国际法责任的理由;被控有违反国际法罪行的人有权得到公平审判。上述原则也反映在有关伊拉克问题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中。2003年5月22日安全理事会第4761次会议通过第1483(2003)号决议明确指出,必须对伊拉克前政权犯下的罪行和暴行追究责任。该决议呼吁各会员国对于伊拉克前政权据称应对罪行和暴行负责的成员拒绝给予安全庇护,并支持将其绳之以法的行动。
第三,实施方式上的突破。对于传统国际法而言,它通常只要求国家遵守和实施国际法,一般并不具体规定国家如何遵守和实施国际法。传统国际法有关国家行为的要求,主要是依靠国家的自觉遵守和实施。而国际刑法由于其规范的“强制性”特点,不仅要求国家自觉遵守,还需要建立有效的实施机制确保“强制性”规范的遵守和实施。因此,国际社会或是建立国际司法机构实施国际刑法规范,或是要求国家承担义务,通过国内法律机制实施国际刑法规范。
国际刑法这种既约束国家也约束个人的特点使之对国际法治与各国法治不断发生影响。国际法治是国际社会所追求的伟大目标。国际法治的第一要素首先是规范要素,即国际社会必须具有国际社会成员必须尊重和遵守的国际法规范。这也就是1945年《联合国宪章》所说的,我联合国人民,尊重由国际条约和国际法其他源渊所规定的国际法义务。(注:现代国际法治的发展与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的活动紧密相连。1945年《联合国宪章》庄严声明,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创造适当环境,俾克维持正义,尊重由条约与国际法其他源渊而起之义务,久而弗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及原则包含了国际法治的精神和措施。1970年10月24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明确指出,联合国宪章在促进“国际法治”上至为重要)没有普遍性的必须遵守的规范,就没有维持“国际正义”的标准和准则,就没有实现国际法治这个目标的手段。由于国际社会的发展不平衡,国际社会不可能在所有领域都形成统一性的规范。但在国际刑法的关键领域,则要求达成符合法治要求的统一性规范,形成在规定“犯罪”和“保护人权”等方面的最低国际标准。不如此,就不可能有效控制危害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国际犯罪。
国际刑法的变革对国际法治的影响,还突出地表现在全球性国际刑法公约适用对象和范围的普遍性。这些全球性公约的生效和实施使得国际法治的范围成为全球性的国际法治。国际刑法的变革和发展对国际法治最重要的影响,就在于国际刑法规范是通过“强行法规范”来维护法治,来预防、禁止和惩治破坏法治的犯罪行为。国际刑法规范所具有的“强行法”性质,使主要以“任意法”规范为主从而具有“软法”之称的国际法越来越多地具有“硬法”的因素。如果缺乏适当的强行法规范维护国际法治,如果国际法规范都可以任意违反而不受惩罚,国际法治就会成为空谈。(注:根据1945年《联合国宪章》我联合国人民(WE THE PEOPLES OF THE UNITED NATIONS)的用语,国际法治并不仅指约束国家的法治。1970年10月24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即国际法原则宣言》由于是规范国家间的关系,因此,在谈“国际法治”时是专门指国家(the rule of law among nations).联合国大会1999年11月17日通过的决议关于“国际法治”的用语是the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我们国内学者在未加限定使用法治(the rule of law)这一用语时,一般是指国内法意义上的法治,但2003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也未加任何限定使用法治(the rule of law)一词,从公约的宗旨和规定来看,法治一词不能仅仅理解为国内法意义上的法治。现在国外有些学者还使用全球法治(the global rule of law)一词。)
国际法治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国际法治链条中的一个关键环节是对规范的有效实施。规范制定的再完备,如果不能有效实施,国际法治就是虚无飘渺的海市蜃楼。曾任纽伦堡检察官的本杰明·费伦茨先生有一句名言,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没有法律就没有正义,没有一个法院来裁定在特定情况下,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合法,就没有有意义的法律。
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是国际刑法直接实施机制的突破性发展,对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具有重要作用。正如联合国主管法律事务副秘书长汉斯·科雷尔所说,历史上把子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的人大多数没有受到惩罚。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曾经有军事法庭,近年来又有处理前南斯拉夫问题和卢旺达问题的两个特设国际刑事法庭,二十世纪的情况也还是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合理地推断,犯下这种暴行的人大多数是相信他们的罪行是不会受到惩罚的。致力于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的人的主要自标之一,就是发挥有效的预防作用。一旦人们清楚看到,国际社会将不再容忍这种残暴的行为,而是会追究责任,并且给予适当的惩罚,不论他们是国家元首、指挥官,还是战场上最低级的士兵或者民兵分子,那些煽动种族灭绝行动的、发动族裔清洗运动、在武装冲突中杀害、强奸和残暴伤害平民、或者用儿童进行令人发指的医学实验的人,将不再能够找到愿意助纣为虐的人。
联合国成立后,一直为推进国际社会的法治而努力工作。其中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推进和传播国际法治文化。国际法治文化是国际法治不可缺少的核心要素。联合国大会1999年11月17日通过的决议明确指出,联合国对加强“国际法治”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工作包括促进争端的和平解决、鼓励国际法的编纂和发展、鼓励国际法的教学和传播,建立国际法的实施机制。
国际刑法公约的缔结、生效和实施也是推进和传播国际法治文化的重要途径。国际法治需要有国际法治文化指导,国际法治文化是国际法治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先进的国际法治文化指导国际良法的形成,又推进国际良治的实现,而形成和确立的国际良法和国际良治又不断丰富和传播先进国际法治文化。国际刑法控制国际犯罪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但国际刑法要维护的是“基于自由、平等、正义及尊重基本人权”的国际和平,是通过刑法手段维护“国际正义”和促进“国际法治”。(注:1970年10月24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即国际法原则宣言》强调维基于“自由、平等、正义即尊重基本人权”的国际和平以及促进“国际法治”。1998年《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强调国际刑事法院应尊重和执行“国际正义”。)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建立和维护基于自由、平等、正义及尊重基本人权的国际和平,就是一种先进的国际法治文化。这种先进的国际法治文化对于正确运用国际刑法措施至关重要。国际刑法规范的形成和实施离不开国家和个人,形成规范和实施规范的国家和个人是否具有国际法治理念和具有何种国际法治理念,对于国际法治具有重要影响。由于刑法手段的特殊性,为了防止刑法手段的滥用,就必须使其法律规则尽可能明确,只有这样,才符合现代国际社会法治国家所奉行的“法无明文不为罪”、“法无明文不处罚”的刑法原则和人权保护原则。
三、中国的责任——促进国际法治与中国法治的良性互动
在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和全球治理的时代,推进国际法治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推动国际法治和中国法治均是中国的重要任务,中国作为一个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大国,应在推动国际法治方面进一步发挥自己的作用,促进国际法治与中国法治的良性互动。
中国应进一步推动国际法治和中国法治的良性互动,是因为国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需要通过国际法治来保障,中国法治也需要良好的国际法治环境。国际法治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要求,但国际法治不会自动形成和实现,需要国际社会强有力的推动。在当今的国际社会,国家依然是推动国际法治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力量。不论是国际法规范的形成、国际法规范的实施以及国际法治文化的传播,中国都可以也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
首先,从规范的形成来说,我们看到,尽管近年来中国在国际刑法公约的谈判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在国际刑法领域游戏规则的形成中,我们的潜力发挥还不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对一些专业性很强的领域研究不够,从而在谈判中未能充分发挥应有的主导作用。其实,在国际法的相关领域,国内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在进行研究,如何在学术研究和制定国际规范中,避免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脱节,更好发挥各方面的作用,以在国际规范的制定中能更好反映中国的利益,可能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均应充分重视的事情。
其次,从规范的实施来说,我国在实施国际刑法公约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例如,作为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的成员国,中国采取多种措施,包括立法、司法、行政和教育措施,履行公约所规定的义务,预防和控制酷刑行为的发生,对犯有酷刑罪的行为人依法进行惩治,对酷刑行为的受害人进行赔偿。但由于宪法没有明确规定国际条约在国内法的地位和实施,我国在实施国际刑法公约方面存在着明显的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我国利用国际刑法公约规定的措施维护我国的合法利益。例如,2000年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以及2003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都明确规定缔约国应当建立金融机构反洗钱制度。公约所规定的金融机构反洗钱法律制度,包括银行和非银行的金融机构采取措施验证客户身份、保持交易记录和报告可疑交易。但我国还没有足够的法律措施有效实施公约的规定。有效实施公约规定不仅是加强国际法治的需要,也是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国内有关方面需要通盘考虑,在国内法上明确规定实施国际条约的问题,并对实施的情况进行检查,以便改进。对于实施而言,还应考虑培养实施公约的人才。不论在国际层面,还是国内层面,我国都面临培养更多的能适应实施公约要求的专门人才。
第三,中国应进一步重视国际法在中国法治中的作用,将宣传和传播中国法治文化与宣传和传播国际法治文化结合起来。国际法治文化应成为中国法治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一个复杂的国际社会,国际法治的道路从来都不是平坦的。在国际法面临挑战的时代,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应在推进和加强国际法治方面进一步作出贡献。为切实推动国际法治和中国法治的良性互动,不仅需要培养既坚持中国法治和国际法治的理念,又具有专门法律知识和技能的人才,以在国际和国内制定和实施规范的层面,有足够的专门人才有效维护中国的利益。还需要在国内大众中培养宣传国际法治的理念,传播尊重和遵守国际法的意识。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实现国际法治和中国法治的最深厚的基础在全体人民,实现国际法治和中国法治最根本的利益也在全体人民。
标签:国际法论文; 刑法理论论文; 刑事犯罪论文; 网络洗钱论文; 法治国家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国际刑事法院论文; 刑法基本原则论文; 法律论文; 银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