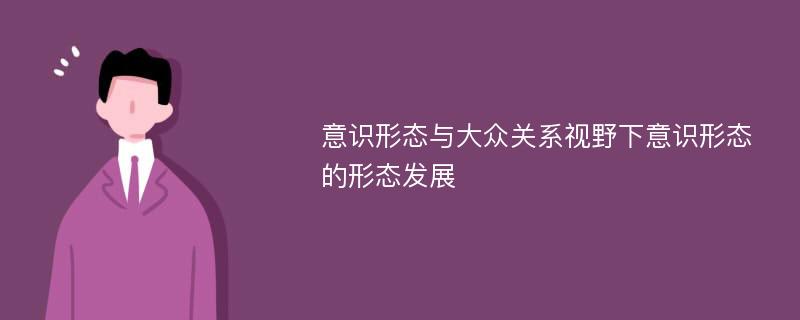
摘 要: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思想蕴含着意识形态与大众关系的线索,揭示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其意识形态的建构,列宁提出了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灌输大众的阶级意识灌输理论,葛兰西深入探讨了有机知识分子教化大众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这些构成了意识形态大众化的教化形态。在后教化形态场景中,技术理性成为一种非传统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即它主要不是表现为统治思想,而是在功能上起到意识形态的作用。大众文化则是通过文化工业的生产、文化消费的实现、文化意义的消解来完成技术理性意识形态对大众的征服。在全球化场景中,无论是文明认同还是文化软实力的博弈,都宣告了所谓意识形态走向“历史的终结”这一结论的谬误。相反,它们意味着意识形态在民族国家层面展开对大众的争夺。大众文化的全球泛滥则折射出现代性意识形态在大众文化层面对世界各国大众的强大影响。同时,发展中国家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与民粹主义运动在欧美发达国家的蓬勃,无不体现出现代性意识形态大众化的内在矛盾。
关键词:意识形态;大众;教化形态;后教化形态;全球化形态
自马克思、恩格斯引发的意识形态研究兴起以来,各种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与实践,始终包含着对意识形态与大众二元关系的关切。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注的是作为理论形态和思想体系的意识形态的建构,尤其是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建构中的作用。同时,也隐含着意识形态作为统治阶级的诉求,不仅要被统治阶级全体所接受,而且也要为被统治阶级大众所接受的思想。列宁在革命实践中,始终将对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争夺和教育当作一个焦点性的问题,把意识形态和大众的关系摆到了一个突出的位置。此后的意识形态问题,无论是在实践中还是学术的研究中,意识形态与大众的关系都成为意识形态考量的重要维度。当今加速发展的全球化趋势,使意识形态与大众关系的纠葛进一步凸显出来。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意识形态与大众的关系被当作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前提,没有得到有效的反思和研究。本文试图从意识形态与大众关系的视角梳理意识形态问题的发展进程和形态演化。
一、意识形态大众化的教化形态
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思想,中外学者都注意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经典阐述:“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8页。这一阐述揭示了意识形态的真正本质和构成。就其本质而言,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就其构成而言,意识形态包含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支配与被支配的两极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只有统治阶级才有能力构建完整的思想精神形态,并凭借其对物质生产资料的支配,获得思想精神形态亦即意识形态的支配权;被统治阶级则不能产生自己完整的思想精神形态,因而同其在物质资料生产中的从属地位一样在思想精神上也是隶属于统治阶级的。在这里,意识形态实际上有两个要素:作为完整思想精神形态的意识形态的生产,和包括被统治阶级在内的大众对意识形态的隶属。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将这种隶属当作自然而然的结果,没有展开分析和说明。他们关注的是这种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是如何构建起来的。
马克思、恩格斯把意识形态建构与知识分子紧密联系起来。对此,他们有过多方面的表述:“分工也以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的形式在统治阶级中间表现出来,因此在这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意识形态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主要的谋生之道,而另一些人对于这些思想和幻想则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并且准备接受这些思想和幻想……”[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9页。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分工的视角道出了意识形态建构的历史前提。这一前提就是统治阶级内部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分工的形成,从事精神劳动的知识分子(思想家)的产生。正是这样的统治阶级内部的专业思想家的幻想和编造造就了意识形态。在这些人之外的其他人并不积极,甚至可以说并没有能力参与这种意识形态的编造。但是,他们会接受并认同这种意识形态。延伸一步讲,被统治阶级实际上从事的是物质劳动的分工,因而就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思想家,他们也不会有真正“自己”的思想和幻想。这一方面意味着被统治阶级没有自己独立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也说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需要知识分子进行专门的思想、理论建构。虽然,作为一种思想形态,意识形态如何转换成被统治阶级大众的观念,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并未着墨,但是,马克思在论述革命理论与大众之间的关系时却间接涉及了这一问题。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直接谈到了理论与大众的关系,其间蕴含着意识形态与大众之间的关系:“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10页。马克思这里描述的正是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理论与大众的关系。理论批判不能代替现实的革命,但是理论在现实革命中可以发挥物质般的力量。马克思所谓“说服”“掌握”隐含着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化大众的意思。无产阶级革命就是要使无产阶级从被统治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在这个过程中,无产阶级就需要有自己的“统治思想”即意识形态,并且要被无产阶级大众所接受和认可。这正是列宁后来所从事的理论与实践。
列宁承继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思想,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与无产阶级大众之间的紧密联系,并据此提出了旨在推动大众参与革命实践活动的“阶级意识灌输理论”。在《怎么办》一文中,列宁指出无产阶级阶级意识需要从外部灌输:“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 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注]《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17、363页。正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与理论斗争基础上,列宁提出了自己的“阶级意识灌输理论”。这一理论发展了马、恩的意识形态学说,它不仅指向现实的意识形态斗争,而且还回应如何克服阶级意识自发性问题——自发性带来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无产阶级大众的奴役——若要克服这一问题,就得灌输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给大众。就理论内容而言,它突出的是灌输意识形态给大众,强调的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与大众的结合。
从大众文化的内在机制看,文化工业是大众文化的内在机制,是技术理性意识形态操纵大众的文化新形态。“利益群体总喜欢从技术的角度来解释文化工业。……技术合理性已经变成了支配合理性本身,具有了社会异化于自身的强制本性”[注]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8页。。文化工业的核心是技术,而奠基于技术之上的技术理性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因此文化工业内在地生产着技术理性意识形态。但也正是由于科学技术推动文化工业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才能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作为技术理性意识形态控制下的文化新形式,不再像传统意识形态那样把一种统治思想强制灌输给大众,而是让大众在生产文化工业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接受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理性意识形态。这样,技术合理性变成统治的合理性,技术具有了“强制”的功能,显示出意识形态的性质。这种意识形态控制大众的实现方式是文化工业,其背后是技术理性对大众文化的操纵与控制。从大众文化的消费功能看,大众文化是一种满足大众消费需求的商品,消解着大众对现实的否定与不满。文化的商品化、娱乐化、标准化,赋予文化以流行、时尚、娱乐等特征,形成了消费特色的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一方面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的宣传,吸引大众参与大众文化消费,通过消费缓解着市场经济带给大众的精神空虚与心理疲乏,“虚假地”满足了大众的内在需要;另一方面,大众文化是资本逻辑与技术理性的产物,大众通过消费来认同意识形态,并沉迷于“赚钱——消费——赚钱——消费”的生活模式里。通过文化消费,大众默认了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现实要求,从而对技术理性意识形态产生认同感。从文化的意义看,大众文化丧失了文化真正的精神追求——批判与反抗社会现实、追求人的自由与解放,而是成为一种感性的娱乐文化。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中说: “文化工业对消费者的影响是通过娱乐确立起来的……晚期资本主义的娱乐是劳动的延伸。……所有的消遣都承受着这种无法医治的痛苦。快乐变成了厌烦……”[注]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3页。“文化工业没有得到升华;相反,它所带来的是压抑”[注]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6页。。可见,文化工业(大众文化)并没有真正满足人的精神需要,它带来的娱乐、快感,不过是大众生活中痛苦的反映。因此,大众文化实际上还是受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支配的,它并没有真正解放大众,也无法让大众获得真正的自由。然而大众文化本身具有多样性的文化意义,它不仅实现了维护统治的意识形态功能,也以流行文化的形式缓解着现代社会生活的工具理性式的压抑,满足了大众文化宣泄的需要。“人们在流行文化的氛围中,以生活化的方式宣泄内心被压抑的情绪”[注]刘怀光,高迪:《流行文化的兴起与宣泄性文化的合法化》,《中州学刊》,2013年第8期。。流行文化的文化宣泄正是通过大众的文化娱乐来实现的,而文化工业的娱乐性又折射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生活的痛苦与无奈。所以,大众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流行文化、娱乐文化。它并没有解放人,但却使大众通过娱乐等文化宣泄方式完成了对意识形态的屈从。于是大众文化成为资本主义的文化新形式,成为意识形态大众化的新形式。
约瑟夫·奈则从国家层面提出了意识形态影响大众的策略,突出强调国家软权力(软力量)资源在全球化竞争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软权力最初的含义是“以无形的力量资源如文化、意识形态和机制确定偏好的能力”。国家软权力有三种来源:“文化(在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政治价值观(当它在海内外都能真正实践这些价值时)以及外交政策(当政策被视为具有合法性及道德威信时)。”[注]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吴晓辉,钱程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11页。约瑟夫·奈的软权力理论与美国文化在海外传播有着直接关系。不论是文化产品意义上的文化亦或政治价值观、外交政策,其本质都是美国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在全球大众层面的投射。他由此引发了一场广为人知的文化软实力讨论热潮。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是意识形态价值话语对大众的争夺问题。我们认为,“一种价值话语要想成为一种文化软实力必须广泛地传播,一方面是理论专业层面的价值话语在学术教育体系的传播……另一方面是大众化话语方式的传播”[注]刘怀光,李华:《论美国软权力的文化机制》,《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作为价值话语的文化软实力,不仅通过教育体系中的理论话语影响精英分子,辐射大众,同时也借助电影、流行音乐等大众文化和流行文化形式在大众之中广泛传播,实现对大众的同化。然而价值话语本质上是一种包含意识形态的话语。西方的话语优势带来的是其文化软实力的世界传播,并导致其意识形态对世界大众的广泛影响。
那么,如何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也就是有机知识分子如何建构意识形态征服大众的问题。葛兰西指出知识分子和普通人存在着“辩证法”和“有机性”。“只有在知识分子和普通人之间存在着与应当存在于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统一同样的统一的时候,人们才能获得文化上的稳定性和和思想上的有机性质”[注]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76页。。这既说明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本身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也说明有机知识分子所建构出来的意识形态与大众生活实践融合一致时(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它们才能征服大众。同时葛兰西还强调了有机知识分子对传统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上”的征服。更进一步,葛兰西提出了通过语言、宗教、民俗等文化路径对大众进行意识形态的传播。在论证“人人都是哲学家”这一命题时,葛兰西看到了语言、常识、宗教、民俗等渗透着大众的“自发哲学”,从而架起了“自发哲学”与实践哲学(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之间的沟通桥梁。语言本身的特性、宗教的意识形态性(信仰统一)、常识与群众的密切关系,这些都成为意识形态向大众传播的有利条件,也是实现群众自发哲学向实践哲学转化的重要载体。在这里,葛兰西所探讨的意识形态大众化具有明显的教化形态,直接把意识形态与大众联系了起来。
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乃是指向西欧特别是意大利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大众的意识形态灌输与控制问题。在《狱中札记》一书中,葛兰西在进行东西方社会状况比较时,指出西欧资本主义社会中强大稳固的市民社会起着意识形态堡垒的作用。“在俄国,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处于原始状态,尚未开化;在西方,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得当,国家一旦动摇,稳定的市民社会结构立即就会显露”[注]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04页。。这里葛兰西把意大利、西欧社会无产阶级革命的困难归结于其稳定的市民社会结构。葛兰西不像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那样主要从经济关系的角度理解市民社会,而是主要从政治的尤其是文化的角度理解市民社会。葛兰西着重研究和描述了统治阶级组织知识分子通过“常识”等渗透大众的方式获得意识形态的、文化的领导权的现实历史与理论。
集中备件储备库的建成大大缩短了紧急状态下备件的供货周期,动叶片锻坯由90天缩短为25天,可以全面满足用户配件保供的需求。长期以来,渤海装备与国内多家大型钢厂如宝钢、抚钢等签署了采购框架协议,与国外轮盘制造企业也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强有力的保证了烟气轮机制造用特种材料的品质和工期。借助近两年来在烟气轮机总成项目上的经验积累,渤海装备还与相关合作商建立了完备的保供机制,在用户急需、急件保供方面提供充足保障。
在当代,全球化成为探讨意识形态与大众关系的新语境。迄今为止,全球化的进程表现为三个相互联系和递进的层面:“第一,全球性的交往;第二,全球交往规则的形成;第三,全球化组织的兴起。”[注]刘怀光,刘若飞:《文化全球化的根据:共同生活的现代性诉求》,《中州学刊》,2014年第10期。全球化不仅是物质层面的全球化,也是精神文化层面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乃是由现代性所推动的。吉登斯说:“现代性正在内在地经历着全球化的过程。”[注]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56页。也有学者指出,“对今日全球化的现状来说,我们可以说,它是现代性的显示结果”[注]沈湘平:《全球化与现代性》,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4页。。正是在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意识形态与大众的关系再次凸显出来。冷战之后意识形态并未走向福山所谓“历史的终结”,而是转向为文化、文明方面。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强调的正是在文化(文明)认同基础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对大众的动员与争夺。约瑟夫·奈引发的文化软实力讨论也和意识形态价值话语对大众的吸引密切相关。这二者都表明着所谓意识形态走向“历史的终结”这一结论的谬误,相反,它们意味着意识形态在民族国家层面展开对大众的争夺。大众文化的全球泛滥则折射出现代性意识形态在大众文化层面对各国大众的强大影响。同时,民族主义运动在发展中国家的高涨与民粹主义运动在欧美发达国家的蓬勃,无不体现大众对现代性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全球化的抵制。一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世界的文学”的说法,富含文化全球化的意味。在马恩视域里,文化全球化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世界的文学的形成代表着文化全球化的必然性以及产生全球化文化的内在可能。不过此时的全球化文化是一种资本主义主导下的殖民文化,其实质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世界扩张。“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4页。。二是文化全球化必然包含着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的成分。意识形态在文化全球化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资产主义体系主导下的文化全球化只能是传播着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与价值理念。要在全世界征服大众,意识形态还必须与大众建立联系,那就不可避免地要把意识形态渗透进各国的大众文化之中。
同时,列宁还认识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从而反复强调要重视无产阶级大众的阶级意识教育。“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 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加强”[注]《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27页。。因此,列宁认为,“我们应当积极地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教育,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注]《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42页。。这里包含着,如果不对工人阶级进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灌输,他们就只能接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灌输。教育或教化的方式对于培养工人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有着重要作用。可以说,列宁的意识形态理论有着重要创新意义,但列宁并没有直接研究资产阶级或其他统治阶级如何进行意识形态的灌输,研究这一问题的是意大利工人阶级的领袖和思想家葛兰西。
马克思关注意识形态的统治作用与完整理论形态的建构,但对于意识形态与大众关系只是一个原则性的指向。列宁认识到知识分子(社会民主党或者说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对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自觉构造和对大众的阶级意识的灌输,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学说本身就是有机知识分子对大众的意识形态教育或教化。在上述经典意识形态大众化思想的探讨中,知识分子需要建构本阶级的意识形态,并通过灌输、教育或教化的方式使之转化为广大社会成员的思想。完整的意识形态包含着一个显著的二元结构:意识形态作为被知识分子构筑的理论或完整思想形态与作为教化对象的大众所接受的观念。知识分子用意识形态教化大众的过程也就是意识形态大众化的过程。诚如俞吾金先生在《意识形态论》中所言,“从结构上看,教化或教育本身正是意识形态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这是非常特殊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方面,意识形态的延续和不断的再生产正是通过教化来实施的;另一方面,意识形态正是通过教化才为人们所接受并成为他们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的”[注]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修订版),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0页。。因此,马克思、列宁、葛兰西的意识形态大众化理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概括为意识形态大众化的教化形态,这也是一种经典形态。
二、意识形态大众化的后教化形态
20世纪3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发达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科学技术的结合促使意识形态与大众关系有了新形态。这种新形态可以说是意识形态大众化的后教化形态。不同于教化方式的经典形态,在后教化形态场景中,意识形态大众化主要表现为科学技术、大众文化对大众生活的直接建构,意识形态与大众呈现出一体化的结构。对于这一新形态的探讨,法兰克福学派影响深远。
法兰克福学派实际上秉承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传统,但他们关注的焦点则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统治大众的新形态,这种新形态并不是传统统治思想的大众宣传,而是技术和技术理性这种在传统上被认为是价值中性的工具,起到了意识形态的功能。马尔库塞认为:“如今,统治不仅通过技术而且作为技术来自我巩固和扩大;而作为技术就为扩展统治权力提供了足够的合法性,这一合法性同化了所有文化层次。”[注]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126页。技术不仅作为形式和手段巩固着统治,而且为统治提供了传统合法性之外的新的充分的根据。因此,“技术理性,这个概念本身可能是意识形态的。不仅是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有计划的、科学的、可靠的、慎重的控制。统治的特殊目的和利益并不是‘随后’或外在地强加于技术的;它们进入了技术机构的建构本身”[注]《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李小兵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第106页。。技术理性成为意识形态,具有了统治的功能。但技术理性又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意识形态。传统意识形态是通过某种构造的统治观念论证统治的合法性,并利用这一观念去实现统治。技术理性并不是我们利用某种技术去实现统治秩序。在现代社会,“技术本身”就是统治,技术本身的合理性就是统治的合理性。这种具有统治功能且渗透于文化中的技术意识(有计划的、科学的、可靠的、慎重的控制意识)就是技术理性。之所以将技术理性定义为统治,就在于它重塑了现代生活——不仅再造了大众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也重建了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领域。
比之于经典形态的意识形态大众化,技术理性这种意识形态影响大众的方式有什么不同呢?从根源上讲,是意识形态本身发生了变化。技术理性被看作适应新的社会发展阶段(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而产生的一种意识形态。它主要不是作为一种统治思想对大众产生影响,而是在功能上起到意识形态的作用。换句话说,意识形态大众化以非教化形态存在着。这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看:首先,在结构上,意识形态与大众关系从二元结构向一元化的变化。经典形态的意识形态大众化的内在前提是预先由知识分子建构出来一种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大众化的过程体现为知识分子用意识形态教化大众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意识形态与大众之间呈现出一种二元结构。这种二元结构主要表现为大众日常生活与专门的意识形态教育或教化生活的分离。这种结构产生的社会背景是大众的知识文化素质普遍较低,自觉意识尚未完全觉醒。而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技术理性则通过科学技术、大众文化等实现其意识形态功能。它在内容上不再表现为一种统治思想,但在功能上发挥意识形态的作用。科学技术、大众文化建构大众生活的过程就是大众接受技术理性意识形态的过程,意识形态与大众之间表现出一体化的结构。相较于经典形态的意识形态大众化,技术理性意识形态与大众关系不仅实现了结构上的变化,也完成了大众化形式的转变。这种改变不仅包括意识形态与大众关系一体化的建构,也内在包含着技术理性对经典的意识形态与大众的二元结构的消解。技术理性意识形态大众化对传统二元结构的消解,根本原因乃是由于科学技术在社会生活中成为“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渗透至社会的各个领域,影响大众生活的各个角落。马尔库塞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从人类解放的力量沦为阶级政治统治的工具。所以意识形态大众化的结构从二元变迁为一元——意识形态对大众生活的直接建构。从社会背景看,这是伴随着科学技术解放生产力、无产阶级大众自觉意识的部分觉醒和知识文化素质的提高而发生的。其次,在形式上,从统治观念灌输转向技术理性对大众生活的直接建构。经典的意识形态大众化通常通过常识、宗教、语言、教育等载体或路径对大众进行意识形态的教化和传播,展现为知识分子对大众的意识形态灌输。而技术理性意识形态虽然也通过技术教育、技术培训、技术教学、大众文化宣传等教化形态起作用,但是其影响大众的形态主要表现为蕴含着技术理性的大众文化、科学技术对大众生活的直接建构。在发达工业社会,“科技不再具有价值中立性,而是参与了世界的构造,而且成为社会的组织原则,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都围绕着技术原则进行了重构,在这种情况下,科技也就参与了意识形态的构造”[注]刘英杰:《论科学技术对意识形态的构造》,《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5期。。同时大众通过文化工业、文化消费、文化宣泄等进入到意识形态构造的生活里。因此,技术理性并非因教化而获得大众认同,乃是从功能上完成了对大众的控制。
五大改造新格局是对新时代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狱制度的重大发展,是关系监狱工作理念、模式和方法的一场深刻变革,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和司法实践意义。笔者欲从全面认识构建改造工作新格局的必要性、全面把握深刻内涵、全面领会内在联系等方面,就如何构建五大改造新格局的实践路径,进行研究和思考,提出了一些粗浅的认识和看法。
另外,建筑施工现场往往区域大,作业点面多,仅靠标准化设施防护及安全管理人员巡查还不够,还应采取视频监控形式,安全管理人员通过各点摄像头全场监控,以此做到全方位无死角盯防。
技术本身是中性的,但是技术与科学的结合使其成为一种巨大的力量。启蒙运动奠定的社会思潮,又以理性的名义,将之拔高到与信仰相对峙的高度,再通过教育系统的科学、技术教学,技术理性成为大众的公共社会意识。这样一种貌似合理的观念成为主流社会意识,即只要是合乎科学的、技术上行得通的,就是现实中合理的。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最终成为现代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趋向。这种文化趋向不仅在学校、国家机构、社会组织等精英主导的地方占据主导地位,而且通过媒体为核心的文化工业成为大众文化的机制。现代大众文化不再是前现代社会虽然受到精英文化的引导和影响但本质上起源于草根阶层的文化,而是按照技术理性的机制通过文化工业的方式批量制造出来的消费文化。当然,文化工业下的大众文化仍然具有多样的文化意义,但它本质上是技术理性在文化上的表现和补充。这样,技术理性的统治既具有了文化形态,又具备了大众的形态,从而其意识形态控制的功能得以实现。大众文化,如果把它仅仅看成是一种民间的或大众的文化,可以说自古就有。但是大众文化真正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文化新形式,发挥着统治的功能,是技术、文化与工业相结合的产物,是在晚期资本主义才有的。所以我们谈到的大众文化与其说是一种大众的文化,倒不如说是文化工业(阿多诺语)。文化工业更能准确表达现代大众文化的特征。文化工业指的是以市场为导向,把技术、文化与工业结合起来,批量生产与复制文化商品的娱乐文化工业体系。那么大众文化何以成为意识形态大众化的新形式呢?这就不得不从大众文化自身出发来探讨。
“但是这些钱太过精致了吧,古钱哪有纯手工打磨,精雕细刻的道理?”孟导拿起一枚陆教授的古钱,用老贾的话来问陆教授。
哈贝马斯说:“新的意识形态同传统意识形态的区别就在于:……把辩护的标准非政治化,代之而来的是把辩护的标准同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的功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注]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70页。技术理性作为新的意识形态,其影响大众的方式不再是政治教化或教育的方式,而是以解决大众的生活中的难题为导向,通过满足大众的生活要求来实现意识形态的功能,大众文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与传统的意识形态大众化的教化形态不同,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里,虽然残存着教化形态的影子,但意识形态影响大众的形态,不再以教化形态为主而是非教化形态起主要作用。从时间上看,这种意识形态大众化的非教化形态诞生于教化形态之后,所以也可以称其为意识形态大众化的后教化形态。
三、意识形态大众化的全球化形态
葛兰西把有机知识分子视为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主体。这是葛兰西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的独到之处。葛兰西指出社会中的所有人都是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的职能并非所有人承担。他的意思是,所有人都有价值观的、意识形态的倾向,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在从事专门的意识形态工作。他对知识分子作了类型区分:有机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传统知识分子是以行会精神表达自身的连续和独立性特点的,“这种自我评价对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不会没有影响 ,其影响具有深远的意义”[注]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页。。他们仿佛具有某种稳定的、连续不断的、超历史的“传统”,坚守着某种不变的价值观,他们多是哲学家、艺术家、教士等。而有机知识分子,与特定的阶级联系在一起,是该阶级的有机组成部分。“每个新阶级随自身一道创造出来并在自身发展过程中进一步加以完善的 ‘有机的’知识分子”[注]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页。,是为该阶级服务的,他们应该积极行动起来,并且成为“领导者”。葛兰西突出强调了有机知识分子的“有机性”、阶级性。所谓有机性其实就是其意识形态功能的专门性。相比较而言,马克思分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作用,列宁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社会民主党)对于大众灌输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作用,而葛兰西则提出了资产阶级有机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上对大众的控制作用,即有机知识分子维护着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导权。
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加速发展,文化凸显出来成为全球意识形态竞争的战略制高点。与马克思相比,学者对全球化背景下意识形态与大众的关系看法也各异。有一种看法认为苏东剧变之后,共产主义崩溃了,只剩下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意识形态。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就是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他在其发表的《历史的终结》一文中声称:“自由民主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人类政体的最后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注]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陈高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页。“确切地说,它(历史的终结)指的是那些奠基性原则和制度不再有进一步的发展了,因为所有真正的大问题都已得到解决”[注]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陈高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0-11页。。这种观点,从表面上看是宣告建立在美苏两极争霸基础上的意识形态竞争消失了,意识形态不再争夺大众,实际上却是夸大了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意识形态的历史命运——意识形态已经完全征服世界大众。这一方面反映冷战后部分共产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真空,让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全球扩张有机可乘;另一方面也体现出西方学者对于意识形态大众化问题一厢情愿式的乐观态度。所以说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一种过于简化的错误观点,这种精英式的看法误以为西方社会认同的意识形态会自动从欧美扩张到全球并获得世界大众的认可。
与福山不同,亨廷顿从(文明)文化、文化认同的视角展开了全球化进程中意识形态与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论述。他说:“文化和文化认同(它在最广泛的层面上是文明认同)形成了冷战后世界上的结合、分裂和冲突模式。”[注]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4页。这既是对福山所谓意识形态走向“历史的终结”的否定,也表明他看到文明认同在全球的国际关系中更加重要。从大的历史背景看,后冷战时代全球政治从两极争霸模式转变为多极和多文明的竞争,这构成文化、文明认同凸显的基本前提。“随着冲突的日益加剧,各方都试图获得属于本文明的国家和集团的支持”[注]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248页。。国家间的竞争转变为文明的冲突,文明集团成为国际竞争的单元。亨廷顿认为,这种文明间的冲突最有可能发生在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伊斯兰教文明之间。文明的冲突要求各社会集团以文明为武器对大众进行动员,这也就是大众的文明认同问题。据亨氏的看法,断层线战争最能体现文明认同的重要性与意识形态对大众的动员。面对文明间的冲突,民族国家需要文明内部的结盟和对大众的文化号召,因而文明冲突反而促进了文明认同。这种认同归根结底是大众的文化或文明认同。亨廷顿说:“文化认同的日益凸显很大程度是个人层面上社会经济现代化的结果,个人层面上的混乱和异化造成了对更有意义的认同的需要。”[注]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108页。文化认同虽与经济社会变迁的有着密切联系,然而实际上是个人的、大众的文化认同竞争。一言以蔽之,亨廷顿超越福山所谓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观点,指出了全球化过程中不同民族国家基于文明认同组成的社会集团对大众的争夺,其实质是以文明作为单位展开意识形态对大众的争夺。
柳传志有一种称为“复盘”的学习方式:一件事情,不论失败或成功,重新演练一遍。大到战略,小到具体问题,原来的目标是什么,当时怎么做的,边界条件是什么,做完再回过头看,是否正确,边界条件是否有变化。这也是一种反思方法。复盘的步骤:回顾目标——结果对比——叙述过程——目我剖析——众人设问——总结规律——案例佐证——复盘归档。
那么谁去灌输?便是不得不回答的问题。列宁说:“为了向工人灌输政治知识,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应当派出自己的队伍分赴各个方面。”[注]《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63页。“我们应当既以理论家的身份,又以宣传员的身份,既以鼓动员的身份,又以组织者的身份‘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注]《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66页。。毫无疑问,作为先锋队的社会民主党,必须承担意识形态灌输的任务。这种灌输面向一切人民阶级,这种灌输不仅是文字的宣传,而且包含言说的鼓动。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意识形态与大众的关系只是作出了侧面的回应,那么在列宁的阶级意识理论里,意识形态与大众的结合则是重中之重,这种结合的方式便是宣传式、鼓动式的灌输。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大众化的关键就是对大众进行意识形态的灌输。在列宁看来,工人无法自发地产生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他指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乃是由知识分子构建出来的,“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那里发展起来的”,“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注]《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17-318,318页。。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知识分子所建构出来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具有一种相对于工人运动的独立性,它与知识分子自身的思想发展逻辑有着紧密的关系。但也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列宁才反复强调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与大众的结合,而结合的方式就是灌输。
如果说约瑟夫·奈的文化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教化形态的意识形态大众化,那么大众文化在全球的扩张意味着意识形态大众化的后教化形态进入了全球场景。大众文化,在这里我们指的是文化工业意义上的大众文化。吉登斯说:“现代性的根本性后果之一是全球化。”[注]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52页。也有学者指出,“现代性是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内在机制,这一机制表现为工具理性、大众文化的全球性扩张”[注]刘怀光,刘若飞:《文化全球化的根据:共同生活的现代性诉求》,《中州学刊》,2014年第10期。。所以大众文化的全球化意味着现代性从西方社会向全球的扩张。
大众文化从西方社会进入到全球场景,根源于现代性的世界扩张。由于现代性起源于西方思想文化以及西方文化工业在全球的强势地位,所以西方意识形态在大众文化层面对世界各国本土文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是教化形态意义上的,更为重要的是后教化形态的作用——其意识形态功能的实现并不依赖教化,而是通过生产机制、文化消费、文化宣泄等来实现。这样,大众文化的全球化折射出西方文明在全球化中的强势地位。然而西方在全球化之中的强势地位并未致使全球走向福山意义上的“历史的终结”,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没有也不可能是世界上唯一的、最后的意识形态。亨廷顿关于文明认同的理论就是对之最有力的反驳,同时也标志着全球化进程中意识形态一元化与多元化竞争的现实景象。大众文化的同一性(本质是现代性意识形态对全球化的主导)与上文谈到的文明冲突、文化软实力竞争(不同意识形态对大众的争夺)就是这种意识形态一元化与多元化竞争的鲜明表现。从表面上看,这种文化“一元化”趋势与“多元化”竞争是矛盾的,但实际上它们是辩证统一的。因为这实际上反映着从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向全球的意识形态(现代性意识形态)的过渡。虽说大众文化有着同一性的趋势,现代性意识形态在全球化中占有强势地位,但是反映大众诉求的全球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并未形成,而是处于历史演进过程之中。全球化中反映大众诉求的主导意识形态并未形成,现实地说明了全球化的发展并不平衡。针对现代性意识形态在全球的扩展带来的利益不均衡,不同民族国家之间、民族国家内部不同阶层有着不同的反应。概而言之,这主要表现为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和发达国家的民粹主义运动。
民族主义运动在发展中国家的高涨是对西方现代性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全球化的抵制。诚如伊曼努尔·华勒斯坦所言,“生产过程结构中空间的等级化使世界经济在核心与边缘之间出现越来越深刻的两极化”[注]伊曼努尔·华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路爱国 ,丁浩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4页。。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其主要目的是通过核心区域(发达国家)对边缘区域(发展中国家)的剥削,获取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剩余价值。现代性意识形态则是这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获取利益方式的反映。在全球化过程中,为抵抗现代性意识形态,争取建立符合各民族共同利益的国际新秩序,民族主义便成为民族国家捍卫自身利益的一种选择。英国民族学家安东尼·史密斯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为某一群体争取和维护自治、统一和认同的意识形态运动”[注]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5-26页。。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族主义就成为发展中国家反对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全球化的一种意识形态运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也就成为发展中国家反对全球化中西方主导的现代性意识形态的工具。
在实际的跨境电商业务中,不只是教科书上的几个大的分类的邮件,还常常涉及寄样通知信、材质确认信、节日问候信等。我们根据跨境电商业务尽可能地多涵盖业务往来的邮件,进一步贴近实际业务,增加案例库的实践性。
从发达国家内部看,民粹主义运动在欧美的复兴或者说蓬勃也是对当下主导全球化的现代性意识形态的不满、抗议。“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引领的全球化带来了严重的贫富差距和巨大的文化与价值变迁,中下层民众产生了强烈的经济不安感和被剥夺感,产生了身份认知上的焦虑感和对后物质主义价值的叛逆情绪,进而需要一种民粹主义的表达”[注]林红:《民粹主义全球性再现的根源:民众与政党的双重维度》,《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2期。。这是基于大众维度对民粹主义产生根源的剖析。虽说发达国家在全球化之中获得了更多的利益,但是这些利益在国家内部不同阶层之间的分配并不均衡,并且拉大了阶层间的贫富差距。这种全球化在发达国家引起的贫富差距,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裂,也带了发达国家内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冲突加剧。此外,经济社会结构变迁带来了文化观念和价值理念的改变、身份政治的加剧,也刺激着民粹主义。当政党或政客把普通民众对全球化现实的不满情绪构造出来进行话语权的争夺时,民粹主义便成为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这种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反应着普通大众自发地对现代性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全球化的抗议,乃至抵制。
光伏发电作为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重要项目,推广于民,是一项造福大众的工程。进行类似光伏发电推广这样的环保能源项目,将有利于我们贯彻落实国家“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的改革目标,有利于我国跻身世界强国的行列。因此,我们认为,利用楼顶空闲空间光伏发电并入网的项目,是很有发展前景的。
但不论是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还是发达国家的民粹主义运动,其实都属于逆全球化的范畴。这种逆全球化是对现代性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全球化的不满,它与现代性推动下的全球化共同推动全球化朝着普惠、均衡的方向发展。马克思说:“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20页。全球化的变革、调整,不仅推动着全球经济利益的分配朝着均衡、普惠的方向前进,也必然要求一种反应大众诉求的在全球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新的意识形态。在全球化的场域里,意识形态与大众关系的形态既不同于经典形态重在教化,也不同于意识形态直接建构大众生活的后教化形态,它是教化形态与后教化形态在全球化场景的延伸,其根本追求是同化全球大众,重点在大众。
The Development of Ideology in the Perspective of Ideology and Mass Relations——Indoctrination form, post- Indoctrination form and globalization form
Liu Huaiguang,Zhang Jinxing
(College of Marxism,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453007, China)
Abstract:The ideology of Marx and Engels contain clue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deology and the masses, which highlights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y by bourgeois intellectuals.Lenin puts foward the theory of inculcation of class consciousness instilling the masses with the proletarian ideology. Gramsci further explores the theory of ideological leadership that organic intellectuals Indoctrinate the masses.These constitute the Indoctrination form of ideology popularization.In the post- indoctrination scene, technical rationality becomes an ideology in the non-traditional sense, that is, it mainly does not appear as a ruling thought, but functions as an ideology. The mass culture is to complete the conquest of the technical rational ideology to the public through the production of cultural industry, the realization of cultural consumption, and the dissolution of cultural significance.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both the civilized identity and the game of cultural soft power have declared the fallacy of the so-called ideology toward the end of history. On the contrary, they mean that ideology competes for masses at the national level. The global spread of mass culture reflects the powerful influence of modern ideology in the different countrys' mass at the mass culture level. At the same time, the rise of the nationalist move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 populist movement i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of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ll reflect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 of the popularization of modern ideology.
Key words:ideology;masses;Indoctrination form;post-Indoctrination form;globalization form
作者简介:刘怀光(1964-),男,河南许昌人,哲学博士,河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意识形态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8BKS163);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基础项目(2019-JCZD-010)
中图分类号:B0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19)03-0010-09
收稿日期:2019-02-17
DOI:10.16366/j.cnki.1000-2359.2019.03.002
[责任编校 张家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