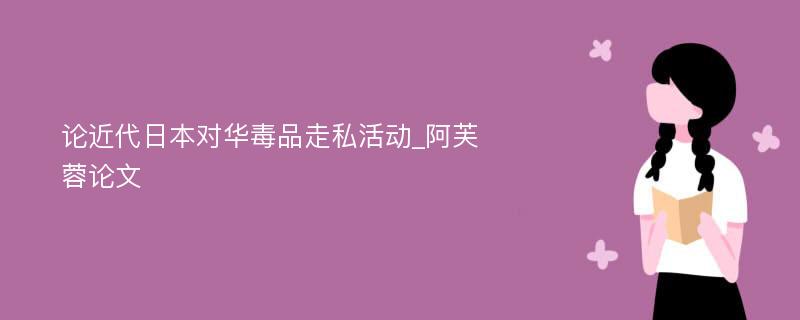
评近代日本对华毒品走私活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毒品论文,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英国因发动维护鸦片走私贸易的鸦片战争而恶名昭著,相对而言,日本在本世纪前半期对华毒品走私的行径尚未被充分地揭露出来,笔者拟对这一问题做一些探讨。
一、清季英国对华鸦片贸易的式微
自从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规定鸦片以“洋药”的名义合法进口后,清政府摄于侵略者的淫威,噤若寒蝉,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岁月中,对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贸易听之任之,丝毫不敢触动,并且抽取税厘,做出饮鸩止渴的短视行为。倒是在华的西方传教士,基于人道立场,不懈地宣传吸食鸦片的危害,吁请英国政府放弃罪恶的鸦片贸易。1906年,苏州禁烟会会长、传教士白乐文发起奏请中国皇帝禁烟的倡议,得到在华西方传教士的热烈响应,有1333名传教士在倡议书上签名。两江总督周馥将倡议书转呈清廷,对清政府下决心禁烟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清廷于当月即宣布准备禁烟。要实行禁烟,堵住国外输入这个祸源至关重要,因此,与英国交涉势在必行。
英国政府鉴于国际反对鸦片贸易的呼声不断高涨,做出准备停止鸦片贸易的姿态。同时,由于英印鸦片受到中国土烟的强劲挑战,出口到中国的数量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下降。1894年,鸦片进口占中国进口贸易总值的20.6%,1895年下降到17%,1900年更进一步下降到14.7%(注: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76页。)。鸦片出口值的持续下降也使英国容易下决心停止鸦片输华。经过中英双方一系列磋商,于1908年3月达成协议,规定以1907年英国输华的5.1万箱鸦片为基数,每年递减1/10,10年(即1917年)减尽(注:《英国蓝皮书》下卷,《外交报》第263期,转引自王宏斌《清末新政时期的禁烟运动》,《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
中国禁烟的努力,得到了国际社会支持。1909年2月,在美国倡议下,13国在上海召开万国禁烟会,通过议案9条,要求各国政府用最严厉的方法取缔吗啡及一切有害的鸦片制造品的制造与销售;各国应采取措施,防止鸦片及其制造品运往任何禁止此类毒品入口的国家。
二、日本对华毒品走私的发端与扩展
进入民国后,国际禁烟禁毒的舆论进一步加强。1912年和1913年,在美国的主持下,在海牙召开了两次国际鸦片会议。在第一次会议上,与会各国签订了《禁烟公约》,规定各国阻止将生熟鸦片、吗啡、高根及其化合原料等私运进口至各国在华租借地;缔约各国在中国设有邮局者,应采用有效力的办法,禁止毒品通过邮政局作为邮包件违禁运入中国(注:罗运炎:《毒品问题》,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86—187页。)。
可以说,清末民初的国内外环境为中国一举禁绝烟毒提供了大好时机。然而,暗中浮动的烟毒走私潜流对中国的努力构成了巨大的破坏,其源头就来自于日本帝国主义。日本虽是历次国际禁烟会议的参加者与历项禁烟公约的签字国,但它对中国的禁烟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日本是禁止向中国输入吗啡公约的签字国之一,然而再也没有比进口日本吗啡的生意更兴旺的了。”(注:(澳)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740页。)英国也不甘心曾给大英帝国带来丰厚利润的毒品贸易就这样收场,但碍于国际条约,不能再直接向中国输送毒品。于是,它便与日本勾结在一起,借日本之手将其制造的毒品贩运到中国。
其实,日本早在19世纪末就挤入向中国走私毒品的行列。英国被迫收束直接的对华贩毒贸易,善于捕捉时机的日本迅速填补了这个“真空”,逐年扩大对华毒品走私量。1911—1914年,日本每年自英国购入的吗啡数量,据英方统计,分别为5.8、12.4、25.2、35.2万盎司,而日本每年仅分别收进2.1、2.1、7.3、9.8万盎司,远少于英方的统计。如1914年,英国对日输出35.2万盎司,日本收进不过9.8万盎司,那25.4万盎司的差额弄到哪里去了呢?原来,这些吗啡从伦敦发出后,根本没有运到日本,而是经由西伯利亚大铁路,或打成邮包,直接输送到日本的关东租借地(大连),再从大连运到东北、华北贩卖。运到日本的那9.8万盎司吗啡也基本没用于医疗,更不会给其本国人吸食,而是用船或邮包运到神户,再装船运到上海。为逃避海关检查,在日本卸船后,由神户、大阪的商人将吗啡混入杂货之中,向中国输出(注:山田豪一:《1910年前后日本对华走私鸦片吗啡的秘密组织的形成》,《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2辑。)。1913年,日本自欧洲直接购买“硬毒品”2583公斤,1915年猛增到10164公斤。这还只是日本直接输华毒品,如将其间接转运到中国的吗啡包括在内,据统计,1911年为5.5吨,1912年达7.5吨,1913年上升到11.25吨,1914年更增至14吨(注:李恩涵:《本世纪30年代前后日本对华北的毒化政策》,《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无怪乎在华外国人认为毒品走私是日本对华贸易中最获利的一项。
日本对华走私毒品,不是一种个人的零星的无计划行为,而是有计划、有预谋、有组织的活动。1895年日本割占台湾后,在台湾推行鸦片“专卖”制度,积累了鸦片制、收、售的一整套“经验”,加之从1915年开始,日本已掌握制造吗啡的技术,贩卖吗啡已不再受制于人,日本开始提出向整个中国大陆贩毒的构想。1916年9月,台湾总督府专卖局局长加来佐贺太郎向日本大隈首相提出《支那鸦片制度意见》,建议把日本在台湾贩卖毒品的方式扩展到整个中国。他做了详细计算,如中国有人口4.2亿,其中5%即2000万人吸食鸦片,照日本在台湾的办法办理,每年能赚到5.54亿日元的巨额利润。他甚至还对在北京、汉口等11个主要城市设立烟膏工厂所需的器材、机械设备、建筑经费、烟膏用量、11个地区的吸烟人数、工厂的位置、成品的搬运等细节问题做了周密的策划(注:山田豪一:《1910年前后日本对华走私鸦片吗啡的秘密组织的形成》,《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2辑。)。
有了如此周密的贩毒计划,日本对华毒品走私简直就是“突飞猛进”了。1918年,日本人将18吨吗啡输入中国(注:端云:《鸦片复活》,《东方杂志》第17卷第17号,1920年10月10日。)。1926年,吗啡和其他麻醉毒物私运中国约40吨之巨,价值3500万元,其绝大部分“功劳”还是要记在日本人头上(注:菊池酉治:《中国鸦片问题和日本人的责任》,《东方杂志》第25卷第4号,1928年2月25日。)。日本向中国大陆秘密输入的鸦片数量也在迅猛增长,到20年代后半期,每年输入额高达10亿元,其中由日本海军直接经手输入中国的鸦片,价值六七千万元,以至于日本人认为“对华贸易的妙味在鸦片卖买”(注:铃木茂三郎:《日本政论家眼中的日本对华经济侵略》,《东方杂志》第25卷第15号,1928年8月10日。)!而且日本人输华毒品的数量还在进一步增加。
20年代后半期,中国境内毒品泛滥成灾,“我国竟成为万国私贩烟土的总贸易场”(注:《禁烟公报》第11期。)。不可否认,向中国走私毒品,各国毒品贩子都难辞其咎,但日本人确乎“独占鳌头”,这一点,连略有良知的日本人都承认不讳,“巨额的吗啡和其他的麻醉毒物大多数是曾经过日本人的手私运来的,这是确凿的事实”(注:菊池酉治:《中国鸦片问题和日本人的责任》,《东方杂志》第25卷第4号,1928年2月25日。)。
日本掌控下的大连是制贩吗啡的中心之一。1913年,日人贩入大连的吗啡达6.25吨,从中取得840万元的高额利润。这种买卖受到日本银行的支持,是在日本政府的赞助和鼓励下进行的(注:山田豪一:《1910年前后日本对华走私鸦片吗啡的秘密组织的形成》,《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2辑。)。后来,日本毒枭干脆把原建于大阪的吗啡、海洛因制造厂迁移到大连和南满铁路沿线各地,以便于直接向中国输送毒品。在中国境内制造违禁毒品再向内地走私贩运,深深地反映了中国的半殖民地性。日人制毒需大量原料,于是波斯红土大半为日人购买,在印度加尔各答,日人也是鸦片的最大买主(注:《日人之吗啡鸦片两贸易》,《东方杂志》第1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
青岛是一个可与大连“齐名”的贩毒中心。1914年,日本以对德宣战为借口,出兵侵占青岛,又迫不急待地掠夺青岛海关。虽然对海关的控制于1915年结束,日军却一直赖到1922年才撤走。日军迟迟不愿撤走的原因之一就是为巨额的贩毒利润所吸引。日军殖民统治机构青岛军政署直接参与了鸦片的走私活动,仿照关东都督府的做法,在日本占领军的庇护下,大批中日下流分子大肆贩毒。刘子山就是其中之一。日人将烟土从台湾、南洋、波斯一带购入,让刘向外发卖,规定贩卖的地方不限于青岛,凡是可去的地方都是贩卖范围;贩卖方法是既批发又零售,鸦片的运输由日军包办(注:崔士杰:《德日侵占青岛及我国接收青岛的经过》,《青岛文史资料》第5辑。)。日韩浪人也大肆活动,在日军的包庇下,胶济铁路上“每处车站都是走私鸦片、吗啡和盐的中心”(注:《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第831页。)。结果,日本侵略者大发横财,青岛军政署的鸦片收益每年都超过300万日元(注:山田豪一:《1910年前后日本对华走私鸦片吗啡的秘密组织的形成》,《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2辑。)。
南方走私毒品的中心是厦门。厦门与台湾一衣带水,在日本纵容下,日台浪人在厦门贩毒一发不可收拾。厦门居住着许多台湾籍民,他们受日本治外法权保护,在大陆犯法,不受中国法律制裁,由日本官吏依日法律审判。实际上,日方多纵容台湾籍民从事贩毒、开烟馆、赌场、妓院等非法营业,尽量不予制裁或从轻发落。台湾籍民在厦加入“台湾公会”后,可在商店门口悬挂会员徽章,中国警察见此便不敢取缔其非法营业,这种徽章因而俗称“护符”。在日领事唆使下,台湾籍民的贩毒行径肆无忌惮。据日领馆估计,在厦居住的约900户台湾籍民中,从事贩毒者约有470户,依赖贩毒生活的达2000人之众,占在厦台民的1/4(注:井上庚二郎(日驻厦门领事):《厦门二於ケル台湾籍民问题》,《台湾近现代史研究》1980年第3号。)。利用殖民地人民毒害半殖民地的同胞,恶化海峡两岸人民血浓于水的亲缘关系,其手段可谓毒辣至极。
这样,从北到南分布着三个走私毒品的据点,而在中国内地,则活跃着大批日韩浪人。当时,在中国关内大约有日本侨民10万人,这些人在其国内大多就是无恶不做的社会渣滓。到中国后,又得到日本治外法权的保护,更是十有八九从事贩毒等违法活动。日人在中国开设的药房,无不贩售吗啡。一有瘾者来买,店主便操着生硬的中国话问道:“抽的,还是扎的?”如果是扎的,店主就在吗啡中掺些麻药卖给瘾者(注:朱庆葆等:《鸦片与近代中国》,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65页。)。连日本妓女都成了吗啡的积极推销者,“凡日本娼妓所到之处,亦即为吗啡所到之处”(注:《日人之吗啡鸦片两贸易》,《东方杂志》第1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
如此猖獗的贩毒行为,是与日本当局的纵容分不开的。在胶济铁路沿线,当中国警察对贩卖吗啡的日本商店突击搜查时,日本宪兵往往把被捕的日本人救走,并强行索取罚款。违犯法律的人向维护法律的人索取罚款,为美籍人士所目睹。在日人的恫吓之下,县知事不得不缴付罚款(注:《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第782页。)。大连、青岛的海关完全为日人把持,毒品输入简直就是到了无人之径。日人向中国走私吗啡大多是经过日本设在中国的客邮用邮包运入,而这些邮包向来一概不许中国海关查验,如此便为毒品输华大开了方便之门。日军还在装有毒品的箱子上贴上“军用品”的标签,就可不受中国海关的查验,一路畅行无阻、堂而皇之地运入中国(注:《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第781页。)。
三、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猖獗的毒品走私
日本于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后,迅速占领了适宜种植鸦片的内蒙东部及热河,强迫东北人民种植鸦片,实行专卖制度。1932年,伪满制定了《暂行鸦片收买法》、《鸦片法》和《鸦片法施行令》,次年又颁布《鸦片专卖法》,东北大规模生产鸦片由此拉开序幕。1934—1937年,东北历年分别栽种罂粟1500、6900、8800、10300顷(注:《东北经济掠夺》,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849—850页。)。收获的鸦片除当地消费一部分外,其余大部分运往关内贩卖。在日本的毒化下,东北各地烟馆林立。据30年代的调查,东北领照的烟馆有3840家,毒馆8400家。
日本还有中国境内大办制毒工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沈阳、承德等地大肆设厂制毒。天津日租界也是大毒窟,英国人罗素爵士、美国作家麦文到中国游历后,都不约而同地指出该租界“向为毒物渊薮,鸦片交易已成公开之秘密(注:1913年3月23日天津《大公报》。)。租界内制毒、吸毒场所的数量与日俱增。早在1921年,租界内就有鸦片烟馆70家,海洛因、吗啡店100家(注:江口圭一:《日中阿片战争》,东京岩波书店1988年版,第40页。)。到了30年代,日租界内的毒品店更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据目击者称,租界内制毒厂在200家以上,售吸所更在千家以上(注:曹骏:《禁烟与抗战之关系》,建康日报社1942年版,第2页。)。
1933—1936年,为配合将华北从中国分离出去的所谓“华北自治运动”,日本利用《塘沽协定》后形成的特殊局面,从陆、海两个方向向中国走私货品,掀起了震惊世界的华北走私狂潮。走私入口的物品多为白糖、人造丝、卷烟等高税货物,日人也乘混乱之机,运进来不少制造毒品的原料(火酒、火油)(注:斛泉:《华北走私之全貌》,《东方杂志》第33卷13号,1936年7月1日。)。在日本策动下,华北成为全世界私制海洛因范围最广的场所。驻郑州的日本领事,竟在其活动地带担当起分销毒品的事务(注:李仲公:《中国禁政问题》,《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讲演录》,重庆1940年印行,第406页。)。在日本的大举毒化下,山西变成了“白面世界”。此外,汉口日租界也是大规模制贩毒品的中心之一。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制贩毒品更在沦陷区各地公开地肆无忌惮地展开,已难以用“走私”视之。英国罗素爵士指出:“日旗所到之处,毒品随之。”(注:曹骏:《禁烟与抗战之关系》,建康日报社1942年版,第2页。)事实确实如此,日本国旗太阳旗甚至被中国普通老百姓目为烟馆毒窟的标志。关于日本在全面侵华战争期间在沦陷区贩卖毒品的行为,已有许多学者揭露,这里只引述美国国务院在1943年9月1日发表的一项关于毒品的备忘录就足够了,“自1936年以来,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其领导人鼓励种植鸦片与制造烟毒,以供应吸食及其它用途,这个国家就是日本”(注:王德溥:《日本在中国占领区使用麻醉毒品戕害中国人民的罪行》,《民国档案》1994年第1期。)。看来,日本走私贩毒行径在侵略战争中已发展为可耻的“一枝独秀”了。
日本在中国沦陷区制贩烟毒毒害民众的事实已斑斑可考,不容抵赖,那么,它对其侵略势力鞭长莫及的国统区又采取什么政策?分隔敌我的“阴阳界”是否阻挡住了日本汹涌的毒潮呢?我在对这个学术界目前较少注意的问题进行探究后,发现日人毒化国统区也非常严重。
抗战爆发后,日本迅疾封锁中国沿海。1937年8月25日,日驻上海海军司令长谷川清发表所谓“遮断航行”宣言,宣布封锁上海至华北沿海。9月5日,日海军部又宣布封锁中国全部海岸。1939年5月26日,日海军部发言人又宣称:“第三国在中国沿海之航行,一律实行封锁。”1940年7月,日军又在越南北部登陆,完成了对中国沿海的封锁(注:常奥定:《经济封锁与反封锁》,重庆1942年版,第9—10页。)。
日本一方面阻止中国与第三国经济交流,一方面加紧向国统区走私日货,独占中国市场。在占领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后,日军在沦陷区建立了五大走私据点:上海、天津、汉口、徐州和广州,大肆向国统区倾销日华。货物种类繁多,计有纺织品、食品、日用品、文化用品、奢侈消费品、五金百货、工业用品、肥料、药品及毒品等,尤以纺织品、奢侈消费品和毒品数量巨大(注:拙文《抗战时期国统区与沦陷区间的走私贸易》,《国民档案》1999年第1期。)。在毒品中,鸦片、海洛因、吗啡、白面、红丸等无所不包。在粤中、粤桂、闽海、豫皖、陕豫、西北等地区,都有大批毒品从日占区走私进来,尤其是在豫皖区,“吃喝嫖赌,无所不为,毒品推销,更为流畅”(注:特种经济调查处:《第五年之倭寇经济侵略》,重庆1943年版,第74—77页。),形成一大特色。
1940年,日本发觉中日战争将是一场长期战争,资源匮乏的日本难以用自身资源支持到底,于是它更多地强调“利用现地资源”以实现“以战养战”。同时,它妄图利用更严密的封锁来困死中国抗日力量,因而几十年一贯的走私倾销的作法开始发生重大改变。1940年,华北日军通过《昭和16年度经济封锁并确保资源要领》,规定:“努力套取非占领区域之重要国防资源,但如由购买而获得时,则向敌区流出之交换物资,务须不致减低封锁效力……交换物资尽量利用鸦片、化妆品、果子酒、人造绢丝等不能增加敌战斗力及生活力之商品。”(注:特种经济调查处:《华北敌伪对我经济封锁概况》(1942年),油印本。)此后日方果真主要借重于毒品等套取国统区战略物资,严密统制沦陷区内的重要物资供其继续侵华。
日人对推销毒品是不遗余力的,方法往往是将毒品廉价提供给奸商,让他们偷运到内地牟取暴利。奸商每向国统区销售一两鸦片,一般可得数十元利润(注:《闽南的走私问题》,战时新闻检查局编:《走私专辑》中,油印本。),有时甚至可得到原价6倍以上的惊人收入(注:《中原的经济漏洞》,《走私专辑》上。)。在日军这种“让利”销售的刺激下,奸商们对贩卖毒品趋之若鹜。高额利润将国民党驻军也吸引过来。在绥远,某团团长侯顺轩借驻守河防的便利,将驻地粮食大半私运渡河资敌,再换购回大烟销售牟利(注:缉私署档案,南京二史馆藏。)。
在华日本公司商号也是日本对国统区走私贩毒政策的积极执行者。有一家名为“东兴公司”的日本公司,声称发明了一种叫“东光剂”的戒毒剂,但在制剂中需“加入一半份量吗啡”,通过它,就可以“捕捉到他们(指吸食者)的生死”,并可“获得无法比拟的巨大利润”。可见,这只不过是一种改头换面的毒品而已。它贩卖毒品是为了抢购“敌占区(指国统区)军用物资和第三国的援蒋物资,并将交换物资移交军队当局”,同时还“收集未占领区的情报,刺探敌情”。据透露,仅1939年2月一次,该公司就向中国境内贩运进该毒品1万公斤,攫取国统区铜、铁、钨、桐油等军用物资数千吨(注:钟山译:《抗战时期日本以毒品换取内地战略物资史料》,《档案与史学》1996年第4期。)。
日本侵略军更是有计划地将毒品输送到国统区。日军在使用中国奸细时,往往把鸦片交给他们,让他们从沦陷区带到国统区出售牟利。这些人为获得鸦片,甘心忍受同胞对他们的诟骂,不惜充当叛徒、汉奸。因日人将鸦片、毒品装在饭盒内,故称鸦片为“饭盒”。有时日军用鸦片来征收粮食或收购物资,鸦片又变成了“高贵药”。临近沦陷区的国统区内,因日军汉奸的走私而充满了“饭盒”和“高贵药”(注:江口圭一:《抗日战争时期的鸦片侵略》,《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1辑。)。
毒品走私给抗战事业造成巨大危害,不仅使大量财富白白浪费,而且大批官员参与其中,腐蚀了基层抗日政权。尤其是军队走私贩毒,更使军纪荡然,战斗力削弱,中条山战役便是其中一例。战役发生前,第38集团军进驻陕县,与敌隔黄河相峙。该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不思防守,专心贩毒牟利,自进驻防区起,就与奸商杨庆亭相勾结,大干贩毒勾当。在他带动下,该军上下无不以贩毒为业。1941年5月7日,日军已在中条山一带发动,次日,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打电话询问前线情况,正在赌博的李家钰竟答以“无事”。战后国防最高委员会在总结战役失利的原因时认为,走私是最大原因(注:国防最高委员会档案,二史馆藏。)。
四、结语
1938年12月26日,蒋介石在驳斥了日首相近卫文麿“更生中国”、“调整国交”的说辞后,谈到了普通中国人对日本人的印象:“老实说,中国的老百姓,一提到日本人,就会联想到它的特务机关和为非作恶的浪人,就会联想到贩鸦片卖吗啡制造白面销售海洛因,包赌包娼,私贩军械,接济土匪,豢养流氓,制造汉奸,一切扰我秩序,败我民德,毒化匪化的阴谋。”(注:《蒋委员长痛斥近卫声明训词全文》,《时事类编特刊》第30期,1939年1月16日。)这真是中国人民眼中日本人的真实“画像”。其毒化中国人民就是为了弱化中国以供其永远欺凌,用心险恶。只有在中国人民彻底击败侵略者后,才摆脱长达几近半个世纪的被毒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