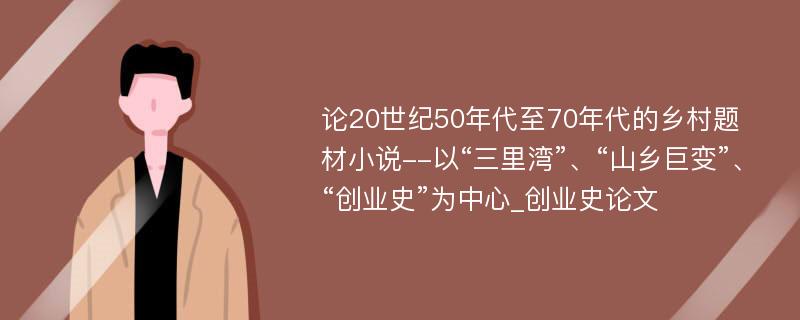
试论五十至七十年代“农村题材”长篇小说——以《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创业史论文,山乡论文,巨变论文,长篇小说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50至70年代的小说一般分为两类,即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前者主要是讲述“革命历史”,它提供的是新的现实秩序赖以成立的合法性资源,解决“我们从哪里来”的问题。后者则大略分为“工业题材”和“农村题材”(“农业题材”),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是谁”和“我们向哪里去”,即通过主体本质的建构来确立现实意义秩序。二者的共同点是都要在意义秩序的建构中展开某种“历史必然性”。
《三里湾》、《山乡巨变》和《创业史》(第一部),被认为是这个时期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本文要考察的,并不是它们的文学特征或美学评价,而是要通过对同一“题材”(对象)的相同或不同叙述的研究,来探讨50年代到7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写作在批评的参与下如何逐步地建构文学的意义秩序和写作规范。
赵树理的“局限”:
“问题小说”与“通俗形式”
在延安时期赵树理的写作被誉为“方向”,不过,建国后文艺界就很少再提,这说明他的小说写作存在着“局限”。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他将小说的“政治性”仅仅理解为配合当前工作、解决工作中的具体问题(“问题小说”)(注:参见赵树理:《也算经验》,《人民日报》1949年6月26日,《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火花》1959年6月号。),这显然过于“狭小”,无法承担建国后意识形态对文学的要求——建构和证明现实秩序的合法性。1950年,《邪不压正》受到批评,值得注意的,是批评者提出要“根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确定赵树理创作各种特色的应有的意义和前进的道路”(注:竹可羽:《再谈“关于〈邪不压正〉”》,《人民日报》1950年2月25日。)。当然,这是委婉的说法。
《三里湾》于1953年冬动笔,1955年春写成。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关于农业合作化的长篇小说,对于当代小说,它的意义还在于,它的叙事方式,以及对它的批评,都或多或少对以后其他作家的同类题材写作产生影响。它们成为影响50年代到70年代长篇小说叙事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里湾》出版后,赞扬的声音居多,不过,这并不意味他放弃了“问题小说”(注:参见赵树理:《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火花)1959年6月号。)。事实上,《三里湾》获得称赞部分地是由于“问题”(具体的题材)的“价值”,但这并不说明赵树理对“价值”就具有了深透的了解。这种“价值”是指:不仅将“合作化”看成是农村的一项具体工作,更重要的是将它看成建构现实意义秩序的一个过程。尽管赵树理选择了一个有“价值”的题材,但在叙述过程中却不能赋予题材以“价值”。所以周扬批评它缺乏“主题的鲜明性和尖锐性”,说赵树理没能表现出农民在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所显示出来的惊人的力量。周扬将此归咎于赵树理处理正面人物时的苍白和单薄,没有表现出人物深刻的“反省”过程(注:周扬:《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议(扩大)上的报告》,《文艺报》,1956年第5、6期。),亦即不但要在行为上,而且还要在思想上对过去进行清算。
周扬的这种要求,在另一位批评家那里也显示出来(注:俞林:《〈三里湾〉读后》,《人民文学》1957年7月号。),他对《三里湾》的最大抱怨是:过于容易地解决了问题,“斗争”没有充分地展开就结束了。这样的批评是有认识前提的,即对形象“定性”的分类分析(批评对阻碍合作化的“形象”的“定性”分析是以“形象”的思想根源为依据的,比如,党内蜕化思想、封建思想、个体农民落后自私思想,等等)(注:此时的人物分类尚未发展到以后的以阶级关系作为分类标准,并且每种成分都被赋予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但在具体分析中已初见端倪,比如论者已经建议作者可以考虑在小说中增加富农及让死去的地主“复活”等。),批评称赞作品写出了“相当广阔的复杂斗争”,也是基于这种分析。重要的不在于“形象”,而在于对形象的意义(定性)分析,只有通过“定性”,形象在现实中才不是偶然的,我们才能因此理解并组织现实。不过,在文本中,我们并不能看到作者也有意识对形象进行这样的分类。这里,《三里湾》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子为我们显示批评和文本的“裂隙”。这就是,文本自身提供了一种不同于批评的,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分类方式,这种方式出现在小说第三章王金生的笔记本里,即“高”、“大”、“好”、“剥”,这是从“物质”的角度来分类的,不同于批评的从“思想”的角度来分类。
发现这种裂隙使我们不能不从对《三里湾》的具体分析中摆脱出来来看批评,我们发现,既不是文本,也不是批评,而是被批评构造了的文本对今后同类题材的写作产生影响,这是“意义”产生的途径。在批评文章中不断出现的“应该”怎样写的“训导”,正是为以后的写作提供“准则”。
另一个妨碍赵树理成为建构农村意义秩序小说家的因素,是小说采用传统评书的说故事的“通俗形式”(注:赵树理:《〈三里湾〉写作前后》,《文艺报》1955年第19期。)。对故事的推重,会不利于形象的塑造。这种将故事和人物对立起来的说法就“习惯”的阅读经验来说似乎确实如此。但这种说法还隐藏着这样的判断,即形象塑造要高于故事的叙述。赵树理自己也认为《三里湾》的缺点是“重事轻人”。而这就和批评所认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同时也是新中国文学的重要任务——塑造英雄形象不相一致。但如果就此得出结论,认为赵树理的这种注重叙述的形式妨碍形象的塑造因而使意义秩序无法建构.这样的分析就还显得表面。这里的问题是,叙述并非不能塑造人物,事实上,传统的以叙述为主的一些古典小说的人物形象同样也让人印象深刻。茅盾也还将“叙述”、“对话和小动作”(粗线条的勾勒和工笔的细描相结合)看成是塑造人物的民族形式特点(注:茅盾:《漫谈文学的民族形式》,《人民日报》1959年2月24日。)。如果我们承认茅盾说的有道理,那么,故事和人物,叙述和人物塑造的对立就不应存在。这就和我们刚才的结论相悖。而同样糟糕的是茅盾在另一篇文章中的论述与此矛盾:“我们心目中先有一个相当清晰的人物形象而还没有完整的故事,这并不为奇;但如果已有完整的故事而人物形象还很模糊,那就得慎重地研究它的缘故。”“事实上,一定是心目中先有了呼之欲出的人物,这才组织起故事来。”(注:茅盾:《关于艺术的技巧》,《文艺学习》1956年第4期。)在此讨论论述的正确与否是困难的,文学构思人言言殊的“不可证”性使我们更倾向于将其看成是一种“要求”,是“应该怎样构思”。那么,这种论述矛盾的解决就只能是,存在着另一类“特殊”的人物,一种可以而且必须是先于和超越故事才能产生的人物,而不是只有伴随着故事产生意义的人物。如果我们将故事理解为人物的行动以及行动的环境,那么这样的人物就具有控制行动及环境的能力,这种能力先在于行动和环境,并且是它们的意义来源。他不来源于故事的叙述,故事只是印证这种能力。这时候,通过外部叙述塑造形象的传统方法就会受到否弃,而“内心分析”的方法则受到推崇。事实上,人物具有“内心力量”的特征也正是50年代至70年代小说对“英雄人物”的一个基本要求。这样,我们就看到意识形态的要求是如何渗透进小说形式技巧中,并通过所谓的“文学”问题的探讨(上述茅盾论构思中的人物和故事的关系)使这种要求“文学化”、“自然化”。
与“叙述”问题相关的是《三里湾》中对“自然时序”连贯性的强调,评书形式的故事性结构是形成这种特征的原因。故事的横向拓展和纵向连贯的缝接是《三里湾》要处理的一个棘手的长篇小说的结构问题,赵树理也注意到空间的拓展在小说中是必需的,所以从第十二章到第十五章设计何科长“巡视”以及画家老梁的三幅图画来展示“空间”(现在的美好及未来的希望)。尽管赵树理比较巧妙地将此纳入到具体的时间链条中,但我们仍可觉察它们和整个故事的脱节。事实上,具体的自然时序的连贯在小说中并不重要(虽然它对故事来说是重要的),因为它不一定能够揭示“意义”——历史发展的向度。所以尽管赵树理讲述了一个合作社成功的扩社过程,但是它仍然缺乏某种“普泛”的意义。这种意义在结构中表现为:将具体的时间空间化,再让空间时间(抽象)化。在50年代至70年代,对小说建构意义秩序的要求必然会贬低时间、故事的结构方式转而提倡空间乃至戏剧冲突的结构方式。
《山乡巨变》:意图和实现
与赵树理囿于“问题小说”不同,周立波是一个有志于抒写时代风云的作家。对于合作化运动来说,赵树理考虑得更多的是这种劳动组织方式给农民带来的物质性的益处,而不在于它是国家意义建构的重要内容。1955年冬毛泽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和《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及按语所强调的就是合作化运动的合理性论证。这些材料可以看成是合作化运动的“非虚构文本”,而小说写作则是将“非虚构文本”转换为“虚构文本”,所以毛泽东才会说:“这里又有一个陈学孟。在中国,这类英雄人物何止成千上万,可惜文学家们还没有去找他们。”(注: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1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周立波明白这一点,他“想把农业合作化的整个过程编织在书里”,并见出“全国性的规模宏伟的运动”,而其中的中心线索是“新与旧,集体主义和私有制度的深刻尖锐、但不流血的矛盾”(注:周立波:《关于〈山乡巨变〉答读者问》,《人民文学》1958年7月号。)。因此,小说故事的进展(从“入乡”到“成立”)和合作化过程是一致的,并且还稍花笔墨写了县里的活动以显示运动的广阔背景。但是,尽管如此,周立波的企望也只得到有限度的实现。许多批评指出小说不能“充分”、“深刻”地表现这一场“伟大”的运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黄秋耘,他指出,虽然《山乡巨变》对合作化运动的“一系列过程都写到了,却没有充分写出农村中基本群众(贫农和下中农)对农业合作化如饥似渴的要求,也没有充分写出基本群众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斗争中逐步得到锻炼和提高,进一步自己解放自己,全心全意为集体事业奋斗到底的革命精神。仿佛农业合作化运动这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是自上而下,自外而内地给带进了这个平静的山乡,而不是这些经历过土地改革的风暴和受到过党的教育和启发的庄稼人从无数痛苦的教训中必然得出的结论和坚决要走的道路。”(注:黄秋耘:《〈山乡巨变〉琐谈),《文艺报》1961年第2期。)探讨合作化运动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探讨何者更接近“真实”是没有意义的并且也永远纠缠不清。重要的是作为现实的意义秩序的建构,它要求在展现历史发展过程中凸显出作为行动者的农民自觉的选择。正是这种自觉的选择才赋予行动者以主体的意义,而在行动者获得主体意义的同时也就建构了现实的意义,并使现实具有了合理性。
《山乡巨变》比《三里湾》“前进”一步的是对于故事和人物关系的认识。周立波认识到对于他要表现的主题来说,塑造人物要远比讲故事来得重要(注:周立波说:“创作《山乡巨变》时我着重考虑了人物的创造,想把农业合作化整个过程编织在书里。”参见注(11)。)。这甚至影响到了小说(特别是正篇)的结构设计,这是一种来源于中国古典小说的“串珠”式的结构方式。它的好处是能够集中篇幅塑造一个人物形象,但它不利于人物之间的联系,也不利于见出人物在整个结构中的位置。不过,既要展示合作化运动的具体过程又要塑造人物,似乎只能选择采用这种结构方式。
所以,尽管“亭面糊”、陈先晋等人的形象塑造都受到赞扬,但是局部的人物的成功和整个结构缺乏整体性的矛盾却是周立波无法解决的。而且如果从结构整体性的角度来评价,人物塑造的“成功”其价值仍是可疑的,就是说人物虽然具有充分的“个性”,但如果不能在整体结构的等级序列中寻找到自己的位置,他就仍然是没有意义的。因此,仅将“亭面糊”、王菊生的性格指认为“面糊”和喜剧性的狡猾;将陈大春和盛清明指认为“鲁莽”和“活泼”等气质性特征的人物塑造显然不能算是“成功”。如果说这种“局限”在“亭面糊”这样意义模糊的“中间人物”身上还可以有限度地被许可,那么,在呈示意义的主要载体——“英雄人物”身上,这种“局限”就无法被“原谅”了。所以当时的批评对刘雨生这个人物的塑造就颇有微词。
和小说结构、人物塑造相关的是小说的叙述者问题,具体来说就是作为外来的党的形象如何与农民形象契合。《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都有一个外来者“进入”的相似的开头,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场景:旧有农村秩序的破坏及重建是由外来者的进入来完成的,或者我们可以说小说的叙述是借助一个外来者的视点来完成。不过这个外来者是党的化身。显然,由于这个外来的叙述者自身强烈的意识形态的权威性质,小说的叙述无法做到完全的“客观化”和“自然化”。“亭面糊”的典型语言就是“搭帮共产党”,“政府作了主,还要我们想?”他不可能成为具有信仰和行动来源意识的主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反映了叙述者自信心的不足,他必须用意识形态的权威来干预叙事,叙事自身无法呈现为“浑圆一体”的状态。这也就是当时的批评所说的“意义”的呈现是“自上而下”的,而非“自下而上”的。
但就《山乡巨变》来说,这个外来的叙述者身份并不纯粹,她除了代表意识形态权威外,还混杂着女性细腻的视点、传统文人的对田园般自然山水的喜好,以及作者在离别多年后重回故乡所显露的亲情。这样,一方面作为外来的意识形态权威的叙述者,她干预叙述,使得文本意义秩序不能以“自然化”的方式呈现;另一方面,这个叙述者又是混杂的,她又在内部削弱意识形态的权威性,使文本呈现出多种“声音”,干扰“意义”的产生。所以黄秋耘才会说《山乡巨变》的思想深度和艺术成就不够“相称”,他既对小说富有诗意的带有女性“阴柔”的田园抒情风格表示赞赏,认为在艺术上较之《暴风骤雨》“更为成熟和完整”,但也意识到这和“时代气息”的距离,亦即缺少“农村中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鲜明图景”,因而希望作者能抒写一点“风云之色”(注:黄秋耘:《〈山乡巨变〉琐谈),《文艺报》1961年第2期。)。事实上这对于五六十年代的农村小说来说并不仅是风格问题,而是意味着当用“农业题材”来替换“乡村小说”时,人与乡村或土地的情感关系就要被转换为政治抒情,它们被一种更为“重要”和宏大的叙事所遮蔽。
《山乡巨变》续篇比正篇迟两年出版。正篇出版后就有读者指出小说“结构显得零乱”,“缺乏一个中心线索贯穿全篇”,这实际上是要求作家要以冲突关系来结构全篇,当时周立波似乎仅将此看成是一个技巧问题,而不是建立文本意义秩序的关键性问题,所以他辩解说:“我以为文学的技巧必须服从于现实事实的逻辑发展。”(注:周立波:《关于〈山乡巨变〉答读者问》,《人民文学》1958年7月号。)不过,周立波在续篇的结构方面还是做了改变。邓秀梅外来的叙述主导的消失使得以冲突关系作为文本结构的基本框架成为可能。朱寨将续篇的冲突线索归纳为三条:“一是合作社与单干户王菊生之间的斗争;一是社内先进人物与落后干部谢庆元间的斗争;一是与反革命分子龚子元间的敌我矛盾。”(注:朱寨:《读〈山乡巨变〉续篇》,《文学评论》1960年第5期,)指出这一点是重要的,因为它是文本建构意义秩序的一个必要前提,人物的意义只能在这样的冲突中才得以建立。但意识到这种叙述规范与在写作中“圆熟”地完成它其间仍有距离,它要求作家改变已有的思维方式来适应它。显然这对于周立波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在续篇中,尽管采用了冲突的结构方式,但这种结构所要求的意义秩序却没有在文本中得到充分的呈现。朱寨在批评中将此理解为作者对“矛盾线索挖掘得不够深入”,没有看到冲突背后“深刻的社会意义”。作为个体的人,刘雨生、王菊生和谢庆元是没有意义的,能产生意义的只能是将个体纳入到一定的群体之中并通过指向未来的二元冲突来达到,由此我们才能想象并建构历史和现实。在这个意义上续篇的冲突结构的设置仍是“幼稚”的,这不仅表现为三条冲突线索缺乏“内在”的联系(没有联系就无法让人物在整个结构中定位,也就无法建构现实秩序),同时也表现为冲突的喜剧性解决对二元对立的削弱(比如王菊生夫妻演的“双簧戏”和谢庆元吃水莽藤自杀的喜剧效果)。而这些也影响了续篇对刘雨生这个英雄人物的塑造,即无法从冲突中赋予人物以意义,尽管刘雨生有英雄的品质,但这种品质却无“意义”可以附丽。所以朱寨这么说:“必须有重大的矛盾和波澜——这是一部较长作品的要求。必须在重大的斗争关头完成自己的英雄形象——这是一部较长作品中正面主人公的要求。”这并不只是对《山乡巨变》的婉转批评,也是对当时小说写作的一个普遍性的要求。当然,形式要求背后显示的是意识形态的内容。
这些,是《山乡巨变》所没有达到的,但在几乎同时期的《创业史》中,柳青却完美地实现了。
《创业史》的“成功”
1947年7月,柳青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种谷记》,不过他自己并不满意(注:柳青懊恼没有从题材中提炼出主题,“作品没有获得足够的力量”。一位同志说他:“党和人民向你这个有了一些生活经验的共产党员作家要求的,比你在《种谷记》里所给的要更多。”参见柳青:《毛泽东思想教导着我》,《人民日报》1951年9月10日。)。在写作的时候,柳青没有意识到他的题材对于将要到来的新中国文学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正如几十年后的文学史著作所分析的:1947年“中国革命还处于新民主主义阶段”,但作者却已“描写了农民由个体劳动走上集体劳动的初步转变,反映了农村中社会主义萌芽,并初步展现了农村处于萌芽状态的社会主义新事物与封建旧势力之间的斗争,这在现代文学史上是第一次出现的全新课题。……最重要的是作者塑造了王加扶这个农村中刚刚出现的、具有初步社会主义理想的新人”。“《种谷记》正是起着由新民主主义文学向社会主义文学过渡的桥梁作用”(注: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第629-63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1950年的一些批评意见,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批评柳青“没有使这样的中心思想成为这个作品的主导思想内容”(注:竹可羽:《评柳青的〈种谷记〉》,《文汇报》1950年6月9日、16日。)。这种批评和要求对写于1947年的《种谷记》来说显然过于苛刻,但如果是着眼于对新中国文学的要求,则是可以理解的。而在几年后《创业史》的写作中,它已经成为柳青非常自觉的追求了。
柳青对《创业史》创作意图的认识是非常清晰的:“《创业史》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注: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延河》1963年8月号。)“为什么”的问题是《三里湾》和《山乡巨变》所无法提出的问题。如果套用爱·摩·福斯特的“故事”和“情节”的区别是在于因果关系的论点(注:参见[英]爱·摩·福斯特:《小说面面观》,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那么,《三里湾》和《山乡巨变》就还只是“故事”,而《创业史》由“为什么”到“怎么样”的回答,就使文本形成一个巨大的“情节”;而意义的产生当然离不开因果关系。所以,尽管《三里湾》和《山乡巨变》对合作化运动在时间进程上都有全过程的表现,但由于总体的因果关系的缺乏,在合作化运动的叙述中建构意义秩序的要求就不能实现;而尽管《创业史》没有全程的描绘,只有几个空间的场面的组接,但它却能够首尾连贯,建构起文本和现实的意义秩序。
前面论及《山乡巨变》正、续篇在结构和叙述者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正篇是按照事件的原始时间过程来结构的,有一个外来的代表意识形态的叙述者,显然由于她的权威力量对叙述的干预而无法使叙述令人信服;在续篇中周立波力图有所改变,因而“放逐”了这个外来叙述者,在结构上以冲突的关系来代替原始时间进程,但是,权威叙述着被“放逐”,就无法在文本中建立“话语等级”(注:凯瑟琳·贝尔西认为古典现实主义的一个特点是“建立故事的‘真实’的话语等级”。对文本的“高层次的可理解性则是通过文本中贯穿全文的话语等级来证实的。这种话语等级主要是借助一种能确定从属位置的特权话语来对引号里的字面或具有象征意义的所有话语发生影响。”参见[英]凯瑟琳·贝尔西《批评的实践》第90-9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使冲突获得高层次的理解并被赋予建构秩序的意义。周立波陷入这样的两难之中。
这种困境在《创业史》中得到了巧妙的解决。同《山乡巨变》续篇一样,柳青也以系列的冲突关系作为小说的结构原则,这是形成意义秩序所必要的“整体性”和“未来指向”的形式保证。它受到王汶石的激赏:“农村各阶层的典型都经过作者的艺术构思,在作品里找到自己的和斗争的位置”,“可是作者柳青同志却是那么吝啬,连个工作组也没给蛤蟆村派呢!”(注:王汶石:《漫谈构思》,《延河》1961年第1期。)
但是,这种冲突的结构方式却只是意义产生的必要条件,它还要求有一个具有特权的权威叙述者,他建立文本阐释的话语等级,由于他的存在,我们才能在更“高”的意义上理解文本。柳青的解决办法是设置了一个历史的叙述者,他既具有权威而同时又隐藏了意识形态的性质,他将对文本的理解纳入到“客观”的“历史发展”的链条之中,这样,现实意义秩序就消弥了自身意识形态性质而呈现为“客观”、“自然”的历史必然性。
一九二九年,就是陕西饥饿史上有名的民国十八年。阴历十月间,下了第一场雪。这时,从渭北高原漫下来拖儿带女的饥民,已经充满了下堡乡的街道。村里的庙宇、祠堂、碾房、磨棚,全被那些操着外乡口音的逃难者,不分男女塞满了。雪后的几天,下堡村的人,每天早晨都带着铲头和铁锹,去掩埋夜间倒毙在路上的无名尸首。
庄稼人啊!在那个年头遇到灾荒,就如同百草遇到黑霜一样,哪里有一点抵抗的能力呢?
这是小说题叙的开篇。一场大灾难是以类似历史纪实的方式来“拍摄”的,俯视的全景镜头和解说人充满历史感的苍凉悲愤的画外音(历史老人的声音)将读者带进小说的叙述:
于是梁三老汉草棚里的矛盾和统一,与下堡乡第五村(即蛤蟆滩)的矛盾和统一,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头几年里纠缠在一起,就构成了这部‘生活故事’的内容……
这样,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充满意识形态意味的对现实秩序的构造就被纳入到历史进程的阐释中,在被历史叙述的过程中自身也获得了历史和现实存在的合理性。所以小说里“思想教育”的描写,并不同于《山乡巨变》和《三里湾》所表现的对集体劳动的物质利益的允诺,而是让高增福讲社会发展史,这个细节来自柳青的亲身经历,但在文本中它的意义更在于揭示了个体的主体建构只有在历史的观照中才成为可能。这种观照在文本中更多的表现为评论和抒情:
生宝感觉到:蛤蟆滩真正有势力的人,被一个新的目标吸引着,换了以他的互助组为中心,都聚集在这里。坚强的人们,来吧!梁生宝和你们同生死,共艰难!现在,他已经分明感觉到:向终南山进军的意义,是更重大了。
乐观和信心来自个体在差异中对自身特性的确知,并意识到自身在一个有目的的历史中占据的位置。当梁生宝感觉到“更重大”的“意义”的时候,这意味着他已经自觉地意识到作为历史的主体肩上所承担的重负。
冲突结构的设置,历史叙述者身份的确立,其目的是为了塑造英雄人物——拥有作为信仰和行动来源的主体性的个体。在新中国文学中,这一直就是重要的任务。因为人物主体的建立同时也表现为国家主体、现实的意义秩序的建立。毛泽东明白无误地道出了这一点:遵化县的合作化运动中的王国藩就被他自豪地看作“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注: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49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正像冲突的结构必须在权威叙述者的聚焦之下才能产生文本的意义,叙述中个体在冲突结构中要获得主体本质也必须将权威叙述者的声音灌录进个体的身体。亦即表现为叙述者和人物的统一,这样人物才拥有高于行动的内心力量。这直接影响到小说人物塑造的方式,它必须抛弃故事和外部描述的手段,而采用进入人物内心的方式。而这正是赵树理和周立波没有完成的。阎纲指出《创业史》在人物塑造方面受到列夫·托尔斯泰的“灵魂辩证法”和鲁迅的“写灵魂”的影响,并认为这“有着很现实的意义”,他借托尔斯泰的口说:“对感情细节的兴趣正确地代替了对事件本身的兴趣,这是一个新的方向。”(注:阎纲:《史诗——〈创业史〉》,《延河》1979年第3期。)李希凡更认为《创业史》如果“不是那样广阔地展开了人物内心世界的描绘”,就“不可能把那还是在社会主义萌芽生活里的新人梁生宝的共产主义风格,描绘得那样深刻感人”(注:李希凡:《漫谈〈创业史〉的思想和艺术》,《文艺报》1960年17-18期合刊。)。这就不仅仅是对《创业史》的人物塑造技巧的探讨,而是为当时小说的人物塑造方法做了普遍性的规范了。
叙述者的声音和人物的合一,也就是王汶石说的“主题提炼,总是通过形象,或与形象血肉相连地进行的”,是要使“思想政治倾向……成为作品的内在的力量和真正的生命”(注:王汶石:《漫谈构思》,《延河》1961年第1期。)。严家炎则称之为要“化党的思想为自身血肉”(注:严家炎:《梁生宝形象和英雄人物创造问题》,《文学评论》1964年第4期。)。不过,既然存在着“相连地进行”和“化”的过程,就表明二者仍有距离。这种要求显示了意识形态对个体的主体本质的建构要获得合理性,除了将意识形态转化为“历史权威”之外,还必须诉诸人物可理解的性格特征。
问题是,这种可理解的性格特征的内涵是什么?获得“真实性”的可理解性又从何而来?这是《创业史》出版后围绕梁生宝形象塑造而引发的一场争论的一个焦点。论争的一方是严家炎,他从艺术价值(成就)的角度认为梁生宝的形象不如梁三老汉来得立体和丰满,其原因是作者没有“紧紧扣住”“农民的气质”(注:严家炎:《关于梁生宝形象》,《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严家炎将此归结为作家的生活根基还不够“丰厚”。但这种解释并不能令人信服。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当我们发现这不是单一的而是普遍的现象,即几乎在所有的五六十年代“农村题材”小说中,像“农民”的,具有“农民气质”的人物形象都不属于“理想人物”,而都是像马多寿、亭面糊、梁三老汉这样的老一辈农民;并且这些作家几乎无一例外都具有丰厚的农村经验时,我们要考虑的可能是,为什么是后者而不是前者被我们指认为更真实的农民?换言之,亦即我们是怎样想象农民的?这显然是一个容易提出而不易解决的复杂问题。但就文学想象来说,我们在老一辈农民形象身上能够看见他们和现代文学中的阿Q、老通宝等有着诸多的相似和联系,因而与其说这种可理解的“真实性”来源于生活,不如说是认同于某种文学传统中对农民本质的一种意义构造。正是这种构造形成了我们可理解的关于农民的“性格、身份、思想、文化”等特征。它们左右着我们对农民的想象,并使我们觉得确实如此和真实自然。而严家炎艺术价值的尺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来源于这种传统,因而他才得出梁生宝形象塑造存在“三多三不足”的结论(注:“写理念活动多,性格刻划不足;外围烘托多,放在冲突中表现不足;抒情讨论多,客观描绘不足。”见注(29)。)。张钟在反驳文章中就指出严家炎之所以“怀疑这个人物(指梁生宝)的思想水平和政治头脑,怀疑这个人物的灵敏的政治眼光和理论水平,怀疑这个人物发现生活中平凡事件的深刻意义的可能性”,是因为他“用一个并不恰当的艺术标准套在新人物的身上”(注:张钟:《梁生宝形象的性格内容与艺术表现——与严家炎同志商榷》,《文学评论》1964年第3期。),并指出这种艺术标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这其实已经隐隐涉及到了艺术标准背后的话语性质。
争论的另一方则将梁生宝的性格特征阐释为“有明确的社会主义自觉性和坚定的革命精神”的“革命新人”(注:张钟:《梁生宝形象的性格内容与艺术表现——与严家炎同志商榷》,《文学评论》1964年第3期。)。姚文元将阿Q、朱老忠、梁生宝这三个人物看成是具有历史目的发展过程的三个标志(注:载《上海文学》1961年第1期。),这既表明了梁生宝的新本质和阿Q、朱老忠的具有质的不同,同时也为梁生宝本质的确立提供了历史的合法性前提。“旧农民”和“新农民”这两个概念的区分意味着两种话语的转换和新的主体本质开始建立,“新农民”形象同时也是“整个国家的形象”,意味着这也是文学中新国家的主体本质和现实意义秩序的建立。不过,以往的文学传统仍不可漠视。就像人们尽管承认梁生宝新本质的存在,但还无法将这种存在视为“自然”,还要诉诸合理性的证明一样,新的文学想象由于缺乏历史的累积还难以将自身的文学经验沉淀为“惯例”和阅读期待并进而形成新的“传统”。这也表明建构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并且还没有最后完成,如果“完成”不仅是指观念和写作的自觉,更是指阅读接受的自然、自觉的话。不过,就《创业史》的写作来说,它在总体上是完成了意识形态对新中国文学长久的期盼,这里的总体不但是指“主题”的提炼,“英雄人物”的塑造,更是指形式的寻找,一种并不只属于某个作家的个别形式,而是属于某一时期文学的带有普遍性形式的寻找。而我们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创业史》是“成功的”。
《创业史》之后以合作化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中,有影响的应该是出版于1964年的《艳阳天》(第二、三卷出版时间为1966年),《艳阳天》在总体上可以说是以前同类题材小说,特别是《创业史》的一个修订本或综合本。50年代到70年代作家经常对文本进行不断修订,最终的结果是以抹杀作家的个性为代价获得意识形态的许可,这是一个作家对自己文本的修改,同样我们也可以将《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和《艳阳天》看作是一个隐身作家(无个性的意识形态性质)对自己一部作品(只不过是作品的名字不同)的不断修订。在《创业史》阶段,这个文本的主体框架已具规模,《艳阳天》则是延续并强化这种模式。柳青在小说卷首的题辞是“创业难……”,这个省略号正是《艳阳天》的内容:“守业更难”。这不仅可以理解为《创业史》是对现实意义秩序的建构,《艳阳天》是强化和巩固这个意义秩序,更可以理解为写作方式的创业与守成。
标签:创业史论文; 山乡巨变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人民文学论文; 长篇小说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文艺报论文; 种谷记论文; 赵树理论文; 延河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