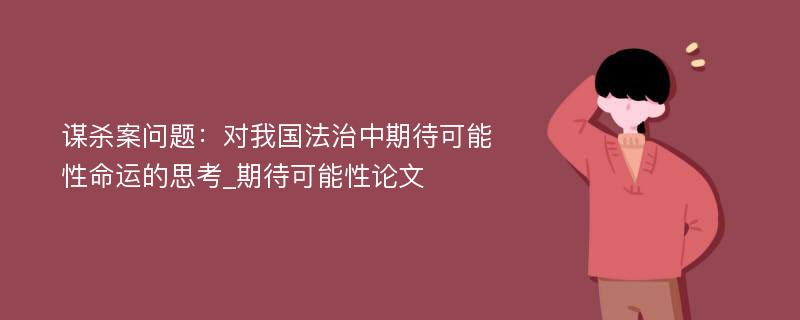
命案追问:期待可能性在中国法治命运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命案论文,中国论文,法治论文,可能性论文,命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0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2-1020(2005)04-0105-03
案例1:农妇某甲因长期遭受其夫某乙暴虐而离家出走,某乙遍寻其妻无果,悍然闯入其邻家内室,以武力威胁邻家男主人某丙替自己找回某甲,否则就以某丙之妻某丁为己妻且不许某丙回家。某丙被迫离家寻某甲,某乙强占某丙之妻某丁。某丙历经千辛万苦找到了某甲,为劝说某甲回家,某丙不惜朝某甲下跪,恳请其回家以拯救他及其妻子某丁。某甲出于恻隐之心勉强回到自家。某乙在某甲回家当晚即暴打她一顿,然后威逼遍体鳞伤的某甲当着孩子面朝他跪下,不许低头,一动不动地盯着他。折磨某甲至半夜后,某乙自己代某甲写了一份遗书并说:”我已经替你写好遗书了,明天再要你的命。”后睡在仍然跪着的妻子某甲面前的床上,某甲悄悄出去找到自己的妹妹、妹夫及其隔壁邻居某丙、某丁求助。5人合计,乘某乙熟睡之机勒死了某乙。尔后,以某甲为首的5人均被定罪判刑。[1]
案例2:1992年起,河北农妇刘某即遭受其夫张某的百般暴打。张某好吃懒做,嗜赌成性。刘某终日操劳,独力维持一家五口人(包括三个孩子)的生活,承担繁重的家务。刘某曾经要求张某的父亲及本村的干部管教张某,但张一意孤行,任何人都不敢劝他,否则他就动手打人,连自己年迈的父亲也打。刘某曾经提出离婚,张某威胁要杀了她和她全部娘家人。刘某也想过自杀,但又丢不下三个年幼的孩子。到2003年1月案发时为止,张某已先后用皮鞭、棍棒、铁锨、斧子等多次伤害刘某的要害部位,包括用铁锨猛砸刘某的头部。刘某不仅人格尊严丧失,伤痕累累,生命安全也受到严重威胁。2003年1月15日晚上,张某再次无端用擀面杖毒打刘某,甚至拿出斧子要砍她。打累了,张某到床上睡着了。次日一早,刘某将毒鼠强拌在端给张某的早餐中,张某服用后中毒身亡。事发后,包括张某自己的亲属在内的全村400多人不约而同地朝前来村里捕人的检察官下跪求情。最后,一审法院在明知本案确有多重可恕情节的情况下,对其判处了有期徒刑12年。[2]
读了上述两案,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会为本为被害人、后成死罪被告人的二人的可悲命运扼腕。人们不禁要问:我国的司法体制怎么啦?真的没有什么能够有效遏制此类虐待犯罪、同时拯救这些受虐人的社会机制吗?她们何以一个个地都不得不以“犯罪”的方式来“自救”?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司法体制、社会行政管理体制、民间救助机制才能卓有成效地拯救她们,同时也能拯救那些因虐待家庭成员最终走向自我毁灭的施暴人?
当然,社会行政管理体制、民间救助机制等都不是这里所要研讨的话题,也非刑法能够包容的问题。基于此,由此命案,这里想要追问的仅仅是:针对诸如此类的欠缺守法期待可能性或适法期待可能性较小的人,我国刑事法制应当如何为其构筑一条依法阻却其刑事责任或减轻其刑事责任的法律出路。
众所周知,“适法期待不可能”在大陆法系被认为是超法规的阻却责任事由。结合上述两案,这里想要强调的是,期待可能性的典型特征是:在意识因素上,行为人已经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发生特定的危害后果;但从意志因素上看,当时境遇下,行为人(乃至社会上一般人)又不可能做出遵从法律规定的意志抉择来。
例如,案例1所举某甲杀死某乙案即如此:行为人已经清楚地知道杀人行为违法,但出于自救/他救(通常是为救助其亲友)或其他保护目的,她/他(乃至社会一般人)在当时境况下,很难做出遵从法律规定的意志抉择。因而期待可能性不是一个认识因素问题,而是一个意志因素问题。案例1可谓典型的“适法期待不能”案件。这是因为,设若该5人当晚不作案,而是束手静待事态发展,到第二天某乙真有可能重残甚而打死某甲(遗书都代某甲写好了);即使次日甲幸免于难并能逃出来,手持其夫头天代她写好的“遗书”去公安机关报案,但我国刑法从不惩处单纯的“犯意表示”行为。同时,我国刑法上也没有诸如“致命暴力恫吓罪”等犯罪规定,公安机关因而爱莫能助。某甲还得回到那施暴成性的某乙身边。至于村委会、乡妇联、县妇联,对本案的受虐人等而言,更是救得了她一时、救不了一世。而从人的自然禀性和本能看,任何身处绝境的人在生命安危遭受严重威胁之际,都会千方百计设法自救的,此乃人之本性的当然表现。这就是说,此种情况下,一般人都会出于自救本能而难以遵从法律规范,因而将案例1定性为欠缺适法期待可能性是合乎情理的。相对而言,案例2的紧迫性比之案例1为小,或可定性为守法期待可能性较小的案例。此外,2003年11月发生的司机李某某因受路霸恶气、怒而撞死拦车人并获死罪、致上千人“说情”请求免其一死的案件,从学理上看,也可谓适法期待可能性较小的案件,[3]至少从笔者接触到的案件资料看是如此。
然而,对诸如此类的具有重大可恕情节的案例,按照现行刑法的规定,被告人等不但全都有罪,而且无任何“法定”的从轻情节可言。难怪案例1的全部被告人被判罪;而对案例2,纵然有被害人本人亲属及其众乡亲的说情,纵然被害人在被毒杀前已经在不劳而获、终日毒打其妻的境况下还进一步使出斧头来欲图加害,纵然家中仅剩下三个年幼的孤儿……,一审法院仍然未对其按“情节较轻”的故意杀人来裁量刑罚。按照我国刑法第232条的规定,对“情节较轻的”故意杀人罪的处断刑罚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为了以法救人而非“人情”救人,国内外专家学者们为此构想了多类法律出路:有学者主张按受虐待或被迫害正在继续中而适用正当防卫;有学者主张沿用英美法上正在启用的、按“受虐妇女综合症”定性从而免除该被鉴定为有此症状者的刑事责任;还有的主张按精神病人对待;也有人主张直接按人身危险性较小而确认为“情节较轻的”犯罪行为酌处,等等。然而,虐待他人也好、路霸拦车也好,即便其行为已经构成犯罪,也非继续犯,因而所谓部分侵害行为“正在继续”不能成立,行为因而仍属“事后”或“事前”防卫显属不当。而综合症或精神病人的做法,即便获得立法或司法鉴定认可,对于此类被告人而言,其后可能会被剥夺或部分剥夺民事行为能力,至少会被社会视作“非正常人”,从而遭致社会歧视。而人身危险性较小说仅限学理解释。就是说,如此操作的结果是:对此类欠缺适法期待可能性或期待可能性较小的案件,刑事立法上仍然没有可予从轻、减轻甚或免除刑事责任的“法定情节”规定。有鉴于此,仅限于刑法学理解释层面的出路构想,会因其威权性过小而缩小其司法适用空间。特别是在重刑主义思潮影响下的我国法官们大多一丝不苟地甚或机械地适用刑法,没有法定从轻、减轻或免责情节可资适用,他们“依法”只得判处死刑、死缓、无期徒刑或相对较长的有期徒刑了。
基于上述种种利弊得失的总体考量,再结合当前中国刑法学界有关重塑中国犯罪论体系的主张,我们设想,可考虑在刑法总则的排除犯罪事由之外,增设特定的、因为适法期待不能或适法期待可能性较小而启动的“阻却责任事由”或“减轻责任事由”。这就是说,将期待可能性设定为法定的而非超法规的阻却责任事由或减轻责任事由。这样,人民法院就可以根据有关主客观情况,在证据确凿而充分的情况下,确认某些因“走投无路、确因自救或拯救家人而被迫杀人”的行为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欠缺期待可能性的“犯罪”行为,属于没有守法“期待可能性”或“期待可能性较小”的行为。
这样设定的合理性、可行性在于:一方面,法律并不认为此类行为当然“合法”。这是因为,人的生命并无优劣之分,法律平等地维护每一个体的生命权益。因而即便是杀死长期虐待自己、且行将进一步恶害自己的人也属“非法”行为。另一方面,一部善法理当是张扬人性、弘扬人本之法;理当是不强人所难之法。而期待可能性理论的核心正在于“法不强人所难”,乃是“想对在强大的国家规范面前喘息不已的国民脆弱的人性倾注刑法的同情之泪”的刑法理论。[4]再者,就中国的国情看,如若不将此类情节设定为法定的可予免责或减责情节,仅依酌定情节量刑,则对实践中发生的确属“适法期待不能”的案件根本不可能通过法官行使“超法规”的自由裁量权作出阻却责任的刑事判决来。此外,对应予减轻刑事责任的案件,也因欠缺法定的从轻或减轻情节而难以得到贯彻。
总而言之,既然司法实践中时见诸如此类的、惩之则合法不合理、不惩则合理不合法的案件,立法上应当根据刑法的实质正义乃至刑法的人道性、公正性、功利性等多向度刑法价值观,将其形式上看来仍属合法、实质上有欠罪刑法定之价值真谛的内容回归到实质正义一边,令刑法成为真正惩恶扬善、张扬人性之法。这一点,大约正是诸如此类的无奈“命案”对期待可能性在中国的法治命运的理论追寻和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