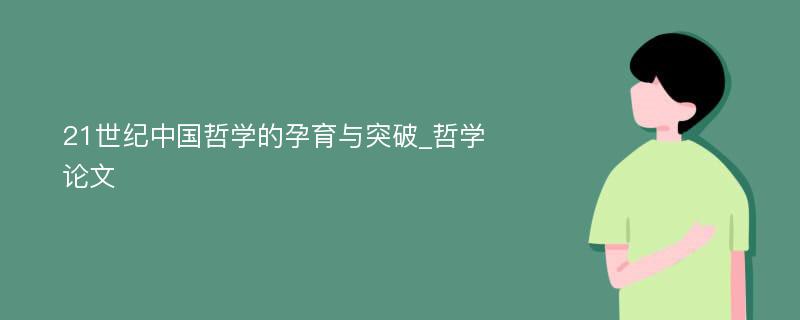
廿一世纪中国哲学的孕育与突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纪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初,梁启超说过一句话:“吾不患外国学术思想之不输入,吾惟患本国学术思想之不发明。”①20世纪末再回味这句话,令人无限感慨:从总体看,本国学术思想的发明多么少啊!泱泱大国,学术上有几多学派?
也许,相对21世纪的中国学术,20世纪注定要担当准备和孕育的历史角色。今天,在两世纪之交来临之际,从中国固有哲学与文化的角度,回顾本世纪沧桑,展望下世纪发展,是一个引人兴味的题目。
有人指出,我国现阶段哲学研究可分为三个群落:原理群(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国学群(中国传统哲学)、西哲群(西方哲学)。本文是从上述第二群落的角度展开的,即议题中心是中国传统与传统哲学的创新孕育和突破。
一 轰轰烈烈的两次大论战
在20世纪中,两次文化大论战在中国哲学与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次论战发生在五四前后,从1915年《新青年》与《东方杂志》就东西方文化问题展开论战开始,争辩延续十余年,先后参与者数百人,发表文章近千篇,专著数十种。当时论战内容分丰富,涉及问题相当广泛,但比较集中于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这场论战直到1927年,因思想战线上争辩的焦点转到社会性质等问题上去,方才告一段落。这场论战的影响至为重大,仅就文化思想而言,也是很深刻的,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形成了前所末有的新局面。它从思想上启发了五四运动,并随着五四运动得到更加深入蓬勃的发展,故被人们称之为“五四新文化运动”。
王元明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规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它超出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眼界,把民族的振兴与向西方的学习,第一次提升到隐藏在直接功利背后的思想观念层面,使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努力从经济、政治转移到思想观念领域。”②
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有其缺陷,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未能正确对待传统。特别是代表新文化运动方向的主流派,在激烈批判传统的同时,未能从更深的层次上揭示传统的本质,进一步改造和革新传统。换句话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火药味足,而建设味少。当然,论战初期,两军对垒,激烈的火药味是可以理解的,但随着论战深入,注意的焦点应逐步转向新传统新文化的建设上来,用新传统“范式”取代旧传统“范式”。林毓生认为:“自由、理性、法治与民主不能经由打倒传统而获得,只能在传统经由创造的转化而逐渐建立起一个新的、有生机的传统的时候才能逐渐获得。”可惜,由于种种原因,五四新文化运动未能对传统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五四人物,不是悲歌慷慨,便是迫不及待,很少能立大志,静下心来做一点精神严谨的思想工作,当我们今天痛切体验到文化界、思想界浮泛之风所产生的结果之后,我们应当在这个时候领略一点历史的教训了。”③
进入80年代,一场新的文化大论战又在中国大陆燃起,虽然时间比20年代论战要短,但气势更为磅礴,参与的专业刊物、普及刊物、大学学报等共达数百种,丛书数十种,论文数千篇。这场论战和先期在港台和海外展开的中西文化论战相汇合,不仅观点交锋,而且人员交流,国际学术讨论频频,颇有世界性大气魄。这场论战,很象是要完成20年代论战没有完成的目标,既是20年代论战的继续,又是进一步深化和发展。这场论战是在我国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形势下产生的,是在冲破了极“左”思想长期禁锢以后开展的,其时代意义更为深远。从儒学复兴、全盘西化、西体中用、中西互为体用、哲学启蒙、彻底摧毁与重建、综合创造等各种各样的主张中,我们可以初步领略到百家争鸣的热烈景象。
一个完整的新文化运动应包括论战(对旧文化批判)和建设(新文化体系建设)两个阶段,如果只有论战而没有随后的建设,就如同只开花不结果一样,即使批判的火力再猛,旧文化仍会以伪装的形式卷土重来。傅铿在评述社会学家韦伯(M.Weber)的观点时指出:“破除一种传统必须同时创建一种更合时宜和环境的、也更富于想象力新传统;只有在新传统的克理斯玛(超凡魅力)力量压倒了旧传统习惯势力之后,旧传统才会逐渐地退出历史舞台,新传统才会赢得人们的广泛支持,才会深入人心。否则的话,凭空是不能破除传统的。没有更好的、更具克理斯玛的传统,旧传统就会死灰复燃。所谓‘不破不立’,作为一种规律,事实上应该倒过来,即‘不立不破’,因为创造传统要比破除传统困难得多。”④新传统取代旧传统,用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观点说就是“一个范式”取代另“一个范式”,他说:“一种范式经过革命向另一范式逐步过渡,正是成熟科学的通常发展模式。”⑤单纯的分析或批判,并不能自然产生新范式,只有经过艰苦的创新和细致的理论建构,新的范式才能逐渐清晰和明朗。令人遗憾的是,20年代和80年代的两次大论战都未能及时转入中国哲学与文化的“新范式”建设,与大论战规模相匹配的新理论建设高潮始终未能形成。照此下去,是不是21世纪再重开第三次大论战?
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和不断深化的国内改革,如果中国固有哲学与文化的发展只停留在口号争辩或琐细的论证上,不能为时代需要的“换脑筋”提供实实在在的新观点新理论,我们就不完成中华民族新旧观念的历史转换,就会严重制约经济改革和其他领域改革的深化发展。只要看一下目前社会上浅薄的思想流行,空洞的说教依旧,怀古复旧情绪蔓延,拜金主义与形式主义横行,每一位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都会感到新传统和新文化的建设何等重要!
二 艰难曲折的孕育之路
从旧传统瓦解到新传统的确立是一个复杂的创造过程。著名心理学家沃勒斯(G.Wallas)曾把创造过程分为准备、孕育、豁朗、证实四个阶段。他这里说的是个人创造历程。笔者觉得,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新传统新文化的创造也可分为上述四个阶段。
创造过程的第一阶段是准备阶段。这种准备阶段包括发现问题、整理资料、明确主攻方向、对问题作多角度多方法的试探解决。创造者会遭到种种挫折,苦思不解,只得把问题搁置一旁,暂时“忘记”。换句话说,“准备阶段”一直到各种尝试未能突破,陷入困境为止。我们前面说的文化大论战可以说是准备阶段的组成部分,通过争论。瓦解旧传统,准备建立新传统,但新传统的路一时难以找到,所以陷入相对沉寂的“孕育”阶段。
在第二阶段孕育阶段,创造者的主要注意力转到其他方面,只有少量注意力以潜在形式围绕困境问题悄悄探索。这就象母鸡在孵蛋时的情况一样,从外表看,鸡卧伏不动,而实际上它所孵的蛋正在发生着育化的演变——鸡雏正在形成。孕育阶段可能是短暂的,也可能是漫长的。就中国固有哲学与文化的新体系建设而言,自20年代文化大论战以来,迄今一直处于孕育阶段。当然,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孕育阶段虽无大规模的建设和重大的突破性成果,但仍有不少学者在做冷静思考、默默探索,为突破性进展到来创造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次文化论战后,30-40年代曾出现一个哲学新体系建设小高潮,其中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贺麟等哲学家卓有影响。
熊十力(1885-1968)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最早自觉创立独特哲学体系的哲学家之一。他的代表作是《新唯识论》。熊十力哲学融儒释为一体,又兼摄西方哲学,内容深邃,论证严密,风格鲜明,形成了独特的新唯识论体系,是本世纪中国传统哲学“返本开新”的先驱。冯友兰(1895-1990)1939年出版《新理学》,以后又陆续出版《新事论》《新世训》等五部著作,形成“贞元六书”,建立了有个性的新理学体系。“在中国现代非马克思主义哲学营垒中,新理学是体系最为完整、内容最为丰富、逻辑系统最为严密的哲学体系。”⑥金岳霖(1895-1984)赞赏中国道家思想,将“道”作为中国哲学最高范畴,汲取了新实在论等西方哲学思想,提出了“道、式、能”的本体论。他在1944年出版《论道》专著,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形而上学体系。贺麟(1902-1992)试图在陆王心学的基础上发展“新心学”,他将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与康德的先验论、黑格尔的唯心论等相结合,在构思“新心学”体系方面做了许多努力。
如果说上述哲学家注意的是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合,则张贷年(1909-)提出的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与中国传统哲学结合走“综合创造”之路的主张更为难能可贵。张贷年在30年代中期提出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为一”,即辩证唯物论、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西方逻辑分析方法三者综合为一,创造中国哲学新的理论形态。40年代他写出著名的“天人五论”(《哲学思维论》、《事理论》、《知实论》、《品德论》、《天人简论》,全面论述了他的综合创新哲学体系要点。
人们有理由期待,由这些探索为契机,中国哲学新理论建设将冲破孕育阶段的模糊和沉闷,迎来新体系建设高潮。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高潮并没有出现。上述“小高潮”一闪而过,新体系建设反而进入了“冬眠”时期。
按创造过程四阶段说,孕育阶段过后是豁朗阶段,即一个苦思不解的问题经过一段孕育,在某时刻,一束耀眼的曙光突然降临,顿时出现“豁然开朗,一通百通”的境界。豁朗阶段是创造取得实质性突破的高潮期,创造者欣喜若狂,思绪万千,心理学家称之为“有啦!”现象、“啊哈!现象。我们民族的哲学与文化,近80年来一直在等待这个“啊哈”“有啦”的豁朗阶段的到来。当然,这不仅需要少数学者的灵感和个人突破,更需要有一个足够规模、足够强度的百家学派大争鸣阶段作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说,如若不能复兴和超越战国时期学派争鸣的气势和规模,中国新文化就难以“豁朗”。中国新文化理论的“豁朗”,不仅将使其成为世界文化中最有活力的部分,而且将引起中国经济理论、政治理论、社会理论、教育理论的连锁反应,这将是中华民族一场新的觉醒运动。
用民族哲学“豁朗”阶段标准衡量,30-40年代哲学新体系建构无论从广度和深度上都远远不够。大部分建构体系受纯哲学范围局限,既缺乏必要的多学科、跨学科视野,更缺乏国外许多哲学学派代表人物那种以某门具体学科为根基,逐渐上升到哲学层次的探索历程。由于学术视野受限,缺乏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根基,因而也就缺乏深刻的原创力。所以看上去是在传统要素基础上“嫁接”出新哲学,而非从根基上重构,换句话说,虽出现过寥若晨星的个别新哲学体系,但在深层上均没有突破传统文化的“范式”。
三 重建中国哲学突破口的探寻
更新传统,重建中国哲学,突破口在哪里?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探索,目前有三个活跃的思潮颇引人注目,他们可以形象地简称为新儒家、新道家和综创家。
(一)当代新儒家
当代新儒家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坚持儒学本位立场,力图复兴儒学。其代表人物之一牟宗三认为,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流。魏晋对道家的重视,六朝乃至隋唐佛学的泛滥,皆为中国文化生命离其自己,为中国文化的歧出。第二,广泛吸收东西方哲学多家思想,对儒学理论进行重构和创新发展。新儒家的使命和宗旨,就是以中国文化命脉(儒学)为本,创建一个大综和,即“我们要求一个大综和,是根据自己的文化生命的命脉来一个大综和,是要跟西方希腊传统所开出来的科学、哲学,以及西方由各种因缘而开出来的民主政治来一个大结合”。⑦简言之,就是“返本开新”,一是返回儒家之学的根本,二是要开出现代科学民主的新局面,以实现儒家“内圣外王”的崇高理想。
新儒家以儒学为本重建中国哲学的学说体系有多种,第一代人(冯友兰、熊十力、贺麟等)的学说体系我们在前面已有简要介绍;第三代人(杜维明、刘述先等)的思想尚在发展中;这里我们仅简介第二代人中三位体系颇有特色的哲学家。
唐君毅(1909-1978)的哲学被称为超越的唯心论。这一哲学的核心,是心本体论。在其代表作《生命的存在与心灵境界》一书中,他综合了中西印哲学对心性的了解,建立起一个以人的生命存在为先在的,展示人的心灵活动之不同层面、不同境界的系统的哲学体系。该体系的建构从转化传统哲学开始,他采取理之六义和外观内省的五性论,分析出先秦的四种典型,再延伸至对汉儒、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和宋明理学的分析,最后把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与佛教唯识无境相结合,提出了心通九境:万物散殊境、依类成化境、功能序运境、感觉互摄境、观照凌虚境、道德实践境、归向一神境、我法二空境、天德流行境。其中天德流行境为儒家最高精神境界,即“尽心知性以知天”的“天人合一”境界。唐君毅认为,一切宇宙的、社会的、人生的问题,都可以归入他的不同境界。最后,他把九境约为客观、主观、超主客观三境,又以三境收归于一念,来说明心本体实为宇宙人生种种境界之源。“道德的形上学”是牟宗三(1909-)哲学的核心,也是他重建儒家传统最本质的内容。“道德的形上学”一语旨在说明儒家思想中的内在性(道德)与超越性(形上学)之关系,其焦点则在于说明如何由内在达于超越,由有限通于无限,实质就是如何通过建构精致的“内圣”理论,曲线开出“新外王(民主和科学)”。在其巨著《心性与性体》一书中,他以东西方哲学二大学说作为建构哲学体系的基础:一是对宋明理学的义理系统拿出一个新纲脉,认同陆王而贬抑程朱。他不仅按照陆王心学“先立大本”的思路建构体系,而且极大地突出了“心即理”的原则。二是吸收德国哲学家康德的某些概念和方法,借康德观点启发理路,勾画蓝图。在牟宗三的体系中,他用儒家的本心性体概念诠释和改造康德的自由意志,通过论证人可有智的直觉、本心性体是绝对无限者,思辨地证明道德实体与宇宙实体的统一性;他用“道德良知自我坎陷”来说明从“无执有存有论”到“执有存有论”的过渡,把科学的认识及其根据问题提升到存有论的层面加以探讨。这些都是他高于传统儒学之处。⑧牟宗三将新儒家理论精辟地概括为“三统并建”,即道统的肯定(肯定儒学之本),政统的建立(实现民主政治制度),学统的开出(实现学术独立性)。
一般说来,新儒家的代表大都承宋明理学。与之相异,方东美(1899-1977)的新儒家思想则直接导源于原始儒学,特别是《易经》,并兼容道墨,因而更带有一种恢弘的气势。方东美把人生哲学视为主要关注之点,建立了“生命本体论”哲学体系。他将“生命”一词从生物学界提升出来,并赋予它以“元体”的意义。作为普遍的元体,生命既体现了现实的感性存在,又同时体现了精神价值。这种生命本体弥漫于自然,内在于万物,渗入于人的创造活动,整个宇宙即展现为生命的大化流行。这样,以生命为普遍本体,宇宙与人生,精神与物质等等便由对峙走向沟通,而人生价值则通过与生命价值的融合而获得了依归⑨。他指出,人作为生命的主体,蕴含着巨大的创造力,“透过这种潜在而持续的创造力,人类足以开拓种种文化价值,在生生不息的创造活动中完成生命,这才是通往精神价值的智慧之门。”⑩方东美认为,他的哲学体系是将西方柏格森、怀特海生命哲学与中国《周易》“生生”哲学融汇贯通的结果。
作为重建中国哲学的先驱者,新儒家率先选定自己的突破口,并一代代艰辛努力,留下了功不可没的贡献。无庸讳言,新儒家在建构中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和根本缺陷。夏乃儒指出了三点(11),首先,中国文化本位与儒家本位说,这是现代新儒与生俱来的“胎记”。其心态不免过于狭隘,其思维模式流于单一而将失去开放性,其思维框架也未脱“中体西用”之窠臼。其次,泛道德主义、道德至上主义和道德决定论,是传统儒学的一个根本缺陷,而现代新儒家并未摆脱传统儒学遗留给他们的这一束缚。再次,“内圣”如何开出“新外王”,也即是儒家道德如何与科学民主相容问题,是现代新儒家重构儒学的核心问题,也是新儒学思想体系内难以克服的基本矛盾。以上三点是很有见地的,由于篇幅关系,本文不再赘言。
(二)当代新道家
在新儒家之外,有没有重构出眉目的其他学派?我们欣喜地看到,当代新道家以与新儒家迥然不同的形象在90年代悄悄问世。1991年董光璧发表《当代新道家兴起的时代背景》等论文,1992年出版专著《当代新道家》,使新道家由“潜”变“显”,带来了重建中国哲学的新风。
《当代新道家》一开篇就以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分裂、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的隔阂为着眼点,站在“建构世界文化新模式”的高度上展开新道家论述,高屋建瓴,气势恢宏。在追溯新道家产生的背景时,董光璧指出,当代新道家的思想是在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危机情势下,同新儒家思想一起并行发展的。其中,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最早系统地阐明了道家思想与科学的关系,指出道家思想的世界意义;日本著名物理学家汤川秀树论述了道家思想的现代性,分析了道家直觉对科学认识的深远意义;美国著名科学家卡普拉推崇道家思想中的生态智慧,并以此为契机建造他的东西文化平衡的世界文化模式。董光璧把上述科学家发展的道家思想的现代形态总结归纳为四个基本论点:道实论、生成论、循环论和无为论。
在道实论中,董光璧从道的奥义、○号的创造、真空的研究几个方面研究了道的现代含义,认为在某种意义上“道”就像现代物理学中的“量子场”。他从粒子了转化、宇宙的创生、定律的起源三个方面论析了道的生成论。在循环论中,他认为循环论的最高要求是建立宇宙循环图像。要使这个理想的宇宙循环图像是科学的,至少要有三个科学循环原理:即物质循环原理、能量循环原理和信息循环原理。在无为论中,他认为老子的“自然无为”思想就是要人们顺其自然,也就是说按规律办事。老子的无为思想在解决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危机中有重要意义,是现代科学人文主义的古典楷模。董光璧进一步认为,老子的怀疑与直觉结合的伟大思想不仅是发展科学的法宝,更是至善的指路明灯。
胡新和在评价新道家时指出:“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亟需扬弃传统文化以重塑适应时代和国情的现代文化大背景中,倡导当代新道家思想的研究与弘扬,对应于在海内外颇为流行并已成气候的现代新儒家思想,确有其独特的意义与优势,并可望成为一种贯通古今、契合东西的新文化观的生长点。”(12)这一评语是中肯的,正象历史上传统儒家和传统道家呈互补之势一样,新儒家和新道家也呈微妙的互补之态,这突出表现在,新儒家是以“内圣”为出发点,由“内圣”达“外王”,形成天人合一;新道家却是以“外王(科学)”为出发点,由“外王”达“内圣”,形成天人合一。一个出发点在内圣圈里,一个出发点却在内圣圈外,互补对称相当鲜明。
《当代新道家》出版后,哲学界反应冷淡。出现这种冷场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我国哲学界三个研究群落(原理群、国学群、西哲群)分家:搞中国传统哲学的,较少注意自然科学与科学哲学;搞科学哲学的,较少注意中国传统哲学;搞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较多注意的是传统教科书体系。这正是重建中国哲学之大忌。
当代新道家不是从哲学家中兴起,而是在自然科学家中产生;不是首先由中国学者复兴,而是很早由外国学者倡导,这种“反常”的发展模式,足以令人深思。正如董光璧在书中所言:“令人遗憾的是,产生伟大生态智慧者老子故乡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没能更早地到道家思想的现代意义,并致力于道家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建设贯通的桥梁。”(13)
新道家理论也有其缺陷和不足。首先,《当代新道家》一书展开的新道家理论较单薄,没有形成系统严谨的理论结构,科学内容的分析和猜测较多,哲学内容的推理和建构较少。作为新道家主要理论的“四论”,其中相当多的内容是用现代自然科学知识证明道的“无中生有”论题,而这一论题只是道家理论的一个起点问题,这说明新道家发展尚处在“初级阶段”。其次,正如新儒家“内圣”开出“外王”遇到困境一样,新道家存在着“外王(科学)”开出“内圣”的困难,即新道家科学的成份多,人文的成份少,几乎无法进入尽心知性的至圣境界。这样,就难以实现其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统一为世界文化新模式的目标和理想。
(三)当代综创家
“综创家”是“综合创新派”的简称,亦称“创建派”,其思想基础和核心是张岱年的“综合创造论”。
早在1935年张岱年即提出了“创造的综合”的主张。“创造的综合”中心思想是:“兼综东西两方之长,发扬中国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遗产,同时采纳西洋的有价值的精良的贡献,融合为一,而成一种新的文化,但不要平庸的调和,而要作一种创造的综合。”换言之,“所谓创造的综合,即不止合二者之长而已,却更要根据两方之长加以新的发展,完全成为一个新的事物。”(14)他进一步指出,中国现在所需要的哲学,最少须能满足以下的4条件:(1)能融会中国先哲思想之精粹与西洋哲学之优长为一大系统;(2)能激励鼓舞国人精神,给国人一种力量;(3)能创发一个新的一贯大原则,并能建立新方法;(4)能与现代科学知识相应合。在上述4条中,第3条是成功的关键:“真正的综合必是一个新的创造。必有一个新的一贯的大原则,为其哲学之根本义,为其系统之中心点,以之应用于各方面,以之统贯各部分。”(15)
1936年张岱年提出了新哲学的具体蓝图:“今后哲学之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主张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新唯物论为基础,一方面将中国哲学关于人生理想的优秀传统结合进来,另一方面将形式逻辑的分析方法综合进来,由此构成一个广大深微的唯物论新哲学。到了40年代,张岱年进一步通过“天人五论”全面论述了他的综合创新哲学体系各要点,形成了系统的“综合创造论”观点。令人惋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天人五论”未能在当时公开发表,客观上延缓了这一重要学派的形成。
80年代,张岱年再次高扬“综合创造论”的旗帜,结合新形势和时代需要,进行了多方面论析和探索,获得累累硕果,被学术界称为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的带头人。方克立等学者在组织宏大的评论“新儒家”学术运动中,鲜明支持并深入研究“综合创新派”的观点,对推动这一学派发展有重要影响。方克立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四句话概括综合创新派的基本方针。他指出:“‘批判继承’是我们继承历史遗产的方针,包括区分历史遗产中的精华和糟粕,对精华也要经过扬弃、批判、改造,经过‘创造性的转化’,才谈得上继承和利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说明继承、利用古代的或外域的优秀文化成果,其目的是为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综合创新’则是讲继承历史遗产和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关系问题。文化的发展不能只有继承,没有创新,而创新又必须以前人取得的成果为基础。诚如张岱年先生所说:‘社会主义文化必然是一个新的创造,同时又是多项有价值的文化成果的新的综合’。”(16)
与此同时,一些海内外学者也纷纷从各自角度提出了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创造性诠释、创造性重构等见解。把中国哲学的“重建”与“创造”紧密联系在一起,已形成一股有特色有影响的思潮。在这一新背景下,张岱年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及时提出可在上述思潮基础上形成一个与新儒家立场和风格不同的学派,并亲自斟酌,提议可称之“创建派”。
在张岱年先生指导笔者《中国哲学研究中的“创建派”初探》(17)一文写作中,笔者体会到张先生提出“创建派”,其含义有几个显著特点:1.视野和心胸更为开阔。以“综合创造论”为基础,不仅放眼大陆,而且放眼港台和海外,着眼实现大联合;2.目标和重点更为突出。80年代泛提文化综合创新,较少提及中国哲学的综合创新问题。现在明确重点是中国哲学的重构。3.原则和核心更为鲜明。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是由儒家的“仁”和道家的“道”组成的,现融入“创”,便形成以“创”为先导,创、仁、道三位一体的新核。这个新核由“创”统而贯之,确立了“一个新的一贯的大原则”。
与新儒家和新道家相比,综创家的优势和特点是鲜明的:她不拘泥以儒为本,或以道为本,而是择两本之长综取之,左右采获,克服偏于人文(新儒家),或偏于科学(新道家)的片面性;她不仅博采儒道两家之长,而且以“创”为本,一以贯之,着眼克服中国传统哲学“圆而神”的和谐有余,“方以智”的锋角不足的重大缺陷。今日社会,是一个竞争社会,是一个创新时代,专长守势的哲学精神,是无法站在时代潮流前列的。以“创”统贯之的“综创家”,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时代性。
综创家的观点体现着马克思哲学的实践精神:作为核心范畴的“创”,不是一个思辨的概念,也不是一个静态用语,它首先意义是人的创造过程、创造实践。以“创”为出发点,向内可以追溯人的心灵、心境和精神,在“创”的过程中体验“尽心知性以知天”的最高“内圣”境界;向外可以创造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使中华民族在国际竞争中屹立世界民族之林,以成“外王”的宏业。这是否就是中国传统哲学孜孜以求的“内圣外王”统一之路?
无庸讳言,在20世纪下半叶重建中国哲学的进程中,大陆学者与港台海外学者形成明显的时间差距。由于历史的曲折,前者“进入角色”过于迟缓,延误了20世纪形成百家争鸣哲学重建高潮的时机。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有了现有的辩证唯物主义教科书体系,中国哲学就用不着创新发展了。这是一种误解,这种误解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不是阻碍民族哲学发展,而是为民族哲学复兴开辟了广阔道路。张岱年先生半个多世纪前满怀激情的指出:“中国能不能建立起新的伟大的哲学,是中国民族能不能再兴之确切的标示。”(18)令人欣慰的是,我国哲学界已重新迈开朝这一目标努力的步伐,漫长的孕育和积极的突破口探寻,正预示着21世纪一个气象万千的中国哲学重建高潮的到来。
注释:
① 《梁启超文选》(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217页。
② 王元明:《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天津师大学报》1992年第6期,第46页。
③ 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出版社1988年版,第149页。
④ 傅铿:《论传统》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⑤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上海科技出版社1980年版,第10页。
⑥ 许全兴等:《中国现代哲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89页。
⑦ 牟宗三:《鹅湖之会》,台湾《联合报》1992年12月20日。
⑧ 郑家栋:《牟宗三对儒家形而上学的重建及其限制》,《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第155页。
⑨ 杨国荣:《人生意义的哲学沉思》,《暨南学报》1992年第4期,第2页。
⑩ 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黎明文化公司1987年版,第129页。
(11) 夏乃儒:《二十一世纪儒学的命运》,《文汇报》1994年1月30日。
(12) 胡新和:《从交融走向新生》,《哲学研究》1994年第6期,第77页。
(13) 董光璧:《当代新道家》,华夏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
(14)(15)(18)
《张岱年文集》第一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65、206、209页。
(16) 王伟华:《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天津日报》1991年12月5日。
(17) 刘仲林:《中国哲学研究中的“创建派”初探》,《哲学研究》1994年第7期。
标签:哲学论文; 儒家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当代新道家论文; 中国哲学史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 理论体系论文; 范式论文; 张岱年论文; 国学论文; 道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