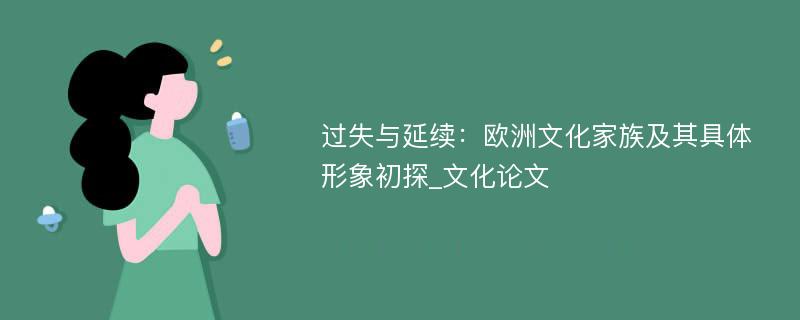
断裂与延续——欧洲文化族及其具象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具象论文,欧洲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以前,欧洲一体化作为一种主要以“帝国”形式出现而体现为政治军事扩张及地理变化的“大一统”运动时,几乎就是数个断裂而表面上关联不大的帝国:罗马帝国、查理曼帝国、奥托帝国、查理五世神圣罗马帝国、路易十四文化帝国和拿破仑帝国等。那么,在“断裂”的表象下是否有作为文化底蕴的内在链接呢?假如有,其维系本因何在?维系本因与外显帝国之间有何关联?或许用断裂与延续的辩证法,从文化学的“内化”与“外显”概念来解读历史,探索“单一欧洲”发展底蕴时,“欧洲文化族”(the European family of cultures)的存在及可以举证的“具象”(representation)将表明,欧洲从纯粹国关视角外显为“分”之历史时代,也存在文化学的“合”之内涵。那么,欧洲一体化运动中最为显著的“断裂”时代——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即民族国家兴起之时自然成了解读对象。
何谓欧洲文化族及其具象
什么是“文化族”(family of cultures)?它的解析要从文化入手。广义的文化是行为模式、物质客体、信仰、价值观等的复杂混合体,狭义的文化则限制在符号的或者说象征性的成分上。克拉克洪说,“文化是一种具体力量,由人创造,由人传播。文化像物理学概念一样,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抽象。人们从未见过地心引力,却看见物体以一定方式下落。同样,人们从未见过文化,见到的是行为规范或遵从共同传统之群体的人为产物。”“文化”在此是一个统称的抽象的集合名词。克拉克洪还说,“社会指一个群体,其成员间的互动大于他们与群体外个人之间的互动,其成员相互合作以达到共同目标。文化指这个群体特有的生活方式。”(注:Clyde Kluckhohn,“The Concept of Culture”,Kroeber A.L.& C.Kluckhohn,Culture: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N.Y.1963,p.73.) 在这里,“文化”又是与具体社会或人群相联系的单数名词,也就是人们说的“一种文化”、“某个文化”。
美国文化学家菲利普·巴格比指出,“几个通常在一起被发现的文化特质联合起来称为‘文化集结’,亦与心理学中的‘情结’相类似。然而,‘集结’和‘特质’毕竟仅仅是相对的概念。”(注:[美]菲利普·巴格比:《文化:历史的投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5页。) 他说,“‘一个文化’就是任意一个特定社会中发现的文化特性和文化集结的总和或集聚。”(注:[美]菲利普·巴格比:《文化:历史的投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6页。)可见,当具体可数的文化成为研究对象时,可以人为地将之进一步分解为文化的各个构成因素。
按照克拉克洪和巴格比的概念,“一个文化”本身就是各种因素的集结,而“文化族”则是数个相类文化构成的家族树。这样,对文化族存在与否的考察,也可以分解为对“族”中各文化所具备的同质因子的考察。对文化族的理解就如英国民族学家安东尼·史密斯所说的,“文化族”的概念类似于“语言族群”的概念,它们都以某几个因素为特征,这些因素并不是在每个对象的任一特例中全部显现,这里存在的只是各种因素构成的“族”,这些因素在若干实例但并非全部实例中相互叠盖和显现”。(注:Anthony D.Smith,“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Idea of European Unity”,International Affair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No.1.) 对于文化与历史的关系,克拉克洪指出文化是历史的积淀,在不止一个意义上指出历史是一个过滤器。(注:Kroeber A.L.& C.Kluckhohn,op.cit.,p.76.) 文化族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才形成的,通常是无预知和无目的的,是各个历史环境的产物,因此,它具有相当的持久性和稳定性。
“欧洲文化族”是史密斯将民族认同理论在欧洲建构中的应用,是他于1992年发表《民族认同与欧洲统一观》,讨论欧洲认同与民族认同、欧洲认同与全球文化的多重关系时提出的概念。他认为,欧洲文化族是在既成而顽强的民族认同以及正在兴起且无定性的全球文化之间的、一种早已有之、尚待认定且能够发展的重要建构,它包括诸如罗马法、政治民主、议会制度、犹太——基督教伦理之类的传统以及诸如人文主义、理性主义、帝国主义、浪漫主义之类的遗产。在这里,作为“一个欧洲文化”而存在的是由各种因素构成的文化族,其“族因”(elements)并非在各个国家和地区、各个阶段和时代全部显现,但是,在构成“欧洲”的地区和时代,却此时此地或彼时彼地、甚至有时交叠地最终全部显现。同时,欧洲文化族可以理解为在欧洲这个大社会中发展的数个特质类同的文化的集结。正像一棵大树,它的枝、叶、果各俱形态,根、基、类却是同一。在中世纪,欧洲文化族是具有各种同质因子的多个地方文化的集结;在民族国家兴起的时代,它是各民族文化的集结。这些文化中必定有一个个同质的、可以人为分解而加以研究的“族因”。这样,欧洲代表了一个支持欧洲文化族的扩散并使之在不同时空相互补充而得益的基地,它又是一个依时间转移而以不同民族国家为空间载体的各子文化不平衡发展的接纳地。
文化的功能是潜在的,其作用在于通过保持与过去的延续,使生活的某些方面具有熟悉性和可预知性;(注:Kroeber A.L.& C.Kluckhohn,op.cit.,p.75.) 同时,文化的成果又是外显的,它可以从耳闻目睹的事实中归纳出来。(注:Kroeber A.L.& C.Kluckhohn,op.cit.,p.78.) 文化本身就是历史的积淀,它的形成要经历无意识、下意识、潜意识(可以理解为文化的自在状态)和有意识(可以理解为文化的自为状态)的过程,这些过程是混合的。只是为了研究方便,我们可以区分无意识状态下的文化,如在人类演进过程中的无意识的传承、积淀以及有意识状态下的文化如绘画、地图之类的精神产品。而“具象”显然属于后者。
何为“具象”?从美学理论角度来说,“具象”强调艺术形象与自然对象基本相似或极为相似,(注:《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页。) 它来源于现实,注重人对物的体验,追求“事物存在”与“人存在”之间的联系。(注:张卫海:“具象绘画及其特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历史上人们根据自己对现实生活的理解而形成的地图、绘画等就是可视性“具象”(visual representations)。神话与传说基本上属于“幻象”(vision),它超越现实,是人们根据自己憧憬的生活之心理需要而创造出来的,(注:张锡坤主编:《新编美学词典》,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6—57页。) 与具象反映现实存在的特质不尽相同。但是,当超越狭义美学艺术而从更广阔的心理文化角度思考时,神话传说也是一种时代心理文化的表现,当人们把世代用语言传承的神话传说用图像表达出来时,这种“幻象”就转化为鲜活的、有考古历史学意义的“具象”。之所以把“具象”概念应用在对“欧洲文化族”的探讨中,是因为它可以从一个因有遗物可见从而至今仍有可视性实证材料的角度反映出“欧洲文化族”存在的不可颠覆性。
英国历史学家米切尔·温特以历史上的可视具象为材料, 讨论“欧洲形象”(European image),认为欧洲实际上是一个“就看你自己如何理解”(注:Michael Winter ed.,Culture and Identity in Europe,p.52.) 的概念,“欧洲”所包含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的涵义都在历史地变动着。同时,各个时代、各个地区的欧洲人用不同的地图、神话、绘画及其他艺术形式形象地描述了他们所理解的欧洲。这样,温特和史密斯对欧洲统一观的研究在方法和理论上就形成了互补:史密斯原创的“文化族”概念说明欧洲统一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温特展示的“具象”为不同时期的“欧洲形象”提供了生动且可视的证明,使诸如欧洲认同、欧洲观念等极为抽象的东西有了依据,成为“欧洲文化族”的最佳举证。
中世纪欧洲文化族及其具象
文化族就像一棵生命树,它不断成长变化,也在于“就看你如何理解”。这样,全面描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欧洲文化族,较之通过例举、分析它在各时代的族因及其表现更加具有可行性。
在古典时代民主政治、罗马法学、帝国制度等遗产的基础上,基督教成为中世纪欧洲文化族最重要的“族因”之一。历史上,基督教不为欧洲所独有,中世纪欧洲文化也并非仅为基督教文化。但是,诞生在中东的基督教在欧洲落叶生根并发展为占绝对优势的宗教则主要发生在中世纪。从希腊罗马的人神同形同性和多元人本,到一本圣经、一个上帝、一个教廷、一个教皇的基督教同一,基督教在中世纪为欧洲集体认同,从精神信仰、教会组织到甚至政教互补的制度构架方面,都提供了一种万物归宗的一元性。“欧洲”人以基督教信仰和宗教社团意识,甚至于以诸如十字军东征等极端形式,共同应对公元6—7世纪“蛮族”的入侵也同化入侵的“蛮族”,共同应对7—9世纪穆斯林的入侵也抗衡入侵的文化,在亚洲伊斯兰宗教文化认同和欧洲基督教宗教文化认同的对应中推进欧洲文化族的发展。那时,基督教随法兰克王国的建立从地中海扩散到高卢、德意志和不列颠,随奥托帝国的建立推进到中欧腹地与东欧部分地区,使“欧洲”这一概念在宗教文化方面有了更广的地域外延。在这种信仰一致的情势下,中世纪欧洲延伸出更多的共同性:大学教育重视基督教文献研讨,教学内容由教会决定;禁欲主义、王权神授、上帝秩序、彼岸希翼等伦理观念普遍存在。这种同一宗教的认同与当时基于村庄—庄园—地方社会的认同以及基于血缘和姻缘的王领认同并存,但宗教认同及其相关的制度力量在广度和深度上远远超过上述两个范畴。作为一种集体身份认同,它具有广博、弥散和持久的心理意识作用。因而,正是在中世纪第一次出现了“欧洲人”的称谓。(注: Michael Winter ed.,Culture and Identity in Europe,p.54.)
其次,中世纪欧洲文化族的另一重要因子是罗马教会。罗马教会在中世纪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宗教文化的外壳,也是制度文化的建构。当然,罗马教会和基督教密不可分,后者是一种思维与信仰,可感知而不可触摸;前者是一种物化机构,可感知又可眼见。公元597年教皇格里高利派密友奥古斯丁携40 名罗马教士前往欧洲最西部的不列颠岛肯特王国传教,建立坎特伯雷大教堂;(注: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11—13世纪罗马教廷组织十字军东征,为基督教认定其东部的文化地理边界。这些事实证明了基督教信仰—教会网络—文化排他意识三位一体的欧洲认同的存在。而在“三位一体”中,罗马教会把各地的基督教信徒组织起来,也就意味着把法兰克、查理曼和神圣罗马帝国的臣民从横向即欧洲文化地缘和纵向即欧洲文化传承方面凝聚在一起。随着基督教的扩展而在欧洲各地建立教堂和教区的漫长过程中,罗马教廷—大主教区—主教区—教区自上而下的层级社会管理网形成了,它与世俗政权既联合又斗争地分享着对欧洲人进行统治的权力:从国王加冕、主教任命到地方征税、文化教育无所不包。从世俗政治角度看,中世纪欧洲仍处于由庄园和王国构成的地方主义的分散状态,其忠诚感属于依封建主义层层分封而形成的大小领地;从教会制度文化的角度看,欧洲人社会生活时时事事处处又与教会发生着联系,其忠诚感归属于罗马教廷及其层级式网状教会。正因为欧洲绝大部分地区都处于罗马教廷统一的制度框架下,所以,无论在世俗政治方面是统一还是分裂,基督教通过遍布欧洲的罗马教会不仅寄托了欧洲人的情感认同,而且构成了欧洲社会管理和社会控制的制度建构。
第三,拉丁文的统一作用是中世纪欧洲文化族的“因素”之一。作为欧洲人引以为豪的古希腊罗马文化的载体,拉丁语在中世纪仍受到重视。蛮族入侵时,“最显著的现象是新移民对拉丁语这一更加丰富和灵活的语言的大规模采纳,由于无数‘蛮族’士兵与当地妇女成婚,其结果使得拉丁语在许多场合下成为他们后代的母语……在短短几个世纪内拉丁语遂成为各地通行的语言。”到8—9世纪,欧洲语言的两种趋势是:一方面从古典拉丁语中产生了纯正准确的拉丁语。艾因哈特在《查理曼传》中道,查理曼对拉丁语之纯熟达到了与母语不相上下的程度,(注:[英]菲利普·沃尔夫:《欧洲的觉醒》,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3页。) 他把拉丁语作为施政和礼拜仪式的专用语言,使《圣经》拉丁文本得到修正和传播。(注:[英]菲利普·沃尔夫:《欧洲的觉醒》,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72页。) 到9世纪拉丁语成为“正统的书面语、教会语、文化和行政语以及欧洲统一的一个因素”。另一方面,欧洲各地各种处于口头阶段、缺乏语法规范、未定型的本土语言与拉丁语并存,它们只能以方言的形式结晶成形,(注:[英]菲利普·沃尔夫:《欧洲的觉醒》,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74页。) 在这些多样性的方言中也存在着一种语言的亲合性。中世纪出现的三次文化发展高峰——9世纪加洛林复兴、10世纪奥托一世复兴和12世纪文艺复兴——都偏重于复兴古典拉丁文化和推进对拉丁文的研究。总之,拉丁文在中世纪欧洲中上层社会的普及和延续,对古典时代“欧洲文化族”因子的保存、中世纪欧洲文化族的发展与近代早期文艺复兴的兴起都至关重要,它从语言学角度在横向上把欧洲不同地区加以链接和聚合,在纵向上把欧洲文化认同加以巩固和传承。
除了表现为宗教、制度、语言等文化功能的隐形形式外,文化现象往往还以各种外在形式充斥于耳闻目睹的历史事实中。中世纪欧洲文化族的外现形式之一就是表面关联不大的世俗强权即欧洲帝国。
法兰克国王克洛维及其子孙历经三个世纪的征服,以巴黎为中心、使用基督教和拉丁语、采邑制和封建主义,营建了主宰西欧三个多世纪的法兰克王国。732年查理·马特领导了阻止穆斯林人入侵西欧的普瓦蒂埃之战,标志着法兰克人成为基督教的捍卫者;马特之孙于公元800年接受罗马教皇加冕,成为“查理曼大帝”,征服萨克逊人并使之皈依基督教,取得了伦巴第,解除了对教皇的威胁,在比利牛斯山外建立基督教帝国和穆斯林西班牙的缓冲地带,建立了包括现今法国、德意志大部、低地国家、阿尔卑斯山诸国、比利牛斯山外区域、意大利北部以及中欧地带的欧洲基督教霸权,(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1982年版,第107页;[美]沃莱斯特:《欧洲中世纪简史》,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88页。) 在西临大西洋东至易北河, 北起北海南到中意大利的“欧洲”,行使帝国的巡回制度和推进统一的文化教育事业,使欧洲大陆的联系得到加强。查理曼大帝也被臣民尊为“欧洲之王”。(注:Michael Wintle,op.cit.,p.54.)
继承东法兰克王位成为萨克逊第二代国王的奥托一世继续推进统一欧洲的梦想:955年在莱希战役打败匈牙利马扎尔人,后又征服意大利王国;962年接受罗马教皇加冕,建立了中世纪第二个欧洲世俗强权神圣罗马帝国,把基督教欧洲的疆界往东推至匈牙利、波兰;1033年奥托二世向西取得勃垠第,使版图进一步扩大。在中世纪德意志人神圣罗马帝国极盛时期,其领土北起波罗的海南到西西里,东起匈牙利、波兰,西到勃垠第、尼德兰。奥托帝国继承查理曼的传统:利用教会的权威巩固统治,促进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同时又用日耳曼人的尚武习俗、探险精神增添欧洲文化内涵,对于欧洲认同的形成不无积极意义。
这两个帝国无不以武力为后盾,但当人们从欧洲认同角度来探讨世俗强权时,两帝国作为欧洲人的共同经历就内化为一种欧洲追忆和历史,为欧洲人共有和缅怀:它们至少是古罗马帝国后把欧洲绝大部分地区统一起来的一种尝试。
总之,上文例举的中世纪欧洲文化族各要素,都充当了整合欧洲的统一因子。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文化族的存在无声无嗅,不可捉摸,无以名状。这样,中世纪欧洲人的地图、漫画、插图、艺术作品等可视性“具象”就成了透析时人心路历程和观念形态、或者说透视该时代欧洲人对欧洲共同“幻象”的遗物。这些呈现为碎片的“具象”,或者用陈乐民、周弘先生的话即“感情代号”,(注:陈乐民、周弘:《欧洲文明的进程》,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63页。) 是知识分子“用自己的头脑升华了或提炼了同时代普通人的、零星的、不自觉的想法”,(注:陈乐民、周弘:《欧洲文明的进程》,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71页。) 它们表明欧洲作为一个整体的观念显然在中世纪已经存在。
具象例举一:《旧约全书·创世纪》第九、十两章记述了诺亚及三子在洪荒后幸存并分得大地的故事。据说诺亚醉酒后裸体躺在方舟里,儿子“含”见后不闻不问,只告知两个兄弟,而“雅弗”和“闪”背对着进去为诺亚盖物遮体。诺亚醒来后说,“含”的孩子将成为其仆人,“雅弗”将长大并居住在“闪”的帐篷里。洪水过后,地球就这样在三个儿子中划分了。后来这个故事成了三大洲的神话起源:“闪”是犹太人和闪米特族的奠基人;“含”的后代接管了亚洲;“雅弗”的后代占有欧洲。对此,陈乐民先生精当地解释道,“闪居住的地方大概是耶路撒冷一带,而雅弗(欧洲先民)本来是异教徒,后来其子孙反而成为基督教的捍卫者,以至于要“挤进闪的帐篷”。(注:陈乐民:《“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4—6页。)它反映了中世纪欧洲人对欧、亚、 非三大洲不同的信仰和文化以及彼此间关系的认知和与此相关的地理学观念。7世纪塞维利亚主教艾西多尔制作的中世纪典型的T/O型地图显示了这种“欧洲观”:地球是一个被大洋包围的圆形平面,由顿河、尼罗河及地中海分割成欧、亚、非三个大洲,分别以雅弗、闪和含的名字标注,欧洲占世界的1/3。(注:Michael Wintle,op.cit.,p.68.) 这幅强调上帝主宰、格局稳定、宗教含义深刻的地图表明,中世纪欧洲人已经把地中海以北、顿河以西看作是一个整体即欧洲。这样,通过T/O型地图作为可视性中介, 把诺亚一雅弗—世界最好的三分之一这三者联系在一起,有助于欧洲人自我形象的形成。
近代初期的欧洲文化族及其具象
近代早期,从内部看,欧洲宗教改革推进着宗教观念和教会组织的民族化,地方王国在内部族裔整合和外部民族对抗中过渡为君主制欧洲民族国家。百年战争使英格兰人退出欧洲大陆,使法兰西人消弭内部分裂,从而“更深刻地意识到他们之间的民族差异”。(注:钱乘旦、许洁明:前引书,第81—82页。) 三十年战争及《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欧洲民族国家的疆界和主权。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的欧洲政治地理基本确立,欧洲不再是一个众多地方王国拥戴一个教皇一个教廷,甚至有时是一个帝国一个皇帝的欧洲,它更多地体现为民族国家认同和民族文化各异的欧洲。从传统国关理论看,这是欧洲历史上显著的“分”之时代。
从外部看,1500年后在世界发展为一个整体的过程中,欧洲通过地理大发现、海外殖民、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在创造西方文明中开了先河,这显然是欧洲的共性。而且,兴起于西欧,向中欧、北欧和南欧推进的工业文明,尽管在不同国家因时因地而发生变异,但毕竟建构了殊途同归的欧洲工业社会,又一次引领了近代世界的发展。(注:许洁明:《殊途同归:近代欧洲工业文明的兴起》,1998年云南人民出版社版,前言。See Jordan Goodman,Gainful Pursuits:the Making of Industrial Europe 1600—1914,London 1988,introduction and conclusion.)问题在于,在近代民族国家兴起和多元民族文化发展的背景下,古典民主政治理念的和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欧洲遗产仍然存在吗?欧洲的共性与各民族多样发展是怎样的关系?对于中世纪帝国—基督教—罗马教会“单一”欧洲的历史是断裂还是延续?倘若两者皆有,那么何为主流何为底蕴?答案的关键仍当在于对近代早期欧洲文化族及其具象的探讨。
近代早期的欧洲强权作为欧洲统一的外在形式仍然体现着欧洲人的梦想。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五世于1519年当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帝位带来了原法兰克帝国东部走廊地带,他从父亲勃垠第公爵菲利普手中继承了尼德兰、奥地利和法兰西大部,从外祖父母西班牙的斐迪南和伊莎贝拉手中继承了西班牙、北意大利等。这样,查理五世统治的神圣罗马帝国把现今的南欧、中欧与西欧连成一片,使之共为哈布斯堡家族“日不落”帝国国土。直到1556年查理五世遁入空门,庞大的帝国才在其弟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其子西班牙国王之间一分为二。(注:郭华榕、徐天新主编:《欧洲的分与合》,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88、118页。)
路易十四代表了17世纪波旁王朝统一欧洲的抱负,虽不曾拥有查理五世那样的皇帝头衔,但他对欧洲科学文化的贡献不可小视。巴勒克拉夫说,从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观点看,路易十四给一大批欧洲诗人、艺术家和学者颁发的奖金,比他进行的战争更为重要;他的凡尔赛宫建筑方案及对各种学院的资助成为欧洲其他君主效法的榜样;法语变成全欧洲有教养阶层的语言,并帮助创造了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的世界文明。总之,此类短暂的世俗强权在以民族国家兴起为主流的近代早期对欧洲统一继续产生着影响,而强权君主的抱负则牵引着欧洲人在思想和感情方面的同一纽带。
同时,欧洲文化族的统一因子仍在发展,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就是显例。文艺复兴这场名为复古实为创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很快成为一种欧洲普遍现象,从整体看,它可分为个三阶段:14—15世纪为第一阶段,中心在意大利;15—16世纪为第二阶段,扩及欧洲西部和南部,在英、法、德、荷、西先后出现高潮;17世纪上半叶是第三阶段,波及欧洲东部和北部。这样,文艺复兴在欧洲各国发生的时间、推进的形式和产生的结果不尽相同,但人文主义、世俗主义在不同程度上渗透到欧洲各国的文学、艺术、哲学、宗教领域,以巨大的震撼力使欧洲人对现实生活有了新的诠释。在古典文化复兴(同一)与本土文化发展(各异)的交织中,在中世纪欧洲文化族的基础上,欧洲人共享的成分增多了。
宗教改革是欧洲多样发展时代之同一性的另一表现形式和重要基础。当文艺复兴作为共有遗产而被欧洲各民族分享时,当人文主义等近代理念在欧洲各地辗转传播时,各地区各民族的本土世俗文化得到充分释放,培植了近代欧洲文化族的另一个因素即宗教改革。威克里夫、路德、伊拉斯谟、慈温里、加尔文等以对基督教人文主义的研究为出发点,走上了批判中古基督教神学的道路,(注:Hermann Kinder and Werner Hilgemann,The Penguin Atlas of World History,London 1978,Vol.1,p.231.) 促发了以宗教信仰近代化和教会组织民族化的改革。无论改革后的信仰向度是路德宗、加尔文宗、安立甘宗还是通过“反宗教改革运动”(注:柴惠庭:《英国清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21—25页。) 变化了的近代天主教,无论改革后建立的教会组织是苏格兰长老会制、英格兰层级主教制还是日内瓦集权共和制,宗教改革都普遍地否定欧洲中世纪农业社会的世界观,为欧洲的近代化从观念和制度上廓清了道路,这就是宗教改革的欧洲同一性。
宗教改革所带来的从宗教教派到世俗政治的分裂也触及欧洲许多地区、民族和国家,使欧洲在“分”之表象下出现多元发展趋势。在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区、各教派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否定中世纪基督教的同时,欧洲统一的中古基督教民族化、世俗化、人文化、近代化和分散化了,呈现出以改革为原点各自建构近代理念和制度体系的散射状。各国各地程度不同的宗教改革具有强烈的本土风格和时间上的共时性,它在欧洲文化地理上造成的局面是:第一,纯粹信奉一种新教的地区并不多。严格地说,只有普鲁士等北德意志邦国、波罗的海沿岸、北欧地区包括冰岛在内基本上成为路德教地区;瑞士和荷兰成为加尔文教地区;英格兰威尔士成为安立甘教地区。但是,宗教改革的影响并非仅仅停留在确立了新教主流地位的国家和地区。法兰西经历了1562—1598年“胡格诺宗教战争”后,虽然最终“保留了天主教,但是在政治和文化上对新教少数派给予了宽容”。(注:Hermann Kinder and Werner Hilgemann,op.cit.,p.247.) 第二,纯粹的天主教国家和地区也不多,只剩下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爱尔兰。更何况,在反宗教改革运动中天主教本身也经历了变化。第三,不少地区特别是中欧成了新教和天主教或者不同新教教派甚至是东正教和犹太教的混杂地区,较为典型的是波兰、立陶宛、匈牙利和奥地利。总之,在宗教改革中“中世纪的整体性被打碎,每个民族在这团乱麻中都在寻找自己的政治出路”。(注:陈乐民、周弘:《欧洲文明的进程》,第114页。) 尽管这似乎意味着“各异”,但是,作为宗教改革过程自身和中古基督教的近代化这一结果,则是欧洲的共同经历和共同趋势。
上文对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欧洲性”之剖析说明,尽管“从近代民族国家兴起以来,民族的身份识别逐渐成为文化和政治的规范,其规模和力量超过其他忠诚圈。”(注:Anthony D.Smith,op.cit.,p.58.) 但是,在以民族认同为特征的多样发展下,近代欧洲文化族显然存在,也就是说民族认同与欧洲认同在一般情况下是能够和平共处的同圆心忠诚圈。简单地说,作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其经历和体验不尽相同,但当他们都作为欧洲人时又有了共同的经历和体验,这些经历和体验在近代民族国家兴起时同样构成了欧洲文化族的因素。只需使用单一欧洲的研究视角,就能发现同一的欧洲文化底蕴。基督教文化的发展就是显例,“文艺复兴并不否定宗教,而是促进了宗教的人文化;民族国家也不否定宗教,而是使宗教民族化了”,(注:陈乐民:《“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第89—90页。) 基督教在经历改革和反改革的重重波涛后保持了活力,基督教文化中内含的原罪与救赎、普世主义等思想仍然存在,只是随时代的更替而有所变化而已。米切尔·温特指出:到14世纪,“欧洲”和“基督教世界”已成为两个可以互换的概念。(注:Michael Wintle,op.cit.,p.55.) 欧洲文化族在新时代的发展也能在具象方面有所明证:
具象例举二:关于欧洲的起源神话,古典作品奥维德的《变型记》描写道,腓尼基蒂尔城国王之女欧罗巴被劫持而坐在宙斯变成的公牛背上,他们游到克里特岛,繁衍了欧洲人的先祖。一直到文艺复兴后期以此为题材的关于欧洲起源的绘画仍然存在,只是中世纪,被劫持少女欧罗巴演化为了头戴王冠、代表欧洲、充满自信的女王形象,该形象的典范之一是奥地利摩拉维亚城堡画家僧侣汉斯(Hans Mont )于16世纪80年代创作的湿壁画。“湿壁画中描绘的女王就是和公牛在一起的欧罗巴。但是,从她胜利者的姿态看显然代表着欧洲大陆”。(注:Michael Wintle,op.cit.,p.77.)
具象例举三:16世纪初约翰内斯·普特兹把欧洲绘制为一幅头戴王冠身着礼服的女王图:头部是16世纪欧洲哈布斯堡君主国的中心伊比利亚半岛,躯干囊括西欧和中欧,右手是意大利,裙子覆盖北起立陶宛南到保加利亚和希腊的整个东欧。(注:Michael Wintle,op.cit.,pp.81—82.) 这幅女王形象的欧洲地图既反映了民族国家兴起时代欧洲国家的自我认定,又反映了属于基督教文明的各国仍共同构成一个休戚相关的整体。后来女王型欧洲地图的中心一直在移动:1588年捷克版本中波希米亚成为欧洲中心即女王挂在胸前的金币;1589年纽伦堡制作的银碗上所画欧洲地图又把纽伦堡作为欧洲中心。这正是民族国家兴起时民族认同和国家意识的表现——几乎每个有实力的民族国家都希望自己成为欧洲的中心。但是与此同时,这些女王形状的地图又表明欧洲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具象例举四:世界地图中也反映着欧洲人同样的心理意识。1572年安特卫普版《世界概览》扉页有一幅亚欧非美四大洲的拟人插图,其中只有欧洲戴王冠端坐上方;18世纪初杰拉尔德·冯·库愣绘制的世界地图中端坐左上方的欧洲女王戴王冠持节杖,接受其他大洲的进贡,战马在她身后,智慧书在她手旁,把欧洲中心论和帝国主义表现得淋漓尽致。
地图实际上是一种装扮为客观科学文献的文化表述,上述绘画和地图至少说明,在近代早期,尽管欧洲人看到民族国家兴起时代的“分”,但欧洲仍然作为一个整体而进入人们的观念,这种集体文化心理因素证明了欧洲文化族的存在。
结语:欧洲统一中断裂与延续的辩证
总之,从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欧洲经历了围绕主权国家兴起出现的多样性发展,诸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欧洲共同经历构成了多样性的统一,充实和发展着近代欧洲文化族。陈乐民和周弘先生在《“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欧洲文明扩张史》、《欧洲文明的进程》中强调,“欧洲观念”是多样性和同一性的结合,“‘欧洲文明’有它的共性,同时又同源异流。”“‘欧洲文明’就其整合性可见其宏观上的‘同’(identity),由此产生‘欧洲主义’。就其支脉的分殊性又可见其微观的‘异’(diversity),由此产生‘民族主义’”。所以,欧洲文明中含着认同中有多样性(diversity in identity)和多样中有认同(identity in diversity)的综合概念。(注:陈乐民、周弘:《欧洲文明扩张史》,东方出版中心1999版,第4页。) “通常在使用‘欧洲观念’这个概念时,多侧重于它的一致性、普遍性。”(注:陈乐民、周弘:《欧洲文明扩张史》,东方出版中心1999版,第301页。) 民族国家兴起时代的欧洲,尽管民族认同逐渐上升,但中世纪留下的作为欧洲认同之思想底格或者说心路历程的文化族并没有消失,近代早期欧洲的经历如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宗教改革和世俗主义、启蒙运动与理性主义又进一步成为欧洲文化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只要欧洲文化族存在,就能找到把欧洲人区别于他人的集体特征。这种延续是最为本质的,此其一。
其二,以“帝国”形式出现的欧洲霸权,无论是征战或移民的结果,还是教皇加冕或王权继承的结果,都很难持久且相互间显现为一种断裂形式。例如,查理曼帝国可能内连着罗马帝国统一欧洲的理想,(注:陈乐民、周弘:《欧洲文明扩张史》,东方出版中心1999版,第43页。) 但它们毕竟是两个毫无关系的政权。奥托帝国之于查理曼帝国、查理五世帝国之于奥托帝国、路易十四帝国之于查理五世帝国、拿破仑帝国之于路易十四帝国,莫不如此。但是,它们对于欧洲整合而言也很重要,正如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军事征战对民族地域认定和民族情感强化的作用一样。相对于未必有延续性的帝国,文化族的影响深刻且延续,它辗转和渗透于欧洲各个时期和许多地区,尽管从来没有哪个文化运动呈现地毯似覆盖和共时性渗透的特征。
其三,倘若既从文化现象的外显如物化制度建构,又从文化功能的内在如心理意识的关联看,欧洲历史上不存在绝对意义的断裂,即使在呈现为“分”之表象的民族国家兴起时代也并非深层文化学意义上的“同一性”断裂;欧洲历史上也不存在完全意义的延续,即便“文化族”作为维系因子得到传承发展和与时俱进的建构,但这种延续也主要是在“根”之意义上的延续,它无法掩去近代尤其是19世纪末欧洲政治地理学意义上的分裂。延续的基础是过去,是传统,但它在本质上面向现实面向未来。克拉克洪说“文化是我们的社会遗产”,“是思考、感觉和信仰的一种方式。是储存在人们的记忆、书本和客观器物中以备将来之用的群体知识。”(注:Kroeber A.L.& C.Kluckhohn,op.cit.,p.72.) 当民族国家兴起时,欧洲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在制度上外显为民族国家体制的建立和国家间均衡观念的产生。但是,作为历史积淀的文化族延续了下来,增添了新的时代内容,上文例举的具象难道不是代表吗?在某些时候甚至断裂的表象和延续的内涵是共时的。欧洲一统的观念在民族国家兴起的时代显然选取了一种隐在形式,被多样发展的民族国家的文化主流所遮蔽,到19世纪末几乎细如游丝,以至于在政治地理和国际关系上表现为争斗和分裂的局面,然而,作为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的“延续”淹而未灭,这就是为各种具象所证实的欧洲文化族。
第四,欧洲文化族无疑是今日欧洲一体化的基因,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经济、政治、社会、公民甚至安全和外交各方面逐一建构的欧共体/欧盟的心理文化底蕴。文化族在其各因素相继出现、发展和抽象为一个概念的过程中,在历史学家使各个“族因”又人为回归到具体时代和场域时,都具有时空二重性。当回溯“欧洲文化族”发展过程时,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古典时代是它的雏形期。中世纪是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阶段。到了近代,“文化族”在继承古典遗产、中世纪精髓的同时,也随着近代世界的发展而更新而变异;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在近代早期民族国家兴起之时,尽管庄园—王国—教廷的三级式基督教普世主义的欧洲,在各地区的族裔整合基础上开始分解为渐具各自特征的民族国家,在政治地理表征上出现一个由“合”到“分”的过程,欧洲文化族被一度气势磅礴的民族文化认同所遮蔽,但它毕竟只是一种促其变化的冲击力。今天,人们为在心理学和文化学方面推动欧洲一体化而采取了种种政策:制定欧洲日、欧洲旗,设立欧洲公共课程,开展欧洲公民建设等,(注:Cris Shore,Building Europe: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London 2000,pp.44—65.) 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在历史积淀基础上“发现”并强化欧洲一统的观念,培育欧洲人的集体认同。这时,从欧洲文化族及其具象片断的研究中找回欧洲人共享的一种精神、一个信念和一统理念,未尝不是建构“新欧洲”的任务。
标签:文化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基督教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英国宗教改革论文; 西欧中世纪论文; 罗马市论文; 中世纪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