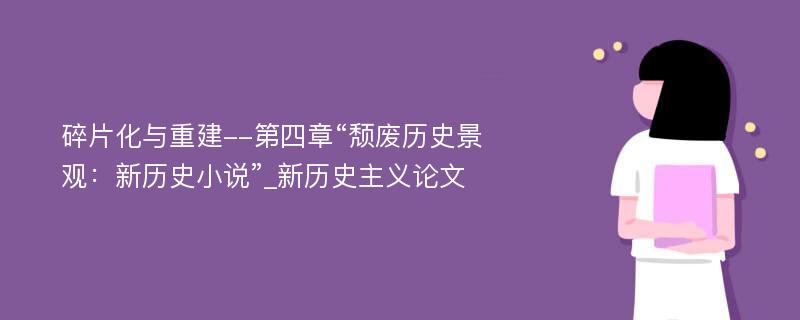
破碎与重构——第四章,颓败的历史景观:新历史主义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主义论文,颓败论文,第四章论文,重构论文,景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一节:新历史主义小说描述
我们现在也许有理由认为,九十年代前后, 确切地说是1989 年到1992年这段时期,最值得文学史记忆的文学现象,莫过于先锋派作家与新写实作家不约而同地遁入“历史”,以致形成被称为“新历史主义”的小说潮流。〔1〕
先锋派作家曾经凭藉独特的形式实验冲出文坛的地表,到了此时他们形式上的挑战性有所收敛、退化,全面性地从形式走向“历史”。苏童写了《米》、《妻妾成群》和《红粉》;格非完成了第一部先锋派的长篇小说《敌人》;就连执著于现实性的形式实验的余华,也创作了《一个地主的死》、《活着》及被誉为最具先锋派个人记忆特色的《呼喊与细雨》;叶兆言的《十字铺》、《半边营》则继续抒写着秦淮河畔的历史颓败故事。
新写实主义的旗号虽然迟至于1989年才亮出,但人们津津乐道的新写实代表作《风景》、《烦恼人生》及刘恒的食色系列,都在这之前问世。他们从现实原生态转向历史本相是在九十年代之初,如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温故一九四二》,刘恒《白日苍河梦》,方方的《祖父在父亲心中》,池莉《预谋杀人》,杨争光《黑风景》、《赌徒》、《棺材铺》,李晓《相会在K市》、《叔叔阿姨大舅和我》、 《民谣》等等。佳作联翩而出。“历史”吸引了这个时期几乎所有充满创造力想象力和富有思想的作家,成为当代文学最激动人心之处。这里,每部作品所触摸到的历史不仅不同于正统的教科书,而且各不相同,独特的历史叙述汇集成极富内蕴的苍茫人生与诡秘的历史世界,寓言式地表达了作家对生活世界及自我的理解。
“新历史主义”这个称谓大概受启于八十年代美国一种新兴的文学批评样式,但新历史主义小说与美国新历史主义批评并没有直接和实际的联系。新历史小说几年来一直在沿续,只不过特定的文化语境引发了更多的作家趋向“历史”,从而形成新历史小说趋向中的一个阶段性的高潮。如果说西方兴起的新历史主义批评,是对形式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学批评的主动反拨,那么新历史主义小说则是特定文化语境下的被动逃遁。从直接的文化语境看,1989年的社会动荡对当代文化是一个强烈的刺激,随之而来的文化审查和意识形态控制,客观上促使文化自身进行调整。新时期以来逐渐解脱的政治依附心态和逐渐加强的个体人格的作家,也因文化氛围的过度紧张而彷徨失措,文学面临着存在方式的再选择。历史叙事正好提供了一个远离现实而又不为意识形态中心完全识别排斥的话语空间。从这种意义上说,新历史主义小说隐含着对特定政治文化的回避与逃遁。
不过文学的这种回避方式并不是纯粹的消极,其实作家在徒具时间标示的“历史”中,刻意重复他们当下体验到的创作性情绪,隐晦地表达了他们的自我救赎与文化救赎。对先锋派而言,曾经形式上的肆意颠覆退化为相对稳定的叙述形态,“历史”就由叙事话语的原材料而转换为历史叙事,从而由失落年代的解构性话语,逐渐走向寻觅历史与文化中人性的幽微之处。而对于新写实群体,从现实生活的原生态到民族历时生存状况,由现实人生的情感零度转化为时间距离的冷静,既排除了现实喧嚣的心态也便于主体文化性的介入。因此重新书写历史,既可以在权力话语的强势下拒绝认同教化世界的精神建构,又可以暂筑一块个体写作的有限自由空间;既能在法权社会实现自我,满足创作主体的言说欲望与精神需求,也维护了文学本身的延续和发展,实现作家的文化责任和使命。
在具体分析新历史主义小说之前,应该注意的是,正统的历史与叙述关系中的唯科学主义话语体系,在异质文化冲击下,经过前期新历史小说的思想质疑和形式颠覆之后,已经全面失去文化霸权的地位而分崩离析。体现在历史意识上,历史决定论已经成为过时的神话。所谓的历史决定论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变易是受特定的历史规律或演化规律支配的,人们透过种种历史表象可以发现这些规律,并以此为据预言人类的必然未来。这种寻找历史阿基米德点的自信在十九世纪近代科学所向披靡中达到的颠巅状态。而二十世纪末的思想家普遍地把这种历史领域的唯科学主义作为乌托邦式的臆想。因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研究对象、实验方法及测试结果的可信度上都不可同日而语。自然科学运用主动的实验向对象提出问题,使对象作出回答,以检验修正和发展主体的假设和理论,而作为对象的历史,无法应答主体的质询,也不限制和拒绝强加于它的规则和理论。科学并非万能,人的理性有限,关于这一点康德早就警示过世人,可是“只有当这样一个结论为科学所裁定时才可望被人们认真的接受。在本世纪由于海森伯在物理上,哥德尔在数学上的发现,科学终于赶上了康德。”〔2 〕人与历史的关系不可能象自然科学那样,把人投影在对象的意义和象征全部抹去,而将其目的性直接地加之于中性和异在的对象上。
现代精神分析学也告诉我们,人类理性乃是作为动物的人长久历史性文化建构的产物,人的精神根须仍伸展下去达到其原始的土壤。正是在上述这些思想文化的背景下,新历史主义把自己的目光、也希望读者的目光从外在的历史社会转向历史世界中的个人命运,以个体无常的命运历史替代社会必然性的历史,以日常生活中的随机性与不确定性替代理性社会的规整性。同时把关注的焦点从社会人生转向人的内在世界,突入人的理性盲区,揭示人自身的有限性。他们不无残酷地揭去以往人类关于自身认识的各种幻想,逼进人类生存的本相;搅动理性阀限之下的非理性淤泥和集体无意识的文化沉淀,为完整的人提供并不完美的艺术例证。
第二节:晦暗的人性
对于人自身的关注,贯穿着整个新时期以来的文学,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不过审视的层面、视角及参照系却不断变换。先锋派作家楔入人的内在深层,显然是发自现代人对自身的疑虑,他们似乎想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人是什么的问题。因为以往关于人的阐释,只限于人的疏明之处而无视幽暗之地,就是说仅仅限于理性调节阀限之上的部分,而人自身被压抑和被遮蔽的非理性部分,作为社会性的禁忌,全然遭到有意或无意地忽略和歪曲。但他们的文本过于形式化、抽象化和理念化。当他们转入历史世界之后,形式上的挑战性有所收敛,虽然他们仍旧关注人的内在世界,但毕竟将人的内存在投射在历时的动态过程上,至少在文本表层,是通过生命客观化的形式来表现那些被压抑和被扭曲的心灵,揭示幻想意识的自我。
一、被压抑与被扭曲的心灵
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再也没有比无意识这个发现更为重要的了,他为理解完整的人铸造了一把开启人性和人的本质奥秘大门的新钥匙。尽管精神分析学在登堂入室之后,没有为正常的人找到更多令人信服的发现,但其体系对西方维多利亚时代留传下来的许多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进行了无情的冲击,并促进了西方人文思想领域与自然科学的进展保持大致的步伐。正是从精神分析学对现存思想和偏见的挑战性上,我们看到新历史主义小说对于幽暗的无意识世界的进掘。
关于人类无意识世界,我们迄今知之甚微,而且艺术作品中的每个人物的内心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每个人的不幸也不尽相同,故此本人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具体文本及人物的阐述上。首先提及的是苏童的《米》,因为它一反作家过去的优雅俊逸而呈现出粗粝狰狞的面目,格外显眼。小说中五龙的生存本能和人最低限度的尊严遭到社会“操作原则”的额外残害,他自身生命机体的内在保护层不堪负重地压制着生存本能的正常释放,从而严重地扭曲了他的精神人格。五龙忍辱负重,终于熬到接管米店并成为地方帮会组织的头目,他的各种畸变的本能与破坏欲望也就同时找到喷发的契机。他本能的破坏性由自我转向外部世界,以变本加厉地施虐方式补偿曾经受虐的缺撼,甚至连妻子和情人也成了他复仇发泄的对象,这种破坏性的报复似乎成为他全部人生的内容。而这种生存本能的病态扩张必然导致死亡本能的替代性回应,他不仅加速了他自己的毁灭,还殃及家人后代。
苏童并不是对五龙这个人物进行静态的精神分析,压抑——报复——死亡的生命动力构形,在天灾人祸的动态历史情境之中生成转换。这个人类的孽种向人们昭示,贫困可能积蓄苦难、挣扎和反抗,也可能通过人类心身的残损而外在地滋生罪恶,生存需求的匮乏本身不见得是一种天然道德优越感的标示,逾越限度的内在压抑可能转换成损害文明的外在破坏。
周梅森的《孤乘》从他稳态化的“煤矿系列”和“战争系列”逸出,把历史的苍凉感投射在江南小城轿帮帮主卜守茹身上。从表层上看,卜守茹一手制造的父毙夫亡的惨祸,是她心态扭曲后的一种残酷的报复。由于她的爱欲遭到她父亲的无情剥夺,而金钱与权欲的膨胀又是其父亲剥夺她的造因,她只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其实,深层地辩析,卜守茹的金钱欲与统治欲比其父、其夫还要强烈,只是她自己不曾觉察。这个具有极强生命欲求的女强人,凭借爱欲被剥夺的生命理由,虚构“合理”的动因,并以此唆使自己不惜一切手段进行报复,以报复的行为满足金钱欲与统治欲。她上通镇守使,下达帮门无赖党徒,终于垄断了小城的轿行,达到连她自己也不想知晓的生命目的。只是到了所有的辉煌被改朝换代的炮声震碎,她才对孑然一身的命运若有所悟。
与其说卜守茹不仁不义、不忠不孝的行为是生的本能过份压抑造成的心灵扭曲的结果,毋宁说是异化的产物。精神分析学的“快乐原则”是针对个人的心理症候而言的;而异化学说是指向社会无意识,其被压抑的心理领域针对社会成员来说具有相似性质。特定时空下的中国女性,与金钱与权利无缘。以社会禁忌为名义的“操作原则”形成严密的心理过滤器,隐秘地编织在社会成员的内心。卜守茹把不可告人的欲念深藏在内心深处,直至这些可怕的欲念以异变方式逸出自我意识而外化为残忍的报复行为,并完全蚀空了她的人性仍不自知。
叶兆言的《半边营》,阴湿窒息的颓败氛围类似张爱玲的《金锁记》。小说中古怪无常,多疑阴鸷的华太太,在极力撑持奄奄一息的家族同时,也在无意识的加速它的灭亡。华太太因命运的不幸毁了一生,她又乖戾地造成儿女的不幸。她的悲剧源自性别角色与历史文化的错位。本来,传统宗法制对女性的社会角色规定,是在家从父、出嫁从夫。而她在家就因独生而充当儿子的角色,出嫁后由于丈夫的懦弱而独撑即将败落的家族。她一生都孤独地处于冲突和挫折的紧张情境之中,从而酿就了畸形的反常心态。一方面她对外界冷漠地放弃信任,对他人无端地猜忌多疑;另一方面对儿女冷酷专横,盲目地窒压和妨碍她们的正常生活,以掩饰内心的虚弱,替代性地缓解自己因生活不幸而造成的自我压抑。不幸的生活残损了华太太的生命结构的内在平衡,而心态失衡又蚀尽了她作为长辈而应有的人性。这种由外至内,再从内到外的反常流程,投射在代际关系上就形成循环式的历史悲剧。
毫无疑问,与现实生活发生错位的华太太的自我,本身就是一种分裂状态的自我,意识形态化的传统文化,对家庭女性的价值定位在于屈从男性的女性人格,以荣格的话讲,就是极力排斥女性本体中的男性人格,这种社会意识形态的个体定位被普遍的内在化。而华太太无法扮演他人期望的女性角色,她的生存处境使她无夫可依,不得不扩张潜在的顽强而坚执的男性人格,这使她的自我处于长期紧张的张力情态之中,形成变态的心理趋势。无论是内存在还是外行为方式,非男非女、亦男亦女的双重人格搅得这个家庭鸡犬不宁暗无天日。
在这述三个文本中,作家显然是将无意识的东西当作能意识的东西加以思索,可谓“哪里有本我,哪里就有自我”。不过他们所体现的无意识的涵盖面大大超过了弗洛伊德所界定的具有泛性论倾向的本能界域。一方面,额外压抑五龙、卜守茹和华太太他们生命本能的凶手,包括自我、他人、社会、文化等等;另一方面屈从生命本能的攻击性也以扭曲和骇人听闻的形式肆意残害和破坏他人的生命及社会文明。就前一方面而言,小说体现了历史世界普遍性的生命压抑和人性残害,这种压抑和残害如此深重而广泛,以致于人物并不象通常期望的那样,把这些压抑和残害作为过去的经历来回忆,而是把它们作为当下的体验来重复。不过作家着重叙述的是人物变态心理及其支配下的反常行为,如果我们把五龙、华太太及卜守茹的畸变人性作为集体的心理症候,就可领会叙事话语中隐喻的“讲述话语的年代”。就后一方而言,小说遗弃了惯常的历史观念,这种历史观念认为,历史世界的灾难源自外在于人的社会制度或者人的有意识思想。而新历史主义把透视的光线投射在人的无意识深层,惊异地揭示内投于心的压抑残损,在人无知无能的情境中扭曲成恐怖的攻击性,而且释放出来的能量对人类文明构成巨大的破坏性。历史世界的灾难原来很大程度上就是人类自身制造的。
二、虚幻的自我意识
提及自我,应说明它在哲学上与心理学上的差异。从哲学上讲,自我是表示人的个体性,主体性和自觉性的概念,指“人能够意识到外部事物(包括他人),又同时意识到自我(有自我意识),意识到自己即自我”,就理性思维而言,自我是认知主体,属精神实体。〔3 〕从心理学上看,自我是个体内心代表理性和常识的部分,它“是受知觉系统影响经过修改来自本我的一部分。”〔4 〕新历史小说在探问人的自我时,更多地是受心理学的影响,但综其描述,又往往具有哲学的意味。
赵少忠是格非的《敌人》中的主人公,他的反常行为与他自我的罅漏分不开。身为族长的赵少忠,因早年家中一场灾难性的大火而留下不可磨灭的创伤性记忆,从而在内心世界烙下一个伴其终身的“敌人”的印记。他的在世存在就是等待那个自我确定的“敌人”出现,常年累月地自由流由流动在内心的“敌人”,形成一种精力贯注而不断冲击由自我设置的心理保护层。而且从本我升华进超我的道德主体严历谴责自我,迫使他对这种一无所知的“敌人”处于戒备状态,而外界又从来没有给他的知觉提供危险的“敌人”信息,自我在三面围攻之中生成焦虑,因此他对外界过于敏感,具有一种超常的经验方式,以致终日生活在一种不祥之兆中,处于现实与非现实的恐怖和神秘氛围里。加之,人本能地具有一种转嫁压力的倾向,即把来自内部本身的刺激当作源自外部世界,于是赵少忠为了消除自己的焦虑,从体验的被动者转为主动的施行者,杀死身边的亲人,以这种方式把自我不堪承受的重负转嫁到替代者身上,缓解本我及超我对自我的压力。实际上赵少忠自我承认的“敌人”并不是外界的实存,而是他内在制造的臆想。小说对作为个体思维中心范畴的自我表示质疑,因为它包含着虚幻和欺骗。幻想一旦植入人的内心世界而形成定势,就可能注入一连串虚假错位的历史,并抑制外界的真实信息而屈从内心的指使。
如果说赵少忠的幻想意识,是自我为了维护内心的平衡而被迫认同的结果,那么池莉《预谋杀人》主人公王腊狗的自我,则是先天植入内心的,因而一直认同本我与超我的刺激,把攻击外部世界的对象作为一生的支撑。他的生活就是算计和等待,处心积虑地要杀死富绅丁宗望。他的内心自动封闭一切关于丁宗望的经验感知,并把自己所有的人生失败的反思都引导为敌视丁宗望。
池莉把王腊狗的自我看作是道德——文化缺陷的印证,这无疑降低了小说的思想品格。王腊狗的自我欺骗不能仅仅归于个体无意识的压抑,而具有社会无意识的内容。他自我虚设的复仇理由,来自具有社会性的共同被压抑,“是贪欲所借以表现自己和只是用另一种方式来借以满足自己的隐蔽形式”。〔5 〕在王腊狗的内心世界潜藏着一种由贪欲而转换的嫉妒和平均化,其完成形态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粗陋的共产主义”,这种人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这种“粗陋的共产主义”是对文化和文明世界的抽象否定,是向贫穷的粗野的和无欲望的人的违反自然的单纯性的倒退。故此王腊狗的自我,实质上是由无意识中自卑的贫贱和偏狭的平均幻化而成的虚假自我。
作家在赵少忠与王腊狗幻想的自我意识中,消解了以往人们关于主体自我的乐观观念,自我不再存在于人与世界的真实关系中,而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封闭性的孤独主体,仿佛只有死守内在世界的平衡,才有安全感;自我也是缺乏反思能力的自发意识,宁愿自我欺骗也不肯抵制变异转换的本能。他们所谓的自我意识不仅充满了空幻而沉溺内向,而且为人自身提供制造罪恶破坏文明的种种“合理的”逻辑。这些作品专注于人的内心深层,展示那些不堪入目的粗隔,以应答以往那些寄托在自我主体之上的超越自身与无限发展的乐观自信的美梦。
讲述历史,本是艺术追求意义的一种重要方式,作家在历史叙述中艺术地表现作为时间中存在的人的某些本质的东西及人对社会历史的理解。而新历史主义作家的历史人物的自我,丧失了知觉——意识系统的规整能力,明显地体现出它与无意识心理的负面联系。由于“无意识心理过程本身是‘无时间性的’。这首先就意味着,它们是不以时间为序的,时间无论如何都不能改变它们,而且时间的观念也不能应用到它们身上。”〔6〕完全可以想象, 缺乏时间标示的历史世界与现实世界会有什么差距。确切地说,新历史主义的历史世界是抹去了具体时间标示的生活世界,而且在这个生活世界中具有价值意义的人消解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充满虚幻自我的个体,是被无意识本能操纵的个体,是自我欺骗的个体。面对这种个体,作家既恐惧而又无能为力。
注释:
〔1 〕本人认为:“新历史主义”小说是近十年来新历史小说趋向中的一个高潮性的表现形态,出于表述及约定俗成的缘故,这里仍然沿用这个称谓。
〔2〕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P38,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1月版。
〔3〕胡曲园主编:《哲学大辞典·马克思主义哲学卷》P359, 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2月版。
〔4〕弗洛依德:《弗洛依德后期著作选》P6,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6月版。
〔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转引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P70,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7月版。
〔6〕弗洛伊德:《弗洛依德后期著作选》P29,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6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