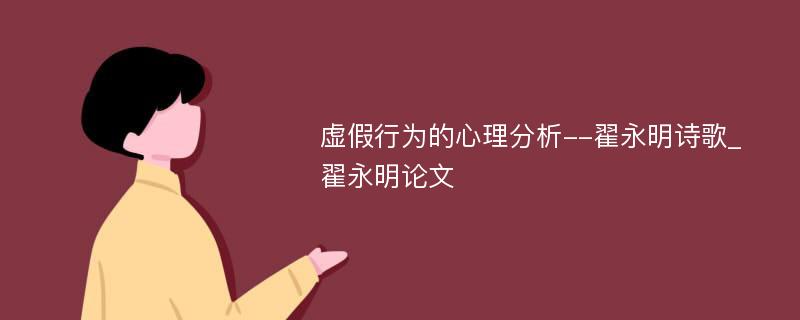
假动作的精神分析——翟永明诗歌务虚笔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歌论文,精神分析论文,动作论文,笔记论文,翟永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l006-6152(2010)05-0011-06
一
翟永明的早期诗歌中布满了“假动作”。①这种活动在语言层面上的假动作并非人们通常理解的奇技淫巧,在翟永明这里,它仿佛烈日下撑开的一把花伞,成为一种自觉而恰切的装饰。如同女性气质中的颔首、掩面、欲说还休一样,这些韵味十足的假动作浸透着一种政治美学,它被时代的总语法暗中授命,推至了翟永明诗歌写作的最前沿。本文着手收集、甄别和分拣翟永明诗歌中的假动作,揣摩这些假动作的发生学意义,并考察它们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以及最终消逝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辨识出这些几乎被指认为翟永明诗歌特征的假动作是如何与时代发生关系,如何听命于时代总语法的指令和召唤的。重新阅读翟永明的诗歌因而成为了必要,并且同时成为了一次恭敬的“打假”行动。
本雅明曾感叹道:“若干世纪以来,文字经历了从直立慢慢躺倒的过程……”[1]如果整个世界的印刷文字都躺倒在了机械复制时代的床榻上,那么我们至少还可以摸索到平躺着的文本身躯上不肯倒伏的器官,即一首诗歌中的那些直立的词。正是踩踏着这类坚挺、直立的砖块,我们才能得以施展轻功,以它们为跳板,穿越眼前这片雾气氤氲的诗歌沼泽。
翟永明以书写黑夜意识独步诗坛,她的早期诗歌(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确如一片沼泽,因为她以排山倒海的长诗(组诗)面目和冷峻晦涩的遣词造句令诗界侧目;同时也更像一片荒原。这里不仅暗藏着一层在T.S.艾略特意义上的“世俗社会里现代人的空虚恐怖感”②,而且,翟永明凭借女性独特的感受力投入创作,从本己的生存体验出发,对一干黑暗词汇的海量运用构成了这种的荒原属性③,这已成为诗界的共识。荒原上终年不生草木、沙尘漫卷、遮天蔽日,这样的物理环境天然适合黑暗词汇的生长。这批先行注射了玄学针剂的黑色词汇也首当其冲地充当了直立的词,成为了我们涉渡的砖块和跳板,将我们带进翟永明的诗歌帝国:
貌似尸体的山峦被黑暗拖曳/附近灌木的心跳隐约可闻(《预感》);
洪水般涌来黑蜘蛛/在骨色的不孕之地,最后的/一只手还在冷静地等待(《臆想》);
黑猫跑过去使光破碎(《夜境》);
黑色旋涡正在茫茫无边(《旋转》)。
这是翟永明在《女人》组诗中营造出的立体而动态的时空场景,一幕幕接近于远古洪荒时代的光学特写。在领略了沼泽状的语词特质和荒原般的冷峻格调之后,我们徒增了第三种观感,即一种洞穴式的生存体验。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著名的“洞穴隐喻”来暗讽人类的生存处境,我们所理解的世界只不过是洞穴中事物的影子罢了。洞穴中的唯一色调就是黑色,而洞穴中发生的头号动作就是看;看世界,即看洞穴里事物的影子。翟永明说:“整个宇宙充满我的眼睛。”(《臆想》)诗人希望通过她的眼睛——确切地说是用她臆想中可穿透精神世界的第三只眼——来目睹这方她置身其中、充满黑暗的洞穴和洞穴中的幻象:
穿黑裙的女人夤夜而来/她秘密的一瞥使我精疲力竭(《预感》)
这是《女人》组诗的开头一句,也是诗人率先在洞穴中看到的一幕。由于那个在夜色中浮现的、穿黑裙的无名女神“秘密的一瞥”,抒情主人公“我”仿佛因此获得了神启,意志世界发生激烈地交锋,使“我”迅速地“精疲力竭”。这场发生在预感中的象征交换,让获得神启的“我”从内到外沾染上了黑色气质。以耗费心神为代价,“我”从现实层面跃迁到想像层面。诗人说:“白昼曾是我身上的一部分,现在被取走。”(《生命》)翟永明在用诗化的句子简短陈述一部女性被凌辱与被损害的历史。取走了白昼即意味着女性被驱逐出诸如理想国、太阳城这样的黄金乐土,坠入了黑暗的深渊和洞穴,开始了她们悲惨的受难历程。但勇敢的诗人在为女性争取主动权:“女性的真正力量就在于既对抗自身命运的暴戾,又服从内心召唤的真实,并在充满矛盾的二者之间建立起黑夜的意识。”[2]“我”的黑夜意识正是基于这两项必要条件建立起来的,“因此,我创造黑夜使人类幸免于难”(《世界》)。“我”开始主动投身并创造黑暗,让它们成为女性的长裙、仆从。诗人通过制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内在洞穴来制衡、抵消外部洞穴的严峻和残酷:
犹如盲者,因此我在大白天看见黑夜(《预感》)
“我”终于变成了一位“盲者”。如博尔赫斯所言,“我”获得了“另一个世界”,一个内在洞穴,一个积极意义上的黑暗世界。而“我”成功获得这一黑暗世界的唯一秘诀在于,翟永明让她的抒情主人公通过闭上眼睛成为一位伪盲者来制造个体的内在洞穴,并用它来抗衡她所存身的外部洞穴。④这便涉及到翟永明诗歌写作中的一个典型的假动作:闭目。张柠最早注意到了翟永明诗歌的这一特征,认为她在‘视觉占有’的行为面前最终是一个逃亡者。”[3]拒绝占有并非拱手相让,如同“我”闭上眼睛但并非仪“对每天的屠杀视而不见”(《生命》)。翟永明在这项绝技中失去了“视觉占有”的锁链,得到了整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大脑中反复重叠的事物/比看得见的一切更长久”(《盲人按摩师的几种方式》);在这个世界里,“我的眼神一度成为琥珀”(《证明》),也同时谙熟“夜使我们学会忍受或是享受”(《人生》)。
在《女人》组诗中,翟永明像她塑造的抒情主人公一样,也出色地扮演着一位盲者。她闭上眼睛,深呼吸,让眼前的黑暗带给她久违的平静和思索的空间。“炎热使我闭上眼睛等待再一次风暴”(《秋天》)。这个意味深长的假动作为诗人提供了一片缓冲地带、一个中继站、一张午睡的床。作为女性的“我”并不想从此在这个个体的内在洞穴里避难,“躲进小楼成一统”,由昏睡入死灭,而是希望在这个假动作的庇护下有所创造:
当我双手交叉,黑暗就降临此地/即刻有梦,来败坏我的年龄(《证明》)
梦,就是“我”在借助闭目这一假动作营造个体的内在洞穴时获得的副产品,是在“我”成为伪盲者之后受孕于黑暗而诞生的骄子。梦在黑暗中的诞生足以对抗时间的暴政,将“我”流逝的年龄横加败坏,从而打破惯常的外部时间秩序,建立起个体的内在洞穴时间体系,即时间的静止。这种无时间感正应和了黑暗洞穴的本质特征,也是梦的一枚重要标签。梦开始从一个时间的横截面上缓缓飘出。“梦显得若有所知,从自己的眼睛里/我看到了忘记开花的时辰”(《预感》)。
因黑暗而选择闭目,因闭目而获得黑暗,这便是翟永明在实施假动作时所遵循的逻辑。适时的闭目暂时取消一位女性在现实世界面前目睹的一切血淋淋的不义、掠夺和凶残,一切“自身命运的暴戾”。在隔绝了外部的消极黑夜之后,相应地迎来了属于女性自身的积极黑夜的降临。这并非自欺欺人的愚昧逻辑,而是苦中作乐的灵魂游戏。儿时趣味盎然的游戏行为在这里变身为成人自慰式的假动作,假动作的实施正是继续践行这一公平的游戏规则,当假动作发出,“夜还是白昼?全都一样”(《旋转》)。翟永明投身于这个积极黑夜,利用假动作来划出一条儿时游戏的延长线,来创造一个诗人的白日梦。弗洛伊德认为:“成人创造一种虚幻的世界来代替原先的游戏,他创造的是一种空中楼阁或我们称之为‘白日梦’的东西。”[4]翟永明用诗歌和诗歌中埋伏的假动作缔造这样一个白日梦,在白日梦里自由地进行自我抒写,以隐喻和暗语与内在黑夜相互交流,“服从内心召唤的真实”。进而在这种既对抗又服从的矛盾体系中支撑起她所谓的“黑夜的意识”。
二
翟永明在残酷暴戾的现实面前选择闭目这一假动作,用语言编织了一个虚幻的个体内在洞穴,并自觉地与洞穴里独有的积极黑暗齐心协力,和盘托出了将抵抗与服从熔于一炉的白日梦。这就是闭目这一翟永明式假动作的使用价值、基本功能,也是它所意指的全部诗学内涵。尽管这一假动作中充满了绝望的色彩,但未必不会带来惊喜的发现。闭目假动作让视觉驶入黑夜,将眼球归零到鸿蒙初辟的起点。然而,恰如一位盲人终年生活于黑暗的环境,却拥有异常发达的听觉一样,闭目假动作使得“我”的听觉系统马力强劲,听力空前活跃。《静安庄》组诗的问世,让翟永明在《女人》中吟唱过“黑夜中的素歌”之后,转而成就她炮制出了一席“听觉的盛宴”:
我来到这里,听见双鱼星的嗥叫/又听见敏感的夜抖动不已(《第一月》);
我在想:怎样才能进入/这时鸦雀无声的村庄(《第二月》);
在水一方,有很怪的树轻轻冷笑(《第五月》);
在它们生长之前,听见土地嘶嘶的/挣扎声,像可怕的胎动(《第十月》);
在《静安庄》中,像这样摹写声音的诗句比比皆是。对可视世界的弃绝转而让抒情主人公“我”尽享听觉盛宴,翟永明式假动作在这种意义上实现了它的交换价值。闭目未必塞听,相反而是助听、畅听甚至是幻听。《静安庄》不但暗示着诗人采取闭目假动作之后听觉的全面重启和复苏,更重要的是,诗人在屏蔽了外部视觉图像的干扰后习得了一种清晰分辨宇宙万籁的特异功能。这种特异功能是在静安庄这个“鸦雀无声的村庄”中得以施展威力的。“我走来,声音概不由己/它把我安排在朝南的厢房”(《第一月》)。从一开始,“我”就听从一个声音的召唤姗姗前来,驻扎在静安庄。敏感的听觉让“我”读透了蕴藏在各类声音中的灵魂和命运。相对于外部世界“越来越高的世纪的喧嚣”,“我”偏偏在这座村庄里听到“双鱼星的嗥叫”“树的冷笑”“土地嘶嘶的挣扎声”“地下的声音”……“我”可以听到村庄各个角落发出的隐秘怪异的声音。从天空到地下,从现世到亡灵,这些声音融贯着自然、历史和潜意识,变得绵延深广,无处不在。静安庄的声学现场围绕着“我”的个体经验敞开:
是我把有毒的声音送入这个地带吗?
我十九,一无所知,本质上仅仅是女人
但从我身上能听见直率的嗥叫
谁能料到我会发育成一种疾病?
(《第九月》)
在这里,“我”蠢蠢欲动的青春期与古老衰朽的静安庄不期而遇,“我”的“有毒的声音”和“直率的嗥叫”与“鸦雀无声的村庄”形成了尖锐的对立,这是新与旧在暗地里进行的奇怪交锋。交锋所产生的电光火石,在闭目但畅听的“我”这里全部转化为各种形式的音响符号,被“我”一一收藏。静安庄是诗人年轻时代留下深刻成长伤痕的地方,“我十九,一无所知,本质上仅仅是女人”,这是抒情主人公抵达静安庄时对年龄、阅历和性别意识简单而彻底地交代,她等同于诗人柏桦所谓的“无辜的使者”(《往事》):一位出使静安庄这座古老村落的年轻使节,带着她那个年龄里唯一的资本:一双紧闭的双眼和一对善于捕捉声音的耳朵。“第一次来我就赶上漆黑的日子”(《第一月》),既有生不逢时之感慨,又为闭目假动作搭桥。
“内心伤口与他们的肉眼练成一线/怎样才能进入静安庄?”(《第二月》)从“我”与静安庄的关系来看,它更接近于卡夫卡笔下的土地测量员K之于城堡的关系,在绝对荒诞的时代被“安顿”在静安庄,却无法真正被静安庄接纳。而当“我无意中走进这个村庄/无意中看见你,我感到/一种来自内部的摧残将诞生”(《第十一月》),“我”在忍受这座“鸦雀无声的村庄”的摧残和折磨,对声音出奇敏感的“我”只能幻想着听到自己身上发出“直率的嗥叫”来负隅顽抗。更残忍的是,静安庄最终扮演了城堡的角色,宣判了“我”的罪状:“把有毒的声音送入这个地带”“我会发育成一种疾病”。“我”对静安庄来说是一个异己分子。在闭目假动作的掩护下,“我”启动了最敏感发达的听觉,我在静安庄听到的一切声响都听从“我”内心波动的调度一同起伏。“我”不动声色,而这些声音成为“我”此时独有的言语方式的外化,在大多数情况下代替“我”奏响内心的哀鸣。“我”被鸦雀无声的静安庄“治罪”,却拥兵十万,夺取了一场声学战役的伟大胜利。
从整体上看,《静安庄》里驳杂的声音谱系实际上围绕着一个处于核心位置的独白声音展开:“我十九,一无所知,本质上仅仅是女人。”十九岁的女人是一个沉默的音符,是一张白纸,是苏珊·格巴所谓的“空白之页”。长期以来,女人在父权制的统治下象征性地被定义成一片混沌、一个缺位、一个否定、一块空白。女人被认为是一种待书写的材料,一块待开垦的土地。女人初夜身下染有血迹的雪白床单理所应当地被装裱起来供人观瞻,因为这符合这个特定时代的语法:女人成为了人们希望成为的样子。当一块神秘的、一尘不染的空白床单的悄然问世却颠覆了这一切既定的秩序。“空白不再是纯洁无瑕的被动的符号,而成了神秘而富有潜能的抵抗行为”。[5]“我”正是处在这个充满了空白想像的年龄:被外界想像也被自我想像。静安庄以古老狰狞的面孔力图鸦雀无声地书写“我”的空白,“我”渴望摒除外力而进行自我书写。在拼命的抵挡和抗拒过程中,“我”慌忙迅速地急于认清自我,却只能听到四处泛滥的声音,这一幻听现象使“我”最终“发育成一种疾病”。病态的“我”的形象更找到了施展假动作的充足理由。因此,《静安庄》诞生于“我”在《女人》中的闭目假动作的巨大背影里。《女人》成为《静安庄》的逻辑前提。
就像当初荒诞地来,现在又面临无原因的走。度过了惊心动魄的十二个月份的“我”,“如今已到离开静安庄的时候”(《第十二月》)。也许是接受静安庄沉默的审判,“我”被远远放逐。“距离是所有事物的中心/在地面上,我仍是异乡的孤身人”(《第十二月》)。也许“我”归根到底摆脱不了一个过客的命运,就像鲁迅作品中那个从记事时候起就一直赶路的过客一样,受一个声音的催促,不停地赶路。[6]在这两个同样对声音患有强迫症的过客身上所不同的是,鲁迅所塑造的过客是一位男性,他可以孑然一身,从生到死,一意孤行,去追求一个美丽的理想国或太阳城;而《静安庄》里的“我”是一位女性,她从一开始就被开除出那片黄金乐土,抛入黑暗的深渊。她摆脱不掉命运使然的悖谬感,她既倔强又脆弱,既争取自尊又忍受屈辱,既想开口说话又难免归于沉默。这是女人天生无法克服的窘境。这样的过客的下场可以用翟永明创作于1999年的一首诗的题目概括为:终于使我周转不灵。
三
翟永明似乎道出了人被抛入世界上之后必然迎来的一种状态。距离是所有事物的中心,人类永远在路上。即使是假动作,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彻底疗救命运中必然的病态成分。《女人》中的主人公因闭上双眼而驶进黑夜,像蝙蝠一样成为夜的使者,勘测女性灵魂的底色。在遨游了整个黑夜王国之后,“我”做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惊人之举:“现在我睁开崭新的眼睛/并对天长叹:完成之后又怎样?”(《结束》)
是怎样的勇气使“我”决定睁开眼睛?闭目一直是“我”入世的姿态,“我”通过这一假动作炮制了一个人造的黑夜,并在其中重新打量自我。如今睁开了眼睛,这显然是对“我”与时代签署的假动作契约的单方面撕毁,是对假动作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否定,是对假动作的出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真动作!翟永明心里藏着一个疑问句:“完成以后又怎样?”这颇似丹尼尔·贝尔关于“真正的问题都出现在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的论断。她让她笔下的抒情主人公睁开眼睛来问这个问题,因为“我”不愿陶醉在自己编织的几近完美的假动作当中。《静安庄》中的听觉盛宴和沉默审判加速了假动作的破产,“我”终于发现了自己的病态和永恒的困窘,假动作所带来的一切终于使我周转不灵。这或许正回答了“完成之后又怎样?”这个疑问。
从《女人》到《静安庄》,从“完成之后又怎样?”到“终于使我周转不灵”,是时代总语法的稳步推演,是逻辑学的大获全胜,是历史书里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却是一个女人的一生。“我”就在十九岁时瞥见了自己完整的一生,顿悟了所有女人的命运。“谁此时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里尔克《秋日》)。翟永明站在静安庄的山岗上迎来自己创作上的一个崭新黎明,虽然据傅雷先生的乐观估计,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远不被黑暗所遮蔽罢了。[7]然而翟永明更宁愿相信存在“黑夜深处那唯一的冷静的光明”。这是她在抛弃了假动作之后,在与时代互敬互谅、尽释前嫌之后,潜心修炼之所在。“我”决定睁开眼睛,用自己的眼睛去看清世界。
在另一首长诗《颜色中的颜色》中,翟永明展示了试图睁眼的努力,尽管它依然身着玄思之作的外衣。经过长久闭目神游并施展假动作与时代抗衡的“我”,由于在黑暗里度过太多的时日,瞳孔松弛地张开着,眼球对光线的敏感度倍加提升,因此从试图睁开的眼睛的缝隙里钻进来的些许光线都会令“我”感到异常的明亮和刺激。《颜色中的颜色》就是一次在久违的光线沐浴下的官能舒展。我迫不及待地睁开双眼,外界的光线一下子全部倾泻进“我”的眼睛里,本能地造成瞳孔急剧缩小,稚嫩的视网膜上只能留下白花花的一片光斑,造成了短暂的“失明”。虽然都属于眼睛的病态,这时的短暂“失明”不同于此前的闭目假动作,后者将“我”带入人造的黑夜,而前者制造了一幅大量白色堆积的太虚幻境。因之,诗中此起彼伏的哲思玄想便不足为奇。
大象无形的白色隐藏在任何颜色中,它组成了颜色的生成,也可以从任何颜色中取走,因此白色堪称“颜色中的颜色”。诗人决定让她的抒情主人公试图睁开眼睛,书写“我”所看到的事物,然而此时“我”只看到了白色。本诗即是对白色的共时遐想,是抛弃假动作庇护后的另一个白日梦:
“白色日益成为——”你说/——“我色彩的灵魂”你说过(《颜色中的颜色》)
从《颜色中的颜色》开始,翟永明正式启用眼睛的日常功能,除了刚刚睁眼后需要面对的大量泛滥的白色之外,进入诗人视线的另一个重要的词汇就是人称代词“你”的涌现。相似的转变也出现在《壁虎与我》《肖像》和《迷途的女人》等作品中。诗人把目光从“我”自己身上稍稍移开,开始打量眼前的对话者,开始关注人间事务和琐屑的世俗生活。这一切转变都陆续体现在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诗歌创作中,但此时只是一个投向现世的眼神而已,它将作为一个信号预示着翟永明正在走向诗歌写作的改良时代。在这个改良时代里,诗人的视野中将有更多的新面孔出现,不但出现了“你”,而且还出现了“他(们)”或“她(们)”,甚至可以说,诗人实际走进的是一个“他(她)”时代,一个主观独白全面隐退、客观呈现广泛登陆的时代。这或许是一种更好地与时代总语法进行对话的形式。《咖啡馆之歌》《盲人按摩师的几种方式》《时间美人之歌》《编织和行为之歌》《去面对一个电话》《小酒馆的现场主题》等作品就在这个更为广阔的写作空间里相继诞生。翟永明不但收起了早期的诗作中频频出现的假动作,睁开眼睛去看这个世界,而且要看个明白,看个真切。诗人在这个“他(她)”时代中获得了新的经验和见识,逐渐找到了新的表达方式和新的语言,这正是我们在她其后的诗作中所有目共睹的。
四
翟永明的个人诗歌创作史是一部从闭目到睁眼的漫长革命史,一部假动作的消亡史。她的作品是不断敞开的,从单极的黑夜中的独白到多极的“他(她)”时代速写,体现了一个对技艺精益求精的诗人的成长过程。假动作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一度造就了一个翟永明的诗歌神话,但永远不会成为诗人的完成时态,她终究是一个履历卓然的过客;所向披靡的“跳读法”在分辨假动作上功不可没,但最终因为找不到当初的沼泽而宣告搁浅,演出了一幕刻舟求剑的荒诞剧。就像翟永明在《潜水艇的悲伤》中写到的那样:“现在我已造好潜水艇/可是水在哪儿?”
潜水艇与水的关系或许可以揭示出一个诗人的语言方式与时代总语法的关系吧。所有的书写都是在时代语法的逼视下进行的,就像潜水艇必须停留在一片广大的水域才能成为自身。潜水艇与水有三种可能的位置关系:沉潜到水下、飘浮在水面或搁置在岸边。由此,写作与时代的关系也可以分别理解为深入时代核心的写作、荡漾在时代表层的写作和脱离时代的写作。深入时代核心的写作就好比稳稳行驶在平静水底的潜水艇,它谙悉时代的总语法,具有波澜不惊的写作姿态,全方位与时代严密契合,与时代融为一体;荡漾在时代表层的写作如同飘浮在水面的潜水艇,因受制于变换的风向、奔涌的激浪和凡尘的喧嚣而全身颤栗不安,它迫不及待地受命于时代的表层语法,却往往逃脱不了周转不灵的命运;脱离时代的写作并非与时代毫无瓜葛,它至少比搁浅在岸边的潜水艇更类似于一座硕大无朋的精致墓园,一个黑暗的洞穴,一件充满能指却悬置灵魂的瓷器,类似于努力燃烧后的灰烬或缺乏羊水的胚胎。
“现在我必须造水”(《潜水艇的悲伤》)。翟永明宣告了她写作的及物性,着手开发可供自己的潜水艇纵横驰骋的水域。因此,从《女人》《静安庄》到《咖啡馆之歌》《时间美人之歌》,诗人正经历着操练自己的潜水艇逐步挪向岸边,直至下水启航的过程。那么在下水之前的缓慢程序,可权当视作一艘潜水艇在真正实现自我完成前所必然做出的假动作,因此它必然会经历着从搁置岸边、荡漾水面到最后沉潜水下这三个阶段。潜水艇生来就该下水,投入水下另一片黑暗,这却是与此前决然不同的黑暗,一种可将其融为一体的黑暗。
翟永明先后依靠施展假动作和抛弃假动作推进了个人诗学的逐步完臻。一个写作者意欲追求一种深入时代核心的写作,对此前的艰苦历练似乎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我们就要充分地理解一套假动作之于时代的特殊含义。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种政治美学;在更高的意义上,它是一种伦理学。“一点灵犀使我倾心注视黑夜的方向”(《结束》),翟永明的诗歌正朝那里走去。
收稿日期:2010-02-10
注释:
①这里的假动作,特指在诗歌写作技术层面上的一种处理方式,具有维特根斯坦所谓的“语言游戏”色彩。通过诗歌中抒情主体的务虚动作(本文以视听感官为例),开辟一条阐释诗歌作品的可能途径,以期实现语言与生活,心灵与世界的混融。
②语出1948年瑞典文学院给T.S.艾略特的授奖词。
③黑暗词汇指的是翟永明早期诗歌中惯用的诸如黑、黑色、黑暗、黑xx、夜(晚)等词汇。
④诗人在10后依然强调这种抗争性。参阅翟永明:《再谈“黑夜意识”和“女性诗歌”》,《诗探索》,1995年第1期。
⑤据粗略统计,《颜色中的颜色》中涉及到“白色”的词汇达42处之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