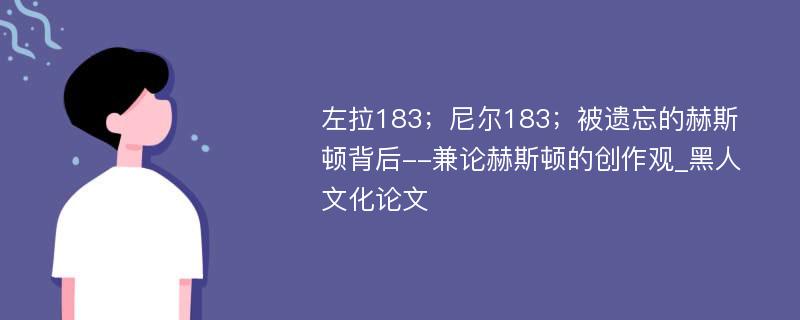
佐拉#183;尼尔#183;赫斯顿被遗忘的背后——兼谈赫斯顿的创作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赫斯论文,被遗忘论文,尼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7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34(2001)02—0098—06
在今天的美国黑人社会,“再生”的佐拉·尼尔·赫斯顿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瞩目和重视,成为黑人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新的热点;受到了普通黑人百姓的普遍喜爱,被视为他们可以引以为自豪的优秀“女儿”。她的小说《她们眼望上苍》广泛流传于黑人之中,成了一部经久不衰的畅销书。更值得注意的是,赫斯顿逐渐得到美国主流社会的承认,她的作品被视为美国文学传统的一部分。
赫斯顿受到青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她被当代黑人女性作家视为他们的“文学母亲”[1](P88);二是她被黑人女权主义者推崇为“女权运动”的一位先驱者;三是她的作品所展现出的黑人文化精神,即“黑人性”,恰恰是今天黑人文化界所要重新承认的艺术价值;四是她的小说在语言运用、叙事策略和对黑人民间口头传统的应用等方面都迎合了今天黑人小说创作的主要趋势。
自70年代末,研究者往往把研究重心放在了对赫斯顿的“再生”意义的认识上,和对赫斯顿作品的艺术魅力的分析上。相比之下,人们对赫斯顿为何被遗忘的原因分析不够。更不用说试图去阐述赫斯顿被遗忘的背后到底在文化思想和艺术审美上蕴含着什么。事实上,分析赫斯顿被遗忘的原因为深刻了解赫斯顿和她的作品构成了一个新的视角。从历史的角度看,赫斯顿代表着超越时代的一种文化意识。她所积极实践的是在艺术创作上强调文化个性和独立性。本文正是从历史的角度全面分析赫斯顿被遗忘的原因,并试图从文化的角度去阐述这一事件的意义。
一
赫斯顿的被遗忘,明显表现在以往的哈莱姆文艺复兴研究几乎只字不提赫斯顿,似乎表明她根本不属于那个时代,更谈不上有任何贡献了。
哈莱姆文艺复兴是发生在美国20世纪20年代的一场标志着黑人觉醒的文艺活动。当时一些年轻的黑人作家从四面八方汇聚到纽约市哈莱姆区——纽约市黑人生活的中心。他们在老一代黑人艺术家的鼓励和支持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勇气,用他们的艺术创作去再现黑人战后形成的新的民族自尊、种族意识、种族团结精神,以及爵士乐时代所特有的那种强劲的生命力和布鲁斯情调。这是黑人文艺发展史上所出现的第一次集体创作高潮,展现了黑人作为一个民族的艺术智慧和创作能力,同时也为弘扬“新黑人”形象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作为黑人文艺发展长河中的一次重要事件,历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作为同时代人的赫斯顿,在她被重新发现之前却被彻底忽视,即便偶尔被提及,往往也是从反面来谈的。如哈根斯在他有关哈莱姆文艺复兴的权威之作《哈莱姆文艺复兴》一书中,往往是以讽刺的口吻来谈论赫斯顿,把她描述成一位投机者和善于利用黑人民间材料为己利的一位奸诈的女人:“贫穷和限制给了她一个去强烈获得机会和一旦机会出现就将不顾一切去抓到机会的本能……黑人民间材料对于佐拉·赫斯顿而言仅仅是另一次机会罢了……在佐拉·赫斯顿的思想与素材之间从来没有一个清楚的界线。”[2](P75)D.L.刘易斯是另一位研究哈莱姆文艺复兴的权威学者,他在《当哈莱姆盛行时》中对赫斯顿只是一笔带过,既没有对她进行肯定也没有否定。这说明刘易斯认为赫斯顿根本不是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重要作家。[3]
赫斯顿1901年出生在佛罗里达的伊顿威尔镇[4](P51)。该镇尽管不是美国第一个黑人社区,但却是第一个由黑人自行管理的黑人城镇。赫斯顿的父亲是一位牧师,9岁时又没有了母亲。 后来在一些白人赞助者的支持下,她分别在哈沃德大学、巴拿德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过,完成了本科和研究生教育。1925年她来到了纽约,并于当年5 月以她的短篇小说《活力》获得了《机遇》杂志举办的短篇小说竞赛二等奖。次年,她与兰斯顿·休斯一起创办了文学杂志《火》,并在此发表了短篇小说《汗水》和剧作《Color Struck》。其中《汗水》被认为是那个时期的最佳短篇小说之一。赫斯顿到达纽约的时候恰恰是哈莱姆文艺复兴发展的巅峰。她不仅仅是那场运动的主要参与者,而且在各方面都取得了成绩。正如她的传记作家罗勃特·海明威所评论的那样:“她给哈莱姆文艺复兴的审美体系贡献了一种真实的民间经验。”[4](P51)他又进一步评论说:“她所代表的是美国黑人生活的那部分已知但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被体验过的经历。”[4](P51)
当然,赫斯顿决非是靠以上几部短篇小说而饮誉当今黑人文坛的。她一生共发表了两部民间故事、四部小说、一部民间歌剧的歌词、两部歌舞剧剧本,多篇论文和一部自传。她是一位受过良好正规教育并且多产的女性作家。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位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已经崭露头角的黑人女性作家会在佛罗里达州圣路亚郡福利院度过其悲惨的晚年、死后被埋葬在长满了野草的无名墓地里呢?
二
赫斯顿天生性格外向,具有敢作敢为的精神。十几岁时便敢跟路过伊顿威尔镇的白人摩托车骑手去外地。她为此多次遭到作为牧师的父亲的斥责。由于父母早亡,她不得不过早地自立,独撑门户。为了生计,她又学会了如何去取悦白人,以获得他们的经济支持。除此之外,她十分了解黑人民间文化,能讲很多黑人民间故事,而且她十分幽默和诙谐。
赫斯顿以其追求自我实现的敢为精神,幽默诙谐的性格和善于搏得白人赞助者喜欢的能力而闻名于当时的哈莱姆文化界。这一点反映在她与同时代黑人作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上。作为当时已有一定成就的黑人女性作家,她与那个时代结下了不结之缘这一事实从反面上得到证实。赫斯顿曾经与兰斯顿·休斯的关系很好。他们不但曾由同一个白人赞助者来支持,而且还有艺术上的合作。他们合写过一部剧本,后来因版权问题发生争执便反目成仇。休斯在自己的传记《大海》中是这样描写赫斯顿的:“……一些白人付钱给她,其唯一目的就是让她坐在周围,作为黑人种族的代表。而她却以一种有失体统的方式做了他们让她做的事情……对她的许多白人朋友来说,她无疑是一个完美的‘黑鬼’,他们赋予这个词的最好意义是:天真的、孩子气的、甜甜的、幽默的、而且相当有色的黑人。”[5](P239)
与赫斯顿同时代的另一位作家华莱士·瑟曼,在小说《春天的婴儿》中把她塑造成其中的一个人物,称她是位故事家:“她是那些到处寻找黑人奇才的白人庞儿。……她讲的故事都庸俗、下流和有趣。 ”[6](P229—300 )他进而又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这样描述她:“就这样……我必须吃饭。我也希望完成学业。今天作一位黑人作者就像是一枝火箭,只要它还坚持住我就充分利用它。我一点也不懂艺术。我更不关心艺术。我最终的目的正如你所知,是想成为一位妇科学家。在我获得必要的训练之前我唯一能生活得容易的方式是把自己装扮成一位有潜力的作者……[6](P229—300)华莱士·瑟曼对赫斯顿的攻击尽管是间接的,但具有很强的讽刺意味。在他笔下,赫斯顿完完全全成为了一个对艺术一无所知,而且是只知道靠讲下流民间故事去取悦白人的投机分子。
兰斯顿·休斯和华莱士·瑟曼都是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的代表人物。尤其是休斯,多才多艺,创作甚丰,被誉为黑人的桂冠诗人。作为哈莱姆文艺复兴的杰出代表,他们对赫斯顿的否定评价对她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他们的看法不但易于被人们接受,而且往往令人们深思。赫斯顿作为一位作家的诚实性和对自己种族的忠诚便因此受到了质疑。
而赫斯顿的创作倾向,即突出黑人民间文化、以黑人下层社会的生活为素材,在语言运用上强调黑人方言在塑造黑人下层人物性格方面的不可替代性,自然而然地加深了人们对她诚实性和忠诚性的怀疑。正如我们所知,哈莱姆文艺复兴的文化基础是当时蓬勃发展的“新黑人”运动。其宗旨是依靠黑人通过战争考验和从南方农村迁移到北方城市的经历所获得的新的民族自豪感去树立新的形象。为了在艺术创作上把新的黑人形象充分展现出来,以改正长期以来带有偏见的而且脸谱式的,以汤姆大叔为典型的黑人形象,赫斯顿同时代的黑人作家都紧紧抓住时代的精神,以各种创作方式,为弘扬“新黑人”形象而积极创作。然而,赫斯顿却反其道而行之,把创作的重点放在了南方农村的黑人民间生活上,以浪漫与现实结合的手法展现了黑人最底层人物的生活现状。塑造出了一批栩栩如生的民间黑人人物的形象。《她们眼望上苍》最能反映出赫斯顿这种创作倾向。最底层黑人那种贫困潦倒的现实,但无忧无虑而乐在其中的生活态度跃然纸上。尽管她所描写的黑人形象逼真、活灵活现,但很容易被人们误解,无意中给构成否定影响的黑人形象增加了活生生的例子。这无疑对正在试图改变形象、争取与白人平等地位的黑人来说是一个败笔。他们会这样认为,赫斯顿为了个人的前途而不惜利用黑人民间材料。这种认识又与休斯和瑟曼对赫斯顿的评价完全吻合。这样一来,赫斯顿就很难被黑人社会所接受了。
另外,赫斯顿出生于南部一个纯黑人的小镇,在黑人完全自治的环境下长大。据她自己讲,她到10岁后才有了黑人的概念。由于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多少直接受白人剥削和压迫的经历,她对白人的概念是支离破碎的、不完整的。因此,她不具有双重的文化意识,在看待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关系上没有产生双重视觉。也没有像其他黑人那样感受到黑人内心的冲突。这就使她与同时代的黑人作家产生了明显的区别。
由于其他黑人作家成长的环境和所经历的一切与赫斯顿的不同,他们往往感到受双重意识的限制,深感作为一个美国黑人的悲哀。他们对自己的文化身份十分敏感但又不置可否。一方面认为自己是美国人,但却没有获得美国白人应有的地位。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面对现实,即他们是一些特殊的美国人,是种族歧视、暴力和私刑的对象。他们清楚地认识到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他们的黑色皮肤。他们的命运由于肤色而变得多灾多难。围绕对“黑色”的认识,美国黑人产生了双重意识。一方面想彻底拥有自我,建立以黑色为标准的认识体系,而另一方面又想融入美国社会,认同欧洲文化,并以此为标准。为此,美国黑人著名思想家杜伯依斯做了如下精辟的论述:“美国黑人的历史是这样一种抗争的历史——渴望获得自我意识之人的地位,渴望把其双重自我融入更好更真实的自我。在这种融合之中,美国黑人希望不失去原来的自我。他不会使美国人非洲化,因为美国人要教给世界和非洲的太多了。在白色崇美主义的洪水之中,他不会漂白他的黑人魂,因为他知道,黑人的血对世界有启示意义。他仅希望使之成为可能的是:一个人既是一个黑人,又是一个美国人,不被他的同胞诅咒和唾弃,不让机会之门当着他的面粗暴地关上。”[7]
与赫斯顿同时代的所有黑人作家几乎都声称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双重意识”的制约,而她却公开宣称没有任何同感,承认她看待世界的唯一视角是黑人的。反过来,在评论与她同时代的那些黑人知识分子时,她又毫不留情地把他们归为“黑人伤感派”,认为他们虽然同为黑人,但决不是她所认可的黑人。赫斯顿这种与当时潮流格格不入的认识势必要造成她与其它黑人知识分子在认知上的冲突,从而导致了她不被接受和承认。但她强调黑人传统文化在形成黑人认识方面的重要性尽管超越了时代的局限性,但在今天已经被广泛承认了。
三
造成赫斯顿被遗忘的另一主要原因是她的审美观与当时黑人文艺界所倡导和追求的“对抗”艺术观相去甚远。就我们所知,黑人文学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明显的政治性,在文学的“教育”和“娱乐”两个功能之间,黑人作家更强调文学创作的社会参与性。文学除了要深刻地反映黑人民众内心深处的情感世界之外,必须要成为黑人争取解放和平等的重要武器。这种艺术思想在黑人文学创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进而使黑人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对抗为主的文学传统。从一开始的“奴隶自述”到哈莱姆文艺复兴,到里查德·赖特的自然主义小说,人们所看到的是黑人作者利用艺术去抗击美国社会的冷漠、无知和虚伪,展现黑人身份重累的历史现实,歌颂黑人为争取平等利益的斗争精神,讽刺那些试图背叛黑色种族的混血儿。严格说来,黑人文学创作始终是围绕黑人在美国的命运的,因此,不关注黑人命运、不为黑人的解放呐喊的作品就不可能成为优秀作品。这种创作观实际上是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的核心思想。克劳德·麦凯那首充满战斗激情的诗《如果我们一定要死的话!》表达的就是这种艺术观。
赫斯顿并没有在创作上接受这种审美观,而认为黑人文学应该去表现黑人民间生活的价值,展示普通黑人百姓的日常生活经历。黑人文学创作必须要根值于黑人传统文化,以此为黑人文学的审美标准。另外,她坚决反对黑人必须依据他们与白人之间的关系来定义自己的现实。她强调黑人存在的独立性和自我性,认为黑人传统文化是黑人形成自己价值取向的基础。她的这些观点充分体现在她的文学创作之中。首先她的作品主要反映的是南方农村黑人的故事,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其次她的作品很少涉及白人,似乎他们根本不存在。而存在的只有黑人,尽管生活艰难,但仍然坚强地活着。至于“对抗”的色彩就更难在她的作品中发现了。她的传世之作《她们眼望上苍》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讲的是在美国大南方农村的一位黑人妇女追求爱情的故事。小说的主人公珍妮·克劳福德在经过三次婚姻之后最后实现了自我,找到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故事涉及到了黑人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大量使用了黑人方言土语和黑人民间故事,因此妙趣横生。今天,这部作品得到黑人和白人的共赏,因为美国的整个政治气候发生了变化,更加趋向文化上的多元性。同时,美国黑人比以往更加自信,敢于承认并接受因偏见而受歧视的传统文化。然而,在小说发表时,美国社会到处存在着对黑人的制度歧视,私刑泛滥,黑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这部对白人残害黑人的暴行不予抗议的小说怎能得到肯定呢?它的作者又怎能被接受呢?
事实上,她的作品一发表,便受到了当时黑人文化界的抨击。首当其冲者便是赫斯顿的老师,著名的黑人文学评论家阿兰·洛克。这位公认为是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的“接生婆”和阐示者是这样评论《她们眼望上苍》的:“现在来谈谈佐拉·尼尔·赫斯顿和她迷人的小说题目:她们眼望上苍。珍妮的故事是不应重讲的,而必须解读。但就这位天才作家迄今的发展来看,她的长处是背景描写和对当代民间故事的惊人再现。她在诗意的措辞、罕见的方言和民间幽默方面表现出来的天才,使她的社会和人物凸显于表层之上,而没有深入到人物的内在心理,也没有对社会背景进行犀利分析。它充其量是一部民间故事。我们非常感激这部本该早就问世的作品,取代了描写黑人的漏洞百出的地方色彩小说。这位成熟的黑人小说家懂得如何讲述可信的故事,这是赫斯顿小姐天生的禀赋,但她何时才能认真写作动机小说和社会文献小说呢?进步与南方小说已经消除这些娱乐性的伪原始人的传奇,而读者却仍然妒忌他们,愿意与他们同乐同愁。”[8]
里查德·赖特这位黑人文学“对抗”传统的大师在评论《她们眼望上苍》时对赫斯顿的评价就更低了。他认为,“……赫斯顿小姐似乎没有任何愿望朝着严肃小说的方向发展……”[9 ]他又进而评论说:“赫斯顿小姐可以写作,却披着一层肤浅的肉欲的外衣。这种肉欲自菲利浦·惠特利时代以来就困扰着黑人的表现方法。她的对话设法捕捉到了黑人的内心活动,体现了黑人纯朴的民间精神,但仅此而已。”[9]
“赫斯顿小姐在小说中心甘情愿地继承了强加给黑人那个戏剧传统,即取悦于‘白人’的吟游技巧,她的人物吃、笑、哭、工作和凶杀,就像钟摆一样在那安全而狭窄的轨道上不停地摆动,在笑声与眼泪之间摆,这就是美国愿意给黑人设定的位置。”[9]
由此可见,赫斯顿就是这样被彻底打入了冷宫。
赫斯顿被重新发现是历史的必然。随着黑人民族自觉斗争的不同深入,黑人政治地位的不断提高和经济状况的不断改善,及黑人民族文化主义者已经步入了时代的舞台,一种对“黑色”前所未有的自信在黑人心中产生了。黑人对于自己传统文化那种不置可否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再把它视为“劣文化”。黑人艺术家们不但在作品创作中颂扬黑人传统文化的价值观,而且认为他们必须转向黑人民间生活,去寻找新的表现形式和内容。就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赫斯顿从被遗忘的角落里挖掘出来。因此,她的再生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
收稿日期:2000—06—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