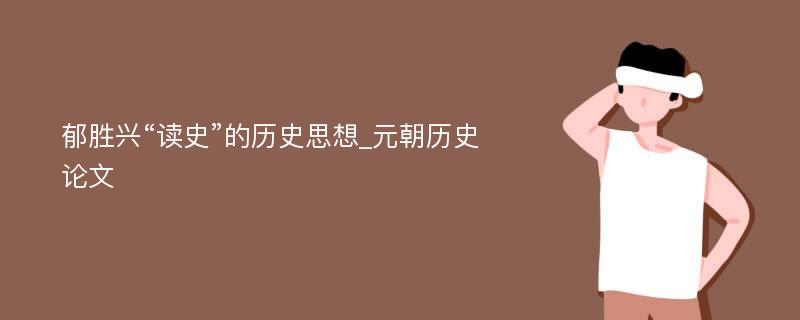
于慎行《读史漫录》的历史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历史论文,读史漫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2)06-0061-06
于慎行(1545-1607)字可远,更字无垢,谥文定,山东东阿人,万历朝官至东阁大学士 ,是明代一位很有声誉的政治家、文学家。于慎行对历史也有许多见解,这主要见于他 的《读史漫录》一书。
《读史漫录》是一部历史评论著作。主要以《史记》、《资治通鉴》等书为依据,评 论历代史实与人物。此书为于慎行在“山居谢客”期间所撰,“秘不示人”,唯其门人 郭应宠得以诵读。于慎行去世后,郭应宠为之“厘次订讹,分汇为十四卷”,大致按所 论之事的时代编次,上起远古伏羲,下迄元代。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四十一年(161 3)曾两次刊刻《读史漫录》,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黄恩彤因钦佩本书,又予以“参订 ”,其“参订”本流传至今。
清代四库馆臣对此书有所评价,称其“所论无甚乖舛,亦无所阐发”。[1](P762)1996 年8月齐鲁书社出版《读史漫录》一书,其《前言》认为:“本书立论大致堪称公允, 并时有卓见”。[2](P3)二者评价,颇有出入。瞿林东教授曾撰《读<读史漫录>琐记》 一文,指出于慎行读史“以‘当天下大事’为寄”,这“正是清代四库馆臣所忽略的” 。[3](P210)文中并对《漫录》中的史学思想作了勾稽与阐发,《读史漫录》的价值才 进一步引起人们的关注。
《读史漫录》始终贯穿着作者对历史的深刻见解,特点是其史论多围绕朝代的治乱存 亡而发。于慎行在史论中主要突出了四个方面的问题,并做了相当充分的阐释:历代治 乱兴衰的根本原因在于“纪纲”;在朝代兴亡的关键时期,有关历史人物及其决策起了 决定性作用;在民族关系中,应公允地评价少数民族与中原皇朝;在认识历史的方法上 ,他着重分析“时势”与“机括”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揭示了历史运动的法则。这四 个问题从不同角度强调了人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这些史论时代气息浓厚,耐人寻味, 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明人对历史的认识,对我们现今思考历史问题,也多有启发。
一、论治乱之原:“天下治乱,惟纪纲”
关注历代兴衰存亡是《读史漫录》的一个主题。对此,于慎行既有其相对普遍的 认识,又能结合不同朝代的特殊情形进行灵活分析,具有启发性。
综观《读史漫录》,可以看出,于慎行认为,“纪纲”是任何一个朝代维系其治乱兴 衰的根本原因。他评论唐文宗朝政时,明确提出:“天下治乱,惟纪纲。若纪纲常张, 即委裘之朝,可以卧理。”[2](P316)
纪纲,也称纲纪,原意是指网罟,多用来比喻朝政。“以网罟喻为政,张之为纲,理 之为纪”。[4](P588)所谓纪纲,可以理解为是对朝政根本制度的实施与管理。在于慎 行看来,纪纲在历代治乱兴衰中都起着根本作用,而在不同的朝代或一个朝代的不同时 期,纪纲的作用又有不同的实现方式。以于慎行对东汉、唐、宋、元代的纪纲状况的分 析为例,可以深入看到“纪纲”在朝代兴亡中的意义。
如论东汉国势的衰败时,于慎行指出乾纲不正是东汉灭亡的根本原因:“桓帝愤梁冀 之横,而与宦官图之,冀诛而权归于内矣;何进愤宦官之乱,而召外兵诛之,内靖而权 归于外矣。总之,乾纲不正,太阿倒持,不彼则此,不左则右,国事至此,何可为者? 观治乱之原,不可不深求其本也。”[2](P120)在这里,于慎行从不同角度称“纪纲” 为“本”、“乾纲”或譬之为“太阿”。所谓“乾纲不正”、“太阿倒持”,是指皇权 已经不完全在皇帝的掌握之中,而过分地倚靠宦官、外戚等。于慎行提出,东汉衰败的 深层原因在于其“根本”已经动摇,即“乾纲不正”,所以才导致变乱屡出不穷,失去 控制。可见,于慎行是把纪纲作为一个朝代治乱存亡的源头与根本来看的。
在论唐朝朋党之争的恶劣影响时,于慎行指出,整饬纪纲还是消除政治纷争的根本手 段:“牛、李之构党也,人主叹曰:‘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此虽无可奈何之 辞,而事理实有然者。河北之贼,所伤在支干,朝廷之党,所伤在腹心。去河北之贼, 所资者兵、马、钱、谷,难办而易筹;去朝廷之党,所仗者纪纲、法度,易知而难行也 。”[2](P310)在这里,于慎行从消除朝廷内部政治纷争的角度,分析了朝廷朋党之争 恶于地方反叛势力的原因。他指出去除朋党之争,能够依靠的正是朝廷的纪纲与法度; 而纪纲已受到朋党势力的左右,如何还能依靠呢?这个评论一方面说明,纪纲是约束、 扼制朝政中不法现象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也说明纪纲被破坏至一定程度时,对于乱政 是无能为力的。由此进一步说明,维护纪纲对于一个朝廷有重要的意义。
于慎行还对纪纲的复杂多样的历史表现形态做了分析。如论东汉,纪纲问题表现为大 将“怙宠恃权,恬不愧畏”、“母后在御,外戚柄国”等,唐朝有朋党之争,宋朝有姑 息之政。元作为外族入主中原,同样存在纪纲问题,且有其特殊之处。于慎行提出,从 来还没有哪个朝廷在建立初期就迫不及待地理财;元朝建国之初即急于理财正是纲纪不 立的表现:“此固不在理财,而在纪纲之不早立也。”[2](P501)而元朝纪纲问题的根 本,在于元朝时太子的确立皆不得法:“元时太子皆不早定,一帝上宾,集亲王议所立 ,而其地方廖阔,亲藩出镇,多在数千里外,甚者万里,往往难于虚位,权宜居摄,遂 为继世之争,故政之不纲,此其根本也。”[2](P508)他对元朝纪纲不立作了详细说明 ,指出了元朝无纪纲的种种表现:“元自世祖统一,诸帝相传,类皆中才之主,非有淫 虐悖乱,失德之事也。亦能响用儒雅,兴起文教,颇采先王之法,以变旧俗,亦非有倾 覆危乱之机也。惟是立国以来,朝无纪纲,国无章程,上无家法,下无职守,大臣可以 杀亲王,妃后可以笞宰相,太子可以阻兵,诸王可以衡命。国师之体,与人主同尊,将 相之体,与奴隶无异,其鄙朴狙犷之风,与女真、契丹已自悬绝,况于中华之声教乎? 所谓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2](P514)元朝大臣、妃后、太子、诸王、国师、将 相等不守身份、恣意作为,原本是蒙古族游牧生活的遗风使然。但于慎行通过对元朝君 主的德才、任人、政策等的分析,去除了元朝败亡的其他原因。他指出,这种粗犷之风 与过去的纯朴已有所不同,何况它与纪纲相差很远,这正是元朝不能长久的原因,从而 更深入地揭示出纪纲对元朝兴亡的意义。
在于慎行的史论中,纪纲不修有多种表现,此不再详举。他所说的“纪纲”实际上是 指维护皇权稳定所必须的、规定的统治者之间的行为规范。于慎行对纪纲的强调,既是 封建制度维护皇权所决定的,同时也与他对明代诸多“近日之弊”的深切关注有关。在 他看来,有明一代尖锐的治乱问题,如朝廷内部政治斗争激烈、民族矛盾严峻、中央与 地方割据势力的斗争以及层出不穷的人民反抗等,皆与纪纲紊乱有关。例如,于慎行论 元朝官制之弊时引申论及明代,认为明朝官制“职任体统”不当,如藩司受到上层职司 的过度牵制,职官设置冗杂、混乱,严重影响了地方行政职能的发挥:“……本朝效其 遗意,设十三藩司,与六部品级相亚,盖犹有行省之意。而职任体统,则以内制外,有 相临之分,固唐、宋监司之任也。抚按之体日隆,而藩司俯首趋承,若其下吏,又卑于 设官之初,则失甚矣。”[2](P501)于慎行是经过对唐、元与明朝官制的比较后得出上 述认识的。他由元朝尚书、行省的设置,看到广置丞相、参知、平章等职,无异于遍设 宰相,不仅职官臃肿,而且彼此稽查,职权纠缠,实际上使纪纲削弱,最终危及国家。 而明朝藩司受制于六部抚按,就像元朝各省职权彼此混杂一样,也是治理中的隐患。而 藩司能否有效地发挥作用,直接关系到明朝边疆的安定。
于慎行对明代纪纲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如御史“下至米盐琐细,吏卒徭役,一一察之 ”,长吏佐史“互相诇察”,[2](P86)边镇“法令滋烦,权任无统”[2](P 63)等职责不守、人事纷争、职司不明、临事掣肘的现象与弊端,有很多明晓的评论。 这些评论与明朝中央集权高度集中有关。明朝为解决皇帝与内阁、首辅以及朝廷与地方 之间的矛盾,使所有权力直接对皇帝负责,导致权力机关变得膨胀庞大、职司冗杂、效 率低下,成为明朝治乱的严重问题,于慎行的史论显然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二、论决策与用人:“夫成败之机,决于一言,顾用者何如耳”
《读史漫录》中论述最多的,是历史人物的行为及其历史作用。
于慎行重视人物评论,是因为他看到,在朝代兴衰存亡的关头,常常面临着一个历史 选择,它要求人们能够正确认识形势,衡量利弊,抓住时机,采取有效措施,保证事态 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在这时,人就显得很重要,人的谋略就显得很重要。他说:“夫 成败之机,决于一言,顾用者何如耳。”[2](P134)这里所说的“机”,是指关系成败 的时机;“言”指的是决策;“用者”,主要是历代君臣,尤其是位居险要,直接关乎 纪纲存否,关乎事态顺逆的大臣。可见,于慎行是从历史的关键时期及相关决策的角度 ,来强调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的。
于慎行推崇那些能够为国家利益着想的人物及其谋略。他认为,“成败兴亡之机,有 一言而定者,此士之所以贵智也”。[2](P205)因为士人的决策往往关系国家的成败兴 亡,所以士人应该重视智谋。对历史上一些人物的智虑,于慎行提出了更公允、精到的 认识,往往超出时论,不拘泥于儒家正统思想的成见。如他对汉代刘敬提出的方略十分 肯定,认为“刘敬所建白数事,皆万世之略。其大者在建都长安,与徙天下豪杰以实关 中”。[2](P42)提醒当国者应借鉴古代成功的治国方略,重视地理形势对国家安危的重 要性。他论及管仲、乐毅之事,以为其才能有隐微难及之处:“管子一匡九合,功盖天 下矣,即乐毅伐齐,其才亦有不可及者……乐之功不难于取齐,而难于散四国之兵。” [2](P16)他指出,管仲和乐毅的才能,并不只在于辅助齐国或燕国在一次战争中取得了 胜利,他们的高超之处在于,身处多国矛盾之中,却能够纵横捭阖,或称霸诸侯或化解 诸侯的威胁。他指出了管、乐的杰出之处,启发人们认识历史人物的价值时注重对其才 能高下显隐的分析。由于注重人物识见的作用,于慎行对那些有政治才能的女主,也予 以相当的肯定:“天之生才,岂惟豪杰丈夫有关气运,即妇人女子与治乱相关者,其生 亦必有自,齐之君王后是也。”[2](P22)这就从理论上对女主存在的合理性做了肯定。 甚至对一些奸臣的正确建议,于慎行也给予肯定,认为不应因人废言。[2](P292)
对历史上那些行为不当而危及国家的人,于慎行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批判。他常常将 历史上朝代的盛衰归因于当时的人事,认为良臣可以挽救国运,而佞臣则会断送朝廷。 如论东汉时,于慎行感叹道:“天下事虽甚难,处者亦必有方略,顾人不思耳。”[2]( P26)他认为,东汉纪纲虽然遭到破坏,国势已经出现衰落的气象,但是宦官、外戚的势 力还不是十分强大,汉桓帝以藩侯继位,正是汉朝挽救朝纲的机会。如果有一二个正直 且有谋略的大臣,东汉就能度过危机,使形势好转。可惜,汉朝当政者犹豫不决,不能 及时任用良臣,以至于错失机会。而奸佞昏庸之臣则足以误国,如唐朝“武氏之立,虽 由李义府、许敬宗发端,其实成于无忌,决于李勣也”。[2](P213)“安禄山之反 ,国忠激之也,哥舒翰之败,国忠成之也。”[2](P251)“元和之末,方镇厎平,长庆 之初,河北复叛,盖有由焉。幽州之乱,宰相崔植等激之也。镇州之乱,度支崔棱激 之也。”[2](P304)“武宗削平僭乱,比迹元和,李德裕之功也。”[2](P318)又如论宋 朝史事时他激愤地讲道:“自古国家成败,固系所用何如,然未有如宋之可恨者也。… …忠义之士,数十人持之而不足;邪佞之贼,一二人坏之而有余,天壤间事有如此,可 不为扼腕太息哉!”[2](P458)
于慎行还进一步揭露了小人误国的心理原因:“小人贪秋毫之利,而忘丘山之祸,以 至丧国亡家灭宗绝祀,皆起于一念好利之心耳!”[2](P26)这是于慎行在分析秦灭六国 时提出的。他认为六国的灭亡主要并不在于秦国,而在于六国国内的趋利小人。这对于 人们识别忠奸贤愚,认识官员的一己私利之心对于国家安危大事的必然的恶劣影响,有 强烈的警戒作用。
当然,我们不能苛求于慎行超越英雄史观的窠臼来评论历史人物。应当强调的是,于 慎行重视人物及其谋略在历史中的作用,是以历史有一定的形势与事机的观念作为基础 的,也与他久在仕途,忧心国运有关。于慎行对历代君臣的评论,不因其是君主而神化 ,不因其是功臣而饰罪,不因其是君子而忽其小人之心,不因其人微而轻其言,实事求 是,只论其言行对国家朝廷是否有利。其中的很多评论,多有发人深省之处。
三、论民族关系:“天理民彝,不以华夷有间也”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怎样看待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是衡量人们历史见解的尺度之 一。于慎行非常关心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以及对民族关系的处理。他的看法突出表达了他 在民族关系问题上的客观态度。
在《读史漫录》中,于慎行一方面仍贬称少数民族为夷狄,认为其落后野蛮,在根本 上视之为中原的异类而加以戒备。另一方面,他的大多数有关少数民族的评论,却是比 较客观的分析,十分坦诚地承认并肯定少数民族的社会地位。于慎行认为,“天理民彝 ,不以华夷有间也”。[2](P493)意谓天地间的法则和伦理不会因为族类不同而有所差 别,是各民族共通的。借天理民彝之说,于慎行对少数民族与中原皇朝平等视之。这对 于改变传统上对少数民族的偏见,无疑是一个进步。于慎行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他看 到,少数民族保存了纯朴的性情和刚强的精神,这些优秀的品质正是那些落后的边族在 与文明昌达的中原皇朝发生战争时能够获胜的主要原因。以北魏孝文帝改革为例,于慎 行曾提出一个不同寻常的观点:“北魏之治,至孝文而盛,其国势,至孝文而衰。…… 夷之所以能胜中国者,徒以其质朴、武健,不好文饰而已。”[2](P179)对于魏孝文帝 ,于慎行并没有简单地加以褒贬,而是看到了盛治中的衰落,是颇具辩证性的认识。他 认为孝文改革未能尊重鲜卑族自身的特点与优点,盲目汉化,使得改革与国势的发展不 相宜。应该说,这个评论对于少数民族避免盲目改革是有警示作用的。从理论上看,这 是发前人之所未发的见解。
对历史事实的尊重与民族理论上的探索,使得于慎行对少数民族的评论展示出很开阔 的胸襟。如他称赞元世祖“宜其混一函夏,功高万古也”,[2](P503)对元世祖的帝王 之略及其统一中原的帝王之业毫不隐晦地予以肯定。对其他边族里的优秀人物也表示称 赞:“夷人每有至性,非中土所及”,“夷狄中往往有忠义之性”等。对此,于慎行认 为原因在于生活方式的差别:“夫效死之节,不见于士夫,而见于夷狄,不出于侯甸, 而出于遐荒,其故何也?大抵都会繁华之地,渐梁浇靡,驰逐声利,忠义之志消,而激 奋之气微。至于遐方远侥,风气淳庞,未尝梁俗鹜华,有所移易,故骁健之材,忠贞之 志,往往有中土士人所不能及者,其居使之然也。”[2](P160-161)
与对少数民族的赞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于中原皇朝,于慎行则深入剖析了其统治 中的各种失败与弊端,对其腐败的痛心鞭挞常常溢于言表。
于慎行十分悲愤地嘲讽、抨击历史上当政者在处理民族关系时的无识无能。他批评中 原朝廷诸大臣或盲目自信或迂腐无知,不知为国之重,恳切地提出“要之制御夷狄,固 不可待之以诚,犹不可不料之以智”。[2](P469)在民族关系上,与仁政为国相比,于 慎行更加注重运用策略来维护国家的利益。他肯定对边疆少数民族应该“惟恩惟信”, 但反对不分形势,迂腐愚昧到损害国体,放弃斗争的地步。他鞭挞宋朝在民族冲突中懦 弱卑劣的政策,指出其当边族入犯时“则召援,援至则议和”,而当边族退去后“则挑 衅,衅成而求解”。[2](P457)他指出,中原朝廷在面临外患时,应当积极备战,锐意 进取,而非苟且偷安。他赞同对少数民族的羁縻政策,如论唐事:“太宗问李继捧曰: ‘汝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诸部?’对曰:‘羌人鸷悍,但羁縻而已,非能制也。’此虽 漫应之语,其实制伏边夷之道,不出于此,即班超告任尚之言也。多事之徒,为苛法以 扰,即决裂而去矣。”[2](P380)李继捧所讲的“羁縻”与“制”是两种不同的政策, 于慎行认为“制”是向少数民族推行繁苛的中原法制,他反对这种强行治理的民族政策 。他对历史上轻率借用边族兵力来解决民族危机的做法,给予严厉批评。如论唐借回纥 兵讨伐史朝义一事,于慎行指出,回纥兵虽然有功于唐,但平定史军主要还不是回纥的 力量;而平定内乱后,回纥兵借机肆虐中原。于慎行以历史为鉴,恳切告诫后人不能轻 易采取类似做法。
于慎行认为,中原皇朝在民族关系中的无能还表现在文法之吏操权弄柄、愚妄无知。 论及唐朝大将薛仁贵、郭子仪威慑突厥、回纥之事时,于慎行批判了刁难、严苛大将的 文法之吏:“文法之吏,喜以三尺绳人,克核之流,好以微瑕指摘,往往折长城于万里 ,摧隆栋于夏屋,而国亦随之。古今若此众矣,可为短气!”[2](P219)论唐光宅元年路 元睿系治胡商一事时,于慎行进一步批评文法之吏侵犯胡商的正当利益:“中国之御夷 狄,惟恩惟信,可以伸威,平时吏士侵渔,上不能禁,使其积忿在心,卒有不逞,所损 多矣!”[2](P219)论宋朝世守麟府的折氏受到监司严厉约束而请求解职一事时,于慎行 抨击文法之吏不能维护反而破坏保塞边族的护疆之心:“保塞蛮夷,惟在为国宣劳,不 侵不叛。至于居处出入,固不必纯用汉法,而以三尺文施于藩篱之虏,使其狡焉有不安 之心,非国之利也。此等事端,起于执法之吏,以深刻取名,守土之官,以好功启衅。 一旦狂澜溃溢,堤防横决,从而收之,亦何及乎!小人慕旦夕之功,为国生事,往往如 此。”[2](P419)历代边将邀功,往往是激化民族矛盾的原因之一。于慎行对此予以鞭 笞,是为笃论。
于慎行对历史上民族关系的重视是有现实原因的,民族矛盾始终是明朝一直未能解决 的问题,并几次严重威胁到明朝的安全。于慎行在史论中警告明朝当政者要正视边疆少 数民族的强盛,在处理民族关系时既要维护国体还要讲究谋略,更不能懦弱屈服。他对 明朝的拳拳之心跃然纸上。
四、论时势与机括:“旋转之间,皆有机括,非以力胜者”
于慎行的史论中贯穿着一个突出的历史观念,即对时势的认识。它既反映了于慎行对 历史的理性认识,也是于慎行的一种历史认识方法。这个历史观念包括以下几层含义:
首先,历史有一定的内在趋势,于慎行常常称之为“势”。《读史漫录》中,“势” 是普遍存在于各种历史事物中的,而且对于不同的历史事物,“势”的表现和意义也有 所不同,如地势、权势、国势、远近之势、大势、当时之势、事势、形势、时势、声势 、情势等等。这里所举的种种的“势”,其含义固然不尽相同,但根据于慎行对大量具 体历史形势的分析,可以看出,所谓“势”是指历史事物所关系到的各种矛盾或力量的 对比,它成为驱动历史事物的内在力量,决定着历史事物的发展方向。于慎行指出,这 种力量即历史形势一旦形成就不可挽回;即便推行一定的措施,也不能改变大势所趋。 “天下事有势成而不可返者,即约之以法,亦无益也。”[2](P271)但对于已经出现的 历史形势,也并非不能有所作为,如果能够把握历史形势的特点,因势利导,就可以使 之发生变化,如论“天下积习极重之势,欲有更张,须以渐为之,使其耳目不摇,乃可 以济”,[2](P339)等等。
“势”中不仅包含着历史方向的意识,而且包含着历史综合力量的意识,对于人们认 识历史的客观性、复杂性及规律性有一定的帮助,是对中国古代“德”、“力”、“心 ”等含义的补充。例如,对“势”的认识会带出“势”与“形”的区别。于慎行看到, 历史上有很多事情看起来很相似,但实际上在内在形势上却有很大差别,他曾指出:“ 事有同形而异情者,不可不辨,然后效亦可睹哉!”[2](P49)于慎行对远古与后世帝位 传承的区别,就是建立在“事”与“势”的差异上的:“尧舜之禅代,非后之禅代也, 事不同也;汤武之放伐,非后之放伐也,势不同也。”[2](P6)帝位由同姓之间的传承 变为异姓之间的争夺;不为天子亦有宗社,变为帝位失去后九庙全毁,于慎行所看到的 历史上帝位传替的变化是微妙的,反映的却是历史上皇权发生的真实的大变化。他触及 了历史上皇权转移的残酷,揭示了皇权历史的事势变化。
其次,历史的内在趋势又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一定的状态,比如萌芽之时、盛 极之时和衰败之时等。《读史漫录》中的很多史论,是对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由来、 起始、状态等的描述和评论。如论“天下之事,必有所由起”,论史还应“推致乱之由 ”,“求其始之所以是”,否则,将不能认识历史形成的真正原因。如论战国时齐国之 乱、吴楚之构时,于慎行指出,轻微的历史起始事件往往酿成严重的历史变化:“夫以 及瓜之代,事至眇也,而至于弑君,争桑之忿,怨至微也,而至于伐国,故蚁穴之漏, 或至滔天,灯烬之延,可以燎野。”[2](P9)历史由来与历史形势有密切的关系,它们 相生相成,即历史形势是由一定的历史由来而开始,当历史形势发展到一定的极端状态 就会催生出新的历史由来;而细微的历史由来也可能发展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形势。他 对曹操、王莽篡政的分析即说明了这个道理:“乱臣贼子,其始进用,未必即有异图, 惟是权宠日盛,势不得下,又见有可为之资,于是逆节萌焉。”[2](P91)在他看来,曹 操、王莽等“乱臣贼子”篡权并不是突然的,他们甚至不是从一开始就心图不轨,而是 一定的环境和条件逐渐促使他们生成了篡逆之心。在这里,于慎行把曹操同王莽相提并 论,有些不妥,但他讨论的是历史事件(曹操、王莽等篡政)的由来(“逆节萌焉”),讨 论的内在前提是历史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趋势(即“势”)。
第三,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决定其发展方向的重要时机,于慎行在史论中称之为“ 事机”、“机”、“机括”、“关节”等。在他看来,天下事“事无大小,必有机括” ,[2](P230)不同的历史形势有不同的历史事机,如果历史形势发生了变化,那么其中 的事机也会发生变化。如当历史形势缓和下来时,事机也随之缓和了下来,所谓“时异 而机缓也”。[2](P378)他认为,事机是历史发生变化的重要时刻,事机到来时,一旦 轻易错失,历史趋势就难以回转了:“天下事惟创始一事姑息,苟幸目前省力,机括一 发,不可复转,以至万万难处。”[2](P343)但如果临机轻举妄动,则也会适得其反: “天下之乱,有将成未成之机,欲制其萌,惟当俟间而动,不可轻有所试,以发其机。 发而不可制,则权首将受其咎,而大乱遂成。”[2](P217)所以于慎行非常看重事机在 历史变化中的关键作用,并认为这是谋略的基础。他常讲“安危之机决于一瞬”,决不 能“牵制优柔,坐失机会”。[2](P390)他指出,不少历史人物能够成功,正是因为他 们把握住了历史事机,“旋转之间,皆有机括,非以力胜者”。[2](P463)
据事机之论,于慎行还提出了古今之辨的认识:“天下之事,各自有机,以古裁今, 只见其泥耳。”[2](P186)“机”既有关键的意思,表明任何事情都有紧要之处;还有 机巧的意思,表明事情的关键各有巧妙之处,不会雷同。于慎行认为,天下任何事情都 有其关键之处(即“机”),因此彼此不同;不能拿古代的事情来裁夺今天的事情,否则 就只能是拘泥于古代了。
于慎行在《读史漫录》中虽然没有更为系统、深刻的形势理论,但他对形势论做了十 分广泛、灵活的运用,使中国古代历史上的许多具体事件与人物获得了新的解释,加深 了人们对“势”的认识。
收稿日期:2002-03-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