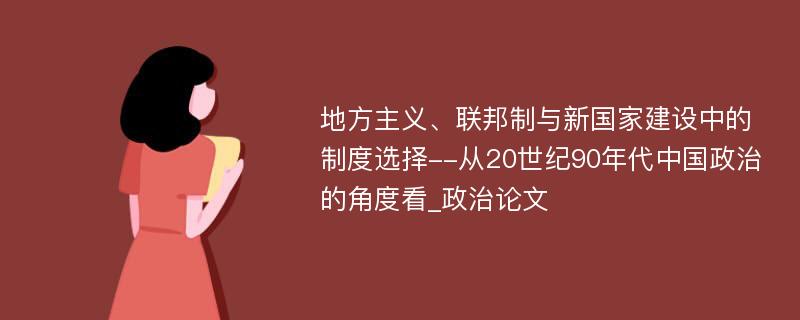
地方主义、联邦主义与新国家构建中的制度选择——考察1910年代中国政治的一个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方主义论文,中国论文,联邦论文,视角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7)04-0063-08
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超大型国家,处在传统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急剧转型的1910年代,传统帝国倾覆后,新国家如何构建,制度如何选择,无疑是1910年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基本主题,也是摆在那时国人尤其是政治精英面前一个根本而又棘手的问题。国际环境和时代背景决定了新国家的构建不可能再是传统帝国制度的简单复制、循环和延续;清末以来国内政治生态和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尤其是地方性力量的成长和壮大,也使新国家构建中的制度选择更加复杂多变。换言之,地方主义、联邦主义使20世纪初中国政治建构增添了新的制度选项,展现和凸显了1910年代中国政治发展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极端的复杂性。
一、民族国家构建中地方主义与联邦主义的互动
在民族国家的语境中,地方主义和联邦主义是有着某种相关性的两个概念,地方主义作为一种表达人们对某一特定地方认同和维系乃至扩大该地方利益的观念和行为,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自然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但国家产生以后,地方主义又有了政治层面的意义,即是指人们的地方政治认同和维系乃至扩大该地方利益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行为。联邦主义则一般是指一个民族国家中权力由中央与组成联邦的成员单位分享的思想和制度安排。联邦主义有时专指其观念形态;其制度形态即所谓联邦制①。在某些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程中,地方主义和联邦主义形成了一种新型互动关系。
一方面,地方主义的新发展,使民族国家构建有了新的制度形式。从古代到近代,国家发展变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国家增大,“在15世纪晚期,欧洲就包括了500个左右的独立政治单元,它们的边界划分常常是模糊不清的。但到1900年,这些政治单元的数目已减少到25个左右”。[1] (P34)中国自秦代开始就形成了大一统的多民族的国家,在直到民国成立前的两千多年中,虽然疆域、人口、民族及行政区划等多有变化,但总体上是扩大的。地域扩大和人口增加使一个民族国家内部的地方性问题凸显,地方诉求、地方认同对国家构建和政治一体化产生重要影响。诚如英国学者维尔分析美国政治的地方主义模式时所指出:“对某一地区或某个社会集团的依附感,向来是人们忠于自己的政治理想、采取政治行动的一种最强大的动力。一个人一旦把他自己同某一地区或某个社会集团的利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以致在那个范围以外他的生活就会失去任何真正的意义,那末,他就已经准备在必要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维护那些利益。在民族意识高度发展的国家里,国家本身就变成这种忠诚的唯一焦点,但在实现全国彻底团结的道路上,还要经历许多阶段,在这些阶段上,对一个地方和一个地区的忠诚可以达到与对整个国家的忠诚同样的程度,有时甚至更为重要。”[2] (P17-18)
国家构建和政治整合过程中,如何包容地方多样性,如何代表和综合不同的地方利益,都是地方主义的发展给民族国家构建提出的问题和挑战。正是为解决这些问题和挑战,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一种新的政治理念、新的国家制度和国家结构形式——联邦主义被创制出来。第一个联邦制的民族国家——美国的诞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被英国分而治之的北美十三州,“具有相同的宗教、相同的语言、相同的民情和几乎相同的法律,并与共同的敌人进行斗争,因而可以说有强大的理由使他们彼此联合起来,结成为一个单一的国家”。“但是,由于他们一开始就各自单独存在,拥有独自管理的政府,所以各自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利益和习惯,对于会使他们各自的重要性消失于全体的重要性中的坚固而完整的联合表示反感。”[3] (P124)在构建国家时,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把联邦建成一个各州保持独立的联盟,或一种召集各州代表在一起讨论与共同利益有关的某些问题的大会”;另一种是“把美洲各殖民地的全体居民联合成为一个单一的国家”。前一种意见显然还是维系原来邦联的状态,即各州的独立存在;后一种意见则会使各州失去独立性,尤其是一些较小的州会变成“一个大国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最后,立法者采取了一种折衷的办法,将理论上不可调和的两种制度强行调和起来”。[3] (P131)一种既建立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又可保障其内部各成员单位的地方特性和利益的新型国家结构制度由此产生。
另一方面,联邦主义的思想和制度,保障和规范地方主义在民族国家内的发展空间。在民族国家构建和政治整合过程中,联邦主义虽是一种从分散到集中的思想和制度安排,但这种集中是以包容和兼顾地方多样性和地方不同利益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地方主义在联邦制国家中是受到一定保护的。对此,维尔在谈到美国的情况时指出:“美国是从独特的殖民地社会中发展起来的,以偏重于强调地方性忠诚的方式逐渐扩展,横跨整个北美大陆的;同时,1787年形成的联邦主义的宪法结构又为这些忠诚的持续表现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于是,区域性的行为方式就成为美国政治史上的明显特征。”“在美国的全部历史上”,“地方主义也一直是政治的原动力”。[2] (P18)
当然,地方主义的发展在联邦国家内毫无疑问又是受限和被规范的,即不能干扰和破坏联邦统一、安全和其他成员利益。正如托克维尔所指出:美国“联邦宪法的当初目的,并不是取消各州的独立存在,而只是缩小这种存在的范围”。[3] (P133)这一制度设计,在保有地方主义发展空间的同时,联邦中央与各州之间、各州之间是相互制衡的。任何一个方面的极端发展,都要受到其他方面的牵制。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援引孟德斯鸠的话说:“如果一个成员企图篡夺最高权力,他不可能在所有的联合起来的各邦中具有同样的权力和威信。如果他对一个邦影响太大,就会使其他各邦惊恐不安。如果他征服了一部分,那些仍旧保持自由的部分,就可能利用被他篡夺以外的力量来反对他,并且在他篡夺成功以前把他打败。”[4] (P42-43)
可见,联邦主义的制度安排是民族国家构建中对地方主义挑战予以积极回应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地方主义是民族国家构建中联邦主义这种新型国家结构形式的催生婆。反过来说,联邦主义则成为一种既可能发挥地方主义正面功能,又可能遏制其负面功能的制度选择。当然,从整个意义上来说,作为“基础性国家制度”的联邦制,“不是一种容易维持的制度,而且也未必能解决广大而多元的国家所面临的问题”。[5] (P263)
二、民族国家构建及其制度选择:1910年代中国政治的一个基本主题
一般认为,民族国家是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长河中创造出来的最强有力、也最为有效的政治单位。吉登斯说它“是拥有边界的权力集装器,是现代时期最为杰出的权力集装器”。它也是继传统国家、绝对主义国家之后的现代国家形式。[6] (P145)在吉登斯看来,“民族-国家存在于由他民族-国家所组成的联合体之中,它是统治的一系列制度模式,它对业已划定边界(国界)的领土实施行政垄断,它的统治靠法律以及对内外部暴力工具的直接控制而得以维护”。[6] (P147)概括说来,现代民族国家的主要特征有:完全自主和领土统一;中央集权;主权人民化;国民文化同质性;统一的民族市场等。[7] (P271-280)
而民族国家构建就是指自近代以来全球范围内发生和发展着的上述特征创立、增加和整合的过程。如果从“民族”和“国家”两个方面来理解,民族国家构建也可分解为“国家构建”和“民族构建”,显然,二者是不同的过程,前者主要是一个政治建构的过程,后者则主要是一个文化建构的过程。在非西方社会,这两个过程往往是重合与同步的。在近代中国也大体如此。一方面建构新的民族国家——中华民国;另一方面,建构新的民族意识——现代中华民族观念②。
同时,从总体上说,民族国家构建不是即时完成的,它甚至是一个漫长和复杂的历史过程,充满曲折和反复,尤其是在非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不仅受内外环境的影响极大,而且制度样本也会影响到制度选择。美国历史学家斯特拉耶指出:“民族国家的形成是缓慢而复杂的事情,过去五十年中产生的政治体系大都从来没有完成过这个过程。纯粹的模仿不能解决它们的问题,因为制度和信仰必须扎根于本国的土地,否则便会枯萎。”[8] (P167)但如果从特定的时间段上来看,民族国家构建的一般轨迹是从分散走向集中,显然它的含义主要是指国家整体和部分之间关系的构建,即国家结构形式的确立③。
分析民族国家构建,毫无疑问是探究其主体的活动,主体确认不容回避。其主体广义上包括“构建”的所有参与者,即参与这个民族国家构建的一切阶级、集团、政党乃至个人,也包括其他国家的政府和国际组织等。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该国内制度建构和制度选择的设计者、决定者和实施者,即政党、政治团体和社会精英。就1910年代的中国而言,主要是指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国民党,和其他政党、集团及其代表人物,以及其他政治和文化精英,尤其是领导革命和在新国家占据统治地位的集团及其代表人物。因为“国家的创建过程和现代国家体系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统治者不懈努力’的结果,‘这些统治者依靠其统治机构来扩展和保证他们的权力基础,并且提高他们自己在管理和动员社会资源上的有效性与影响力’。”[1] (P57)
当1911年以武昌起义和各省“独立”宣告清王朝这个传统帝国覆灭时,以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相号召的新的民族国家构建及其制度选择,就成为当时迫切的政治主题。何以言之?首先,从民族国家构建的一般情况上看,革命是民族国家建构的一种基本形式和基本动力。对旧的国家和社会制度而言,革命是一种剧烈的破坏;革命之后,马上就要重建新的国家和社会。在一整套国家制度中,国体和国家结构是其中基本的制度。有西方学者也将国家结构概括为两个“基础性国家制度”和“总体层次制度”之一,[9] (P113)所以,在民族国家构建中,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是单一制,还是联邦制,这是首先必须做出选择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其他制度的确立,尤其是中央和地方的各方面具体制度。而一旦被选定和形塑,它就拥有了稳定性与合法性,难以再进行整体性改变。所以,民族国家建构初始阶段的一般状况表明,国家结构形式的确立,是革命后新国家构建一个当然的政治主题,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恰值构建新的民族国家的伊始,当然也概莫能外。
其次,从实际情况看,辛亥革命后国家结构制度并不是已经确立下来的、无须选择的制度。恰恰相反,成为一个仍存在某种变数的问题。这一点,当时的政党、政治集团和政治人物的认知与关注以及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角逐是最好的说明。“1911年11月,当梁启超公开拒绝接受袁世凯提供的清朝官职时,他指出,国家面临的基本问题有两个:政体应该是君主制的还是共和制的;政体的组织应该是联邦制的还是一元制的。前一个问题已被革命解决了,而后一个问题尚待做出回答”。[10] (P252)1914年7月,戴季陶在《民国》杂志上发表《中华民国与联邦组织》长文,全面阐述了他的联邦制主张。其中,对这一问题在民初政治中的“主题”地位及对整个国家政治的决定性影响做过精彩的分析。他说道:“革命之失败,以省制不定为一大原因,而将来革命之机,亦动于此。识者其信吾言乎?自第一次革命成功以来,至第二次革命时止,其悬而未决之大问题为何乎?省制问题也。革命之起也,由于各省独立,是共和政治为各省势力所集合而构成者,事实如斯也。然而,自南京参议院成立时起,至国会被解散时止,此二年间,议院曾未有关于此大关键一定解决策。唯因循敷衍,以从事与不完全之立法,至国基不定,政本不立。中央与省之权限不清,各省之服从中央与否,纯为势力问题。是以在南京政府时,成各省独自成风之势,及袁世凯当权,更结中央压制地方之果。不特此也,各省相互间冲突无已时,中央党派消长之影响,直接则及于地方官吏。地方官吏为保其位置故,亦遂不能不各自置私。政海恶潮,达于极度。……且也,省议会既不成宪法上之机关,而都督民政长乃不能不为中央官吏之走狗。而县之一区域,在法律上无丝毫之保障,政治更无丝毫之位置矣。司法机关,亦为有若无矣。政治状态既若此,人民之权利自由其被蹂躏也非奇事矣。”[1] (P777-778)
再次,这一问题的反复和持续也是其主题地位的体现。袁世凯推行专制独裁和复辟帝制,不仅未能使新国家构建中单一制国家结构的制度选择确定下来,反而强化了地方主义者和一切反对专制追求民主的人对联邦主义和地方分权主义的诉求。护国战争后,一度被袁世凯压制的联邦主义声浪又起。1916年8月,国民党的《民国日报》发表署名佐治的《今后吾人之建国观念》的社论,直言道:“顾民国之组织究为单形乎?抑为复形乎?此实建国之根本问题。非有适当之解决,其政治终不能趋于正轨。”并指认民国为联邦制国家,“夫民国已成之形,固明明为复形也,何政治家讳言之乎。民国成立之历史以省为基础,此人人之所能言也。而今兹之重建共和亦以省之力为最大,是省之于民国为重要构成分子明矣”。[12] 同年9月召开的制宪会议上,“省制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论辩的双方一度陷于僵局。在此期间,有些甚至原来主张中央集权的人也转而提倡分权和联邦主义,李大钊就是其中一例。1916年11月李大钊在《宪法公言》第4期上发表了《省制与宪法》一文,一改两年之前秉持的中央集权主张,提出并详细论证了通过选择联邦制实现国家统一的观点,指出:“入民国以来,联邦主义与统一主义时呈对峙之观”,实际上,“联邦绝非与统一相背而驰,且为达于统一之捷径也”。[13] (P237)美国学者麦科德认为,“护国战争期间‘独立’的南方各省和‘忠诚’的北方各省再次宣布自治,这意味着重新回到应明确规定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宪法问题上来。广州政府为了依从支持自己的各省,不得不同意他们实行高度的省自治。”[14] (P93)此乃据实之论。
可见,整个1910年代,时人关注和冀求解决的国家政治问题中,国家结构即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制度安排始终是一个根本和焦点,由此凸显其在当时中国政治发展中的“主题”地位。
三、地方主义:民族国家构建中选择联邦制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原动力
一个有着长久中央集权单一制传统的大国,在革命之后的新国家构建中,国家结构的制度选择并不定型,联邦主义喧嚣一时,并付诸某种实际的制度选择。究其原因,固然很多,但地方主义无疑是个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是民初联邦主义思想和制度实践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原动力。
第一,清末以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国家重心下移和地方性力量扩张是其基本的社会背景。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发生后,在内外夹击之下,中央王朝维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能力大幅下降,不得不让中央以外的地方力量担负起拯救国家(王朝)、恢复和重建统治秩序的责任。但在政治生活中,权力和责任总是要统一的。让地方性力量承担起国家更大更多的责任,也就必须让他们分享更大更多的权力。此后,清王朝虽形式上还保持着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局面,但国家权力体制不断发生着实质性的改变,日益形成权力分散、权力重心下移的“多中心”局面,即所谓“督抚专政”是也。主要体现在军权、财权、决策权、人事权、司法权、外交权等全面地由中央向省级地方转移。并随着“洋务”新政在各地的不断开办,地方社会中“绅”、“商”阶层日益成长、壮大和活跃,与封疆大吏的关系也日趋紧密,直至形成利益共同体。一方面,绅商阶层的成长,使之越来越成为地方大员所倚重的力量,成为他们权力运转的物质和精神的支柱。另一方面,这种关系的发展,就使封疆大吏由中央代理人逐渐成为地方代理人,从而使省级国家权力的性质事实上悄悄改变,这种原本属于中央授权的权力俨然成了地方社会的自然生长物。换句话说,省级国家权力日益扎根地方,中央难以再拿回去了,这也是中央王朝所始料不及的。而清末“新政”中各省咨议局的设立,则可视为连接此时地方主义政治层面和社会层面的一种组织化和制度化。因为其议员大都由各省官僚和士绅组成。在因应中央王朝不利于他们双方的政策时,他们会以这个机构作为交流和共谋对策的制度平台。至此,晚清地方主义从中央权力向省级转移开始,到这种权力与地方社会结合为止,形成政治与社会的连接,中央王朝与各省在权力关系上出现了难以弥合的深深裂痕。从封疆大吏到咨议局议员等地方势力,几乎都成为革命可以争取和能够争取的力量。从某种程度上说,辛亥革命的发生和成功得益于地方主义的发展,反过来,地方主义经过辛亥革命也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对此,民初康有为的论说虽不失偏颇,但也不乏精彩。他说:“若今日危亡,中国之大患,尤在各省都督之自立也。因旧督抚专权之弊,遂成今都督割据之害。盖直省辖地之广大,督抚威权之专严,本已有半立国之体,适当革命之后,更用军兴之制,各都督拥兵自立,无所秉承,募重兵而专杀戮,用私人而任黜陟,聚货财而行纸币,争地域而事战攻,肆贪欲而厚贿聚。其于中央政府,只秉正朔而已,岂徒不奉号令,亦且不奉贡职,甚且虚张兵额,反索饷需,动以兵哗为相胁制。遂致政府自借外债,甘以中国听人监理,以羁縻之。比之唐之藩镇,周之列国,尤有甚焉。各省议局,不畏豆剖瓜分之祸,尚为窃权自治之言,日争自立之图,以助成专横之焰,遂致政府号令,不行于国门,外人觊觎,议分夫弱肉,而各省都督议员,乐巢危幕,熟寝积薪,争此席位,肆其贪狠,以为安也,岂不怪哉。”[15] (P749)
第二,辛亥革命后地方势力直接而持续的联邦主义的诉求和制度实践是其基本的体现。武昌起义伴随各省的纷纷“独立”,新国家的构建就提上日程,选择什么样的制度有利于保障甚至是扩大地方权益,独立各省的地方当局在既有的制度样本中,舍弃单一制而选择联邦制,可谓是一种理性选择。独立各省当局诸如湖北、江苏、浙江、江西、贵州、广西等的省级制度安排,或多或少都有联邦成分和色彩,明显体现在政府组织的中央架构和分享国家主权,如统帅军队、行使外交权等。[16] (P605-634)地方当局的联邦主义制度实践和诉求主张是并行的。1911年农历9月21日,独立的江浙两省都督程德全和汤寿潜联电沪督陈其美,倡议仿效美国,构建联邦国家。电文指出:“自武汉起义,各省响应,共和政治,已为全国舆论所公认。然事必有所取,则功乃易于观成。美利坚合众国之制,当为吾国他日之模范……急宜仿照美国第一次会议方法,于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关,磋商对内对外妥善方法,以期保疆土之统一,复人之和平。”[17] (P284)其他独立各省如山东、广东等也都有类似的呼吁。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地方当局这种联邦主义的诉求和制度实践,背后是清末以来壮大起来的各省士绅的有力支撑。诚如有学者指出:“各省(如湖南)的士绅都把本省看作是扩大参政权力、要求政治自主的合适的角斗场所。这种明显的地方主义并没有背离原来吸引晚清的士绅从政的民族主义,相反,它建立在一种认为各省实现自治就能使国家在整体上强大起来的模糊的联邦主义思想的基础上。”[14] (P87)
第三,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联邦主义主张和诉求,有对美国联邦制向往和移植的一面;也有对当时地方主义现实谋求理想的解决之道。在1910年代的中国,曾有过联邦主义主张和诉求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一时难做准确的统计,但章士钊、张东荪、章太炎、丁佛言、李剑农等是其中的代表者。纵观他们申述倡导联邦主义的理由,在赞美这一制度之外,就是当时中国地方主义的现实存在。对此,有学者指出:“盖社会上之论者,皆已深知,中国自清末起,省区尾大不掉之势已成,特别是辛亥革命军兴以来各省都督,自拥重兵俨然列国,加上省界意识已成,行联邦制度,乃是势顺而易之举。何况以本省之人,施本省之政,既合服务桑梓之情,对本省之政痛,易于着手改进,且进而能使各省竞争国家政治更添进步之动力,所以社会人士,颇多乐于附合此说,如章士钊等,就是其中健者。”[18] (P51)
第四,孙中山本人和国民党内的联邦主义的主张和诉求,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孙及其追随者对美国联邦制和民主制的憧憬和追求;二是因应现实的策略运用,即对抗袁世凯北洋集团的专制独裁和对地方主义现实的某种承认。有学者研究认为,“1911—1920年之间联邦的观念业已风行各地,而各省事实上已成为中国政治上的自主机构。但是,虽然有待于更进一步的研究,目前的资料却显示联治的观念二种截然不同的形式出现。国民党的联邦论,纯粹是策略上的运用——暂时撤退以待于全国有利于统一的政治情势。至于那些在1911年以来所流行‘宣告独立’风气下的士绅和保守分子,所倾向的联治思想,则似乎其来有自,反映了长久以来即已深入人心的地方分权思想。”[19] (P323)这种看法是符合实际的。
归根结底,1910年代,新国家构建中将联邦主义作为制度选项,表面上是各色精英的主张和活动,背后则是地方力量和地方主义的作用。
四、结语:博弈、权变与路径依赖
1910年代的中国,时代赋予开国和当国者及政治精英们太多太重的使命和责任,他们因出身背景、自身素养、理念信仰参差,及现实利害的考量,而力难胜任。无法像美国的开国和当国者们坐下来为构建新国家而谋划和创制,只能是因时顺势。当国者袁世凯以势张欲,传统单一制则破而复立;以省区为中心的地方主义扩张,则有联邦主义的诉求和制度实践。其结果形成新国家构建中制度选择的博弈、权变和路径依赖。
以中央(君主)专制为内核的传统单一制,是袁世凯等辈的制度需求。它实现的有利条件是:第一,其传统性使之易于复制,无需支付创制成本;第二,其大一统表征仍具感召力;第三,有当时国内最大最集中最强有力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的实力支撑;第四,无需付出学习成本;第五,一般大众没有接受的问题。而其实现的不利条件:第一,刚刚被打破,有复旧之感;第二,背负“专制”恶名;第三,孙中山国民党和地方势力以及追求民主制的精英存在接受的问题。
联邦制主要是地方主义者的制度需求。它实现的有利条件:第一,有成功的先例,有被接受的可能;第二,有制度样本,创制成本不高,可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制度设计;第三,与传统单一制相比,“新”的优势明显。其实现的不利条件:第一,“洋”名使一般民众陌生,有接受的问题;第二,有破坏统一之嫌;第三,虽有实力支撑,但显分散,不及前者;第四,需要付出学习成本;第五,北洋集团强力抵制。
中央地方均权单一制可以说是孙中山国民党的制度需求,也应是新的民族国家理想的制度需求。但它在当时几乎没有实现的有利条件,基本上都是不利的条件:第一,没有现成的制度样本,创制成本很高,短时间内无法完成制度设计;第二,无实力集团的支撑,孙中山本人曾在联邦和单一之间反复,国民党内当时更没有一个对此一致的意见;第三,理想色彩浓厚,不宜于实践。
综合比较可以看出,传统单一制虽最具备复制和实现的条件,但在当时的国际环境和时代背景下,受到后两者的牵制,无法实现合法性、稳定性和正规性复制和延续,未能体现为新国家构建中堂而皇之的制度安排,而是在与其他两者博弈中发生权变,外壳蜕变内核尚存。联邦主义作为外来的新的理念和制度,在新国家的构建中虽具备了某些实现的条件,尤其是有地方性力量作为其主体和动力,但由于它与中国文化和历史传统的隔膜,受到传统单一制的强力制衡,在1910年代的博弈之后发生权变,弃“联邦”这个洋名,造“联省”之名而意欲本土化。在长期大一统观念熏陶之下,民初的政治和知识精英们对联邦主义的认知也往往带上“中国特色”,将“联邦”与“分裂”划等号,“提到联邦便认为存心破坏统一”。[20] (P8)袁世凯等的恶意运作又强化了这种认知。1914年8月,袁氏发布大总统令,查禁国民党人宣传联邦制等主张的组织——人权急进社,谓:“夫联邦之制,系因其国内自相雄长,本为联署,故谋团体之结合,以巩固其国基,我国本系完全统一之邦,岂宜先自剖分,予人以可乘之机,殊不知其意何居。”[21] 造成倡导联邦之人或对联邦二字有时“讳莫如深”,或极力辩白联邦与统一之正相关性。经此蜕变的联邦主义,以联省自治的面目出现于20年代前半期,并形成了发展的高峰,但也不过是最后一搏。虽然1910年代新国家构建中的制度选择尚未出现最后的结果,但其轨迹已清晰可寻,即辛亥革命打破了传统的单一制后,在新的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现代中央集权单一制(即以民主制为内核,以中央集权为主,适当包容地方多样性)虽然是多种制度选择中理想的一种,但实际选择过程中居于主体和优势地位的只能是变了形的传统单一制。这种结果可以视之为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政治制度是一种人为创造物。大多数政治制度当然都会随着时间而演变,但是每个国家在历史的关键点上,都曾有过选择制度的机会,从而使政治具有‘创造性’”。[5] (P274)1910年代的中国恰恰就处在这样的“历史的关键点上”,方有了包括“基础性国家制度”的国家结构形式在内的制度选择的机会,但在这种政治社会剧变和历史大转换的岁月中,制度选择受到主体自身条件、需求和外部环境及其互动关系的影响和制约。在博弈和权变背后,实乃强大的历史惯性在起作用。
从地方主义与联邦主义的互动,考察1910年代中国新的民族国家构建的一段历程,不难看出,在当时的内外部环境下,一方面,新的民族国家构建中的“基础性国家制度”建设是何等重要而又难以一蹴而就,凸显其在1910年中国政治中的主题地位,而当时的政治精英又难以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适乎当时中国的理想的制度模型——现代中央集权单一制无法创制实施,变形的传统单一制复归,而使整个国家政治难上轨道,动荡混乱,不能稳定发展。另一方面,地方主义的极端发展,虽使联邦主义在新国家构建过程中喧嚣一时,但终因难契大多数中国人之需求又与中国历史、文化隔膜而无果而终。可见,对中国这样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家来说,越是在“历史的关键点上”,“基础性国家制度”建设的所谓“政治创造”越应考虑到制度历史和制度变革的关联、衔接、适应和协调。
注释:
①联邦主义也泛指一种分权制衡的思想和制度,“是一种政府形式”、“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甚至是“一种生活方式”。(参见奥斯特罗姆:《美国联邦主义》,第245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但本文还是在民族国家构建即国家结构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
②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及与中华民国建立的关系,有学者已做深入的研究,(参见黄兴涛:《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载郭双林、王续添编《中国近代史读本》(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所以,本文的“民族国家构建”,基本上不包含“民族构建”的意义,这也是正标题中使用“新国家构建”之所在。
③限于研讨的主题,本文的“民族国家构建”一词的使用主要在这个意义上,相应的,制度选择一词也主要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即国家结构的制度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