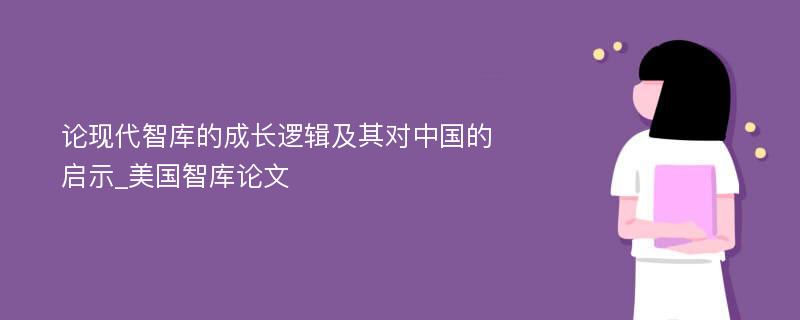
论现代智库的成长逻辑及其对我国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启示论文,逻辑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27(2015)01-0139-09 智库是现代公共政策活动发展的必然产物。现代智库自出现以来,一直在公共决策系统中占据重要位置,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与之不相称的是,很长时间以来国外关于智库的研究并不多见。直到1971年,以美国学者保罗·迪克逊(Paul Dickson)的《智库》(Think Tanks)发表为标志,第一部专门介绍智库的学术著述方才问世。其后,关于智库的研究逐渐深入并兴盛。现如今,国外智库研究已形成较系统科学的智库研究体系。相对而言,国内有关智库的研究尤为滞后,专门性研究在20世纪末才刚刚起步。但近年来智库逐渐为人们所重视,相关研究成果也量质齐增。从研究议题的倾向性来看,我们可以将国内关于智库的学术研究大体分为“理论认知—理论自觉—理论自信”的三个递次演进的阶段: 第一,“理论认知”阶段。智库是“舶来品”,早自1982年起,吴天佑等国内一些学者通过文献研读和翻译、实地考察及学术交流等方式认识智库,相关论述侧重于智库的概念引入、类型介绍和功能分析等描述性研究。这一时期的研究具有启蒙性,目的是让国内更多人认识和了解智库。 第二,“理论自觉”阶段。大约在2006年前后,以薛澜、朱旭峰、王莉丽等为代表的国内智库的先锋研究者不再满足于定性化的介绍性研究,开始深入探索和分析智库的运作机理、现实表现、未来发展等,研究方法也开始从单一的描述性经验研究转向比较研究、历史研究、定量分析等多元化研究。并且,专门开展智库研究的组织和团队开始形成,如2009年国内率先成立的专业智库研究机构——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尝试将研究视野聚焦于本土智库的研究,体现了中国智库研究者的学术自觉性。 第三,“理论自信”阶段。2012年以来,随着学界多年来的研究和呼吁,以及我国公共决策发展的现实需要,智库为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所重视,建设高质量智库成为政界与学界共同关注的热点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这也标志着国内智库研究迈入探索既有别于西方又不同于传统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阶段。此后,相关研究成果呈井喷趋势,在全社会形成了智库研究热潮。 显然,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近年来关于智库研究的热潮已经兴起。但是,“在全社会智库热之际,我们也必须对智库问题进行一些冷思考,对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进行梳理,避免由于认识上的误区而影响智库的健康发展。”①对智库基本问题的“冷思考”紧迫而确有必要,目前有诸多智库的基本问题尚需进一步探索,既有共时性问题,也有历时性问题。其中,关于智库的产生与发展等历史的基本问题显然不可回避。目前对此问题的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智库成长的现象描述上,研究内容大多偏好对智库成长的阶段历程的叙事,国外如唐纳德·阿伯尔森(Donald Abelson)的四次发展浪潮说、詹姆斯·G.迈克甘(James G.McGann)的四阶段说、詹姆斯·A.斯密斯(James Allen Smith)的三阶段论等,国内主要也是在遵循国外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或繁或简的区分。这些研究对智库成长的阶段划分大多是以业已形成的特征作为依据,至于这些特征是如何形成的、为何如此发展、相关因素是如何建构智库的成长等逻辑关系探究力度尚显不足。笔者认为,如果不能深刻理解智库的来龙去脉、不能准确梳理其中的逻辑关系,而迫不及待地开展诸如怎样建设智库、如何评价智库、如何提升智库影响力等更深入的研究,这种做法虽然能够促进智库研究的表面繁荣,但长此以往,却会带来认知上的混乱、甚至研究的不得要领的弊端。因此,历史地审视现代智库的成长,总结其生成和演变的必然性,从中提炼其合理性,并剖析其中的固有缺陷和不足,从而启迪与警示中国特色智库发展的探索,这恰是我们现阶段应该“冷思考”的一个基本问题。 二、现代智库成长的“知识——权力”逻辑 现代智库兴起于美国、发展于美国、繁盛于美国。一定程度上,一部现代智库成长史可以浓缩并体现在美国智库的全部演进历程中。学者贾曼和科兹米恩(Jarman & Kouzimin)甚至认为,智库成长的“种子尚未真正在美国以外的地区开枝散叶”②。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不少学者将原因归结为美国的政治环境,如里奇(David M.Ricci)认为,“如果不从美国民主政治的实际加以研究,便无法窥知智库的全貌。”③实际上,甚至“整个政策分析的发展主要是源于美国政府的巨大发展,而不是社会科学知识的发展”④。专业于政策研究和分析的智库在美国兴盛的原因,根本上是植根于美国的政治生态。那么,美国的政治过程中为什么要引入智库?笔者认为,现代国家的权力普遍建立在一定的知识之上,“知识一方面规范和约束权力的运行,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知识为现代国家权力运行提供正当性证明。”⑤权力需要知识,现代国家的发展也因此包含了权力知识化的趋势。所谓权力知识化,即权力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知识建构过程,意味着权力的合法存在及有效运行必须借助知识的确证和支撑。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政治系统的权力知识化倾向开始凸显,人们相信权力可以借助理性化的知识获得正当性,实际上,现代政治科学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然而,在1883年“彭德尔顿法”所确立的“两官分途而治”的原则下,政务官被赋予决策权,政策的形成主要由暂时性的(temporary)政务官所主导,而非职业常任(permanent)的事务官。“尽管政务官被赋予了决策权,但他们却缺乏做好决策工作的能力”。⑥这样,权力知识化与政治系统内部知识能力不足的矛盾就被呈现出来。如何化解这一矛盾?美国的政治实践演化出两条路径:其一是通过发展事务官参与政策制定,从系统内部挖掘公务员的专业智慧以弥补政策制定的知识不足。“在政策制定阶段,公务员所扮演的政策顾问的角色十分重要”,因为,“公务员被教育培训成为通才,凭借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比那些任期并不长的政务官更了解政策制定的细节”⑦。其二则是寻求诸如智库、外部专家等局外人的帮助,以获取决策所需的知识和咨询。而且,通过“旋转门”(revolving door)机制,智库同时还能够提供政府所需的政策人才,从而可以直接充实权力系统的智力资源。对于第一种途径,显然背离了这一时期所推崇的“政治行政分立”的原则,不可避免的模糊了公务员的非政治化或政治中立的立场。而且公务员过多的参与政策制定,还容易导致行政权独大和部门统治等问题。相对而言,第二种途径则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这类问题,这样,第二种途径成为美国政治系统的优选,体制外部的智库也在其中得以兴起,成为“知识和权力之间桥梁”。⑧当然,智库在逻辑上是被严格限定为超越党派属性、独立的外部政策参与实体。 智库兴起于权力知识化的过程,但智库真正发展并发挥作用,还得益于美国的权力体制的多元分散性和权力运行的开放性。首先,美国的权力体制具有明显的分权甚至是分裂的特征,表现在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与制衡的权力结构,还表现在由国会、行政机构、利益集团构成的“铁三角”格局以及联邦与地方各拥实权的权力关系等方面。在这种情形下,不同的权力主体往往需要不同的理性而有力的政策理念和政策方案,以影响公共政策进而达到预期目的。于是,“在这样一个多元独立的机构分享权力的系统中,决策者并不局限于政党程序,智库可以通过多个渠道沟通他们的想法到数百立法者。”⑨这就在客观上为智库介入政策过程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通道。其次,美国权力运行的开放性。政府具有天然的保守性,20世纪之前的美国政府同样也不例外。直到20世纪初,美国进入伟大的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政府在此期间进行了一系列深刻的制度变革,改革改善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提高了政府效率,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政府运作的透明度与开放性。而其后的“新政”(New Deal),则更全面地冲击了美国政府的保守习惯。“新政”选择了国家对经济社会的全面干预,突破了之前占主流的“自由放任”模式,这就“迫切要求学者们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去为这种国家干预提供理论证明和方式、方法的支持”,⑩与之前的拒绝开放相比,“新政”却热情欢迎专家介入到对政府的研究中来。罗斯福新政中专家的参与广度和深度是空前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智库的成长。实际上,智库的另一种指称智囊团(brain trust)一词就是在这一时期流行起来。(11)此后,美国权力运行的开放性不断增强,权力的开放性是智库政策研究和发挥影响的前提:一方面开放的权力能够接受外部的研究,外部智库能够较全面准确地从体制中获取研究所需信息,使得深层次研究政策体制和过程变得可行;另一方面,权力运行的开放性同时增强了政治系统对外部知识等要素流入的接纳程度和包容性,也使得智库的研究成果更便捷输入成为可能。 由此,我们梳理出一条智库成长的“知识—权力”的逻辑过程:在权力体制的多元分散性和权力运行机制的开放性条件下,政治知识化过程与政治系统内部智力资源不足的矛盾催生和催长了现代智库。这一背景下,现代智库在逻辑上被要求成为桥接权力与知识的中介者,同时还应是超越党派政治、中立的非政府组织。 三、现代智库成长的“知识—市场”逻辑 知识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成果,人类的认识具有无限性,因而从根本上讲,知识是可以无限供给的。但在人类认知发展的具体阶段,人类活动对知识的需求超过知识的实际供给的情况却可能存在,这就会出现知识的稀缺性问题。近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对知识的需求总量急剧增加,而“很多重要知识的可使用规模并没有同步增长,结果导致20世纪知识稀缺问题的凸现”。(12)知识的稀缺性赋予了知识的“交易价值”,知识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易或交换形成了思想市场。现代社会,咨询业是思想市场中重要的专业生产和供给知识的行业,而企业、公共机构、社会组织甚至个人均可能是思想知识的消费者。咨询业涉及范围较广,智库只是其中专门从事公共政策思想知识生产和交换的组织化主体,是思想市场中知识的专业组织者和生产者。也就是说,现代智库是思想市场中的活动主体,是咨询业的分支。据迪克森(Paul Dickson)的考证,智库最早出现在19世纪30年代的美国。1832年,美国财政部针对汽船上的蒸汽锅炉爆炸问题,与费城富兰克林研究所签订了委托研究合同,由此开启了政府利用外部研究机构的智慧去解决问题之先河。(13)虽然,迪克森的观点并不为多数学者所认同,但迪克森的研究至少揭示了其时提供知识服务的咨询业的客观存在。实际上,咨询业萌芽于19世纪初的英美,最早是面向工业化生产中工厂车间的工程技术咨询,如一般认为1818年成立的“英国土木工程师学会”就是最早私人咨询的开端。(14)此后,咨询活动的范围逐渐扩展至工业、农业、文化等领域,咨询活动的内容也由技术咨询延展至管理咨询、决策咨询等,其间也有诸如富兰克林研究所零星的政府咨询活动,但大都是偶然现象,并且为政府提供咨询的活动一般都不是这些机构的主业。直至20世纪初,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建构了对政策思想产品的市场需求,一批专业从事政策分析和研究并试图影响公共政策的咨询机构开始涌现,如1910年成立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1919年成立的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Revolution and Peace)以及1927年成立的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等,学界普遍将其时出现的这一类型咨询机构视为现代智库的起源。 智库发轫于现代咨询业,是思想市场的活动主体。但是,智库思想市场不同于一般产品市场,其产品的市场需求主要来自政府部门。正是政府事务的扩大以及复杂化建构了对专业政策知识的需求,激活了政策思想市场。迈克甘在系统梳理美国智库的演进历程时,将现代智库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并且认为每一个阶段都是由一些主要国际国内剧变引发美国政府事务重心的转变以及政策新挑战,进而激发新一代智库的创建。(15)具体来说,包括:(1)一战后,美国政府面临先进的工业经济管理以及不断增长的国际责任的挑战,扩大了政府对专家知识的需求,引发了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代表的智库的兴起;(2)二战前后,美国的国防建设管理以及新的全球安全部署的需求,促使了以兰德公司为代表的军事/知识复合体智库的发展;(3)1960年代,约翰逊政府发起了向贫困宣战运动,国内尤其是城市社会事务成为政府关注的重点。在越南战争的反弹导致来自政府军事合同枯竭的同时,以城市研究所为代表的国内事务型智库走向繁荣;(16)(4)1970年代以来,作为对美国政府事务的日趋复杂性以及数量众多的智库间激烈竞争的回应,以传统基金会为代表的专门型智库成为智库发展的新趋势。新兴的这类智库往往选择聚焦于一个狭窄的受众或采用单一议题取向,专门化倾向明显。可见,政府事务的需求奠定了美国思想市场的发展,时至今日,“在美国,约55%的咨询业务来自企业,其余部分则来自联邦、州、市、镇各级政府和公共机构”。(17)总之,智库在美国属于一种市场份额较高的、特殊的咨询产业,而正是政府的蓬勃需求激活了智库思想市场,也造就了今日美国智库的繁荣。 智库思想市场不同于一般产品市场还在于活动主体的行为目的和性质不同。“智库思想市场与物质产品市场的最大区别在于:供给者在向需求者提供商品时所追求的并不是利润的最大化,而是影响力的最大化”。(18)确实,智库的“主要动机是研究,而不是为了获利”(19)。也就是说智库在思想市场中主要通过研究以实现影响力最大化。智库的影响力具有递进性,一方面体现在智库产品被决策采纳程度以及对政策形成的影响程度上,这是智库的直接影响力;另一方面则表现在智库影响的政策所产生的经济、社会效应上,这是智库的间接影响力。智库的行为目的决定了其自身的组织性质,因此,智库一般被视作非营利组织、社会公益组织。当然,非营利并不意味着无利润,现实中,不少智库是有利润的,之所以将其界定为非营利组织,人们看重的是智库服务决策、影响公共方面的主要动机,至于利润,只不过是其中的副产品。 智库思想市场与一般产品市场又有共同之处,它们都具有自由开放、多元竞争等现代市场的基本特征。智库思想市场是自由开放的市场,在1974年发表于《美国经济学评论》(AER)的《产品市场和思想市场》一文中,科斯强调思想市场(market for ideas)和产品市场(market for goods)同等重要,科斯在文中援引并赞同阿伦·迪莱克特(Aaron Director)的观点——“在承认商品和服务在竞争性市场自发交易的好处之前,自由交流思想的优越性就已被认可。”并且进一步明确指出“在思想市场中,政府管制是不适宜的,应该对政府管制加以严格限制。”实际上,美国法律对政府管制思想市场进行严格限制,使得智库思想市场相对开放自由,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智库活动独立自主性。而且,政府还通过一系列财税政策鼓励和支持智库活动,例如:在智库成立方面,美国的绝大多数智库根据《所得税法》注册为非营利组织,从而获得免税资格;而在智库运作方面,美国政府通常设置专门研究资助基金资助智库研究、主动邀请智库成员参加圆桌会议听取智库意见等。 自由开放的思想市场环境,促进了美国智库的兴盛。目前美国智库有1800余家,其中既有预算千余元、几个人组成的小型智库、也不乏有开支上千万、拥有几百名成员的大型智库。随着智库的蓬勃发展,智库之间的竞争也变得异常剧烈。迈克甘将智库间竞争比喻为“理念战争”(the War of Ideas),并将其与一战(World War I)、二战(World WarⅡ)、向贫困宣战(the War on Poverty)并列为影响美国智库发展的四个主要的国内外剧变事件。实际上,由于美国的智库普遍没有财政供养,需要凭自身实力提供优质的研究成果赢得客户、资助者的信任,从而获得应有报酬和未来资助以维持自身运转。智库间竞争不仅仅是思想观念的交锋,它关系到智库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参与市场竞争的大大小小各类型智库,为了吸引客户的注意,各智库无不绞尽脑汁,透过各种方式及媒体管道提升影响力及知名度。(20)通过竞争,客观上实现优胜劣汰,提升了智库行业的生产效率,改善了智库产业结构,进而实现智库资源的优化配置。 总之,依循市场逻辑,我们看到,现代智库发轫于思想市场中的咨询业,是政策知识的专业生产者与组织者。具有知识密集优势的智库的存在,适应了政策思想产品的市场需求。在自由开放、多元竞争的思想市场机制作用下,现代智库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走向兴旺。 四、现代智库成长的内在缺陷及其异化 如前所述,现代智库的成长有着深刻的逻辑必然性:在权力知识化中深嵌于公共决策过程、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实现优化发展。现代智库也因此在逻辑上被定位为既是具有市场比较优势的政策知识专业生产者与组织者,又是超越党派政治、独立的“权力/知识”的中介者。简单地说,现代智库即是独立、专业从事政策知识生产与组织的非营利组织,这也印证了人们对现代智库的一般理解和定义(21)。然而,托马斯·麦维兹(Thomas.Medvetz)在研究美国智库实际运作时曾感慨道:“智库是什么?评论家们对它的描绘是矛盾的,例如,既是‘知识的圣殿’(sanctuary for intellectuals),又是‘虚伪的游说公司’(lobbying firm in disguise)”。 智库理想上是以知识的力量影响并服务于公共政策科学化,麦维兹的困惑在于,智库在现实中可能成为以游说技巧代替专业知识、服务私利而非公益的私人经济组织。我们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智库成长逻辑上异化的可能。智库的异化必然导致研究信度的降低,最终削弱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对此,安德鲁·里奇(Andrew.Rich)坦言:“如果没有可信的研究和分析,决策的基础会变成金钱、利益和说客。” (一)权力逻辑的异化:智库知识与政治权力的“双重俘获” 本处所指的权力逻辑的异化是相对于权力知识化而言的一种极端状态,实质上是知识与政治领域的混淆。从现实来看,我们可以区分两种可能的情形: 其一,“知识为权力俘获”:智库沦为权力的附庸和工具。美国智库常常以“超越党派政治的独立性”著称,但在美国政治现实中,拥有政治权力的政治精英对智库进行控制和利用的情况广泛存在。在这种情形下,知识成为权力的附庸,智库及其中的专家则丧失主体性和自由。实际上,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一些智库的这种转变就已经非常明显了,“这一时期可以看作是智库发展上的一个转折点,智库不再坚守传统智库研究的客观性和中立性”。(22)当智库沦为权力肆意把玩的工具时,首先,其所从事的活动往往不是知识探索与政策研究,而只是对政治精英们的政策偏好和主张所做的粉饰性工作。其次,美国的“一些智库往往还是竞选团队的一份子”(23),成为政治候选人的竞选工具。讽刺的是,“总统候选人和国会议员成立智库或利用它们,不仅是为他们的政治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避免来自竞选捐助的财务法律限制。”(24)此外,更为极端的是,一些智库在政治精英的要求下毫无原则地为不正当决策辩护和背书,智库观点成为其“定制的专家意见”。这样,智库不再是追求知识的真理性和实用性为旨归,而是丧失客观立场,为权力所俘获,沦为在“真善美”的知识外包下的权力附庸和工具。 其二,“权力为知识俘获”:智库的话语独白和专家霸权。相对而言,专业的智库通常会优先生产或获取知识,并通过知识鸿沟形成话语优势。当话语优势足够巨大,往往会在政策对话中,对其他政策主体产生话语排斥,并进而形成以专家为核心的“话语独白”局面。从政策权力分配来看,过度话语优势重新建构了智库在公共决策中的权威,把智库及其专家的作用推到一个核心和主导的地位,形成“知识/权力”垄断体制,从而促使一种“专家霸权”的异化现象出现在政策活动中。现实中,专家霸权可以具体表现在政策问题建构、政策方案规划以及政策评估等诸多方面。依循政策过程逻辑,政策问题构建是公共政策活动的逻辑起点,专家霸权因此首先体现在政策问题建构上。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政策科学的兴起,专家的地位及作用迅速得以提升,“政策问题建构权逐渐转移到技术专家手中,在政策问题建构方面,政治部门和行政部门都沦为技术专家的玩偶,从而进入‘专家治国’的阶段。”(25)其次,专家霸权还体现在政策方案规划上。那格尔曾指出:“尽管在原则上那些处在最高层次上的人有权正式决策,但实际上往往只是批准专家提供的方案。”这样,一些智库通过圈定政策方案选项潜在地主宰了政府政策选择。再次,在政策评估领域同样容易出现专家霸权倾向。“在政治生活中,思想库由于有其独到的政策评估功能而起着一种‘社会医师’的作用。”(26)智库通过政策评估,形成关于政府政策得失成败的“权威性”评判结论,从而逆向上影响、制约甚至是主导政策运行。总之,权力越是重视知识,智库及其专家在政策中就享有更多的话语权,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政策的科学化。但是,当智库凭借知识优势垄断政策话语权,俘获公共决策的权力,导致对其他政策主体尤其是公众的排斥,则必然构成对公共决策的公共性、民主性的破坏。 (二)市场逻辑的异化:智库功利化与智库思想市场失灵的可能 如前所述,智库成长的“知识—市场”逻辑揭示了市场机制通过优化智库资源配置来促进智库发展的事实,我们同时也指出,智库思想市场不同于一般的产品市场,智库是非营利的,并且是以影响力最大化而非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然而,现实中一些智库的运转却违背了市场逻辑的原本安排,我们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智库成长的市场逻辑异化,异化主要表现在智库功利化和智库思想市场失灵两个方面。 首先,智库违背其非营利属性,成为具有功利化倾向的经济工具。智库毕竟是由不同领域的专家个体组成,个体的私人需要使得智库成员本能上也具有“经济人”动机。在美国,出于自身利益需要,不少智库成员或明里或暗地的为富人、企业、财团提供政策游说服务,并从中捞取高额酬劳。“我们发现,至少有49名来自美国最具影响力的25家智库中的20家的高级职员、董事或受托人,同时在外部实体身兼说客”。(27)在个人强烈的利己动机刺激下,智库成员往往会在实际中尽可能地利用一切资源来实现利益最大化,而不是追求知识的真理性、实用性或者所声称的服务公益性。 就智库组织本身而言,虽然智库在美国的法律形式上被确定为非营利组织,根本上是拒绝金钱导向的。但作为一个组织实体,同样面临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的生存问题,因而资金问题往往成为诸多智库考虑的首要问题。智库需要资金支撑运转,但若过分考虑和追逐金钱,则容易迷失自我,跌入“金钱依附陷阱”,并在背离非营利甚或社会公益的道路上渐行渐远。此外,近年来美国一些私人财团热衷资助智库,其动机并非出于公益心或慈善心,而是基于服务其私人财富的考量。在他们眼里,智库只是其经济实力转换为政治权力的工具。对此,科瓦奇明确指出,美国不少智库已“成为重大经济利益的工具”(28),这也间接反映了智库的功利化倾向。 其次,诚如科斯所言,“思想市场就和商品市场一样,在现实中可能遭遇市场失灵”。智库思想市场失灵是指智库思想市场也有其内在局限,导致出现资源配置低效甚至无效的情况。智库思想市场失灵主要表现在:(1)资金来源上的动力不足问题。作为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的智库,其资金来源既不同于政府的凭借权威的“强制”式获取,也不同于营利组织的基于私利的“互利”性获取,而是主要采取出于公益心的“自愿”捐助的方式获取。然而,高度的公益自觉尚未在现代社会普及,自愿资助的人或组织毕竟有限。因此,相对而言,智库获取资源的效率显然是微弱的,这就导致智库活动所需要的开支与所能筹集到的资金之间存在巨大缺口的情况。(2)智库研究的短视问题。在竞争激烈的智库思想市场,为自我生存和发展计,“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智库所关心的首要问题必须是消费者的直接需要,而对关乎社会长期发展的国家战略研究等投资大、利润小和风险大的项目,就势必缺乏必要的资金和人员投入。”(29)从根本上看,研究短视问题不可避免地限制了智库在增进社会公益最大化方面的贡献。(3)智库影响的外部性问题。如前所述,智库及其成员的功利化倾向使得智库成为少数人影响政策的工具。由此,金钱支配知识,进而影响权力。政策形成则更多地考虑和体现智库服务的少数人诉求,这也意味着政策更容易对其倾斜。因为公共政策本质上是“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同等情况下,诉求较少考量的其他群体、大众也就可能面临政策利益的受损,从而出现外部性侵损。 五、对我国智库发展的启示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至少包含两个层面的意蕴:其一,建设满足政策科学化、民主化需要的现代智库;其二,智库应具有中国特色。前者体现的是智库发展的共性,后者则体现了我国智库的个性。个性的彰显应该建立在普遍的共性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建设有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首先应该满足智库成长的基本条件、遵循智库发展的客观规律。通过对现代智库成长、繁荣的逻辑梳理,我们认为,中国智库的发展既要吸收和借鉴现代智库成长中的合理因素,同时也要警惕并规避其内在缺陷及异化的可能。基于此,依循现代智库的成长逻辑,我们分别从“国家—市场—智库自身”三个维度提出我国智库发展的基本路径。 (一)国家层面:改革与优化中国智库成长的政治生态 如前文所述,智库成长的“知识—权力”逻辑揭示了智库兴起于权力知识化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一国的权力体制及运行机制状况决定了该国智库的成长状况。因而,从国家层面看,建设和发展中国智库首先要着眼于既有权力体制机制的改革优化上。 1.转变理念,从制度上确保智库有效融入公共政策体制机制中。公共政策是政府施政的基本工具和主要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共权力知识化的外在表现也就是公共政策科学化。现代公共政策科学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谋”与“断”分离,也即咨询研究与决策行动的专业分工。智库专职于咨询研究,政府则专心于决策行动,智库以咨询的科学性保证政府决策的科学性,两者有机互动但又不可混为一谈。因而,智库的发展需要破除政府包办咨询与决策的全能思维,转而确立“谋”、“断”分离的科学决策的理念,从思想上接受并发挥智库作为政府外脑所发挥的咨询参谋功能。智库有效融入公共政策体制机制,还需要构建“咨询先行”的公共决策法定程序予以保障。在美国等智库发达国家,咨询是公共决策中的法定程序,公共项目运作之前都须有不同的咨询报告为参考,这有效地为智库大展身手创造了制度空间。当前,我国应在完善重大行政决策专家咨询论证制度的基础上,扩大专家咨询的决策范围,同时严格专家参与的程序规定,避免将决策咨询变味为“奉命论证”,最终从制度上保障智库作用的充分发挥。 2.促进权力体制机制的公开、透明,为智库研究创设政治条件。如前所述,权力的开放性是智库政策研究和发挥影响的前提。信息是决策的基础,信息同样也是智库开展政策研究与决策咨询的前提,而现代社会,政府垄断了全社会绝大部分的信息资源。因此,促进权力体制机制的公开化、透明化,为智库研究创设条件最重要的是完善并有效贯彻政府信息公共开制度。智库从事政策分析活动所需的信息,首先要尽可能全面,其次是要尽可能准确可靠。(30)就我国而言,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标志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已迈入法制化时代,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了显著改进。然而,现实中还存在一些地方和部门选择性公开、形式化公开等问题,导致公开的信息全面性、准确性、实用性不足,信息公开的不足势必影响我国智库研究的科学性。因而,今后应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细化措施、监督约束机制等方面的完善力度。实际上,美国是公认的世界上信息公开最为发达的国家,其智库的繁荣一定程度得益于其全面、可靠的信息支撑,这一点值得我们借鉴。 (二)市场层面:培育、发展和规范中国智库思想市场 智库成长的“知识—市场”逻辑表明,智库的兴旺繁荣离不开成熟的思想市场支撑。但我们也看到,智库的现实运转中还存有智库思想市场失灵的可能。为此,政府需要综合运用规制性政策与激励性政策,既有效培育智库思想市场,又适当规制智库思想市场。 1.政府应放松智库思想市场准入限制,并通过一系列财税政策培育市场。首先,一个活跃的市场,必定是多元主体相互竞争的市场。目前,我国智库普遍采取登记管理制度,严苛的登记注册已严重限制我国智库的发展,导致官办智库与民间智库比例悬殊、市场主体结构单一等诸多问题。因此,基于我国智库发展的现实状况,借鉴智库的国际经验,当前有必要简化智库登记注册的手续、降低门槛,让更多的社会主体更便捷地参与进来,从而丰富我国智库思想市场。其次,在市场机制主导的社会中,“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市场”。智库思想市场的需求主要来自政府,因此,政府应扩大对智库思想产品的需求、完善智库咨询研究的购买机制,从而在需求端激活智库思想市场。再次,对智库组织实施税收和财政方面的优惠是各国普遍做法,如美国绝大多数智库都是免税组织,享有全部收入免税待遇,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智库的吸引力。 2.完善法律制度,依法规制智库思想市场。如前所述,智库思想市场同一般产品市场一样,都有市场失灵的风险。因此,为确保智库思想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有必要对智库思想市场进行适当规制。一方面,完善智库相关法律制度,将智库纳入国家法律的制度体系并对其行为进行有效的规范管理。法律制度既是对智库行为的系统约束,又是衡量其行为正当性标准,使对智库的规制有法可依。另一方面,由于智库成员本能上也具有“经济人”动机,其咨询研究存在出于自身利益需要而非服务公益的风险,导致“专家失灵”,进而降低咨询的质量、减损决策的科学性。因此,还有必要建立健全智库专家的咨询论证责任机制,对于咨询研究违反法律规定、导致决策失误并造成危害性社会后果的智库及其专家,应依法追求其责任,从而规避和减少智库咨询的功利化和随意性。 (三)智库自身:明晰中国智库角色定位、不断提升智库影响力 智库是什么?为何存在?这应该是每一个中国智库成立、发展中应认真反思的问题。明晰中国智库的角色定位过程,实际上也是中国智库“智库意识”的觉醒过程。一方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定位首先要承认现代智库的基本特征,从智库成长的“知识—权力”逻辑和“知识—市场”逻辑来看,现代智库本质上是桥接权力与知识的中介者、具有市场比较优势的知识生产者与组织者。这属于智库的基本定位,具有普适性。另一方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角色定位,还应立足中国实际、结合国家改革与发展的战略部署,这也是中国智库不同于其他国家智库的特色之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智库属于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战略上看,我们应在治理现代化的图景中定位中国智库的未来发展。我们认为,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我国智库的角色定位至少还体现在:(1)实现公益的服务者。中国智库应该树立服务决策、服务人民、服务公益的导向,而不应沦为金钱或权力工具。(2)分享治权的行动者。中国智库是国家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质是构建党领导下,包括智库在内的多元平等主体的有机合作和良性互动式公共事务管理新模式。(3)促进共识的协调者。理性是增进共识的基础,在利益高度觉醒和利益深度分化的当下中国,中国智库还应该凭借其理性知识优势在公共决策中发挥利益协调作用。(4)公共政策的宣传者。当共识达成、政策出台之后,中国智库还应是党和政府与民众沟通的得力助手,要善于用专业知识解释政策,为民众排疑解惑。 如果说准确定位智库的角色是中国智库立足之基,那么持续提升智库影响力则是中国智库的发展之本。如前所述,现代智库所追求的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影响力最大化。为此,发展中国特色智库,首先要打开门来办智库,积极吸纳各方面的专业人才。人才是智库的核心资源,智库的优势正是体现在人才和知识的密集上。现代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决定了对知识要求的综合性,因此,中国智库应加强自身人才队伍建设,搭建来源广泛且知识互补性强的研究团队。其次,注重研究的质量。质量是智库影响力的生命线,中国智库应着眼于政府和公共事务发展的现实需要来开展研究,讲究研究成果的实效性。同时,中国智库还应注重克服智库研究的短视问题,立足于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战略格局,使研究更具战略前瞻性。再次,中国智库要“走出去”。在现代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下,“酒香不怕巷子深”早已变为“酒香也怕巷子深”,中国智库影响力的提升还取决于自身在市场中的主动性。中国智库一方面应强化其成果输送与推广机制,积极与政府、媒介接触,通过各种渠道发挥影响力;另一方面,从长远看,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体现国家软实力的中国智库还应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增强国际话语权、提升其国际影响力。 ①薛澜:《智库热的冷思考:破解中国特色智库发展之道》,载于《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5期。 ②Alan Jarman,and Alexander Kouzmin,"Public Sector Think Tanks in Inter-Agency Policy-Making:Designing Enhanced Government Capacity",Canadian Public Administration,1994,Vol.36,No.4,pp.499-529. ③David M.Ricci,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s:The New Washington and the Rise of Think Tanks,Yale University Press,1993,p.3. ④Allen.Schick,"Beyond Analysis",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1977,Vol.37,No.3,pp.258-263. ⑤强世功:《从“知识/权力”的角度看政治学的重建》,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13年第1期。 ⑥J.Blondel,"Ministerial Careers and the Nature of Parliamentary Government:The Case of Austria and Belgium",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1988,Vol.16,No.1,pp.51-71. ⑦[美]盖伊·彼得斯:《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 ⑧James G.McGann,Comparative Think Tanks,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2005,p.12. ⑨Donald E.Abelson,and Christine M.Carberry,"Policy Experts in Presidential Campaigns:A Model of Think Tank Recruitment",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1997,Vol.27,No.4,pp.679-697. ⑩张康之、张乾友:《定义“公共行政”概念的三种取向》,载于《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 (11)1932年,罗斯福竞选总统时,曾获益于大学教授们的帮助。在顺利当选为美国第32届总统后,罗斯福选择继续重视和使用政府以外的专家来提供咨询,一些记者在新闻报道中把这些专家顾问称为“brain trust”,此后这种用法逐渐流行开来。 (12)王开明、万君康:《知识经济学性质》,载于《经济问题》2001年第5期。 (13)Paul Dickson,Think Tanks.New York Athenaeum,1972,p.9. (14)冯之浚、张念椿:《现代咨询学》,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15)James G.McGann,"Academics to Ideologues:A Brief History of the Public Policy Research Industry",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1992,Vol.25,No.4,pp.733-740. (16)李若:《从国外咨询产业发展看入世后我国咨询业政策选择及发展趋势》,载于《情报科学》2003年第2期。 (17)王莉丽:《中国智库思想市场的培育与规制》,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18)D.STONE,Capturing the Political Imagination:Think Tanks and the Policy Process,Frank Cass,1996,p.13. (19)Donald E.Abelson,Do Think Tanks Matter?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2002,pp.74-83. (20)Thomas Medvetz,Think Tanks in America,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2,p.29. (21)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目前流行度较高的智库定义,均不约而同地强调了智库的独立性、非营利性、专业性等特征。如斯通对智库的定义是“那些独立于政府、政党和利益集团,并从事公共政策问题分析的非营利组织。”参见D.STONE,Capturing the Political Imagination:Think Tanks and the Policy Process,Frank Cass,1996,p.16.迈克甘认为“智库是指独立于政府、社会利益集团如公司、利益团体以及政党等力量的具有相对自治性的政策研究组织。”参见James G.McGann,Comparative Think Tanks,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2005.p.1.里奇把智库界定为“独立的、不以利益为取向的非营利组织,它们生产专业知识以及思想观念,并主要借此来获得支持并影响政策制定过程。”参见A.RICH,Think Tanks,Public Policy,and the Politics of Expertis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11. (22)Rich,Andrew.Think Tanks,Public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Expertis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p.214-215. (23)张康之、向玉琼:《美国的智库建设与MPP教育》,载于《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9期。 (24)Donald E.Abelson,Do Think Tanks Matter?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Public Policy Institutes,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2009,p.90. (25)Kubilay Yado Arin,Think Tanks:The Brain Trusts of US Foreign Policy,Springer VS,2014,p.11. (26)张康之、向玉琼:《从政策问题建构看社会治理体系演变》,载于《河北学刊》2014年第1期。 (27)钱再见:《现代公共政策学》,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6页。 (28)Brooke Williams,and Ken.Silverstein,"Meet the Think Tank Scholars who Are Also Beltway Lobbyists",The New Republic,May 10,2013. (29)P.Kovacs,"Neointellectuals:willing Tools on a Veritable Crusade",Critical Education Policy Studies,2008,Vol.6,No.1,p.1. (30)罗纳德·科斯:《商品市场和思想市场》,载于《美国经济评论》1974年第6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