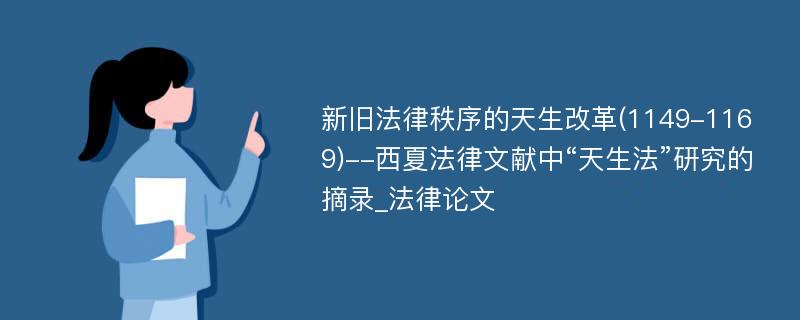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1149—1169年)》——西夏法律文献《天盛律令》研究专著节选译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律令论文,西夏论文,译文论文,专著论文,文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旧新定律令》和与其相关的现存西夏立法文献的编纂历史
在中国法律史上,从李悝的《法经》(《法律经典》)开始,再到宋朝的立法,只有上面所提到的《唐律疏议》《宋刑统》和现行的宋朝立法才能成为西夏法律制定可参考的文献史料。与此同时,律令的编纂者们还利用了一些西夏法律以及此前颁布的一些西夏诏令,特别是反映以前年代司法实践的那些诏令。而且关于法律的学说和那些年代的一些法律理论,不能不对编纂者们的工作产生影响。根据律令原文判断,在12世纪,一些中原刑事法典、一些西夏法律、判例,可能是他们在编纂《改旧新定律令》时所利用的主要法律文献资料。法律创作是国家活动的一种形式,它“同时包括在把修改载入现行法规方面,在一些陈旧法规废除方面,以及在调整早已被采用的法令方面的国家专门活动,把它们整理成一定的系统——立法的系统化”[1]579。这类法律创作活动乃是编纂工作的重点。编纂工作经过了做出法律创作决定的全部阶段——创立律令方案,讨论、提交法律创作机关(皇帝)审查,皇帝做出决定和颁布律令(公布和生效)。在西夏和中原,皇帝履行了唯一法律创作机关、唯一立法者的角色。“皇帝从史料中来到了我们面前——K.宾格尔写到——他是最高的、唯一的、核心的立法者。在立法领域,除了自己的良知、理性和国家利益外,他不受任何事情和某种传统,即一般的说处在国家法理之外的所有因素的限制。他的官员们解答他在立法事务中的疑难问题,没有任何能够禁止其绝对设制”[2]48。“法”、“法律”的概念含有与传统立法的联系,并具有“内在的它所固有的连续性的品质”,但遵守传统,对皇帝与其说是道德的,不如说是对国家法律的责任[3]49。
虽然对法律的深入研究和修改是官员们的事情,正如在《改旧新定律令》的实例中我们所看见的那样,皇帝自己不可能研究案件的技术细节,他不仅是唯一的和绝对的立法者,而且还是进行最终诉讼审判的最高法官[2]56。皇帝履行的最高法官职务,使被他做出的或被其赞成的法院刑事判决具有了特别法律创造性的意义。皇帝的决定往往以诏令的形式被公布,而这样的一些诏令渐渐地变成立法命令。正如K.博雍戈尔认为的那样,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使中国法律成为以前例为基础的法律[3]。该特点不仅成为中国法律,而且也成为整个远东法律的特点。例如,在我们的西夏资料中,我们有K.博雍戈尔所表达的观点的很好证明。编号为4189的手写本恰好是一些诏令和上级法院判决的内容简要(唐朝时《敕节本》或者《敕录本》被称之为《敕令内容简述》),即获得法律效力的1163—1168年间内对不同案件所做出的司法判决内容的简要记录。既然今后我们已经不会专门重新回到对于这个重要手写本的详细评述,那么现在正是应该援引关于在西夏上级法院重要判决的简要记录中曾被提及的那些问题的主要信息的时候。
天盛十五年八月(1163年)中书省关于被抵押的仆人和田宅在被送去抵押、到天盛十九年十月(1167年)为止的情况下的赎回制度和关于课以物主或代替他们的其他人在赎回的抵押财产的抵押上收受的所得税制度的决定已被摘要记载下来。注有天盛十六年六月七日(1164年)日期的记录。向皇帝呈文复述关于北方兵役局(经略)一连两三年都非常多雨,庄稼都淹死了,百姓过着穷日子,很多人不知要怎样恢复家业,他们将自家妻子、儿女和其他亲属卖给外人成为朴欣加和妮妮(失去人身自由的一些人),下面将要详细地说到。许多原先自由的人,现在成为了奴隶或仆人。从今以后,出卖过亲属的人们已被命令交还出卖亲属所得到的钱财,并且带回被卖掉的亲属。对出卖过亲属的人们宣布了大赦,因为按照现行立法,出卖亲属为奴是犯罪行为。
以主管部门按照向“觐奏院”所呈递的一些报告为基础,通过天盛十八年六月三日(1166年)的决定,下面的内容确定了下来:按照现行立法,如果朴欣加盗去主人的财物,那么他就要受到主人的惩罚,虽然主人没有声称对他拥有支配权。即使主人声称对他拥有支配权,那么对偷过自己主人财物的朴欣加的惩罚方法依律而定。另外,如果朴欣加偷去的不是主人的财物而是别人的,即外人的财物,为了惩罚,禁止把他转交给主人,只能根据法律对他做出刑事判决。
天盛十六年十一月(1164年),觐奏院向国王报告在法律试行期间,一些官员把由他负责监督的官马让给其他人骑乘。借出过官马的一些官员因为受贿依法受到了惩罚,惩罚视官马交回的期限和该马使用一天的价钱而定。因为使用官马,没按指定的1-2天的期限归还,有罪的人应当服1年苦役,对告发这件事的人,按规定奖励20缗钱币。因为使用官马没按指定期限归还而超过一个月,应当服10年苦役,而且确定奖励告密人100缗数目的钱币。直接认证官马是属于某人的那人,将作为从犯被惩罚。
天盛十七年(1165年)的一份记载中,反映的是一个妮妮的问题。她是奴隶,是一支强盗匪帮的参与者,为此曾被判处苦役并送往额济纳(哈拉—浩特)服流刑。问题发生了,谁应该供给她衣服并养活她。这个问题是在她的主人,即某一位官员的参与下决定的。
天盛十九年最后的一个冬月(1168年)通过的决定已经下令赦免朴欣加们,他们从主人那里获得自由后,曾在后勤队服过兵役。如他们所愿,又转到正规军中服役,承担繁重工作。此外,注有天盛二十年(1168年)日期的最后记录含有关于某个叫任阿厚的官员的最高民事判决,他是管理通信院的老官员之一。据案件记述,上面所指出的官员和自己的一个妮妮姘居并生了子女,决定宣布她是自己合法的妻子,姘居所生的子女是自己的婚生子女。他公开宣布自己的决定,但没有举行结婚和祭祀仪式。任阿厚与这个妮妮的婚姻被认为是非法的:第一,因为任阿厚没有举行结婚和祭祀仪式;第二,因为这个婚姻破坏了社会道德准则,造成“贵族和下流人”的混淆。这使子女陷于非议,他们的父亲原来是贵族,而母亲则出身低下,连任阿厚的亲戚们也陷入了难为情的处境中。由于他的婚姻,亲戚们渐渐变成社会地位低下的亲戚[3]。
允许我们具体地评定远东法律中具有前例作用的西夏法律的这个重要文献的简短内容就是这样,重要的是准确断定了《改旧新定律令》制定的年代。问题在于上列判决中的某些人记入了《改旧新定律令》。我们所知道的它的编纂时代——天盛朝——包括20个年头(1149—1169年)。在1149年、1169年或中间的某一年,从编号为4189的手写本中汲取的信息正好帮助我们确定了律令制定的准确年代。1166年关于朴欣加因在主人或别人那里犯了盗窃罪而受惩罚的法令,在已颁布的律令中反映了出来。律令第109条条文里说,如果朴欣加或妮妮偷了主人的财物,则主人应向管理部门报告偷窃行为。管理部门进行了案件的侦察,而且如果发现被偷去的财产的确是主人的,则将案件移交主人自己处理,只按他的请求依法惩罚犯了盗窃罪的朴欣加。可见,律令至少编成于1166年之后。无论1168年的关于朴欣加从主人那里获得自由在后勤部队服役的权利判决(第377条),还是关于任阿厚的案件,都在律令中得到了反映。律令准许认为妮妮是妻子,而她所生的子女是婚生子女。如果结婚时,他们将给保护神送来专门的祭品(第1421条),但任阿厚什么事也没有做。基于这些类推,我们认为律令的编纂工作完成不在1168年以前,而在1169年,于是得出《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的编纂年代是1169年。此外在这三个实例中,我们看到了皇帝的司法判决前例,编纂法典时也要考虑。
这样,可以推测认为《改旧新定律令》,即保存下来的一些西夏法律文献之中,具有中原法律发展的传统。无论西夏法律的那些规范,还是条例本身,它们都曾在西夏的国家组织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了。虽说这部大型律令似乎涵盖了西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实际上,生活还是比律令中规定的情况更加多种多样。律令还是需要增补和修改。皇帝关于一系列案件审判的实践,已成为审查类似罪行时人人必须遵守的一些新前例。
在苏联社会科学院列宁格勒分院所藏的西夏手抄本和木刻本汇编的概述里,《新法》《亥年新法》《光定时代猴年新法》已经不止一次被提到[4]86-92;89。而在不久前,仍旧不清楚的是:这里所说的是不是一些不同的文献,或者是一些不同名称的同一文献?文献内容怎样?现在我们能回答这些问题。
文献名称多样性的一些客观原因在于,大量的手抄本书籍没有保存下来,或者很多书名页保存得不好。一些书籍开本不同,而条文又是用不同笔迹抄写的,列入同一本书内的文献章数也不一样,已保存下来的各章名称——《新法》和《亥年新法》迫使我们不能不长时间地认为,它们可能是两种不同的文献。对条文的详细研究和对其的仔细校订是必要的,以便确认这是署有不同名称的同一本文献。以前没有注意到的那个文献,同时也被找到了。档案号为2842的手抄本封面上有“亥年新法,第十二章”的标题,而在页背面的正文开头是“新法第十二章”。档案号为5591的手抄本封面上并排有两个标题:“新法第十六章”和“亥年新法第十六章”。档案号为8183和2622的两份文献有“亥年新法”标题,而档案号是749的一份文献有“新法”标题。这些书籍内容的校订,使我们相信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同一部文献。它们虽名称不同,但原文的内容完全重合,我们也在编号为5591和2819的手抄本中找到了。可见,在我们面前的是两种不同名称的同一部文献,它们当中的一个——《亥年新法》可能是其比较完整的名称。
既然它们是新的,而在《改旧新定律令》中又没有被提到,那么可以合理地推测,认为《新法》编纂成于《改旧新定律令》之后。1169年以后,按照十二生肖的循环,猪(亥)年正好是1179年、1191年、1203年、1215年、1226年和1237年(原文如此一译者),而它们之中的任何一年,除了1237年以外(因为西夏国家灭亡于1227年),都可以假定是《新法》编纂完成和颁布的年份。现有的某些手抄本中的抄写日期帮助我们做出了必要的、更加准确的修正,这些材料显示它们都与光定朝和1215年之后的时间有关。档案号为827的手抄本有“鼠年,一月”,“光定,鼠年,一月”的日期,这与1216年1月21日至1216年2月18日是吻合的。档案号为2819的手写本有“光定,蛇年,五月,九日”也就是1221年5月31日。档案号为2842的手写本注明的日期是“光定,蛇年,七月,十四日”,也就是1221年6月30日。由此可见,《新法》编纂完成或颁布的猪(亥)年,毫无疑问,正是1215年。额济纳《哈拉——浩特》延迟收到了《新法》,据我们所推知,大约从1216年开始重新抄写。至于被H.A.聂夫斯基提及的,注有光定朝(1212年)猴年《新法》的一些手抄本,无论在我们所知的一些文献抄本中,还是H.A.聂夫斯基在30年代亲自所作的,科学院列宁格勒东方研究院所藏的西夏总额的财产登记簿的笔记中,都没有找到。可是这个日期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在《新法》第八章的原文中,光定朝猴年几次被提到。在光定朝猴年(1212年),在[京城]郊区突然发生了大火。此前颁布的一些诏令被废除了,于是政府加大了对告密者[告发火灾的造因人]的奖赏和对造因人的惩罚[5]32。全部惩罚措施都增加了一个等级。而且“如果在《新法》发生效力以前,在光定[朝代](1212年4月26日)猴年3月23日以前,女人还没有成为丈夫家庭中的一员,就希望得到[丈夫]拨出的办酒宴的[返还钱财],[如果婚约没有实现],就禁止[负责人员]接受这样的要求”[5]38。
这样一来,可见《新法》是从1212年,即猴年4月26日起生效的。所以H.A.聂夫斯基阅读了这一章的原文,并指出了这个日期,却没有任何解释。在蒙古人又一次差点儿占领西夏京城后,1212年把某些改变引入西夏立法未必是偶然的。1211年夏天,西夏皇位更迭,遵顼继安全而立,开始推行新政策,而使《新法》生效就是其中之一。可以认为《新法》是从1212年4月26日起生效,而颁布于1215年,即按十二生肖循环的猪(亥)年,所以被称作《亥年新法》。不过这样我们暂时能够解释从应该遵守《新法》的那个日子起与它们的命名日期之间三年之差。也许,在1212年4月26日之后所犯下的那些罪行,被建议按照《新法》加以惩罚,虽然它们就颁布在1215年或更晚。
《亥年新法》是不是西夏国家独创的新律令,或者只是对《改旧新定律令》的补充和修改?阅读《新法》原文表明,在我们面前的不是替代旧法典的独创的一部律令,而是在那之后的40年内所累积起来的对旧律令的补充和修改。在《改旧新定律令》和《新法》里,章的划分相同,章内篇目的分类也相同。在没有对其进行补充和修改的律令中的那些篇目,在《新法》中是没有的。而且,最终这被《新法》条文内容证明无误。例如,在《新法》第三章第一条中说:“律令中已经指出,没有参与过抢劫勾结,但是接受过抵押寄存的,借过[他的]钱,出卖过[赃物],或者收到过偷来的财产中的一份,并[同时]知道[它]是赃物,对[此人]的惩罚比对行劫时施加或没有施加暴力的从犯的惩罚降低一个等级。可是在律令里,没有指出如何处理同知道被强盗匪帮侵占偷来的财物有关系的那些人。于是适当地在《新法》里补充道:知道这笔财物被强盗匪帮偷去,又参加了[其]分劈,以及把(它)卖掉,借了债,寄存起来或接受了抵押的人,被惩办12年终身苦役。服满苦役之后,无返回自家的权利……”[5]5。
《新法》中对《改旧新定律令》的一些修改和补充反映了国家一些生活条件的改变。例如在第一章中,法律增加了因刑事罪行而惩罚赎金的可能性,并且早先依照律令被允许用铁做赎金,被用一百铜币顶一斤(约600克)铁价的货币赎金所替代[5]3,这一方面反映了西夏货币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反映了国库缺少货币。修改考虑到了前例,在第八章第四条中,事情的实质已经说明,它的司法判决已被书面命令,做今后这样情况下惩罚措施的规范。某尚阿西基和张阿四哥邀来李热勒津,即某施布尔的妻子,他们买酒喝了,给了女人四缗钱币。之后,尚阿西基用暴力占有了李热勒津。按照诏令,尚阿西基受到了5年苦役劳动的惩罚,而阿四哥因共谋被判处1年苦役劳动。“在这之后,《新法》里说,如果将有类似阿四哥犯了的那种犯罪,则应该根据这个法律对待”[5]36-37。
总之,《新法》《亥年新法》以及H.A.聂夫斯基所提到的《光定时代猴年新法》都是从1212年4月26日起生效的同一部文献,它是大约在1215年颁布的,是对《改旧新定律令》的一些补充和修改。也许这些补充和修改没被木刻出版,而1216年以后,它们又在各地被司吏复写多份,以手抄书的形式分别送到各地方机关。中国法律史学家吕思仁写道:“每一个朝代开始曾被公布过的法律,在它统治的整个时期始终是不变的。但实际上,每经过一个五年或者十年,在新的一些情况下,就会出现新的规则,在得到皇帝的批准后,这些新规则结集在了一起,被分类,除了法律书籍中与案件有关的条文外,立即得以生效。它们和基本条文具有同样的效力”[6]240。西夏的《新法》就是这样。
《新法》本质上与不知名的编号为4189的手抄本不同,它们不是皇帝或某些别的上级简单法院关于不同案件的随便的、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的判决记录,而是对王朝现行律令的有系统的补充和修正。其实,对于新的、更加改进的律令出版,也就是说对于新出版的《改旧新定律令》来说,它们都是很好的准备。
关于《改旧新定律令》名称的几句话。在西夏原文中,从H.A.聂夫斯基时期起,习惯上应当这样翻译律令名称的那部分,字面上的意思是:“改变旧东西,确定新东西”。在律令被我们公布的不久以前,在《碧玉镜》的原文中找到确证之前,这样的书名必须以在西夏国家里刑法典的存在为前提[7]146。类似的一些法典名称,我们在契丹人和女真人那里也遇见过①。
西夏法律文献研究的历史极短,只有H.A.聂夫斯基在准备本人的科学院列宁格勒东方研究所藏的西夏搜集品的概述《西夏古代文献和它的总额》的时候,对它们有兴趣。这个概述最初是H.A.聂夫斯基在1935年3月20日的苏联科学院会议上宣读的一个报告,包含有关于西夏法律文献的以下信息:在我们的搜集品中,有一部非常有意思的著作,无论是西夏国家的国体,还是西夏国家中的社会关系,研究它的学术著作都应该阐明。我说的是由20册构成的“天盛时代(1149-1171年)被修改的法律法典”。这个法典是被一个法典编纂委员会编纂成的,编纂成员中有几位汉人,这会使人认为该法典是适合于西夏特点的宋法典的译本。在几乎全部搜集品中,除了现有的这个木刻作品以外,我们找到另外一部叫做“光定时代(1212年)猴年新法”名称的法典手写书籍[8]89。《改旧新定律令》是对研究西夏社会和国家来说意义最重大的文献资料。可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律令是宋法典译本,还是适合于西夏特点的本国法典?他的推测没有得到证实。
有时个人在西夏立法史方面的一些见解是很有价值的,最初以研究单个条文的汉文文献资料为基础的著名日本历史学家冈崎精郎发表的《西夏古代历史研究》专题论著里。他认为由女真人在全国按照中原样式创立的、没有附入女真风俗习惯法的法典,即《皇统新制》(1145年)会影响西夏《改旧新定律令》的编纂,而金代法典《泰和律》(1201年)会影响《新法》的编纂[9]348-349。这些女真法典没有保存下来,倒是西夏法律文献被保存下来了[10]148-149。所以,西夏法律文献当前还需要研究。我们希望公布《改旧新定律令》的综合性原文,即它的第一部和存在某些缺点的俄文译本,把必要的材料交到研究者的手中,必将被关心中世纪远东法律的人饶有兴趣地接受。
文献结构
《改旧新定律令》之所以不是宋法典的译本,因为西夏的法典编纂者们在选择文献的叙述形式和确定文献结构时拒绝了盲目遵循中原样式。
法典是以目录开始的,更准确地说是以目录指南开始的,那里除了章的目录外,每一章中条文数量的说明和各篇的名称都被整理成关于条文内容的简短信息,这便于刑事案件的判决查询。这个目录与《唐律疏议》和《宋刑统》用的目录指南毫无区别。
律令全集分成20章,在每一章中对其被叙述的条文在数量方面也有一定规定,并且容易领会。有些章中的条文数量不一样,从第5章中的37条到第13章中的116条(在第1章前的引言中已经指出第13章中有115条)与中原一些法典不同,在西夏律令中,我们没有找到传统的12篇②。
西夏律令中的每一章,一个或几个看来曾被认为同源的立法篇目损坏了,但是选题的原则向来并不被严格执行。律令原文被分为若干条文,在这种情况下,西夏法典的编纂者们放弃了中原样式。大家知道,条文明确表述一定的行为规矩和法律规范,两项式的和三项式的条文结构理论是存在的。两项式的结构要求,将条文划分为两个成分——罪状和制裁,三项式的结构要求将条文划分为三个成分——假设、罪状和制裁。最近几年,大多数研究者将法律条文、规范分为三部分。“法律规范具有三个成分(或者三个组成部分)——有指明条件的假设,有规则起作用所具备的前提,有含有该规则的罪状,也有对犯过该规则的人说来即将来到的、已指明不利后果的制裁”[1]351。
西夏律令的条文符合时代对这样的条文所提出的全部规则,并在结构方面与现代法典条文没有不同。我们举第三章中第127条文作为例子:“如果一个没有参加过有关盗窃勾结和偷窃畜物的人(假设)知道有关盗窃的谈话而又参与分赃并运走[赃]物,购买、借钱、藏匿或典当[赃物](罪状),则[他]应受得的惩罚比对犯下该盗窃的从犯被裁定的惩罚降低一个等级,考虑到这个窃盗是怎样引起的情况——施暴或没有施暴(制裁)”。
大容量的条文被分成数节(例如,第一条中有9节),而非常大的一些条文又被分成几部分,多半分成两部分。条文开头通常直接从正文和上页边划分开的上线框开始顶格写满全行。并用倒写的西夏字作标志显示出来。如果条文被分成两个部分,下一个部分也以同样的标志开始,但从上线框起留出一个标志符的空格,就是说隔一个标准标志符大小的间隙。在我的部分条文的译文中,曾用大写字母“A”和“ъ”作标志。第606条文甚至被分成三部分—“A”.“ъ”和“B”,一些节段被用一个西夏字“一”标志分出,并从上线框边起留出两个标志符空处。译文中,它们用放在方括弧内的俄文数字做标记。例如,第785条中有13节。既然出版者认为分出更加细小的条文是需要的,则这已经成为没有记号的专门标志,而简单的还以行首大空行——3—4个标志以及从上边线框起更大空行的方法作标志,空处挤满了小花饰。某些条文很长,关于允许的原料耗损定额的第1256条,大概是律令中最长的条文。
可见,《改旧新定律令》里的条文,完全不像中原法典中的条文。中原法典条文,最初以扼要的形式作出,然后用诠释《疏》、解释《议》补充好(由此,唐法典的全称《唐律疏议》—《附有诠释和说明的唐朝刑法典》)以及关于该条文被提出的问题——《问》和对于它们的回答——《答》。在宋法典中,还发现有《附有许可的命令引文》——《准》。从《宋刑统》中,我们举一个简短例子:“偷窃官方或属于私人的一匹马或者一头公牛并宰杀它的各种人,应受两年半苦役处罚”。在诠释和说明中说:“马和公牛被使用在军中。所以它们与其他牲畜不同。如果某人偷窃和宰杀[一匹马或者一头公牛],则被处罚两年半苦役劳动。即使将要谈的是比两年半苦役更重大的应受惩罚的占有,则应将其看作一般盗窃,并且对[有罪人]的惩罚措施增加一个等级。即使在这样一些人中,他将偷走和宰杀的通常不是被用来耕地和作活的牦牛,则这种偷窃被看作是一般的盗窃”[11]8。显而易见,在扩大和调整条文原文使所有被律令考虑到的该法规附加的一些个别情况分散于若干节段以后,西夏法学家们或许可从本质上违反中原样式。大概回答问题有困难,所以他们就这样处理了。这是否反映了个别传统,或者他们的动机是神的企求和力求达到更适合于目的的叙述方式的愿望,我们无从知晓。但是他们制定的律令在法律文化领域中,处在人类进步轨道中,并体现了西夏国家法律发展的高超水平。
在我的译文中,法典的全部条文按次序已被编上了号码。原稿正文中的条文号码没有被保存,为了使用译文方便,它已被我们采用。
已被西夏人接受的传统中国法律理论,在另外一部专题论著中,我们已对其作了研究[12]。
译文中( )内除了个别几个注明译者外,全为克氏语,【 】内文字为西夏原文省略处,也为克氏所加。
注释:
①日又增轮.辽史研究,第64,67,72页;宫食一定Со-зндзцдай-но хосай-тосайбан кцко,第127页.
②参看:唐法典(第1卷,总则)[M].由W.约翰逊写的序言译文,朴林斯顿,19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