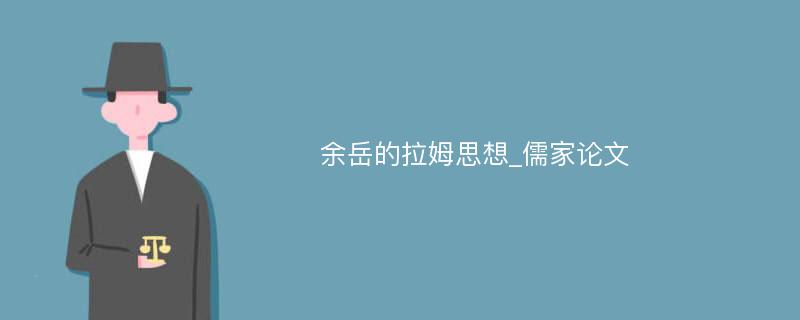
俞樾公羊思想发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羊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04)-03-0088-07
俞樾(1821-1907),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他是晚清“最有声望”(注:顾颉刚:《秦汉的方士和儒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5页。)的经学家。《春在堂全集》是他的学术成果的总集,近500卷。其主要学术成就是校勘、训诂群经、诸子和归纳古文“文例”,因此,向以朴学家驰名中外。值得指出的是,俞樾虽致力于朴学,就其经学思想而言,却又具有公羊学倾向。章太炎曾指出:俞樾“治《春秋》颇右公羊”(注:章太炎:《俞先生传》,见《章大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211页。)。傅斯年先生更是从“主义”上将俞樾归入到公羊家的队伍中。(注:傅斯年著:《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见《傅斯年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116-117页。)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仅是相因为说而已,尚没有人对俞樾的公羊思想作系统的整理。因此之故,有的学者对俞樾的公羊学倾向抱持一种怀疑,认为俞樾治经“仅涉《公羊》之微言大义”,“尚不及三科九旨,更无论大一统”(注:杨向奎:《俞樾〈曲园学案〉》,见《清儒学案新编》第五卷,齐鲁书社1994年版,512页。)。有鉴于此,本文拟着重联系“三科九旨”、“大一统”等公羊基本思想,对俞樾的公羊学思想进行具体的考察。
一
俞樾一再说明,应以《春秋》为“素王之法”。这与公羊家以《春秋》当新王之说类似。所谓“以《春秋》当新王”,大意谓孔子作《春秋》,以《春秋》一经行天子褒贬进退、存亡继绝之权,而为一新王之法。此说为公羊家历代相传之旧说。《春秋》首书“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曰:“王者孰谓,谓文王也。”这即是说,《春秋》所托之王并不是周平王东迁之后周王朝实际在位的周王,而是另一位并不存在的文王。此文王是周始受命之王,又非《春秋》二百四十多年间颁正朔之王。《春秋》当新王之说,由此发其端。孟子云:“《春秋》,天子之事。”(注:《孟子·滕文公下》。见陈戍国点校:《四书五经》,岳麓书社1991年版,93页。)在公羊家看来,这里的“天子”,亦是就“新王”而言。司马迁指出:“孔子闵王道废而邪道兴……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注:司马迁著:《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二版,3115页。)又谓《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注:司马迁著:《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二版,3297页。)司马迁这里的所谓“王”,当指《春秋》所托之“新王”。《春秋》当新王之义,董仲舒发明最多,何休进一步发扬其说。在董仲舒所著的《春秋繁露》一书中,每每提到:“《春秋》作新王之事、变周之制”、“《春秋》上黜夏、下存周,以《春秋》当新王”之类的说法。这里不一一具引。清代公羊学家刘逢禄于《公羊何氏释例》一书中对《春秋》当新王之义亦有一段极具代表性的概括,他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春秋》是也。故日归明于西而以火继之,尧舜禹汤文武之没而以《春秋》治之,虽百世可知也。”(注:刘逢禄:《公羊何氏释例·王鲁例第十一》。转引杨向奎主编:《清儒学案新编》第四卷,齐鲁书社1985年版,41-42页。)“托王于鲁”与“《春秋》当新王”之说,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春秋》当新王”重在说明孔子作《春秋》的目的,“托王于鲁”强调《春秋》一经的表达手法,然其根本内涵则依然是以《春秋》当新王。
俞樾接受了公羊学的这一思想,且在著作中反复加以阐明,可以说,这是他训释《春秋》经传的基本出发点和指导思想。他认为:左氏纪事之书,于鲁国之史,知之悉,言之详。而公羊子则说经之书,鲁事非所知,说经而已。且谓“经者,孔子为万世立素王之法,非为鲁记事也”(注:俞樾:《经课续编》卷五,2页,《春在堂全书》光绪二十三年重订本(石印本)。)。因此,他认为《公羊春秋》既是传孔氏之经,所言礼制为素王之制,不必完全与鲁史相符。又谓“孔子生衰周,不得位,乃托鲁史,成《春秋》,立素王之法,垂示后世”(注:俞樾:《达斋丛说》,2页,见《曲园杂纂》,同上。)。他论“春秋天子之事”,更直接强调:《春秋》所书,“皆孔子所立素王之法”(注:俞樾:《诂经精舍自课文》卷二,2页,见《第一楼丛书》,同上。)。俞樾又详言“托王于鲁”之义。他指出:孟子所谓“《春秋》天子之事”即公羊家托王于鲁之说,强调:素王之法不得不有所托,而鲁为父母之国,所见、所闻、所传闻较他国可据,故托之。他进一步阐发其旨云:“隐公非受命之君也,而《春秋》于是乎始,则以为始受命也;鲁哀公时,非太平也,而《春秋》于是乎终,则以为人道浃,王道备,功至于获麟也。”又云:“内而鲁十二公及季、孟诸大夫,外而周天子及齐、晋、秦、楚诸国之君若臣,无非《春秋》所托以行法。譬犹奕焉,彼皆棋也,孔子作《春秋》,则举棋者也。”(注:俞樾:《诂经精舍自课文》卷二,2页,见《第一楼丛书》,同上。)俞樾又论学者不信“托王于鲁”之非,认为孟子既言《春秋》为天子之事,则何氏之说固有所受,且言“自宋以来,儒者举不识《春秋》之义,惟苏明允独得之。”苏洵(明允)论《春秋》云:“有善而赏之,非曰吾赏之,鲁赏之也;有罪而罚之,非曰吾罚之,鲁罚之也。鲁之赏罚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权予之,何也?曰:天子之权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予鲁也。”俞樾深赏其言,认为“此即黜周王鲁之说”(注:俞樾:《湖楼笔谈》卷一,5页,见同上。),因谓孔广森笃信《公羊》,而又对“托王于鲁”之说不以为然,未免买椟而还珠。俞樾又以“托王于鲁”之义释《春秋》,他释“隐公不书即位”云:“鲁之隐公犹周之文王,文王虽受命改元,然必待武王而后定鼎乎郏鄏。”因以为隐公不书即位,乃圣人“示开创之始”,王业未成,从而见“创业之难”。(注:俞樾:《湖楼笔谈》卷一,5页,见同上。)又释《公羊传》“王者孰谓,谓文王也”之“文王”曰:“周自武王始改正朔,则王正月宜为武王,乃云文王者,盖武王既有天下者也,文王则未有天下而创立王者制度者也。孔子作《春秋》,托王于鲁,鲁亦未有天下,而孔子借鲁以立王者之制,是以文王王鲁,不以武王王鲁也。”(注:俞樾:《茶香室经说》卷十三,1页,《春在堂全书》光绪二十三年重订本(石印本)。)俞樾解隐元年经书天王、而《公羊传》两言诸侯之故云:“《春秋》托王于鲁,周鲁交涉始于此事,故于传文微见其意。经书天王,而传两言诸侯,所谓齐王德于邦君,示黜周王鲁之意义也。”(注:俞樾:《茶香室经说》卷十三,1页,《春在堂全书》光绪二十三年重订本(石印本)。)成二年,《春秋》书“……曹公子手及齐侯战于鞌”,《公羊传》认为,所以书公子手,则“忧内也”。俞樾认为,大夫得忧内,不得忧外。而此年鞌之战,曹使大夫帅师从鲁,与齐战,依《春秋》“义例”,不当书“曹”。所以书者,《春秋》托王于鲁,故曹忧外而谓之忧内,“内,谓鲁也。”(注:俞樾:《茶香室经说》卷十三,3页,《春在堂全书》光绪二十三年重订本(石印本)。)俞樾又以“托王于鲁”之义辩谷梁氏之非。隐九年,《谷梁传》有“聘诸侯非正”之语,俞樾不以为然。他认为:天子于诸侯曰问,诸侯于天子曰聘,《春秋》隐九年书“聘”,正见圣人“托王于鲁”之义。他指出:《春秋》“托王于鲁”,故于天王书“来”,聘于小国,书“来朝”,隐然以鲁当新王。因谓谷梁子“浅于春秋……未达《春秋》托王于鲁之义。”(注:俞樾:《经课续编》卷六,3页,《春在堂全书》光绪二十三年重订本(石印本)。)上述表明,俞樾不仅笃信“托王于鲁”之说,于《春秋》经传之训诂亦能曲径旁通,对“托王于鲁”之义多所发挥。
俞樾所谓“托王于鲁”之“王”,所谓“素王”,其实即指孔子本人。他说:“天意固以孔子作《春秋》,为周兴五百年后之王者。”(注:俞樾:《茶香室经说》卷十六,5页,《春在堂全书》光绪二十三年重订本(石印本)。)他论《论语》“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云:“孔子一文王也,文王未有天下,而一王制度已备,是无天下之名而有天下之实。孔子际苍姬之未运,建百王之大法,作《春秋》一经,借鲁以立王者之制,是文王为有周一代之文王,孔子为继周万世之文王。”(注:俞樾:《茶香室经说》卷十六,3页,《春在堂全书》光绪二十三年重订本(石印本)。)由此可见,在俞樾看来,文王、鲁王,皆是孔子假托之王,皆是棋子而已,孔子作为“举棋者”即是“素王”的真实主体,亦是“托王于鲁”之“王”。
二
公羊家口说微言,有孔子改制之说。所谓孔子改制,是指孔子改周之旧制,立《春秋》之新制。由于孔子改制说未明著于竹帛,至汉乃由公羊家宣于世,故后儒多不信孔子改制说。古文家之立场更是激烈反对,认为孔子之志在“从周”,决不在改制。然孔子改制说与《春秋》新王说、《春秋》王鲁说实有内在的联系。俞樾既以孔子为周兴五百年后之新王,且以其为“继周万世之文王”。孔子改旧制立新制便是顺理成章之事。
俞樾论及周末大乱的原因时指出:周人兼二代之所有,而增二代之所无,礼乐制度于是大备,虽孔子之圣,不知所以加之,至其末,则举先王之法尽废之而后已。又云:“治不极,乱不生;治之极,乱之端也。”他因此指出:“自尧舜至周文武未远也,而养生送死之具已穷而无可复加,此其所以大乱耶?”(注:俞樾:《东野毕善御论》,《佚文》,2页,见《俞楼杂纂》。同上。)有见于此,俞樾认为“孔子将作《春秋》,先修王法”(注:俞樾:《达斋丛说》,2页,见《曲园杂纂》,同上。)。因作《王制说》,详论《礼记·王制》中的三等爵制、三时田制、建国之制、立学之制以及公田籍而不税之制。认为这些制度与公羊师说“往往符合”。因谓《王制》为孔子所作,而由门弟子私相纂辑而成。他强调:后儒见《王制》“与《周礼》不合而疑之,不知此固素王之法也”(注:俞樾:《达斋丛说》,2页,见《曲园杂纂》,同上。)。隐五年《公羊传》,何休注云:“礼,天子六师、方伯二师、诸侯一师。”此说与《周礼》不合,学者多致其疑。俞樾则认为,此乃“孔子所定之制,公羊家传之,而何劭公述之者也”(注:俞樾:《经课续编》卷五,2页,《春在堂全书》光绪二十三年重订本(石印本)。)。然他又疑其文有阙失,认为当作天子六师、方伯四师、大国诸侯二师、小国诸侯一师。他又释昭五年《公羊传》“然则曷为不言三卿,五亦有中,三亦有中”之文,认为依《春秋》孔子之制,不得有中军,有中军,非《春秋》之法。又云鲁于襄十一年作三军,至此舍之,则无中军。且云舍之之故,认为《春秋》至昭公之初,已入所见之世,有文致太平之端,适有舍中军一事,圣人记之以见《春秋》之法。因谓《公羊传》之文乃广言之,不单就鲁国而言。意谓现有三军者,就三而舍其中;现有五军者,就五而舍其中。又谓三而舍其中,此《春秋》大国诸侯二师之法;五而舍其中,则《春秋》方伯四师之法。这样,文致太平之时,则“皆合乎素王之制矣”。(注:俞樾:《经课续编》卷五,2页,《春在堂全书》光绪二十三年重订本(石印本)。)
值得指出的是,俞樾虽以孔子改制为说,赞成公羊家变周之文、从殷之质的说法。然俞樾所理解的改制仅仅是形式的改变。《论语》云:“文犹质也,质犹文也。”俞樾释该文云:“文质之异,异乎其在外者也。至其中之所存,如君臣之主敬、父子之主恩,不以文而有加,不以质而有损也。”(注:俞樾:《群经平议》卷三十一,2页,同上。)
三
三统说是《春秋》微言,赖口说相传。三统说的源头在《论语》和《春秋》经传之中,然其义隐晦,因此,不同公羊家之说颇存异议。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中,对三统说进行了详细的论述。《白虎通》亦有一段文字集中论通三统之义。董仲舒的三统说主要有“三王”“五帝”“九皇”等概念。三统即指“三王”之统,强调“同时称王者三”。所谓“同时称王者三”,即新王确立王统地位后,使前二代王之后退封百里为侯国,他们形式上保留前代之王的统绪,仍继承原来的正朔和服色,客而不朝。“五帝”“九皇”则是三王之前更久远的朝代。退出“三王”者为帝,帝数有五;退出“五帝”者为皇,皇数有九。董仲舒的三统说一是强调三统更替。即每当一王兴起受命而王时,就有一新王之统加入三统,同时也有一旧王之统退出三统,而形成一具有新内容的三统。二是认为三统礼制不同。在他看来,每一王兴起,必建一新统。在此新统中,正朔、服色、礼乐制度都与前王之统不同,以示新王统受命于天。他又以黑、白、赤三色分别代表不同的三统,以示三正之色不同。《白虎通》之三统说不同于董仲舒三统之处,主要在于它强调二王之后若有圣德,天下安之,可再受命为王。如周代殷而王,殷退为二王后,若殷后有圣德,天下安之,殷后可再受命而王。《白虎通》以为这种“非其运次”的情况出现,同样是合理的。
俞樾对董仲舒的三统说是基本赞同的。他在《孝经先王申郑注义》一文中,详引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云:“王者之治,必正号、绌王,谓之帝,存二王之后,同时称帝者五,称王者三,是故周人之王,上推神农为九皇,而改号轩辕,谓之黄帝(注:今说以神农为炎帝)。因存帝颛顼、帝喾、帝尧之帝号,绌虞而号舜,曰帝舜,录五帝以小国。下存禹之后于杞,存汤之后于宋,以方百里,爵号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然则,九皇五帝三王之名,随世代而迭迁。因谓董氏所谓《春秋》作新王之法,殷周为王者之后,绌夏改号,禹谓之帝。”乃“《春秋》之制也。”(注:俞樾:《经课续编》卷七,3页,《春在堂全书》光绪二十三年重订本(石印本)。)俞樾论《诗经》“鲁无《风》而有《颂》”之故,再次详引该文,认为《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注:俞樾:《湖楼笔谈》卷二,3页,见《第一楼丛书》,同上。)。他还指出:《春秋》书王二月、王三月,即是三统之义。他又论《论语》“周监于二代”云:“唐虞帝而非王,非周所得而监。”又谓“夏礼吾能言之,殷礼吾能言之”并非指孔子不能言唐虞之礼,而是“唐虞之帝制,非所用于王者之世”,故孔子所不言。又谓颜渊问为邦,孔子不以韶舞冠夏时之前,而退列于后,“亦以其帝焉而远之也。”又论孟子言性善必称尧舜,而论取民、论建学则仅及夏商周,而不及尧舜。因谓孟子深得三统之义。(注:俞樾:《经课续编》卷七,3页,《春在堂全书》光绪二十三年重订本(石印本)。)俞樾又将三统说运用于经传训诂的学术实践中,如文十三年《公羊传》书:“鲁祭,周公何以为牲?周公用白牡。”俞樾释周公用白牡之故云:武王崩,而成王幼,以殷制而论,周公当王,而周公谦不敢当,故摄而不立,及周公既没,成王以周公为有大勋劳,若以殷制,周公本宜及天子位,故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不用周礼而用殷礼。因谓“周公人臣,本不当用天子礼乐,其得用天子礼乐者,从殷制也”(注:俞樾:《经课续编》卷二,3页,《春在堂全书》光绪二十三年重订本(石印本)。)。殷尚白,故用白牡。
需要指出的是,在大多数场合下,俞樾论三统说,多发挥董氏之旨。但他也曾以《白虎通》之义说经。其说《毛诗》“惟此二国”,就是一个显例。他在这里强调,二王后若其德足以号令天下,则不限于运次,仍可为王。(注:俞樾:《群经平议》卷十一,3页,同上。)可见,他的三统说,在一定程度上,还兼采了《白虎通》中的思想。
四
大一统说,是公羊家关于政治秩序的学说。公羊家关于大一统的论述,主要体现在《春秋》经传和董仲舒、何休的思想言论中。公羊家的大一统思想有“形上”含义和“形下”含义两个方面。“形上”含义即“以元统天”、“立元正始”。所谓“以元统天”,就是以元或元气作为宇宙万物的本体,强调宇宙万物、人类社会以至山川草木、鸟兽昆虫都是从元或元气所出。所谓“立元正始”是指宇宙中的万事万物与人类历史中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制度,都必须有一个纯正的开端,惟其如此,才能获得意义和价值。其归结点是:一统的政治秩序不能统于客观外在的道,不能统于人格化的天,亦不能统于暴力。强调一统的政治秩序必须统于先天的元,这样才算合理合法。大一统的“形下”含义是尊王,建立王道政治,通过王统维系天下,实现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一统局面。
俞樾于大一统的“形上”之义阐发不多,然亦偶有涉及。他说:“天地,一气之所弥纶也,气之所感,聚而成形,非惟人得天地之气,即飞潜动植,无不得天地之气以为气。”(注:俞樾:《啸香馆笔记》卷四,《泡中富贵》,民国书社中华元年版。(原署啸香馆侍者著))他又说:“盘古者,元气之名也。”因以盘古之传说,证“天地之中,形形色色,皆元气之所生也。”(注:俞樾:《宾萌集》卷三,1页,《春在堂全书》光绪二十三年重订本(石印本)。)他以气释神、释鬼、释魂魄、释仙怪。不过,他又认为“气之可养”,养之之法,则在于“持志以率气”(注:俞樾:《群经平议》卷三十二,4页,同上。)。他所谓“志”,又指“义”与“道”而言。这与“以元统天”虽有不同,然都认为“气”是构成世界万物的基本单元。
俞樾对大一统的阐发,重在“形下”层面,即“尊王”。他论闵子骞,谓闵子骞在鲁昭公被逐之时,不忘故君,辞费宰以从故君,因以“所养者深,所争者大”许之,并谓“冉有、子贡之徒,皆不及焉”(注:俞樾:《佚文》,2页,见《俞楼杂纂》,同上。)。他又引《论语·先进篇》“仍旧贯”一语以释长府之事不见于《春秋》之故,认为长府本为财货之府,然昭公居之以攻季氏,则已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鲁人为长府乃季氏想要消除人们对昭公的怀念,此所以《春秋》不书。又谓《论语》“仍旧贯”之“仍”鲁读为“仁”,“仁”即爱,“仍旧贯”即“爱旧贯”。因谓闵子为此言,而孔子许之“言必有中”,实为“圣门之微言”。(注:俞樾:《湖楼笔谈》卷一,6页。又见《诂经精舍自课文》卷一,4页;《佚文》,2页。(《第一楼丛书》/《俞楼杂纂》)。《春在堂全书》光绪二十三年重订本(石印本)。)这里所谓“微言”,其实即指“尊王”而言。俞樾又谓孔子忧君臣之义废而作《春秋》,于是作《春秋论》三篇,详论《春秋》尊君之义。他强调:“人之罪固有可赎,若弑君之罪,虽功存一时、泽及万世,不以赎其毫末也。”(注:俞樾:《佚文》,3页,见《俞楼杂纂》,同上。)他论姜氏会齐侯,谓《春秋》详书姜氏淫乃“圣人别嫌明微”之意;他论“郑伯克段于鄢”,认为《春秋》非罪郑伯,这些均显示出俞樾的尊王思想。王何以尊?俞樾认为王得以尊的关键在“一”,即将风俗政教归于天子。他说:“世之盛也,国无异政,家无殊俗,考礼正刑一德,归于天子。所谓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也。”又说:“周之衰,王者不作,于是诸侯之强大者起而为长。齐桓兴,齐为盟主,晋文出,晋为盟主,《春秋》亦遂从而予之。何者?天下不可以无所一也。”(注:俞樾:《达斋春秋论》,4页,见《曲园杂纂》,同上。)在他看来,尊王是正、是经;一于诸侯,则是权,是变。从尊王的要求出发,俞樾认为“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因此,他认为圣人为治之先在于“正名”,“万物之名皆不可以不正”(注:俞樾:《宾萌集》卷二,6页,《春在堂全书》光绪二十三年重订本(石印本)。)。何谓“正名”?俞樾以“正百物之名”释之,然其重点则在人伦关系。他说:“孔子论为政,必也正名,而《大学》之教,始于格物,其义一也。周公作《尔雅》,自天地以至草木禽兽,一一训释之。盖亦格物之事,推而言之,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皆格物也。物不格,则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妇不妇,尚足与言君臣父子夫妇之道乎。”(注:俞樾:《达斋丛说》,2页,见《曲园杂纂》,同上。)然而,在俞樾的尊王思想中,并非片面要求人们尊王,王所以尊,天下所以一于王,在一定意义上也决定于为王者自身。他继承和发扬了公羊家“众所归往谓之王”的思想,他释文王所以称王之故云:“众所归往谓之王,虞芮质成之后,六州咸附,则已有王之实矣。有其实,岂可辞其名,此文王所以称王也。”(注:俞樾:《达斋丛说》,1页,见《曲园杂纂》,同上。)又谓周自幽厉以下,众不归往、不朝诸侯,则天下已失,故孟子云:“三代之失天下以不仁”,认为孟子虽处周世,而俨然以后世之人待周的原因即在于此。从这一思想出发,俞樾认为后世之人残山剩水仍以蜀汉为正统乃不达“众所归往谓之王”之义。另一方面,他又强调:为王者不应“示天下以异”,对殊方异俗、奇形诡制“摈之而勿御,绝之而勿传,邦国勿赖其用,考工勿详其法。”世之君子才可能“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而胥一世之人才可能“范以先王之法”,并最终达到“耳目一,风俗同,天下长治而久安”的效果。(注:俞樾:《达斋丛说》,5页,见《曲园杂纂》,同上。)
五
俞樾的“夷夏之辨”思想亦与传统公羊学思想一致,即从文化上而非种族上区分“夷”与“夏”。他释《公羊传》“秦之为狄,自崤之战始”一文时认为,秦得周之故都,文武成康之旧治,崤之战以后,秦用由余,以其治戎者治秦,秦俗之敝至于妇公并踞,而“秦于是乎狄矣!”(注:俞樾:《茶香室经说》卷十三,5页,《春在堂全书》光绪二十三年重订本(石印本)。)《论语》“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北宋经学家邢丙疏云:“言夷狄虽有君长而无礼义。中国虽偶无君……而礼义不废,故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南朝(梁)经学家皇疏则云:“周室既衰,诸侯放恣,礼乐征伐之权不复出自天子,反不如夷狄之国尚有尊长统属,不至如我中国之无君也。”朱熹采皇疏。俞樾则认为:“此章之义自以邢疏为善。”(注:俞樾:《论语古注择从》,2页,见《俞楼杂纂》,同上。)由此可见,俞樾在“夷”、“夏”分别的标准上,与其他公羊学者并无差异。然而,俞樾将这一学说与“三世说”结合起来,却又形成一套与近代其他一些公羊家完全不同的历史观。公羊学的“三世说”是将《春秋》242年间的十二世分为孔子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所传闻世历隐、桓、庄、闵、僖五世;所闻世历文、宣、成、襄四世;所见世历昭、定、哀三世。公羊家在这一历史划分的基础上,又赋予三世不同的政治意义,从而形成他们“非常异义可怪”的历史观,并以此寄托他们的政治理想。根据这一学说,人类历史演进的不同阶段是有高低之分的,但这种高低之分的标准不在政治与经济,而在道德。世愈进,人类普遍的道德水平愈高,王化愈广,而“夷”、“夏”的区别也趋于消失。到了太平世,则夷狄已进至于爵,远近大小若一。也就是说,太平世之时,夷狄道德水准大进,能行诸夏礼乐,在道德上与诸夏无别。俞樾虽然也以道德水准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高低,也强调三世进化,然其进化的结果却不是“夷”、“夏”差距的消失,而是鸿沟的扩大,因此,世愈进,“夷夏之辨”愈严。他的这一思想在《于越解》一文中得到充分的表现。定五年《公羊传》:“于越入吴,于越者何?越者何?于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俞樾首先是考定《春秋》书“于越”的年代为定五年和哀十三年,书“越”的年代为昭五年和昭三十年。又引庄五年《公羊传》“倪者何?小邾娄也。小邾娄则曷为谓之倪,未能以其名通也”之文,且将未能以名通称“倪”,能以名通称“小邾娄”与《公羊传》称“越”、称“于越”比较,认为其前后顺序正好颠倒。因详释其所以颠倒之故云:“此圣人之深意,《春秋》之大义也。楚始见经曰荆,其后曰楚,此引而进之也。越始见经曰越,其后曰于越,此推而远之也。”又论《春秋》何以推而远之,认为“当《春秋》之初,王制未立,内治未修,夷狄得以狎至乎中国。故此一荆也,俄而楚人矣,俄而楚子矣,君、大夫皆见于经,与中国等。见夷狄之狎至莫得而禁之也。若定、哀之间,《春秋》成矣,《春秋》成而文致太平。于是此一越也,外之曰于越。见内治修明,外侮不至,凡夷狄之人皆屏之四裔,不与我同中国,故借越以示义也。”从这些思想出发,俞樾又指出,汉时呼韩邪单于来朝,唐时西北诸蕃请上尊号为天可汗,皆有违圣人之意。最后他还提出:“《春秋》内诸夏而外四夷,胥天下之越而于越之,斯可以攘外而安内矣!”(注:俞樾:《经课续编》卷二,7页,《春在堂全书》光绪二十三年重订本(石印本)。)他在《论介人侵萧》、《论楚子伐陆浑之戎》两文中,进一步阐发严夷夏之辨的必要,强调“华戎杂居,未有不乱者也”(注:俞樾:《达斋春秋论》,4页,见《曲园杂纂》,同上。)。甚至要求中国与夷狄断绝一切往来,“外而不内,硫而不戚”(注:俞樾:《达斋春秋论》,3-4页,见《曲园杂纂》,同上。)。这些材料表明,“世愈进,夷夏之辨愈严”是俞樾“三世说”的一个显著特点。此外,俞樾又认为,世愈进,道德水平愈高,封建体制也愈完善。他认为,三代以上属上古时代,上古时代的特征是“公天下”,“自天子以至于里胥,皆众立之。”(注:俞樾:《达斋春秋论》,1页,见《曲园杂纂》,同上。)诸侯不属于天子的屏藩,大夫不属于诸侯的臣仆,“自天子、诸侯以至一命之士、抱关击柝之吏,各量其力之所能任,以自事其事,以自食其食,故曰:位曰天位,禄曰天禄。”(注:俞樾:《湖楼笔谈》卷二,2页,见《第一楼丛书》,同上。)因谓天生管仲,使之匡天下,并非私齐,为齐生管仲。因此,他认为不能以管仲不为公子纠尽忠而相于齐桓公而非之。因为时代不一样,不能用后世家天下的道德标准要求管仲。然而,俞樾并不以天下为公是理想社会,他于《礼记》独取《王制》而不取《礼运》的思想根源即在于此。《春秋》书“卫人立晋”,《公羊传》曰:“立者何?立者不宜立者也。其称人何?众立之辞也。众虽欲立之,其立之则非也。”《谷梁传》曰:“立者不宜立者也,晋之名恶也,其称人以立之,何也?得众也,得众则是贤也。《春秋》之义,诸侯与正而不与贤也。”俞樾详引其文,且谓“公、谷之说,得《春秋》之义矣。”他强调:“上古之义,非可施于后世……若以上古之义复施于后世,大乱之道也。”且谓“《春秋》特书卫人立晋,以明上无天子,下无方伯,自相推奉,为大乱之道。”他又说:“不问其当立不当立,苟以其得众而遂予之,则天下之乱自此多矣!海外荒远之国,君臣之分未明,或由众人推择,遂为之长,岁食其俸而治其事,若傭焉者,榛榛狉狉,固难与语《春秋》之义也。”(注:俞樾:《达斋春秋论》,1页,见《曲园杂纂》,同上。)可见,在俞樾心目中,尊王重道才是理想社会的标准,“公天下”则是社会未进化、道德水平低下的表现。
以上分析表明,俞樾相当系统地吸收了公羊学的基本思想,并将其运用于对儒家经典的训诂、考释中。不仅如此,俞樾还将“六经”视为一个整体,并把公羊思想看成是贯串儒家经典的基本思想。他说:“夫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为后世法,皆所以治来世也。”(注:俞樾:《春在堂随笔》,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42页。)这表明,公羊学在一定意义上成了俞樾治经的指导思想。需要指出的是,俞樾对公羊思想并不限于简单的吸收,他还从自己的现实政治立场出发,对一些公羊思想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正。在三统说方面,他兼采了董仲舒和《白虎通》中的观点,把二者结合起来。他提出的“三世说”具有浓厚的保守色彩,与通常意义上的公羊“三世说”的内涵有着本质差异。在他看来,世愈进,“夷夏之辨”愈严,中国越是应该断绝与“夷”“狄”的一切往来。这样一种思想与中国近代面对的时代潮流是背道而驰的。不过,俞樾并没有简单地运用这一思想评判近代中外文化相互交流的现实。他把人类社会分为“小九州”时代和“大九州”时代,并认为近代中国正处于“大九州”时代的初级阶段,“大战国”时期。他说“今日之天下,乃一大战国也”(注:俞樾:《王子庄〈中外和战议〉序》,《春在堂杂文五编》卷六,32页,光绪二十五年置订本。),并指出,在这样一种“大战国”时期,应兼重商务,“通万国之有无”(注:俞樾:《刘筱舫观察六十寿序》,《春在堂杂文六编》卷十,23页,同上。);在文化上,则应相互交流,以便从文化上“化彼为我”(注:俞樾:《金眉生廉访六十寿序》,《春在堂杂文续编》卷五,7页,《春在堂全书》光绪二十三年重订本(石印本)。)。这是俞樾对现实政治的矛盾态度在经学上的反映。
[收稿日期]2003-10-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