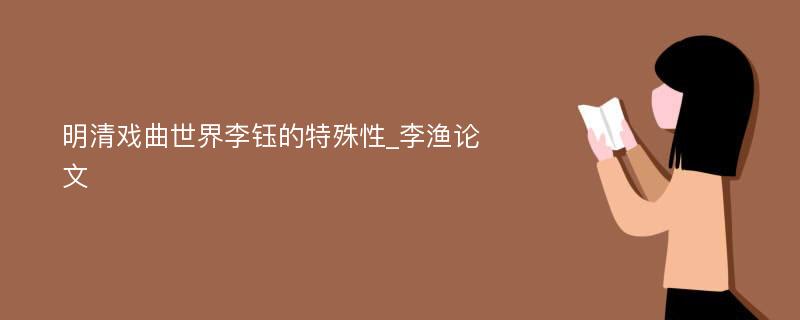
明清戏曲界中的李渔之特异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李渔论文,特异性论文,戏曲论文,明清论文,界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关于李渔,我迄今作有十余篇文章考评过他。(注:《剧作家李笠翁》,载《艺文研究》第42号,1981年12月,第78—112页。
2《李渔的戏曲及其评价》,载《艺文研究》第43号,1982年12月,第51—73页。汉译:《李渔全集》第20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52—272页。
3《游戏文艺——其理解之难》,载《中国——社会与文化》第2号,1987年6月,第246—252页。汉译:《艺术研究》第11辑, 浙江省艺术研究所1989年,第329—337页。
4《关于李渔评价的考察》,载《艺文研究》第54号,1989年3 月,第103—133页。汉译:《艺术研究》第11辑,第338—358页。
5《李笠翁的戏曲与歌舞伎》,载《演剧学》第31号,1990年1月,第96—105页。汉译:《地方戏艺术》总第 51 期, 河南省戏剧研究所1992年,第3—8页。
6《〈闲情偶寄〉考(一)》,载《艺文研究》第59号,1991年3月,第75—100页。汉译:《中国文化与世界》第1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57—75页。
7《戏作者气质——李笠翁与日本》,载《新日本文学大系》第80卷,月报33,岩波书店,1992年2月,第1—4页。汉译:《艺海》第1 号,湖南省艺术研究所1993年,第40—41页。
8《〈闲情偶寄〉考(二)》,载《艺文研究》第60号,1992年3月,第23—45页。
9《〈闲情偶寄〉考(三),载《艺文研究》第65号,1994年3月,第246—268页。
10《李笠翁与日本的戏作者》,载《中国典籍与文化》总第14期,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期,第87—93页。) 本文拟在过去论述的基础上稍作归纳,就标题所示即李渔在明清戏曲界中的特异性问题,略抒已见。
在明清戏曲界或将范围扩展至中国虚构文学(小说、戏曲)的历史中,李渔都可视作是发挥了极为异样才具的特殊存在。
李渔首先对戏曲演剧有着极其明确的独特认识与见解。他在非常著名的《风筝误》末尾的收场诗里,将他对传奇的见地,至为质直地和盘托出。即,戏者戏也,不过是让观众开心解忧的娱乐工具,既然是娱乐那么就要有喜剧,对那些特意花钱来开怀解闷的全体观众,自己的戏剧要写得令他们笑逐颜开、乐不可支。(注:李渔有诗:“传奇原为消愁设,费尽杖头歌一阕;何事将钱买哭声?反令变喜成悲咽。惟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吾忧;举世尽成弥勒佛,度人秃笔始堪投。”)
也就是说,他自己写作戏曲的目的,除了对观众提供慰藉而外无他,为着博得娱情和绝倒,所以直接了当地一味强调娱乐性之重要。他就是带着如此这般单纯明快的自觉和企念去写作的。他为之创作的观众对象,并不只限于有教养的读书人,而是包含了没有学识的妇女儿童在内的一般民众。(注:李渔有言:“传奇不比文章,文章做与读书人看,故不怪其深;戏文做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又与不读书之妇人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词曲部.忌填塞))始终保持通俗平易、 肤浅俗流的水平,让老百姓们乐呵呵笑哈哈的,把本事和剧情的花样翻新作为娱乐性和游戏性的重点来追求,唯此为最优先。“戏剧”就是“play”即嬉耍,因为原本即属老百姓的娱乐,所以先要立足于让人看了不能不喜笑颜开的演剧观和作剧精神。以这样的作者之明确意图和创作意识而被创造出的《笠翁十种曲》,其作风和手法当然有别于他人,显而易见地有其醒目的独特性。
笠翁戏曲大都有着通俗的风情恋爱喜剧的特色。他的喜剧与本来深刻的人生和社会问题相分离,至轻至巧。那些展示男女风月色恋的香艳故事,任谁也会意趣盎然津津有味地看下去,这是李渔考虑到的,他有着喜剧作家的天性。
李渔简截明快地认为,剧作总归是编造的,故往往以完全虚构的情节推出全新的创作。另外,剧作内容也必须努力去除陈腐,翻新求奇,因此无论如何也要最先追求“新奇”。(注:李渔有言:“新也者,天下事物之美称也。”“新即奇之别名也。”(词曲部.脱窠旧)“有奇事方有奇文。”(词曲部.结构第一)) “新奇”二字为其常常叨念于心,执着地孜孜以求。
关于剧的内容,从来的作者们大抵看重非虚构的内容,基于既成的历史和小说故事,难以说是纯粹的创作,但却是元杂剧以来的传统。特别是明清的传奇,这种倾向更甚,一般的作品都愿以历史上的著名人物或者广为人知的现成故事为题材。
李渔与众不同,他自觉而有意识地创作虚构的作品。其作品无不着眼于内容的新奇,特别是用故事情节的有趣性来吸引观众和读者,这可说是自觉的作家的作品创作。虽然《十种曲》中的《意中缘》、《玉搔头》采用了历史人物,《蜃中楼》依据了既成的故事,但其他7 种都成于作者的创作。然而就在《意中缘》的第一出里,作者这样说道:
作者明言虚幻,看官可免拘牵。从来无谎不瞒天,只要古人情愿。
这个剧本在采用并非虚构的实有著名人物(董其昌、陈继儒)之点上是珍稀之作,正因如此作者才故意这样引人注目地有意“明言”。
其他如《玉搔头》是唯一有着所谓历史剧体裁的作品,然其内容方面却与《意中缘》的情态相同,在作假和瞎编之点上全无异样。
异常之作还有《蜃中楼》。它是将著名元杂剧《柳毅传书》和《张生煮海》两个均为年轻男子和龙女的恋爱故事——谁读了也会明白是编造的两个神话故事,至为精巧地交错融合,而创造出的一个新的传奇世界。其实这在日本歌舞伎里是剧作法中一个叫做“绹交”(naimaze)的重要手法。中国的戏曲作品中这样的例子虽不如歌舞伎多,但像《蜃中楼》那样巧妙绵密地纠合既成的两种元杂剧却是此外无他的。即,将数个既成故事巧妙地纠合缠绕使之一元化,而创制出新的别样的虚构世界。意趣丛生地戏耍于二重乃至多重的虚构世界。作者作剧上的独特感觉,于此可见一斑。
例如在《比目鱼》里,剧中两度将先前著名作品《荆钗记》的场面作为该剧的“剧中剧”来上演,必须看到正是这一重要创作意图使该剧亦成为特异之作。即,作为“剧中剧”而被演出的《荆钗记》中的部分,内容已直接地嫁接到该剧的情节上。基于这样一种“绹交”手法、非常考究的作意趣向(“趣向”是日本歌舞伎术语,就是为使作品更有趣而在构想及构成上所下的功夫而言的,即a contrivance,a plot ),是该剧的重要机杼。可以说这是只有李渔才会有的突出奇想。
总之,李渔在作剧时最先意识到的,是“新奇”的故事之虚构的奇趣,即想出有趣的花样及如何将其精致巧妙地穿织在一起。为此他才特别留意于意外与偶然、误会、乔装、化身、剧中剧、大翻转等等崭新奇拨的局面和趣向,然后始终是别有用心、暗藏机关,巧妙地组装情节架构。
因此,在实际的舞台构成的组织方面,他是完全带着独自的意图和认识的。那就是倏忽间给予突然的惊人变化,让观众全然无法预测未来的剧情将如何发展:
戏场关目,全在出奇变相,令人不能悬拟。
(《闲情偶寄》演习部·脱套第五)
他还将这样的作剧手法譬作“歇后语”和“戏法”,说:“宜作郑五歇后,令人揣摩下文,不知此事如何结果。……戏法无真假,戏文无工拙,只是使人想不到,猜不着,便是好戏法、好戏文。”(词曲部.小收煞)从这里我们也可以了解到,他决不是将剧情质直地展开,而是注重用奇想天外的虚构和悬念,以达一味地让观众感到惊奇之目的。而且,这才的确是他的戏剧创作手法(小说也一样)。
暂举一例加以说明。《奈何天》描写的是一个丑八怪的男人竟然娶了三个美貌女子,剧终时他却奇迹般地变成了美男子。作者有意借助这一“奇迹”,使剧情发生突然的变化,由此体现出“大翻转”的趣味性。为达这一目的,作者在构思时埋下了周密的伏笔,在多处穿插了意外的起伏,使所有的剧情都编排在精心设计的极为巧妙的架构上。
如果仅看“奇迹”这一局部场面,人们不难会联想起《琵琶记》第二十七出的《感格成坟》和《还魂记》第三十五出《回生》的两个戏剧场面。前者,由赵五娘的至孝,出现了感天动地神助墓成的奇迹。后者,因杜丽娘的纯爱至情而造成了她的起死回生。然而,由于剧情的编排极其纯朴自然,故这两场戏中出现的奇迹未必会令观众感到惊奇。
在《比目鱼》里,作者依旧采用了“奇迹”这一构思。剧中的一对男女投河自尽后变为比目鱼,又由比目鱼返身为人回到人世。该戏曲在舞台表演方法的处理上相当精致,十分地讲究技巧,在创作和趣味上完全有别于《琵琶记》和《还魂记》。
李渔的戏剧创作法就是神施鬼设、不怕造作地一味追求新奇的情节结构及由此产生的剧情变化上的趣味性。他力求在戏剧虚构场景的编派、戏剧性情节状况的设定以及漂亮精巧的舞台结构等等方面倾注其所有本领,施展其所有才华。他安排各种动物登台亮相,大量采用有观看价值的素材。同时他当然不会忘却如何提高观众兴致,更不会忘却施展他天生的绝技,即利用色与笑、滑稽与猥亵所带来的效果去滋润各个场面。
总之,作为一名戏剧作家,他的创作手法和技能,其舞台效果及独特的创作风格,决非一般文人、业余爱好者所具备,令人一看便知这一切都是出自职业作家之手。事实上,当时他与营利性的书籍出版商、通俗出版界关系非常密切(他本人就是开过书铺的出版商),所以他以著作业者的身份,靠写书包括戏剧小说维持生活。换句话说,作为职业作家,李渔是深深意识到观众和读者,然后去施展他的职业才华的。因此,他的创作风格使人强烈地感觉出的特点,就是带着技艺非常精湛的职业手艺人的味儿。在这一点上,他的确是一名手艺人风格的艺术家 (artisan)。不少作家出于文人的业余爱好也创作了戏曲, 但李渔跟他们有着性质上的不同,有着明显的界线。李渔的剧作与其说是文人、读书人的创作,还不如说是其以精通实际舞台表演的行家自居所编导成的戏曲,其戏曲创作上的独创性也因此而被认识。
二
李渔所生的晚明万历时期,是随着所谓文化过熟而来的各方面方针、原则出现大幅度崩溃的时代,可说是呈现出一种无原则的自由化涣散状态的时代。“雅”与“俗”的原则也同样分崩离析。譬如,以陈继儒为代表的所谓“山人”派的文人辈出,出现了读书人与商人之间的界限极为含混、两者混同融为一体的状况。这也是晚明时期的社会特征。李渔本人也是公然承执“山人”派香火的文人。
戏曲文化本身也令人感到达到了一种熟透了的状态。“雅”、“俗”境界在此状态下亦变得暖昧迷离,与此同时是“雅”与“俗”的两极之间因距离的含混而产生的膨胀。
一方面是出现了戏曲明显地向典雅化、“案头化”方向发展的倾向;另一方面是出现了以芜杂、零乱、卑俗的宣泄过剩精力的剧目耸动舞台的状况。
然而,明清的戏曲史如众所周知,其主流是社会地位很高的士大夫、文人作为业余爱好而创作的南戏(传奇)的历史。可以说是由于这种作家所事,所以戏曲明显地朝文人的趣味化、贵族化的方向发展。因此,将戏曲作为文学高度予以评价、染笔于戏曲的知识分子急遽增加。在他们看来,“戏曲”是作为正统文学的“诗词”的延续,正因为他们能够将自身的古典式的教养和表达技能投入其中,所以才有一试笔墨的价值。这种认识很容易令人产生错觉,以为戏曲同时也是曲辞,结果一味寻行数墨地注重字句的雕琢。尤其在传奇的鼎盛时期、也就是文化烂熟时期的嘉靖万历年间,不仅曲词,就连道白也要求词藻华丽的现象十分严重,以至出现了视传奇为纯文学作品,仅止于书斋里鉴赏的“案头化”倾向。然而,这种戏曲当然是只能限定于一部分有教养者们的读物。
在当时的民间自不必多言,舞台上频频演出的都是些极其一般、卑俗荒诞、芜杂不堪的剧目。譬如以下所记载的那样:
近来牛鬼蛇神之剧充塞宇内,使庆贺宴集之家,终日见鬼遇怪,谓非此不足悚人观听。
(《风筝误》朴斋主人总评)
……更妙在一线到底,一气如话,不似时剧新本,作女扮男装,神头鬼脸通套也。
(朱素臣《秦楼月》卷末笠翁评语)
传奇至今日,怪幻极矣。生甫登场,即思易姓;旦方出色,便要改装。兼以非想非因,无头无绪;只求热闹,不问根由;但要出奇,不顾文理。近日作手,要如阮圆海之灵奇,李笠翁之冷隽,盖亦不可多得者矣。
(张岱《琅嬛文集》卷三《答袁箨庵》)
据上所述,当时的舞台上演出的剧目几乎都是牛鬼蛇神、光怪陆离之剧。神头鬼面、阴阳颠倒极为盛行,近似胡编乱造、怪诞不经的戏剧很多。这些戏剧可谓坚挺地向“巴洛克式演剧”(注:关于“巴洛克”(baroque)演剧,请参看注①之2和5所提及的我的有关文章。) 的高度倾斜,起劲地张扬着野性发泄着过剩精力的玩意儿,无疑是些内容极其芜杂,结构极为离谱的非常卑俗的戏剧。而且由于其内容之卑俗,所以几乎都未能作为戏曲史上的作品而流传后世。然而,这些戏剧在专注于舞台性和尽力追求舞台演出的实际效果上,是并无过错的。
根据前面引述的材料来看,在当时的舞台上,剧中人忽而“变化身态”,忽而“乔装改扮”的趣向比比皆是。这种作剧之趣向,如前所述,李渔也神乎其技,而且是更为花样百出地采用了。由此可以察知这种倾向已经见容于当时的舞台了。虽说如此,但是因为那些市井戏目实在是太卑俗芜杂,所以阮大铖(圆海)及李渔的戏曲受到了张岱特别高的评价。
其实,李渔留意各种戏曲性场面的趣向,试图使剧情更加纷呈有趣的创作倾向,在明末时期代表作家的戏曲方面上已经十分地引人注目了。例如,有范文若的《花筵赚》,吴炳的《西园记》、《绿牡丹》,袁于令的《西楼记》等等。其中阮大铖的《燕子笺》、《春灯谜》两部作品,更以趣向性倾向的显著而尤为闻名。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上普遍认为阮大铖、吴炳师承汤显祖之“临川派”,范文若、袁于令则从属于沈璟的“吴江派”,甚至在语言表达方面都具有文人趣味的高格调和文学的书香气。另一方面,前面提及的他们的那些作品都已特别钟意、留心各种戏剧场面的趣向,追求剧情的趣味性。譬如改扮、误认、替身、代作诗词、误解、误报、错过、错误等等的花样百出。
我认为这种倾向的出现,与该时期戏曲文化的成熟并非毫无关系。伴随着商业经济的显著发展,一般民众生活随之丰富,易于他们参与文化活动,是应予考虑的时代背景。亦即文学已趋大众化了。例如名目众多的白话通俗小说的产生和出版,是该时代的一大特色。戏曲也在另一方面显现出大众化、通俗化的倾向。不管怎么说,李渔都是在该时期这些作家老前辈之后,直接承其流风余绪的作家。
然而,李渔的戏曲作品与上述老前辈们仍然有着明显的区别。从包含语言表现在内的戏曲整体所携的韵味上看,他的戏曲可以说完全彻底地通俗化了。当然,这是因为他的戏曲创作精神和目的,与其他的任何作家都有着根本的相异之处。
让我们简单地看一下李渔之后的清康熙至乾隆年间的作品,在万树的《拥双艳三种》、张坚的《玉燕堂四种》、沈起凤的《沈氏四种》等剧目里,如前所述的特别着意于戏曲之趣向的作风,亦能明显地看到。与此相反,所谓正统派的创作风格的剧目,有洪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蒋士铨的《藏园九种》等剧。在过去的戏曲史上受到高度评价的则是后者,这也是不言而喻的。
三
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那样,李渔认为:戏曲原本就是具有通俗性和大众性的娱乐。他就是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大胆地进行创作的。
但是,中国自古以来,“文以载道”、“为经世济民而文”的基本前提与大原则是一贯受到承认并且长期束缚、支配着文人及读书人的。中国文学期待着现实性、社会性的作用与效果,并视之为文学发展所必备的重要条件和原则。戏曲界也认为:“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琵琶记》第一出),风教攸关,至为重要。这种观念成了明初以后一般的普遍观念。这也许跟大部分作家是著名的读书人有关。但是,同时又把阐释以儒教立场为主流的劝善惩恶的伦理观和忠孝节义作为思想基础,并在这基础上加进了起源于佛教的因果报应观念。
表面上采用正统原则是中国戏曲小说的常规老套,也是必不可少的大框架。因此,李渔在戏曲方面也不断宣扬劝惩主义。(注:李渔语:“传奇一书,昔人以代木铎,因愚夫愚妇识字知书者少,劝使为善,诫使勿恶,其道无由,故设此种文词,借优人说法,与大众其听。谓善者如此收场,不善者如此结果,使人知所趋避。”(词曲部.诫讽刺)
又曰:“卜其可传与否,则在三事;曰情,曰文,曰有裨风教。……情文具备,而不轨乎正道,无益于劝惩,使观者、听者哑然一笑而遂已者,而终不传。”(《香草亭传奇》序))其原因是,儒教意识形态的势力绝对强大,长期统治着思想界言论界,既然如此,至少也得在表面上标榜一番,唯有这样方能得以安心。这样就能巧施掩饰,实际上是给观众提供取乐消遣。这种态度,正好与日本江户时期的“戏作家”们也有相同之处。(注:关于“戏作”及“戏作者”,请参看注①之3、4、5、7、10所提及的我的有关文章。)
我们必须看到,即便一会儿标榜劝惩,一会儿强调儒教伦理,这样做归根结底是想掩饰构思表达上的技巧。譬如,李渔在他自己创作的戏曲收场诗里这样写道:
莫道词人无小补,也将弱管助皇猷。
《凰求凤》
迩来节义颇荒唐,尽将宣淫罪戏场。思借戏场维节义,系铃人授解铃方。
《比目鱼》
这些话都在极力颂扬自己的作品不单纯是娱乐和消遣,但实际上,都只不过是掩饰表面,假装循规蹈矩。也就是说掩饰亦成了构思上的一种手段和技巧。李渔故意反执根深蒂固的儒教伦理,力图写出滑稽可笑的虚构故事(fiction),这是他的惯用手法, 在中国文人中李渔可谓是不可多得的故事作家(storyteller)及娱乐提供者(entertainer)。
长期以来,中国文人一直对虚构故事缺乏认识,对“创作”之含意很不理解。例如,往往拘泥于“事实”,动不动就要查考作品中的人物原型就是其中的一种表现。把戏曲和小说都看做纯粹是一种虚构故事,直接把它作为虚构的故事来欣赏,这种意识,作家和读者双方都缺乏,或者说双方都很陌生,都不拿手,怎么也无法拂去被趣味所吸引的罪恶感及因循守旧的作风。尽情享受风趣并沉溺于其中的时候,读书人总有一种内疚感。虽然的确是有趣,但又不能感兴趣,他们被这种矛盾的心理束缚着。也许这是他们受到了表面上坚决否定创作虚构之儒教伦理的强烈影响的结果。
然而,李渔却立足于独特、自由的见解,与这些读书人的传统性见解全然不同。他故意有意识地追求故事内容的“新奇”进行“创作”。他清楚地意识和认识到了戏曲(以及小说)原有的虚构的趣味性、编造的趣味性,一味地、有意识地、做作地追求这种趣味性。因此,中国戏曲小说史上他的独创性必须得到承认。
从语言表现的方面上看,李渔诸作品追求的不是修辞的美,而仅以通俗的平易明快的旨趣为限,因此不能得到高度的评价也是当然之事。清代的李调元曾激赏乾隆戏曲家蒋士铨的作品“为近时第一”,说过这样的话:
以腹有诗书,故随手拈来,无不蕴藉,不似笠翁辈一味优伶俳语也。
(《雨村曲话》卷下)
也就是说,修辞上的“蕴藉”与否,是作品评价时的重要基准。明代的何良俊,就曾以“关之辞激励而少蕴藉”的看法,未给关汉卿以较高的置评。
但是,从李渔的立场上看,词章的华美与格调的优雅,创作伊始就不是他有意逢迎之处。他并不在意“蕴藉”,反倒更瞩目于“一味优伶俳语”的叠出。(注:笠翁手则握笔,口却登场,全以身代梨园,复以神魂四绕;考其关目,试其声音,好则直书,否则搁笔;此其所以观听咸宜也。(词曲部.词别繁减))因此,其舞台演员宾白的至为洗练与巧妙,是谁都不能不承认的。
本来生动、逼真、平俗的会话语体,即以“一味优伶俳语”连缀的写作,是通俗文学必具的必要条件。李渔天生就有着通俗作家的资质。因此,经其手而成的小说(《无声戏》、《十二楼》等),无不为通俗小说,其戏曲也是可以称为“通俗戏曲”的。其小说不用说是这样,其戏曲让人看到的,也不是很起眼的大事,归根到底不过是开怀释闷的游戏,这方面他是很坦率的。对虚构抱以拘谨及内疚是知识分子的传统感觉,或说是以非俗尚雅的精神为根底的文学传统,对此李渔是站在独特立场上的。他对支撑着中国正统文学的两根大桩即所谓载道主义和文辞主义,不拘泥且不受其束缚,也可说是索性不予理会。他这样的极其异样的作家的出现,是以明末清初各种方针原则大幅度崩溃的特异时代为背景的。
四
如前所述,李调元以李渔的文辞为不“蕴藉”,对其“一味优伶之俳语”所持的批判态度是显而易见的,然实际上他对李渔的作品格外喜好,情有独钟。在梁廷楠的《曲话》卷二之中有这样一段话:“笠翁十种,曲白俱近平妥。行世已久,姑免置喙。”在此番评论之后,接着又描述道:
近人惟绵州李太史调元最深喜之,谓“如景星庆云,先睹为快”,家居时常令歌伶搬演为乐。
我们由此可知作为原则而托出的表面见解,与实际现实之间有极大脱节的现象。中国传统文人、知识阶层尽管依正统派意识,因李渔戏曲之通俗而不能予之高度的评价,而实际上又乐于娱悦其通俗之趣。在作为原则批判排斥的同时又暗中喜好和享受,这矛盾着的两个侧面的同时并立,乃我以为需注目之处。即令是对通俗的虚构故事的趣味性心向往之,也不能全盘照收、径情直言,明显地反映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正统派意识及其原则方针是何等的强固。由此,当然可以察知像李调元那样的李渔戏曲的暗自喜好者一定不乏其人。
譬如,与李渔大致同时代的黄周星在《制曲枝语》之中说道:
制曲之诀,虽尽于“雅俗共赏”四字,仍可以一字括之,曰:“趣”。……近日如笠翁十种,情文俱妙,允称当行。
黄周星于此将李渔的戏曲认作合于“雅俗共赏”的出色作品,此类评价的部分存在,十分值得注目。较之黄周星的正面评价,李调元虽相当弯曲,但总算是给了相应的评价。也就是说,李调元归根到底,也想必是从“雅俗共赏”这个视点来承认李渔戏曲的。
至于李渔自身如何认识自家的作品,他在给友人尤侗(展成)的书信中这样写道:
历观大作,皆趋最上一乘。弟则巴人下里,是其本色,非止调不能高,即使能高,亦忧寡和,所谓“多买胭脂绘牡丹”也。
(《李笠翁一家言》卷三《复尤展成先后五札》之五)
这种对自家作品风格的认识是至为坦率的。即以娱乐本位的大众通俗演剧为指向,不追求所谓有文人趣味的典雅戏曲,于此亦可一目了然。明知自己的戏曲从传统的戏曲编剧立场上着眼会得到种种批判,却还是在戏曲的创作上一味追求着通俗的趣味性。
问题归根结底在于如何把握和评价李渔戏曲所带有的这种极为特异的“通俗性”。如果从正面方向上去予以评价的话,就只能象黄周星(或者李调元)那样地从“雅俗共赏”的视点上去予以认定,这就是置评的立场之一。
一般说起“通俗”总是带着贬义,李渔作为通俗作家从来是被轻视的。但是通俗也含有从高级到低级的各种各样的水平线,不能一概而论,总不能因为是通俗就一概加以排斥和蔑视吧。通俗的作品中也可能有优秀出色之作,这应该得到我们的理解和认识。
李渔的戏曲在众多的通俗作品中,是出色的,且其艺术完成度也算是颇高的。在无数通俗作家、大众作家里,他可说是格外出众的例外存在。于此也可以得见李渔的特异性吧。
附带说一下,我曾提示过李渔的戏曲与莎士比亚的戏剧以及日本的歌舞伎属于同类即同属“巴洛克戏剧”脉系。李渔的戏曲,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般观念上看,是与文人的作派相去甚远的通俗怪诞之作,然而从世界演剧的一般水平线上眺视时,却并非异样之作,实际上是带着某种超出时代和地域的普遍性的。对李渔戏曲的“特异性”,我想可以这样地去理解。
关于李渔非常著名的戏曲理论(即《闲情偶寄》之词曲部与演习部),我还想再附上一笔。这本来是作为他的随笔集的一个环节,以随心所欲的口吻信笔成之的。因此,在随处确实可见李渔独特的出色见地和识见之同时,又不能忽视这是作者操着游戏之笔涉笔成趣的可读性极强的读物,从中足以窥见作者决非一般寻常的特异才能即“异才”的样式,应该说是极为特异的戏曲论。(注:关于这点,请参看注①之6 所提到的我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