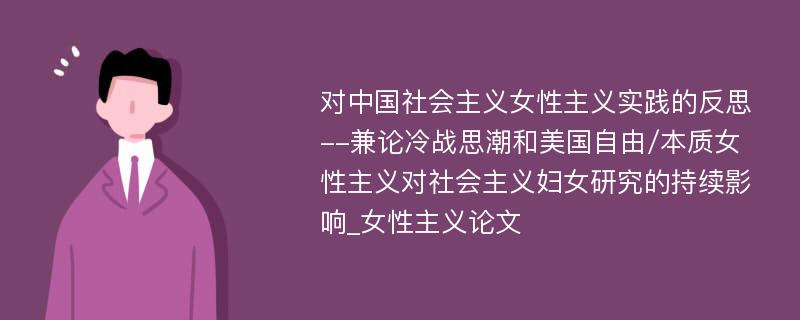
中国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实践再思考——兼论美国冷战思潮、自由/本质女性主义对社会主义妇女研究的持续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性主义论文,思潮论文,美国论文,冷战论文,本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442.9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15)03-0005-15 在当今英语学界乃至世界范围的研究场域中,讨论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妇女解放必须面对几种根深蒂固的研究范式,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两种思维定论是:(1)社会主义革命具有父权本质;(2)性别系统和女性主义实践(运动和研究)都应该具有自治独立地位。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性别研究已出现了一些比较多元和相对成熟的成果①,但进一步揭示这几种范式在历史与政治上的根源并做出进一步的批评研究,还远远不够。这些研究范式所得出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性别的论述,不仅延长了冷战意识形态,也严重妨碍了对社会主义遗产具有批判借鉴性的评估,影响了具有创意性的跨国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在全球的发展。同时,这些片面的结论也严重阻碍了对中国妇女和女性主义实践在不同阶段所面临的真正历史局限、悖论和问题的考察和研究。 在本文中,笔者首先批判性地扼要分析上述两种研究范式背后的历史和政治渊源,揭示它们对中国社会主义和妇女研究的持续影响。接下来,笔者将重新追溯和勾勒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中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实践的历史,侧重强调中国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实践的体制化特征,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在中国特定历史场景里结合的特殊意义,凸显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实践的多维主体性。本文的主旨,除了揭示社会主义和性别跨国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冷战思维和自由/本质女性主义意识形态,除了加入当今部分学者的共同努力,展示社会主义革命和性别的多元张力之外,还希望能为全球不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历史、为跨国女性主义和文化提供不同的女性主义研究框架和方法。 一、关于社会主义和中国妇女的研究框架:冷战意识形态和西方自由/本质女性主义 在中国性别与女性主义研究领域里,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一批社会科学学术成果奠定了今天对中国社会主义与性别研究的主流论述。这些从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角度出发的著作中最有代表性的包括朱迪思·斯泰西(Judith Stacey)的《中国的父权与社会主义革命》(1983)、菲莉斯·安德思(Phyllis Andors)的《未完成的中国妇女解放,1949-1980)(1983)、凯·安·约翰逊(Kay Ann Johnson)的《中国的女性、家庭与农民革命》(1983)以及玛杰里·沃尔夫(Margery Wolf)的《延后的革命:中国当代女性》(1985)②。当然,这些著作之间并非没有差异,特别是在行文语调和作者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总体态度上。例如,有些作者认为中国共产党还是有意解决妇女问题的,不过社会主义中国的妇女解放一直被延误了;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不过是在多种父权力量之间的一个协调,从来就没有真正试图解放妇女。但这些著作的共同点体现在它们近似统一的结论,而正是这样相互影响并不断重复的结论给学界和大众读者对中国社会主义和妇女解放的看法奠定了难以动摇的根基。这些著作的总体结论包括: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背离了“五四”女性主义运动的实质,使得性别革命缺乏“自治性”,在面对其他阶级、民族等“紧迫”问题时总是在性别问题上让步;中国共产党很多时候不过是在利用妇女的劳动、劳力来为战争、生产和经济发展服务;在面对不同地区的对妇女解放政策和实践对抗或抵制的力量时,共产党没有能够强有力地进行控制和反击;农村的传统父权习俗包括经济生产合作形式以及婚嫁方式没有被根除。总之,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还是父权革命,没有能够解放中国妇女。 尼尔·戴蒙德(Neil Diamant)在对中国1950年《婚姻法》的英文研究提出修正和批评时,揭示并分析了为什么在西方学界,这几部20世纪80年代的著作会成为日后关于女性和社会主义中国的“日常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1](P172)。他举出三种可能的原因:“这些书籍要解决的是女性主义理论所关注的问题,它们都是由声望很好的出版社出版因而声誉不错,而且都是平装版[容易销售],而最重要的是,它们经常被指定为[大学]课程教材,用以探讨‘中国女性’‘女性与发展’或‘性别在中国’——这在美国可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市场。”[1](P172)今天,很难找到一本关于1950年《婚姻法》的参考书(或一篇文章)是没有引用上述研究作品的。[1](P173)戴蒙德论述的这几点都很重要,尤其是第一个点,因为这些学术著作带有对(西方)女性主义及其理论在世界范围内运用的探究色彩,它们的影响便超出了其各自特定的社会科学领域,也超出了中国学领域。例如,在第一篇研究中国当代女性电影的英语文章里,裴开瑞(Chris Berry)便引用了朱迪思·斯泰西的结论来探讨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中国的妇女解放问题[2](PP8-19)。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的学者们针对这些关于中国的“日常智慧”表示了种种关注。一部分学者质疑了这批研究著作中对中国妇女参与革命历史的史籍以及对她们主体性的严重无视和忽视③,另一部分学者试图纠正被误读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内部构成并非一成不变的,其政策也并不是简单划一,中国共产党在具体历史环境中的种种措施,更不是在教条的铁腕控制之下,不顾及国际、地域、历史差别而制定的[3](PP xxxix-lxix)[4][5](PP915-942)。尽管这些晚近的作品给性别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带来了更多元的研究视角,但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影响用戴蒙德的话来说还是“保持着惊人的坚韧性”[1](P172)④。更严重的是,这些影响甚广的著作中关于性别和社会主义所得出的普遍性结论和所使用的理论框架甚少受到挑战。笔者在下文中通过集中分析斯泰西的著作《中国的父权制与社会主义革命》,来阐明这些“日常智慧”产生和盛行的历史、政治和理论基础。 何汉理(Harry Harding)在研究美国大众和知识分子对于有关社会主义中国的观念和话语时,追溯了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的发展脉络,得出了下面的结论:“如果在70年代美国人认为共产主义在中国取得了胜利,那么80年代初最常见的判断则是共产主义在中国失败了——而且败得相当惨。”[6](P257)何汉理这篇文章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将80年代美国对中国的贬斥同美国80年代新兴的新保守主义以及在美国知识分子中重新燃起的对资产阶级价值观的追寻(例如个人自由、隐私和正义)联系起来。他指出,特别是在第二次冷战时期或冷战的第二个激化阶段(1979—1985),美国再次见证了将西方价值观普世化的趋势,同时也产生了“用这些价值观来打量中国”[6](P258)的范式。何汉理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极端印象,不管是理想化还是妖魔化,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内部政治的反映,而美国人在20世纪80年代对社会主义中国的诋毁究其实是受新保守主义支持的冷战思维的影响。何汉理这些看法可谓一针见血,为下文(重新)解读斯泰西的著作提供了必要的语境。 斯泰西自己有关中国妇女解放的研究经历了类似何汉理勾勒的线索,从极端乐观的评价(1975)截然转向彻底否定[7](PP2-3)。《中国的父权制与社会主义革命》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女性主义学者对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妇女解放的幻灭和否定。斯泰西开篇便提出“为什么社会主义没有解放中国妇女”[7](P5)⑤这样一个问题,明显的是为一个已经有预设结论的问题寻找证据,而不是探讨社会主义在中国性别转型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这位研究西方家庭变迁的社会学家从没有接受过中国语言或历史的训练,但她认为西方学者研究欧洲家庭史特别是欧洲农村家庭变迁的成果和结论可以用来讨论中国问题。在这本书中,她将自己的研究集中在中国现代的农民家庭上,特别是解放区和之后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农民家庭。借用西方学者对欧洲农民经济和家庭在早期现代工业化中的变迁的较有创意的新近研究成果——农民家庭为了保存某些传统父权价值而有意识地顺应家庭结构在现代工业化过程中的某些变革——来说明中国社会主义农民革命其主旨也是为了保存最根本的传统父权价值。她声称,社会主义革命从来就没有真正考虑过妇女解放,而是和传统父权结构联手,为共产主义者攫取权力。说得更明确一些,她认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在1949年之前,只不过是用“新民主父权制”替换了儒家父权制,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种“新民主父权制”又被“父权制的社会主义”所替换[7]P253)。斯泰西的单维度结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父权制革命”[7](P253)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语境中成为强劲话语,许多人称誉这一结论为中国社会主义研究提供了“新颖”的视角⑥。 今天看来,《中国的父权制与社会主义革命》远远没有满足学术研究所需的基本标准,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内的标准。然而,此处的关键不在于集中批评某一本著作的缺陷,而是揭示冷战意识形态对于这批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成果的产生与接受起到的无孔不入的作用,因为冷战意识不仅可以让这位非中国专家的有关中国的研究结论成为主流学术话语,还可以让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研究中国的专家抛开自己田野调查的结果以达到具有冷战意义的结论⑦。换句话说,冷战意识不仅成为研究社会主义和女性解放的重要政治框架,它还积极建构学术走向和结论。 另外一支对20世纪80年代关于妇女和社会主义中国的“日常智慧”起到重要影响的话语是西方自由/本质女性主义。西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强调在资本主义体系内争取女性个人、法律权利。在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的左翼女性主义者(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影响)在左翼运动中开始同左翼男性产生分歧,尤其是后者对女性的歧视使得部分左翼女性主义者在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脱离左翼阵线,形成了本质女性主义⑧(Radical Feminism)新阵营。本质女性主义开始还比较激进,她们批判左、右阵营中的父权思想。但由于其在理论上开始建立诸如父权文化和男性中心文化具有跨历史性和普世性的假设,认为女性受压迫是世界上一切不平等的起源,不会因为经济基础的改变而变化,以及性和性别体系(sex-gender system)具有独立性等较为绝对的论点,她们逐渐开始放弃左翼运动的具体宗旨和政治理念包括消除阶级压迫和资本主义体制。西方“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流派也正是在此时崛起,主要是对早先机械马克思女性主义侧重经济和阶级分析提出批评,要求将性别作为同阶级同样重要的范畴来看待,一方面强调父权制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定物质基础[8](PP1-33),另一方面要求将“上层建筑”和文化层面中的男性统治表现纳入批判和讨论[9]。西方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同时也对本质女性主义抽象的反历史、反唯物主义的普世父权制提出质疑,重申具体历史和经济形态中不同父权体现的重要性以及揭示资本主义新型父权再生的关键。但是,由于英美两国保守势力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崛起,由于西方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二元论”(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左翼话语在资本主义系统中的进一步边缘化,西方女性主义总体上开始转向文化领域,并开始脱离社会运动。原本带有左翼色彩的女性主义不再提倡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因为在她们看来父权制超越具体政治经济体系和历史社会,具有独立性质,所以她们转向提高个体的性别文化意识,从而导致部分本质女性主义者向“文化女性主义”(Cultural Feminism)者发展,在社会和政治变化上开始转向保守和无为。1975年以后,根据埃伦·威利斯(Ellen Willis,当时参与左翼女性主义转型的活动家和学者)的观点,西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只强调在资本主义体系内争取女性个人、法律权利的流派——开始同本质女性主义联合并成为主导力量⑨。美国左翼女性主义本质化(反历史唯物主义)以后,逐渐同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联手,从而转向维护资本主义系统的保守走向,这是部分像斯泰西这样的女性主义学者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妇女运动立场转变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斯泰西整本书的结构,充分体现了西方左翼女性主义从机械、狭隘和西方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演变成具有保守倾向的本质女性主义并开始做出维护资本主义体系的冷战结论的过程。 冷战话语和西方自由,本质女性主义的密切配合,是美国8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的学术研究的根基,造成的影响延续至今。如果说冷战意识形态根本否定社会主义能够以任何方式解放中国妇女,那么西方自由,本质女性主义话语则强化了这种观点,因为这个话语视点强调父权制具有超历史、跨地域的普及性,认定世界上所有的女性主义都应该首先是个人主义的,应该独立甚至对立于其他政治、社会、经济问题与运动[7](P264)。斯泰西的书稿从头到尾都自觉不自觉地把妇女的权益和中国共产党发起的社会主义重要运动——无论是反帝战争、阶级革命还是经济改革——隔绝开来甚至对立起来,似乎中国妇女完全置身于现代中国历史之外,她们的解放应该在一种“真空”中完成,否则就是被利用。上文提到的其他学者虽然不如斯泰西极端,但她们一样强调女性主义运动的“自治”,还坚持强调将“女性平等”[10][11](PP63-64)问题与其他经济、政治、社会问题区分开来的必要性。 斯泰西的著作典型地代表了美国自由/本质女性主义在第二次冷战浪潮中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妇女解放的研究走向。最重要的是,她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从根本上界定为农村家庭革命[同城市个人主义革命相对],是对20世纪初农村传统父权制家庭危机的回应,目的是将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父权制权力重新分配给广大的男性农民,即她所谓的“新的民主父权制”[7](P86、P116)。这种定义不仅忽视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本质,而且极大地缩小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范围,也削弱了它的历史和国际意义,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从更广阔的政治、经济、社会语境中剥离出来,并将女性主义实践局限在个人主义权利和家庭革命。实际上,殖民现代性的全球语境对于界定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革命有重大意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早期的辛亥革命一样,都具有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运动特征。中国的女性主义无论是国民党提倡的自由女权主义还是共产党提倡的社会主义妇女解放,都和反帝的民族主义革命分不开。此外,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其他大多数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又不一样,它还是反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运动。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实践在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也具有多维性质:它反对历史上各种父权制,也反对阶级压迫,同时也是民族主义独立运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斯泰西的研究视野和结论抹杀了非西方语境里现代革命的复杂性,因而也忽视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在(地缘)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里引起的激烈的结构性变化。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将父权等级制直接并仅仅等同于家庭的存在[7](P116),斯泰西轻而易举地制造出两对相对立的价值换算(equations):家庭=父权制,而个人主义=女性主义。“当农民同从前一样用家庭的而非个人主义的条条框框来计算他们的利益时,他们打的还是父权制的算盘,是按照性别和长幼秩序来保证不同的花费、机会和利益。”[7](P255)斯泰西用西方资本主义大生产对农村家庭经济的破坏和摧毁以及资本主义体系中中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信条来衡量和判断一个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半殖民地国家兴起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女性主义实践,不仅显示了研究主体将西方个人主义、自由女性主义作为衡量世界女性主义实践的普世原则的方法,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对资本主义经济大生产中所产生的更严酷的、在全球范围内的性别分工和阶级不平等、更强势的新型父权制的形成的规避和默许。正如某些西方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所指出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大生产对封建家长制的摧毁并不说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摒弃了男性中心。新的性别压迫,同阶级压迫一道,是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必然[9][12](P73)。更为关键的是,作者对资本主义体制中产生的“核心家庭”(中产和/或无产阶级)中的女性地位缺乏历史的评述,仿佛资本主义体制中的“父权制家庭”已经在女性主义意义上解体了。当然,斯泰西也只有用这种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以及普世本质的女性主义话语原则来检测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中的性别问题才能得出符合冷战意识的结论,那就是,资本主义胜过社会主义[7](P262)。 更具体地说,斯泰西这种以家庭经济和文化为中心的框架,以抽象的、跨历史跨区域的父权制价值为支点的论述暴露出她对中国农村妇女现状的盲然。第一,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国农村劳动妇女受到的压迫不能用家庭或性别的单一框架来理解。除了西方和日本的经济/军事帝国主义和各种战争带来的动荡,女性农民同男性农民一样受着本土地主阶层的剥削和压迫,因而她们有着同男性农民相似的政治和经济要求[13](P263)。因为阶层、阶级以及城乡和地区的差异,中国妇女之间的差异极大,并不是一个有机的统一的整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系列运动中不少是直接针对男女底层劳动者的共同经济利益的,特别强调女性解放中的经济权益。例如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让当时的贫苦农民家庭(包括农妇)得到了基本的经济利益,并同时通过立法给予妇女土地拥有权,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举措。从理论上讲,斯泰西好像按照唯物主义思路,认定只要以农业家庭为中心的经济体系还存在,父权制就仍然存在;但这种抽象的、狭隘的唯物主义完全背弃了历史的复杂性,暴露了机械的、西方中心的女性主义立场。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无法彻底改变以家庭为中心的农村经济结构,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并非国家执政党,它不可能在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买办资本主义体系以及中国农村长期存在的封建等级经济制度(并不仅仅是家庭的)中,在共产党工农武装为自身生存而进行的殊死搏斗中,在民族独立和内战的绵延战火中,开展社会大生产和体制公有化并长期巩固其成果。斯泰西完全无视历史状况和底层农妇的多种需求,不加分析地将1940年的土地改革定义为父权性质:“土地改革保证女性有平等的土地权,但以家庭为中心的经济和主导的父权制价值观有效地阻挡了绝大多数女性得到任何权益。”[7](P130)更严重的问题是,斯泰西完全避开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贯彻的新《婚姻法》中对家庭父权价值的种种挑战。这种高度选择性的、只以孤立的家庭为研究中心,并将农业家庭视为女性问题所有根源的方法,不仅显示出其没有能力将阶级或社会等级结构纳入她的研究框架中,更为重要的是,揭示了她对国际资本殖民主义的盲然或者潜意识的支持(因为她完全无视经济和政治帝国主义对中国农村的影响,坚信只有资本主义才为“女性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供土壤)。土改绝不只是像斯泰西所说的,把父权简单地重新分配给男性老百姓,因为土改改变了在中国延续千年的父权阶级等级结构的一个物质基础,直接动摇了中国特定的父权经济制(土地拥有权)的根本,而且土改运动本身还特别强调动员农妇在公共场合表达自身遭受的种种压迫,发表自己的意见,对底层农妇参与公共事务和产生掌控自我命运的意识起着重要的作用[13](P264)。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新土地法赋予农妇平等的土地权,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如同其他研究中国的学者已经指出的,都具有划时代意义,为农村妇女解放建立了至关重要的物质条件和制度支持[13](PP262-264)[14](PP75-76)。在当时的战争年代,当其他改革——例如生产方式的国有化和家庭经济的解体——都不可能发生的时候,女性经济权利在局部地区的制度化就显得更加重要和难能可贵。连斯泰西最后也不得不承认:“妇女在法律上享有的新的土地权,虽然容易被剥夺,但连同妇女公开参与土地再分配一起,在物质基础上增进了她们在新建立的民主父权秩序中的地位。”[7](P135)这个显得有些“无奈”的表述深刻揭示了她在总体论述上的矛盾,也就是说她一方面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的父权本质,可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广大农村妇女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有着空前未有的历史改变。这种矛盾性暴露出预先设定的冷战意识形态、自由/本质女性主义理论同斯泰西所提取的历史素材之间的逻辑裂缝。 从学术著作的论述结构上看,《中国的父权制与社会主义革命》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中国(1949年以前和以后)两部分在方法和视点上相互存在着深刻矛盾,更显示其设定的冷战结论和自由/本质女性主义的立场。在谈及1949年之前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斯泰西采用抽象机械的唯物主义的方法一再强调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像资本主义工业革命那样)打破农村以家庭为单元的经济生产模式,所以社会主义革命是父权性质的。可当讨论到1949年以后50年代的中国农村时——那时的中国农村的确实行了社会主义大生产和经济体制公有化,并从本质上改变了以个体家庭为生产单位——斯泰西却笔锋一转,不再触及这些在前半部著述中至关重要的家庭经济模式,开始用本质文化女性主义的抽象观点来检测社会主义中国农村中不变/遗留的父权传统习俗和家庭文化意识;用军队以男性为主(男人—女人对立观)的例证说明新型公共父权的兴起。这是一本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和女性解放的学术专著,可斯泰西竟然对1950年新《婚姻法》不着什么笔墨,更没有对其历史重大意义有任何分析。由于作者自身对社会主义文化体制的广泛性和高强度意识形态宣传的隔阂,斯泰西还断然声称社会主义实践在社会、文化层面上没有深刻批判传统父权,因而让后者能成功地一次又一次在“集体化”、“大跃进”、“文革”等运动中抵抗“进步”力量,捍卫并保持了传统父权的主要因素[7](PP203-227)。 这种随意或强行更变主体论争逻辑和方法的行为也在深层次上说明了主流美国女性主义学者自身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困惑、分裂和转向维护现存资本主义体系的保守倾向。更为严重的是,斯泰西这种脱离具体历史的结论完全是预设性的,因而在对社会主义革命作任何具体分析之前就已经断言了革命的失败。斯泰西在其专著的结尾一章中再次强调,贫穷的农业社会首先不能帮助建立一个“自治自主的女性主义运动”,更不能使任何女性主义运动强大到在革命过程中起到“独立自主的作用”[7](P262)。很明显,不需任何实际研究,斯泰西本来就已经完全可以断定中国这样的贫穷农业社会没有什么可能产生任何“独立”的女性主义运动,因而很“自然”就会得出强化冷战意识形态的预先设定的结论,那就是:“女性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比在社会主义社会能找到更适宜发展的土壤。”[7](P266) 以斯泰西为代表的20世纪80年代有关社会主义政治和性别研究的主流范式至今仍在发挥影响。有关中国女性与社会主义的研究还在继续强调个人主义与“独立自主”的实践,强调性和性别系统的自治性(autonomy of a sex-gender system)[7](PP264-265),继续强化中国女性与中国政治和阶级革命之间的“本能”的对抗关系。社会主义革命在妇女解放问题上仍然被视为是一个“自然”的失败[15]。这种顽固的“日常智慧”导致了学术界对社会主义中国女性文化的全然漠视。中国女性作家和导演在社会主义电影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被看成和中国男性一样,是顺应(conform)主流政治的,因而是非女性主义的⑩。 突破这些冷战和自由/本质女性主义的研究范式不仅需要研究中国的学者们持续不断的努力,也需要全球知识分子为促进国际政治和全球政治文化的变革做出不懈的工作。当今,新自由主义资本结构和政府管理在全世界的传播,从不同的角度挑战了女性主义和地区学的研究。女性主义学者在新的历史状况下需要重新审视历史遗产,探讨历史和当前形势共同带来的跨国关系研究中的问题并提出对策。 二、中国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体制化的建构和多维主体性 (一)女性主义实践的体制根基 任何女性主义话语和实践都具有一定的体制性,都同其生成的经济政治体系直接关联。西方女性主义实践虽然常常以占据边缘来强调自身对某些主流价值的批判,但常常忽视了自身同资本主义其他主流话语和实践的关联性甚至共谋。笔者强调女性主义实践的制度化性质,并不是说女性主义可以被简化为或完全受制于已有的或新兴的制度与范式而没有自身的批判和干预能力,也不是说各种女性主义实践或文化在相同的制度语境里会表现出统一的形式。相反,笔者认为将女性主义实践的制度背景纳入考虑,可以起到以下几个重要作用:第一,揭示出什么因素或力量在不同的政治区域和历史时期可以让什么样的女性主义实践得以开展和实现;第二,理解特定的女性主义实践和现存的以及新兴的体系、制度、话语之间的权力消长;第三,也是更重要的,是对长期以来的一个神话,即认为女性主义“是”或者“应该是”独立于政治、经济、文化权威与体制——不管是帝国主义的或民族主义的,以国家为基础的还是以市场为走向的体制——的观点,给予解构和批驳。换言之,虽然女性主义实践在历史上都具有一定的批判意义和政治干预性,但它们同各种制度力量之间的关系却是十分复杂的,例如有些制度力量可能在促使中产阶级女性解放方面起到积极作用,可在其他领域里却是具有压迫性和“反动”性的。我们必须充分理解这些互动,才能评价特定女性主义实践在历史上的贡献和局限。对女性主义的这种认识也可以让我们进一步意识到,在特定地域和历史语境中,女性主义实践的某些局限是制度造成的,因而也只有通过变革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才能最后解决。 对女性主义体制化的研究,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分析处于相对边缘化位置的女性主义实践与核心政治、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边缘化或错位的立场并不必然意味着政治上的颠覆或对抗。许多边缘化的实践被包容在更广阔的体制内,甚至得到后者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不少边缘化的实践往往和核心的政治、经济力量在其他社会问题或在不同的政治领域里产生共谋合作。例如,虽然女性主义实验先锋电影在西方资本主义体制下被边缘化,但它却得到私有财产话语和中产阶级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卫护。其实,带有精英及男性中心色彩的先锋电影或艺术电影已经在主导经济和政治体系中被体制化了,它在艺术领域里的经典化是不容忽视的。毫无疑问,20世纪70年代的女性实验电影对于揭露和挑战好莱坞商业电影中的性别差异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如果以为女性实验电影可以颠覆好莱坞并挑战整体的资本主义父权制,那就遮蔽了西方女性主义文化实践与体制及主流话语之间的复杂关系。过分扩大女性电影在资本主义体制中的作用,说明后结构“话语”女性主义看不到自身对广阔的政治、经济体制的依赖,也意识不到自身有意无意地同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与制度在其他层次上合谋的事实。二是探究不同国家、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女性主义实践。尽管所有女性主义实践都具有制度的成分,但女性主义能融入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制度的程度却因不同的政治经济体系而异。第一世界女性主义实践的途径是通过维护中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争取女性的经济与法律权利,或者宣扬边缘的左翼理想而确立的,而第三世界的女性主义实践却和反帝国主义的主流独立政治运动、国家建设以及经济发展有直接关联。这种差别意义重大,要求我们重新认识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的民族国家成分,并且进一步审视这些民族国家是怎样在主流制度与文化中推进(或者制约)女性主义实践的。中国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实践使这种再解读尤为必要。笔者在下文中将集中梳理社会主义革命历史中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制度化的历程。 (二)制度化与整合化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 在考察历史上不同女性主义的角色和功能的时候,一个重要的步骤便是分析它们在政治、社会、经济语境中的制度化过程。西方女性主义在全世界,特别是在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首先是西方帝国主义和资本扩张的结果,但并不是所有西方女性主义观念和实践都能在本土环境里扎根成长。在中国由皇权制度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中,各种女性主义(包括无政府主义女性主义、自由女性主义、进化和优生女性主义、马克思主女性主义)一一登场,但只有经过本土制度化的女性主义,或整合进当地政治、社会、经济实践中的女性主义,才能成为中国现代历史中起主力作用的系统力量之一(11)。 本文中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概念,指的是20世纪20年代初以来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女性主义实践。这里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和资本主义西方社会里左派知识分子在20世纪70年代结合本质女性主义论点而提倡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批评话语不同,它是理论和革命在一个具体的第三世界场景中的本土化实践和历史体验。中国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源于“五四”文化运动(1915-1925)中都市自由个人主义女性主义、民族主义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话语(12),因而同时容纳了激进的个人主义、女权运动、反帝思潮和社会主义对女性解放观念的阐释。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作为文化批评话语形式,在“五四”文化运动之初就已形成[16](PP66-67);它直接阐明了关于妇女解放的一系列核心的马克思主义观念,诸如废除私有产权和资本主义,妇女参与社会生产和政治管理,妇女解放从中产阶级权利运动过渡到劳动妇女的阶级与性别解放,以及社会主义是妇女解放的政治经济基础,等等。但直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才有了进入制度化阶段的可能性,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观念自此才和一个投身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实践的政治组织挂钩。 中国共产党在1922年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这是一份组织和指导女性主义活动的正式纲领,强调中国妇女运动既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也是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17](P159)。将妇女解放的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结合起来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的一项基本政策[14](P58)。这种理论与政治的明确性使中国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在当时多种外来的女性主义话语中逐渐形成自身独特的轨迹,为女性主义在体制上融入社会主义革命奠定了基础。整个2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持续发展,直接参与民族主义革命、劳工运动以及国共联合发起的铲除军阀和改革政治的北伐运动(1922-1927)。1925年中国共产党在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采取了新的《妇女运动决议案》,强调工农妇女在党领导的妇女运动中的核心地位[17](PP161-162)[18](106)。可是1927年国共的分裂,以及随之而来对妇女积极分子、中共党员的血腥镇压和都市里的白色恐怖使得中国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实践产生了急剧的变化。 国民党的镇压迫使城市里的中共党员转入地下,而一部分中共党员在这个时候重新开始尝试在农村组织共产主义力量。2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它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转型,其中包括对自身的女性主义政策以及所属阶层和群体进行的反思。中国共产党开始面对广大的农村妇女,而不仅仅是城市女工,重新自我定位。作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一个重要阶段,中国共产党这时期对农村妇女以及底层劳工妇女的认识造就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在未来中国实践的新方向。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给中国语境里的农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提供了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理论依据。毛泽东在这篇文章里指出,中国男人(农民)怎样受着政权、族权和神权的支配,而中国妇女却在这三种权力之外,还受着夫权的压制[19](P44-46)。毛泽东认为,地主的政治权力是其他三种权力的根基,因此摧毁土地经济关系并推翻地主的权力是粉碎传统社会体制的第一步。在中国历史上,农村妇女第一次被再现为中国政治、经济、宗教、社会体制最底层的群体,并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直接挂钩。同时,作为受压迫最深的群体,中国农村妇女——连同男性农民——被视为或建构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导力量,将给传统中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1928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妇女运动决议案》(以下简称《决议案》),深刻反省了中国共产党前一段时间妇女运动中的问题,诸如偏重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群众,缺乏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的具体目标和计划。《决议案》还洞见了国民党时期那种所谓跨阶层跨阶级的“一般的妇女运动”在国共合作彻底分裂后已被进一步的阶级化,已经没有实际意义[20](PP11-12)。另外,《决议案》认为,停留在女权主义层次上的妇女运动,是通过“离开政治离开革命而以和平方法和宣传以解放妇女”,因而“完全是空想、幻想”[20](P12)。《决议案》指出社会主义妇女运动必须转向“工农妇女”。虽然农村妇女在中共四大关于妇女运动的文件(1925年)中就有出现,但到了六大的《妇女运动决议案》才成为中心议题之一。“农妇受压迫最甚,这是引导她们参加革命的基础。”[20](P16)“党的最大任务是认定农民妇女乃最积极的革命参加者,而尽量的吸收到一切农民组织中来。”[17](P163)[21](PPI85-186)。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中共领导层对工农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中作用的深刻认识,促使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成为未来共产主义革命的核心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开始面对广大的工农妇女,特别是农村妇女,重新自我定位。作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一个重要阶段,中国共产党这一时期对农村妇女以及底层劳工妇女的重新认识和构建推动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同未来中国革命实践的相互依赖关系。《决议案》讨论农村妇女运动结尾处还特别强调“在中国的[农村]环境中,组织单独的妇女协会是不适合的……如已有这种组织,应使之并入一般的组织。但当执行时,不应因此而失掉了已有的积极分子“[20](P17)。 1931年中国共产党闽赣苏维埃共和国成立,部分中共党员一方面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理论,一方面发展出了一个本土化的理论和实践平台,旨在解决中国语境里互相关联的阶级、性别和民族独立运动问题。在这初始阶段,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开始系统性地得以制度化,并被纳入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成为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步骤便是江西瑞金全国代表大会宣布了苏维埃共和国宪法,保障工人阶级人人平等和妇女的彻底解放。 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的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加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宗教,在苏维埃法律前一律平等,皆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公民。 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彻底的实行妇女解放为目的,承认婚姻自由,实行各种保护女性的办法,使妇女能够从事实上逐渐得到脱离家务束缚的物质基础,而参加全社会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生活(13)。 除了宪法保证和全新平等政治伦理的提倡,苏维埃共和国还制定了具体的法律以保障民众平等的地位和参与权。“这些法律标志着和传统的决裂,反映出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承诺和苏联的影响”;它们“直接具体地影响到了在婚姻和家庭中的妇女,[特别]是她们同土地、工厂和各种新政治机制间的关系”[22](P65)。在保证了男女都有土地分配的同等权利之外,苏维埃政府还于1931年12月11日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了女性有结婚和离婚的自由[23](PP151-154)。在首页的《条例》“决议”上,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毛泽东、项英和张国焘指出:“只有工农革命胜利,男女从经济上得到第一次解放,男女婚姻关系才随着变更而得到自由。”[23](P151)但在当时的苏区,虽然男女婚姻已取得一定自由的基础,但由于“女子刚从封建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她们的身体许多受到很大的损害(如缠足),尚未恢复,她们的经济尚未完全独立,所以关于离婚问题,应偏于保护女子,而把离婚而起的义务和责任,多交给男子负担”[23](P151)。在第五章有关离婚后男女财产的处理中,《条例》规定:“男女各得田地,财产债务各自处理,在结婚满一年,男女共同经营所增加得财产,男女评分,如有小孩则按人口评分。男女同居所负的公共债务,归男子负责结偿……离婚后,女子如未再行结婚,男子须维持其生活,或代种田地,直至再行结婚为止。”[23](P153)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从法律上将农村妇女的社会解放同她们的经济、物质独立直接联系起来,并在保护和保证妇女经济要求的前提下提倡婚姻特别是离婚自由。无疑,该《条例》在最大程度上冲击了中国农村家庭父权制和价值观念。新政府还非常明白具体落实这些新法规的重要性,因而特别强调:重要的不仅仅是制定新法,而是贯彻新法[21](P191)。在所有的党组织里都设有特定的妇女部门,另外还有本地的妇女代表大会主持妇女工作。妇女扫盲班和培训课也开办起来,主要培养妇女积极分子的领导技能,同时也为了打破传统的性别分工。这些难得的举措让一大批妇女走出了家门,投身到政治、经济活动中去[21](PP191-192)。简言之,中国共产党在1931年的政策和措施为苏区农妇运动的制度化和发展指明了方向[14](P60)。 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还针对各地农民对妇女运动的偏见和抵抗,开展了高强度的阶段性政治文化运动,加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制度化建设。江西苏区坐落在较为闭塞、落后的农村地区,在这里建立一个在政治和社会上激进超前的现代政权,面临着重大的挑战。根深蒂固的传统家庭价值观使得某些现代女性主义观念,尤其是妇女婚姻/离婚自由以及参与社会生产活动,在当地产生了格格不入的异化效果。而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不仅阻碍了应该长期进行的循序渐进的文化教育,也扰乱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政策的执行。因此,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些短期强劲的政治运动和大众动员,特别是在政治、军事不稳定的时期。大众动员自此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加强领导与政府管理的一种代表性方法,一直沿用到社会主义时期。这里笔者想强调的是,在中国的具体历史环境中,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制度化体现出鲜明的、自上而下、全体动员式的模式。虽然阶段性的运动形式有时显得不够正式和系统化,但它们在特定的条件下为传播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思想,挑战农民的传统性别观念,动员妇女入党、参政、从事生产发挥了关键作用(14)。在江西苏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体制化既采取了正式的法律形式,也采纳了种种非正式的运动教育手段,从而开创了中国妇女参与政治、经济甚至军事活动的历史先例。群众运动也直接促进了各地女性教育和女性主义文化的发展。 要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制度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之间的互相依存关系是需要特别强调的。这种彼此依存关系不只是反映了女性解放是无产阶级革命整体的一部分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更为重要的是,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的历史特定性和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笔者在上文曾指出,西方自由/本质女性主义研究一方面谴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是父权制的革命,一方面认为女性解放应该独立于中国其他政治运动,甚至是对立于这些运动。而那些批评中国共产党违背其早期“五四”时期女性主义宗旨的学者忽略了“五四”女性主义实践的历史局限和多元混杂性。当时西方的经济殖民主义和中国的落后农业经济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全面发展,中产/资产阶级难以形成和壮大,自由与个人主义价值观无法在中国大众中普及。换句话说,“五四”时期带有自由主义特点的女性主义不仅受西方经济殖民主义的束缚,也脱离了中国的国情和大众。尽管在文化领域里,个人主义女性主义具有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作用,而且这种批判贯穿了革命年代,并在革命结束之后依然起着一定的效应,但因为绝大多数的中国女性是农妇和城市劳工,这种倾向半殖民都市中/资产阶级自由权利和个体声音的女性主义实践无法在中国扩展和扎根。中国的历史现实为女性解放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和历史基础。那种一味要求中国共产党在与工农阶级联手发动推翻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时,必须坚持“五四”激进的城市资产阶级自由/个人女性主义实践的观点,不仅仅暴露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学者对中国现实和历史条件的无视或漠然,更为重要的是,这也反映了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意义和本质的无视或抵触。同样重要的是,“五四”女性主义实践具有多元混杂性,它表现了第三世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和受马克思主义思潮、苏联革命影响的女性主义。所以中国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实践也可以说是对“五四”女性主义多元思潮的一种本土化的继承,也是对世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的一种创新和突破。 其实,20世纪20年代末,在中国共产党介绍给江西民众的所有重要现代和革命理念中最让当地农民,无论男女,最难以接受的便是妇女解放(15)。虽然当时的妇女解放话语,因为考虑到农村人口和当地情况已经同“五四”激进个人主义女性主义有了区别,但因为上千年的儒家传统、凋敝的农村经济和蔽塞的地理政治社会环境,提倡女性从事社会生产并赋予她们参政议政的权利以及婚姻自由权利在当时的环境中是极端激进的,超出了本地民众的想象和接受程度。各地的反弹在江西苏维埃政府初建时就已出现[24]。后来当红军在1934年被迫撤离苏区,转战到更偏僻更保守的西北地区,这些女性主义实践——尤其是女性的结婚、离婚权——不断受到男女农民的持续抵抗。所以说,在社会主义革命转战南北期间,共产党不断调整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政策,并不是一种主动选择、让步或同男性农民达成交易,而是历史现实给出的唯一可能的途径。这种与当地民众的冲突其实更清楚地表明,性别问题和女性主义问题,完全不可能在忽视当地其他社会、政治和经济情况下进行。一味强调从20年代到40年代中国(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女性主义运动应该走“独立”和“自治”的路线,其结果只能让女性主义和当地民众更加疏远,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在中国农村的彻底失败(16)。当然,所谓独立的纯粹的女性解放本身只是一个预设的神话,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在世界任何地方落实。所以可以说在当时的历史状况和条件下,中国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成为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同1920年末以来共产主义革命的其他方面——特别是阶级斗争、民族独立革命和经济发展——相互依靠,是女性主义实践在中国环境里得以生存并持续发展的关键。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这种相互依靠关系还体现在另一层面上,这个层面同样重要和值得关注,那就是,如果中国共产党没有严格制定并努力倡导和执行女性主义政策,特别是对女性主义的各种制度化和本土化的推进,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取得最后的成功的。由于比较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理念、生产建设、道义支持、社会变革和战争援助诸方面都离不开中国的农村劳动妇女,所以在二三十年代之交,以农村为根据地的中共领导们并不是简单地把自己当做农村妇女的外来解放者。他们采取的方法是重新界定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将农夫农妇视为革命的核心力量。凯西·莱蒙·沃克(Kathy Lemons Walker)就曾指出:“妇女运动的新动向是保证中国共产党和农村人口打成一片的最重要的部分。”[14](P60)假如中国共产党没有责无旁贷地坚持开展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实践,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很难成功的。正如一名美国记者在考察40年代苏区时目睹了当地妇女的革命激情后写道:“因为他们[共产党]找到了开启这些妇女心房的钥匙,他们也便找到了战胜蒋介石的渠道。”[21](P219)阶级和性别平等构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目标、伦理和实践准则,也是构建男女工农成为革命核心主体的重要机制。20时代末到30年代初期草拟和发表的一些中共档案都一再指出中国妇女运动是“整个革命斗争不可缺少的力量”[25](PP63-64)。迫于民族危机、国民党军事进攻、各地的保守力量的反扑以及不同地区的民众状况,中国共产党在性别问题和阶级问题(17)上都做出过“妥协”或调节,但这不代表在根本原则上的让步。在具体实践中,无视中国地区环境和条件的教条主义,例如,中国共产党内部固守马克思主义的城市工人阶级斗争理论和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者,最后导致江西苏区的革命力量面临毁灭的危险[26](P82-84),才是中国阶级和性别革命的真正危险所在。 正因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依赖于农村劳动妇女和女性主义实践,这才加速了江西苏区对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制度化整合,并推动了中国共产党持续对妇女运动内部问题的反思。1931年,中国共产党对苏区的妇女运动开展了一次广泛的评估,发现大量问题都是由于当地中下层领导工作不力,对推动农村妇女运动不情不愿。根据这次评估,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新政策来改善这些情况,例如采用更有效的组织、招募方式,让女性走上当地的领导岗位[14](PP58-59)。1934年,毛泽东调查了长岗乡地区的妇女工作之后,对当地的成绩做出了批评。他的结论是政策太笼统,没有顾及女性的特殊利益。妇女教育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向工农妇女解析新政策也没提上日程。他特别强调要关照当地妇女的需求,并将她们的权益和其他政治问题挂钩:“女工农妇代表会,首先应抓紧妇女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跟着这些问题的动员,联系到一切政治的动员,在这一点上,许多地方的注意是非常不够的,就是长岗乡也缺乏充分注意。每个乡苏维埃都应该把领导女工农妇代表会的工作,放在自己的日程上。”[27](P14)[21](PP196-197)1939年2月20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发布了一项特殊的关于开展妇女工作的决定,督促党组织克服妇女工作中的问题,必须“用各种方法解释妇女大众在抗战建国及将来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坚决消灭党的一切组织与党员中对于妇女及妇女运动所存在的那种陈旧的、庸俗的及中世纪的态度的各种残余,纠正一切对于妇女工作的轻视、忽视与消极的态度”。决定还要求“立即建立与健全各级党的委员会下的妇女部与妇女运动委员会”,“动员全党女干部与女党员,起来担任妇女工作”,并“注意对于女党员的吸收及女干部的培养”[18](P346)。同年3月3日,中央妇委会也发表了指示信,指出要缩短抗战胜利和建设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业,“假使没有占人口半数的妇女积极参加,成功是不可能的”。指示信还强调:“只有加强全党对妇女工作的注意和克服党内许多党员轻视妇女工作的现象,才能把妇女工作提高到应有的地位,才能转变党内工作最薄弱的这一环。”“如果我们轻视妇女工作,实际上将拖延革命和抗战胜利的到来。”[18](P346,P350)因此在1941年解放区选举的时候,提倡妇女权利的运动也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而被认为是阶级革命的重要转折的1945年的土地改革,也直接同妇女土地和经济平等权利直接挂钩。 在回顾了中国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在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的制度化和本土化及其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互相依赖性之后,笔者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实践不可避免地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在理论层面上,国际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主要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理论,因而在不同阶段会多少受制于它的一些基本观点。第一,马克思关于女性解放观点认为,消灭了私有财产制并让妇女参与社会大生产,妇女解放和平等问题就基本解决了。可是,正如其他女性主义学者已经指出的,经济结构的转变和妇女走出传统性别分工、参加社会大生产并不一定自然而然地摧毁传统父权价值观或摒除新的男性中心话语的产生。第二,马克思理论偏重经济再生产,未系统探索妇女在人类繁衍和劳力再生产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大生产中全球性新型性别分工的产生。第三,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是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为原型的,因而对复杂的、多层次的反西方殖民的第三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指导作用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所以第三世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建构必须在本土实践中发展。 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层面上,中国落后的农业经济,大量处于文盲状态的农村人口,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不容轻视的地域差异,再加上半殖民的畸形政治经济体系,都给中国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实践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和挑战。中国共产党在执行妇女运动政策时在党内党外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阻力,导致了进程的缓慢以及持续性效果的减弱。中国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实践深刻揭示了女性主义不可能超越其历史环境,也不可能孤立存在,独立于其他的现代政治、社会、文化运动和变革。中国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实践的某些局限是历史的,也是同中国革命其他方面的历史局限相关联的。那种认为女性主义在不同历史地域场景都应该“独立”重复一个普世主题,都应该自我复制,并在世界各地产生相同的意义的观点,那种认定社会主义革命,无论其具体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如何,都应该一次性地解决所有理论上对性别问题的设想,都具有霸权色彩和盲目脱离实际的倾向。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美国学界中国妇女研究领域中一个最常见的问题便是“社会主义[能够]解放妇女吗?”[22](P62)这一问题本身传达了一种对女性解放一统性的理解,认为女性解放可以一蹴而就,似乎在完成与未完成之间能划上一条清楚的界限。这种观点忽略了特定的历史过程、具体的地缘政治环境和国际政治,以及“解放”这个概念在不同历史时刻的不同历史意义。通过给“社会主义”“解放”和“妇女”这些概念预定一个普世、一统的、绝对的并且是抽象的含义,“社会主义[能够]解放妇女吗?”这个问题在不经意间,自然而然地就变成了斯泰西在其1983年出版的著作里开篇提出的问题:“为什么社会主义没有解放中国女性?” 总之,只有进一步考察女性主义制度化在不同历史语境里的根基和发展过程,才能让我们将女性主义同切实环境联系起来,更好地理解不同女性主义实践的不同的政治和经济构成,从而也更合理地评价它们的贡献和局限。中国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实践源于“五四”多元女性主义文化实践,在1920年中国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发展成体制化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主流实践。性别在中国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实践中绝不是孤立或“独立”的力量,而是同社会主义革命其他政治、社会和经济议程直接相关、相互依赖的,因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主体性具有多重维度。最后,中国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和其他第三世界女性主义一样,具有明显的民族主义特点。中国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实践的这些核心特征直接质疑了西方自由/本质女性主义普世化的假设,为跨国女性主义理论和多样政治经济场景中发展出来的女性主义实践提供了一个另类模式。 注释: ①例如以下这些研究著述对扩展、丰富以前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性别的学术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Gilmartin,Christina K..Engender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Radical Women,Communist Politics,and Mass Movements in the 1920s[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 Saich,Tony.Introduction[A].in 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Documents and Analysis[C].ed.Tony Saich,Armonk,N.Y.:M.E.Sharpe,1996:xxxix-lxix.; Diamant,Neil J..Re-Examining the Impact of the 1950 Marriage Law:State Improvisation,Local Initiative and Rural Family Change[J].The China Quarterly,2000,(161):171-198; Diamant,Nell J..Revolutionizing the Family:Politics,Love,and Divorce in Urban and Rural China,1949-1968[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 Dooling,Amy.Women's Literary Feminis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M].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5; Chen,Tina Mai.Female Icons,Feminist Iconography? Socialist Rhetoric and Women's Agency in 1950s China[J].Gender and History,2003,15(2):268-295; Chen,Tina Mai.Socialism,Aestheticized Bodies and International Circuits of Gender.Soviet Female Film Star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949-1969[J].Journal of the Canadi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Online),2007,18(2):53-80; Yan,Haiping.Chinese Women Writers and the Feminist Imagination,1905-1948[M].New York:Routledge,2006; Zhong,Xueping.Women Can Hold up Half the Sky[A].in Words and Their Stories:Essays on the Language of Chinese Revolution[C].ed.Wang Ban.Leiden:Brill,2010:227-248; Wang,Zheng.Creating a Socialist Feminist Cultural Front:Women of China(1949-1966)[J].The China Quarterly,2010,(204):827-849; Wang,Lingzhen.Socialist Cinema and Female Authorship:Overdetermination and Subjective Revisions in Dong Kena's Small Grass Grows on the Kunlun Mountain(1962)[J].in Chinese Women's Cinema:Transnational Contexts[C].ed.Lingzhen Wang,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1:47-65. ②当然也有例外,但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的对学术界有持续影响的著作都受制于并进一步强化了当时的冷战意识形态。 ③中国现代女性的个体能动性,尤其是她们在政治、社会、文化运动中的积极参与,成为过去20年出版的一批学术成果中的重要主题。见Gilmartin,Christina K..Engender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Radical Women,Communist Politics,and Mass Movements in the 1920s[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 Wang,Zheng.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Oral and Textual Histories[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 Dooling,Amy.Women's Literary Feminis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M].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5; Hershatter,Gail.The Gender of Memory:Rural Women and China's Collective Past[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1. ④虽然后来的学术论述对80年代有关中国女性与社会主义研究做过不同层次的修改,但其背后的冷战思维和自由/本质女性主义基础框架依然坚固并影响深入。典型的例子见Evans,Harriet.The Language of Liberation:Gender and Jiefang in Early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iscourse[J].Intersections:Gender,History and Culture in the Asian Context,1998,(1)(online journal). ⑤这个问题才是斯泰西开展其整个研究项目的驱动力,虽然她也提出了另外几个关于家庭转型和社会转变的问题。 ⑥20世纪80年代,大量评价都用“新颖”这个词来描述此书的视角和分析。见此书封皮背面的宣传。 ⑦历史学家凯·安·约翰逊就是一个较典型的例子。在她的书中,约翰逊对现代中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分析和描述是比较具体和有层次的,但最终她还是舍弃了自己的田野研究材料,“硬性”做出了如下同她自己的分析并不十分吻合的结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是父权制的革命。这种历史素材和作者结论间的矛盾,也从侧面揭示了冷战范式对学术论述的巨大影响。见Johnson,Kay Ann.Women,the Family 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China[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3; Diamond,Norma.Review of Women,the Family 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China by Kay Ann Johnson[J].The China Quarterly,1985,(103):530-531. ⑧“Radical Feminism”在国内一般翻译为“激进女性主义”或“激进女权主义”,但Radical Feminism同政治或行动上的“激进”并没有直接关系,它反而是美国以及总体西方女性主义在70年代开始转向保守、转向文化领域的开端。“Radical Feminism”中的“radical”是拉丁语“root”(根)的意思,这里用作形容词,表示触及性别不平等的“根本”和“本质”原因的女性主义。Radical Feminism的几个主旨是:(1)性别不平等是历史上一切不平等的起源;(2)父权制和男尊女卑是超/跨历史阶段并普世存在的现象,不会因为历史上阶级矛盾问题的解决而消失;(3)男女性差异是性别不平等的原因;现存社会是彻底的男性社会,所以女性主义运动需要独立自治,不能同其他运动混合;(4)整个社会体系需要革命化的变革,但一切要从私人空间(家庭)和(女性)“意识提高”(counsciousness raising)活动开始。我将Radical Feminism翻译成“本质女性主义”的三个主要原因是:(1)Radical Feminism的词源本身强调的是根本与本质的问题;(2)它的实践今天看来可以断定为文化本质主义——认为父权制自古就有,亘古不变,而且普世皆同。没有差异;(3)正是这样的Radical Feminism促进并发展了后来的文化女性主义——提倡女性特质的文化,以及“女性本质主义”——性差异是一切本源。换句话说,虽然“Radical Feminism”从未简单声称生理决定论(biological determinism),但它对父权制所作的具有普世性、超历史性的定义,对性别不平等完全起源于性差异的看法,以及它对女性受到的身体和性压迫的强调,又使它同本质主义(essentialism)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质女性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有一定积极意义,可以因为它与批判资本主义体系的左翼女性主义分道扬镳,所以它在以后的发展中有意无意地转变为在维持资本主义体制的基础上提倡女性主义意识和文化,与西方主流自由女性主义殊途同归——都在资本主义体系内寻求生存和发展。 ⑨关于本质女性主义的详细讨论,请参阅Willis,Ellen.Radical Feminist and Feminist Radicalism[J].Social Text,1984,(9/10):91-118。 ⑩这种结合西方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的冷战、自由女性主义研究方式对当代中国女导演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 (11)在民国时代,自由女性主义在部分程度上被国民政府法律化(不同于多方位的机制化),但其实践却深度受制于资本主义和中产阶级在现代中国的有限发展、国民党内的保守力量以及它自身同中国大多数农村和工人阶级人口间的割裂。 (12)李大钊、陈独秀、陈望道和其他人在“五四”时代开始引介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观。见李静之:《中国妇女运动研究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13)《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931年11月7日)前言和第十一条。 (14)根据Kathy Lemons Walker的说法,有三种主要因素使得当时的妇女运动取得重要成效:不断增强的政党(共产党)支持,为调动女性积极性而新制定的方法和组织形式,以及战争动员。见Walker,Kathy LeMons.The Party and Peasant Women[A].in Chinese Communists and Rural Society,1927-1934[C].eds..Philip Huang,et.al..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61. (15)关于在中国农民中发动一场持续的、成功的现代无产阶级革命的艰难程度,见Saich,Tony.Introduction[A].in 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Documents and Analysis[C].ed.Tony Saich,Armonk,N.Y.:M.E.Sharpe,1996:1-liv. (16)把结婚和离婚当成妇女解放的重心,这样的做法在江西苏维埃时期招致了当地农民农妇的强烈反对。见汤水清:《乡村妇女在苏维埃革命中的差异性选择——以中央苏区为中心的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11期,第85-94页。 (17)中国共产党在江西苏维埃时期出于对经济发展的考虑,抗战以后为了建立统一战线的需要,不止一次地在阶级政策上妥协,包括同地方城乡精英阶层的关系。见Moise,Edwin E..Modern China:A History(3rd edition)[M].New York and London:Longman,2008:80-82; Saich,Tony.Introduction[A].in 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Documents and Analysis[C].ed.Tony Saich,Armonk,N.Y.:M.E.Sharpe,1996:xivi-liv.标签:女性主义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美国革命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政治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性别文化论文; 社会主义阵营论文; 社会思潮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世界现代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