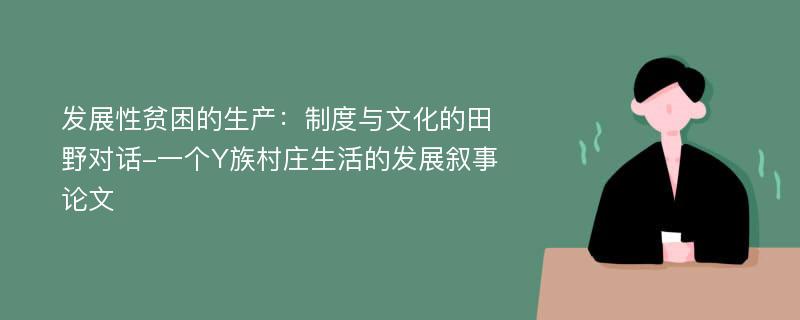
发展性贫困的生产:制度与文化的田野对话*
—— 一个Y族村庄生活的发展叙事
□李小云,吴一凡,董 强,宋海燕
[摘 要] 研究将Y 村的贫困定义为发展性贫困。与生存性贫困不同的是,发展性贫困的致贫原因一方面深深地嵌入在发展的制度中,另一方面又与群体是否具有适合发展的现代性的伦理相互联系。认为现代意义的贫困生产是在不利于贫困群体的发展制度和贫困群体现代性伦理缺失的相互作用下发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过程。
[关键词] 贫困;进取模式;发展制度;发展综合征;社会文化实践
一、问题的提出
贫困问题是一个古老的话题。自中世纪以来,贫困问题就是神学家、政治家、公务员、学者、纳税人和人道主义者关注的重要问题。[1](P16)有关贫困原因的理论主要有三个不同的流派。第一种观点认为是穷人的特定属性导致了他们的贫困,[2]有研究指出,懒惰、缺乏道德操守、受教育水平低、缺乏技能等个人因素导致了贫困,[3](P92)这一观点总的来说是将贫困归咎于个体的失败。[4](P101)19世纪美国作家阿尔杰(Horatio Algerde)的小说描述了数百个由贫穷到富裕的故事,主人翁无论开始多么贫困到最后几乎都依靠他们内生动力和不懈的努力摆脱了贫困,这些故事的核心含义是一个人的命运主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就是至今都在影响着社会大众观念的所谓“决定收入的进取模式(achievement model of income determination)”。[5](P1)长期以来,这一模式也影响了无论是着眼于一个国家、还是一个群体或个体贫困问题的研究。美国经济学家索洛(Robert Solow)对于个人努力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系统论述[6]以及社会经济学家格伦·路易(Glenn Loury)对于收入的代际转移与分配的研究[7]算是受到这一模式影响而形成的经典的贫困理论研究。经济学家们通常认为自由竞争在自由民主制度的条件下能够支持相似的个体和群体的经济状况逐步趋同。有一些证据支持这一理论,例如,根据国际要素均衡理论,在一定条件下,自由贸易可以平等化贸易伙伴间的工资率。然而,即使在所谓的相似条件下,贫困仍然普遍地、长久地存在于全球范围、一个国家、甚至一个社区中,这实际上已经挑战了进取模式对于贫困的解释。
第二种观点认为贫困的环境产生贫困的文化,而陷入贫困文化的群体则无法摆脱贫困。刘易斯(Oscar Lewis)的《贫困文化:墨西哥五个家庭实录》、班费尔德(Edward C.Banfield)的《一个落后社会的伦理基础》、哈瑞顿(Michael Harrington)的《另类美国》,通过来自墨西哥、意大利和美国等不同社会的经验资料,共同构筑起贫困文化的概念架构。[8]刘易斯在他题为《贫困文化》一文中指出:“贫困文化一旦形成,就必然倾向于永恒。棚户区的孩子,到6~7岁时,通常已经吸收贫困亚文化的基本态度和价值观念。因此,他们在心理上,不准备接受那些可能改变他们生活的种种变迁的条件或改善的机会”。[9]刘易斯的贫困文化理论实际上也是美国主流的个体失败导致贫困理论的某种翻版,尽管刘易斯更多地强调了贫困的群体性,隐含了个体无法通过自身努力摆脱亚文化条件下贫困的立论,这一观点其后被发展成为所谓的贫困文化陷阱的理论。国内很多学者采用这一观点研究中国,[10](P52~60)特别是中国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他们简单地将少数民族的贫困看成是这些群体的所谓贫困文化,[11]也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是对贫困文化的误用与滥用。[12]
第三个观点认为贫困是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层面结构性的问题。这里讲的结构主要是指基本的社会制度,如私有制以及一系列的社会经济政策。卢梭认为私有制是人类不平等的根源。[13](P67~68)马克思更是系统地论述了资本主义条件下贫困的根源。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方式下,生产资料所有者能够通过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使工人贫困化。随着资本的增长,工人阶级的贫困会进一步加剧,因为“资本增长得愈迅速,工人阶级的就业手段即生活资料就相对地缩减得愈厉害”。[14](P380)马克·兰克(Mark Rank)是当代美国著名的贫困问题专家,与相信美国的贫困主要是个人懒惰不进取的主流观点不同的是,他系统的实证研究表明经济体制和社会政策是导致美国贫困的重要结构性要素。他认为美国的经济结构无法为所有参与者提供足够的机会,这是造成美国贫困的重要原因,[15](P53~65)其次,美国的社会政策在帮助穷人方面也是失败的。[16]这一点与阿莱斯娜(Alberto Alesina)等对美国的研究相一致。阿莱斯娜等的研究深刻地揭示了美国的贫困与政治制度的关系。[17](P77~94)
在学生学习阶段,不论在哪个岗位,都要按照双方共同制定的人才培养方案,在该上课时都要到指定地点完成相应的理论学习、实践操作任务。在学习形式,上课时间上更灵活些。比如连续几天下雨,就以理论讲授为主;每周的前几天打球客人少,以上课为主,后几天打球客人多,学生就回到各自的岗位上。
在过去十多年中,经济学家们将上述的理论进一步具体化,从微观的角度提出了解释贫困顽固存在的三个方面理论观点。第一个理论观点认为能否越过贫困可能取决于能否越过某种所谓的关键的门槛(critical thresholds),也就是说如果个人财富和人力资本达不到这个关键点,任何个人的努力都无法帮助其越过贫困陷阱;[18]第二个理论认为由于所谓的制度失灵(dysfunctional institutions)导致了国家和群体或个体努力进取的失败,也就是说无论任何努力,由于某种制度方面的原因都无法突破贫困陷阱;[19]第三是由于所谓的“邻里效应(neighborhood effect)”,主要是指个体和其所在的群体之间的互动影响了群体的进取努力,导致群体陷入贫困陷阱。[20]有文献对此进行了系统性的回顾,[21]也有研究指出,不同的社区环境及社交阶层会持续影响几代人的收入造成持续性的不平等。[22]
Y 村民小组(以下简称“Y 村”)位于西南某省的一个国家级贫困县,被确认为国家级贫困村。① 据村里老党员回忆,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其他村子还尚未解决温饱问题时,Y 村已经基本解决了,还自办村小、开展夜校扫除文盲等,因此,当时村民认为自己属于“先进村”。2000年以后,村民逐渐感觉和其他村开始有了差距,“比其他村穷”,但是直到2015年,对于Y 村属于贫困村这一情况村民才有所知晓。 Y 村于1982年由山里旧址搬迁到现居住地,地处热带雨林自然保护区内,平均海拔在800米左右,年平均气温为20℃,年均降雨量在1 600~1 780毫米之间。② 根据2015年当地县志查询得知。 全村常住人口57户共206人,其中劳动力有138人,除2位上门女婿为汉族外,其余皆为Y 族。Y 村现有土地782.3亩,其中水田145.7亩,旱地636.6亩,橡胶林地2 800亩左右(其中半数与某橡胶开发公司存在橡胶开发争议)。人均水田地0.67亩,人均旱地2.95亩。① 本文数据除特定说明外,关于Y 村的各项数据均来源于2015年课题组成员在Y 村展开的调查数据。 农户主要以种养业为生,种植水稻、玉米、甘蔗及砂仁,养殖冬瓜猪等。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甘蔗种植、砂仁采摘、外出打工及国家转移性补贴。② 国家转移性补贴在2015年主要是退耕还林款和农业综合直补,直到2018年才开始有边民补助等。
这种潜移默化的规范和引导,营造了良好的励志教育的校园环境。思政工作者要善于抓住学生课余、自习时间,对学生可能存在的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艰苦奋斗精神弱化、社会责任感缺乏的现象进行分析与解决,为励志教育增添光彩。通过对典型人物或先进事迹的宣传,增强学生的竞争意识,带动学生“学比赶帮超”的热情,通过榜样的力量促使学生的道德观、价值观、人生观得到提升。励志成才,燃起学生心中希望之火;树立榜样,让学生朝着目标果敢前行。
从研究的方法上说,该项工作可能会陷入莫斯(David Mosse)所提出“参与者—内部人”的方法伦理尴尬中,因为它是在一项以政府、村民等多方合作开展的项目为基础上所进行的理论思考,这种研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对贫困做的各项指标或者其他不同维度调查,也不同于以参与式方法做田野志的人类学研究,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所处的身份可能会模糊了社会调查和自身经历的界限,但正如莫斯同时也指出那样,这样的研究具备真正意义的“真实性”,是“内部人的民族志”或者“自我民族志”。[23](P19~24)事实上,在研究过程中村民对作者几乎知无不言,讲述各种从个体意识出发的细枝末节,但作者仍须遵循社会科学基本的研究伦理。作为Y 村发展的“内部人”的优势虽然能使我们更清楚地展示乡村的政治社会关系,但也不得不承认,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身为研究者的客观性。
[46]《明英宗实录》(台北1962年影印本)卷二二四,《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卷一六二,倪敬传。
二、Y村:一个没有富人村庄
本文是针对西南某地一个Y 族贫困山村贫困状况的观察。Y 村作为一个长期处于封闭的贫困村落,发生在其中的村落日常生活以及作者在Y 村的扶贫实践为作者提供了探究贫困原因理想的案例,更为重要的是,Y 村典型的亚文化社会特点也为我们更好地理解贫困的文化问题提供了典范的素材。本文不是针对贫困的理论论述,而主要希望能从Y 村村民日常生活的社会实践中观察涉及贫困的相关问题,特别是希望能通过村民的日常生活叙事与现有的贫困理论展开对话,在微观层面展示贫困的根源和摆脱贫困的实践路径。
初到Y 村的第一印象就是村里没有一栋砖混房,全村都是没有窗户的破旧木房。进村的唯一通道是8公里曲折的土路,开车要40分钟,雨季来临时就无法通车。经调查得知,村民自旧址搬迁到现居住地以来,普遍缺乏固定资产,以住房为核心的固定资产折旧严重,没有一间符合安全标准的住房。2015年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4 303元。根据全村可支配收入的数据选择F统计量,使用SPSS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在给出显著性水平α=0.05的条件下,计算检验统计量的观测值和概率P值。得出结论:不同人口数量的农户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均值无显著差异,这意味着家庭人口数量的不同没有对人均可支配收入产生显著影响,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存在显著差异,说明村庄呈现集体性的低收入状态。
过年吃杀猪饭是Y 村一年中重要的仪式。每家的猪都是大家一起处理,做成杀猪饭一起吃。过年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挨家挨户去杀猪、吃杀猪饭,每户杀了猪之后,除留下猪油和少量的肉外,基本都吃完了。村民很少考虑把冬瓜猪做成腊肉等去卖,养冬瓜猪主要是为了自己吃。这几年努力发展冬瓜猪商品化一直没有太大的进展。外面的人一进村就说:“你们太懒,养一头也是养,养两头也是养,为啥不多养一些?这样好的猪肉能卖大价钱的,你们不做。”这就像村民过去种的旱谷,品质特好,但是很难市场化、规模化。Y 村的猪就如同过去的旱谷一样,对于村民来说是生存性的生产,无论是作物的品种还是村民的技能都无法适应市场的需要。事实上,扶贫项目带到村里的小猪,后来大部分都没有成活,村里贫困户H 姐说:“发了6头小猪,一个月全死了呀!”和她类似的是,其他贫困户里得到的猪也大都没有成活。Y 村农民的生产是基于生存伦理的社会文化实践。这种社会文化实践是嵌于农民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之中的,对于共同体的生活来说尤其重要。[36](P114~115)但这种实践形态与基于市场竞争的发展伦理完全不同,农民一旦被卷入市场竞争中,就将会面临风险。[37]
2015年之前村里确定贫困户的名额,很多人都不愿意参加,2016年重新核查建档立卡户发现,贫困户都是村干部,因为当初大家都不愿意当贫困户,所以干部带头了。现在需要按照上面下达的名额重新确定。因为大家知道这次贫困户是有好处的,所以都争当贫困户。在开会确定谁是贫困户时,Y 姐站在门口说:“这个村谁是富裕户?谁是贫困户?大家都一样。”参会的人都沉默着,同意Y 姐的意见。Y 村这么多年有人出去跑,但是没有一个人致富。L叔说:“除了两户有辆破的没有牌照的卡车外,全村没有一辆汽车,别的村都有很多汽车的。”
2015年Y 村人均消费支出为5 098元,主要流向教育、医疗、烟酒以及购置摩托车等消费方面,超出同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近20个百分点。在低收入的条件下,现代消费文化不断推高Y 村农户的实际支出,致使相当多的农户依靠债务维持消费,到2015年人均累积债务为3 049元。现代性的福利要素如教育、医疗等又继续构成农户的刚性支出内容,加之农户传统的支出,使得农户陷入了“三重性”(低收入、高支出、高债务)下的贫困陷阱。假定按照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高增长点9%来计算,并同时假定农户支出维持在2015年的水平,那么农户只有到2021年才能还清债务,一旦生病、教育产生额外的支出,农户还会加重债务。对于Y 村农户来讲,改善福利的优先选项是住房,而建一套安全住房至少需要10万,这意味着,即使按照9%的可支配收入高增长值,在支出不变的情况下,要建起这样一栋房也是遥遥无期的。事实上,2016年之前,Y 村没有一户建过新房,建一栋新房是Y 村每一户的梦想。
Y 村不是没有想致富的人。村里说D 哥两兄弟就能折腾。D 大哥前些年在外面跑,和人一起去老挝做药材生意,弄了点钱,后来租地种甘蔗遭到大象破坏,损失近百万,村里人说他“首富变‘首负’”。D 家小兄弟也是搞到了点钱,加上从其他亲戚那里借的钱,开始做起了砂仁生意,结果赶上砂仁价格下降,囤了一堆的砂仁果在家里,卖会亏本,不卖又欠着人家的债,两头为难。与内地乡村甚至与山下的村子不同的是,Y 村的社会分化程度很低,呈现出集体性的贫困状态。Y 村的人每天都在忙着,早上六点出去就找猪食喂猪、砍甘蔗等等,有时甚至还会半夜去割胶。Y 村人常常说“找钱太难,不会找”,习惯将他们挣来的钱称之为“苦来的”。这一地方化的表达事实上非常准确的描述了他们的状态,对于他们来说,挣钱是一件很难的事,需要花精力去“找”,从别人不屑于去干的工种中寻求一份工,即使是能“找到钱”,也是要通过比寻常人付出更辛苦的劳动来换取低廉的报酬的。Y 村的境遇既是普遍的,也是特殊的,在西南地区的山区有很多和Y 村相似的村庄,属于所谓的深度贫困村。[24]
综上而述的是一个现代化发展语境下的Y 村。但同时,Y 村也是一个没有饥饿、依靠农作物和雨林天然的赏赐就能生活的村庄,村民们在盖房、农忙等时节相互帮工,平日有了困难也会相互借钱。L 叔回忆:“我们Y 族过去也是很苦的,但是我们在山里种的旱谷好吃,有冬瓜猪肉,还可以在林子里找很多吃的,现在不行了,现在没有钱,什么都没有。”问起村民们对今后生活最大的担忧,都是说不知道去哪里找钱。没有钱的影响是广泛和深远的,没有钱就盖不起房子,无法获取教育和医疗服务,话费交不起,摩托车也没钱加油无法出村,甚至讨不到老婆。在受到现代化的影响下的Y 村,没有钱人们寸步难行、无从发展。两种不同的叙事展示了类似Y 村这样的少数民族在发展中面临的困境。从食物和居住等基本需求的角度讲,贫困有其客观性和绝对性,如果一个群体处于饥饿和没有基本居住等条件之下,我们可以将这样的群体称之为贫困群体,这就是所谓的生存性贫困。但是,很显然Y 村不属于这一类。如果说Y 村是一个深度性贫困村的话,更严格地说,它其实是一个发展性的深度贫困村庄。
三、贫困:发展制度的嵌入物
Y 村2015年日常支出占总开支高达41%,而生产经营投入仅占20%,凸显了Y 村文化结构与现代市场经济伦理的张力。在日常支出结构中,烟酒花费占比最大,为25%。Y 村村民偏好喝酒,几乎天天都喝酒,大家坐在一起吃饭,往往饭菜没吃下去几口,酒就已经一杯尽了,D 哥说:“酒就是粮食,喝了明天就有力气干活,醉了更好,什么烦恼都没了。”喝酒高兴了大家就一起喊“丢,丢,丢丢丢丢”① 这是Y 村的敬酒令。 ,洪亮的喝酒声在这个山村里回响,祛除了村民的疲劳,召唤着村落的生命力。Y 村几乎每家每户的男性都抽烟,尤其是青壮年,至少每天消耗一包烟,尤其是碰到盖房和农忙时节,村里人常常聚在一起干劳动,消耗较平常会更多。他们通常购买一包烟的价格为8~11元不等,保守估计一个男性每年买烟花费在3 000元以上。问村民能不能少抽点烟,他们几乎都会说:“不行啊,我们累了烦了就要抽烟啊,是放松和休息啊。”年轻的小Z说得文艺一些,“烟是寂寞,酒是快乐”,坦诚烟酒对于他们确实是很重要的慰藉方式。但因为烟酒的支出占到了家庭收入很大的一个部分,所以作者经常与村民讨论能否少抽。天冷的季节到了晚上每家都会围着烤火,大家坐在一起聊天,老人还是会抽旱烟,年轻人都抽买的烟,说一句话吐出一团云雾,混着柴火的烟气,恍惚中人们的疲劳和烦恼好似都散掉了。作者也常常晚上与农民坐在一起烤火聊天,不自觉受到影响,烟也会抽得越来越多。有一些外来的人总是很鄙视地说:“他们就知道抽烟喝酒,活该穷!”然而Y 村也有不近烟酒的人,日子却并未因此好过多少。P哥因为患病戒掉了烟酒,但他也发现“朋友们慢慢就不叫我一起玩了”。Y 村近90%的年轻人承认自己开始抽烟喝酒的年龄早于16岁,并且几乎都是被其他人带着开始抽烟喝酒的。当然也有例外,有一家的两兄弟从小随妈妈改嫁过来,不敢像其他小孩一样找家里要钱,因此从未沾染上抽烟喝酒的习惯,“我们知道抽别人的烟喝别人的酒都是要还回去的,所以我们就不弄”,但村里人少不了议论他俩,说“他们两兄弟最抠,从来不叫我们去吃饭,也不递烟”。戒掉烟酒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被群体排斥。因此,当外界用鄙夷的口气去评判他们抽烟喝酒的文化时,应当注意到这种文化对于Y 村重要的社会内涵,事实上,试图以牺牲抽烟喝酒所带来的感受以及烟酒对于他们的社会文化意义来换取存钱或者投资都是很苦难的。
根据2015年的调查数据,Y 村共有30户有非农就业的收入,主要包括工资性收入、长期外出务工收入和周边短期零工收入。截至2015年,Y 村高中毕业的年轻人只有4人,只有他们才可能外出务工。小Z是高中毕业,2015年他在广东务工10个月,月薪从2 400涨到3 500元,除去在外基本开销,他固定每个月往家里寄2 000元贴补家用。但是,Y 村像他这样能出去打工的人很少。村民说,外出打工要有文化,要会说普通话,普通话都说不好,去外面打工人家不要。村里15~25岁群体平均受教育年限最高,为7.3年,其次是26~36岁群体,平均受教育年限为4.1年,这意味着村里的年轻人多数都未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学历仅相当于小学高年级水平。受此限制,Y 村村民平时只能下山打点零工,多从事建筑、收获香蕉、收获蔬菜等体力工作,每个小时工作10~20元,每天50~100元不等。经常外出打工的P哥说:“我们在外边打工都是别人不干的事,累得像个猪,一天干得太累,就这样一年也最多打两个月。”Y 村村民的非农业就业在劳动力市场处于最低端,几乎没有任何技术含量。他们到山下给D 族村子的农民收获冬季蔬菜,很多D 族的农民把地租出去给外地人种香蕉,Y 村的给这些外地人打工。村里人说D 族村,“他们有田,有学校,有公路,医院就在村旁边,领导都是他们D 族的人啊”。一方面,Y 村的农民由于文化水平低和语言不通无法进入远距离的就业市场,同时,就近又只能在产业链的低端打工,收入十分有限。D 族村的人说“他们Y 族人太懒,这里有活,他们也不愿意干”,而Y 村的人说“干一天从早到晚,才有80~100块,干得太累,别的事都干不了,累坏了,生病花的钱很多”。Y 村的村民虽然文化不高,但是他们也算账。市场经济的机制看似对每个人是公平的,但是对于处于贫困状态的穷人来说则很难在就业市场中真正受益。不同群体利用市场规则凭借其特有的资源相互竞争,看起来公平,而在“强—弱”的结构关系中,强者垄断了机会和利益,实际上处于不同的起跑线上。[29]马克·兰克对于美国的研究证明很多处于下层的穷人,由于他们的一些特点导致他们在就业市场处于极度不利的地位。[16]国内的一些研究也从不同角度说明了就业市场少数民族群里所处的不利地位。[30]在现代化或者发展的语境之下,改善福利的路径是具有条件性的,这种条件性使得这些少数民族群体在就业市场中受到挤压。[31]
Y 村一直以来民风朴实,但算不上“遵纪守法”。据作者这四年的观察,Y 村坐过牢的至少有6人,主要因为盗猎和砍伐。Y 村地处自然保护区内,村民长久以来养成了靠山吃山的习惯。P大哥和帮忙运输的小W 就曾因为砍树被抓获,分别处以30 000元和8 000元的罚款。P大哥想不通,“以前我们Y 族都是这样的啊,怎么到我这儿就不行了呢,没有木头我们靠什么呢”?P大哥被关进去有大半年的时间,他的媳妇不仅要缴纳罚款,还要花钱继续盖房,只身前往景洪打工却被骗至缅甸大山里给工人做饭,过了两个月才回来,只挣了4 000元,人瘦了一大圈,“我是真的压力很大,老乖(老公)指望不上,小孩还要上学,房子也停不得”。小W 更委屈,“我就是帮堂哥运个木头,也不是我砍的”。但P大哥一家自顾不暇,8 000元罚款只好由小W 自己出了。村里人更想不通的是,有一户因为使用了一株被雷劈倒的大树而被罚款5 000元。Y 族过去有狩猎的习惯,捕猎野味是一种男性力量的象征,村里人因为打猎被处罚金的有3位以上。这些年来,随着森林公安和林业部门的宣传,Y 村村民逐渐有所改观。但是,另外一些形式的处罚却并未消失。村里人出行基本靠摩托车,但除了有2辆摩托车上了牌照以外,其他均为无照黑车,村民购置摩托车除了在山上干农活以外,也接送小孩、去附近打零工,但是经常会有交警大队开展交通整治行动,村里有3人曾因不挂牌、无证驾驶被扣车拘留过,交了2 000块钱才取回摩托车。摩托车作为村民生活的必需品,几乎算是家庭中最大的资产购置了,一辆7 000元左右的摩托车,村民往往只能付得起两三千,剩下的都是向老板赊账,什么时候有钱了什么时候再还。在这样的条件下,认为村民能够花钱花精力到县里考一个摩托车驾驶证、给摩托车挂号牌,实在是一件不切实际的事情。
2015年Y 村医疗户均支出4 233元,占农户家庭总支出比例为17%。一旦家中有人患有严重疾病,则会对家庭产生极重的负担。2015年,Y 村新农合参保人数为120人,参合率仅为58%,农户一般只给家中身体不好的成员支付新农合参保费用。Y 村医疗费用最高的是P哥,2015年他共花了24 000元用于治病,他患有严重的胃病,需要长期服药,且药费不在医保范围内。另外他的母亲和弟弟分别患有严重的妇科病及皮肤病,同年医疗支出分别为10 000元和4 000元。三人合计治疗疾病费用为38 000元,全家人当年入不敷出,只能消耗往年积蓄及向外借债度日。有研究对贫困地区农民合作医疗支付能力进行考察,认为贫困人群的客观支付能力欠缺。[33]另外,现行医疗保障体系并非针对贫困人群设计,其模式无法达到防贫目的,还是会对贫困人群的经济产生较大消耗。[34]
Y 村农户收入不高,还常常面临各种制度的约束,支出也日益增加。小孩教育支出在家庭支出的比例很高。村民平时最受困惑的就是教育的支出,因为每周都得给孩子钱,A 哥说:“天天问爸妈要,就算每次没给多少钱,算算下来也是不少钱。”2015年Y 村共有28户农户家庭需要支付教育费用,平均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百分比为19.4%。在教育支出最多的10户农户中,只有两户农户家庭纯收入(扣除生产性支出)减去教育费用还有结余。其余8户农户家庭教育对收入的消解作用相当明显,有5户当年需要依靠往年存款或者借款度日,另有3户减去后所剩无几。
为了检验和督促学生进行有效的在线学习,教师可以利用网络教学平台发布作业任务及通知公告,也通过QQ群或者微信等网络聊天工具进行在线答疑、开展小组讨论等活动,此外还要根据教学需要建立试题库供学生练习测试。学生登录网络自主学习平台的次数及在线测试成绩纳入平时成绩的评定之中。由于在线测试具有提交成绩之后马上自动给出测试成绩的特点,既可以激发学生的网络自主学习能力,同时也可以缓解大班教学模式下教师批改测试题阅卷的压力。
Y 村相比于周边其他村子确实穷了一些,很少有女性愿意嫁进来,因此村里男性不得不去老挝寻找合适的女性。在Y 村一共有8户中老通婚家庭,其中只有5户办了结婚证。但无论办不办结婚证,Y 村的老挝女性都很难享受到各种政策待遇。虽然地方的政府也在想尽办法为这些家庭解决问题,但是由于受到政策的限制,根本性的问题解决不了。本来娶老挝媳妇的家庭就经济条件不好的,组建家庭之后,不但支持性的补助没有变多,其他的花费反而增加了,家庭就陷入更加贫困的状态。有研究指出,跨境婚姻家庭持续发展能力较弱,在教育、医疗等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进口贫困”导致家庭经济功能更加脆弱。[32]
Y 村的村民都想致富,但是他们的日常社会实践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个人的致富努力。作为一个封闭的山地村落以及相互连亲的大的亲属团体,福利分享和平均主义是村庄生存的伦理。正如安德森(Andersson Elina)在肯尼亚和乌干达的调研发现,农户必须团结起来以应对食物短缺和生存风险,[35]因此分享、互助、平均主义是互动中的关键词。相互帮工是Y 村普遍性的社会实践,无论盖房还是收获甘蔗都是帮工完成,帮工的日子里,主人家需要杀猪、杀鸡,每天要管饭和酒,还要备烟,花销不少。在Y 村发展客房项目以来,村民陆陆续续都要盖房,作者曾经建议村民互相免去管饭这一形式,大家都能省钱。但村民都不同意,“每天都得去山里抬木头,不吃肉不喝酒我们没力气呀,反正穷也不是穷我们这一顿饭”。尽管大家都缺钱,但没有一户接受这个提议,因为没有人可以仅依靠个人的力量把房子建好。就像老话说的那样,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在Y 村,虽然大家都比较穷,但相互借钱非常普遍,而且没有利息,村民说都是村里人,有的还是亲戚,哪好意思要利息。村里人都了解彼此的经济状况,谁家甘蔗卖了多少钱,谁家小孩上学花了多少钱,都是一笔明白账。如果有钱不借给别人是要受到指责的,而且如果那样做,日后他/她家有事大家也不会帮他/她,基于这种群体压力及集体认同,村里人甚至会从银行或者信用社贷款,借款给需要用钱的村民。M 就曾提到他曾经于2013年向银行贷款17 000元用于帮助他兄弟建房。山下有零活需要人,村里人得到消息了都是告诉大家尽量一起去。外面有打工的机会,村里人都是让大家一起去做。D 哥说“只要我知道哪里需要打工,都会告诉村里的人,看谁愿意去”,问他不怕别人抢了他的机会,他说不怕,反正都是大家挣啊。不能说Y 村的人都事事为别人考虑,当在Y 村发展客房项目以后,关于谁家先安排客人住这一问题还是有闲话的。很多专家都说在村里发展客房,将来谁住谁不住很麻烦,没法做到一碗水端平。但是在实践中发现村民非常遵守约定的规矩,很少发生大的争议。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村庄的平均主义传统。Y 村的村民也会存钱,但是他们的收入很低,日常开支很大,客观上存不了钱。但是不能否认的是,缺乏储蓄也是他们的习惯。Y 哥说:“今年(2018年),我还是挣了不少钱,有两万多,但是一点都没存啊,都花了,到处都需要用钱啊,再说了,存钱干什么呢?”为了让村民投资客房,我们不得不先把客房收入控制起来,然后帮他们先投资,然后再从收入里扣。
四、懒惰和现代性的悖论
Y 村的贫困与其说是“贫困”,倒不如说是“欠发达”。Y 村没有普遍的饥饿,而是与“发达”状态下的财富和福利的差距。村民常常挂在口头上的话是“我们很穷啊,你看村里连一辆车都没有”。如果把30~40年作为一个时间跨度来对比的话,山下的D 村和Y 村虽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但也不能说差别巨大。L叔说:“过去他们就算比我们好,但是也好不到太多啊。”按照2015年的观察,两个村的发展差距是很大的。D 村70%以上的家庭有汽车,有的甚至还有两辆。一个山下一个山上,相隔不到10公里,都是一个国家,一种制度,不能说两个村是两个世界,但也算是两个天地。双方对于这个差距都有自己的说法。Y 村的人说D 村地好,橡胶树多。的确,D 村地处平原地,交通发达,种橡胶树早,赶上过去橡胶价格高的时候,所以都发了财。D 村的人说Y 村的人太懒,不愿意干活,现在橡胶价格低也不挣钱了,他们就搞冬季蔬菜啊,一样能挣钱,但是Y村的就懒得种。Y 村地处山区,水田很少,山地多,只能种甘蔗,过去没有硬化路,种的冬季蔬菜没有老板来收,自己也没法运出去,菜都烂在地里,农民也就丧失了兴趣。Y 村种橡胶晚,等到橡胶树长成的时候胶价也降了下来,卖不到钱了。显然,地理和基础设施的差异对于发展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如果从生存性能力而言,Y 村并非真正的“贫困”。Y 村过去在山里种旱谷,一年的产量一般可以达到每亩800斤。他们在山里第一年砍树种旱谷,7年后再回到第一年的地方,实行“种7不种8”的传统轮作,同时家家都养冬瓜猪,自己织布,用植物提取的靛蓝染布。自然保护政策开始实施以来,他们被视作雨林的破坏者,不能在山里砍树种地了。Y 村的村民说:“过去的树都是他们砍的啊,我们砍了树,都要等到快10年树大了才砍的。”Y 村的村民的确不会种水稻,不会种香蕉和橡胶,也不会种冬季蔬菜。Y 村的贫困境遇恰恰是由传统向现代的过渡出现的“发展综合征”。
贫困是特定条件下个体和群体福利绝对或相对缺失的一种状态,由于贫困首先表现在物化的指标上,如食物的供给等,因此,贫困是客观性也是绝对的。但是,贫困又是相对的。我们看到的Y 村的贫困如果放在非洲的农村绝对不算贫困。Y 村没有饥饿,有电,有安全饮水,小孩都能上学。但是与国内的其他村庄比,却是贫困的。从上述对于Y 村的介绍似乎可以发现,Y 村的低收入是造成贫困的主要原因,且低收入无法应对现代性的支出也是造成贫困的原因之一。由此可见,Y 村的贫困超越了绝对生存性贫困的范畴。从Y 村的收入结构可以看出农户收入主要以农业为主,其中甘蔗是收入的主要来源。虽然甘蔗的预期收益有糖厂的合同保障,但甘蔗平均每亩的收入为2 000元,其中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成本达到了1 200元左右,因此,除去成本之外的纯收入每亩也只有800元。如果发生野象的侵害,每亩只能得到700元的补偿,2015年全村57%面积的甘蔗被大象侵害。D 哥2015年近4亩地的甘蔗全部被野象吃掉,一年预期一万元的收入拿到了2 000元左右的补偿。D 哥感慨“现在大象比人重要,它们也要吃东西才能活啊”。受限于交通、资金等方面的因素,Y 村的甘蔗只能卖给当地的糖厂,农户没有其他的选择。当地糖厂收购农户的甘蔗是给每位农户收购票,农户要等糖厂的车进村按照票号来拉甘蔗。为了能做好收购的准备,农户都是接到通知后通宵带着头灯在地里抢收,以便能赶上第二天早上糖厂派来的车。甘蔗的收获时间短,工作量大,需要农户之间相互帮工才能完成,如果一些农户因为大象侵害不种甘蔗,其他农户也就没法种了。到2018年,Y 村几乎没有农户种植甘蔗了。在这样的条件下,农户没有甘蔗的定价权,一亩地的野生动物保护补偿又很低,使得Y 村以农业为主的生计极为困难。事实上,过去40年中国农村贫困的大规模缓解除了在改革开放初期依靠农业和其后面向市场的经济作物以外,后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非农就业的增长。[25]距离城市近的乡村会率先实现结构转变,而边远地区依然以农业为主的生计结构将是贫困的结构性问题,[26]同时地处保护区的农户生计[27]与生态保护的矛盾也一直是这些地区农户脱贫的重要问题。[28]很显然,农户的生计结构与市场和制度的不协调是Y 村农户普遍低收入状态的主要原因。
马克·兰克对于美国广泛接受的穷人贫困是因为个人努力失败的文化贫困观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他基于自己的实证研究认为美国的贫困主要是就业歧视和社会保障缺位造成的结构性贫困。[16]Y 村日常生活的困境一方面折射了发展转型条件下中国乡村普遍存在的问题,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呈现了贫困的发生机制;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了作为少数民族群体在发展的体制下面对市场经济所处的地位是比主体民族的贫困群体更加不利,呈现了这一类群体被“再贫困化”的机制。很显然,在发展的语境下,Y 村村民的贫困从很大程度上说是制度性和结构性的,将这一类群体的贫困根源归结为他们的文化至少是片面的。
工程机械电气及自动化维护技术其中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远程在线监测电气设备,由于我国科学水平欠缺,达不到要求,所以我们就必须加大对电气自动化的研究的投入力度,设计者脑子要活泛,可以采纳新概念,主动学习和借鉴国外的技术水平和经验,促进我国工程机械电气自动化的发展,进而实现自主创新。
商业银行参与PPP项目的模式、风险与对策……………………………………张连怀,高仁德,柳小风(4,56)
这些年也有村民尝试着新的挣钱路子。A 哥胆子大,看别村有人种甘蔗发了财,也想各种办法筹钱租了80亩地种甘蔗,请村里人去地里干活,没想到雨一下就是十多天,停工的时候大家都在地里休息。“停工不停生活费呀,大家不干劳动,白吃白喝,我不去买一点好的人家会说我呢,说实话,请外面的人划来多了,一天100块,不开工不给钱,打发了就回去了,也不用管饭。”难以预料的雨水天气不仅影响了甘蔗正常的生长和管理,也极大地耗费了A 哥的资金。他说:“我都没想到今年工费要花这么多! 今年看样子收不回来本钱咯,也不好意思见人了,钱都没得还!”他打算明年再用兄弟的地种芭蕉,“今年芭蕉行情好,要是我今年种的话就发了。不过我明年种也可以,等来年甘蔗地好管理一些,我老婆就去守甘蔗地,我去管芭蕉地。管得住的,不怕大象的,只要我们努力干,就是可以挣钱的,只有这样才能把钱还上”。A 哥已经算不清他欠了多少钱了,反正“这个也欠,那个也欠。每天一睁眼就是哪里去找钱,这几年我和老婆到处折腾,却始终挣不到钱,还搞得家不像家,连个房子都没得”。拖家带口的不容易,单身汉的日子也不好过。Q 哥尚未婚娶,家里就他一个人,“信用社贷不到款了,看我就一个人,怕我还不上”。为了能有钱建房,他只能半夜开车运香蕉挣点钱。山里都是蚊虫,他全身上下被咬得没一块好皮肤,从晚上11点干到早上6点,装了500箱香蕉,除去油费,最后才剩下300块。他哭了,“钱太难挣了,为什么我这么辛苦还是挣不到钱,我都快翻下山去了”。他用挣来的钱买材料,一晚上的辛苦最后换成一小堆瓦片。后来他的叔叔因为盖房盖到一半,缺了一些材料直接就拿去用了,到现在也没还给他。Q 哥自我宽慰“反正一家人嘛,大家也都觉得是应该的,毕竟奶奶跟着叔叔住,就当我这些材料是给奶奶的吧”。
Y 村日常的社会实践充满了机会分享、利益分享和缺乏储蓄等各种被认为导致贫困的“抑制进取”的社会文化实践 。[38](P2~9)然而,将这些实践看作是导致贫困的文化则是值得商榷的。Y 村这些社会文化实践是低水平物质供给条件下集体性生存的策略,这些文化实践有效地规避了群体陷入生存性贫困的困境。前述所介绍的Y 村呈现的无富人的村庄社会景观一方面展示了Y 村的发展意义上的贫困,同时也展示了传统社会文化实践在保持集体性生存安全方面的有效性。因此,与其从一般意义说这些文化是导致贫困的原因,倒不如严格地说这些文化实践与在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中获得财富的要求不相适应。
五、结果与讨论
脱贫攻坚计划实施政策在强调依靠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的同时,不断推出了一系列针对消除制度和结构性致贫因素的政策措施,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为贫困人口创造公平的发展环境也是脱贫攻坚的重要举措之一。[39]Y 村于2015年以后在这些政策的支持下发生的巨大变化恰恰验证了贫困的结构性立论。
撬动社会资本方面,直接股权和直接债权优于直接补贴,核心原因在于政府投资的示范效应。政府引导基金的直接投资传递出宏观调控对新兴产业的态度,并且减轻了新兴产业内外部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有助于引导社会资本投向新兴产业。相对而言,直接补贴的信息公开程度较差,并且补贴对应产业发展的不确定性,信号效应较弱。而FOF的投资模式优于直接投资模式,具体表现在FOF模式能够直接影响风险投资基金的选择标的,有助于引导社会资本投资新兴产业。
在婚姻家庭社会工作领域,虽然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善、规范的服务标准体系和管理标准体系,但由于婚姻家庭事项范围广、种类繁多,并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服务和管理的各项标准制定速度难以达到新增事项的发展速度,标准制定及完善过程存在不确定性等因素,所以未能形成一个完整、协调及有效的标准体系。同时,由于服务对象个人经历不同、服务需求多样化,各服务单位难以统一社区活动方案、小组服务计划以及开展服务流程等,所以导致诸如入户调查流程、服务方法方式、服务效果评价等部分服务层面标准缺乏。
中国地域广阔,各地社会经济状况差异巨大,任何一项政策的实施都会因为不同的社会文化条件而产生不同的效果。过去40年,中国发展是市场与体制共同演进的过程,本着“有什么用什么”发展经验,[40](P241~243)在全国实施促进贫困人口产业扶贫的政策可能是地理条件好,受教育程度高,社会文化伦理更接近现代市场要求的群体优先受益。全国类似Y 村这样的深度性贫困群体之所以在过去40多年的发展中居然没有一个富人的案例说明地处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群体很难借助市场经济的大潮发展自己。将全国的贫困人口都归类于特点均一的“穷人”,实行统一政策必然会发生政策在某类群体上的实施效果异化。Y 村以及像一些地区这样的发展滞后现象实质是大一统性的机械发展主义模式遭遇地方性特点的典型性写照。发展体制下的市场机制的公平性是有条件的,在市场中的公平竞争并非是平等的,这个过程是有“文化中心”的。处于文化边缘的群体很容易“被贫困化”和“被再贫困化”。从发展的角度讲,扶持少数民族贫困群体需要差异化的减贫政策,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政策需要有社会文化敏感性,需要支持少数民族贫困群体发育能基于自身文化实践同时又能与现代发展制度有机衔接发展方式。与Y 村相似的很多类似的少数民族村庄的日常文化实践如福利、利益和机会分享等均是这些群体维系集体性生存安全的社会文化策略。这些社会文化实践隐含了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维系社会秩序,构建社会关系,从事社会生产的基本逻辑和文化智慧。这些文化实践不仅不是造成贫困的文化,恰恰是大大缓解了生存性贫困的基本社会机制。在现代发展制度资源供给不足的情况下,Y 村的大量收入通过相互的拆借转变成了村内的流动资金,支持了村民日常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因为村民无法及时从任何国家的发展体制中借到急需的钱。显然如果仅仅简单地从村民很少储蓄这点,可能会得出他们不储蓄不投资的结论。相互拆借没有利息可以被看作为没有市场观念,但是Y 村无法统计的没有利息的拆解降低了本来就缺乏资金农户的融资成本。帮工看似会消耗人情和大量的食物,但是却极大地减少了雇佣外来人的现金支付的压力。Y 村看似是一个“贫困村”,但事实上则是一个在资源稀缺条件下自我治理有序的社会。Y 村和其他少数民族村庄所呈现的发展滞后的社会文化动态与刘易斯所阐述的贫困文化群体完全不同,因此,一般意义的文化贫困理论不适合解释Y 村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
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不同的视角对Y 村的讲述和呈现是不同的。因此,Y 村的贫困超越了某种客观和绝对的“贫困”水平,属于与全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比较而产生的“发展性贫困”。Y 村长期地处交通不便的山区,2015年很少有外面的人进入村庄,但是,村庄已经或多或少地整合到了全国范围的发展潮流中,总体上呈现了消费率先融入了市场,如交通工具和手机的使用已经在长期处于相对低的物质福利水平的Y村普及。然而,问题是,与消费模式进入市场不一致的是经济生产依然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同时文化实践在主体上依然以传统为主,造成了面对现代性扩张的尴尬。现代性视角将这种尴尬看作是他们处于贫困文化之中,将他们的发展滞后归结于他们所具有的社会文化特性。而问题恰恰是,现代性扩张条件下不断推高的消费逐渐转变成刚需消费,如教育,医疗,手机、摩托车等拉大了收入和消费的差距,造成了Y 村的债务,呈现出了所谓的深度性贫困。这样一种贫困和Y 村的文化并无太大的相关性,而且很大程度上也是制度性的原因。
当然,从发展的角度讲,Y 村以及类似的少数民族群体的确也面临着如何有机地融入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三个负面的张力。首先是国家治理的需要与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发展之间的矛盾。将普通话扶贫作为扶贫内容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国家治理面对这一矛盾的政策考量。其次是现代发展体制下的文化中心主义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不适应。民族经济的概念对于缓解这一张力提供了具体的路径,然而,这可能又引发新的矛盾。第三是少数民族的传统社会伦理和技能与现代性伦理和技能之间的张力。作者不主张被动的“民族本位”,呼吁探索两者之间的有机对接。一方面,传统的社会文化实践本身并不必然是“抑制进取的文化”,而且恰恰是扶贫重要的社会资源。即使很多的社会文化实践不利于进入市场竞争,但在很多的地方社会文化实践中又存在着“消解进取抑制”的实践形态。因此,通过消除所谓的“贫困文化”的路径是值得商榷的;另一方面,不同的文化群体均存在自身的“现代性”的逻辑和路径。中国作为相对于西方一个另类的社会文化的现代化发展实践也证明了“多样性、现代性”的客观可行性。
[参 考 文 献]
[1]Hartwell R M.Long debate on poverty[M].St.Louis:Washington University,1986.
[2]Feagin J R.Poverty:We still believe that 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J].Psychology Today,1972(6).
[3]Gilens M.Why Americans hate welfare:Race,media,and the politics of antipoverty policy[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9.
[4]Kluegel J R,Smith E R.Beliefs about inequality:Americans'views of what is and what ought to be[M].New York:De Gruyter,1986.
[5]Bowles,S.,Steven N.Durlauf,Karla Hoff.Poverty trap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
[6]Samuelson P A,Solow R M.A complete capital model involving heterogeneous capital goods[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56(4).
[7]Loury G C.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earnings[J].Journal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1981.
[8]周怡.贫困研究:结构解释与文化解释的对垒[J].社会学研究,2002(3).
[9]Oscar L.The culture of poverty[J].Scientific American,1966(4).
[10]王小强,白南风.富饶的贫困:中国落后地区的经济考察[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11]高香芝,徐贵恒.贫困文化对民族地区反贫困的多层次影响[J].理论学习与探索,2008(2).
[12]李文钢.贫困文化论的误用与滥用[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
[13][法]让·雅克·卢梭,著,吕卓,译.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14]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5]Rank M R.One nation,underprivileged:Why American poverty affects us all[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16]Rank M R,Hirschl T A.Rags or riches?Estimating the probabilities of poverty and affluence across the adult American life span[J].Social Science Quarterly,2001(4).
[17]Alesina A,Glaeser E,Glaeser E L.Fighting poverty in the US and Europe:A world of difference[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18]Murphy K M,Shleifer A,Vishny R W.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big push[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9(5).
[19]Tebaldi E,Mohan R.Institutions and poverty[J].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2010(6).
[20]Di Falco S,Bulte E.A dark side of social capital?Kinship,consumption,and savings[J].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2011(8).
[21]Durlauf S N.A theory of persistent income inequality[J].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1996(1).
[22]Sampson R J,Morenoff J D,Gannon-Rowley T.Assessing“neighborhood effects”:Social processes and new directions in research[J].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2002(1).
[23]Mosse D.Adventures in Aidl and:The anthropology of professionals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M].New York:Berghahn Books,2011.
[24]李小云.把深度性贫困的治理作为精准扶贫的重中之重[J].老区建设,2017(7).
[25]李小云,徐进,于乐荣.中国减贫四十年:基于历史与社会学的尝试性解释[J].社会学研究,2018(6).
[26]李小云.新时期农村贫困问题及其治理[J].党政干部参考,2015(21).
[27]张海鹏,姜志德.自然保护区生态经济矛盾解析[J].林业经济问题,2004(5).
[28]王昌海.中国自然保护区给予周边社区了什么?——基于1998~2014年陕西、四川和甘肃三省农户调查数据[J].管理世界,2017(3).
[29]李小云.贫困人口陷入“结构性贫困陷阱了吗”话[N].农民日报,2015-05-27(003).
[30]里昕.基于族际对比的少数民族农民工就业竞争能力研究[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
[31]李小云,屈哨兵,赫琳,等.“语言与贫困”多人谈[J].语言战略研究,2019(1).
[32]李向春,袁春生.云南跨境婚姻管理[J].云南社会科学,2015(1).
[33]龚向光,胡善联,程晓明.贫困地区农民合作医疗支付能力研究[J].中国卫生经济,1998(1).
[34]蒲川,游岚,张维斌.农村贫困人口的医疗保障问题研究——以新农合和医疗救助制度的衔接为视角[J].农村经济,2010(3).
[35]Andersson E,Gabrielsson S.“Because of poverty,we had to come together”:collective action for improved food security in rural Kenya and Uganda[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2012(3).
[36][匈牙利]卡尔·波兰尼,著,黄树民,译.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37]邓万春.关于农民市场风险的一种表述——市场“规则”与“场所”的关系逻辑[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
[38]Murray C.Losing ground:American social policy,1950-1980[M].New York:Basic Books,1994.
[39]汪三贵,曾小溪.从区域扶贫开发到精准扶贫——改革开放40年中国扶贫政策的演进及脱贫攻坚的难点和对策[J].农业经济问题,2018(8).
[40]Ang Y Y.How China escaped the poverty trap[M].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6.
Poverty Production:A Dialogue Between Structure and Culture——An Ethnography of a Y Ethnic Village in South-western China
LI Xiao-yun,WU Yi-fan,DONG Qiang,SONG Hai-yan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94,China )
Abstract: This paper conceives the poverty of Y Village as developmental poverty.Different from survival poverty,the cause of developmental poverty is deeply embedded in the institutions of development,and at the same time,it is also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possession of a set of modern ethics by the poor.The paper postulates the poverty in a modern standard as the result of the entangled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institutions of development that are disadvantageous to the poor and lack of modern market ethics by the poor.
Key Words: poverty;advance mode;development system;development syndrome;social and cultural practice
[中图分类号] G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179(2019)03-0164-11
* 收稿日期 2019-01-20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2018TC037);云南省李小云专家工作站项目。
[责任编辑 秦红增][专业编辑 王柏中][责任校对 石彬筠]
[作者简介] 李小云(1961~ ),陕西定边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农村发展与减贫、国际发展。吴一凡(1993~ ),女,湖北仙桃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农村发展与管理。董强(1977~ ),山西平遥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农村社会治理。宋海燕(1975~ ),女,黑龙江哈尔滨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农村发展。北京,邮编:100094。
标签:贫困论文; 进取模式论文; 发展制度论文; 发展综合征论文; 社会文化实践论文;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