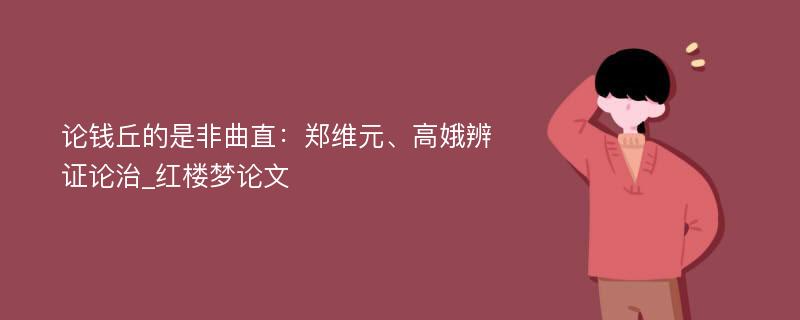
千秋功罪谁与评说 为程伟元与高鹗辨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功罪论文,千秋论文,谁与论文,高鹗辨诬论文,程伟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红楼梦》研究史上,程伟元与高鹗曾因为搜采、整理、撰印百二十回本《红楼梦》(世称“程高本”),而受到红学家们的注意和评论。近二百年来,随着红学研究的深入和程高二人生平资料的发现,人们对程高的评价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由于某些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对程高评价中的不实之词,仍然在影响着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对于某些错误的论断要加以辩析和澄清,这不仅需要有坚实的证据,而且还必须摒弃头脑中的成见。唯其如此,方能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来评价程高的贡献和他们在红学史上应有的历史地位。
“书商”之说纯系臆测
从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甲本”问世,程伟元的名字就同百二十回本《红楼梦》连在了一起。但是,从1991年到本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程伟元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除了一印再印的百二十回本《红楼梦》(不论是“程甲本”还是“程乙本”)上照例署上他的名字之外,就极少有人再提到“程伟元”三个字了。八十年代,是脂本倡行天下之时,程伟元的名字竟然“消失”了,附骥在八十回之后的“程高本”只剩下了名列进士榜上的高兰墅了。
寻其原因,不外是两点:(1)高鹗“续书”说的影响。 某些人尽管对程伟元、高鹗的生平才艺毫无研究,但却“大胆”相信高鹗是《红楼梦》后四十回的续作者,同样把程高二人的“叙”视为说“鬼话”。(2)对程伟元的身世一无所知,却相信某些人所说的“书商”说。 八十年代,程伟元的生平资料本已有了突破性的发现,新的研究成果本已证明程伟元绝非是一介“书商”。〔1〕。 但某些人因有某种心理“障碍”,不愿承认这个事实,来个装聋作哑,以免丢了“权威”的面子。
事实总归是事实,历史谁也无法改变。程伟元不是一介“书商”,而是一位“文章妙手”。他不仅能诗善画,而且还是一位书法高手。晋昌、刘大观、孙锡、李梨等人的诗文,还有王尔烈的寿屏的发现,都充分证明了这一事实〔2〕,所谓“书商”之说, 提供不出一丝一毫的有力证据。例如有人说,程伟元是“萃文书屋”的老板,请问何以为据?难道《新绣全部绣像红楼梦》是“萃文书屋”活字刷印就能证明?倘如此,那高鹗一起署名又何在例外?或许有人又说,人家高鹗后来中了进士,当了御史,升了侍读〔3〕,而程伟元榜上无名,“大清搢绅余书” 又无履历,不是“书商”又是什么? 其实这是一种荒谬绝伦的逻辑,难道不中进士、不当官就得当“书商”?新发现的程伟元生平资料恰恰证明他远出“关外”,到盛京将军幕府当了“案牍”,事余时间还设馆授课,教起书法了〔4〕。在辽东, 这住“冷士”的交游踪迹说明他并没有去当“萃文书屋”的阔老板。因此,“书商”说纯系一种臆测之词,根本站不住脚的。
程高之《序》是实话还是“鬼话”
程伟元与高鹗在“程甲本”排印既竣之时各写了一篇短《序》,交待他们搜集、整理、排印的经过和目的。“程乙本”问世之时又加了一篇联合署名的“引言”,说明他们为什么在“程甲本”刚刚问世不久又要重新校订排印第二个本子。这三篇文字,凡是研究《红楼梦》的人都很熟悉。特别是那些评论过《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人,时常引用这三篇文字中的一些话,甚至是全文转录。因此,本文不再全文转录了。
主张《红楼梦》后四十回为高鹗所续或是他人所续的人认为,程伟元与高鹗的《序》中的话是一唱一和,互相“掩盖”,都是“假话”、“谎话”,甚至是“鬼话”。那么,程高之《序》、《引言》中的话真是“假话”、“谎话”、“鬼话”吗?它“谎”在何处?“鬼”在哪里?又有何证据呢?其实,尽管胡适等人说得振振有词,某些人也相信不疑,却实在经不起推敲。我们翻开他们的著作仔细搜寻他们的“铁证”,至多不过是以下两点“大胆”的推测之词而已。
(1)程伟元在《序》中说:“然原目一百二十卷, 今所传祗八十卷,殊非全本”,又云:“是书既有百二十卷之目,岂无全璧。”这两句话即是胡适所指的“假话”之一。胡适在《红楼梦考证》(改定稿)〔5〕中说:
《红楼梦》当日虽只有八十回,但原本却有一百二十卷的目录。这话可惜无从考证。(戚本目录并无后四十回)我从前想当时各钞本中大概有些是有后四十回目录的,但我现在对于这一层很有点怀疑了。
胡适的这段话很明显是对程《序》中所说的“原目一百二十卷”表示“怀疑”。其根据是“戚本目录并无后四十回”,他没有提出其它证据。
在此,我不想引证更多材料来辩驳,略举二例即可说明胡适的看法是错的。其一,程伟元在《序》中反复强调“今传八十回”,这句话并没有说谎。舒元炜在乾隆五十四年的序中也说自己所见只八十回,《红楼梦补序》作者犀脊山樵也说“尝见过《红楼梦》元本,止于八十回”。今发现的十二种早期钞本多数也止于八十回,都证明程伟元的话是真实的,并非说谎。其二,说到“原目一百二十卷”也非空穴来风。周春《阅红楼梦随笔》(《红楼梦记》)中记载:“乾隆庚戌(五十五年,1990)秋,杨畹耕语余云:‘雁隅以重价购钞本两部:一为《石头记》,八十回;一为《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微有异同。……壬子冬,知吴门坊间已开雕矣。”这条记载说明“程甲本”问世之前已有了一百二十回钞本在流传,并非只有八十回钞本一种。因此,当时程伟元看到一百二十卷目录,或是看到一百二十回《红楼梦》钞本,都不足为奇。用只有八十回的戚本证明程序中的话是“假话”、“谎话”,怀疑它的真实性,是用错了证据。从常理上说,以戚本证程甲本原目的存在与否这是违反考证常识的,即戚本没有后四十回或后四十回目录,不能证明程伟元就没有看见过一百二十卷的目录或一百二十回钞本。其三,如今我们已发现的“蒙古王府本”和“梦稿本”,不仅有一百二十回目录,而且还有一百二十回的全文,实物证明程伟元的话也是其实可信的。
(2)程伟元在《序》中说:“……数年以来,仅积有二十余卷。一日偶于鼓担上得十余卷,遂重价购之”。胡适在《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中说:“程序说先得二十余卷,后又在鼓担上得十余卷。此话便是作伪的铁证,因为世间没有这样奇巧的事!”胡适的这段话流毒甚广,后来的一些权威学者把这段话奉若神明加以引用。其实,稍微读一读胡适的原文就会发现,胡博士没有提供任何文字根据就下了这么一个结论,而且还说是“铁证”。他的唯一理由就是“因为世间没有这样奇巧的事!”这是考证吗?难道世间真的就无可能存在这种“奇巧”的事了吗?不!世间“奇巧”的事,可以说多不胜数!古人云:“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就是说的这种“奇巧”。历代的书画收藏大家,在“鼓担”购到久欲购置的奇珍异器,偶然得之,意外相见之事,至今成为佳话者屡见不鲜。在《红楼梦》版本史上,此类事也不乏其例。以胡博士所见的“甲戌本”得之之“巧”,残之所“奇”,难道不也是证据吗?如以胡博士之高见,“甲戌本”的出现,上面多了一个“广告”,岂不又是“作伪铁证”?在《红楼梦》只传八十回的情况下,急欲得后几十回,心情可想而知。看见有后几十回就购也非程伟元一人,逍遥子在《后红楼梦序》中就说:“同人相传雪芹尚有《后红楼梦》三十卷,遍访未能得,艺林深惜之。”后来他听说白云外史、散花居士得到,先是“借读”,然后“爰以重价得之”,梓行。这个续书出现,说明当时的一些情况。因此,我认为胡适等人以上面两点来否定程《序》的真实性,是不足为训的。不是程《序》说“假话”、“谎话”、“鬼话”,恰恰是胡适先生自己说了“大话”、“诳话”、“武断”的话。
“分任之”与“遂襄其役”
评论“程甲本”、“程乙本”的功过是非,自然要提及程伟元、高鹗,这是正常现象。奇怪的是,近世以来的评论家们常常只提高鹗而只字不提程伟元,好象根本不存在程伟元一样。这种现象到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之后,尤为突出,似乎程伟元也成了“走资派”或是“反动权威”,他的名字不宜于见之《红楼梦》,剥夺了他应该享有的“权力”。追根寻底,当然与程伟元被认定为“书商”有关。此外,也与某些人认为程伟元根本就没有做什么工作,只是出资刷印而已有关。其实,这又是大错特错的事。
首先,搜采《红楼梦》各种钞本的工作是程伟元一人独立完成的,高鹗并没有参与其事。这在程、高二人的《序》中说得明明白白,毫不含糊。程《序》说:“爰为竭力搜罗,自藏书家甚至故纸堆中无不留心,数年以来,仅积有二十余卷。一日偶于鼓担上得十余卷,遂重价购之。”高《序》说得更清楚:“予闻《红楼梦》脍炙人口者,几二十余年,然无全璧,无足本。向曾从友人借观。窃以染指尝鼎为憾。今年春,友人程子小泉过予,以其所购全书见示,且曰:‘此仆数年铢积寸累之苦心,将付剞劂,公同好。……’”证明程伟元在“搜罗”上确曾是付过“苦心”,且是他一人完成的。
其次,在整理百二十回本时,程伟元也并非“袖手旁观”而由高鹗独立完成。程《序》中说:“乃同友人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复为镌板,以公同好”。说明他参与了“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的工作。高《序》中说:程伟元将全部得来的稿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春天才拿给高鹗看,并邀请他共同整理部分稿。高引程的话说:“子闲且惫矣,盍分任之?”,翻译成白话就是:“你现在闻暇无事,能不能与我分担整理工作?”高鹗答应了。他说:“予以是书虽稗官野史之流,然尚不谬于名教,欣然拜诺,正以波斯奴见宝为幸,遂襄其役。”这里先是用“欣然拜诺”,即高高兴兴答应了程伟元的请求;然后又用了“遂襄其役”一语,即是说他“于是帮助程伟元完成这项工作。”襄者,从旁帮助也。其役者,指整理《红楼梦》这件事。由此可以看出,是程伟元请高鹗帮忙,而高鹗也不过是“分”担其中一部分工作,而并非全部工作。谁是主谁是客,难道不十分清楚吗?胡适当年位高名显,况“研究”的学问又十分宽广,可能没有时间细读程高之《序》,下了一个错误的判断。那么,后世的一些权威(又是那么多)要“打倒”胡适新红学派的时候,为什么不再重新读一读程高之《序》呢?为什么还要把胡适的错误结论一直奉为圣条呢?如今有些人摆出一副公允的面孔,要恢复《红楼梦》后四十回的真面目,还程高一个公道,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是沿袭着胡适的结论,把整理、排印之功过归于高鹗一个,重犯胡适当年的错误。事实说明,程伟元是“搜罗”、“整理”、“出版”《红楼梦》百二十回本的“第一人”,而高鹗在“整理”、“出版”上是参与者,是“第二人”。
“俱兰墅所补”与“续书”之说的由来
《红楼梦》“程甲本”、“程乙本”问世之初,所署的名字,只有曹雪芹一人,读者也完全是把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作为一个“整体”来读。因此,在一段时间里并没有什么“著作权”的争论。到了嘉道以后,许多“笔记”、“诗话”中才有了一些零星的记录,说法纷纭,莫衷一是。诸如曹雪芹著书说、曹雪芹修改说、高鹗著书说,等等。但高鹗“续书”之说则较晚些。根据现在能够看到的有关资料,明确说高鹗“续书”的第一个是《八旗画录》的作者李放。他在记述曹雪芹的事迹时说:
曹霑,号雪芹,宜从孙……所著《红楼梦》小说, 称古今平话第一。
在此之下小字注道:
嘉庆时,汉军高进士鹗酷嗜此书,续作四十卷附于后,自号“红楼外史”。……
那么,李放的“续作”说又是从何处来的,根据是什么,并没明确的说明。但是,在李放之前,关于高鹗“所补”之说确是较为流行的。其始作俑者首推张船山。张船山(1764—1814),名问陶,字仲治,号船山,四川遂宁人,清代诗人,兼善书画;乾隆朝进士,官吏部郎中,终山东莱州知府,其名气远过程高二人。他当年与高鹗有“同年”之谊,所以他的记载成为后来人指高鹗为“续作”者的重要根据。他于嘉庆三年写了一首赠高鹗的诗,其诗题中注明“传奇《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诗中还有一句“艳情人自说红楼”。其实,张船山的诗题小注也好,还是“艳情人自说红楼”也好,都没有“续作”的意思。即使从训话学的角度看“补”与“续”二字,绝非同义,也没有互代之义,怎么能说“所补”就是“续作”呢?以我的理解,张船山的“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至多告诉我们,当年高鹗与程伟元“分任之”的时候,高鹗主要是负责后四十回的整理工作。而“所补”二字,恰恰为程伟元之《序》中所说:“见其前后起伏,尚属接笋,然漶漫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拟成全部”作有力的证据。“所补”即“截长补短”之“补”。在程伟元、高鹗联合署名的《红楼梦引言》中对“补”字作了更详尽的说明:
书中前八十回抄本,各家互异;今广集核勘,准情酌理,补遗订讹。其间或有增损数字处,意在便于披阅,非敢争胜前人。
又说:
是书沿传既久,坊间缮本及诸家所藏秘稿,繁简歧出,前后错见,即如六十七回,此有彼无,题同文异,燕石莫辨。惟择其情理较协者,取为定本。
接下又道:
书中后四十回像就历年所得,集腋成裘,更无他本可考。惟按其前后关照者,略为修辑,使其有应接而无矛盾。至其原文,未敢臆改,俟再得善本,更为厘定,且不欲尽掩其本来面目也。
从到目前为止所发现的早期八十回抄本也好,还是发现的一百二十回抄本也好,都证明程《序》、《引言》中的话是事实。前人所写的许多“摘误”和今人的诸多“指谬”、“批评”,也都说明程高并没有说“假话”、“谎话”,更不是“鬼话”。张船山的“所补”说根本不能作“续作”之证据,而确是“补遗订讹”的好证据。
有人为了证明高鹗是“续作”者,把高鹗所写的《重订〈红楼梦〉小说既竣题》〔6〕一诗拿来作证据,这更是荒唐无稽。 高鹗的这首“既竣题”见之于他的及门弟子华龄所编的《月小山房遗稿》,诗全文是:
重订《红楼梦》小说既竣
老去风情减昔年,万花丛里日高眠。昨宵偶抱嫦娥月,悟得光明自在禅。
这首诗标题只能证明高鹗参加了“重订”《红楼梦》——即修改“程甲本”和“程乙本”的工作,作了“订”讹的活儿,仍然无一丝一毫的“续作”的影子。仔细研究嘉道以后,特别是光绪年间的诸家“笔记”的记载,我们清楚看到当时人多以“所补”二字为根据传来传去,到了李放时才把“所补”传成了“续作”。他们没有“考证”事实的真相如何,只是把“偶闻”记载下来,且又是互相转抄而已。
真正把“续书”说肯定下来的人是新红学的开山泰斗胡适。他只是根据一些“偶闻”记载而下的判断,根本没有提供一条可资查证的证据。而后世学者沿袭胡适之说时,把胡适的话看成了“真理”,不加审辨地引用,实际上是以讹传讹。
这里要澄清一个事实,程伟元“搜罗”来的残稿中已有了后四十回,这在程《序》中作了明确说明,而直到1791年春高鹗始看到“全璧”的真面目。至于此前的后四十回“原搞”是不是曹雪芹“原稿”和谁是“续作”者是两回事,而高鹗不是“续作”者是事实,不能把两个不同的题搅在一起,甚至后四十回质量如何都扣到了高鹗头上,那是不公平的。在高鹗的时代,他只看到了那样的“后四十回”——即程伟元搜罗来的本子就是那样,高鹗也无可奈何〔7〕。 高鹗的任务是“整理”——“补遗订讹”,而不是做研究、作“考证”,这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有什么错处不在高鹗。后四十回水平如何也不应当由高鹗来承担。至于高鹗“补”的水平高低,那需要有证据说明他那些地方“补”错了,不能把后四十回所有不好的地方都归结到他头上去。
我个人认为,从高鹗的《重订〈红楼梦〉小说既竣题》诗和他在乾隆五十年以前所写的全部诗词看,他那时的才学识都不足以担起“续”《红楼梦》的重任。况且,他在乾隆五十六年春天起才看到程伟元搜罗的稿子,更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续作”后四十回附于前八十回之后。他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整理、重订《红楼梦》之后,对《红楼梦》及搜罗、整理、重订《红楼梦》的意义究竟有那些足以称道的见解呢?除了一句“悟得光明自在禅”之外,我们对高鹗的思想境界和美学造诣,实在不敢恭维。我不明白一些人把“续书”作者的桂冠戴在高鹗头上究竟是为了贬他呢?还是捧他?
张筠嫁给了哪个“高氏”?
在抨击高鹗“续书”罪过的一些文章中,有人甚至攻击高鹗的人身,咒骂他惨无人道的害死了颇有诗才、比他小很多岁的张筠。根据就是张船山《船山诗草》中的那首《冬日将谋迄假出齐化门哭四妹筠墓》〔8〕诗题之下的小字注:“妹适汉军高氏,丁未卒于京师”。 全诗共四首,其一云:
似闻垂死尚吞声,二十年人了一生。
拜墓无鬼天厄汝,辞家久客鬼怜兄。
再来早慰庭帏望,一痛难抒骨肉情。
寄语孤魂休夜哭,登车从我共西征。
诗题小注明明写着是“汉军高氏”,并没有写“汉军高鹗”。“高氏”不等于高鹗,这是连小学生都懂的道理。当时在京城里汉军姓高之人多矣,而且相当多的“高氏”都是从龙入关者,列于汉军籍。把“高氏”变为高鹗者,没有任何证据,后世人不详察,完全是人云亦云。借此而骂高鹗是“罗刹”,除非拿出证据来,否则无法使人相信此说。清光绪间人震钧在《六尺偶闻》中说:
张船山有妹嫁汉军高兰墅(鹗),以抑郁而卒,见船山诗集。按兰墅,乾隆乙卯玉殿傅胪,亦有诗才。世行小说《红楼梦》一书,即兰墅所为。余尝见其书诗册,有印曰“红楼外史”,则其人必放宕之士矣。兰墅能诗,而船山集中绝少唱和。可知其妹饮恨而终也。〔9〕。
震钧的“偶闻”谬种流传,不知毒害了多少人,甚至某些有名的大家也上了他的当,把他的话当作“证据”而痛骂高鹗。
首先,震钧的记录采自“船山诗集”,但恰恰“船山诗集”中说的是“汉军高氏”而不是“汉军高鹗”。显然,是震钧“想当然耳”,篡改了张船山的原文。其次,震钧提供了一条“证据”,说“兰墅能诗,而船山集中绝少唱和,可知其妹饮恨而终也。”“绝少唱和”是事实,但并非没有唱和。《船山诗草》中收入的《赠高兰墅同年》〔10〕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先看张船山的原诗:
赠高兰墅(鹗)同年
(传奇《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
无花无酒耐深秋,洒扫云房且唱酬。
侠气君能空紫墓,艳情人自说红楼。
逶迟把臂如今雨,得失关心此旧游。
弹指十三年已去,朱衣帘外亦白头。
从诗中的“弹指十三年已去”一句,可推算出张船山写这首诗的时间应在嘉庆六年(1801)。因为张船山是在乾隆四十九年(1984)入京,五十年(1985)“下第出都”, 与兄玄白等“举家归蜀”。 五十三年(1788)三月再次由成都入京,九月中顺天乡试第十三名,并在此次与高鹗相识于京。从五十三年至嘉庆六年,其前后恰好是“十三年已去”。这里还可以从张船山的行踪上找到一条根据,即张船山于嘉庆三年一月十七日从成都出发返回北京,三月抵京,四月移居京内贾家胡同。到了嘉庆六年,船山“入秋闱分校”与高鹗再度相逢,互诉别后的情形,高鹗曾说及参加整理《红楼梦》的情形而船山亦当读到程本《红楼梦》,故有诗题小注“传奇《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和“艳情人自说红楼”之语。从张船山的诗题、诗中“逶迟把臂如今雨”诸句看,他们的私交甚好,视同“今雨”。从丁未张筠卒到嘉庆三年,时间不过是相隔十年多。张船山怎么可能把一个害死自己妹妹的“罗刹”高鹗视为“逶迟把臂”的“今雨”呢?怎么又可能称赞其有“侠气”?竟写出“赠高兰墅同年”的诗?倘若高鹗真是害死张筠的“恶鬼”,张船山又是写诗“赠同年”,又是称“今雨”,那他有何颜面去见九泉之下的妹妹张筠呢?难道我们能说张船山也是一个不顾廉耻的无赖之徒吗?所有这一切,只证明一个问题:张筠所嫁的“汉军高氏”,根本就不是高鹗。惟其如此,方能解释张船山的赠高鹗诗和诗的内容。这一观点,并非是我第一个发现,第一个写文章。早在二十几年前,就有朱南铣先生提出此说〔11〕。其中我记得的还有徐恭时先生〔12〕。但是,从那时到现在仍然有一些学者不顾事实,仍然把震钧的“偶闻”作为论证高鹗无才无德的根据,这是令人感到莫明其妙的事情。
结论
为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派,向以考证著称于世。应当承认,他们在曹雪芹家世生平、著作权、脂本考证等方面确实多有建树,也为后世学者所称道,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也是他们在红学史上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是,也无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新红学派不论是其开山泰斗还是其集大成者,在《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评价上和所谓“高鹗续书”说上的论断,都是无法让人苟同和称善的。他们的错误论断和某些编见影响之深之广,简直成了一种痼疾,达到一种难以“医治”的程度。这种“痼疾”不仅成了新红学自身的悲哀,也是整个红学史上的一种悲哀。正因为如此,今天的红学研究者应该以一种自省的态度,把以往的史料、论断加以重新审察是十分必要的。
程伟元、高鹗的“冤案”的拖至今天已有二百年了。重视和研究程高的《序》、《引言》及相关的史料,澄清某些被歪曲了二百年的是是非非,不仅是为了给程高洗刷“冤屈”,更重要的是对《红楼梦》的成书过程、曹雪芹的“著作权”,乃至全面认识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关系,正确评价后四十回的历史地位和程高的历史地位,都有极为深远的意义。我们有责任把扣在程高头上的上的不实之词澄清,还给程高一个公道!
这就是我撰写本文的出发点和目的。
1995年4月18日
于京华放眼堂
注释:
〔1〕参见胡文彬、周雷:《程伟元与红楼梦》一文, 载《文物》月刊1976年10月号。
〔2〕参见《新发现的程伟元生平资料》, 辽宁第一师范学院中文系编《红楼梦研究资料选集》三下。
〔3〕参见胡文彬、周雷辑注《高鹗诗文集》,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9月版第139页。
〔4〕金朝觐:《题程小泉先生画册》诗小序, 见《新发现程伟元生平资料》,载《红楼梦资料选集》三下,第205页。
〔5〕胡适:《红楼梦考证》(改定稿》, 载《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75页—118页。
〔6〕高鹗:《重订〈红楼梦〉小说既竣题》,载胡文彬、 周雷辑注《高鹗诗文集》,天津百花文艺社1984年8月版,第38页。
〔7〕犀脊山樵在《红楼梦补序》中说:“余在京师时, 尝见过《红楼梦》元本,止八十回,至金玉联姻,黛玉谢世而止。”又说:“原书金玉联姻,非出自贾母、王夫人之意,盖奉元妃之命,宝玉无可如何而就之,黛玉因此抑郁而亡,亦未以钗冒黛之说”。此本尚未发现,甚为重要。
〔8〕张船山:《冬日将谋乞假出齐化门哭四妹筠墓》, 载《船山诗草》卷五《松筠集》,转引自一粟《红楼梦卷》第20页。
〔9〕震钧的这条记载转引自一粟《红楼梦卷》,中华书局1965 年7月版第24页。
〔10〕张船山:《赠兰墅(鹗)同年》,原载《船山诗草》卷16,辛癸集;转引自一粟《红楼梦卷》第20—21页。
〔11〕朱南铣:《〈红楼梦〉后四十回作者问题札记》,载《红楼梦研究集刊》第六、七集。
〔12〕徐恭时:《续梦贾假与甄真——程伟元、高鹗与〈红楼梦新语〉》,载《红楼梦学刊》1982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