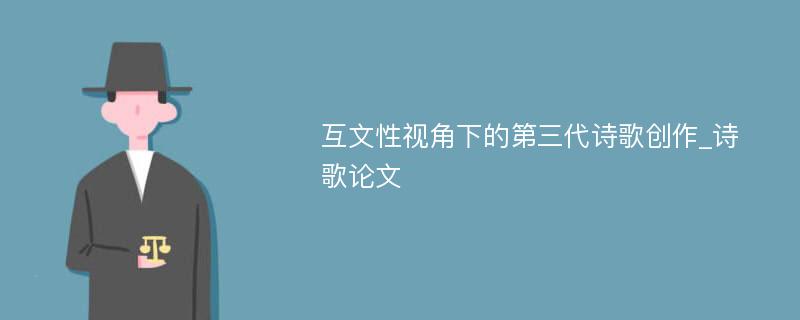
互文视野中的第三代诗歌写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歌论文,视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成长啊,随风成长/仅仅三天,三天!//一颗心红了/祖国正临街吹响//吹啊,吹,早来的青春/吹绿爱情,也吹绿大地的思想//瞧,政治多么美/夏天穿上了军装//生活啊!欢乐啊!/那最后一枚像章/那自由与怀乡之歌/哦,不!那十岁的无瑕的天堂
如果隐去这首诗的作者、题目和写作时间等相关信息,对中国当代文学稍具常识的读者会敏感地发现这首诗里另一个更为庞大的前文本的存在,并很自然地将对前文本的辨认以及由此带来的意义异延作为阐释这首诗的入口。比如由“心红了”、“军装”、“像章”等字眼代表的广场文化的主能指,使读者链接到整个文革文学的语辞系统。进一步注意到这首诗的内容,甚至还可以读到一个和文革文学重复性的主题:对“政治”和“祖国”没有来由的赞美和向往。在类似于街头游行的喧闹语调下,文本发出了一个高亢、明丽的声音。在幼小的追随者的前方,是文革时期的时代公共话语和公共意志。这是一个集体狂欢的祭坛,——人群着装整齐,色彩相类,表情沉醉,没有质疑和犹豫,中间祭奠的是近于狂热的共同理想,他们虔诚的咒语就是不停地对某个庞然大物所唱的颂歌。①
这是第三代诗歌运动中的著名诗人柏桦在1989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时所写的《1966年夏天》。从题目和写作时间可以知道这是诗人对童年经验的复述和追忆。值得对这次追忆投注较多的目光,在于这首诗所面对的历史事件——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当代新诗写作的重要影响:在红卫兵诗歌中被反复歌颂,不断升华;在之后的朦胧诗中被反复控诉、持续揭露。在这两条截然相反的道路上,这一写作资源所蕴藏的主题意义似乎被穷尽了。甚至两类诗歌作品的作者可能是同一个人,他已经演练了历史赋予的所有动作要领(歌颂、揭发、忏悔、控诉、再揭发、再歌颂)和角色转换(追随者、怀疑者、大我、小我、英雄、人),并生产出数量空前的诗歌作品,在不同权利集团和民众那里赢取了政治和道德上的支持。写作的可能性和人类的巨大伤痛似乎在历史的重要关头被同时消化掉了,剩下的就是在怀旧或者教化的氛围中重复有定论的主题,并使用已经充分自足的修辞系统。柏桦这首诗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下似乎很“突兀”地出现了:同样处理文革经验,却没有那些历史在场者的义正辞严和滔滔独白,其抒情者的形象更是暧昧不明。同样的情形可以从很多第三代诗人那里看到,那么如何通过有效的解读将这类诗以及这类诗人的写作纳入更大的叙述结构?
一、写作“成规”的调整
首先要做的恐怕不仅仅是对具体文本的考据。如果对互文性的理解不是那么狭隘地拘囿在文本间的关系,而是充分考虑阅读者的处境,把这首诗的写作纳入文学史的叙述序列,就会发现这种写作不仅仅是一种追忆,而是对读者至少包括两种阅读经验——文革文学和与之相对的新时期文学对文革的不同描述——的改造和重写。在这里,文学成为一种延续集体记忆的特殊方式。同时,一个携带了自身语义、规范和习俗的词语在进入另一种语境中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新的语境的压力,使其原有附着的语义、规范和习俗在挤压下变形、歪曲、澄清或再度膨胀。因此,对某种语境具有标识意义的词语在新的语境的再度出现,往往表征的不仅是对原有附着物的传递和延续,还可能是新的涂抹、修正、删除或添加。
很显然,这里使用的“词语”在写作的意义上更多的是指由整个能指系统构成的具体文本。当这些写作资源不再是第一次“纯洁”(即未被使用和描摹)地出现在作者面前时,已形成的文学史事实就会不断地对后来的写作和阅读施加压力。随之而来的批评和研究也无法把自己面对的文本看作是清白的,而应该充分考虑该写作资源——或者说是一种共同的记忆——在延续的过程中是如何被一步步重构和塑造成型的。这种情形甚至出现在历史的此类在场者那里:尾随别人发言者不仅意味着写作行为的历时性演替,也是在已有发言者曾经置身并用自己的呼号进行培育的政治氛围、读者选择和评价体系中使用一种更具复合性的声音。这种境地的先验性,甚至武断到了根本不容后来者考虑先在发言者的“真实”度和言说效果是否令人满意。当然,后者的缺失往往成为前者获取话语权的口实。于是,后来者往往将自己设定在对先在发言者的修正上,或者故意追求一种特异的叙述方式,因为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完全被先在者的声音覆盖。不过,这一话语空间极其逼仄。
而对第三代诗歌来说,似乎处境更加尴尬。诗人们同样经历了文革这场巨大的悲剧。只不过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出现的。与那些当时和后来发言的在场者不同,由于年龄所限,在历史给定的控诉空间里,他们暂时无法获取呈现自身经验的机会,只能被他们的父兄虚构成一种微弱的声音成为他们经验的旁证,或者模拟为成人的声音淹没在他们父兄的合唱中,使得这种独特的创伤经验很少被历史打捞而没有得到足够的注视和尊重。即使获得了表达自身经验的机会,也会被认为是不足为凭的,不具备像直接参与历史进程者那样的发言可信度。可以说,这种不被信任是幼小的旁观者言说时所必然面对的尴尬处境。但是,这并不足以成为抹杀他们文革经验独特性的根据,或者说,“真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争辩和质疑的,而“真实”本身并不构成文学文本的必然要素。
具体到写作实践中,第三代诗人要“讲述”自己的文革经验,首先要对先在的写作“成规”进行调整。著名的第三代诗人丁当的《回忆》可以看作对自身写作视角转换的隐喻。在诗中,丁当处理了这样一种经验:回忆少年时从楼梯上摔下后的全部过程。“我玩味着疼痛、留血、摔倒的全部过程/哭泣的时间很长到天黑/直到遍地月色改变了我的处境”。到这里,读者以为作者将会有怎样一番抒情,结果没有,“直到我用心解了一天的大便/才安然无恙,动身回家”,到此,丁当并没有收手,“此时,轻佻地想起那伤心的一跤/幸灾乐祸直到天明/我用下流的腔调抚弄这桩往事/象摆弄一只捉到手的麻雀”。回忆的过程就是一个圈套,“轻佻”、“幸灾乐祸”、“下流”、“抚弄”这些词语已经透射出作者对事件本身的判断,可是诗的一开始他使用的是“伤心”、“悲哀”、“月色”、“处境”这些诗歌传统中可以好好煽情的词语,让读者的审美期待伤心地摔了一跤。不过,作者似乎也通过这种自然主义的笔触告诉读者:所谓回忆,在普通人那里,很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矫情造作的感受,有的只是疼痛和哭泣本身,也就是这些体会在时间之流中不期而至的荡漾,就足以引逗着一个人进入回忆的“光晕”。用巴赫金的话,就是这些“比较粗陋”,“绝对欢快的,无所畏惧的,无拘无束和坦白直率的言语”,“都具有对世界进行滑稽改编、贬低、物质化和肉体化的强大力量”。②
二、宏大叙事的缩减
在这个意义上,丁当的诗可以作为一个隐喻来解读:少年在楼梯上摔下来的经历并非是一个致命的遭遇,也带来了足够的疼痛,由于没有其他人在场,或是其他人根本不认为这是一种值得长久为之动容的行为,而且过度的抚摸让这种疼痛突然显得虚假起来。但是,这的确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痛感。只不过在现有的叙事模式里,处于较低的叙述层级,甚至根本就不在现有的文学视阈之内,任何突出、放大只能被人认为矫情可笑。因此,“少年”必须对原有叙事模式的进行整体篡改,比如运用更加原生态的语言进行逼真的“小叙事”。这涉及叙述语调、材质选择、语气转换和修辞调整等一系列的文本实践。
约瑟夫·布罗茨基说:“诗人与众不同,他始终意识到,人们通常所谓缪斯的声音,其实是语言的指令;不是语言凑巧成为他的手段,相反,他是语言赖以继续生存的工具。然而,即使有人把语言想象成某种活的生物(这是极公平的说法),它也无法进行伦理选择。”③或者说,语言就是诗人的自我镜像。所以,进入第三代诗人的文本是一个便捷的方式:从诗人对写作对象和自我身份的设定中探查他们在诸种话语权力关系间的进退取舍。
回到开头引用的柏桦的诗。这首诗中红卫兵诗歌的痕迹,本文开头已经加以论述,在这里,更让人感兴趣的地方在于,这首诗——如柏桦所说,一首“怀念文化革命之美的小诗”④——把自己和红卫兵诗歌以及朦胧诗区分开来的到底是什么?在一个十岁的孩子那里,成长恐怕还是一个缓慢的话题。可是,在柏桦这首诗里却得到一个符咒般的力量的催化。“成长啊,随风成长/仅仅三天,三天!”一个感叹词,两个感叹号,给了这首诗一种难以抑制的加速度。“祖国”、“青春”、“政治”、“爱情”这些大词在一首短诗中同时呈现和到达,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青春的偶像:身着绿色军装(很多人应该知道,身穿绿色军装的解放军形象曾经受到过何等的礼赞,而在文革的氛围中,由于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需要,这种崇拜发展到了极度狂热的程度,在文学、舞蹈、美术等各个艺术门类中都是一个主能指),遍布大街小巷,拥有爱情、拥抱政治。因此,这是一个可以切近模仿的对象,偶像们的成长故事、家庭出身、英勇事迹、喜欢的颜色、发型、说话的方式、用词,喜欢读的书等一切(当然这来自于一个更大的模仿,换句话说,那是一个青春激进的共同体)。这也是一个巨大的符号系统,失去了充满歧义的所指。他们的冲动是一种对革命符号及其衍生物的崇拜。
对红卫兵一代来说,当时青春的到来是实实在在的,可以触摸的现实,他们也在模仿和崇拜偶像,他们有《愤怒》并质疑《命运》,但他们依然《热爱生命》、《相信未来》。⑤而对于旁观者来说,青春只是一种幻美的梦想,在从上至下的政治和道德的链条上,他们已经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比如从红小兵到红卫兵),开除、表扬、惩戒、光荣这些机制已经给了他们种种承诺,所以,一切都将是自然而然、如期而至的,梦想在降临前已经开始叙事。所以不去怀疑也不必怀疑,有的只是歌唱和追随。但是,历史突然出轨。他们尔后写下的关于文革的诗歌和红卫兵诗歌有着巨大的区别,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间横亘的朦胧诗,让他们意识到了潜意识里可能的歌唱和追随只是“最后一枚像章”。“他的主要经历和情绪,是在毛泽东时代酝酿而成的——包括他很小就莫名其妙恐惧地流鼻血,记住,我们经历的是革命半成品的后果,而非革命,也非无产阶级的全面胜利。……所以,他,柏桦,还有所有这代人,和那时代一样,永远徘徊在亦新亦旧上,词语更新换代,人却庸俗之至。一切都流逝得太快了。故青春作为特别的品质,涌入了浪漫主义者的血管”。⑥他们对历史包括自身的质疑、不屑和反思暗含其中,在书写文革时也综合了业已存在的立场不同的多种话语形式:应和的、反对的、青春冲动的和滑稽模仿的,同时将它们打散、混杂,从而发出一种同样丰富而又不可替代的声音。
三、正在发育中的色情
还有色情。这似乎是一个被夸大的话题,处在童年的孩子应该还没有多少色情的欲望。但是,当对回忆的书写成为一个当下发生的事件时,当下的一切必然对回忆大举侵犯。尤其是当回忆的私密性(在朦胧诗那里,这种私密更多的是对政治的不满,他们后来的控诉是公共话语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奇异地和青春(即旁观者写作时的年龄)粘合在一起时,正在发育时的念头就被挖掘出来。杨黎有这样一首诗:
今儿个下午阳光灿烂/我转过身,朝着远处/一块巨大的石头走去/三两个少女在那石头边上/随便坐着/她们五彩的衣服/闪闪烁烁//这样的下午当然不多/我一边走一边猜想下雨的时候/现在反正连一丝风也没有/阳光静静地照着/现在太美了!那石头/和石头背后一片/灿烂的远天
——杨黎:《毛主席,我将永远记着您》
在文革中,人民对领袖的忠诚构成了其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常常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在种种革命活动中。在红卫兵诗歌中这种歌唱占了相当比重,他们用多种方式表达对领袖及其事业的忠心和迷恋,比如复沓、排比、夸饰、合唱等等,甚至于“暗中对接上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情感修辞方式——以恋人关系喻指诗人与君主的关系的传统。纷纷以滚烫的恋人誓词,表达着他们对‘伟大领袖’的炽热之爱”⑦。杨黎这首诗的题目就属此类,它和“永远在一起”、“永远想着您”、“永远歌唱您”是同一种套语的繁殖。这首诗里出现的是一个很纯粹的幻景,构图干净,色彩夺目。抒情主人公“我”虽然动作简单(“走”),可心里却带有一丝色情的念头,而这念头始终只是念头,最后竟然有变成了对美的礼赞,并再次描述背景,似乎图画中心美丽的少女被遗忘了或者从来没有出现过,被石头和和相对空泛的远天取代。
这种纯然空想的色情和这首诗的题目似乎没有任何关系。其实,陈旧的题目与当下的写作时间之间的落差暗示了这只可能是一首追忆之诗,只不过诗歌的内容是引起追忆的由头,好像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里反复摩挲的旧报纸和香味,是一种具体的、更具日常性的追忆线索,即点击这个套语激活的却是带有色情幻觉的回忆。在这里,杨黎运用的是一个幻梦或者类似于幻梦的一次走神,而不是一个革命圣地、重要节日或者刻骨铭心的苦难、极富历史感的文化遗迹、领袖人物的工作场所等等文革诗歌和朦胧诗中常见的意象。不管怎样,它与庞大的公共话语系统发生了极具个人化的勾连。应该注意到,这里的色情并未实现,而是在美的感召下踪迹皆无。这真的是一个不错的借口,就像这里的政治怀念一样,在题目里出现后就永远走失了,它在个人的体味中显得僵硬、疲软和做作,同时又不可或缺。这样一来,似乎诗人的真正目的并非追忆偶像,而是借助对偶像的追忆来描画童年幻想。这样一来,政治话语和色情话语就互相杂和,互为线索,表里不分。
这首诗也可以与柏桦的下面这段对一个女红卫兵的回忆相互阐释。
一阵风过,我抬起头来,看见一位女红卫兵站在我的面前。她最多只有15岁,但我却觉得比我大很多。她微笑着把一枚毛主席像章轻快而准确地别在我幼小的左胸上。就在这别上的一刹那,我那才飞走的灵魂回到了我的体内,我又一次兴奋起来,这兴奋是那么真实、那么亲切、没有一丝的模糊不清;它好像就停在我的心尖上,在我体内如风骀荡,连我的指头都感到那兴奋在跳跃。⑧
可以说,这是一种未经命名的色情,还没有发育到足以成为任何更为实在的想法。这种具体、细腻、无法说出的性感造成了其想望对象身份的含混不清:母亲、姐姐、情人。或许有趣的地方还不仅在这里——这只是一种可以通约和共同感知的骚动,而在于这种感觉与身历的历史事件相关话语的嫁接及其后果:一种诗歌的政治修辞术。
同时,这也是旁观者对政治的一种有效的解码术,打入宏大叙事话语内部,有意肢解、剑走偏锋,从而有效溢出原有的叙事模式,并避免了红卫兵诗歌和朦胧诗书写的单一化立场——热爱、反对或者二者的杂糅。追忆本身就是一次互文行动,因此,第三代诗人在书写文革时的主要表达策略是戏仿。作为一种互文性修辞,戏仿常常被细化为戏拟和仿作,体现为在现有文本中使用前文本并对前文本进行转换和模仿的派生式(相对于引用和拼贴的共生式)互文。戏拟是出于玩味和逆反而对原文进行转换或扭曲,从而达到喜剧性的讽刺效果(如前引柏桦的诗);仿作则是“从模仿对象处提炼出后者的手法结构,然后加以诠释,并利用新的参照,根据自己所要给读者产生的效果,重新忠实于这一结构”。⑨在这些旁观者的话语实践中,这两种方法常常彼此不分,加之其抒情姿态常常是严肃与调侃兼而有之,所以,这里不再加以区分。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作为文革旁观者的经历对第三代诗人的思想观念和话语实践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他们的历史(童年)创伤经验被遮蔽本身就显示了历史进行集体发言时整合能力的缺失和这种经验的异质性。在这个意义上,重写文革主题不仅必然地葆有延续人类记忆的意义,更是借助这种容纳了自身当下境遇的历史再传递,讲述自己曾在历史宏大叙事中被忽略不计的故事,并容留更加细小却足够独特的经验。还有一点必须注意,由于这一经验事实的发生出现在童年,从精神分析学的观点看,不仅会在日后的行为中不自觉地流露,而且可能带来某种性格结构。对于写作者,尤其是童年经验有着特殊意义的诗人来说,这种力量对其写作的影响更不可小觑。如果旁观者使得这些经验呈现出来,就意味着它们必须使用他们自己的话语方式、修辞系统,并与当时的历史境地建立必要的上下文关系。也就是说,旁观者相对于先在发言者的种种“特异姿态”,不单单是历史遗留在他们身上的必然印痕,同时也是一种更为准确、丰富的标识,来达到凸现自身的需要。
注释:
①当然,这首诗的主题与文革文学的差异也是十分显明的,将在后文作具体论述。
②巴赫金著,李兆林等译:《拉伯雷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24页。
③约瑟夫·布罗茨基著,王希苏、常辉译:《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漓江出版社1990年版,第558页。
④柏桦:《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01年版,第14页。
⑤这些都是《今天》作者群的先驱食指的代表作品的名称。
⑥钟鸣:《旁观者》,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776页。
⑦王家平:《节日庆典与广场狂欢——红卫兵诗歌的精神特质之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1期。
⑧柏桦:《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01年版,第13页。
⑨蒂费纳·萨莫瓦约著,邵炜译:《互文性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