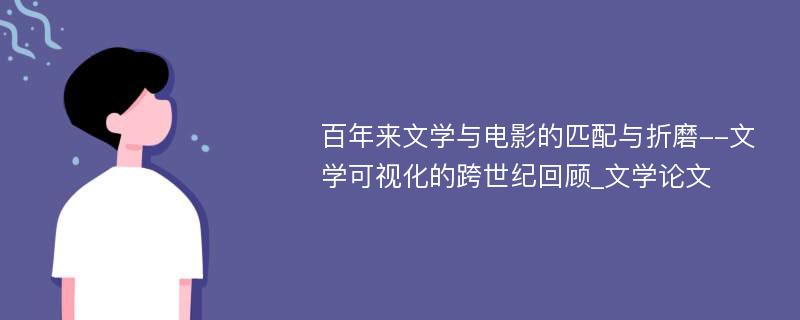
文学与电影的百年匹配与折磨——文学影像化的跨世纪回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论文,跨世纪论文,影像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百年前,在法国巴黎迦夫埃昏暗的地下室,卢米艾尔兄弟摄制并且公映了世界第一部电影。从此,文学——尤其是小说与电影之间,便呈现出意义明确但却若即若离、似远似近的纠缠甚至是折磨的关系。这里所谓“意义明确”指的是——文学与电影的叙事话语之间相互承袭和借鉴的技术性关系。
一
16世纪起始,中国的造纸与活字印刷术进入西方后,掌握文学的叙述能力即等于掌握了符号性的权力。于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或文字“作者”开始出现——他们不再是“三一律”时代那种古代戏剧、史诗、传奇故事的忠实记录者,也不再是抽象意义上的美学加工者或艺术模拟的代言人,而是成为一个对“自我”有坚定自觉的“世界创造者”。他们在文学中创造世界,文学家是他们营造出来的世界造物主。在写实主义时期,文学甚至还企图营造虚构的世界,并设想将那虚幻的“真空”落实到活生生的现实世界中。必须看到,这种虚拟的创造,正是文字的符号权力被推向极至的最夸张时刻。
文学家以文字叙述故事,而电影则用形象的视听画面描绘故事。由于文字与画面之间存在着分合难定的暧昧与紧张关系,于是电影和文学之间也就展现出独特的爱恨情仇。固而,它们相互之间的追逐、模仿、躲闪、离弃、折磨和创新等等演进过程,也就成了不但是研究电影,同时也是研究文学的人不能不必须去注意的时代课题。
一百年来,电影逐步由从属于戏剧、从属于文字创造的叙事与知觉逻辑中挣脱,获得空前的自主性。它不但获得与文学足以相伴的语言方法以及感知形式,甚至还穿透文字世界,单独悬浮在艺术的境界当中。由于电影语言方法的催逼,文学也不得不在创作类型、叙述逻辑、想象力的开放等方面持续推展。从文学生存的意义看,电影的进步乃是防止文学创造源泉枯竭的关键。
回顾电影语法及其图像思维方式的演变,我们则会发现,默片时代的电影,本质上乃是戏剧内核的延伸。缺乏声音伴陪的默片画面几乎无法表达任何具有时间以及思维纵深的事务与内涵,而只能充当模拟戏剧夸张式表达的单元而已。随着有声电影的出现,电影的进步日趋快速。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意大利为始的电影前卫(先锋)运动,真正开启了图像语言与文字语言的竞争。
大战后的电影艺术前卫运动,应当被视为一种对美学新领域的试探。举凡文学的叙事方法,无一不被电影所试验、创新和扬弃。这个阶段也是电影导演自我定位为电影作者的阶段——正如图像语言的工作者和文字语言黄金时代的小说作者一样,他们掀起某种先锋运动的目的,是企图建造出以自我为中心、为内核的语言及思考逻辑。
到本世纪尾声之际,电影的科技、特殊效果处理,尤其是电脑制图科技更加发达,我们几乎能相当肯定地说,如果文学是资产阶级文明的最高文化形式,那么,电影即是电子传媒时代的最高文化标志。因此,电影与文学之间是存在莫大竞争的。这种竞争,电影语法和叙事语境的发展可作证明。而且在电影的胁迫之下,文学的创新过程也是一种有力证明:捷克作家昆德拉刻意要创作一部不能被改编的文学小说;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安德尔·加缪的获诺贝尔奖的文学作品《局外人》、《堕落》、《瘟疫》等等,皆难套搬银幕;爱尔兰著名作家捷姆森·乔依斯的意识流作品,如《尤利西斯》、《菲内根的觉醒》等,其内容的晦涩程度,是电影语言根本无法企及的;美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汤姆森·富尔森·艾略特为避免电影的追逐,而将他的文学想象力,向无限的、几乎无法确定的、甚至没有形体的想象中的文学世界推展——这或者可以说,都是文学家在有了电影的竞争之后被诱发出来的文学独有的创造潜能。
二
由于电影和小说的种种竞争性的存在,观看电影也就成了观众探索两种语言叙事差异的最好时机。同样的故事,两种不同的语言和逻辑,它们的特点何在?它们的限制何在?诸如,由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改编拍摄的影片《布拉格之春》,原著本义大量流失,致使小说的文学叙事主旨得不偿失。不过,片中男女主人公车祸死亡的一幕,电影的宗教意象,却如神来之笔,甚至超越了昆德拉本人的文学创意。再看根据麦诺·麦克宁原著《大河之恋》改拍的电影,小说原品高度诗意化,其编导罗伯特·雷德福只能加添情节,以使它更易于呈现故事节奏,但与此同时却显示出电影语言的局限。
文学与电影在语言和逻辑上相互竞争追逐,其演变过程大大丰富了文字及图像这两个异同语言世界的叙事能力。甚至,也还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人们的感知能力。此外,电影与文学长期以来也还从事着对观众与读者的竞争。过去,文学读者大量流失,文学逐步走向凋萎,每隔几年社会上便间歇性产生所谓“文学死亡”等等悲观论调——其最大的论据,就是电影抢走了阅读者。
难道,电影与文学之间真的如此敌对不堪?事实上,在强势的电影视听文化抢占了大批文学读者的同时,它也在为文学创造出更多的“立体”的全方位的读者。单以欧美国家为例,目前它们每年平均拍摄一千部电影,一千部电影就意味着一千个故事。而这些故事多由电影商人指令编写或征求剧本,但是其中可用的剧本往往有限。于是,古典小说、经典作品以及创新的通俗小说等等,就成了电影剧本的最主要来源。由于电影的缘故,文学又找回了它的第二个春天。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我们甚至可以讲,文学是电影的软体(“软件”)及研究发展部门,也是电影的题库。特别是近年来,电影工业的系统化行销思路日趋完善,在推出电影的同时,有关的小说也在大量廉价问世。具有国际化性格的电影,遂将各国小说推向了整个世界。
以近年来的电影为例,就可以看出它对文学的帮助。小说如《无是生非》、《暴风雨》、《此情可问天》、《呼啸山庄》、《吸血鬼》、《三剑客》、《情人》、《萌芽》、《人鼠之间》、《纯真年代》、《海狼》、《大河之恋》等等即拍成了电影;根据新经典小说拍摄的电影还有智利前总统侄女伊莎贝拉所著《精灵之屋》、英国波依德的《非洲善人》、中国台湾谭恩美的《喜福会》、中国大陆余华的《活着》等等;由通俗畅销小说改编拍摄的电影更多,如美国的《与狼共舞》、《生于七月四日》、《侏罗纪公园》、《律师事务所》、《本能》、《太阳升起》、《亡命天涯》、《绝命追杀令》、《爱国者游戏》、《天生杀手》、《阿甘正传》等等。尤其是《生死时速》、《亡命天涯》、《阿甘正传》和《麦迪逊郡桥》等文学作品,其原创故事不但是制片商们眼中的抢手货,而且影片也确实创下了空前的票房纪录。
美国电影制片商们堪称经营有术,他们瞄准和死盯住时下畅销通俗小说,如美国畅销书王约翰·格雷塞姆的《委托人》,珍妮·史密丽的《千亩地》和金·沃泽克特的《来自乡村俱乐部的字条》等,有意思的是,继《麦迪逊郡桥》之后,罗伯特·詹姆斯·沃勒又将推出他的第二部小说《慢步华尔兹》,而当此书尚在腹中打稿时,就已经被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敲定下了拍摄版权的合同。
三
眼下电影界流行着一句脍炙人口的“大白话”——“Forrest Gump(阿甘)才编写电影剧本”。小说因电影而骤然窜红,电影则依靠小说为“题库”大走运气,两者已经成为时下国际电影界最佳搭配和组合。随着电影的日益全球化,小说也比以前更容易跨越国与国的界限。中国大陆影院自1995年始,引进了10部国际大片,以记帐方式进行签约放映;台湾近来的电影小说也迅速成为一种重要的出版类型:《金色豪门》、《辛德勒的名单》、《蜘蛛女之吻》、《大河之恋》、《纯真年代》、《巧克力情人》等等,都因电影的推动而翻译面世。
由此看来,与文学竞争阅读者的电影,现在反过来会帮助文学寻觅正在消失中的读者了。面对这种情形,我们不禁想起本世纪20年代廉价版“企鹅文库”的出现——当时,英国的整个国势发展仍处于巅峰状态。繁荣造成生活多样化,印刷工业日趋发达,使得通俗廉价的所谓“纸浆文学”大盛,装帧精致的传统文学读者日稀。于是,廉价纸版面的“企鹅文库”遂告出现。“企鹅文库”是精致文学向当时最前哨的印刷造纸工业的妥协,借着这种妥协,传统文学成了平常百姓可以读后便弃的读物,同时也扩增了无数新文学读者。
昔日传统文学借“纸浆文学”的形式而“循环”复生,如同今日的小说,借着电影视听艺术,再造第二春。在文学的社会学意义上,这等于文学本身在结构上新加了一个电影的结构。这也是一种文学关系的改变——文学除了有自足的发展逻辑外,同时也受到电影的制约。用发展的眼光看,电影将成为文学的过滤网,能改编为电影的,对作者而言,乃是名利双收的保证,不能通过这个过滤网的,则难免寂寥没世。
还应注意到的问题是,所有的文学作品,在完成创作并发行之后,都将面临着一个“遗忘期”的挑战。而其中绝大多数的文学作品都将会被人遗忘或者淘汰,只有极少数不会恶遭筛除。往后,电影在这个问题中所扮演的角色,显然会逐渐加重,这样的时间越长,电影对文学的影响也就会越大。文学的“遗忘期”在发达的电影工业国度里,表现得更加充分和具体。好莱坞作为美国文化的典型代表,在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从文学作品中提取电影素材的例子俯拾皆是。
1915年著名电影导演D·W·格里菲斯的电影史诗《一个国家诞生》,是取自弗兰克·E ·伍德的《民族人》和托马斯·逖克逊的《豹斑》两部小说。从此,文学与商业电影之间搭起一座必然成功的桥梁,并且由此文学电影开始形成自己独有的风格。这一风格的起点,是以40年代后期的雷蒙·钱德勒、格雷厄姆·格里纳的文学作品改拍成同名电影《酣睡》和《布赖顿岩石》为代表。
为什么好莱坞单单会在40年代末形成一股“文学电影”的巨潮呢?这里,我们需要稍微注意一下当时美国社会的时代背景——经济大萧条已悄然平止,美国人民开始充满信心地逐渐从痛苦、忧虑和贫穷中振作起来,面对眼前一派崭新的勃勃生机,好莱坞电影人自然不肯错过此刻良机,于是,早已酝酿好的电影“黄金时代”开始了。其实,美国电影的黄金时代堪称转瞬即逝,这一时期真正的黄金热点,甚至都没有能够持续一年。但必须清楚地看到,该黄金时代的每一部电影精品,都是以文学作品为先导的,如《乱世佳人》、《绿野仙踪》、《关山飞渡》、《呼啸山庄》、《间奏曲》、《米诺契卡》、《黑色凯旋》、《史密斯先生来到华盛顿》……只可惜,这种乐观的电影时局,很快就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毁灭了。
进入60年代,在反主流文化思潮的影响和冲击下,文学家弗·纳波夫的小说《洛丽塔》、艾里亚·卡赞的《欲望号街车》、刘·华莱士的《宾虚》、亨利·菲尔丁的《汤姆·琼斯》、D·H·劳伦斯的《恋爱中的女人》、彼埃尔·布尔的《桂河大桥》等等文学作品被相继搬上银幕。
到了80年代,好莱坞银幕上掀涌起回归怀旧的情绪,于是伊萨克·迪纳森的小说佳作《印度之行》、《走出非洲》,朱迪斯·格斯特的《普通人》,拉雷麦克默屈里的《感情关系》,英格玛·伯格曼的《芬妮与亚历山大》,欧内斯特·汤普森的剧本《金色池塘》,伊萨贝尔·科勒特的《猎鹿人》等等,即成为当时最具特征的电影代表作品。
90年代,好莱坞更是频频出现轰动国际影坛的扛鼎之作,而这些电影均以文学——小说为基础,如《与狼共舞》(作者为自由撰稿人迈克尔·布莱克)、《好家伙》(作者为记者尼古拉斯·皮利吉)、《苏醒》(作者为医生奥立佛·皮利吉)、《命运的逆转》(作者为律师艾伦·德肖维茨)、《俄罗斯之屋》(作者为记者约翰·卡莱)、《待到重逢时》(作者为女作家朱迪思·克伦茨)、《辛德勒名单》(作者为托马斯·金内利)、《侏罗纪公园》(作者为迈克尔·克赖顿)、《阿甘正传》(作者为温斯顿·格卢姆)、《麦迪逊郡桥》(作者为罗伯特·詹姆斯·沃勒)等等。
好莱坞电影的命脉究竟掌握在谁的手里呢?一部炙手可热的文学作品,一位知名度甚高的作家,本身就是电影围攻的热点。单以好莱坞的制片商而言,他们敢于用天文数字一样的价码,买断一部文学作品甚至故事构思,这对于文学来讲,不能不是一个相当富于刺激的挑战。这样看来,百年来的电影进程,不但是小说与电影之间的互动、刺激、影响、渗透、匹配和折磨的历史,而且也还是商业意识对于文学的利益怂恿,以及文学对商业物欲全面接受的历史。
四
目前,电影与通俗文学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影响已十分明显。通俗文学的叙述形态常常模拟电影的画面和段落经营,因此,观众在阅读电影精品《沉默的羔羊》、《单身女郎》、《侏罗纪公园》、《揭发真相》、《亡命天涯》、《真实的谎言》等影片时,则会发现,这些小说原创和改编拍摄的电影所传达出的意象,也即镂刻在心智模板上的效果,是完全相仿的。一部畅销的通俗小说改拍电影,分镜头剧本的改编也只要照搬原意即可,这无疑是电影对小说的一种吞噬。当然,这种吞噬并不仅仅是一种电影技术单元上的显示,而是社会意义上的,亦即是电影文化意义上的呈露。
我们以日本通俗小说名家松本清张创作的小说为例,来看看他的作品与电影的关系。据统计,松本清张一生创作的764部作品中, 在日本被改编拍摄成的影视作品的数量,定占位首。 经其文学作品改编的500余部影视作品,宛如“社会形象”的森林,收拢且抚慰了日本战后破败残缺的“母性风土”。赏析松本清张的电影作品,我们会发现,他的作品最注重的是人情和人性。如影片《天城奇案》、《砂器》、《眼之壁》、《零的焦点》、《雾之旗》、《影之车》、《疑惑》等等,都是这方面的突出范本。问题在于,小说在布局和构架的趣味上,确实易于模仿,但是人性与人情,则是电影改编的最难空间。
相比松本清张而言,法国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文学作品,则更易于搬上银幕,因为她的文字本身,就犹如一格格排置好的电影画面。诸如前不久公映的《情人》、《广岛之恋》、《如歌的行板》、《孩子们》、《印度之歌》等等。
从视觉感受上看,玛格丽特的电影仿佛无一不是情与死的行板,而且影像化的叙事内涵,也都着力突显着人物情感的单一故事,甚至仅仅与性有关。但问题在于,我们在阅读玛格丽特原著的时候,从她的字里行间,的确搜寻不到如此“单纯”直面性爱的东西。玛格丽特的文学母题,虽然没有她所要阐释的什么社会必然,但有一点极其明确——玛格丽特在殖民主义者统治下的印度支那长期生活的经历,决定了她文学创作中的严肃和公正性质。因此,我们或许能够认为,玛格丽特的电影(他人改编拍制)决非玛格丽特文学,其电影缺少玛格丽特文学中罕见的对女人纯情欲望的叙述。
提到通俗电影的兴盛,我们不能不联想到中国大陆影坛的王朔电影。王朔把他电影作品中的人物推到商品化社会的中间地带,并且赋予他们怀疑主义的人格。他们撕去信仰和道德规范的面纱,给当代无处皈依的心理情结提示了亵渎的满足。王朔电影的主角们,在社会中没有确定的位置,象《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里的张明、《轮回》里的石岜、《大喘气》里的丁建、《顽主》里的于观、杨重、马青等等,无一不是“躲避崇高”的“边缘人”。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这里说的“躲避崇高”的“边缘人”,只是经过改编之后的王朔电影中的形象,而并非王朔原作中的人物。事实上,“躲避崇高”也好,“边缘人”也罢,那都是影评人抬举“电影的论语”,这里的评语差不多跟王朔原作关系不大。王朔仅仅是凭着直觉在价值倾斜的状态中,认同了生活中的不完整性的存在,王朔笔下的人物不是有意识地用什么“躲避崇高”去观察和对待世界。王朔甚至没有能力将他的人物提携到这个份上。而经过改编后的电影呢?王朔的人物几乎纯情到了琼瑶作品的浪漫天地。
相对“躲避崇高”而言,我们自然会将审美的视界转移到中国著名导演谢晋创作的影片上面。谢晋曾讲过——我深信一部影片也是一次生命的燃烧。谢晋的这句名言是无可置疑的,但同时,我们也还必须看到并且不容否认,谢晋电影除了给观众以“崇高的使命感”以外,素来还给人一种“改编大师”的印象。自谢晋大师的成名作《女篮五号》、《红色娘子军》起始,到《舞台姐妹》、《青春》、《啊!摇篮》、《天云山传奇》、《高山下的花环》,一直到《芙蓉镇》、《最后的贵族》、《清凉寺的钟声》和1995年最新影片《女儿谷》等等,无一不是以文学作品为蓝本的影像精品。更值得注意的是,谢晋在从事电影艺术创作半个多世纪的漫长旅路上,居然能够一直纠缠和荡漾在文学的潮海之中,用文学精华滋养着自己的电影生命。
但遗憾的是,谢晋导演的这种崇高的使命感觉,除了只在《红色娘子军》、《青春》、《高山下的花环》等影片中有明显感悟之外,我们仿佛实在很难在诸如《牧马人》、《最后的贵族》、《芙蓉镇》等片中找到同样神圣、崇高的感觉,并且特别有所投入。至于谢晋1995年夏天执导的社会问题新片《女儿谷》,则更接近于一部“时事性新闻的纪录影片”而已。
艺术是有巅峰的,艺术生命的燃烧,会不会也能够在巅峰尽处燃烧殆尽?正如王朔“江郎才尽”一样,谢晋的影片是否也有自己的“客观规律”呢?好就好在,谢晋不同于王朔,他是不断用他人的文学生命之火来燃烧个人电影使命的;而王朔呢,全都“糜烂”于作茧自缚的所谓“痞子文学”当中了……
五
在电影艺术特有的叙事逻辑的主控之下,传统意义上的精典文学作品,也正日益受到电影商业化心理的刺激、推拿和反馈,并且还明显地逐渐朝着注重通俗故事——文学化情节的位置上漂泊和移动。比如中国知名作家王蒙——学界一向认为王蒙的所谓意识流作品,是最难入镜的文学作品。笔者在1995年8月对王蒙先生的一次采访中, 他也直言不讳,承认自己不是一个专意去写文学故事的人。他的数十部作品中,至今只有《青春万岁》、《选择的历程》、《高原的风》、《蝴蝶》是被改编成影视作品的。或许,王蒙的新作《暗杀》之类,正是冲破自己“不写故事”的前卫作品,至少,《暗杀》主题,俨然是一种商业性的征兆吧?
面对电影的商业化的普遍沦陷,自然也有个别优秀作家岿然清高,至少他们不情愿他人改编和动容(或曰糟践)自己的文学作品。特别突显的代表人物,是当代哥伦比亚的加伯利亚·贾西亚·马尔科斯,这位44岁盛年赢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拉美作家,一生广见,“游戏似地”居住过全球各地,承袭了加勒比海人讲故事的传统与听故事的习俗,凭借手中一枝健笔,游历于文学的茫茫沧海。
马尔科斯在文学叙事方面的独特语境,使得任何对他的文学作品进行改编的电影人,均实感不易。因为马尔科斯“魔幻现实主义”先入为主的导读影响,趋使电影人极难在他作品的字里行间寻觅到马尔科斯文学的“影视特性”。比如马尔科斯《伊兰迪拉》中钞票幻化成蝴蝶飞起,《罗马神迹》中小女孩儿死而复生,《意中人》里情到深处发热自焚的男子,《养鸽女传奇》中11年不睡觉,只要睡就有做梦预言能力的妇人,《有一双大翅膀的老人》里振翼飞翔的老人,《夏日保姆》中双重人格的保姆等等,都是马尔科斯文学语言上较难化幻成影视具象的内容。
马尔科斯的文学作品,即使改编成为电影,其西班牙语境笼罩下的历史与文化,也都不可能是马尔科斯文学本身意义上的实体。或许,我们可称马尔科斯的电影为其文学本身的颠覆与背叛——即“异化”。事实也是如此,不管电影怎样由小说“转换”过来,其间的语言差异,决定了两种门类的艺术相持的永久性对立。如果,小说中的主旨意义,包括叙事、结构等经过改编后,不复存在于电影之中,那么,文字与图像两者之间的矛盾,便会由此生发和扩展。必须指出的原则问题是——文学原著的主题情节、人物形象的塑造等等,如果不存在于改编后的电影艺术之中,就不能称之为“纯粹”意义上的改编。
对此,马尔科斯也承认,他认为自己在创作举世名篇《百年孤独》之前,他在写每一部小说时,或许每下一笔,都可能联想到电影的画面。但是,自《百年孤独》以后,小说与电影能够相互代换的传统信念荡然无存。这也就是说,不管其间的缘由如何,马尔科斯的文学,确实是一种不易“翻译”成电影的文字叙事作品。再深一步讲,就是文学只要保持其独立性,电影则极难渗透进入。但事实上却不那么简单,文学从来都是耐不住寂寞的,尤其面对电影的无限诱惑。所以,电影的日趋商业化,也是在于文学本身的“媚俗”。因为文学(小说)明白,只要进入大众传媒的影像层次,便有“出人头地”之机。
文学是最难电影化的东西,只要改编,它就会成为一种质的转换。众所周知,电影、文学和戏剧相互之间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它们当然是完全不同的艺术品种。读者可以根据小说作品中的人物、故事产生不同的想法和理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可是一旦将文学作品生硬搬上银幕,该作品便被电影定型化了,文学艺术自身的张力和外延即被局限住了,这恐怕是对文学的变相扼杀。但文学改编电影也有唯一益处——电影高速发展的同时,也胁迫着文学向纯娱乐性推进。今天的人们,也已经普遍认同了这一点。但同时,却忽略了文学自身艺术特性的升腾。在商业化社会飞速发展与升华的状态之下,人们已经顾不得文学本该拥有的纯粹的“艺术”呻吟了。
既然谈到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一纯粹的学术问题,那么,我们也就不妨对这个接受美学范畴的内容,进行一下深究。
对于这同一个问题,艺术家与观众(读者)的接受心理不尽相同。艺术家(包括小说家)在阅读生活之后,就走火入魔般地去寻找人与世界的关系的“熔点”;也就是说,艺术家只是仅仅关心他们的艺术作品对我们人类世界的重新理解。小说家的文字也好,电影的照像也好,艺术家的直接目的,都是为了使观众(读者)确信,他们的艺术作品就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对于这一点,安德列、巴赞、戈达尔、雷乃、路易·德吕克、格里菲斯、阿兰·罗伯格里耶等等电影艺术大师早有论断在先了。
观众(读者)对艺术作品的感受却与艺术家们迥然相异。通常,读者在看过文学作品之后,便会对将由此改编的电影期望过高,但往往,这种想法确是不符合实际的。艺术家在动笔之前,他面对的只是一个世界,而读者呢?他们看到的,是经过加工之后的真实世界。文学创作的最初,是一种单纯和直接的心理观照。而电影则是通过一整套社会机构以及个人对每个画面都实施了潜在审视(督检)的东西。从本质上说,电影只是一种创作形式,是一系列源自社会想象的集体性画面的影像与思想。
从我们所探讨的这种意义上看,电影显然不是一个被确定的指标,“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就极有针对性了。电影是我们观众(读者)生活环境的一种无秩的反应。对观众(读者)而言,阅读文学作品可以是个人的审美或者再创作的(接受心理)精神的劳动;而电影则是强加给你的,电影的潜在目的,有显著的推销功用。电影为我们的情感冲动设置了一片缓冲的地带。而文学却趋使我们直接进入“极乐世界”……
电影入世百年以来,一直处在跟文学既联合又斗争的局面当中。电影的叙事系统呢,严格一点讲,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逐渐浮显出来的。也就是说,电影语言的叙事能力,不过只有半个世纪的生成和发展履历。至少,在文学和电影生命里程上看,两者间的相互“翻译”,确实是一个相当难调和的客观存在。
如果,文学作品所探讨的内容,是影视叙事语言上发展较为成熟的问题,那么由电影来进行表达,可能不会太离谱。可是,文学作品本身倘是符号式的,或是充满联想与诗意性质的,那么要想进行相互间的所谓“翻译”,就需要审慎斟酌了。换言之,如果文学所要再现的,是某种传统意识下所产生的问题,再由对电影语言较娴熟的人才改编成电影时,则可能不会糟蹋这部文学作品,否则,文学的终极命运,是不可想象的;与此同时,以文学为依托的电影未来的命脉,必然也是惶惶不可终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