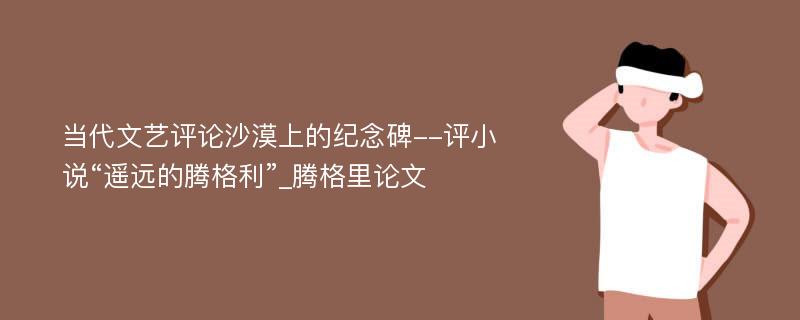
当代文艺评论 大漠上的一座丰碑——评长篇小说《遥远的腾格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漠论文,一座论文,丰碑论文,长篇小说论文,文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蒙古作家协会主席扎拉嘎胡同志在为蒙古族青年作家敖·奇达布日的长篇小说《遥远的腾格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5年5 月版)作的“序”中写道:“《遥远的腾格里》的出现,犹如在大漠深处挖出了一座年久的丰碑。碑上镌刻着活佛喇嘛唱不尽的悲欢,痴男怨女说不完的残景。使得碑柱既沉重又飘摇,既清冷又严峻。”
《遥远的腾格里》以座落在腾格里大漠上的穆吉朗寺第七世葛根(活佛)桑布道尔吉与牧羊女高娃曲折缠绵的爱情故事为主线,描写了该寺喇嘛及寺庙周围牧民们从本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所经历的风风雨雨,掀开了寺庙这一神秘世界的帷幕,反映了蒙古族人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兴衰荣辱,揭示了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给人以深刻的启迪。作者以娴熟的艺术表现手法,塑造了桑布道尔吉、高娃,尼玛等具有民族性格的人物形象;以清新优美的语言,描绘出一幅幅大漠风景画、风俗画,从而使这部作品具有了浓郁的民族风格,给读者以新颖独特的美学享受。
(一)
《遥远的腾格里》的深刻思想内涵,主要是通过作品的主人公、穆吉朗寺的葛根桑布道尔吉这一典型形象去显示的。
桑布道尔吉原本是一个普通牧民的儿子,但在他出生后一年零四十九天,就被按照喇嘛教礼仪,指定为穆吉朗寺第六世葛根的转世灵童,继为第七世葛根。他在父母身边的那段童年生活是快乐的,额吉(母亲)每天背着他在美丽的查干淖尔湖边放牧,他常常依偎在额吉温暖的背上,在她那优美、动听的歌声中甜甜地进入梦乡。醒来后,就跟着额吉在沙窝里捡沙葱,捉迷藏,从高高的沙丘上向下滑……小桑布道尔吉六岁那年,被用八抬大轿接到穆吉朗寺,开始了他的青灯生涯。他从此失去了母爱、父爱,常年累月与古佛青灯为伴。他常常是在恐惧中睡去,在恶梦中惊醒,他哭喊着寻找额吉,泪水浸湿檀香木枕头。后来,在经师扎木苏大喇嘛的长期教诲熏陶下,桑布道尔吉变成了一个身披黄缎袈裟的泥塑,感情世界如同一片荒凉的沙漠。
桑布道尔吉十八岁那年夏天,在查干淖尔湖边偶然同美丽的牧羊姑娘高娃相遇,他年轻的驱体里第一次产生了一种异样的莫名其妙的躁动,“第一次感觉到自己装满经文、经律的内心世界里好象缺少了点什么。”然而,当远处传来古刹钟声时,他无可奈何地搓动着手里的玛尼佛珠,默默地离开了高娃。桑布道尔吉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搏斗,人的本性终于战胜了“神灵的力量”。他深深地爱上了高娃,爱得那么真诚,那么热烈。美丽的查干淖尔湖边,留下了他们爱情的深深印迹。他在高娃面前,逐渐变成了一个充满活力、充满七情六欲的人,但一回到穆吉朗寺,他又俨然是一位众人信仰的四大皆空的神。
桑布道尔吉虽然被众人尊为“大漠一神”,而且据说他只要摸一下谁的头顶,或者为谁念一段经,就能帮助那人消灾降福。然而,他对旗札萨克辅国公(王爷)的独眼公子这只在大漠上横行霸道为非作歹的狼,竟然束手无策。当他意识到自己将因与高娃的幽会而惨遭独眼公子的毒手时,他听从了侍僧尼玛的劝告,远离开穆吉朗寺,前往青海塔尔寺修行去了。七年后的一个秋天他重返家乡,亘古大漠已旧貌换新颜,只是他心爱的高娃姑娘已成为他人之妻。他明知高娃生的巴特尔是自己的儿子,却又不能相认,这更使他感到悲哀、怅然。当文明之花绽开在腾格里大漠时,穆吉朗寺的大门悄然关闭,一些中青年喇嘛纷纷还俗。桑布道尔吉也不象过去那样念经,摸头顶,给牧民以心灵上的安慰和麻醉,而是实实在在地为牧民做好事。他身背装满药的褡裢,骑着骆驼走在人烟稀少、缺医少药的大漠,为人治病,救死扶伤,博得了人们的爱戴和尊敬,成了远近闻名的“大漠神医”。他由原来的“神”,还原为人。他从人间烟火里,从人们朴实的生活中得到启示,懂得了“世上有信神者,也有无神论者。信与不信是由个人的信仰决定的。”他以往那根深蒂固的宗教观开始动摇了。
1966年,中国大地上刮起一场铺天盖地的“文化大革命”风暴。腾格里大漠上的人们自然未能幸免于难。善良的人们被打成“牛鬼蛇神”,惨遭毒打。桑布道尔吉曾无数次地长跪在佛像脚下念经,求菩萨保佑好人平安,却始终无济于事。桑布道尔吉面对这一严酷的事实,昔日长期形成的宗教观彻底轰毁了。他愤怒地指着寺院中菩萨的鼻子呼喊道:“你口口声声说普度众生,可你拯救过谁?众生受难,你为什么不发慈悲?……这一切都是骗人的、虚伪的、假的……”这些对宗教迷信的揭露和批判,由于出自“大漠一神”桑布道尔吉之口,显得格外有力,字字句句震天撼地。
1976年10月,全国人民终于将危害十年之久的“四害”,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党的宗教政策又回到了腾格里大漠。桑布道尔吉经不住两位老喇嘛的苦苦哀求,“无可奈何”地回到穆吉朗寺。但此时的他,已清醒地认识到了“佛门净地”和葛根的真实面孔。八十年代中期,六十高龄的桑布道尔吉葛根回顾自己一生走过的曲折道路,终于大彻大悟。他明白了,“不管是葛根、僧人、俗人,都是一样的人。只不过社会生活把一些人武断地推上了另一个偶像、图腾的地位,以此来迷惑别人,也欺骗了自己。一些人追踪这虚无飘渺的东西,在人间另一个世界里苦度一生;一些人则中途醒悟、叛逆,解脱自己;一些人则在神与人之间徘徊一生……”就这样,《遥》作通过桑布道尔吉整个一生的旅程,向人们揭开了神佛身上那层神秘的面纱。不仅如此,《遥》作还或多或少地描写了穆吉朗寺的大喇嘛扎木苏、二喇嘛德德木、三喇嘛章古达及其他小喇嘛们,同生活在查干淖尔湖畔的牧民妇女之间的爱情悲剧,唱出了一曲曲令人回肠荡气的哀歌,从而启示读者去正确认识宗教对人性的扭曲。
《遥》作对宗教问题的探索的深刻性,还在于它形象地显示了人们要彻底摆脱神学束缚的艰巨性和光明前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国历史跨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桑布道尔吉又稀里糊涂地被穆吉朗寺的喇嘛们扶上葛根的法座。腾格里大漠中的人们还象三十年前一样,对葛根和菩萨无限崇拜,而且在朝拜的人流中,还加入了青年牧民和少年。作品告诉人们,随着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的消亡,随着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宗教产生的条件也将随之而消亡。但是人们的思想意识的发展,总是落后于物质生活条件的发展。宗教意识作为一种“更高的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恩格斯语),不会也不可能马上消亡。它的生命力在一定范围内还没有衰落,它的消亡需要漫长曲折的历程。这正如作者在《遥》作卷首题辞中指出的那样:“世上是否有神?若追踪其根迹,或叛逆其旨意,同样要经过艰难而漫长的跋涉……”然而,宗教消亡道路的漫长,不等于到达目的地的无望。《遥》作结尾处透露了这样的信息,由于党的宗教政策的落实,穆吉朗寺各殿顶端仍是那般金碧辉煌;主殿潮格沁大殿顶端的镀金法轮,仍是那般闪烁着金辉,可好象又渐渐失去了昔日那神秘的色彩了。“桑布道尔吉葛根圆寂时,并没有留下遗嘱,可谁也没有提及葛根的‘转世’之事”。显然,无论是桑布道尔吉还是穆吉朗寺的喇嘛们,对葛根的迷信程度已经有所减弱,除了少数人之外,人们不再相信上帝真实地存在于我们之上。《遥》作预示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文化知识的普及,宗教的本质将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披着圣光的上帝真身,在人们的意识中将逐渐淡化、消失。“菩萨保佑”一词,将不再是虔诚的祷告,而仅仅表示一种良好的祝愿。那时,宗教对人们头脑的束缚,将成为遥远的往事。
(二)
《遥远的腾格里》中仅次于桑布道尔吉的另一个主要人物,即本书中的女主人公高娃。她的形象从另一个侧面显示了作品的深刻内涵。
高娃出生在位于穆吉朗寺附近的查干淖尔湖边一位普通牧民家庭。她聪明,美丽,活泼。在富有浪漫色彩的查干淖尔湖边,她象一只欢乐的鸟儿,愉快地唱着她内心深处的歌。在她十八岁那年的夏季,与被称为“大漠一神”的年轻葛根桑布道尔吉相遇并相恋。她虽然知道身为高阶层喇嘛的桑布道尔吉不能与她最终结合,但她仍然深爱着这位“桑布哥哥”。她的内心一片纯洁,而且带着天生的野性,只要有爱情存在着,其它一切都不重要。但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她的命运飘忽不定,她被王府抓去做侍女。旗札萨克王府保安队长独眼公子,还带领人马来到高娃家,残酷毒打高娃的额吉银吉玛,任意宰杀高娃家的羊。作为“大漠一神”的桑布道吉尔也无可奈何。后来,聪明的高娃从王府逃了出来,可桑布道尔吉却被迫远行塔尔寺。当她最终听到“桑布哥哥”被害死的消息之后,她唯一的一线希望泯灭了。这时候她已经有了桑布与她的爱情结晶小巴特尔,在悲苦与绝望中,她嫁给了最初向她提过亲的掌驼手巴拉吉。酗酒成性的巴拉吉,不仅未能给她那满是创作的心灵以抚慰,反而使她陷入了更深的痛苦之中。
而富有戏剧性的是桑布的归来(这已是七年以后了),使她再次悲喜交加。愁的是苦苦等待的恋人迟迟归来时,自己已为人妻,喜的是能与他重逢,那是做梦都想的。就这样,他们俩心中几乎早已熄灭的爱情之火又复燃起来,使这两位昔日的恋人又得到苦涩的爱情。新中国成立之后,高娃进入了旗少数民族干部学校学习,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成长为一名出色的蒙古族妇女干部,并在共同工作与奋斗中,与以前帮助过她的尼玛逐渐产生了爱情。她勇敢地摆脱了不幸的婚姻,与巴拉吉离婚,同尼玛结合。这次的爱情与前两次是不同的。同桑布道吉尔的恋情是她少女的心中自然产生的,但桑布道尔吉的特殊身份使她不能够得到他。而与巴拉吉的结合更是在被迫无奈中。同尼玛的结合是在共同生活与工作的基础上建立的爱,她是十分珍视这爱情的。桑布道尔吉也深深知道他与高娃的距离越来越远,他也为高娃的幸福而祝福,但落后的生产方式夺走了尼玛的性命——这位人民的好儿子,在带领牧民挖井时不幸遇难。高娃又一次趺进命运的低谷里。
接踵而来的“文化大革命”,又把高娃与桑布道尔吉推向一起——他俩同时被打成“牛鬼蛇神”。在高娃生命垂危的紧急关头,桑布道尔吉细心照料她,并给以精神的寄托。当黑夜过去,新的曙光来临,这患难与共的两颗心终于贴到一起时,生活又以不同的方式使他们无法结合——桑布道尔吉已丧失了性功能,变成了“半个废人”。高娃又一次品尝到了宗教带给她的苦果,虽然她未必明确认识到这一点。值得庆幸的是,粉粹“四人帮”后,她在政治上获得了彻底解放,儿子巴特尔成为大学教师,两个女儿也都上了大学。这是作为当年查干淖尔湖畔牧羊女的她,连做梦都想不到的。
高娃的命运是具有典型性的,读者从她半个多世纪的人生旅程中,不仅看到生活在腾格里大漠上的妇女们的命运,而且看到了整个蒙古族劳动人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坎坷经历和兴衰荣辱。解放前查干淖尔湖畔的牧民们,无不深受宗教迷信的束缚和摧残。不但高娃与桑布道尔吉虽有刻骨铭心的爱情却不能结合,高娃的额吉银吉玛也是如此。她年轻时与穆吉朗寺的二喇嘛德德木相恋,并生下了高娃,但俩人始终未能结合,更不能使父女相认,享受天伦之乐。与高娃一样善良而美丽的牧羊女哈申其木格,被旗札萨克王府抢去,强娶为辅国公(王爷)的小妾,受尽凌辱……读者还看到,解放前,“腾格里大漠上到处兵匪骚乱,抢掠财物,宰杀牲畜,欺辱百姓,奸淫妇女,无恶不做。”独眼公子带领王府保安队兵痞,闯入佛门圣地穆吉朗寺,毒打喇嘛,抢劫财物,就连金佛像都不放过。全国解放后,高娃当上了国家干部,桑布道尔吉还俗当了医生,还被选为旗政协常委。腾格里大漠上的人们,也都过上了好日子。“文化大革命”中,公社党委书记罗布桑及桑布道尔吉、高娃等善良的人们惨遭迫害,昔日洗涤净化众生心灵的穆吉朗寺,变成了善良人们遭受磨难的地方。1976年的春雷,驱散了“四人帮”喷吐在中国上空的乌云,高娃及腾格里大漠上的蒙古族人民,又获得了第二次解放。还俗的穆吉朗寺二喇嘛德德木同哈申其木格结婚,喜得贵子;巴拉吉改掉了酗酒的毛病,与达日玛结合,过上了好日子。
高娃及腾格里大漠上的人们半个多世纪以来所经历的风风雨雨,显示了一个平凡而伟大的真理:神佛不可能给蒙古族人民带来任何好处,只有紧跟中国共产党,推翻国民党反动派及蒙古族封建王公贵族“独眼公子”之流的统治,排除林彪、“四人帮”以及坏人宝力道之流的破坏,蒙古族人民才能走向光明,走向幸福。
(三)
《遥远的腾格里》在塑造桑布道尔吉、高娃等人物形象,展示生活在大漠上的蒙古族人民命运的同时,还以诗一般的语言,描绘出腾格里大漠变幻多姿的自然景观、描绘出蒙古族牧民中朴实淳厚的风尚习俗以及喇嘛教的种种复杂礼仪。读着这部小说,读者仿佛进入了一个神奇的世界,顿觉眼界大开,新颖无比。
小说一开始,就浓墨重彩地描绘了腾格里大漠那种奇妙的景象:“浩瀚的腾格里大漠,茫茫无垠,连绵起伏的沙丘一直延伸到天际。金黄色的沙漠与强烈的阳光组成了单一色的世界”。由于气候干旱,“刚刚长出嫩叶的牧草被烤黄了,枯萎了,骆驼背上那挺立的双峰倒下去了,牧人脸上的笑容消失了。”这幅大漠旱象图,是故事发生的本世纪二十年代腾格里大漠那萧条破败景象的真实写照,它为后来成为“大漠一神”的桑布道尔吉的出生提供了恰当的环境。宗教是在生产力低下,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们为战胜天灾人祸而创造出来的,为的是依靠神佛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马克思语)。由于久旱之后降了一场喜雨,而桑布道尔吉恰好在下雨那天出生,牧民们于是对朝格登大喇嘛关于桑布道尔吉就是已故的穆吉朗寺六世葛根的转世灵童的说法深信不疑。这幅大漠旱象图中,也隐隐流露出作家对这片土地的无限热爱和深切忧虑之情。而当作品中的男女主人公桑布道尔吉和高娃在查干淖尔湖边相会时,大漠上则是另外一番景象:“沙沟里一簇簇沙蒿、红柳、芨芨草、骆驼刺、沙葱争相吐绿,如同金黄色的绸缎上撒满了颗颗晶莹的宝石一般。查干淖尔湖象镶嵌在大漠里的一面镜子,在阳光下那么明净,那么耀眼。……湖面上一群水鸭在尽情地游弋着,嬉戏着,忽儿展开翅膀,拍打着水花飞向湖心茂密的芦苇丛里……羊儿、驼儿在湖边悠闲觅食……”这一切都是那般美好,就象作品中男女主人公此时此刻的心情一样,纯洁而无忧无虑。他们两人的爱情,伴随着这生机勃勃、情趣盎然的大漠景象而生根,开花了。后来,当桑布道尔吉被迫要远行塔尔寺,不得不离开他心爱的姑娘高娃时,大漠则又是另一番景象:“残缺的下弦月悬挂在灰朦朦的天幕上,清幽幽的月光淡淡地挥洒在莽莽苍苍的腾格里沙漠上,使沉寂的大漠更加显得深邃、凄然。”此时高娃姑娘的歌声,也失去了以往那明快、甜蜜、圆润,而是句句含着悠扬的苍凉,悠扬的悲哀。以至竟使得“残月沮丧地躲进云层里,湖边的骆驼高高扬起了头”。好的诗歌具有深邃的意境,但意境却并非诗歌的专利。好的小说同样可以创造出意境。《遥》的作者敖·奇达布日具有诗人气质,他以一支饱蘸激情的笔去描绘腾格里大漠的风光,并且融情于景,情景交融,使这部长篇充满了诗情画意。
《遥》作不仅描绘了一幅幅腾格里大漠的风景画,为人物活动提供了适宜的自然环境,而且描绘出一幅幅大漠人的生活风俗画,为人物活动提供了恰当的社会环境。作品中那一幅幅色彩鲜明、情趣盎然的风俗画,无不充分地反映了大漠上的蒙古族人民所特有的文化教养和心理素质。无论是牧羊姑娘在辽阔的草原上放声高歌的情景,还是蒙古包里主人热情款待来客的礼节,抑或是年轻喇嘛们骑着骆驼围猎黄羊的场面,还有那庄严、肃穆、隆重的葬礼……无不显示出蒙古族人民勤劳、善良的美德和对生活无限热爱的情感。然而,作品中着墨最多的风俗画,则是喇嘛教那种种繁琐的礼仪。请看穆吉朗寺一次庙会中的个别场景。
咚、咚、咚……
随着寺院中古银杉树上吊的大口黄铜钟发出的钟声,院中高台上喇嘛乐队的八个两丈多长、盆口粗的低音长号吹响了,声如牛吼,森严可怖,远震数里,紧接着金号、银号、羊角号和鼓钹一同吹响起来。刹时,整个寺院,整个大漠都被笼罩在这个阴森、恐怖、神秘的世界里。
善男信女们刚刚跨入主殿,顿觉自己已经沐浴在菩萨莫大的恩惠之中。他们在几个司殿喇嘛的指点下,怀着敬畏的虔诚,先给众佛点烧几炷香后,站在菩萨像前,闭上眼睛,双手合在胸前默默祈祷片刻,然后伸展身躯匍倒在地磕起长头,接着又站起来,转向葛根跪下,爬到葛根法座旁顶礼膜拜,磕起响头。他们个个嘴里念念有词,祈求菩萨、葛根保佑他们吉祥如意,风调雨顺,五畜兴旺;有的祈求消灾避祸,过上平安富裕的日子;有的向葛根忏悔自己的罪过,祈求菩萨宽恕;有的扑在葛根脚下,吻着他的袈裟……随之又站起来,恭恭敬敬地低头接受葛根为他们摸顶赐恩。当葛根抬起手在他们头顶上摸一下的刹那,他们更是那般的激动、亢奋……此外,如草原牧民祭敖包,赶庙会,喇嘛们为灵童“洗礼”、穆吉朗寺的“迎圣经”、跳“查玛”(跳鬼)、“切里奥”(辩论)等场面,都被作者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得有声有色、生动逼真,给读者以身临其境之感。需要指出的是,作者之所以精雕细刻地描绘这些宗教仪式,绝不是为了搜奇猎异,以满足读者的好奇心,更不是为了渲染少数民族的陋习。作者描绘这些繁琐的、使人感到压抑的宗教礼仪,目的在于撩起盖在宗教上面那层神秘面纱,让读者认清其实质。这样,作品中喇嘛教礼仪构成的风俗画,就成为作品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对于塑造人物的形象和深化作品的主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四)
恩格斯1888年写给英国女作家玛·哈克奈斯的信中,赞扬她的中篇小说《城市姑娘》表现出作家“真正艺术家的勇气”。应该看到,敖·奇达布日也是具有恩格斯赞扬的具有“真正艺术家的勇气”的一位作家。
敖·奇达布日的真正艺术家的勇气,首先表现在他敢于涉足宗教活动这个棘手的题材。宗教作为一种距离经济基础较为遥远的意识形态,有其复杂性。它是在生产力落后,人类对自然力量无知的情况下产生的。是人自己创造了神,并加以崇拜,欺骗麻痹自己。所以,马克思称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鸦片”,列宁称它是“精神的劣质酒”。虽然历史上一些农民起义领袖曾利用宗教来号召人民加入起义队伍,但就宗教创立以来所起的作用来说,主要是对人民的愚弄。蒙古族人民自从接受佛教以来,其身心都深受喇嘛教这一“精神鸦片”的毒害,被喇嘛教的浓雾所迷惑、麻木。然而,由于宗教往往同政治问题和民族问题纠缠在一起,这就大大增加了文学艺术对它准确反映的难度。有人将宗教戏称为文学创作的“雷区”,不是没有道理的。我国文学史上,以活佛为题材的作品极少见。进入新时期以来,玛拉沁夫的《活佛的故事》和哈斯乌拉的《虔诚者的遗作》,通过活佛思想历程的描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喇嘛教的某些本质方面。但由于这两部作品均为短篇小说,因而其题材容量和思想内涵难免受到某些限制。《遥》作则以长篇小说的形式去反映一个活佛坎坷的一生,这在内蒙古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学史上,无疑具有开创性意义。
当然,如果作家只有勇气而缺乏必要的能力,则最终还是难以通过“雷区”的。敖·奇达布日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仅敢于去闯宗教这一文学创作的“雷区”,而且善于运用文学创作的规律,讲述了桑布道尔吉和高娃曲折动人的爱情故事,以及大漠上人们的悲欢离合,塑造了桑布道尔吉、高娃、尼玛等一些活灵活现的艺术形象。作家在塑造这些形象时,充分调动了文学创作中的各种艺术手段。有时描绘其肖象,借肖象去反映人物的身份、教养、思想、性格;有时细致入微地描绘其心理活动,向读者展示主人公心灵深处的秘密;有时描绘其语言,以显示其内心深处那细微的变化;有时描绘其行动,让人物用自己的语言说明自己。由于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既鲜明生动,又真实可信,故而使读者在获得审美享受的同时,受到了思想上的启示。作家于是也顺利地通过了“雷区”,实现了自己的创作意图。
敖·奇达布日的真正艺术家的勇气,还表现在他不趋时,不媚俗,以严肃的态度创作了这部高品位的作品。近年来,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一些“头脑灵活”的作家奉行“一切向钱看”的准则,为使自己的作品畅销,不惜降格以求,去迎合以经济效益为宗旨的出版商及欣赏趣味低下的读者的需要,大肆渲染色情及打斗场面。有的作者还在书名上煞费苦心,标上“艳史”“秘史”“风流”“男人”“女人”等字样,以招来顾客。敖·奇达布日却相反,他没有将这部以桑布道尔吉与高娃的爱情故事为主线的小说,定名为“风流活佛”、“一个活佛与一个女人”、“几个僧人与几个女人”之类,而定名为《遥远的腾格里》。这一充满诗意的书名,令人联想到大漠地域的辽阔和历史的久远,产生一种苍茫感和神秘感。“腾格里”汉语意为“苍天”,“遥远的腾格里”还可理解为,苍天距离我们太遥远,太虚无飘渺,所以人类不应该寄希望于苍天及其代表神佛。“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遥》作不仅书名不俗,而且内容也很高雅。它没有那些胡编乱造,破绽百出的所谓“动人情节”,也没有那些“拳头加枕头”式的刺激人的感官的细节和场面。在艺术表现手法上,《遥》作中也看不到时下颇为流行的那些打乱时空顺序等新花样。作家严格地遵循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用诗一般优美的语言,讲述了一个生动感人的故事。作品中即使写男女主人公做爱的情景,也写得很真,很美,充满诗情画意。当高娃终于从“独眼公子”府上逃出,来到查干淖尔湖边与她亲爱的“桑布哥”幽会时,作品中写道:
这对真诚相爱的情侣又在查干淖尔湖边、腾格里大漠的怀抱里相会了。这不是梦境,而是实实在在地背靠金灿灿的沙丘,脚踩绿茵茵的草滩相望着,爱抚着……
一切归于寂静,周围是广褒的荒原、高大的沙丘、茂密的芦苇丛、静默的湖泊……
蓝天上,飘来一朵湿润的云,绵绵缠缠在大漠上空飘来荡去。陡然间,甘露如丝,点点滴滴,注入这片焦灼干裂的土地……两只银燕穿行在云雾里,张开焦渴的双唇,一口口贪婪地吻着淅淅沥沥、透明而浑浊、甜蜜的甘露……
天晴了。云朵从太阳背后羞怯地散去,那两只银燕自由地遨翔在蓝天、大漠间。
文艺作品中的性爱描写,不是性爱生活的实录、照搬,而要经过艺术的加工提炼,要给人以美感。在上述描写中,作家先用诗的语言,描绘了男女主人公做爱时环境的优美,衬托出俩人心中感情的纯洁、美好。接着,作者又以丝丝细雨滴入大漠焦灼干裂的土地和银燕贪婪地吻着甜蜜的甘露,来喻示男女主人公做爱时的感受。后来,作者又以“云朵从太阳背后羞怯地散去”、“两只银燕自由地遨翔在蓝天、大漠间”,象征男女主人公此时此刻那欢快而羞涩的心情。整个做爱过程,写得细腻,传神,含蓄,适度,具有很高的美学品位。而上述性爱描写,对塑造男女主人公形象和深化作品主题,都具有重要作用,也是故事情节发展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同时下某些作品中那与情节和主题无关的粗俗的、意在刺激读者感官的性爱描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敖·奇达布日的真正艺术家的勇气,来自他那崇高的使命感。他出生于内蒙古科尔沁草原上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从小阅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暴风骤雨》、《茫茫的草原》、《红路》等大量革命文学作品,从中汲取了丰富的思想营养和艺术营养。他热爱自己的家乡,热爱自己的民族,热爱伟大的祖国,热爱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因此,他常为自己的同胞中残存的某些阻碍民族进步的痼疾而深感忧虑。《遥》作“后记”中写道:“记得有一次到一个边境苏木工作时,见到苏木学校的校舍破烂不堪,又无人问津,然而离苏木不远的一座寺庙正在修复,很红火,牧人们从怀里掏出大把大把的钞票捐赠寺庙,甚至有的牧人把正在上学的孩子从学校接走,送到庙里当小喇嘛。后来类似的所见所闻,促使我提起笔开拓这一题材的小说”。敖·奇达布日正是怀着唤醒那些受宗教愚弄而不自觉的同胞、从而振兴蒙古族的崇高使命感。才勇敢地涉足宗教这个文学创作的“雷区”。为了胜利地通过“雷区”,他付出了极为艰辛的劳动。敖·奇达布日创作《遥》作成功的经验又一次表明,作家只有怀着崇高的使命感去从事创作,才会具有“真正艺术家的勇气”,并付出艰辛的劳动,从而获得成功。而某些文坛大腕为了赚钱,坐在豪华饭店沙发上“侃”出来的东西,则只能是些胡编乱造,破绽百出的“劣质品”。然而,奇怪的是,关于作家应树立崇高使命感这一正确主张,时下竟成为某些“新潮文论家”冷嘲热讽的对象。在他们看来,文学创作是非理性活动,“任何理性因素的介入都必然在某种程度上损害文学的纯洁性”,文学的作用仅仅是供人们“玩”而已。面对敖·奇达布日的创作经历和《遥远的腾格里》这部佳作,不知“新潮文论家”们作何感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