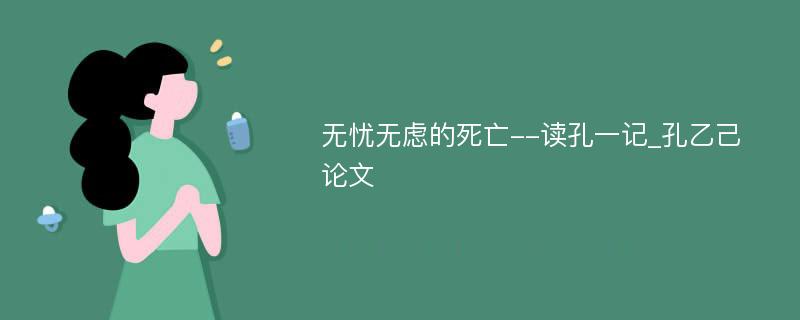
无人悲哀的死亡——读《孔乙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悲哀论文,孔乙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单篇阅读,要进入分析的层次,比较困难。因为矛盾不是现成的。
怎么办呢?
还原。
鲁迅在《孔乙己》中,几乎涉及了孔乙己的一生。从他一直考不取最起码的秀才,中老年潦倒落魄,无以为生,偷书,被打致残,直到最后消失、死亡。经历的时间,起码有几十年,但是,全文只有三千字左右。这么短的篇幅写这么多的事情,怎么可能讨好?
鲁迅虽然写到了这么多,但大多是从别人的嘴巴里说出来的,并没有直接、正面描写孔乙己。比如他的应考,他的不中,他的偷书,甚至挨打致残都发生在幕后,在小说中,只是被出场人物间接提起。可以说,那些决定他命运的事件,使孔乙己成为孔乙己的那些情景,鲁迅一件也没有写。
这些情节,如果要让吴敬梓用《范进中举》的办法来处理,肯定是要正面描写的,而且还要加以渲染。不写这么重要的场面、情节,说明鲁迅对这些不感兴趣,或者,鲁迅认为,这些不是他要表现的重点。那么,鲁迅在这篇小说中写了些什么呢?
非常令人吃惊的是,鲁迅只选取了三个场面,而孔乙己本人只有两次出场——在咸亨酒店的场面。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两个场面和孔乙己的命运关系并不大。第一个场面,是他偷书了,已经被打过了,来买酒时,被嘲笑了;第二个场面,是他被打残了,又来买酒,又被嘲笑了。如果要揭示孔乙己潦倒的根源,批判科举制度,这两个场面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如果要表达对孔乙己的同情,那完全可以正面写他遭毒打的场面,像《范进中举》那样,细致地描写发生在主人公身上的事件,在场人物的反应等等,但是,鲁迅明显回避了这样的写法。
这是不是舍本逐末呢?关键不在于舍本逐末,而在于鲁迅衡量“本”和“末”的准则。
三个正面描写的场面,主要写了些什么呢?写作的重点、焦点,是人们是如何看待这个人的。最不可忽略的,是鲁迅是用一个人的眼光去看孔乙己的。
这副眼光是属于一个特殊人物的,一个小店员的。对于这个小店员,鲁迅很舍得花笔墨,一开头就花了两个大段。这是因为,鲁迅需要小店员的眼睛,以不以为意的观感,和孔乙己拉开情绪的距离。
小说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个小店员与孔乙己错位的观感。在他观感以内的,就大加描述;在他观感以外的,通通省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小说写的并不仅仅是孔乙己。其实,这正是鲁迅的匠心,也是创作的原则,或者小说美学的原则:重要的不是人物遭遇,而是,这个人物,在他人的、多元的眼光中的心理奇观。鲁迅之所以弃医从文,就是因为他看到日俄战争时期,中国人为俄国人当间谍,被执行枪决之前示众,而中国同胞却麻木地当看客。在鲁迅看来,为他国做间谍送死固然是悲剧,但是,对同胞之悲剧漠然地观看,更是悲剧。
咸亨酒店中的各色人物,对于孔乙己的命运,对于他的遭遇,当然是麻木的,但是,作为一个小店员,他的漠然,又有其特点。这个特点,就是“无聊”、“单调”,所看的都是“凶面孔”、“教人活泼不得”。但是,在这样沉闷的氛围中,“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这里的笑声,不是一般的描述,而是整篇小说情绪的逻辑起点和整篇小说结构的支点。
第一个场面,突出了孔乙己“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提示遭受过殴打。
按理说,这个人非常不幸,没有起码的出息,无以为生,是一个失败的读书人,又近乎小偷。更糟糕的是,他还是不成功的、时常被抓住的小偷,显然,命运是很悲惨的,心情应该是很痛苦的。然而,恰恰是这样一个人,却给小店带来欢乐。不但这个小店员,而且“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甚至“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鲁迅立意的焦点,显然就在这种笑上。
开头写小店员的无聊,就是为了反衬孔乙己带来的笑声。
因偷书而挨打,有什么好笑的呢?在这种笑里,鲁迅挖出了什么深刻的东西呢?
首先是这个已经沦为小偷的、无用的人,从道德理性看,“好喝懒做”。偷窃,是恶的,但是,情感价值上,恰恰又是带来了欢乐的。
这种欢乐,是有一点喜剧性的。
一方面是那些喝酒的,嘲笑他又偷了书,又挨打了,而且有人指出,是亲眼看见,“吊着打”的。这是确凿的事实,而孔乙己否认的态度是十分坚决的,“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但是,否认的理由却又十分薄弱,甚至是不成理由的:“窃书不能算偷”。显而易见,这不过是把偷窃的概念从白话变成了文言,并没有改变偷窃的实质。
这就显得荒谬可笑了。这种可笑,构成了小说的幽默基调。
其次,在这种荒谬可笑中,还隐含着更深的意味,孔乙己虽然潦倒、沦落到如此地步,却还在维护着他的一点自尊。文言文的用语,“污人清白”、“君子固穷”,为一般酒客所不懂,成为读书人最后的“面子”的盾牌。但是,不管什么样的话语,总不能改变亲眼目睹的事实。因而,这最后的对自尊的维护,显然是无效的,甚至是理屈词穷的表现,只能“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
在这种笑声里,并没有太明显的恶意,其中还有也明知其理屈,而予以原谅的意味。
这表明,这种嘲弄是温和的。
但是,无效的抵抗,是对外部世界来说的,对孔乙己来说,却是不可或缺的。口头上不承认自己是小偷,在他自己内心,也并没有小偷的感觉。号称冷峻的鲁迅,没有让他在大庭广众面前承认自己是小偷,没有让他的自尊心公开地彻底瓦解,彻底地不要脸面。相反,鲁迅特别写到孔乙己在酒店里的“品行”比别人好,从不拖欠酒钱。他还主动教导小店员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对围过来要吃他的茴香豆的孩子,软弱地说着“多乎哉?不多也”。联系到小说开头,写他穿着长衫,却不是坐着喝,而是站着慢慢地喝。这都在提示,在他自己的感觉中,他还是残留着一点“读书人”的身份和自尊的。
鲁迅对孔乙己,并没有厌恶的成分,只是调侃而已,在调侃中有同情。可以说,小说是幽默的,并不是讽刺的,并没有揭露孔乙己的恶劣品质的意思,明明是屡屡提及,但在具体行文中,却满是为之辩护的成分。字里行间,似乎留下了矛盾:
孔乙己……没有进学,又不会营生;于是愈过愈穷,弄到将要讨饭了。幸而写得一笔好字,便替人家钞钞书,换一碗饭吃。可惜他又有一样坏脾气,便是好喝懒做。坐不到几天,便连人和书籍纸张笔砚,一齐失踪。如是几次,叫他钞书的人也没有了。孔乙己没有法,便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窃的事。
在鲁迅的话语中,孔乙己的偷窃被分为两种,一种是,抄书时把人家的书籍、纸张、笔砚一齐偷了,美其名曰:“一齐失踪”。另一种是,“偶然做些偷窃的事”,“偷窃”,显然有别于书籍纸张笔墨的“一齐失踪”。偷窃的对象,那应该是书籍笔墨以外的,可能是更加值钱的东西。对这种愈加值钱的东西,鲁迅的行文是“偷窃”,而对书籍笔墨纸张,鲁迅的具体行文就含蓄得多了:叫做“连人和书籍纸张笔砚,一齐失踪”,如果把这也算在偷窃之中,则不应该叫做“偶然做些偷窃的事”。何况后来在人们的议论中——“他总仍旧是偷”,可见,在鲁迅心目中,孔乙己偷书,是不包括在“偶然”“偷窃”之中的。这不正是孔乙己窃书不算偷的逻辑的翻版吗?正是在这样的话语中,鲁迅流露出了对孔乙己的宽容、温情和回护。
在鲁迅看来,孔乙己不过是科举制度的牺牲品。制度是可恶的,但人,却是值得同情的。孔乙己第一次出场时,读者感觉不到严酷的讽刺的因素,其间的笑,带着温情的调侃。
接下去,在第二个场面中,孔乙己并没有出场。一般情况下,场面的连贯性,由情节的因果性、并行性相联系,但在这里,并没有因果和并行关系,其间有一句过渡的话语:
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
孔乙己出场,人们是快活的,不出场,人们也是快活的。对于这句话,叶圣陶在不止一篇文章中表示赞赏。在我看来,这正是小说构思的意脉所在,整个小说,都是以孔乙己所引起的笑为脉络的。这个构思是很深沉的。一个苦命的人物,在公众场合出现却能带来欢乐。但是,没有他,人们也一样快活。这有什么值得深思的呢?小说写下去,在酒店里,人们发现,孔乙己长久没有来了。
一个喝酒的人说道,“他怎么会来?……他打折了腿了。”掌柜说,“哦!”“他总仍旧是偷。这一回,是自己发昏,竟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他家的东西,偷得的么?”“后来怎么样?”“怎么样?先写服辩,后来是打,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后来呢?”“后来打折了腿了。”“打折了怎样呢?”“怎样?……谁晓得?许是死了。”掌柜也不再问,仍然慢慢的算他的账。
这里,有个小小的疑问。前面的叙述是,孔乙己使人快活,没有他,别人也快活。可是这里从字面上看,好像并没有任何文字直接写到人们的快活。但是,从对话的语调中,仍然可以看出那个提供消息者的心态。说他被打折了腿,归结为“他自己发昏”,“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他家的东西,偷得的么?”这和孔乙己在场时的那种欢乐、调侃,在情绪上是大有不同的。对于丁举人打折了孔乙己的腿这样野蛮的人身伤害,说话者没有半点保留,相反还给人一种津津乐道的感觉。也许这就是鲁迅所提示的快活。特别是,说到孔乙己可能是死了的时候,说话的和听话的,都没有震惊。“掌柜也不再问,仍然慢慢的算他的账。”对于一个给酒店带来欢笑的人的厄运,人们居然一点反应也没有。这里,就充分显示出鲁迅写对话的笔力了。
当然,这里有一点似乎是不能回避的,就是鲁迅明明说,孔乙己不在场人们也是快活的,而在上述文字中,却没有快活的字眼。鲁迅为什么没有直接写喝酒的那个人快活地说着这样的事情呢?这可能与鲁迅追求白描式的对话有关。鲁迅在《二心集·看书琐记》中说:
高尔基很惊服巴尔扎克小说里写对话的巧妙,以为并不描写人物的模样,却能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像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八月份《文学》内《我的文学修养》)中国还没有那样好手段的小说家,但《水浒》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
很可能,鲁迅在这里,就是有意不去直接点明说话者那种津津乐道的神态和兴高采烈的情绪,而把想象的空间留给读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快活”啊。一个人死了,居然没有人感到悲哀,反而将其“快活”地作为谈资。
表面的热闹和潜在的悲凉,不着一字,从容不迫,含蓄隽永,显示了鲁迅笔墨的最高火候。如果在这里,粗心的读者感觉还不够明显的话,到了下面,孔乙己第二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出场,就不能不有所震动了。这时的孔乙己被打折了腿,已经不能走路。鲁迅以小店员的视角,导引着读者逐步发现孔乙己的狼狈和悲惨。先是看到他盘着两腿,下面垫着一个蒲包,后是发现他是用手撑着地面“走”的。躯体残损到这种程度,在这么与平常不同的情况下,掌柜的“仍然同平常一样,笑着对他说,‘孔乙己,你又偷了东西了!’”
一个人被打得不能走路,只能用手走路了,本是很悲惨的事,人们本该有惊讶,有同情,至少是礼貌性的沉默,可是,掌柜的不但当面揭短,而且还“笑着”。这就是说,这位掌柜的,并没有感到自己的话是多么残酷,有着多么严酷的伤害性,相反,倒是感觉到并无恶意,很亲切地开玩笑似的。
但他这回却不十分分辩,单说了一句“不要取笑!”“取笑?要是不偷,怎么会打断腿?”孔乙己低声说道,“跌断,跌,跌……”他的眼色,很像恳求掌柜,不要再提。此时已经聚集了几个人,便和掌柜都笑了。
鲁迅在这里揭示的是,所有的人,似乎都没有敌意,都没有恶意,甚至在说话中,还多多少少包含着某种玩笑的友好的性质。但是,这对孔乙己却是一种严重的伤害。因为,从一开始,他讳言偷,就是为了维护最后的自尊,哪怕是无效的抵抗,也是要否认“偷”的定性的。这是他最后的精神的底线。但是,众人,无恶意的人们,却偏偏反复打击他最后残余的自尊。这是很恶毒的,但又是没有明确的主观恶意的,鲁迅所揭示的就是这种含着笑意的恶毒。关键在于,这种貌似友好的笑中,包含着冷酷,对人的精神的麻木不仁,对人的同情心的阙如。
孔乙己已经被逼到找不到文言词语来维护自己自尊的程度,连“跌断”这样的掩饰之语,都没有信心说下去了,可是酒店里的人,却都“笑了”。这种“笑”的内涵太丰富了。一方面当然有不予追究的意味,另一方面,又有心照不宣地识破孔乙己的理屈词穷,获得心灵满足的意思。这一切明明是鲁迅式的深邃的洞察,但是,文字上,鲁迅却没有任何形容和渲染,只是很平淡地叙述,“仍然同平常一样,笑着对他说”,连一点描写都没有,更不要说是抒情了。但是,唯其平静,平常,平淡,才显出诸如此类的残酷人情,司空见惯,没有感觉,没有痛苦,而鲁迅的笔墨,就是要揭示这种世态的可怕。
不一会,他喝完酒,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
孔乙己如此痛苦,如此狼狈地用手撑着地面离去,酒店里的众人,居然一个个都沉浸在自己的欢乐的“说笑声”中。世态炎凉竟至于此,这是何等的意味深长。更加精致的还在后面,孔乙己在酒店粉板上留下了欠十九个铜钱的记录,年关没有再来,第二年端午,也没有来。人们记得的只是“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过了中秋,又到年关,仍然没有再来。小说的最后一句是:
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
一个人死了,留在人们心里的,就只是十九个钱的欠账,这笔账,是写在粉板上的,是一抹就消失的。一个人的生命,在众人心目中,竟然是这样的无所谓。他在世的时候,人们拿他作为笑料,他去世了,人们居然一点感觉也没有。既没有同情,也没有悲哀。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生,什么样的世态啊。这里不但有鲁迅对人生的严峻讽喻,而且有鲁迅在艺术上的创造性的探索。对这篇小说在艺术上这样的追求,鲁迅特别有心得,他的学生孙伏园,在《关于鲁迅先生》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曾问过鲁迅先生,其(按:指《呐喊》)中,哪一篇最好。他说他最喜欢《孔乙己》,所以已译了外国文。我问他的好处,他说能于寥寥数页之中将社会对于苦人的冷淡,不慌不忙地描写出来,讽刺又不很显露,有大家的作风。①
这样的回答,可能有点出乎意料,在我们印象中,在《呐喊》中,被鲁迅喜欢的作品至少不应该是《孔乙己》,而应该是《阿Q正传》、《狂人日记》、《药》等名篇。但是,在鲁迅自己看来,这些名篇,恰恰是他不太满意的。傅斯年以孟真的笔名写的《一段疯话》中对鲁迅的《狂人日记》大加称赞。但是,鲁迅却在和他的通信中表示:
《狂人日记》很幼稚,而且太逼促,照艺术上说,是不应该的。②
从两篇小说的对比中,可以感到鲁迅对艺术的执著和严谨。
鲁迅擅长写人物的死亡,可以说,每一个都不重复。我们记得阿Q的死亡,是悲剧性的冤假错案,但却以喜剧的方法处理。而祥林嫂死亡,同样是悲剧性的,鲁迅却创造了悲剧的抒情的氛围。在《孤独者》中,魏连殳的死亡,则又是另一样,那是含着冷笑的死:冷笑着这世界,也冷笑着自己,是反抗势利,胜利的死,但是,又以人格上同流合污为代价,是失败的死。故氛围沉重而严峻,主人公的哭,是挣扎着像受伤的狼的长号,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而《铸剑》中,英雄的慷慨赴义,偏偏和暴君合葬,变得荒诞。唯独孔乙己的死,既不是悲剧的,也不是喜剧的。在表现方法上,也只有平淡的叙述。
鲁迅善于在人物死亡之后,大笔浓墨表现周围人物的心理反应,多方面加以渲染。阿Q的死亡,鲁迅正面只写了“如微尘一般的迸散了”,似乎偷工减料。但接着而来的是,心理多方面的效果:举人老爷没有追到赃,赵府损失了辫子和赏钱,故皆号啕。更特别的是舆论,第一,未庄,阿Q坏,被枪毙就是证据。第二,城里,枪毙不如杀头好看,又没有唱一句好戏。城里乡下,人们的反应妙就妙在同样极端荒谬,反差又如此之大。而祥林嫂的死亡,反应也是多元错位的,鲁四老爷,说她死在旧历年关,不是时候,可见是个谬种。茶房认为,“还不是穷死的”,没有任何异常的感觉,没有任何情绪上的反应。而整个鲁镇的人们,一个个都忙着祝福,虔诚地祈求来年的幸福。只有一个外来的“我”感到不可推卸的、沉重的内疚。以人物心理反应创造多元心理反应,可以说是鲁迅的惯用手法,然而,在《孔乙己》中鲁迅却显示了另外一种手法,那就是没有悲哀的悲剧。没有明显的讽刺,也没有调侃性的幽默。既没有《祝福》中的抒情,也没有《阿Q正传》和《药》中的反讽,更没有《孤独者》死亡后那种对各方面虚假反应的洞察,在《孔乙己》里,有的只是,三言两语,精简到无以复加的叙述。这种叙述的境界就是鲁迅所说的“不慌不忙”,也就是不像《狂人日记》那样“逼促”。“讽刺”而“不很显露”,这就是鲁迅追求的“大家的作风”。反过来说,如果不这样写,而把主观思想过分直接地暴露出来,那就是“逼促”,“讽刺”而“很显露”,在鲁迅看来,就不是“大家的作风”。拿这个标准去衡量《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可能就都不够理想了。从这里可以看出鲁迅在艺术上对自己是如何苛刻。
注释:
①孙伏园《关于鲁迅先生》,《晨报·副刊》,1924年1月12日
②《对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见》,《新潮》,第一卷第四期(1919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