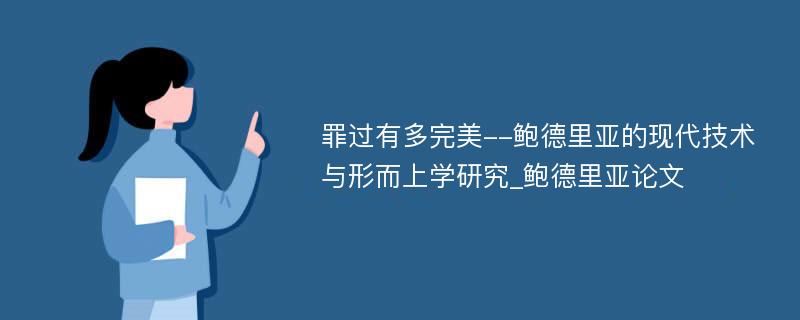
完美何以有罪——鲍德里亚对现代技术与形而上学问题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里论文,形而上学论文,完美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65.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3)02-0055-07
“完美的罪行”是一个法律上的用语。其意思是说一个人在犯罪时不露马脚,完美无缺。当今法国著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把该术语移用到对现代技术社会特征的分析中,并用于阐释有关实在的后形而上学的问题。本文将在阐释鲍德里亚“完美罪行”有关思想的基础上,引申出完美的罪行与现代技术哲学的密切关系,然后结合当今信息网络时代有关“虚拟实在”的问题,对现代技术与形而上学关系这一新的哲学问题做一评价。
一、何谓完美
何谓完美,它又有何罪?这个问题本身令人感到非常奇怪和不可思议。本来,在我们这 个还有着贫穷、饥饿,还有人间罪恶的现实世界,在人与人之间还存在着不平等和虚伪 欺诈的世界里,在不时还笼罩着战争和恐怖主义阴影的地球上,在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有 诸多缺憾和失意的理想世界的追求中,追求完美,是人人梦寐以求的目标。然而,当今 著名的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却一反常态,在20世纪90年代推出了《完美的罪行》一书, 并提出了“完美的罪行”这一令人困惑的概念。《完美的罪行》一书是鲍德里亚在其学 术生涯后期出版的一本非常抽象晦涩的哲学专著,也是最能代表其世界观和后期哲学思 想的重要著作。因此,搞清楚“完美的罪行”的意义,厘清这位哲人思想的深邃的哲学 洞见,在当今的科技时代,就显得尤为必要。
首先,我们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完美”。从字意上讲,完美就是“无缺陷”,也可以说就是“天衣无缝”、“完美无缺”等等,它表现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从逻辑上讲,完美是一个形容词,一个修饰词,而非一个主体,也非一个对象,何以要让它来承担“罪行”这一恶名呢?
或许,我们可以从辩证法的视角出发,从完美的对立面,也就是邪恶来进行理解。一个物或对象,由于太过于完美了,反而会走向其反面,并导致邪恶等等。这一理解不符合鲍德里亚的本意。因为,鲍德里亚在其另一本专著《命定策略》中声称:他的思想完全不是黑格尔所讲的对立双方的互相转化,相反,他追求的是一种命定的,事物按其自身发展至极限,直至完美,抑或发展到系统的崩溃的策略。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癌症的病变。我们知道,癌细胞的扩散,并不会导致其对立面,即病体的痊愈;相反,一旦癌细胞扩散,它就会一直以超常的速度发展,直到把所有正常的细胞全部吞噬,使生命毁灭为止。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人类对视觉美的追求,从最初的人工画像,到近代照相技术的发展,一直到当今最先进的数字成像技术,可是,视觉艺术的发展也没有朝反向转化,而是一直按照自身的发展逻辑前进,永远没有止境,直到极限的完美。所以鲍德里亚说:“世界不再是辩证的,它肯定要走向极端,而不是平衡;它肯定走向激进的对立,而不是调和或综合。”[1](P7)完美就是对极限或极至的理想追求。它包括了对立的两个极端,但却并不包括双方的相互的转化。因此,从辩证法的对立双方的相互转化来对完美的罪行的加以理解,显然不符合鲍德里亚的本意。
那么究竟如何去理解完美呢?鲍德里亚的“完美”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对这一问题,鲍德里亚在《完美的罪行》中,通过一首诗列举了完美的各种形式如:“死亡的形式——人们以顽强的治疗避免死亡/脸形和体型,人们通过外科美容术追求着。/世界的形式,人们通过虚拟使人忘却了。/每个人的形式,某一天将通过克隆个体细胞而取消之……”[2](P107-108)
从这首诗可以看出,所谓完美,是和人类对生活中各种形式的极限追求联系在一起的。这一追求最主要的是由于高科技的发展而达到的完美,如“以顽强的治疗避免死亡”,“通过外科美容术追求”脸形和体型的完美,“通过克隆个体细胞”来取消人的自然 遗传的疾病、丑陋等不完美努力,等等。所有这些,惟有通过现代高科技的发展和进步 才能达到。实际上,从人类发展至今,除了大自然的造化所形成的自然的“完美”之外 ,惟有科学技术才具有如此的威力。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技术的人为的完美超越 自然的完美。如现代的IT技术。由于电脑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广泛的应用,使得人类的许 多幻想都变成了现实,而且IT数字技术所达到的“以假乱真”程度,实在是令人瞠目结 舌。用鲍德里亚的话来说,“仿真(simulation)”并不是本真(reality),但它却超越 本真,比本真还要真,是一种超真实的真(super-reality)。从这点看,完美的罪行是 和鲍德里亚的仿真、虚像的技术观点相关,与他的命定的理论密切相联。
把完美和高科技的发展和进步相联系,是鲍德里亚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21世纪的世界是一个充满了现代技术的世界。我们的生活到处都打上了现代高技术的烙印。人们正是通过发展现代高技术来追求物本身的完美、人本身的完美和我们生活世界的完美。然而,事物的发展并不是“天随人愿”,对完美的追求是否会导致一个完美的结果,或完美的结局呢?鲍德里亚对此的回答是否定的。在他看来,完美的追求所导致的是绝对的同一性和差异性的消失,而这一结果是人对“完美”的追求的初衷所未曾料到的。例如 ,克隆技术的发展,使得“无差异”的人的大量“制造”在未来成为可能,并在技术上 可以达到完美的地步。如鲍德里亚所说,不再有他者、敌人、掠夺者、消极性、死亡、 相异性、诱惑、秘密和定命等等,而是沟通、谈判、伤风败俗的克隆和性冷淡等等。在 这一过程中,真正的、原始的实在反而遭到了人为的技术的遮盖,实在遭到了完美的谋 杀,而这就构成了完美的罪行。所以,完美主要是从技术意义上理解的,即技术上的完 善和天衣无缝。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鲍德里亚虽然否定黑格尔的辩证法,但是在 他对完美的论述中,似乎也难以完全祛除黑格尔辩证法的相互转化的色彩。
其次,完美不仅包括了(技术)功能上的完善和至善至美,而且还包括了意愿和意志的要求,而这二者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以电子计算机的人工智能为例,鲍德里亚说, 我们渴望电子计算机进入智能自动编程,希望它们变得比我们更聪明,但是我们却不会 让它们拥有人的意志和愿望。这些高级人造生命的智慧本身必须是我们愿望的体现。我 们对它们的要求是,一方面它们在智慧上和体力上都比我们人类要强,但另一方面,他 们却没有自由、没有意愿、没有要求、没有性欲。尤其重要的是,我们人类绝对不给予 它们一个最重要东西,那就是上帝最终向人类做出让步的:恶的智慧。也就是说,我们 不希望它们惹“祸”,不希望他们像我们人类那样具有理性的判断的能力,甚至会成为 攻击我们的对手。我们对拥有人工智能的计算机的所有这些方面要求,是一个完美的要 求。我们希望他们是完善的。同样,对于克隆人,我们人类又何尝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美 好的愿望呢?我们人类的这一美好的主观愿望只有通过技术革新和技术进步才能变为现 实。嫦娥奔月是人类自古以来的美丽幻想,但在20世纪的60年代,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 ,这一美好的愿望终于变成了现实,人类的足迹终于踏上了月球。所以“完美的”意愿 和意志,与“完美的”技术功能是密切相联的。今天,由于技术的突飞猛进,我们人类 的这一美好的愿望,一部分已经或正在实现,也就是技术制造物品正在成为我们人类的 得力的助手。当然,从实际结果看,美好的意愿和意志的追求本身,并不意味着结果本 身也是完美的。也就是说,我们在试图实现我们人类愿望的过程中,在剥夺技术的物品 的欲望方面,我们却并不成功,甚至到处遭到挫折。我们所制造的技术物品并不是完全 听命于我们自己的意愿和控制,相反,它们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祸害和灾难。 “完美的”追求,结果导致了物本身变成了具有某种欲望的“活”物,成了控制我们人 类自身的东西。从人类的意愿和意志的完美追求出发,也是理解鲍德里亚在80-90年代 思想变化的重要线索。
二、完美的罪行并不完美:技术的报复
按照鲍德里亚的解释,“假如没有表面现象,万物就会是一桩完美的罪行,既无罪犯、也无受害者,也无动机的罪行。其实情会永远地隐退,其秘密也永远不会被发现。”[2](P6)然而事实上,这只是人们美好的幻想。因为凡事物皆有表象,所以完美肯定是有罪的。鲍德里亚说:“完美的罪行就是创造一个无缺陷的世界并不留痕迹地离开这个世界的罪行。但是,在这方面,我们没有成功。我们仍然到处留下痕迹——病毒、笔误、病菌和灾难。”[2](P43)这里鲍德里亚所说的完美“留下的痕迹——病毒、笔误、病菌和灾难”等等,其实指的就是人类在技术进步、追求技术和工艺上完美的进程中,所付出的代价。通俗地讲,它指的就是技术对人类的报复,或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副作用。
我们看到,拥有部分人类智能的电子计算机,在给人类带来福音的同时,却给这个电子世界留下了数不清的计算机病毒,使我们整天都生活在担心病毒和黑客的入侵的恐惧之中。目前,我们已经基本可以从技术上解决克隆人的问题,但如何对待这些克隆人,是否让他们享有与我们人类同样的权利,还是让他们成为我们的奴役对象,这构成了我 们人类的最大的伦理困惑。一旦克隆人的所有技术问题得以解决,那么,就可以按照我 们人类的意愿,从最“完美”的角度出发,来克隆大批的俊男美女。这就是所谓的“完 美”。但问题是,这些克隆人却与技术制造的一般的物体和商品不同,他们也不再是具 有人工智能的机器人,他们是具有自己的愿望、意志和智力水平的我们的同类。那么, 我们所有的伦理原则和法律制度是否应该都适用于他们?他们对我们人类和当今的社会 是否能构成一个更大的威胁?不管这些问题的答案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一旦克隆人 出世,它绝对不可能按照技术的完美性的设计那样行事,因为他们是“人”,是拥有自 己的意志、愿望和目的的人。所以用鲍德里亚的话来说,克隆人必然将会留下更多的“ 痕迹”。它对我们的人类的生存,无论是在生物性、伦理性或社会性方面,必然构成人 类有史以来的最大的挑战和冲击。而且我们现在也不能预测,这一最新的生物技术成果 ,可能会对我们的人类造成多么大的副作用,它又是如何报复我们人类的。
鲍德里亚对技术的副作用的论述,不是泛泛而论,当然更不是实证方法的数据堆积,而是采取非常玄思的方法,对现代技术的特征进行哲学反思。他是继海德格尔之后的又一位重要的技术思想家。在《完美的罪行》的最后一章“镜中人的报复”中,鲍德里亚从当代技术的特征,即仿真和虚像出发来谈论现代技术对我们人类的报复,也就是他所谓的“镜中人的报复”。他通过两个世界,即博尔赫斯的《镜中野兽》中镜子世界和人类社会的现实世界,来阐明技术在当今的不可忽视的巨大的副作用。
从完美出发,就可以解释鲍德里亚的物的命定性理论,即“物”必然是命定的物。也就是为什么物是有意志的,有活力的原因。因为当今的物已经不是古代和近代的“死物”,而是已经变成了“活”的物,在物中已经包含了人的意识、意志和高科技等因素。不仅如此,现代的物,已经是具有人的最高智慧的“物”,如机器人和克隆人等等。所以,鲍德里亚说:“今天,是命运通过科学的屏幕又向我们这边退回来了。最后,绕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弯子,也许是科学加速了期限到来。”[2](P45)
面对着现代技术不断制造出来的大量的“命定之物”,我们人类有什么作为呢?鲍德里亚给出了一个非常悲观的答案,即一种宿命论的回答,只不过这一宿命论披上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外衣,也就是他所说的“命运通过科学的屏幕又向我们这边退回来了”。在他看来,科学技术越发展,它对人的控制就越强,反过来,人类在科技的强大威力面前则显得束手无策,无能为力,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而这一切,都归咎于现代技术的发展,即“科学加速了期限的到来”。
从鲍德里亚对技术的报复的分析来看,鲍德里亚虽然否认他的完美的思想来自于黑格尔的辩证法,但他对完美的罪行的技术表现,即现代技术的副作用的分析,还是透露出明显的辩证法的色彩。只不过他以思辨晦涩的形式,对当今科学技术的副作用进行分析。所谓科学技术的“双刃剑”的特性,在鲍德里亚这里,更多地体现为现代技术报复和对未来的悲观预言。所以,我们说,对“完美的罪行”这一概念的理解,也完全可以从辩证的角度入手加以理解,但前提是必须着眼于完美的罪行与现代技术的关联这一视角。但是很可惜,目前在对鲍德里亚思想的研究中,大家对这一点的认识还远远不够。
三、完美、虚拟与实在
那么,完美的罪行是否仅仅表现为技术对人类的报复,即技术的副作用呢?其实,对技术的副作用的论述,仅仅是鲍德里亚对“完美”的罪行表现的一个次要方面,这一点目前在对当今科学技术的研究中已经人所共知,也就是所谓的科学技术的“双刃剑”特性。鲍德里亚对完美的罪行的理解远非如此简单,他把我们带到了更深的层次,也就是对现代技术和形而上学的哲学反思之中。同时他的完美的罪行的思想,与其早期的核心概 念“仿真”和“虚像”也是密切相关的,是这两个概念的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现在, 我们先来看完美究竟何罪之有这一具有浓重形而上学色彩的问题。
鲍德里亚认为,完美的罪行就是对“实在的谋杀”。在该书的前言中,鲍德里亚又开宗明义地说:“本书写的是一桩罪行——谋杀实在罪的始末。也是消除一种幻觉——根本的幻觉,对世界的根本性的幻觉的经过,实在不会在幻觉中消失,而是幻觉消失在全部的实在中。”因此,按照鲍德里亚的说法,“谋杀实在”的罪名,就只能罩在“完美”的头上了。这样,对完美的理解就与传统形而上学的实在问题联系在一起了。由于技术的完美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使得原来的实在世界被完美掩盖了,被遮蔽了,使我们看不见实在,不知道实在为何物了。那么,完美是如何谋杀实在呢?在鲍德里亚看来,完美对实在的谋杀,正是通过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的方式,使实在消失了。鲍得里亚 说:“完美的罪行是通过使所有的数据现实化,通过改变我们所有的行为,所有纯信息 的事件,无条件实现这个世界的罪行——总之:最终的解决办法是通过克隆实在和以现 实的复制品消灭现实的实物,使世界提前分解。”[2](P28)
这里,一个自然而然的逻辑问题就被提出来了,那就是完美何以能谋杀实在?或者说完美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谋杀实在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把对完美的罪行的理解与鲍德里亚的两个核心概念——仿真(simulation)和虚像(simulacra)联系起来。
这两个概念是鲍德里亚在80年代之前提出的重要概念。“仿真”一词是现代技术上常用的一个专业技术词语,从字面意义上讲,仿真自然不是一种实在的“真”,而是一种“虚真”,是对实在之真的模仿或模拟。但是在鲍德里亚看来,仿真比实在的真还要真得多,是一种超真实的真。如果要深入地理解仿真,就必须把它与“虚像”概念联系起 来。虚像的意思是非真实的景象,有的翻译为“幻想”或“类象”,以表示和“幻觉” 等的区别,当然其主要意思还是表示与实在的表象或表征的区别。其实,在鲍德里亚看 来,所谓的“虚像”,非但不假,反而比“实在之像”更真实。因为他的“虚像”不以 实在为摹本,而是以复制品,甚至以虚构的摹本而成的“像”,并且它可以借助于现代 数字技术,可以无限地复制此类的“虚像”。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科技及其人工 产品充斥了我们的生活世界。我们就生活在一个充满了仿真和虚像的“超真实”的技术 世界,大量的仿真和虚像掩盖了原始的“实在”,并构成了对现实世界的“实在”的谋 杀。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电子媒体,如电视广告和网络的“虚拟世界”的出现。由于现代 数字技术的发展,大量的信息符号的泛滥,现代技术媒体的信息的饱和与符号的无限增 多,使得人们生活在大量的符号的支配之下,人们在感受大量符号为人们带来更快、更 准确有用的信息的前提下,也在饱受着大量的无用的符号的视觉的冲击。而这些电子媒 体所带来的符号,是一种符号的游戏,是一种没有所指的符号。因此,新技术,特别是 电子媒体技术的发展,使我们与我们周围的世界之间,就不再是观念和实在世界的关系 问题,而是涉及到实在的隐退和消失的问题。虚拟世界的出现和实在世界的隐退就相互 伴随而来。鲍德里亚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愈多,而意义则愈加匮乏的世界中。” “信息吞噬了自身的内容,它阻断了交流,掩没了社会。”“信息把意义和社会消解为 一种雾状的、难以辨认的状态。由此导致了不是更多的创新,相反是全部的熵。因此大 众媒体不是社会的生产者,而是恰恰相反,是大众社会的内爆。这只是符号微观层次上 的意义内爆的在宏观上的扩大。”[3](P79-81)
显然,完美的罪行,也就是谋杀实在的罪行,它与仿真和虚像所导致的符号的无限增多密切相关。由于仿真和虚像造成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失真”或“超真实”,甚至达到了完美的状态,所以原始的“实在”的世界就遭到了谋杀。这一自然的逻辑结果,并不是哲学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而是和外在的因素,是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巨大的社会功能联系在一起的。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电子媒体和网络世界所形成的“虚拟”世界,它必然构成对“实在”世界的挑战。具体到哲学领域,就是几千年来传统形而上 学的“真理(truth)”问题和近代哲学所发展而来的“实在(reality)”问题,都遭遇到 了现代技术所形成的完美的“超真实”的世界,也就是“虚拟”世界的挑战。用鲍德里 亚的话来说,现代技术的完美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使得我们再也看不见实在,不知道 实在为何物了。而原来我们基于经验所形成的对世界的看法和观点,却都是对“世界根 本性的幻觉”。
至此,我们不能不强调鲍德里亚对“虚拟世界”这一世纪之交的最热门话题的超前性 预测。也就是说,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他提出“仿真”和“虚像”这两个概 念,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表象问题进行攻击的时候,他已经敏锐地觉察到现代科学技术对 传统形而上学问题所构成的巨大冲击。而这一问题的提出,势必构成了对传统形而上学 有关“真理”、“实在”等哲学问题的严重挑战。这就是鲍德里亚的完美的罪行思想所 引发的形而上学问题的哲学反思。当然,他在80年代发展而来的玄学(pataphysics)也 是在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基础上,试图重构虚拟的“完美的”形而上学的尝试。对于这 一问题,需要进一步进行深入研究。
其次,从本体论角度看,鲍德里亚在谈论完美的罪行对实在的谋杀的时候,完全是一个“怀旧的”本体论观持有者。也就是说,鲍德里亚虽然强调虚拟世界的无孔不入、无处不在,强调其对现实的“实在”世界的掩盖,但在其心灵深处,他对传统的原始的自然的“实在”世界,有一种深深的怀念之情和惋惜之情。他肯定有那么一个本真的自然实在世界的存在,“实在不会在幻觉中消失,而是幻觉消失在全部的实在中”。这一思 想秉承了法国思想界,特别是自近代启蒙思想家卢梭以来惯有的抨击现实、回归“原始 自然”的一种精神向往和追求。这里,鲍德里亚有关现代技术与现代形而上学问题的论 述,其实涉及到现代技术哲学中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技术实在与自然实在的关系问 题。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已经深刻 地打上现代技术的烙印,我们已经很难看到一个原始的自然的世界。诺大的世界,已经 没有一方原始的自然净土了。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虚拟技术实在的存在,只是它不 是一种纯自然实在,虚拟技术实在已经完全没有原始自然实在的痕迹,变成了真正的现 代技术的“人造物”。但我们必须看到,现代技术所创造的虚拟技术实在虽然打上人的 活动的印记,但它仍然是一种社会性和实践性的实在。鲍德里亚所谓的完美的罪行,即 对实在的谋杀,其实质就是技术实在对原始的自然实在的侵蚀和遮盖。鲍德里亚把这两 种实在完全对立起来,从当今技术的社会实践效果看,并不一定完全正确。因为虽然大 量符号所造成的虚拟技术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但它终究替代不了现实的实在世界。鲍 德里亚对原始自然的实在的怀念虽然令人尊敬,但并一定完全正确。这一点我们必须要 有清醒的认识。
第三,我们必须清楚,鲍德里亚在强调“虚像”或虚拟世界的重要性的同时,已经陷入了极端悲观的技术决定论的陷阱。他在看到当今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巨大作用的同时,过分夸大了当代技术对我们生活和社会的负面的决定性作用,并对未来技术的社会影响持有一种极度悲观的心态。这是一种非常矛盾的心态的表现。一方面,他对现代技术的社会影响有深刻的体会,他也承认现代技术的巨大的社会威力;但另一方面,他却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影响做了一种完全悲观的负面的理解。在他看来,我们人类在我们的技术制造物面前,已经完全无能为力了,只能完全听命于技术之“物”的摆布。这一技术决定论基础上的悲观主义论调与上述对原始的自然实在的怀念是对应的,但也是我们不能 完全苟同,且必须对之批判的。我们说,现代技术的确具有巨大威力和不可预见性,并对传统的哲学问题构成了巨大的冲击。当今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包括符号的泛滥和虚拟空间的出现,确实需要我们对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问题,包括本体、存在、实在与虚无等问题进行新的思考,但却不能因此否定人在技术的面前的巨大作用,不能只见“物”而不见“人”。须知,既然人发明了技术,那么人在技术这一庞然大物面前,绝对不可能束手就擒,坐以待毙。我们既不能是技术的悲观论者,也不能是技术的盲目的乐观论者,而应当结合现代技术和社会的关系,进行认真的思考和分析。这是我们在研究鲍德里亚的技术哲学思想时,尤其要注意的。
总之,通过对完美的罪行的分析,我们认为,鲍德里亚的“完美的罪行”这一命题所包含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它丰富了技术哲学的内容。它既是技术意义上的完美,也是人的意愿和意志的完美的体现;完美的罪行既是对实在的谋杀,也是对传统形而上学问题的挑战;完美的罪行凸现现代技术社会的实在与虚拟问题,同时也是对现代技术的副作用的控诉。但与此同时,“完美的罪行”也暴露了鲍德里亚思想的极端的技术决定论和悲观主义的思想内容。这就是鲍德里亚“完美的罪行”的思想所包含的深刻而又复杂的哲学意义。
收稿日期:2003-0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