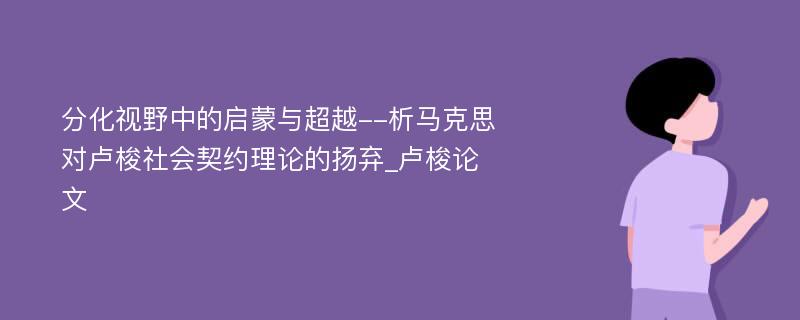
异化观上的启迪与超越——试析马克思对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扬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卢梭论文,马克思论文,启迪论文,契约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西方近代思想史上,洛克的“社会契约论”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之间的差异耐人寻味,双方在价值旨趣上虽然都强调“社会契约”对个性价值——自由、平等、财产、安全等“自然权利”的保护,但在具体路向上却各趋一途。在洛克看来,人类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是一种历史进步,因此,人们订立“社会契约”有利于每个人在公共权力的庇佑下获得更大发展;最好的国家是能保障个人“自然权利”的政治制度,这当然非“人民主权”的民主政体莫属。而依据卢梭的视角,人类由“自然状态”迈向“社会状态”意味着人的“社会——理性”异化,所以人们订立“社会契约”的目的在于解决异化问题;最好的国家是符合社会“公意”并克服“众意”(人们出于私心而杂合的异化理性)的民主制度,只有它才称得上名副其实的“人民主权”国家。卢梭的学说强调克服“社会——理性”异化,实现社会“公意”,因此其重点不在于洛克所关注的“个人与国家”关系,而在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他是西方近代史上对社会异化发出抗议之第一人。无独有偶,马克思继卢梭之后也对西方近代史上的同类异化现象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批判。这样,在“异化论”上,前者因其首开先河而闻名遐迩,后者由于最为深刻而铄古振今,双方存在着文化演序中一脉相承的契接关系。事实上,卢梭在其“社会契约论”的三大部分:“自然状态——天性说”,“社会状态——理性异化观”,“社会契约——异化克服论”中,先后探讨了近代人类发展不可避免的三大难题:人是否具有“本然”价值?社会异化对人类意味着什么?人类应当怎样克服社会异化?马克思正是在接着对这三太难题的再思索中,批判性地吸取并超越了卢梭思趣中的人类意义(扬弃其阶级意义),才达到了“异化观”理论的新高峰。
一、人是否具有“本然”价值?
卢梭认为,人作为万物之灵,自然秉有动物不具备的“本然”(内在于本质中的)价值——“德性”价值。他用“自然状态——天性说”予以论证:在自然状态中,人类在生活中起作用的只是两个先于理性的“天性”原理:“一个原理使我们热切地关切我们的幸福和我们自己的保存;另一个原理使我们看到任何有感觉的生物,主要是我们的同类遭受灭亡或痛苦的时候,会感到一种天然的憎恶。”(注: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67页。)这就是说,人禀有自我保存的“自爱心”与同情别人的“怜悯心”两大天性;而“自然法”(西方价值观认同的“自然存在的绝对公正原则”)则是这两大天性的协调与保障。由“自爱心”分生出天然的自由权利——每个人出于自保的目的都有权以“自由主动者”的身份活动;而由”怜悯心”导致了平等的自然权利——只有平等的个人之间才能和平共处。由此可见,在卢梭的眼底,“自然法”无形中代表着“至善”的普遍“公意”,因此由它规范的每个人的天性顺理成章地趋向善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道德的善同我们的天性是一致的”(注:卢梭:《爱弥儿》,下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11页。), 人类具有天赋的“本然”价值——道德价值,而“自然状态”就是以“德性”为基础的人人自由平等的人类“本然”状态。应该指出:卢梭提出人的“本然”价值,并非出于科学的实证,而是为了社会批判的需要。他要告诉世人:合理性的社会是符合人类“本然”价值——道德价值的社会,而现存的社会都不是出于人的“本然”价值,因此当然得不到人们道德上的(自律的)服从,难以成为每个人自由与平等的社会保障。据此,他提出:“实然”社会的合理性根据必须到人的“本然”价值中去寻找,这就要求人们抖落一切文明社会的负累而直抵作为始元的“天性”,然后依据天性的“本然”价值重新构筑适合每个人本性的“好的生活”,并以此订立能保障每个人自由平等的“社会契约”。由此可见,卢梭之所以设定人的“本然”价值,是他以人类天性的名义对社会所作的要求——实践理性意义上的“绝对命令”。在他看来,现实社会哪怕永远达不到它的要求,它对社会的要求也永远是合法(合“自然法”)的,而且是永远有效的。
马克思的思理认同卢梭关于建树人类“本然”价值的构想。在马克思看来,人作为理性的存在物,与动物相区别的根本特征之一就是对“合理性”生活的不懈追求,即使普遍意义的合理性境域在经验世界中永远无法达到,人也不会甘心处于不合理的现实之中,而总要借助于自己的奋斗去不断趋向理想目标,这就是人所特有的超越行为。在这个意义上,人为自身设立“本然”价值作为努力争取的理想目标,是完全符合人的本质生活的。但马克思不赞同卢梭把人的“本然”价值规定为“德性”价值,他从“实然”的异化劳动中考察出寓于其中的一般劳动的“本然”意义,并把它设立为人的“本然”价值。依据马克思的视界,作为文化创造活动的劳动实践,不仅是维护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手段,也是建构符合人性的合理性社会的最终源泉,因此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他指出:“实际创造一个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的自然界,这是人作为有意识的存在物(……)的自我确证。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则甚至摆脱肉体的需要进行生产,并且只有在他摆脱了这种需要时才真正地进行生产;动物只生产自己本身,而人则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与自己的产品相对立。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0—51页。)这就是说,人能按照各种物种的尺度和自身的内在尺度进行劳动实践活动(文化创造活动),并借助这一活动扬弃自然界与人自身的自在性与给定性,重新建立起人与自然的统一,这就是人所独具的“本然”价值。在这个价值中,人的劳动所秉有的“自由自觉性”理所当然地成为人的最深层本质。而由于人的改造自然的劳动必然是社会劳动,所以当每个人都在合理的社会分工中从事着自主活动时,他们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平等主体,从而真正做到了“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2页。)
根据马克思的以上理据,卢梭把人的“本然”价值归结为“德性”价值,显然是以偏概全的,它的根本缺失就在于割裂道德与实践之源的内在联系。从源头上看,道德发韧于人类的劳动实践。由于人类的劳动采取社会性的分工与合作形式,这就决定了人们必然进行协作和交往。而协作与交往一旦形成,就使个人进入到关系之中,他不仅要意识到自我,也须意识到他人,并要在自我和他人之间造就新的平衡。于是,人们在感情上形成相互尊重,在认识上内化外在的秩序和规则,在行动上确定共同的目的和意图。这一切就成为道德产生的直接动因。由此可见,“道德……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1页。)从实践上看,道德的功能从来不是天赋的,而是由人们在实践中自己建构的,即使是人的最高道德——全然的“无我之境”,也是“自我”根据现实生活的种种因果联系和必然性所作出的忘我的价值实现。换言之,也即“自我”立足于整个历史时代的文化精神,根据现实所提供的必然趋势与未来理想所选择的最高价值取向。在“自我”看来,自己在对理想和事业的执着追求中实现了自我价值与人类价值的浑融齐一:因为它使自己成为了整个社会群体不断绵续的一部分,成为了全部历史存在的更高形式的自我,因此,在这种实现中包含着自我的最高价值,自我作出牺牲是完全值得的。
二、社会异化对人类意昧着什么?
在卢梭的笔下,社会异化是人的无可奈何的宿命悲剧。卢梭用他的“社会状态——理性异化观”进行演述:自然人具有异于动物的特质——自我完善化能力,由此不断地推动了人类物质文明与知识理性的演进。然而,知识理性的进步却造成了人善良天性的消泯,当每个人的理性都发展到“这是我的”这类私有观念时,“自然状态”也就被非道德的私有制社会状态取代了。由此可见,社会的异化也即理性的异化,故可称为“社会——理性”异化。其异化的质底在于:文明的进步本应落实到人性的改造上,然而,无情的事实却是,“社会——理性”的演进不仅无助于人性的完善,反而使人性远离了“本然”的道德之源。这样,失去道德基础的私有制社会推行人奴役人的制度,就使人不仅沦为富人与暴君的奴隶,还沦为同伴的奴隶,沦为自身偏私、贪欲、虚荣、野心的奴隶,从而造成了个人自由平等权利的荡然无存。
马克思的“异化”观首肯卢梭关于“社会异化具有必然性”的思路。他指出:异化内在于人的生命活动——劳动之中,因为卢梭所谓的“人的自我完善化能力”在质底上就是劳动实践能力,由于人的劳动必然要采取社会分工的形式,而“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各个私有者之间的劈分,从而也包含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所有制本身各种不同的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4—75页。)因此,“分工和私有制是同个同义语, 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形式而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7页。 )资本主义私有制对个人的“本然”价值——“自由自觉的劳动”的贬抑,就是社会异化的底蕴。由此可见,社会异化的根源不在于人的理性而在于人的劳动,其实质不是“德性异化”而是“劳动异化”。
根据马克思的视野,劳动异化表现为“物役性”现象,即:“个人在一种社会规定(关系)上的物化,同时这种规定对个人来说又是外在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76页。 )在这里,“产品支配生产者,物支配主体,已实现的劳动支配正在实现的劳动”(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303—304页。 )。也就是说,人创造出来的物在一种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反过来奴役人,从而使得劳动不是对个性自由、平等发展的肯定,反而表征着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疏离。马克思剖析其原因说:“关键不在于物化,而在于异化、外化、外在化,在于物的权力不归工人所有,而归人格化的生产条件即资本所有,这种物的权力把社会本身当作自身的一个要素而置于同自己相对立的地位。”(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360页。)换言之, 也即资产阶级通过占有物(生产条件)而获得了统治无产阶级的权力。
然而,马克思坚决否认“社会异化对人类只具有悲剧色彩”的论断。在他看来,异化是人类发展必付的历史代价,因为历史的演进本身就内含着进步与代价的矛盾运动。历史不会直线式地正线上升,也不会一味表现为负线倒退,而是由上升与倒退交替进行构成的发展序列。这一序列的实质内容即是由进步与代价关系形成的张力:一方面,进步与代价相互对立,进步是对代价的否定,新的代价又是对旧的进步的否定;另一方面,两者又是统一的,进步借助扬弃代价来实现,而代价的付出恰是为了获得新的进步。因此,任何一种发展都是在克服代价的基础上达到的,没有付出代价的进步,本质上不能称之为发展意义上的进步。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异化作为人类发展的代价环节,否定中包含着肯定因素。它“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扬弃了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的“人的依赖关系”,从而为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个性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具体说来,(1)在资本主义社会, 人的活动及其产品均转化为交换价值,这既以人身依附关系的解体为前提,也以个人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为基础,个人间的这种相辅相成关系构成了他们社会联系和社会环境的主体内容,从而为恢复个性之间的平等权利提供了历史条件。(2)交往价值成为社会关系之中心价值, 普遍交换成为个人的生存条件,以致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第一次发生分化,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物的关系,这就强化了个人的独立地位,从而为往后、共产主义条件下的自由个性全面发展提供了人格前提。(3 )伴随着“物的依赖关系”的全方位扩张,人类历史成为世界历史,个人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生产和消费被置于世界市场之中,民族和地方的文学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6卷,〔上〕,第109页。),以致于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这就为人类扬弃异化奠定了丰厚的主客观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消灭异化的共产主义运动便应运而生了。由此可见:(4)“自我异化的扬弃跟自我异化走着同一条道路。 ”(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0页。)共产主义运动的主体是无产阶级,“工人在这里所以从一开始就站得比资本家高,是因为资本家的根就扎在这个异化过程中,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绝对满足,但是工人作为这个过程的牺牲品却从一开始就处于反抗关系中,并且感到它是奴役的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第48—49页。)这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由于丧失了生产资料而绝缘于个人自主活动(有益于个性发展的社会劳动),因而也失去了自我成全的手段,被资本主义社会异化为“非人”。这就决定了在无产阶级中必然产生出根本革命的共产主义意识。这个根本革命将彻底结束异化的私有制社会并使劳动复归于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从而恢复现实个人对社会的主体地位。由此可见,作为异化之扬弃的共产主义,不仅与异化的现实在世界处于抽象的对立之中,还与后者之间存在本质的关联,即异化的世界本身构成它的否定性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异化的扬弃被理解为一个过程的话,它也决不是外在于自我异化的另一个过程,因为异化的扬弃除开自我异化的世界之外并没有另一个“彼岸的”基础。
三、人类应当怎样克服社会异化?
在卢梭看来,人类克服“社会——理性”异化的途径应该是:诉诸革命来疗治社会的非道德顽症,并在革命之后,根据人的“本然”价值订立公正的“社会契约”,用民主政体来取代以往那种主奴模式的专制国家。为此,他在“社会契约——异化克服论”中解喻道:既然人是由于无情的宿命和自身的私欲才沦为社会的牺牲品的,因此,为了消灭社会异化,我们“应当回到原始的状态和原始的本性,不是为了停留在这种状态,而是为了以此为出发点,彻底重建我们的生活。这时我们就不会再屈从自己的本能和欲望,而会自己选择方向,支配自己的命运了。”(注:E·卡西勒:《启蒙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第266页。)这就“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 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护卫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结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象以往一样地自由。”(注: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3页。)卢梭为人类选择的是扎根于每个人的德性中的以“社会公意”为归依的民主国家模式。在个人方面,每个人都根据“完全出自理性的普遍正义”(自然法的别称)(注: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8页。)签订“社会契约”,并向由此而产生的国家转让全部个人权利,这样,得到了“自己所丧失的一切东西的等价物”,即能用集体的力量来保全自己的利益。在社会方面,由于社会集体的形成源于每个参加者的道德之心,因此它完全合乎人类的“本然”价值。这样,在人们依据公德创立集体规则并自律服从的意义上,社会存在着“道德的自由”——“社会公意所约束着的社会自由”。又因为“公意”是扎根于每个人德性中的正义性综合,而不是个人私心杂合的“众意”,因此,“公意永远是公正的,而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注: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9页。)。这样植基于“公意”之上的社会也就永远是正义的。在国家方面,国家秉承“公意”而建构,并以其至高无上的法律保护“公意”,但国家的立法权属于构成国家的每一个公民,其行政官员随时处于人民的监督之下。这样,当“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而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注: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4—25页。)时,国家便体现为所有平等公民的“人民主权”。
马克思的理论认为,尽管卢梭的思致因其未着眼于消灭异化的根源——私有制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他所倡导的用革命否定非人道的专制权力,用民主制取代君主制的路向至少在现实的历史中完成了两个进步:(1)在政治上, 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相对于封建主义的“权本主义”是一大进步。个人主义的局限表现为它在实际上的“物役性”(物的依赖性)——物质财富的增长以牺牲人的全面发展为代价;但它至少以人本主义的名义宣告了“人是目的”并赋予道德以一定的地位。而“权本主义”则根本否认个人的独立性与价值,它只承认专制权力的绝对目的,并把无条件服从专制权力作为最高的道德准则。在它看来,权力的存在是人存在的根据,权力的价值是人的价值的根本尺度,有权就有一切,无权就一钱不值,于是权力成了法力无边的神。在这种氛围中,“权力崇拜”随之而来:人的一切行为为了权力;人的一切理性服从权力;人可以不择手段去窃取权力,人可以拼命钻营去分享权力,人可以寡廉鲜耻去讨好权力。“权本主义”的温床滋生出各种各样的畸形人格,如暴君人格、两面派人格、奴才人格等等。总之,在“权本主义”者那里,唯有私利,没有道德;唯有主奴等级,没有人的尊严;唯有弱肉强食的兽道,没有自由平等的人道。可见,“权本主义”比“个人主义”具有更大的落后性。(2)在经济上, “资本剥削”形式取代“权力剥削”形式也是一种进步。所谓“权力剥削”是指,君主官僚集团凭借专制特权,无偿地占有社会财富与必要劳动。它与“资本剥削”相比,具有更大的野蛮性。“资本剥削”的基础是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而“权力剥削”的基础是少数人拥有的政治特权。“资本剥削”至少在外观上遵循等价交换原则,而“权力剥削”则是赤裸裸的不等价交换。“资本剥削”主要发生在社会产品的分配过程中,“权力剥削”则主要发生在社会产品的再分配过程中。“资本剥削”占有的是他人的剩余劳动,“权力剥削”则占有他人的必要劳动。然而,从根本上说,卢梭的“异化克服论”毕竟只达到了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水准,如果要用它来完成“人类解放”,无异于痴人说梦。因为卢梭的理想是通过每个人返回天性的“全善”来达到社会公意的“全智”,最终完成国家组织形式的“全能”,而这只能在人上升为神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这样,卢梭的设计在根本上有悖于人的存在本性,因此只能是一种人永远无法抵及的“乌托邦理想图”。
马克思主张,克服社会异化不能仅停留在“政治解放”的表层与“伦理重构”的幻想,而应深入到“人类解放”的深层——消灭异化的渊薮:私有制与异化劳动。这一任务的完成只能借助于共产主义运动。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留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注: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2卷,第120页。)从中可见:
第一,共产主义在价值取向上要复归人的“本然”价值。马克思认为人的发展曾经有赖于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私有制),但人在异化劳动或私有财产中实现自己本质的同时,也背离了自己的“本然”价值,发生了“物役性”的社会异化。所以,社会异化实际上是人的自我异化,对它的扬弃也必须是人自己的事——必得“通过人”。“通过人”要做的事是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它要达到两个目的:一是改造背叛人类“本然”价值的私有制环境,实现公有制,使联合起来的个人占有高度发达的全部生产力的总和。这样,“自发”的旧式分工就能被人类的“自觉”分工所取代,从而使劳动从个人谋生的手段转化为全面发展自由个性的功能,真正表现为人的“自我实现,主体的物化,也就是实在的自由。”(注: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6卷〔下〕,第122页。 )二是改造人在阶级社会中发展起来的异化人性,使人成为无愧于“本然”价值的新人。这样,“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办法能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的东西,才能建立新社会的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第40页。)也就是说,只有经过革命,现实的个人被锤炼为赋有新社会品格的新人,才能扬弃异化劳动而从事自由劳动,并且与新的社会环境溶为一体。
第二,共产主义在核心目标上要实现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异化的扬弃除开落实到现实个人本身的丰富与发展外,并无别的目的,所以它只是“为了人”。正因为异化的扬弃在质底上是对人的“本然”价值——“自由自觉的劳动”在生命状态上的确认,它由此才成为“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或所谓“人向自由、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所以,共产主义的最终要求不是结束物对人的统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而是一切形式的人对物的仰赖和屈从。它所追求和实现的人对物的那种驾驭,不是以生产资料的占有为人的主要的乃至唯一的所求,而只是把这种占有视为对自己的本质对象化存在的占有,从而在占有的基础上使人的社会活动达到质的提升:由满足人的生理需要为中心转向以追求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由消极地占有外部物质财富转为主动地创造、发展自身,占有精神财富和时间财富。
第三,共产主义在社会形态上要达到“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马克思的眼底,共产主义所要达到的“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本身即是人的生命活动的体现,因而是历史(人的生命活动的真正延伸)的,是依照人的内在尺度或属人的需要实现的,因此它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人类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实现着的“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提升,说明了共产主义恰是高于以往任何社会的新型社会。在经济上,它保存并扩延了以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从而为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在政治上,它保存并超越了“政治解放”的积极成果,以消灭阶级、消灭国家的形式使人的“原有力量”回归社会母体,从而实现了名副其实的自由、平等人权。在道德上,它保存并弘扬了人类德性的全部精华,使个人的全面发展能与所有人的全面发展在道德职责的基础上谐调一致。不仅如此,马克思甚至认为,共产主义就是道德职责——个人全面发展这一职责的实现和现实:“个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到了外部世界对个人才能的实际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为个人本身所驾驭的时候,才不再是理想、职责等等,这才真是共产主义者所向往的。”由此可见,共产主义社会的性质正如马克思自己所界定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纵观全文可见,马克思的异化观是对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批判性吸收与超越。它表现为:在“人的‘本然’价值观”上,马克思以“自由自觉的劳动”价值超越了卢梭的“德性”价值;在“社会异化说”方面,马克思以“劳动异化论”超越了卢梭的“理性异化说”;在“社会异化克服论”上,马克思以“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学说超越了卢梭的“政治解放”思趣。由此可见,马克思的社会思想远非卢梭所能比拟,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卢梭的社会观仅着眼于“实然”的市民社会,而马克思的眼光则远眺后资本主义的“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
标签:卢梭论文; 社会契约论论文; 共产主义社会论文; 人类天性论文; 共产主义国家论文; 人类进步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