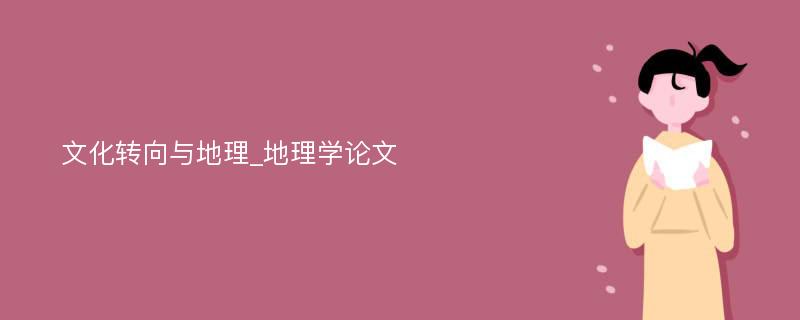
文化转向与地理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理学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几十年来,在西方(主要是英语国家)人文社会科学中出现了对文化研究的热潮,被称为“文化转向”,有评论说,这一发展可看作“二战”以来的一次极为深刻的社会观与政治观的变化。多种社会学科均将“文化”置于研究的焦点,在有关社会正义、归属、认同、价值等问题的研究中,创出一派新局面。在文化转向的社会科学潮流中,人文地理学者亦十分活跃,而文化地理学更因时而动,成为最具时代精神的地理学分支之一。
英国地理学家约翰斯顿,在其有名的当代地理学评述著作《地理学与地理学家》第五版中,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人文地理学发展正名为“文化转向”,明确列为一章。新近出版的由西方文化地理学骁将邓肯等人主编的《文化地理学读本》(A Companion to Cultural Geography,2004)中,拿出两章,专门研讨“文化转向”。西方人文地理学中的文化转向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后现代思潮为理论基础,以所谓“新文化地理学”的崛起为主要代表。一般认为,英国地理学家杰克逊(Jackson)与考斯格罗夫(Cosgrove)首发新文化地理学的先声,提出要注重文化的内部运作、符号生产与价值内涵,进而基于这些内容来考察空间构成、空间秩序、空间竞争。“文化转向”令本来就相当人文化的西方地理学,向社会人文渊薮中又深入了一层。
由于社会人文的繁盛滋生,社会问题日益多于自然环境的问题,人类社会自身的危机凸现在思想家与学者面前。早在十八世纪,马尔萨斯便指出社会问题可能比自然问题更为紧迫。一八七一年德国的统一,使地理学家拉采尔十分振奋,他将注意力从学院式研究转到德国的人文现实,研究德国人如何生活。拉采尔并到世界各地考察。十一年后,他出版了《人类地理学》第一卷,又过九年出版《人类地理学》第二卷。尽管拉采尔将“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用于人类社会,有许多负面影响,但拉采尔的研究毕竟开西方人文地理之先河,百多年来,西方人文地理研究一直在强劲发展。
二十世纪的前半,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影响很大,地理学家索尔(Carl Sauer)受其影响,将人类学、社会学的视角引入人文地理研究。以致在用词上,索尔也喜用area这个人类学家常用的词,而当时地理学家用得多的是region。索尔后来执教于加州伯克利大学地理系多年,在他的带领下,逐渐形成了极具文化特色、历史特色的“伯克利学派”。一般说,西方成熟的文化地理学,就是从美国伯克利学派开始的(而二十世纪后期的“新文化地理学”也是以挑战伯克利学派而产生的)。地理学与其他社会科学携手,拓展视野,更新视角,吸收相关理论,不断丰富自身的内容,这是西方人文地理学持续深入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只要翻看一下约翰斯顿编辑的《人文地理学辞典》(柴彦威等译,商务印书馆二○○四年版),就能发现西方人文地理学的概念阵容相当宽,许多重要的社会科学的基础概念、前沿概念,在人文地理研究中都有所借鉴。
伯克利学派采用的文化概念,是在否定环境决定论的背景下(索尔批判的对象是自己的老师森普尔女士与当红学者亨廷顿的观点),借鉴了人类学家的“超机体(superorganic)”文化概念,将文化(而不是自然环境)看作制控人类行为的重要力量,而且是一种稳定的力量。在文化、环境、人三者的关系上,文化是动力,人是行动者,环境是改造对象。文化的存在先于行动的人,这是伯克利学派研究的前提。这种文化概念,其实也是传统的对文化的理解方式。英文culture(文化)一词,其拉丁原义是“栽培”、“养育”的意思,人有了culture,就是受到了培育、教养。所以早期人类学者表述的文化概念常有“超机体”的味道,如:“文化有它自己的生命,受着它本身的原则以及它自己的法则所支配。几世纪以来,它怀抱每一代刚出生的成员并将他们塑造成人,提供他们信仰、行为模式、情感与态度。”(怀特)在这类文化概念中,有很强的文化决定论色彩。
以一种既定的文化为参照,或以抽取文化特征为第一步基础工作,然后考察人——按照文化原则行动的人——如何改变了自然景观,而创造出相应的文化景观,是伯克利文化地理学派主要的研究套路。因受早期人类学的影响,索尔本人的文化地理研究对象主要是非欧洲文化区,且重农村轻城市。索尔的学生逐渐重视“美国文化”,对美国本土文化景观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其综合成果以《美国文化地理》一书为代表。此书作者泽林斯基(Wilbur Zelinsky,索尔的学生)明确表示,他采用的是“超机体”文化概念,并刻画了“美国文化”这个超机体的特征:一、强烈的、几乎是无政府的个人主义;二、视动态与变化为最高价值;三、机器主义的世界观;四、尽善尽美主义兼救世主。泽林斯基从这几个方面着眼,分析了美国文化景观的特色。
二十世纪二十至五十年代,是美国文化地理伯克利学派的兴盛期,影响很大。索尔本人也曾当选美国地理学家协会主席。对伯克利学派(英文地理学文献中也用索尔名字的变体Sauerian指称这个学派),在回顾西方近代地理学发展的著述中,总有大段评论。二十世纪初的地理学界,对学科性质的理解依然含混不清,而索尔倡导以文化景观为研究对象,很清楚明白地确立了地理学的一个人文方向。
不过,对于中国地理学界来说,索尔的名字似乎是近一二十年才开始为人们熟知。在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尽管中国学者奋力引进西方现代地理学理论,但对索尔的学派似乎未多留意。在近代编写的众多中文地理文献中,鲜见索尔的名字。此种情况或许由于两项原因。二十世纪初,国家贫弱,中国地理学家一来救国心切,二来以科学精神为尚,故多看重救国救民的“人生地理学”(经济地理)与科学描述山川大地的自然地理学。索尔的文化研究远不及环境决定论具有更多的“科学”震撼性。另一项原因,现今文化地理学的发展高潮,提升了索尔学派的历史地位。在二十至四十年代,索尔学派尽管在美国国内享有声名,但在世界地理学界,或未及今天想像的那般显赫。
伯克利学派使用的“超机体”文化概念,乃是预设了社会上存在一个主导性的覆盖整个社会的文化力量,这一文化力量是给定的、统一的、稳定的。而对于这个文化,即主流文化,学者们是可以准确无误地再现陈述(representation)的。“超机体”文化概念不是索尔的创造,而只是传统的延用。这一传统文化概念在二十世纪中后期开始遭到激烈批判。在话语、文本、解构等新潮理论的背景下,超越人自身而存在的“超机体”文化概念当然被抛弃。进而,对文化景观的理解也出现新的视角,景观不再是客观的自在情景,而是要凭主观“阅读”的“文本”,一切符号意义、文本误读、再创作等问题随之而来。新文化地理学最初给人的印象,多是就这些问题进行阐发。
随着文化转向的深入,新文化地理学的关注范围开始加大,其主要表现在对“社会空间(social space)”的非正义性进行批判。对文化概念的新理解是文化地理研究范围拓展的理论基础。关于文化的概念,新派学者们放弃了“生活方式”这类散漫描述,而直指文化内涵的焦点——价值观以及相关联的符号意义。地理学家考斯格罗夫说:“目前人文地理学中的文化转向,引入了新的隐喻和类比,它们更符合对意义而不是功能的强调。”学者们进而指出,社会中的价值观是多样的,相互冲突的,可以演变的。对于长期被忽略的“他者(others)”的文化价值,应给予关注、同情,并为其所受的来自“主流”文化的歧视、压抑伸张正义。
各类后现代思潮推动了对“常规”观念的挑战,而所谓常规观念正大量流行于西方社会。如果说,洪堡、李特尔是考察非西方世界而开近代地理学之先河,那么后现代地理学则是以研究西方社会自身而兴起。西方社会的弊病,尤其是美国社会的弊病,成为激进学者们群起而攻之的对象。在对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不公正性进行挖掘时,价值观的潜在影响,价值观的压抑、冲突,几乎到处被发现,在西方社会园囿中,原来也是荆棘丛生。
在以西方(美国)为代表的现代化社会中,在社会空间的分布格局上,显现着或隐现着许多歧视、压抑、排斥、不公正的情景(如女性空间、同性恋空间、无家可归者空间等等),这些正是新文化地理学在“文化转向”中关注的主题。以社会空间取代自然空间(甚至完全放弃自然空间),是新文化地理学研究主题的一大特征。随着文化概念的变化,文化地理学研究的不仅是文化人的地理,而且是具有种种价值属性的各类社会群体的社会空间。正因为此,令文化地理学与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的许多研究相交错。因以“价值”为核心的新文化概念的普遍应用,诸学科均将各类社会群体的价值表述纳入研究视野,“文化转向”遂成风气。
社会存在、社会关系的空间形态,与其时间形态一样,属基本形态。而具体的空间形态总与特定价值、符号、意义相对应,于是文化地理学以特有的空间思维,揭示价值的空间形态,讨论符号意义的空间再现。在人文社会研究中,地理学的地位再次受到尊重。而在“文化转向”的同时,社会学、政治学等亦出现“空间转向”,社会空间问题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所谓“社会空间”,不是指一个客观、抽象的几何空间,可以在里面“填充”各类社会内容。社会空间总是具体的,是具体的社会事物的存在形式。对社会空间的任何“填充”其实都是“侵入”和“争夺”。社会空间不可能是一种静止的存在,社会的任何发展震荡,都将导致社会空间的变异、空间话语的更新。
后工业社会的发展,导致一系列社会变化。面临这个时代,英国文化学者戴维·钱尼说:“文化以及一系列相关概念,不但是位于核心的话题,同时也是最有效的学术资源,可以促使我们重新理解当代社会生活。”“如何理解现代、现代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后现代,这成为文化转向的触因以及文化转向中一再遇到的问题。”对现代社会中社会空间的文化诠释,自然成为新文化地理学者踊跃而先的领域。
女性主义在西方社会科学中的膨胀,在文化地理中也有反映,甚至有人以为女性主义地理学家(不必都是女性)是新文化地理学的重要推动群体。社会空间中的女性空间与男性空间的“争夺”,被充分讨论。大社会是男性空间的天下,“家’则是男性空间压迫女性空间的场所。住宅是给“标准”家庭设计的,而女性、残疾人都不是主要考虑的对象。女性在家是unpaid worker(无偿工作者),而男性在家是享乐者。家对男人、女人意义不同。城里的雕像是男性英雄,象征男人成就。而商场却是以诱惑女性消费为主题的。所谓“公共空间”其实是男性空间,而完全不考虑女性的安全感,天黑之后则更是青年男子的世界。
家,可以是与外部大社会对抗的基地,是家庭暴力的巢穴,是男人失意时的避难所。但“家”又是“无家可归者(homeless)”无法企及的一种空间。在美国社会“无家可归者”是一个显著的社会群体,他们在街角、公园渐渐创造自己的空间。伯克利大学校园外面不远处,有一块草地,其间驻满“无家可归者”的营帐,是一个有名的“另类”空间。
唐人街是移民空间的代表,尽管华裔社会学家提醒人们“中国不是一个只会开饭馆的国度”,但中式餐馆仍是唐人街的象征。无论几代下来,在唐人街生活的华裔仍摆脱不了“移民”、“另类”的社会定位。是这个“社会空间”令华人永远翻不了身。想进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华人,则必须离开这个空间、这个场所。然而,他又必须在新的、十足美国社会(所谓美国主流社会)的空间中,“挤”出一块“上等华人”、“美式华人”的空间,这又谈何容易。鉴于他的身份,他的文化空间永远是一个问题。在归属与选择之间,充满痛苦。
美国黑人群体、女性群体,甚至同性恋群体、流浪群体都在力求显示自己的文化,争得自己的社会空间,而一部分华人则要掩饰自己的文化,化解自己的社会空间。这种不同的趋向反映了不同的历史经验,也反映了不同的价值观,一些华人以为“丢人”、“低人”的东西,黑人、同性恋者并不以为然。
文化学者们注意到,在今日社会(不只是西方社会),有一类迅速壮大起来的文化形态,正在空间中迅猛扩展,它就是大众流行文化。流行文化的迅速扩展,使原有文化秩序混乱,精英文化不再是社会文化的主宰者,流行文化开始主宰社会。边缘文化、底层文化(如街舞、土话小品)汇入流行文化而抢占空间,在景观中凸显。进入了这样的气氛中,知识分子虽然更加自由,却失掉了对社会的影响力。大量文化形式转化为产业,成为消费资源。我们新拥有的不仅是“知识经济”,也是“文化经济”。
一些学术知识是流行文化的重要资源。地理知识从来贴近大众,如今更卷入流行文化、时尚文化,在市场中畅行。美国的《美国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加拿大的《加拿大地理》(Canadian Geographic)和英国的《地理杂志》(Geographical)都有很好的市场效益。中国的《中国国家地理》、《华夏人文地理》也是同样。史学、考古学的一部分知识内容也转入流行文化,但它们的话语权却根本不在历史学家或考古学家手里。
流行文化具有抢占社会空间的天性,在流行文化占据的辽阔空间中,很难再找到精英文化的符号象征。城市空间、媒体空间是广告话语的世界,而广告话语依托的正是流行文化。承认一个场所等于接受一个意义框架。在影视、报刊、广告充斥的空间场所中,受众(无论他的真实身份怎样)一律被定位为“消费者”,因为流行文化的消费性大于审美性。在这样的社会空间中,文化精英们首先感到了文化危机。
文化精英,其实不只是文化精英,在流行文化获得空间霸权的时下,必须进行空间的重建或改组,以证明自身的价值,住宅装修即是最基本的空间重建与符号设计。在流行文化的压力下,各类社会群体都在建构不同类型的空间场所,以展示这个群体的重要价值与关系结构。社会空间的改组动力不仅仅是金钱,更有文化。能动者善于组合环境中的资源,而消极者在社会动荡中只是环境的奴隶。从文化地理的角度说,如何与流行文化分庭抗礼,确保自己的社会空间,并张扬自身的价值,是社会空间重新分配的重要课题。郊区向来是精英们看不起的地方,但现在可能是一种文化保留地。“郊区是一种出于道德考虑的居住形式,就这一点说,是一个相当现代的场所。”(钱尼)。
社会贵族(出身的、精神的、政治的)对大众流行文化的反抗办法,是打造自己的空间场所,尤其要区别于“大众”,抢占社会空间的“头等舱”。而为社会贵族刻意打造头等舱的做法,正是大众文化流行框架下的产物。文化框架不仅提供意义,也提供词汇,今天的“贵族”已经丧失自己的词汇,所以,社会贵族空间已不复存在。旅游文化是十足的大众流行文化,也是典型的大众地理文化,它将各类神圣文化、高雅文化的空间场所(皇宫、贵族庭院、教堂庙宇、高等学府)与地方特色空间(古村落、古城邑、自然绝景)统统改造为大众旅游文化空间。
文化在社会中的变化与震荡,深深地影响着今日的生活。文化转向的确以文化危机为诱因。“空间就是金钱”,然而与金钱并行的还有“空间就是文化”。社会地理学家哈维说今日的社会空间正在被压缩,高密度的社会空间令人窒息。私人空间、群体空间、公共空间、功能空间(包括环境空间)之间的竞争正在改变社会空间的整体格局。我们不得不面对这场文化的空间转向,如果不愿做空间环境的奴隶,就必须要清醒和敢为,这就是新文化地理学正在提醒我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