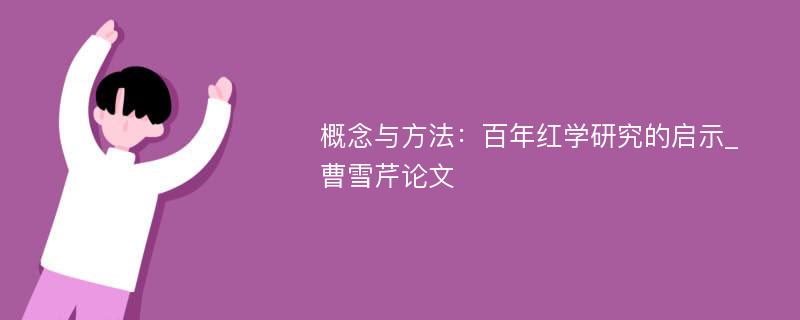
观念与方法:百年红学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学论文,启示论文,观念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的学者曾将本世纪的红学分为三个时期,即1921年前的旧红学时期,1921年至1954年的新红学时期和1954年之后的当代红学时期。然而我们却不难发现,新红学的建立并不意味着旧红学的终结。同样,1954年之后,旧、新红学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其地位与影响与未可小视,红学似乎呈现出一种“无时序状态”。因此,依照时间顺序将红学划分为若干个时期的作法似乎意义不大。依笔者之见,百年红学之争,实际上是观念之争与方法之争,而观念与方法也正是今后红学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有鉴于此,本文拟从观念与方法入手,对百年红学略作剖析,以就正于诸位方家。
一
20世纪初,新红学的创立者胡适与旧红学索隐派的代表蔡元培之间曾有过一场激烈的论争。当时虽然谁也没有说服谁,但索隐派占据红学主导地位的局面却由此打破了。人们原以为索隐派从此会销声匿迹,然而事实却远非如此。就在新红学不断发展的二三十年代,又出现了阚铎的《红楼梦抉微》、寿鹏飞的《红楼梦本事辩证》和景梅九的《石头记真谛》等索隐派的论著。直至八九十年代,有人仍宣称“要理直气壮地维护索隐派”(注:许宝骙:《抉微索隐,共话红楼》,载1981年5月2日《团结报》。),冯精志则连续出版了三部索隐式作品:《百年宫廷秘史——〈红楼梦〉谜底》(1992)、《大观园之迹》(1993)、《曹雪芹披露的宫廷秘闻》(1995),还有作者自称是“索隐考证派”的《红楼解梦》(注:霍国玲、霍纪平、霍力君:《红楼解梦》,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初版,中国文学出版社1995年增订版。)等等。
索隐派前后绵延了近一个世纪,尽管上述著作各自的动机、内容、结论不尽一致,但其观念与方法却有着共通之处。在索隐派看来,小说既然是“野史”,那么其中肯定有着历史的影子。何况曹雪芹开卷伊始便明确告诉我们“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不过实录其事,又非假拟妄称”。再如《儒林外史》、《孽海花》等小说也的确隐含着真实的事件和人物。于是,他们千方百计地要求索出《红楼梦》所隐含、所影射的“本事”或微言大义。他们从历史著作、野史杂记、诗词随笔以及民间传闻中,搜集有关的或似乎有关的资料,与《红楼梦》中的描写相互排比对照,猜测推想,穿凿附会。尽管难以自圆其说,前后抵牾,甚至漏洞百出,他们却自以为找到了《红楼梦》的真谛。毫无疑问,索隐派的观念与方法是不正确的,但是仅仅给他们加上主观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的帽子,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关键在于指明其观念何以有误,其方法何以不妥。
能够从理论上阐明索隐派观念与方法的还应首推蔡元培先生。他在1922年为《石头记索隐》第6版所作的《自序》中,一方面为“索隐”辩护,一方面又反驳了胡适的“自传说”。蔡元培先生认为:
胡先生以曹雪芹生平,大端既已考定,遂断定《石头记》是“曹雪芹的自叙传”,“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自叙的书”,“曹雪芹即是《红楼梦》开端时那个深自忏悔的我,即是书里甄、贾(真假)两个宝玉的底本”。案书中既云真事隐去,并非仅隐去真姓名,则不得以书中所叙之事为真。又使宝玉为作者自身之影子,则何必有甄贾两个宝玉?(鄙意甄、贾二字,实因古人有正统伪朝之习见而起,贾雨村举正邪两赋而来之人物,有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等,故吾疑甄宝玉影宏光,贾宝玉影允礽也。)
蔡元培先生还以《儿女英雄传》和《儒林外史》为例论道:“《儿女英雄传》,自言十三妹为‘玉’字之分析”,“又以纪献唐影年羹尧,纪与年,唐与尧,虽尚简单,而献与羹则自‘犬曰羹献’之文来。”“《儒林外史》之庄绍光既程绵庄,马纯上即冯粹中,牛布衣即朱草衣”。认为这种作法“正是中国文人习惯”。因此,他认为研究《红楼梦》的思想主要应从推求书中人物入手,研究的方法可从三方面去推求:一是“品性相类者”,二是“轶事有征者”,三是“姓名相关者”(注:《石头记索隐》第6版《自序》,载《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42~146页。)。
对于蔡元培先生的这种观念与方法,胡适于同年在《跋〈红楼梦考证〉》中曾给予了批评。胡适认为“有几种小说是可以采用蔡先生方法的”,如《孽海花》、《儒林外史》。但“大多数的小说是决不可适用这个方法的。历史的小说如《三国志》,传奇的小说如《水浒传》,游戏的小说如《西游记》,都是不能用蔡先生的方法来推求书中人物的”。又引用了顾颉刚先生举出的两个重要理由来说明这一点:
(一)别种小说的影射人物,只是换了他姓名,男还是男,女还是女,所做的职业还是本人的职业。何以一到《红楼梦》就会男变为女,官僚和文人都会变成宅眷?
(二)别种小说的影射事情,总是保存他们原来的关系。何以一到《红楼梦》,无关系的就会发生关系了?例如蔡先生考定宝玉为允礽,黛玉为朱竹垞,薛宝钗为高士奇,试问允礽和朱竹垞有何恋爱的关系?朱竹垞与高士奇有何吃醋的关系?
于是,胡适得出结论说“正因为《红楼梦》与《儒林外史》不是同一类的书。用‘品性,轶事,姓名’三项来推求《红楼梦》里的人物,就像用这个方法来推求《金瓶梅》里西门庆的一妻五妾影射何人:结果必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注:《跋〈红楼梦考证〉》,同注③第137~139页。)。
应当承认,胡适、顾颉刚的意见是正确的,但为什么却说服不了索隐派以至于索隐派的论著继续出现呢?笔者以为原因有这样几点:首先传统的小说观念根深蒂固。究竟什么是小说,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已不成为问题。但是在古代,却是一个长期处于模糊状态的概念。其中影响较大的一种观点,便是将小说视为正史的补充,所谓“羽翼信史”、“补正史之不足”、“稗史亦史”等说法,就是这种观点的简略表述。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认为小说创作必须依据历史,只能作有条件、有限制的虚构,人们阅读小说也必须注重其史鉴功能,因而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明清兴亡史”,是一部“有价值的历史专书”也就理所当然了。其次某些小说的确有暗隐某事、影射某人的情形,如上面所举《儒林外史》、《儿女英雄传》、《孽海花》等,于是便极易使人们产生一种错觉,仿佛所有的小说背后都隐含着真实的事件和人物。再次,《红楼梦》真假结合、虚实相生的艺术手法更给人们留下了猜测的余地和想象的空间。作者自称“将真事隐去”,究竟隐去了什么样的“真事”?书中经常写到“判词”、“谜语”、“谶语”,其真实含义又是什么?最后,从索隐派的主观动机来看,或为某政治目的所支使,或为一己之兴趣所左右,或为造成某种轰动效应所故为。客观原因与主观动机相结合,索隐派的长期存在便是不言而喻的了。
我们搞清了索隐派存在的原因后,一方面可避免不再走索隐的路子,一方面可对索隐新著的出现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不但不为所谓的“新发现”所迷惑,甚至不必花太多的笔墨去与之纠缠。因为当代的索隐派正希望有人去反驳、去批判,这恰好符合了他们要造成某种“轰动效应”的初衷。
二
新红学之所以能够将《红楼梦》研究纳入科学规范的道路,为红学的发展打开一个新的局面,首先因为新红学运用了科学的研究方法。新红学的创始人之一胡适对方法问题有着明确的意识与主张,他曾说道:
我这几年做的讲学的文章,范围好像很杂乱,——从《墨子〈小取〉篇》到《红楼梦》——目的却很简单。我的唯一的目的是注重学问思想的方法。故这些文章,……都可说是方法论的文章(注:《胡适文存·序例》。)。
40年之后他又说道:
我是用乾、嘉以来一班学者治经的考证训诂的方法来考证最普遍的小说,叫人知道治学的方法(注:胡适1961年5月6日的谈话,载《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第374页。)。
胡适将其治学方法归纳为十个字,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曾引起人们的许多非议。科学研究离不开假设,但是这种假设应当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而不应当凭空设想。胡适实际上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在归纳出的十个字之后紧接着说道:“要大胆的提出假设,但这种假设还得想法子证明。所以小心的求证,要想法子证实假设或者否证假设,比大胆的假设还更重要。”(注:胡适1961年5月6日的谈话,载《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第227页。)联系到《红楼梦》的研究,他说:“要解决‘《红楼梦》有什么用意’这个问题,当然就有许多假设。提出问题求解决,是很好的事情,但先要看这些假设是否能够得到证明。……从事实上照极平常的做学问的方法,我提出一个很平常的假设,就是《红楼梦》这本书的作者在开头时说的,他是在说老实话,把他所看见的可爱的女孩子们描写出来,所以书中描写的人物可以把个性充分表现出来。”(注:胡适1961年5月6日的谈话,载《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第229页。)
胡适在提出这个“平常的假设”时,是依据了不少的材料和事实的,并非向空虚构。如关于曹家任江宁织造的情况,关于曹雪芹与敦诚、敦敏交往的情况,关于脂评本《石头记》的情况等等,他都有相当的了解和认识。在证明这个假设时,他对曹雪芹的生平家世、对《红楼梦》的版本都进行了实事求是的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绩。新红学的其他代表人物如俞平伯、顾颉刚以及众多的红学家运用考证的方法也都取得了累累的硕果。诚如顾颉刚早在20年代所指出的那样:
……红学研究了近一百年,没有什么成绩。适之先生做了《红楼梦考证》之后,不过一年,就有这一部系统完备的著作。这并不是从前人特别糊涂,我们特别聪颖,只是研究的方法改过来了。……我希望大家看着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从此悟得一个研究学问的方法,……(注:胡适1961年5月6日的谈话,载《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第246页。)
一种科学方法的运用,便可以从根本上扭转红学的方向,这的确能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
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考证的方法过去是,将来也依然是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但是如果把考证方法引向极端,远离了文学研究的目的,甚至于钻牛角尖、为考证而考证,那就失去了考证的意义。或者认为考证是唯一的研究方法,其他文本研究都是无根之谈,恐怕也非确论。有的红学家便宣称,不知道曹雪芹是谁的儿子,不知道脂砚斋是何人,不知道续书为谁所作,就无权研究《红楼梦》,这种说法本身就暴露出了对文学研究目的的模糊认识和狭隘理解。说到底,作者生平的考证也好,版本的考证也好,都是为文本研究打基础的,是文本研究的前期准备。没有这种基础固然难于对文本作出深入研究,但仅仅停留在此基础上,研究工作不过刚刚起步而已。考证需要有材料,由于种种原因,材料不完善或不具备的情形常常发生,考证工作难以向纵深进展,但绝不应因此就终止文本的研究。在更多的情况下,基础的考证与文本的研究是同步进行的。那种坚持认为只有将全部问题都考证确实之后,才能进行文本研究的观点,只不过是痴人说梦。
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运用考证方法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其“自叙传”的观点却又难以让世人苟同。为了证明贾府即曹家、贾宝玉即曹雪芹,而作的种种考证,更令人感到有胶柱鼓瑟、牵强附会之嫌。对此,胡适、俞平伯在以后的论著中都有所修正。这就告诉我们,考证应有正确的观念作指导。“自叙传”与“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虽相差仅有一步之遥,但却是两种不同的小说观念。如果一定要证明《红楼梦》就是曹雪芹的自叙传,那就必定会陷入自造的泥淖而无法自拔;如果将《红楼梦》视为饱含作者经历与酸辛的“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那谁又能不举双手赞成呢?就是这样一个观念上的修正,新红学花费了数十年的时间,而其造成的影响,恐怕至今仍未消失。
新红学在方法上的成功与在观念上的失误,都同样值得我们深思和记取。
三
将《红楼梦》视为一部小说并对其进行文学的研究,尽管被某些红学家所不齿甚至于将其排除在红学领域之外,但在百年红学史上,其地位与影响仍不可低估。与考证方法不同,文学批评方法与时代思潮、与审美意识等观念形态的东西联系更为密切。考证以资料为依据,文学批评则以理论为工具。考证得出的结论有可能成为终极真理,文学批评则很难画上一个最终的句号。但并不能因此就说,文学批评既无必要更无价值。全面正确地评价百年红学史上的文学批评的是是非非,对于今后红学的发展,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近来,有论者撰文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即“《红楼梦》文本的意义始终在云笼雾罩之中,从来没有真正地‘敞开’过”(注:见梁归智:《红楼梦研究的意义》,载《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1期。)。红学领域常常有石破天惊的观点冒出,这或许又是一个。我们不禁要问,《红楼梦》莫非是部“天书”吗?何以“始终在云笼雾罩之中”呢?这种表面上要抬高《红楼梦》、甚至于要将其抬入云端的作法,愿望或许是好的,但实际上却将《红楼梦》打入了冷宫。我们认为,如同所有的文学名著一样,对《红楼梦》文本意义的认识和把握,需要历代研究者的不断努力,不断探索,每一位认真严肃的红学家都为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是红学史上第一篇运用文学批评方法研究《红楼梦》的专论。王国维根据叔本华的理论,认为《红楼梦》在美学方面的价值,主要表现为它是一部“眩惑之原质殆绝”,“示人生之真相,又示解脱之不可已”的悲剧,是一部“彻头彻尾之悲剧”。他进而分析宝黛的悲剧原因“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注: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载《静庵文集》,光绪三十一年印本。)。在索隐派占据红学主导地位的光绪年间,王国维便能指出《红楼梦》的悲剧性质,显然是新观念与新方法的引入所致。尽管王国维的这篇专论还存在着许多的不足,但无论如何它标志着红学的一种发展与进步,表明着对《红楼梦》文本意义的一种理解和把握,而且这种理解和把握自有其深刻之处。
“五四”时期,不少学者运用西方的学术文艺观念和批评方法,使红学领域又出现了新的面貌。吴宓将《红楼梦》与但丁的作品相比较,认为《红楼梦》广泛地反映了社会面貌(注:吴宓:《红楼梦新谈》,载1920年《民心周报》第1卷第17、18期。)。佩之则进一步指出:“一部《红楼梦》,他的主义,只有批评社会四个大字。”“书里面的社会情形,正是吾国社会极好的一幅写照。”“生在几百年前的人,居然想到这许多重大问题,是很不容易的。书中攻击社会的地方,正是现在的人所竭力攻击的地方。”(注:佩之:《红楼梦新评》,载1920年《小说月报》第11卷第6、7号。)由于观念和方法的更新,这些评论文章对《红楼梦》文本意义的见解与说明都有其合理之处。但与此同时,西方文艺观念的过分搬用,也使其产生了某些不切实际的评论。
鲁迅先生也是一位受到西方文艺观念深刻影响的文学家,然而他却没有机械地照搬西方的观念与方法。鲁迅指出:
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载《鲁迅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28页。)。
《红楼梦》的写实性、真实性、创造性被鲁迅一语道破。对《红楼梦》的悲剧特征、对宝玉形象的社会内容,鲁迅也都作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在论及《红楼梦》后四十回时,鲁迅没有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而是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比较和评析。
到了40年代,许多红学家进一步集中研究《红楼梦》的文本,并且取得了新的成绩。1942年正中书局出版了李辰东的《红楼梦研究》,这是一部较全面研究《红楼梦》的论著。假如我们稍微留心一下便不难发现,凡是论者借鉴一些新观念、新方法时,往往能够有新的见解出现。例如他运用“缺陷论”、“补偿论”来解释《红楼梦》的创作成因,运用“移情说”来分析《红楼梦》的人物描写,运用泰纳的“意象说”来评论《红楼梦》的情感表现,运用德国美学家巩都尔富的理论来规定曹雪芹在世界文学里的地位,都是颇富新意的观点,对于打开人们的思路,帮助人们认识《红楼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还有一些评论者不同程度地接受并运用了新的观念和方法,认识到了人物形象的重要性,于是他们集中讨论《红楼梦》的人物。太愚的《红楼梦人物论》和张天翼等人的《贾宝玉的出家》便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的人物评论集(注:太愚:《红楼梦人物论》,国际文化服务社1948年印行;张天翼:《贾宝玉的出家》,东南出版社1945年版。)。我们先不谈他们观点的正误和分析的深浅,仅从他们采用的人物分析方法这一点来说,已经具有了开拓性的意义。
就在红学领域不断尝试着运用新观念、新方法的时候,新红学派的代表人物俞平伯先生却依然故我地在原地踏步,这集中表现在《红楼梦研究》与《红楼梦简论》两部论著中(注:《红楼梦研究》,棠棣出版社1952年版;《红楼梦简论》,载《新建设》1954年3月号。)。这两部论著的观念与方法并非一无可取,但平心而论,其提供的新东西的确是微乎其微,显示出一种观念的陈腐与方法的僵化。抛开政治的原因不谈,仅就其缺乏生机的观念与琐屑的研究方法而提出批评,也实在是情理之中的事。因此,李希凡、蓝翎两位青年学者运用新的观念和方法,力求对《红楼梦》作出新的解释,实际上是时代的要求,也是红学自身发展的要求。在这之后进行的《红楼梦》讨论和发表的若干论著中,何其芳的《论〈红楼梦〉》和蒋和森的《红楼梦论稿》(注:何其芳:《论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蒋和森:《红楼梦论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影响最为广泛,而它们恰恰是运用了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艺观念与方法。
80年代以来,观念与方法问题再度成为红学界关注的焦点,1982年在上海召开的红学会上,部分青年学者就提出了这一问题。各种新观念与新方法的引进,使红学领域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局面,《红楼梦》文本的意义正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各个层次逐步得到揭示。但是也应看到,观念与方法问题是一个永久性的问题,许多研究者习惯于静止的和纯微观的研究方法,重视资料的发掘、编纂和考订工作,忽视新观念与新方法的引进和运用。因此,就当前研究状况来说,新观念与新方法不是太多了,而是还远远不够。
总结以往的经验与教训,在运用新观念与新方法探讨《红楼梦》的文本意义时,有几点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一是对新观念与新方法不能机械照搬,要尽量将其消化吃透,变成自身肌体的养料,而不是附在表面的皮毛。当然,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需要对中西文化的全面深刻了解,需要深厚的理论素养。但是,我们也没有必要被其吓倒,任何学术研究都是累积型的,都是循序渐进的,我们的研究不要求、事实上也不可能达到终极的真理,只要做出了开拓性的尝试,其意义就远胜过稳健的原地踏步。二是在运用新观念与新方法时,应该有一种“自我否定”的精神。就是说这种观念与方法能否行得通,自己要先打上几个问号。要尊重其他的观念与方法,不要错误地认为只有自己掌握了真理。要善于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比较,要具备择善而从的心理素质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三是要尽量避免或减少非学术性思潮与因素的影响。蔡元培的索隐显然受到了排满反清的政治影响,胡适的自传说也与其政治观点相联系。实际上他们这些人的学问不可谓不深,识见不可谓不高明,然而一旦被非学术性的因素所干扰,就难免产生谬误和偏差。我们的研究既要体现出时代的特色,又要避免时代的局限,这是一个悖论,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解决的两难问题。
面对21世纪的挑战,我们必须认清《红楼梦》文本的研究乃是红学的当务之急,这就需要我们掌握科学的观念与方法,这是红学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之所在。
标签:曹雪芹论文; 红楼梦论文; 红楼梦评论论文; 红楼梦研究论文; 文学论文; 儿女英雄传论文; 读书论文; 儒林外史论文; 胡适论文; 孽海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