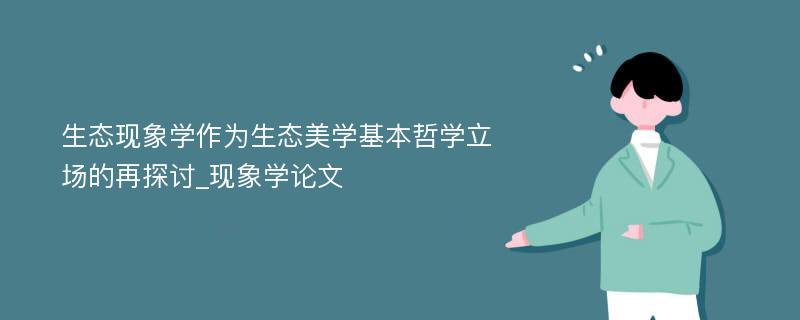
再论作为生态美学基本哲学立场的生态现象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论文,现象学论文,美学论文,立场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1 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4)05-0116-10 2011年本人曾写《生态现象学方法与生态存在论审美观》一文,发表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该文提出:“生态美学的基本范畴是生态存在论审美观,其所遵循的主要研究方法是生态现象学方法。”但该文主要论述的还是德国哲学家U.梅勒的生态现象学报告的相关问题,没有充分展开。本文希图在上文基础上更加全面地论述作为生态美学基本哲学立场的生态现象学方法,认为当代现象学的产生与发展就是为了克服现代工业革命过程中唯科技主义以及人与自然二分对立的二元论哲学观,因此整个现象学哲学都具有浓郁的生态内涵,均可称为生态现象学,经历了产生、发展与逐渐成熟的过程;而且,生态现象学反映了当代哲学的发展方向,是一种生态文明时代的主导型哲学。从其发展来看,到海德格尔已经是成熟形态的生态现象学,其表现为早期以“存在与世界”的生态存在论在世模式对主客二分的认识论在世模式的突破,后期是更加彻底的“天地神人四方游戏”在世模式的提出。而梅洛-庞蒂则以其身体哲学进一步沟通了天人、身心与东西。本文试从胡塞尔、海德格尔与梅洛-庞蒂着手,较为全面地论述作为生态美学基本哲学立场的生态现象学。 一、胡塞尔:现象学必然导向生态现象学 1.现象学产生于对欧洲唯科技主义哲学危机的批判 长期以来,我们片面地将生态现象学局限于2003年梅勒在生态现象学报告中所说的内容。其实,现象学本身就包含着浓郁的生态哲学内涵,就是生态哲学或生态现象学。早在20世纪初期的1900年前后,胡塞尔提出现象学哲学之时,就是基于对长期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欧洲唯科技主义哲学的批判。这是一种以科技思维特别是数学思维压制人性、压制自然的理性主义传统和形而上学传统,“涉及人在与人和非人的周围世界的相处中能否自由地自我决定的问题,涉及人能否自由地在他的众多的可能性中理性地塑造自己和他的周围世界的问题”[1](P982)。胡塞尔认为这种唯科技主义哲学导致的是一场哲学与文化的危机,当然也是一场社会的危机,并敏锐地预示着生态危机的到来。对于这种危机的批判与突破就是胡塞尔力创现象学的出发点,也是其现象学必然包含生态意识并走向生态现象学的明证。胡塞尔指出,这种危机表现为“对形而上学可能性的怀疑,对作为一代新人的指导者的普遍哲学的信仰的崩溃”[1](P988)。这里讲的“形而上学”与“普遍哲学信仰”主要就是指古希腊以来的理性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这种形而上学和普遍哲学信仰的特点就是将精密科学特别是以数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作为拯救哲学之途径与方法的楷模。胡塞尔指出,欧洲从古希腊以来特别是17世纪以来的传统就是“对哲学的所有拯救都依赖于这一点,即:哲学把精密科学作为方法楷模,首先把数学和数学的自然科学作为方法的楷模”[1](P40)。胡塞尔在这里指出传统欧洲文化将“数学和数学的自然科学作为方法的楷模”是非常贴切与重要的。因为,从古希腊以来由航海业的发达导致几何学的发达,导致其后数学以及数学的自然科学一直是欧洲统领性的学科,渗透于一切学科之中,乃至工业革命以降将宇宙与人看作机器等。这种机械的数学的思维是欧洲唯科技主义的主要特征,也是从算计的角度看待人与自然从而导致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以及对于自然的滥发的重要文化原因。胡塞尔已经在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深感这种思维方式的危害,而力求创造一种新的哲学,“它需要全新的出发点以及一种全新的方法,它们使它与任何‘自然的’科学从原则上区别开来”[1](P41)。这种新的哲学就是包含浓郁生态内涵的现象学即生态现象学。这是胡塞尔与传统的一种决裂,也是他对传统之中错误的可贵反思。他在写于1901年的《逻辑研究》前言中引用了歌德的名言,“没有什么能比对犯过的错误的批评更严厉了”。意味着他的“逻辑研究”及其现象学研究是对传统欧洲形而上学与人类中心错误的“批评”与纠正。 2.现象学的“悬搁”与“现象学还原”是对传统的人与自然对立的二元论的超越 胡塞尔深刻地总结了欧洲哲学发展的历史,认为尽管古希腊时期已经有了理性主义与形而上学传统,但17世纪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主客二分、人与自然对立的二元论哲学观才愈来愈加严重,特别是以伽利略与笛卡儿为其代表。他说,伽利略的几何学与数学说明“作为实在的自我封闭的物体世界的自然观是通过伽利略才第一次宣告产生的。随着数学化很快被视为理所当然,自我封闭的自然的因果关系的观念相应而生。在此,一切事件被认为都可一义性地和预先地加以规定。显然,这就为二元论开道铺路。此后不久,二元论就在笛卡尔那里产生了……可以说,世界被分裂为二:自然世界和心灵世界”[1](P1038-1039)。这说明,近代以降,人与自然二分对立的二元论哲学不断发展,成为人类压榨自然的理论工具。胡塞尔的现象学则是对于这种二元论的重要突破。他提出的重要原则与方法就是“悬搁”与“现象学还原”。对于“悬搁”,他说道,“但我要使用‘现象学’的‘悬置’(停止判断),它使我完全放弃任何关于时空此在的判断”[1](P383)。也就是说要“悬搁”或“悬置”一切在时空中存在的实体性判断,包括物质的与精神的都加上括号、加以排除或进行中止或者是存而不论。最后是“现象学的还原”,即“回到现象本身”。他说,“所谓现象学的还原:这就是在客观实在的所有入侵面前彻底地纯化现象学的意识领域并保持其纯粹性的方法”[1](P159)。也就是排除物质的与精神的实体回到现象本身即意向性,这就是一种“超越”。他说:“而纯粹现象学则是一门关于‘纯粹现象’的本质学说……这就是说,它不立足于那种通过超越的统觉而被给予的物理的和动物的自然,亦即心理物理自然的基地之上,它不做任何与超越意识的对象有关的经验设定和判断设定;也就是说,他不确定任何关于物理的和心理的自然现实的真理(即不确定任何在历史意义上的心理学真理)并且不把任何真理作为前提、作为定律接受下来。”[1](P688)在这里,胡塞尔机智地运用现象学的“悬搁”和“现象学还原”的方法,排除了任何物质或精神的实体性“真理”,从而将主客以及人与自然二元对立这一导致生态危机的哲学根基加以根本动摇。 3.现象学的“交互主体性”原则是克服“唯我论”与“人类中心论”的有效努力 胡塞尔对于交互主体性的研究开始于1905年,几乎与现象学的提出同步,一直延续至1935年之后,可以说交互主体性是与他的现象学研究一致的。而交互主体性理论是对“唯我论”与“人类中心论”的有效克服,某种程度上消解了人与自然的对立,包含着浓郁的人与自然相并、人与自然为友的当代生态哲学内涵。首先,交互主体性是对“唯我论”的一种有效克服。因为,现象学理论通过“现象学还原”悬搁了各种物质与精神的实体,最后只剩下“意向”,很容易被看作是“唯我论”,而“唯我论”以及与之相关的“人类中心论”本来就是欧洲传统哲学特别是近代欧洲哲学的本有之义。因此,胡塞尔对此非常警惕,在创立现象学之初就开始注意这个问题。他在著名的《笛卡尔的沉思》的第五沉思中指出,由于现象学的先验还原必然会引起“非常重要的异议”,那就是“如果我这个沉思着的自我,通过现象学悬搁,把自己还原为我的绝对先验自我时,我不就成为我自己的根据了吗?同时,只要我以现象学名义继续前后一贯的自身说明,我不仍然还是那个我自己的根据吗?因此,要解决对象存在问题并已经表现为哲学的现象学,不就要打上先验唯我论的印记吗?”[1](P876)为此,胡塞尔提出交互主体性的重要概念并对之加以解决。他说:“我所经验到的这个世界连同他人在内……并不是我个人综合的产物,而只是一个外在于我的世界,一个交互主体性的世界。”[2](P125)其内涵是“把一切构造性的持存都看作只是这个唯一自我的本己内容”[2](P204-205)。也就是说在意向性活动中的“自我”即唯一自我的本己内容与自我构造的一切现象即构造性的持存都是同格的,在意向性活动中构成“交互主体性”。胡塞尔还非常生动地运用现象学方法分析了“我”与“他人”的关系,指出在意向性活动中“他人”即是“主体”,“我”与“他人”的关系是一种交互主体性的关系。他说,“他们同样在经验着我所经验的这同一个世界,而且同时还经验着我,甚至在我经验这个世界和在世界中的其他人时也如此”,他将此称作是一种“陌生的、交互主体经验”。[1](P878)以上胡塞尔关于“我”与“他者”的交互主体性关系的论述非同寻常,解构了传统哲学中主客以及人与自然的二分对立,为新的“并存”与“共生”等生态哲学观念的产生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海德格尔:成熟形态的生态现象学 美国现代生态理论家将海德格尔称为现代“具有生态观的形而上学理论家”,即生态哲学家。但学术界对于海氏的生态哲学思想还是有诸多误解,大多将其后期哲学思想看作是“生态哲学”思想。其实,海氏整个哲学思想都属于生态哲学思想,只是后期更加全面彻底。我们认为生态哲学思想不一定要标举出“生态”二字,而是只要在世界观上离开人类中心论力主人与自然的须臾难离那就是生态哲学思想,而海氏1927年出版《存在与时间》一书,提出“此在与世界”的在世模式,就标志着他的生态哲学思想的形成。1946年海氏又发表了著名的《论人类中心论的信》。宋祖良认为,“根据海德格尔在《论柏拉图的真理学说》和《论Humanismus的信》中对Humanismus的使用,认为这个德文词应译为人之中心说(人类中心论)或人本主义”[3](P228)。宋氏认为,该文的主旨是对于人类中心论及其表现——科技主义之束缚的突破,该文成为海氏后期较为彻底的生态世界观的纲领。他后期一再强调的“天地神人四方游戏”则是对于此在与世界二分思维的进一步突破,走向更加彻底的人与自然友好相处融为一体的生态世界观,并包含了与东方“天人合一”的对话,说明其存在论生态观是更加成熟的生态现象学。 1.建立人与自然须臾难离的“此在与世界”在世模式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的开头即通过引用柏拉图的话对存在问题的“茫然失措”指出:“‘存在着’这个词究竟意指什么?我们今天对这个问题有答案了吗?不。所以现在要重新提出存在的这一意义问题。”[4](P1)他认为,主要是解决哲学史上长期将“存在”与“存在者”加以混淆的问题,“把存在从存在者中崭露出来,解说存在本身,这是存在论的任务”[4](P34)。海氏认为,“存在”是动词,是过程,是不在场,而“存在者”则是名词,是实体,是在场。将两者混淆,以“存在者”代替“存在”是一种主客二分、人与自然对立的传统认识论在世模式与世界观。只有通过现象学的“悬搁”才能将两者相分,走向主客不分、人与自然须臾难离的“此在与世界”的在世模式。海氏认为:“某个‘在世界之内的’存在者在世界之中,或说这个存在者在世;就是说:它能够领会到自己在它的‘天命’中已经同那些在它自己的世界之内同它照面的存在者的存在缚在一起了。”[4](P69)说明这种“在世”模式是“此在与世界”的“相缚”,是人与自然的须臾难离。其表现形态为“在之中”,即“我居住于世界,我把世界作为如此这般熟悉之所而依寓之、逗留之”[4](P67)。 2.创建“天地神人四方游戏”的生态世界观 事实证明,海氏早期所提“此在与世界”的在世模式虽是对于传统认识论的突破,但仍然包含着此在与世界的二分因素,没有完全摆脱主客与天人二分模式,这就是海氏不断提出的“大地与世界的争执”。1936年之后,海氏经历了新的哲学转型,更加彻底地运用现象学方法摆脱了二分模式,走向主客与天人的交融和谐,提出“天地神人四方游戏”之说。先是在其1936年前后所写的《哲学论稿》中就开始探索从此在与世界走向天人之际的课题。他说:“作为基本情调,抑制贯通并调谐着世界与大地之争执的亲密性,因而也调谐着本有过程之突发的纷争。作为这种争执的纷争,此-在的本质就在于:把存有之真理,亦即最后之神,庇护入存在者之中。”[5](P39)这里,已经包含了突破世界与大地的纷争走向人神相谐的重要内涵。此后,海氏沿着人神相谐之路继续前进。1950年写了重要的《物》,以壶为例说明壶之物性不在其是一种器皿,也不在它是一种认识的表象,而是作为容器包含着被馈赠的大地之泉、天空的雨露、人之饮品与神之祭品等天地神人四方交融的因素。海氏说:“这四方是共属一体的,本就是统一的。它们先于一切在场者而出现,已经被卷入一个唯一的四重整体中了。”[6](P1173)也就是说,壶之物性集中体现了天人交融、自然与人和谐的美好生存之境。1959年,海氏更在《荷尔德林的大地与天空》的演讲中明确提出“天地神人四方游戏”之说。他说:“于是就有四种声音在鸣响:天空、大地、人、神。在这四种声音中,命运把整个无限的关系聚集起来。”[7](P210)“天地神人四方游戏”是更加彻底的生态世界观,是一种可以与东方“天人合一”相对话与交融的生态世界观,是中西交流对话的产物。 3.批判现代技术“促逼”与“座架”的破坏自然本质,呼唤救度生态危机的“诗意栖居” 海德格尔在胡塞尔批判欧洲危机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欧洲现代由唯科技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所导致的人类借助现代科技对于自然生态的极大破坏。他在著名的《技术的追问》的演讲中以及其他篇章中进行了这方面的深入思考。他说,“现代技术之本质显示于我们称之为座架的东西中”[6](P941),“我们以座架(Ge-stell)一词来命名那种促逼着的要求,这种要求把人聚集起来,使之去订造作为持存物的自行解蔽的东西”[6](P937)。所谓“座架”与“促逼”,实际上是凭借技术对于人与自然的一种机械的订造与摆置,是一种缺乏人性内涵的纯粹机械的与数学的对自然“提出蛮横要求”[6](P932-933)的行为。海氏认为,座架与促逼所导致的恶果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泛滥与自然生态的破坏,实际上由于大规模无度开发导致自然对象的严重破坏,人已经失去了促逼与摆置的对象,但人还是以地球的主人自居,使自己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他说:“但正是受到如此威胁的人膨胀开来,神气活现地成为地球的主人的角色了。”[6](P945)海氏认为,地球破坏与人类的膨胀导致极为危险的境地,但人类并非无救,而是在极度危险之处恰恰蕴含着救度。他引用荷尔德林的诗“但哪里有危险,哪里也有救”,并说道:“那么就毋宁说,恰恰是技术之本质必然于自身中蕴含着救渡的生长。”[6](P946)那就是呼唤一种与技术的栖居相异的“诗意的栖居”。这是一个相异于技术的新领域,他说:“此领域一方面与技术之本质有亲缘关系,另一方面却又与技术之本质有根本的不同。这样一个领域乃是艺术。”[6](P954)艺术与技术的相同是它们都是一种制造(art),但其不同之处则是一种不受束缚的“游戏”与“自由”。在这种人与自然生态的自由的游戏中走向诗意的栖居。 4.生态语言学的创立 一般认为,生态语言学是1972年由美国语言学家艾纳尔·豪根(Einar Haogen)在一篇题为《语言生态学》的文章中正式提出的,而英国语言学家迈克尔·韩礼德(Michael Halliday)于1990年在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上作了有关“语言与生态学之间的连接”的发言,此后“生态语言学”才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正式建立起来。但其实早在20世纪20—30年代海德格尔就已经创立了生态语言学,包含极为丰富的内容。海氏认为,应该放弃“框架语言”,恢复“天然语言”。他有力地批判了工业革命时代唯科技主义泛滥的情况下由于人的本质的丧失导致语言本质的丧失,使得语言失去其“天然语言”本性,成为“框架语言”。他说:“框架,向各方向进行支配的现代技术的本质,为自己预定了形式化的语言,一种消息,由于这种消息,人千篇一律地成为技术上算计的生物,即被安排成技术上算计的生物,并逐步放弃了‘天然的语言’。”[3](P259)这种所谓“框架语言”就是通过“逻辑”与“语法”对于“天然语言”进行霸占式的解释,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统治”,是使语言由存在之家变成“对存在者进行统治的工具”[6](P363)。海氏还以著名的“语言是存在的家”[6](P358)点出了语言的本质。所谓“语言是存在的家”,这里的“语言”是反映存在的“道说”而不是具体的“言说”。所谓“道说”是一种自然形态的可以与自然对话的“无声之说”,是德国早期浪漫派所力主的“自然语言”观,认为自然与人都有语言,可以对话。人与自然的对话说明人的本质“比单纯的被设想为理性的生物的人更多一些。……更原始些因而在本质上更本质性些”[6](P385)。这就是人的生存本质,与自然一体,倾听自然的自然本质。正是人类长期忽视而当前应该重视之处。语言是存在的家,也可以说语言是人与自然共同的生存之家。海氏认为,“思的人们与创作的人们是这个家的看家人”[6](P358),在这里,“看家人”是人的责任之所在,人要看护好“语言”这个家,保护好语言的自然本性,通过语言使人得以美好生存。“人不是存在者的主人。人是存在的看护者。”[6](P385)也就是说,人不是通过语言对存在者(自然)施行暴力,而是保护好自然等存在者,使人得以美好生存。海氏还特别重视各种方言土语,认为它们反映了语言对于大地的归属性。他说:“在土语中,地方和大地在各不同地说话。但是,嘴不只是被想象为有机体的躯体的一种器官,而且躯体和嘴属于大地的涌动和生长。”[3](P268)说明语言与大地的归属关系,说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孕育一方语言的生命与语言之特性。 三、梅洛-庞蒂:身体现象学是生态现象学的新发展 梅洛-庞蒂是继海德格尔之后欧洲最重要的现象学理论家。他有机会阅读了胡塞尔晚年的手稿得以继承其现象学的新成果,而且由于时代的发展,他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身体现象学。身体现象学是在海氏存在论现象学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成为崭新的生命论哲学。这种身体现象学是生态现象学的新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人与自然生态共生共荣新关系的新的理论支点。 1.“身体本体论”是生态现象学的新发展 梅洛-庞蒂在海氏“此在本体论”的基础上将之发展为“身体本体论”。在这里,“此在”变成了“身体”。“身体”是人与世界的“媒介物”,是人与世界关联的“枢纽”,是人存在的基础。他说:“身体是在世界上存在的媒介物,拥有一个身体,对一个生物来说就是介入一个确定的环境,参与某些计划和继续置身于其中。”[8](P116)这里的“身体”并不是生理的身体,而是存在的身体,是意向的身体,也是生存的身体。所谓意向的身体就是意向性所达到的身体,所谓生存的身体就是人的生理机能与精神机能借以凭借的身体。由此,才产生了著名的“幻肢”现象。也就是截肢者仍然会在自己的意向中呈现其被截的肢体从而产生幻觉,当然这也是截肢者的一种生存的记忆与愿望。梅氏认为这是一种“习惯身体”而不是“当前身体的层次”。正是这种意向的存在的身体成为人与自然生态的“媒介物”与“枢纽”。梅氏认为这个身体就是真正的先验,就是生命。他说:“胡塞尔在他的晚期哲学中承认,任何反省应始于重新回到生命世界(Lebenswelt)的描述。”[8](P459)这就将身体现象学推向了生命现象学,从而将生态现象学推向新的阶段。在生命的层次上人与自然生态的平等共生就具有了更强的理论合理性。 2.“肉身间性”(Intercorporedlity)是人与自然生态共生关系的深化 梅氏的理论中身体与自然生态是一种间性的、可逆的关系,也就是所谓“肉身间性”的关系。这种“肉身间性”就是一种整体性的关系、共生共荣的关系。梅氏提出著名的“双重感觉”的观点,也就是著名的左手触摸右手的“触摸”与“被触摸”的双重感觉。他说,“我们的身体是通过它给予我的‘双重感觉’这个事实被认识的:当我用我的左手触摸我的右手时,作为对象的右手也有这种特殊的感知特性”,这是“两只手能在‘触摸’与‘被触摸’功能之间转换的一种模棱两可的结构”。[8](P129)这种“双重感觉”存在于身体整体性之中,犹如左手与右手、身体任何部分与其他部分的整体关系。为此,他提出著名的“身体图式”概念。他说:“身体图式应该能向我提供我的身体的某一个部分在做一个运动时其各个部分的位置变化,每一个局部刺激在整个身体中的位置,一个复杂动作在每一时刻所完成的运动的总和,以及最后,当前的运动觉和关节觉印象在视觉语言中的连续表达。”[8](P136)这其实是一种统一性或整一性的感觉能力,不仅身体各部分之间,而且包括身体各种感觉之间,都是一种整体的关系。 不仅如此,梅氏还认为人与世界也是一种整一性共生共荣的关系。在这里梅氏继承发展了海氏的“此在与世界”关系的理论,认为身体与世界的关系不是一个在一个之中而是须臾难离,不可分离。他说:“不应该说我们的身体是在空间里,也不应该说我们的身体是在时间里。我们的身体寓于空间和时间中。”[8](P185)他认为这其实是坚持现象学所必然导致的结果。他认为,人与世界关系中的“身体”是一种“现象身体”即意向性中的身体,这种意向性中的“现象身体”不仅包括意向所达到的整一性的身体,而且包括意向所达到的与身体紧密相连的世界。他说:“我们的客观身体的一部分与一个物体的每一次接触实际上是与实在的或可能的整个现象身体的接触。”[8](P401“)现象身体”的提出是梅氏对于现象学的新创见,意义重大。 3.生态语言学的新拓展 生态语言学虽是1972年提出的,但前文已经说到其实海德格尔早在1927年的《存在与时间》中就已经涉及生态语言学的有关问题。梅洛-庞蒂则在其写于1945年的《知觉现象学》中进一步对生态语言学做了新的拓展,主要是他将语言与身体紧密相连并由此达到自然生态世界。在这里梅氏实际上论述的是身体语言学,当然他这里的身体是现象学的身体,是寓于世界之中的身体。他明确提出“言语是身体固有的”[8](P252),这就将言语与身体紧密联系。继而提出,言语“是身体在表现,是身体在说话”[8](P256)。身体如何在说话呢?梅氏认为是身体通过动作在说话。他说:“言语是一种动作,言语的意义是一个世界。”[8](P240)这就揭示了言语的本质,说明无论作为言语的发声还是说话时的表情,言语都是一种身体的动作,当然这个动作并不局限于身体本身,而是从现象学的身体而言是紧密联系于世界的。他认为,动作具有深广的世界意义,不同地域人的动作都含有特殊的不相同的意义,“日本人和西方人表达愤怒和爱情的动作实际上并不相同”[8](P245)。这当然有其环境、地域、文化与水土的差异,揭示了生成语言的自然生态背景。梅氏还进一步阐述了语言的文化本质,认为言语是对“身体本身的神秘本质的”揭示,明确说明言语通过身体所蕴含的深刻文化内涵。主要是言语与生存的紧密联系,“言语是我们的生存超过自然存在的部分”[8](P255)。 4.现象学自由观是对人类改造自然生态的限制 关于自由观,传统认识论一直认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与掌握。在传统认识论看来,只要认识并掌握了事物的必然规律人类就获得了自由,可以放手地去改造自然生态,肆意进行所谓的“人化自然”的活动,由此产生一系列严重的破坏自然生态环境的事件,导致人类目前已经难以维持基本的生存权利。梅氏一反传统认识论自由观提出现象学自由观。现象学自由观是经过意向性悬搁之后的自由观,也就是经过意向性将客观的必然性与主观的选择性统统加以悬搁,最后剩下受到主客体限制的相对的自由性。梅氏认为:“没有决定论,也没有绝对的选择。”[8](P567)这就将客观的决定论与主观选择的绝对性全部加以悬搁。他对现象学的自由进行回答:“自由是什么?出生,就是出生自世界和出生在世界。”[8](P567)在这里,无论“出生自世界”还是“出生在世界”都要受到出生与世界两个要素的制约,自由不是绝对的,不可能存在无任何制约的人对自然的“人化”。梅氏明确指出:“被具体看待的自由始终是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一种会合。”[8](P568)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都会对自由形成约束,“甚至在黑格尔的国家中的介入,都不能使我超越所有差异,都不能使我对一切都是自由的”[8](P569)。梅氏认为,黑格尔所推崇的作为最高理性体现的“国家”也不会具有绝对自由的权力。这就对工具理性时代的认识论自由观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提出一种崭新的现象学相对自由观,对于人的肆意掠夺自然进行了必要的约束。 5.现象学生命哲学走向东西生态哲学的融通 梅洛-庞蒂于1960年在《符号》一书中指出,东方的古代智慧同样应当在哲学殿堂中占据一席之地,西方哲学应当向印度哲学和中国哲学学习。梅氏甚至在对灵感的论述中提出艺术创作中呼吸的问题。他说,艺术创作的灵感状态中“确实是有存在的吸气与呼气,即在存在里面的呼吸”[9](P137)。这已经是与中国古代生命论艺术理论中的阴阳与呼吸相呼应了,进一步说明东西方艺术在生命论中的相遇。由此可见,梅氏在《符号》一书中有关中西文化的论述说明他认识到现象学生命哲学充分体现了中西哲学的融通。他所说的生命哲学是相异于西方传统认识论语境下人类中心的生命论哲学、主客二分对立的生命哲学,力主万物一体、主客模棱两可与间性的生命哲学。这就与东方的万物齐一、生生不已与天人合一的生命论哲学具有了相通性。身体与生命成为沟通东西方哲学的桥梁。 四、生态现象学是生态存在论美学的基本方法与根本途径 诞生于20世纪初的现象学是人文学科领域的一场深刻的革命,它颠覆了工业革命以降的认识论哲学代之以存在论哲学,颠覆了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代之以整体性、关系性与间性的思维模式,颠覆了人类中心主义代之以生态整体论。这就为新的生态哲学与生态美学的诞生开辟了道路。诚如梅洛-庞蒂所言:“真正的哲学在于重新学会看世界。”[8](P18)现象学让我们确立了一种新的“看世界”的视角与方法,这就为新的生态哲学与生态美学提供了基本的方法。我们曾经多次说过,生态美学是一种新的生态存在论美学,只有从生态现象学与生态存在论哲学的崭新视角才能理解生态美学。生态美学的产生其实也是美学领域的一场革命,是对传统认识论美学、实体性美学、形式论美学的突破。而胡塞尔、海德格尔与梅洛-庞蒂随着他们在生态现象学上的逐步深入,生态美学也逐步走向深入。可以说胡塞尔对于生态美学是一种开路与奠基的作用;到海德格尔则是生态美学的深入;而梅洛-庞蒂则使生态美学走向成熟。 首先,胡塞尔的现象学是对于传统认识论美学的突破,也是新的生态存在论美学的开启。 众所周知,传统认识论美学是一种实体性美学,力主美在客观物质或美在主观精神。而现象学则颠覆了这种实体性美学,开启了新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胡塞尔在其完成向先验现象学突破的同时写下了有关艺术直观与现象学直观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胡塞尔为新的生态存在论美学开辟了道路,奠定了方法。他明确提出了现象学是把握哲学基本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他说:“为了把握哲学基本问题的清晰意义和为了把握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我曾进行了多年的努力,我所得到的恒久的收获就是‘现象学的’方法。”[1](P1201)在这里,胡塞尔将现象学提到根本方法的高度并充分看到其在建设新的生态存在论美学形态中的重要作用。他首先运用了现象学的直观的纯粹的方法对于传统认识论哲学与美学的实体性思维进行了解构。他说:“对一个纯粹美学的艺术作品的直观是在严格排除任何智慧的存在性表态和任何感情、意愿的表态的情况下进行的……或者说,艺术作品将我们置身于一种纯粹美学的、排除了任何表态的直观之中。”[1](P1202)说明现象学方法是一种排除凭借智慧对于客观存在物的审美以及凭借感情的主观性审美,它是一种纯粹的直观的意向性的审美。他说,“现象学的方法也要求严格地排除所有存在性的执态”,要求“把一切认识都看作是可疑的并且不接受任何已有的存在”,“剩下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在纯粹的直观中(在纯粹直观的分析和抽象中)阐明内在于现象之中的意义”。[1](P1202、1203)他进一步对于美学与艺术的特点论述道,“现象学的直观与‘纯粹’艺术中的美学直观是相近的”,而艺术家“不是观察着的自然研究者和心理学家,不是一个对人进行实际观察的观察家,就好像他的目的是在于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一样。当他观察世界时,世界对他来说成为现象,世界的存在对他来说无关紧要,正如哲学家(在理性批判中)所做的那样”。[1](P1203、1203-1204)这说明,在他看来艺术与审美不是对于自然与人的科学研究,并不关心世界的实际存在,而是对于世界的一种纯粹的直观,世界以意向中的“现象”的形态呈现出来,世界与人是一种意向性的关系,不是实体的关系。这就对于传统实体性美学进行了有力的解构,从而为新的生态存在论美学的诞生进行了准备。胡塞尔还在后来的《笛卡尔的沉思》一书中提出“相互主体性”的重要问题,为生态哲学与生态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次,海德格尔的生态存在论是生态美学理论的系统表达。 海德格尔第一次自觉地将现象学与存在论哲学紧密相连,他说:“存在论只有作为现象学才是可能的。”[6](P70)在他看来,传统认识论将存在与存在者加以混淆,只有现象学才通过悬搁在意向性之中直观世界之本质。因而现象学与存在论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只有现象学才真正突破了传统认识论哲学。海氏贯穿始终的一个观点就是“生存论”,他说:“此在无论如何总要以某种方式与之相关的那个存在,我们称之为生存。”[5](P41)“此在”的存在就是在世界中生存,是一种具有时间性的生命过程,从而为梅洛-庞蒂的身体哲学与身体美学奠定了基础,也使生态美学成为异于传统认识论美学形式之美的更高级美学形态。他还借助现象学提出了“此在与世界”的存在论在世模式,以此与“主体与客体”的认识论在世模式加以区别。这种“此在与世界”的在世模式形成一种在人世界之中的人与自然的须臾难离的间性关系。他说,“在之中”等于说“我居住于世界,我把世界作为如此这般熟悉之所而依寓之、逗留之”[4](P67)。后期,海氏对于人与世界的关系进一步加以探讨,提出著名的“天地神人四方游戏”之说,从而为生态哲学与生态美学的人与自然生态的间性关系充实了丰富的内涵。海氏又对美加以界定:“美是作为无蔽的真理的一种现身方式。”[6](P276)在这里,海氏将由遮蔽到澄明之真理的呈现作为美之发生过程,是在“世界与大地”的天人关系中,在“此在”的阐释中使美逐步呈现。美是过程,美是阐释,也是此时此刻的体验。这就赋予美以生态与体验的内容。当然,海氏对于美的更加具体的阐释就是著名的“家园意识”。早在1927年的《存在与时间》中海氏就指出了当代严重存在的“无家可归”状态,成为人生之畏。此后,海氏于1943年纪念荷尔德林逝世100周年之际提出重要的“家园意识”。他认为,“‘家园’意指这样一个空间,它赋予人一个处所,人唯在其中才能有‘在家’之感,因而才能在其命运的本已要素中存在”[7](P15)。“家园意识”、“在家”、“诗意的栖居”,成为人与自然生态美好和谐关系的贴切表述,从而使得生态美学成为一种关系之美、栖居之美。 最后,梅洛-庞蒂使生态存在论美学走向“身体-生命美学”。 梅洛-庞蒂的身体哲学不仅开启了生态哲学的新篇章,而且开启了生态美学的新篇章。他在晚年写作了非常重要的《塞尚的疑惑》一文,通过印象派画家塞尚对于艺术创作中现实与知觉关系的疑惑,将其身体哲学与现象学直观的方法成功地运用于艺术创作理论,创造了一种新的身体-生命美学,是一种新的生态美学形态。我们现在考虑,为什么梅洛-庞蒂选中塞尚作为阐释他的审美与艺术观的典型呢?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原来塞尚的作品与创作经验非常符合现象学,特别是知觉现象学直观的基本观点。梅洛-庞蒂借助塞尚提出的这种“身体-生命美学”在“本质直观”、“身体本体”与“肉身间性”理论的指导下提出了“师法自然”与“原初体验”等极为重要的美学观点。所谓“师法自然”是梅氏所记塞尚在其晚年去世前一个月所说的对于自己的疑惑和焦虑的看法。塞尚的一生除了绘画还是绘画,绘画是他的全部世界,他的存在之本。他没有门徒,没有家人的支持,没有评论家的鼓励,在母亲去世的那个下午,在被警察跟踪的时光他都在画着,他不断地被人质疑,甚至说他的画是一个醉酒的清洁工的涂鸦,如此等等。面对这一切,塞尚在生命最后的回答是:“我师法自然。”可以说这是他一生艺术创作的总结。在这里,梅洛-庞蒂引用这个观点说明他非常赞同这个观点。这个“师法自然”包含极为丰富的内容,是梅氏特有的“自然本体”的观点。这里的自然既不是客观的大自然,也不是主观的意念中的自然,当然也不是中国道家的自然而然,而是知觉现象学中的自然,即是作为整体性的“身体图式”中的自然,是知觉中身体与世界可逆性的自然,可以说是身体与世界共同的“自然”,梅氏曾说,画家“正是在把他的身体借用给世界的时候,画家才把世界变成绘画”[9](P128)。他对“自然”极为推崇,借塞尚的话说:“我们所有的一切皆源于自然,我们存在于其中;没有什么别的更值得铭记的了。”又说:“他们(指古典主义画家)创造绘画;而我们做的是夺取自然的片段。”[9](P45)①他举出法国画家雷诺阿的油画《大浴女》,明明是画家对着大海画的,但画面呈现给我们的却是四位浴女在河水中浴后歇息与远景洗浴的景象,特别表现了河中蓝蓝的水。其实这幅画是雷诺阿对着大海画的,但茫茫的大海变成了河流,海水的蓝色变成河水的蓝色。这其实本真地道出了梅氏所谓“师法自然”之“自然”的具体内涵,自然不是现实,不是观念,而是最原初的诗性感受。在这幅画里,梅氏认为雷诺阿不是表现大海或大河,只是表现了一种对于海水这种液体的询问与解释,雷诺阿之所以这样画,“是因为我们向大海询问的只是它解释液体、显示液体并把液体与它自己交织在一起,以便使液体说出这、说出那,简而言之,使之成为水的全部显现中的一种方式”[10](P69)。这就是所谓的“师法自然”。梅氏还对于这种“师法自然”做了进一步的阐发,那就是艺术家需要一种“原初的体验”。他说:“在这里,把灵魂与肉体、思想与视觉的区别对立起来是徒劳的,因为塞尚恰恰重新回到了这些概念所由提出的初始经验,这种经验告知我们,这些概念是不可分离的。”[9](P49)这个“原初的体验”是一种未经人类的知识和社会的环境所影响的体验。首先,这不是一些“人造客体”即通常所谓的“环境”。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由人建造的物的环境当中,置身家中,街上,城市里的各种事物当中,而大部分时间我们只有通过人类的活动才能看见这些东西。对人类的活动,它们能成为实用的起点。我们早已习惯把这些东西想象成必要的、不容置疑地存在着的。然而塞尚的画却把这种习以为常变得悬而未决,他揭示的是人赖以定居的人化的自然之底蕴。”[9](P50)例如,梅氏认为巴尔扎克在《驴皮记》中所写的“桌布的洁白”、“新落的雪”、“对称的玫瑰红”与“黄棕色的螺旋纹”等都能在绘画中表现,但诸如“簇拥”这样的人造景象就不好表现了。他还认为,“原初的体验”与科学的透视是不相容的,“激活画家动作的永远不会只是透视法,几何学,颜色配合或不论什么样的知识。一点点作出一幅画来的所有动作,只有一个唯一的主题,那就是风景的整体性与绝对充实性——塞尚恰当地称这为主题”[9](P51)。最后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未经人类影响的前文明时期的风景。梅氏具体描写道:“而自然本身也被剥去了为万物有灵论者们预备的那些属性:比如说风景是无风的,阿奈西湖的水纹丝不动,而那些游移着的冰冷之物就像初创天地的时候那样。这是一个缺少友爱与亲密的世界,在那里人们的日子不好过,一切人类感情的流露都遭禁止。”[9](P50)可见这是一个回到人类本源的原初世界,也是人的原初体验。这与维柯的“原始诗性思维”非常相像,也是万物有灵时期人凭借身体感官所进行的人与自然统一的思维。这正是一种生态的审美的艺术的思维,需要我们很好地借鉴与运用。梅氏的生态审美观是很彻底的,他借助胡塞尔的思想提出了“地球根基”的思想,说道:“当我们居住在其他星球时,我们能移动或搬动的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生活的‘地面’或‘根基’,然而,即使我们能扩展我们的祖国,我们也不能取消我们的祖国。由于按照定义,地球是独一无二的,是我们成为其居民时行走在它上面的土地,所以,地球的后裔能与之进行交流的生物同时成了人,——也可以说,仍将是独一无二的更一般的人类之变种的地球人。地球是我们的时间和我们的空间的母体:由时间构成的任何概念必须以共存于一个惟一世界的具体存在的我们的原始时期为前提。可能世界的任何想象都归结为我们的世界观。”[11](P224)这里的“地球”按照“肉身间性”理论也就是“身体”,在这里“地球根基”也就成为“身体根基”。“自然之外无他物”就成为真正的生态整体论,关爱地球与关爱身体是一个事物的两面,人与生态真正地统一了起来。 现象学开辟了生态哲学的新天地,也开辟了生态美学的新天地,在中西古今结合的背景下,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注释: ①此段引文字句笔者略作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