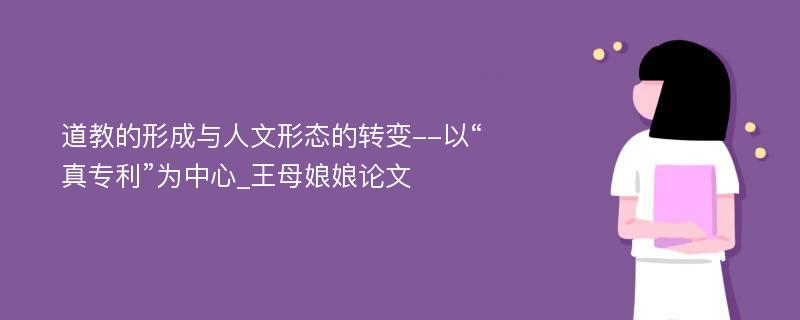
道教的形成与人文型态的变迁——以《真诰》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教论文,型态论文,人文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公元五世纪初产生的几部有代表性的上清派道教经典中,似乎可以找到对于理解道教的形成具有重要参照价值的东西。其中,《真诰》无疑是最重要的。《真诰》仙真世界的营构有其内在的理路与法则,这就是,它表现出基于宗教的视域统摄自然、人文及历史的努力。这在中国文化史上乃是一次重大的转折,其根本含义是,在伦理性人文诠释系统遭受严重危机之际试图确立一新的人文诠释系统也即宗教性人文诠释系统。这一人文型态的迁化是与道学向道教的演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样,道教的成立也就是主流文化由单一的伦理型向伦理与宗教二元型的嬗变过程。这一历史情境对于道教性格的塑造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它使道教的产生及发展始终有一伦理型人文系统为其参照视镜,并由此反映出道教与佛教、基督教等的显著差异以及它自身的复杂性格。这就是为什么道教难以界定、产生时代迄今仍不能确立的主要原因。《真诰》便是这一文化转折的产物。
一、道教的形成意味着中夏人文形态的变迁
在周文衰弊情境下成长起来的儒道之学,是中夏人文同源异流的两支学脉,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主体。儒道之学共同的特点在于,它们不是以某一“绝对预设”为逻辑起点而人为营构的思辨体系,而是运用性取予之学:一则观象取理,一则予理于事;其根本原则是:以类取,以类予。儒道所属的这种人文形态决定了它们的伦理性格(东汉郑玄注《礼记·乐记》云:“伦犹类也;理,分也。”本文所谓伦理即在此意义上使用。)——不独是对实存之理的取用,还贯彻着止于至善的原则。中夏人文学因而又被称为义理之学。陆九渊说:“我注六经,六经注我”,道出了义理之学的一个重要特点,这就是文本与主体之间的互训性。如果单方面强调“我注六经,”就会使主体沦落为文本的注脚,从而消解主体的生成。同样,单方面强调“六经注我,”就会取消文本对主体的参照功能,从而使主体沦为“自然人”,导致张载所说的“人化物”的异化现象。文本与主体的互训意味着文本的非人为设定性,这种精神使得中国“有的就是伦理”,出现了“以伦理为本位”、“以道德代宗教”的情况。(参见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94年,第77—123页)德国思想家谢林也指出, 中国原本(尤指佛教传入以前)是一个根本无教制、无上帝,绝对非僧侣、纯理性的国家。(谢林《中国——神话哲学》,载《德国思想家论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儒道之间适成一重反训,如同训诂学中存在着的以“乱”训“治”一样。道学着眼于客形与本体相离的人文实况,强调二者在现实中经常存在的紧张与对峙;儒学则坚信二者必有附丽的一面。因而,道学所主张的为学与为道的分途在儒学那里并不成立,在道学那里具有正面、肯定色彩的执一在儒学中却具有负面、否定的意义。儒学坚信礼与理的合一,“道——德——仁——义——礼”的人文筹划意味着道的一步步落实。道学则认为礼是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仁义礼不过是道德虚化以后蹩脚的人为补救,因而,趋向本体的行程必然是逐步剥落“礼——义——仁”、直指本性的自然运作。儒道之学虽然存在着观照视角的差异,但其最终归趣则并无不同,这就是它们共同追求物各付物、各得其理的伦理社会。这种伦理不是人为制定的契约和规范,而是宇宙本有的秩序与法则。
儒道的伦理性格还表现在其思维方式的非对象性,事实上,人们通常以“天人合一”来表述这一点。把自然世界看作某种物理的世界,看作我们不属于其中的分析对象,从而使人成为认识活动中的判断主体,这种主观设定对于儒道之学来说从一开始就没有意义。对象性思维往往与范畴的实体化、现成性联系在一起,而儒道之学则充盈着一种原发境域的构成(Konstitution)识度。(参见张祥龙《现象学的构成观与中国哲学》,载《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1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孟子说:“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就内在地包蕴着对对象性思维的拒斥。马丁·布伯指出老庄道学的立足点是一种彻底的自然的一元,对象性与道学无关。(参见布伯《道教》,载《德国思想家论中国》)
儒道的伦理性格决定了中夏人文非宗教的特点,在较长历史时期内,宗教精神始终难以渗透到文化大传统中去。伦理性人文诠释系统在先秦两汉一直占据主宰地位。这决定了佛教初传时不能在宗教意义上而只能作为方术被国人接受,也同样决定了真正意义上的道教的形成需要艰难且长久的历程,因为,它必须确立宗教性人文诠释系统,把伦理精神定位的世界重新给予宗教的安排。
儒道之学赖以产生的礼乐社会一步步的崩溃,给伦理性人文带来了危机,也给宗教精神的萌芽提供了契机。《墨子》天志、明鬼的思想以及苦行态度都是早期宗教精神萌芽的表现,汉末太平道及五斗米道团的出现,是宗教精神的进一步发展。但这些并不意味着道教的成立。(参见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20页)完整系统的理论、神谱、仪式、方法等等久久不能产生,这正根源于伦理人文对宗教精神的拒斥。但天下多故的历史情境及佛教的推动导致了双重结果:一方面是佛教宗教人文的伦理化;一方面是中土伦理人文的宗教化。蓬勃发展的宗教人文渐渐能够与伦理人文相抗衡,二者的碰撞交融导致了道教出世时的特殊面目:其它宗教一般说来都是先成为整体性宗教,随发展而流为派别;而道教却是先出现不同的派别,随着发展再融汇为整体意义上的道教。(参见卢国龙《中国重玄学》,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19—20页)这一融汇过程,发生在南北朝时期,也就是《真诰》产生的时候。而这一时期,正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在中土确立的时期:组织性道教的出现与佛教在宗教意义上被国人接受是同时的。佛教的传布对道教的成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不仅是因为佛教曾依傍于黄老道术,有益于改变道学的面目;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佛教带来了宗教性致思方式。道教的成立意味着它必须以宗教性致思方式重组自然、人文及历史。这也就意味着人文形态的巨大变迁。
《道教序》提出的“自然之教”向“神明之教”的过渡,就其内在的思想逻辑而言可以看作是对这一人文形态变迁的宗教性表述。自然之教是不言、无为之教,虽无义说(关于善的陈述),但却享有义理之实。神明之教,“义说则有,据理则无。”因而,前者是“实教”,后者是“权教”。(参阅《云笈七签》卷三《道教本始部》)自然之教只是对实存之理的自我性取用,而不存在对象性的言语教诫,这也正是伦理人文的特征。神明之教无有实理,出于“义说”的要求,采用方便应化的态度,人为地营造教化体系。这种设定精神与宗教人文有其内在深刻关联。这里的问题是:道教怎样处理与自己分属不同人文类型的老庄道学?鉴于道学的巨大影响与崇高地位,敏睿的道教学者一方面对老庄提出批评,拒绝承认把道教的起源追溯到老庄那里。例如,葛洪批评老子于金丹神仙之事“泛论较略”,文子、庄子、关令尹喜之徒“其去神仙,已千亿里矣”,“演其大旨,永无至言”。(《抱朴子·释滞》)陆修静三洞经法和灵宝经十二部类法中,《老子》不在其一。又如《云笈七签》卷三《道教所起》云:“老子《道德经》未入三洞之教。今人学多浮浅,唯诵《道德》,不识真经,即谓道教起自庄周,始乎柱下(老子)。”显然否认道教源于老庄道学。另一方面,道教学者又以宗教的视域重塑老庄,神化老子。日本学者砂山稔在《道教和老子》一文中详细叙述了老子在道教中不断宗教化的过程。(参见福井康顺等监修《道教》,第二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道学与道教的深刻的不一致性及其间的接续关系,在这里都得到了深刻的展示。而道教所以能依附于道学而不是儒学,也正是由于道学着眼于事物与本体相离的一面更易于导向对象性的致思方式。
二、《真诰》确立了宗教性人文诠释系统
我认为《真诰》是道教产生,也是中国宗教真正确立的文本标志。理由是:《真诰》自觉地表现出建构宗教性人文诠释系统的努力,它通过仙真世界的主观营造而实现对自然、人文及历史的宗教处理。在对世界进行宗教诠释的同时,也确立了宗教思维模式。
仙本来并无宗教蕴含。《说文》仙作仚,“人在山上貌,从人从山”,本指离群索居而求形全的隐逸之士。仙的出现与古代王朝更替时产生的逸民现象有关。孔子政治理想中就有“举逸民”一项。《晋书·隐逸传》中的郭文举、孙登、朱冲等,皆朝廷屡辟不就,甘栖山林。这类隐逸之士栖居山林,很注意养生之学,这使得仙的含义发生了一次改变。《释名·释长幼》云:“老而不死曰仙;仙,迁也,迁入山也。”由此,仙已转换为长生炼养之学,也即仙学。陈撄宁先生揭示了仙学与道教的区别,强调仙学的非宗教特点。(参见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第4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4—403 页)如果说仙学象陈先生所说的那样有其独特的义理,是可操作的、近于实验性质的学术,那么,道教的神仙说则不具义理根基,只有宗教意义。如《真诰》谓读《大洞真经》万遍即可成仙,就是如此。
在《真诰》中,仙与真乃是以异化形式出现的人格范型之不同阶位,是前定构想而后照着改良的日用参照系统,而成仙之道则是成人之道的宗教表述。仙真的宗教性在于他不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只是道德观念的载体。安禄君有一戒语说:“夫真者都无情欲之感、男女之想也”(《真诰》卷六《甄命授第二》),就是一个说明。而且,《真诰》所谓的成神之道实则是一个道德修养过程。南岳夫人如下的诰语显然是把道德作为修炼的前提条件:“虚妄者德之病,华衒者身之灾,滞者失之首,耻者体之籥,遣此四难,然后可以问道耳……有淫愆之心,勿以行上真之道也。”(《真诰》卷二《运象篇第二》)在修炼过程中,道德性功过是衡量效果的标准。《真诰》谓:“积功满千,虽有过,故得仙。功满三百而过不足相补者,子仙。功满二百者,孙仙。子无过而又无功德,籍先人功德便得仙,所谓先人余庆。其无志多过者,可得富贵,仙不可冀也。”(《真诰》卷五《甄命授第一》)又说:“有恶知非,悔过从善,罪灭善积,亦得道也。”(《真诰》卷六《甄命授第二》)道德在道教中始终是成仙飞举的决定性因素,而在仙学中,神丹大药才是成仙的关键所在。
许谧由人间许长史成为山中许道士最终步入仙界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断接受仙真教化,“洗心自励,沐浴思新”的过程。而仙真在这里成了“布道者,”陶弘景在《真诰·叙录》中明确指出了仙真的教士身分,“南真自是训授之师,紫微则下教之匠。”仙真在这里又一次显示了其宗教性:除了是道德观念和施教者的载体,仙真自身再也没有其他意义。也就是说,仙真作为传教者的抽象,其意义不在自身,而在受教者那里,就象宗教终极、上帝等不具有自我性,只是向人而在的。宗教的向性就在于这种对象性。而在伦理人文中,教者的意义具有自向、内反的特点,教化他人只是努力追求自我的完善,因而不存在对象性的往教。《白虎通·辟雍》说:“《曲礼》曰:‘闻有来学,无往教也。’《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白虎通》的这一思想与孔子的不言之教、老子的无为之教、《易传》的“神道设教”有其内在的一致性。孔颖达解释“神道设教”时说:“天既不言而行,不为而成,圣人法则天之神道,本身自行善,垂化于人,不假言语教戒,不须威刑恐逼,在下自然观化服从。”而所谓神道,则是“微妙无方,理不可知,目不可见,不知所以然而然”者。(《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36页)在这里,教是一个过程,一种运动,是自我生命本体的动态显现与垂示,对象性被彻底排除在这一过程之外。教化他人的最重要的效果是自身的不断圆满、止于至善。而在《真诰》中,仙真施教的目标则在于他们的对象,因而,他们不是等着受教者“来学”,而是主动地降真于受教者“往教”之。观其所用手段,不是“本身自行善”,而是“真诰”,也即孔颖达所谓的“言语教戒”。
《真诰》以宗教方式处理这些言语教戒,也就是使之神圣化,把它们说成真人的垂训,意在通过心理或精神方面的“威刑恐逼”而易于落实。于是,人为造作的文献变成了扶乩降真而产生的圣经,且富有“实中之空,空中之有,有中之无象”(《真诰》卷一《运象篇第一》)的神秘性。为什么要借助凡人的手笔进行记录呢?紫微夫人有如下的说明:“至于书迹之示,则挥形纸札,文理昺注,粗好外著,元翰挺焕,而范质用显,默藻斯坦,形传尘浊。苟骞露有骸之物,而得与世进退,上玷逸真之詠,下亏有隔之禁,亦我等所不行,露法所不许也。……夫真仙之人,曷为弃本领之文迹,手画淫乱之下字耶?……”(同上)《真诰》初本书法不用真隶,而用行草,被解释“皆是受旨时书既忽遽贵略,后更追忆前语,随后增损”(《真诰》卷十九《翼真检第一》)的结果。创作过程的神圣化以及文本的圣经化势必造成文本的上帝性。“六经注我”不再成为可能,而“我注六经”则成为事实。人成了文本的注脚,而失却了与之互训的可能。《真诰》谓《大洞真经》是仙道之至经,读之万过便仙,明《大洞》者为仙卿,服金丹者为大夫。(《真诰》卷五《甄命授第一》)这里,启信尊经是以牺牲实存之理为代价的。
与民间传说不同,《真诰》中仙真的降临是群体性的,《周氏冥通记》中也是如此。仙的宗教蕴含并不意味着一两个仙人降真,满足某些个体性愿望,而是意味着仙真世界的为人所发现。而此仙真世界乃是人间伦理社会亦即《真诰》所谓“太平”的理想表征。仙真世界有自己的官僚体制,组织系统和制度科仪。进入这一世界需要经过反复的试探和考验,神仙资格的获得需要有道德的保证。如许谧之所以获得仙籍,乃是由于他内明中正,略有伯(仙)形。(《真诰》卷二《运象篇第二》)仙真世界的每个成员各有自己的司职、排行及领地,不得相互僭越,否则就会受到仙官的考罚。《真诰》采用了民间流行的谪仙观念,而又与之不同,表现在《真诰》突显了道德教化在其中的决定作用。王褒等曾一次性开除四十四名神仙,原因在于这些人有淫愆之心。正所谓“鄙耻不除,生籍不书。”(同上)
《稽神杻》篇讲述道教地理,“区贯山水,宣叙洞宅”,开启后来的“洞天福地”之说。自然的青山秀水成为仙境在人间的落实形态。这种宗教处理也是兼顾广土众民平实而又现实的心理以便于启信。
《真诰》以宗教眼光审视历史的时候,历史便成为抽象观念的说明,时间性在这里完全失去了意义。从尧舜三代到汉晋六朝,几千年的历史统统被网罗到非时间性的仙真世界里。耐人寻味的是,《真诰》把历史过程敉平、硬化为干瘪的道德事件,通过历史人物的仙界分封而阐发宗教思想。晋王衍女字进贤,为悯怀太子妃。洛阳之乱中,刘曜、石勒掠而欲妻之。进贤守贞,骂曰:‘我皇太子妇、司徒公之女,而胡羌小子敢欲干我乎!”言毕即投河中。其侍婢六出亦随主投河。主婢二人俱得为仙。六出善,有心节,本姓田,系魏时浚仪令田讽之孙。《真诰》认为,六出以卑贱之身投河却得升仙,不惟由于她善节贞,亦是得了田讽阴德的佑庇。(《真诰》卷十三《稽神枢第三》)这实际是在阐发“道德长生”(《真诰》卷六《甄命授第二》)及果报观念。同样,比干与李善被抽象为忠孝之载体,俱已成仙。在正史中因救助他人而饿死的刘翊,在党锢之祸中以气节闻名的夏馥,都被《真诰》赋予了神仙身分。历代帝王,由于杀戮太多,不能成为仙真。《真诰》分封他们为仙人属下的“四明公宾友。”
总之,《真诰》表现出以宗教的立场重新解释世界的自觉,这实际上是一种建立宗教性人文诠释系统的努力,这在《真诰》中是前后一贯的。
三、《真诰》道德教化的非伦理性
《真诰》以宗教视域统摄自然、人文及历史,由上文可知,本质上是以抽象的道德观念为中心重组“此在”(Dasein)身处其间的时空序列,以此强韧地维持其对伦理的关怀。弗雷泽曾经说过,宗教没有任何理论的目的,它所有的只是伦理。这实际道出了宗教与伦理之间有深刻关联,而这一关联,乃是宗教的又一向性所在。但作为社会——政治、历史性教化体系的宗教,本质上是伦理匮乏的产物。而人们通常所谓的宗教伦理,仅仅是道德教化(“义说”)而已。其出发点是把存在者塑造为某种观念的载体或附庸,或使存在者朝向一个异已的终极。而且,这种教化生存在语言与意识中,而不是现实的制度与行为里,它意在挽回已经沦落的现实性伦理。但是,这种教化恰恰是对伦理本身的悖离。
在中国古代思想中,伦理并不意味着某种道德的说教,它也与任何抽象的道德观念(如善)及虚设的终极无关。它的真正含义是“阴阳万物”各有的“伦类分理,”(《十三经注疏》第1528页),简言之,就是存在者各从其类、各得其理,各自成为他自己,而不是他者。伦理的存在是自在的、自然的,老子用“无名”表述它的非人为设定性质,《易传》用“百姓日用而不知”描述其发生效用的情形。因而,伦理也就是宇宙本有的仪则与天秩,伦理人文只是主体在日用中使之明现而已。而宗教人文既然是伦理匮乏时的代用品,其对伦理的处理当然只能是人为的营造,而非运用与显现,如《真诰》对自然、人文及历史的宗教处理就是以抽象的道德观念为基点的逻辑推衍。《庄子·天道》可谓从运用层面概括了这两种人文的特点:“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为也则为天下用而不足。”
《真诰》的人为营造性质突出地表现在对民间神话传说的处理上。我将以西王母传说的演变及人神婚恋情节为例加以说明。
《山海经》中的西王母,“梯几而戴胜,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淮南子·览冥训》则有“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的记载。而在两汉的考古文物如镜铭上,多有“寿如东王公西王母”字样。可见,西王母传说已成为祈求长寿长生愿望的神话表述。传说中的西王母是如何经过宗教性改造而成为仙真世界的最高神格的呢?最值得深思的是在上清道籍中有西王母多达二十余女的构想,而这一点与现存文献中有关西王母民间传说的资料大不相同,在这些文献中根本找不到西王母广收女儿的记载。事实上,西王母广收女儿乃是上清经系缔造仙真世界十分必要的大手笔。仙真世界既然作为伦理社会的理想表征而被营造,那么显然的道理是,这一世界的“公民”必须以群体形式出现,他们之间必须具有人伦关系。于是便有了西王母拥有众多女儿的设计。更为重要的原因也许在于,上清道徒多是高层士族,其时尤多奉道世家,且在门阀制度之下,故对仙界的设计必然要带上宗法色彩。这样就不难理解,西王母从单纯的以三青鸟为使,衍变到《汉武帝内传》时身边已有了侍女群,再到《真诰》时又有了一群女儿。至此,西王母的宗教改造已初步完成。民间传说由于是内在愿望的心理满足,因而在那里西王母可以是邪恶专横的独裁者的象征,如在《牛郎织女》中的那样。但是,西王母一走进道教徒编织的仙真世界,立刻就有了“母亲神”的特征。这一意象成为保佑、生养、慈爱、关怀的“道德原型”。至此,道德在《真诰》中已得到神格化、实在化、本原化、普泛化的宗教处理。
《真诰》还以道教徒和仙真女之间的人神婚恋为情节展开主题。《真诰》记录了三组人神婚恋:羊权与愕绿华、杨羲与安妃、许谧与云林夫人。这不能被单纯地理解为上清道士在修炼过程中经由精神恍惚的病态而获得的神灵附体的宗教性神秘体验现象。这是因为,当时广为流传着“弦超”、“杜兰香”、“何参军女”、“青溪庙神”、“张璞”、“董永”等等人神婚恋的传说,《真诰》过多地强调仙真的司职、排行、治所,显系对这些传说的宗教处理,这样做的好处是教义可以迅速地传播。而且,《真诰》尽可能地删落传说所具有的恋爱情调,婚恋双方“虽名之为夫妇,不行夫妇之迹”(《真诰》卷二《运象篇第二》),被纯化为施教者与受教者的关系。许谧在给云林夫人的信中明确地交待了这种身分:“自奉教以来,洗心自励,沐浴思新。其劝奖也标明得道之妙致;其检戒也陈宿命之本迹。”(《真诰》卷三《运象篇第三》)《真诰》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反对魏晋流行的原天师道房中术,而提倡高雅的房中术——偶景或隐书。《真诰》力求从教化角度重新观照房中术:把它纳入到人伦的范围中来,房中术实践双方是经由人神婚恋而产生的夫妇关系,在具体操作中道德品质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总之,恋爱与方术的淡化,道德教化的加强,在《真诰》中是明显的事实。这也正是《真诰》为什么以人神婚恋展开内容的主要内容。
无论是对西王母传说的改造,还是对人神婚恋故事的宗教处理,《真诰》都着眼于道德教化,并以之为中心建构一主观的伦理世界。宗教与伦理的关联之具体含义也就是宗教是向着伦理而在的,是伦理的异化形式。自在、自然的伦理一旦经过宗教的营构便成为诸多规范的总和,后者在落实中无疑会蜕变为侵夺存在者本身的权力话语,存在者对之的屈服(也即宗教本身的兑现)无疑是以异化自身、成为他者为代价的。因此,《真诰》的教化系统甚至所有的宗教都是既指向伦理,同时又悖离伦理的。马丁·布伯曾把伦理性老庄道学称为教,教是一种不同于宗教的人文型态。“在宗教信徒的灵魂中总是一再产生出对自由,即对教的渴望,人们一再勇敢地进行宗教改革,勇敢地回归教并更新教。但这些举动注定是要失败的。”“这种轰轰烈烈的运动注定不会演变为教,”而是演变为“净化了的宗教。”(布伯《道教》)布伯揭示的宗教与教的复杂关系也正是宗教与伦理之间的关联的实质。学界中人往往过多地强调了二者之间的一致与和谐,而忽视了它们之间的紧张及冲突,宗教生活史表明,后者比前者更为根本。
四、结论
综上所述,在魏晋以前,中夏人文是非宗教的伦理人文,这种人文景观决定了道教的产生实质上是伦理人文到宗教人文的形态变迁过程。这一文化转折是动乱多变的时代造成的,《真诰》谓“末世多疾,宜当服御耳”(卷六《甄命授第二》),多少透露了一些消息。由于伦理人文的巨大影响,道教一直在宗教与非宗教人文之间摆动,如晚唐出现的先天学与内丹学在某种意义上确实逸出了宗教的领域,今人陈撄宁把仙学与道教区分开来并非毫无理据。道教在人文形态上的特殊性格根源于道教的产生与发展始终有一伦理性人文为其参照视镜,而这是基督教、印度佛教所没有的。因而,道教的研究要从中夏人文的实际出发,而不应根据现代流行的“宗教”、“伦理”等观念主观演绎,生搬硬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