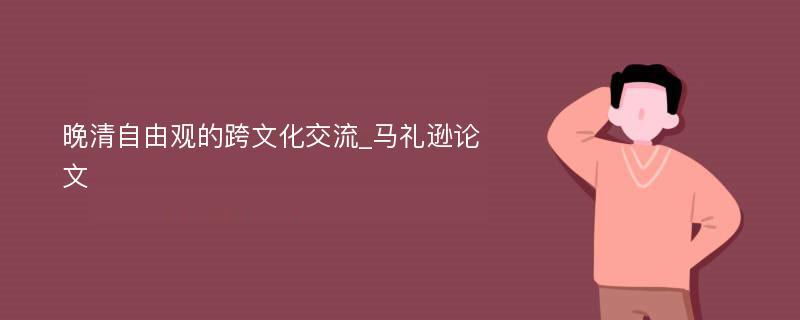
晚清自由观念的跨文化传播进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路论文,晚清论文,跨文化论文,观念论文,自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由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之重要观念,是社会主义继承和发展近代先进政治文明的成果之一,标志着社会的高度理性和先进特征。但任何一种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无一不有其传播的架构和历时性规律。“自由”作为观念传播史的重要研究命题和代表性个案,对其传播规律的厘清和省思,有助于把握这一观念在不同跨文化传播时期的历史状貌和实质内容,也有利于深入理解自由思想递嬗衍变的基本规律。 “自由”一词,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其辞而无政治哲学义。后汉郑玄曾有“去止不敢自由”①之言,《三国志》有“节度不得自由”②之语,古诗词中“自由”屡见不鲜,但它们只存“专由、自在”之义,并无政治意义上的观念联系。诚如(严复,1986b)所言:“政界自由之义,原为我国所不谈。即自唐虞三代,至于今时,中国言治之书,浩如烟海,亦未闻有持民得自由,即为治道之盛者。”虽然,作为其语源意义,西语“自由”(liberty)成为政治观念之前也具有“无拘无束、任意自专”的语义,但其作为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所秉持的核心政治理念早已脱离了本初意味,就连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在讨论自由时,也开宗明义:“这篇论文的主题不是所谓意志自由,不是这个与那被称为哲学必然性的教义不幸相反的东西。这里所要讨论的乃是公民自由或称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密尔,1959) 或认为,在先秦诸子的思想中,庄子的“在宥”③与自由思想暗合。谭嗣同在其《仁学》一书中,将庄子的“在宥”与自由观念相提并论,“庄曰:‘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治者,有国之义也;在宥者,无国之义也。曰:‘在宥,盖自由之音转’。旨哉言乎,人人能自由,是必为无国之民”(谭嗣同,1986)。(康有为,1984)亦言:“庄周言在宥天下,大发自然之旨,盖孔子极深之学说也。”“在”义为“自在”,“宥”义为“宽容”,《在宥》之旨在于反对人为,提倡顺应万物自然,达到不为物役、自在体道、无为而为的理想境界,所以在宥思想与自由主义有着本质上的差异。严复也曾认为儒家思想中的“恕”与“絜矩”④之道与自由观念有相似之处,但他谨慎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然谓之相似则可,谓之真同则大不可。”(严复,1986a) 在“自由”观念缺失的文化语境下,晚清迎来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⑤。虽然西方社会已经进入资本主义快速发展时期,但满清政府依然闭目塞听,固步自封,“那里的制度犹如台球那么结实——它是那么完整、精确、苛求,以至于想不服从就会冒很大的风险。要摆脱它要么靠贪污舞弊,或者靠惰性——即什么都不干,——而极少靠积极性来实现。禁止革新,只要参照惯例就足够了。”(佩雷菲特,1993)严酷的等级,僵化的专制和隔绝带来的是信息渠道的扭曲与阻塞,不了解基本的自然科学知识,更谈不上要求自由、平等与人民权利的近代民主思想(何兆武,2001)。而就在这一时期,西方新教传教士纷纷赴华。他们刊行报刊、出版书籍,希图在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中找寻一条文化调适之路,实现自己的宗教理想⑥。也正是在这种文化实践中,欧美日臻成熟的自由观念伴随着圣经和铁血开始了在晚清社会的传播路径建构。 为彰显这一观念的传播模式和规律,本文将从语汇源流、政治交往、报刊观念场三个维度,厘清并还原自由观念跨文化传播的清晰进路,同时对该个案的认知误区作去伪存真的考辨。 一、语汇意义上自由观念的源流 1807年,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赴华。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着手编辑一部汉语字典⑦。在接下来的15年间,马礼逊在借鉴《康熙字典》、《艺文备览》等工具书的基础上(叶再生,2003),编辑了《汉语字典》⑧。这部字典是近代较早也是最完整最详尽的中英文字典,在跨文化交流史上具有筚路蓝缕之功。字典由英国在澳门创办的东印度公司印刷所(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承印,共刊行约1500部⑨,在中国地区亦有销售(叶再生,2003)。 在《汉语字典》中,马礼逊将“Liberty”和“Freedom”译为“自主之理”。这是近代思想史上对于这两个词汇最早的中文解释,虽然释义简单,也没有涉及到现今中国耳熟能详的“自由”一词,但是字典已经对其所附带的政治含义有所涉及。在“Liberty”词条下,马礼逊(1822)译为“not under the control of any one自主之理”,并例以“Liberty or a mild government that gives repose to the people行宽政乃以民安”,这对“Liberty”的政治意味有了较为平实的理解和表达;而在“Freedom”词条下,马译为“principles of self rule自主之理”,并例以“free government,liberal rule宽政”(Morrison,1822)。这些词汇的解释,摒弃了其根源语义,较多地吸纳了西方先进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难能可贵的是对译这个词的时候,马礼逊(1822)提到了“freedom of speech”的观念,虽然马礼逊以古语“大开言路”言之,但这一表述蕴含了西方“言论自由”的观念,具有先河意义。 有学者认为,马礼逊《字典》存世量少、流传不广、在国内几乎失传,故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几近于无⑩。此观点忽略了思想发展中的层累状况。马礼逊《字典》作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工具的滥觞之作,其后寓华传教士皆奉为圭臬(容闳,1981)。在早期中文期刊引述西方观念时,《字典》的指导意义清晰可见。最具代表性的是1838年《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以“自主之理”对西方自由观念进行了专文刊介。而传教士的文化活动,无疑影响到了近代许多开明人士的思想,无论是践履过欧美,还是于本土放眼望世界者,他们在进行积极的政治思考时,往往将语言工具中渗透的思想纳入到自己的著作之中。譬如严复(1981)在《群己权界论·译凡例》中阐释,西文Liberty,原古文为Libertas,其字与常用的Freedom同义。Freedom,是指“无挂碍也”,又与Slavery(奴隶)、Subjection(臣服)、Bondage(约束)、Necessity(必须)等字为对义。而《字典》对“Free”进行翻译时,无法用汉语中准确的词汇相匹配,只能解释为“not a slave,不为奴”(Morrison,1822)。可见,严复对自由的语义理解与马礼逊基本一致。 1844年,美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刊行《英华韵府历阶》,其中将“Liberty”译为“自主、不能任意”(卫三畏,1844),除了继承马礼逊的译述观点外,又加上了此词的本源语义。 1847-1848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在《汉语字典》基础上于上海刊行《英汉字典》。第二卷中,麦都思(1848)将“Liberty”译为“自主”,将“the principle of liberty”解为“自主之理”,并进一步解释:“to be left to one's own will任意擅专、自由得意、由得自己、自主之事”。而对“Free”的解释,则是“自主、自由、自主掌、自专”,承袭马礼逊的“not a slave,不为人奴”,并增“宽裕、宽容、自得、自若”之义解(Medhurst,1847)。对“Freedom”解释为“任意擅专、自主之事”,且首次提到“Free-man”(自由民)概念,译为“自主之民”(Medhurst,1847)。麦都思第一次以“自由”一词对译这两个英语词汇,“自由”对应“自由观念”当由此发端。 设若上述三部字典还未对“Liberty”的政治语义作充分表述的话,那么在罗存德的《英华字典》中,这种情况得以改观。传教士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1822-1893)在1868年经由香港孖刺西报社(“Daily Press”)印行的《英华字典》中,对“Liberty”进行了深入的解释。解义为“freedom from restraint自主、自由、治己、自操”(Lobscheid,1868)。为区分不同语义空间,罗进行了分类释义,指出“To be at liberty,任其意、听其便、听他自主、由得自己、为自主、无阻无碍”(Lobscheid,1868)的基本语义,但更多的是其政治语义的解释,情况如下:第一,提到“天赋自由”的观念(Natural liberty),译为“任从心意、任从性而行”;第二,提到了“公民自由”的观念(Civil liberty),译为“法中任行”,中国向无“公民”概念,此解释基本上涉及到了这一政治概念的精髓所在;第三,提到“政治自由”的观念(Political liberty),译为“国治己之权”,这涉及到了共和思想的核心理念;第四,提到“宗教信仰自由”的观念(Religious liberty),译为“任意择教、从某教在人”;第五,提到了“出版自由”的观念(Liberty of press),译为“任意写印”(Lobscheid,1868)。这一现象,学界认知付之阙如。 虽然罗存德对于“自由”的理解仅只言片语,不成系统,但这些向度大致反映了自由主义的主要观点。这部字典在晚清流通最为广泛,至于它在后来西学观念的传播中影响无从考证,但就190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华英音韵字典集成》中“Liberty”一词大致沿用罗存德的解释来看,《华英字典》应该在其刊行之后的东西方交流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熊月之,1999)和现代双义字典相比,关于“自由”的解释在这几部字典中更加倾向于政治思想。自由主义的经典著作On Liberty刊行于1859年,此前二百年间,自由一直是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的核心观念,19世纪初叶成为其学理化的黄金时期。传教士字典中“自由”之义的政治化倾向应和此时西方学界政治哲学思考有关。在信息封闭的道咸年间,东西方跨文化传播大致呈单向度特征,其主体亦以西方传教士为主,而中国士人缺乏跨文化传播的主动性,所以并没有出现与之相抗衡的华人编纂的高质量双语字典。这些由西方传教士编纂、教会基金支持印行的字典,自然就成为了当时中国具有开放心态的知识分子和大量赴华传教士的重要工具,其中词汇的社会化思辨自然会对中国士人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有学者认为严复以“自繇”译“Liberty”代表其审慎态度,具有创造之功(颜德如,宝成关,2003),殊不知这一译法在传教士字典中早有尝试(11)。 “自由”在异质文化语境中的语汇意义上的传播,为这一政治观念的传播奠定了良好的概念基础。名实对举,无疑有利于自由的讨论和观念的延伸。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概念历经讨论、实验的过程促进了对自由思想的深度思考。“自由”对译的调适过程,符合跨文化传播的基本规律,为这一观念在晚清时期的传播助益良多。 二、政治交往中自由观念的表达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个别开明士人方才醒悟“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繙夷书始。”(魏源,1876)但这一思想并未引起朝野的普遍重视。直至第二次鸦片战争,东西外交活动的日渐频繁,满清政府因翻译人才的匮乏而深陷被动(熊月之,1995)。(冯桂芬,2002)曾言:“今通商为时政之一,既不能不与洋人交,则必通其志,达其欲,周知其虚实情伪,而后能收称物平施之效。互市二十年来,彼酋类多能习我语言文字之人,其尤能读我经史,于朝章国政、吏治民情,言之历历;而我官员绅士中绝无其人,宋聋、郑昭固已相形见绌。”至同治元年,方在北京设立同文馆,隶属于总理衙门。同文馆的建立为清政府吸纳和培养了大批翻译人才,但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影响,同文馆的翻译主要倾向于格物致知和资于外交的法律书籍,对于西方政治思想和哲学观念所涉无多。 在中西外交活动中,多有外交照会和条约签订。1858年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中,第三款规定:“Her Majesty's Representative shall be at liberty to choose his own servants and attendants。”中文版为:“(大臣)雇觅夫役,亦随其意。”第五款中有“liberty to send and receive his correspondence”的观念。两处“自由”的表述,亦少有政治思想的意味,可见,至少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并没有在政治话语中引进“自由”的观念。 意大利学者马西尼认为,“自由”一词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中应该是在1872年。这一年出版了志刚的《初使泰西记》,“我们在他的日记里,还发现‘自由’(freedom)和‘自主’(independence)这两个词”(马西尼,1997)。许多学者认为志刚一书涉及到的这两个词,只是在照录《中美续增条约》(12)条款时提及。这种认识失之偏颇。因为条约的形成是由“蒲使(蒲安臣)拟成八条洋文,柏协理口述,志使(志刚)译汉文”的(志刚,1981)。也就是说,志刚是第一位使用“自由”一词的满清官员。《中美续增新约》于1868年7月28日签订。条约第四条中有“enjoy entire liberty of conscience”的表述;第五条中有“the mutual advantage of the free migration and emigration of their citizens and subjects respectively from the one country to the other”的表述,译为:“两国人民互相来往,……得以自由,才有利益”(13)。在这两条中,前者申述了“宗教信仰自由”,后者陈明“自由生活是人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虽然对于前者,志刚无“自由”一词表述,而后者又无西语“liberty”或“freedom”等政治语汇相对应,但二者相互发明,“自由”一词具有了政治思想意义。 1870年代,对于自由观念有了更为自觉的理解。1876年,郭嵩焘使欧,其后日记曾提及英国的自由党,因无对应汉语词汇,只能音译(郭嵩焘等,1998)。次年,黄遵宪使日,感受到明治维新给日本带来的深刻变化:“明维元年,德川氏废,王政始复古,伟矣哉,中兴之功也。而近来西学大行,乃有倡美利坚合众国自由之说者”(黄遵宪,1985)。由于深受日本学界所引介的自由观念的影响,黄遵宪在其后的《日本国志·礼俗志》中,对“自由”一词进行了政治性解读:“自由者,不为人所拘束之义也。其意谓人各有身,身各自由,为上者不能压抑之、束缚之也”(转引自黄遵宪,1985)。虽然黄提及“天赋自由、生存平等”的理念,对自由观念的理解并不全面,但他无疑是晚清较早对自由思想有特殊政治思考的中国人。 1886年,张荫桓使美。10月31日,张记录了美国自由女神像的情况,文中称“自主之像”(张荫桓,2004)。12月15日,张记录了蔡毅约翻译的美国宪法及其1791年、1798年、1803年、1865年、1868年、1870年宪法诸修正案,比较准确地再现了美国宪法的政治精神。文中有言:“美为民主之国,应译其创国例备览……我合众国人民意欲联合众邦,以益巩固、昭公义、保安居、敦守卫,兴利除弊,爰及后裔,永享自由之福。”(张荫桓,2004)并翻译了第一修正案中关于宗教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的观念:“民间立教奉教各行其是,国会不得立例禁阻,至于言论著述,安分聚会、负屈请伸等事皆得任便行之,国会毋得立例拘制。”(张荫桓,2004)蔡毅约的翻译已经比较符合我们今天关于自由的政治语意习惯。但对于“Liberty”的翻译并没有对词稳定,在1791修正案第五款中,“Liberty”就被翻译为“拘制人之行藏”(张荫桓,2004)(14)。蔡毅约的美国宪法译本,张荫桓于国内并未见过刊本(15),但并不能说明它未流入中国。1881年,以编采西方新闻为宗旨的报纸《西国近事》就曾刊载过一则新闻:“中国驻美使署有随员蔡锡勇译成美国律法一书。该员在美三年,广交天文历学之士,时往公议堂及律师处留心考察,译成此书,详加注解。经钦使咨送总理衙门,想邀懋赏矣。”(钟天纬,1883)蔡锡勇即是蔡毅约,“美国律法一书”应是美国宪法单行本。走出国门的中国人明显感受到了民主自由和专制集权的不同,开始思考开明政治体制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迥异命运,但是这些思想在当时并未引起国人的注意。因为蔡毅约的译本流进了官僚机构,就连外交官张荫桓出国前都未曾见过;而张的日记只有到了甲午战败的1896年才得以刊刻流通。1897年10月,《时务报》刊载《美国合邦盟约》,应是摘自于张的日记。 所以,自由观念的出现好似秋雨荒原上的火星,未于士林成燎原之势,而是寂灭无痕。直至维新变法前后,才在严复、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等对于西方社会和满清政治的思考中得以展开。 三、传教士报刊中自由观念的引介 作为西方成熟的社会思潮,自由观念在晚清赴华传教士的文化活动中必然有所呈现。较早也较为完整地介绍这一政治思想的传教士报刊是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1851)主编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1838年,《东西洋考》载《自主之理》一文。文章延用马礼逊《字典》的译法,阐述了西方近代政治思想中的自由观念。其所谓“自由”(“自主之理”),不是恣意妄为,无所顾忌(“自主之理,与纵情自用迥分别矣”),而是在法律的范围内,人民拥有生存权、发展权和政治权利,进而实现民主政治并拥有广阔的生存空间,即“按例任意而行”。换言之,自由的基础是成熟的宪政体制,以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其观点如下(16): 第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实现自由的基础。法律必须周延全面(“所设之律例千条万绪”),必须以宪法作为其定制的基础(“皆以彰副宪体”),必须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衡量标准(“所设之例,必为益众者”,“易者推民之益而禀”),必须具有恒久的稳定性(“一设则不可改”)。而法律,应以自由精神为指归,结合具体情况制定(“情不背理,律协乎情”),并具有道德的考量(“律以诛心为先”)。在此法律框架下,“上自国主公侯,下而士民凡众,不论何人,犯之者一齐治罪,不论男女、老幼、尊贵、卑贱,从重究治,稍不宽贷。且按察使有犯,应题参处”,从而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第二,程序正义是人身自由的保障。程序正义体现在法律的执行上:其一,“设使愿拿住人物,而不出宪票,以无凭据捉人,恐惧陷民,致卒役诬良受罪,定不可也。必须循律例办事,而不准恣肆焉。”这是近代法理中“无罪推定”原则(17)最早被介绍到中国来的言论;其二,“设使将罪犯禁狱,届期必须出狱,研讯审事,即如明镜,鉴察秋毫瞒他不得。”如果罪犯刑期已满,必须按照法律的规定按时解除对人身自由的限制。 第三,信息公开与监督是保证自由的必要条件。只有信息公开,才能避免渎职枉法,才能实现真正的公平。文中提及法院诉讼的陪审制度(“副审良民”),并需要公开案情,“遂将案之节恃著撰,敷于天下,令庶民自主细辩定拟之义不义否”。如此则可对相关官员进行监督,严防其危害公民利益,“至于臬宪,其俸禄甚厚,不敢收陋规,人视之如见其肺肝。真可谓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 第四,破除专制是实现自由的重要动力。专制取消了人民财产安全,从而致使整个社会陷入凝滞乃至危险境界:“倘主势迫胁,擅作威福,良民丧心,既畏暴主,最惮勤劳,恐所利之物强夺也。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但各国操自主之理,百姓勤务本业,百计经营,上不畏,下不仇。自主之人调倪事务,是以此样之国大典,贸易运物甚盛,富庶丰享,文风日旺,其不美哉。” 第五,言论和著作自由是精神自由的重要内容。“欲守此自主之理,大开言路,任言无碍,各语其意,各著其志。至于国政之法度,可以议论慷慨。若官员错了,抑官行苛政,酷于猛虎,明然谏责,致申训诫警,如此露皮漏肉,破衣露体,不可逞志妄行焉。”呈前文所考,“大开言路,任言无碍”即为“言论自由”;“各语其意,各著其志”即为“出版自由”。而对于“国政法度”可以“议论慷慨”,使其“不可逞志妄行”,破坏自由之环境。 第六,保障宗教信仰自由是精神自由的重要构成。“国民若操自主之理,不敢禁神道,而容诸凡各随所见焉。虽攻异端,然不从严究治其徒也”,指出宗教信仰自由以消弭社会冲突为目标。当然,郭实腊的宗教自由是站在基督教的立场上,存在着一定的局限。 《自主之理》一文较为充分地阐述了自由思想的基本框架,一些学者纠缠于“Liberty”与“自由”的名相问题,忽略了内容梳理,对该文的认知缺乏理性思考。有人认为1887年的《申报》中《论西国自由之理相爱之情》是较早对自由观念进行明确阐述的例证。其表述如下:西国之所谓自由者,谓君与民近,其势不相悬殊,上与下通,其情不相隔阂,国中有大事,必集官绅而讨论,而庶民亦得参清议焉。君曰可而民尽曰否,不得行也。民尽曰可,而君独曰否,亦不得行也。盖所谓国事者,君与庶民共之者也。虽有暴君在上,毋得私虐一民。民有罪,君不得曲法以宵之。盖法者,天之所定,人心之公义,非君一人所能予夺其间,故亦毋得私庇一民。维彼庶民,苟能奉公守法,兢兢自爱,怀刑而畏罚,虽至老死,不涉讼庭,不见官长,以优游于牗下,晚饭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富贵,清静贞正以自娱,即贫且贱,何害焉。此之谓自由。(18) 相较之下,其自由观念除了调适以儒道思想之外,理论内容并未超出《自主之理》所阐述的范围。 可见,郭实腊对于“自主之理”(亦即“自由”)的理解和阐释是较为深刻的。当然,其目的不是为了推动中国政治思想的进步,而是通过彰显西方进步文明来消除国人的排外情绪(方汉奇,张之华,1994)。所以,郭实腊在《东西洋考》中并未停留在对于“自主之理”的孤篇阐述上,而是通过对西方政治状况的描述来让这一观念具象化再现。大致有: 1.《法兰西国》:“自道光十年至今,此民自操权,擅自立王,而悦服矣。但有多人甚愿推自主之理,莫不恨人之君焉。”(19)1830年,法国国王查理十世颁布镇压自由主义的法律,扩充贵族势力,限制公民权利,导致七月革命的爆发(吕一民,2012)。革命成功后,法国实现了君主立宪政体。但与自由共和的思想尚有差异,于是使出现了自由主义者的抗争。此文记录了发生在1835年费厄斯基刺杀国王的一个政治事件(吕一民,2012)。 2.《西班牙国》:“西班牙,国后髫年,母亲代操权焉。不幸其戚不悦,侵国,挑唆庶民。国后之军无钱粮,国家亏欠,赋税之出纳皆混,在上位者无奈何,而劫其百姓矣。如此留患于后,但此祸无不己求者。既然庶民被窘迫,甚好自主之理,再先设定例。有将军数位、尊贵、鄙践各品,上陈保护国家,宁死不可背自主之理矣。”(20)又载:“西班牙国未平,自王崩,后代公主治国,庶民结党,或好自主之理,或固执异端焉。”(21)此处叙述的是西班牙伊萨贝尔女王继位,为应对卡洛斯等保守派的挑战,支持自由主义者的历史事件(许昌财,2009)。 3.《荷兰国志略》中提到这种荷兰“自主之理”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宋朝时期:“至国公之权渐衰,由是民尚公论自主之理也。商贾操权,仇对国君。”(22)文中表明尼德兰新兴的资产阶级推动了自由思想的发展(王德昭,1987)。 4.《教宗地方》:“嘉庆元年(1796),法兰西三军,大获胜捷,甚恨异端,放纵无道,驱逐教皇,后夺其地矣。嘉庆十八年(1813),复登位,仍旧仗势倚情,自大矜夸,横行霸道。但列西国,今知自主之理,藐视其吓呼,而自主行为。”(23)这里讲的是自由主义盛行的欧洲列强对拿破仑政权的态度。 5.《法兰西国王》:“道光十年,千百姓之誉,庶民举首望之,欲为君焉。遂驱古王,而立之矣。既是如此,不期其心志与日俱更,因欲肆行操自主之理,且摄总权,相争辩驳,而民安焉。国王秉公,施仁发政,抱济世安民之才绥靖国也,故此国保泰降福。”(24)1830年革命成功后,奥尔良公爵路易·腓立浦继承王位,君主专制体制被废除,废除出版审查法,暂时给自由派更多的权利。(吕一民,2012) 6.《西班牙》:“西班牙国,尊贵皆好自主之理,自觉弹遏国民难矣。故立志募庶民,不论老幼擐甲持戈,力逐乱徒,兼摄总政。”(25) 对于英国国会的介绍,《东西洋考》说:“英吉利国之公会,甚推自主之理,开诸阻挡,自操权焉。五爵不悦,争论不止。倘国要旺相,必有自主之理。不然,民人无力,百工废,而士农商工,未知尽力竭力矣。”(26)上述新闻或史政材料,较全面地反映了30年代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状况,而其中自由观念向为支配力量。正是这种机缘巧合,所以在传教士赴华尚未取得合法地位的30年代,西方自由思想便有了偶然传播的可能。当然,马礼逊和郭实腊亦有对出版自由的介绍。前者的《论出版权益》发表于《广州纪录报》(27),英文撰写,影响不大;后者则是在引介西方新闻纸过程中有所提及(28)。 但是,自由观念的跨文化传播没有持续进行,迟至1880年代,传教士报刊对于自由思想的引介才又以描述西方政体的方式呈现于晚清士人。1881年,美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在《万国公报》连载《环游地球述略》,记录了美国的社会状况、历史人物和政治体制,其中曾译介美国宪法及诸修正案,侧面反映了公民自由的法律精神:“一、公议堂大臣不得行法关系立教,亦不得阻人愿从何教,且不得禁人言论、报馆登录、聚集会议、具奏上闻、求免责备。”“二、保护邦国实为要务,不得禁民自备洋枪。”“四、不准无故行查民产、拿获人民、搜检书信等事,倘奉官查访,须求实据,并须立誓详言访查何地何人何事则可。”“五、凡有犯法之事,官署审问当以律。……凡斩杀、囚狱、封产等事务,须照律审定,不得违逆律法。”(林乐知,1881)其文章所介绍的宗教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人身自由等观念,虽然在郭实腊的《东西洋考》中早就有所体现,但后者的文化影响力要比《万国公报》弱得多。林乐知对于美国宪法和修正案的引介,虽然与蔡锡勇在时间上相差无几,但林乐知藉报刊示之于国人,要比蔡锡勇和张荫桓早了15年。 1883年3月24日,《万国公报》刊行了德传教士花之安的《新闻纸论》一文,集中解释了新闻自由观念对社会进步和政治发展的重要作用: 纵有上谕颁行,京报叠发……惟缙绅阀阅、衙署幕僚无不备览,而庶民于京报亦鲜得览观焉,悉以劝善惩恶哉?此中国不设新报馆之疏也。夫朝廷寄封疆于督抚,民隐实难周知,……而新闻纸则查察真确,不敢妄谈,而于民间疾苦冤屈,无不遍达。……若新报则采访探索,即穷乡僻壤,无论事之巨细皆录入其中,不特传之本国,而且传之异邦。则下民受屈有不能自鸣者,新报代为之鸣。(29) 这些观念在1880年代无疑是对于近代新式报刊的社会功能的一次总结,濡染着西方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政治精神,也影响着后来维新派人士对新式报纸的认识。梁启超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观点基本上与此文相类(梁启超,1988)。 1885年,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口译、应祖锡记述的《佐治刍言》面世。此书为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翰·希尔·伯顿(John Hill Burton,1809-1881)所作。作为一部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该书以亚当·斯密的自由竞争、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作为其理论内容,其中自由观念是其立论的基础。如在第二章中曾言: 天赋既人以生命,又必赋人以材力,使其能求衣食以保其生命。顾人既有此材力,必当用力操持,自尽职分。若不能自主作事,则材力仍归无用,大负上天笃生之意矣。故无论何国、何类、何色之人,各有身体,必各能自主,而不能稍让于人。苟其无作奸犯科之事,则虽朝廷官长,亦不能夺其自主之本分。……是以国家所定律法、章程,俱准人人得以自主,惟不守法者,始以刑法束缚之。(傅兰雅,2002)又言: 故无论何种人皆应自立主见,作何种事业可以度日,作何种乐事可以养身,而为上者亦当听其自然,使人人各得自主之益。虽天之生人,其才智与际遇不能一概而论,……然其所以治人与受治于人者,仍是君民一体之理,其于人之生命,与夫自主、自重,及所管产业等事,均无妨碍也。(傅兰雅,2002) 书中所言“自主”即为政治思想中之“自由”,而这自由得以实行的基础是平等权利、契约精神和民主体制的保障,经济发展和繁荣亦赖此而致,“人人俱能自主,人人俱能工作,方能十分富庶”。《佐治刍言》将政治经济学中的自由主义思想引入中国,开风气之先。(梁启超,2005)亦曾如此评论该书:“《佐治刍言》,言立国之理,及人所当为之事。凡国与国相处,人与人相处之道,悉备焉。皆用几何公论,探本穷原,论政治最通之书。” 至于1890年代,华夏兵祸联结,政局动荡,士人聚讼朝政,维新思想日盛,国民心智渐开,中国的思想界呈现相对繁荣。期间,学术开始由“西士倡议”变成了“中士主导”,晚清维新知识分子开始积极思考中国的前途,中国政治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自由观念的讨论也在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开始涌现,许多涉外中国士人关涉自由的著作纷纷刊行,康有为、严复、郑观应、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等维新人士开始讨论自由思想,形成了中国自由观念生成史中一个的重要阶段。期间,外国传教士报刊中没有出现独立介绍自由思想的文本,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庚子之变。 1900年,《万国公报》刊载由英国医生马林(Willams Edwards Maclin,1860-1947)口译、李玉书笔述的《自由篇》,这是迄今可见行世最早的有关论述自由思想的系统性论著。该书为英国哲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所著。《自由篇》共21章,前置“论略”,后附“絜要”,以连载的形式,自1900年5月始至1902年1月止,历时18个月(30)。广有影响的报刊媒介如此持续地而集中地宣传此种思想,其社会影响亦不容轻视。 《自由篇》原本为何,向无考证。《自由论略》中对翻译情况有所涉及: 格致家有施本思或译斯宾塞尔者,即此本意而作自由书或译太平公例,洋洋洒洒,何啻万言,究其指归,即以解羁释缚为第一要义。篇中首言理益之辨,次明感通之由,而以用才为率性之断,以体和为进化之本,然后杂采各事以证之。呜呼!可谓富矣。然其所为自然者,又非言无所事事而郅治自可几也。……故其中有一定之公例焉,曰:“人欲自由,当以他人之自由为界”。篇章虽富,而莫不以此理为归。(31) 在《论略》中,译者提及该书可译为《太平公例》。严复在《天演论》的案语中亦曾提及此书(赫胥黎,1981)。循此名,底本应是斯宾塞的《第一原理》(32)或《社会学原理》(33)。但考其实,则内容不尽相符。根据《自由篇》的章节内容考察,应选译自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据斯宾塞序言可知,这部著作成书于1850年12月,1890年删定再版(34)。此作品初版时名为:“Social Statics:or,The Conditions essential to Happiness specified,and the First of them Developed”(35),可译为:《社会静力学:或,幸福的根本及其首要条件的说明》,“太平公例”的翻译符合其书副题的基本精神。该书第六章阐述“第一原理”,有其文曰:“Every man has freedom to do all that he wills,provided he infringes not the equal freedom of any other man.”《自由论略》中翻译为“人欲自由,当以他人之自由为界”,而严复(1981)翻译为“人得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为界”。并且《自由篇》内容基本上出自该书的第四章至二十九章。综上,马林所译之《自由篇》、严复所言《太平公例》是以《社会静力学》(1851)这部在西方流传颇广、影响巨大的著作为底本节译而成。(36) 在《自由篇》中,“自由”是社会进步、人类幸福的第一原理(First Principles),它不单是“人生而平等”的基本表现,同时也是人的本性中最根本的意愿,“自由一心,乃生人别具之愿,欲推相感之心,亦复如是。其在己也,为一身之谋;其在人也,为打大公之量。”(马林,李玉书,1902)也就是说,“自由”看似指向自我,实则是群治和谐的重要保证。它是社会进步、人生幸福、情感满足、族群及社会个体平等的根本保证,也是社会进化的主要动力。《自由篇》主要反映了社会进化的过程是任何社会力量不可抗拒的,“天道不主故常,而世事终于完美”(李玉书,1900)(37),只有快慢之分,并无有无之别,而这种社会的进化是呈递嬗状态的,“占据之事渐除,束缚之风尽去,而后人乃得其自然之性、同然之理,以恢宏其志量,焕发其才猷,而致乎最宜之境”(李玉书,1900)(38)。在社会进化的过程中,自由是“进化之大枢纽、大关键也”(李玉书,1900)(39),也就是说,自由是人类自身解放和完善的文化标志。在这里,进化论有了更为丰富的内容,“天演之义,所苞如此,斯宾塞氏至推之农商工兵语言文学之间,皆可以天演明其消息所以然之故”(赫胥黎,1981)。正是由于斯宾塞对于“自由”、“社会进化论”、“社会关系”、“自由和功利”(即“理益论”)的相对严谨的论证,所以这部作品在19世纪后半叶享誉欧美。严复在解释《天演论》论时,也不断利用斯宾塞的“社会进化”理论来修正赫胥黎的不足,并指出“自其说出,论化之士十八九宗之”(赫胥黎,1981)。 《自由篇》以其丰富的理论内容、先进的社会学理念、通达晓畅的语言,对斯宾塞的社会学观念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对西方盛行的富于学理的自由思想进行了传播。应该说,这部著作对于西方自由观念的引介功不可没。 《万国公报》在其后的政治传播中涉及自由思想的文章大致有《论美国之前程》(40)、《美国法制原理·论法律与自由》(41)、《译谭随笔·俄国释放之大风潮》(42)、《译谭随笔·论著作自由权之限止》(43)、《译谭随笔·释自由》(44)、《英国自由兴盛记》(45)等篇。这些文章涉及出版自由、自由政体史等问题。其中《释自由》对“自由“的解释最为平实,不单厘清了“自由”对译混乱的问题,指出了“自由”的获得需要民众不懈的追求,同时也分析了日常观念中“自由”的误读,及满清政府对自由思想的政治束缚,这些观念可资教益,节文如下:“西国有最珍贵、最宝重之两名词,为人人所敬爱,求而逐得,则幸福无穷;求而不得,则惨毒无算,而不惜掷相等之价值,流血购之者,即自由(Liberty)和自主(Free)是也。人或不解此两名词之本意,强以无教化、无法律,放纵佚荡当之。于是犯当世之忌讳,甚至欲使译西籍者,悬为禁例,深没其文,此焚书愚民之故智,而令自由自主之萌芽,永不发生于中国,诚大可痛矣。余不得不略为引证以辨明之。夫自由之说,不但中国之易于误用也,在西国亦时有之,故自由必与法律(Law)并行。如美国极重自由,亦极重法律。……法律之所以有,在保护人民之权利,而激动(励)以行其义务。故法律为行事之规条,定其应行与不应行之分。以有法律之故,而人民权利愈显,享此权利者,即得其自由矣。此自由与法律之真理解也。”(46)《自由篇》之后,西方传教士对于自由观念的译介传播均不及前者,加之中国学者对这一观念的思考日渐丰富,西方传教士报刊对此命题的传播逐渐式微,但濡染之功,兢兢之力,当不可磨灭。 严复(1986a)曾言:“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异,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正是在这种与天赋自由相悖的晚清社会环境中,中西知识分子以不同的方式对自由观念完成了历时性的跨文化传播,使其成为清末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的政治理念之一,也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的政治目标。在此过程中,新教传教士的文化活动使得这一观念的跨文化传播贯穿了晚清的整个历史过程,虽然传教士的根本目的是完成古老中国的基督化,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在宗教努力的同时“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马克思,1995),实现了对西方政治文明不同程度的引介。当历史将社会反思的重任置于晚清士人面前时,应该说他们是站在这些跨文化传播先驱的肩膀上来眺望世界和洞照自我的。 总体而言,“自由”从异质文化概念逐渐成为中土社会普遍认同的核心政治理念,考其传播脉络,可以清晰地探寻到这一观念概念介入、实践演化、讨论深入的诸多问题,不单于观念传播史研究有补,亦于华夏文化对外传播有启发意义。基于上述,“自由”观念的跨文化传播理路呈现出积聚的趋势和复合传播的特点,亦可称之为“层累式传播模式”。换言之,即成功的观念传播必须符合语汇环境的成熟、实践领域的深入和观念空间的形成这一复合式框架,在不断深入的讨论中完成观念的普适化。“自由”观念作为成功的跨文化传播个案,其历时性考察可直观地彰显这一传播模式的力量。 ①语出郑玄注《礼记·少仪》。所涉“自由”之语在郑注中尚有其他。见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北大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023. ②语出《三国志·吴·朱桓传》。见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59:1312. ③观念出自《庄子·外篇·在宥第十一》。参见王先谦,刘武撰.庄子集解·庄子集解内篇补正.北京:中华书局,1987:90. ④语出自《大学》:“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10. ⑤见李鸿章.筹议海防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一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4:53.薛福成亦有相似言论。 ⑥《广学会四十周年纪念》曾言:“本会之宗旨,表面论文,虽曰灌输文化,开启民智,改良社会,化导家庭,培养灵修,破除迷信,造福女界,嘉惠儿童。然实际论之,无非欲以基督之福音,圣教之精义,借文字而阐扬真理,期望我国民众,共明救世大道,信仰天下人间唯一之救世主也。”见李时岳.《李提摩太》.北京:中华书局,1964:28. ⑦《伦敦会给马礼逊的指示》中记载“你也许有幸可以编一本汉语字典”。See Morrison E.(1839).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rs of Robert Morrison,D.D.,London:Longman,Orme,Brown,Green,and Langmans,p.95-97. ⑧此字典共分三部:第一部按中文部首检字法编排,中文名“字典”,共三卷,分别出版于1815年、1822年和1823年;第二部按中文音序检字法编排,中文名“五车韵府”,共两卷,分别出版于1819年和1820年;第三部是按英文字母表顺序排列,英文名“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共一卷,1822年出版。参见:(1).Morrison,R.(1815,1822,1823).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London:Kingsbury,Parbury and Allen;(2).Morrison,R.(1819,1820).五车韵府(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Shanghai(上海):London Mission Press;(3).Morrison,R.(1822).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London:Black,Parbury and Allen. ⑨见Morse H.(1926).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1635-1834,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Vol 3,p.240.其中600部运往欧洲,500部由马礼逊购得留存,当在中国传播。 ⑩事实上,《汉语字典》在晚清影响广泛,分别于1865年、1875、1899年在华重印。参见叶再生.马礼逊与《中国语文字典》.《新闻出版交流》,2003:3. (11)其具体情况可参见卫三畏.英华分韵撮要.广州:羊城中和行梓行,咸丰丙辰年(1856):686. (12)《中美续增条约》是由美国卸任驻华公使蒲安臣在1868年代表清政府与美国订立的条约。又称《蒲安臣条约》,《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对等条约。 (13)文本参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261-262. (14)张荫桓的这部分日记内容记于1886-1889年,称为《奉使日记》,后于1896年刊行,名为《三洲日记》。参考张荫桓.张荫桓日记.上海:上海书店,2004. (15)张荫桓在日记中说:“此项译文,不知吾华有无刊本,录于简端,以资考核。”见张荫桓.张荫桓日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96. (16)下文分析中的原文皆引自《自主之理》一文,故不一一注释。文章载于《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道光戊戌年三月)。以下该刊物简称《东西洋考》。 (17)参照贝卡里亚著,黄风译.论犯罪与刑法.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15-24。原著成书于1764年。 (18)《论西国自由之理相爱之情》作者不详,刊载于《申报》,1887年10月2日。 (19)《东西洋考》设《新闻》专栏,该材料载于道光丁酉年(1837年)正月号之《新闻》。 (20)(21)两则新闻刊载于《东西洋考》的道光丁酉(1837)年三月号和乙未(1835)年六月号。 (22)该文载于《东西洋考》的道光戊戌(1838)年二月号。 (23)(24)两则新闻载于《东西洋考》的道光戊戌(1838)年三月号和四月号。 (25)(26)此两则新闻载于《东西洋考》的《新闻》专栏,分别刊于道光戊戌(1838)年五月号和乙未(1835)年六月号。 (27)见Morrison E.(1839).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rs of Robert Morrison,D.D.,London:Longman,Orme,Brown,Green,and Langmans,p.481. (28)道光癸巳年十二月,《东西洋考》载《新闻纸略论》,其中有“议论各事更为随意,于例无禁”的言论。 (29)此文后收于《自西徂东》一书中。参考花之安.《自西徂东·第五十二章新闻纸论》.上海:中华印务总局承刊1884年版影印本。 (30)1901年5月、8月、11月未载。 (31)《自由论略并序》为李玉书撰写,载于《万国公报》1900年5月号,阐明了斯宾塞理论的核心思想。 (32)Spencer H.(1862).First Principles.London:Covent Garden.该书是斯宾塞早期思想的代表作。 (33)Spencer H.(1899).The Principles of Sociology.New York:D.Appleton and Company.该书作于1870年代中期。 (34)参考斯宾塞著,张雄武译.社会静力学(节略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5)Spencer H.(1851).Social Statics:or,The Conditions essential to Happiness specified,and the First of them Developed.London:John Chapman. (36)1999年商务印书馆翻译的《社会静力学》应为斯宾塞1890年的修订删节版,《自由篇》中部分内容未见于此版本。 (37)(38)(39)李玉书.《自由论略并序》,《万国公报》,1900年5月。 (40)该文为林乐知译,任保罗述,载于《万国公报》,1903年1月。 (41)该文为林乐知译,范祎述,载于《万国公报》,1903年1月。 (42)(43)(44)三篇文章为林乐知译,范祎述,载于《万国公报》的《译谭随笔》专栏,时间分别为1903年4月、8月和12月。 (45)该文为马林译,李玉书述,载于《万国公报》,1904年2月-11月。 (46)该文为林乐知译,范祎述,载于《万国公报》,190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