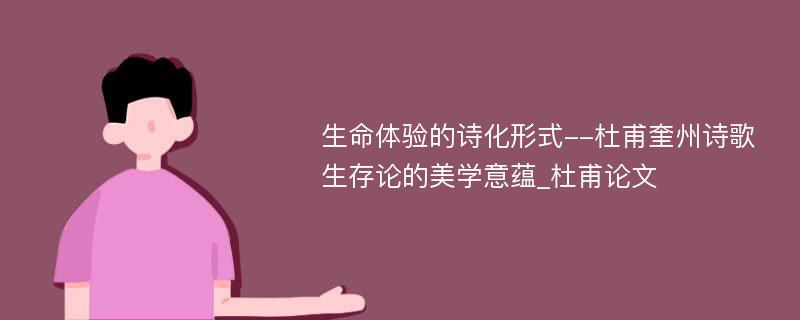
生命体验的诗化形态——杜甫夔州诗的生存论美学意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蕴论文,杜甫论文,的诗论文,美学论文,形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写于杜甫去世之前不久的夔州诗,是杜甫生命旅程最后阶段的挽歌。关注现实,心忧民生的政治诗情,仍是其创作主旨,是杜甫主体生命的社会价值的延伸。面对死亡,杜甫以特有的敏感,展示了他从生存状态上向终结存在的生存论思考。夔州诗以日常琐事为题材的篇章,表现出垂暮老人对于生命的贪恋,以诗歌在生与死之间寻求尽可能多的生活。总之,夔州诗是杜甫晚年生命向终结存在的艺术形式,其深层内核是杜甫对此在的生命体验,这既是对死的超越,也是对生的回归。
读杜甫夔州诗,人们会感到,在那忧愤沉郁的诗情中,隐含着一种生命凋零的深切哀恸;在那雄浑悲壮的诗境背后,飘荡着一片死亡临近的森冷阴影。诗人强烈的求生欲发为浩茫的人世感慨;对死的预感化作痛切的自悼自怜。这种真切的生命体验使人鼻酸泪流,心碎肠断。然而,夔州诗的这一特征虽曾有人提及,但却鲜为论者评说。传统诗学往往只重视杜甫诗歌中那些儒家社会政治理想方面的内容,而对作为现实生活中一个真实的人的情感生活,尤其是深层心态,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诚然,关注现实,追怀历史,指陈时事,心忧民生,仍然是夔州诗的主要题旨①。但是,病老迟暮的杜甫,已不复是“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的少年郎,他挣扎于乱世之中,生与死的尖锐冲突形成夔州诗的深层结构,赋予它一种生命体验的独特色彩。现实与历史、时事与民生都和杜甫个人的生命感受结合在一起。揭示夔州诗中蕴含的恋生情态和畏死情结,无疑将深化人们对夔州诗的认识,特别是对探求杜甫晚年诗风的成因将有所启迪,从而以一个新的视角来评论其美学价值。
夔州政治诗情:主体生命社会价值的延伸
出身“奉儒守官”之家的杜甫,以儒家政治理想为其信仰,以儒家人生哲学作为立身之本。“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是杜甫一生的政治抱负。然而历玄、肃、代三宗,他的这一抱负都未能实现。虽经安史之乱,饱尝流离之苦,晚年的杜甫却依然如故:“死为星辰终不灭,致君尧舜焉肯朽!”(《可叹》)“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遣兴寄苏涣侍御》)显然,“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是杜甫至高无上的人生目标,也是他衡量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尺度。
杜甫在夔州,政治热情未曾减退,甚至比以往更为执著。此时,他已不复为朝臣,虽然为朝廷分忧的忠心未变,却空有荒山野谷中局外人的焦虑。对于杜甫来说,作为实践活动的政治已转化为作为精神活动的政治——亦即以诗歌形式表现出来的政治情感和政治意识,这不过是以张扬儒家政治理想的方式来强化自身残存的生命,扩大和延伸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而这,正是杜甫晚年沉湎于臆想中的政治生活不能解脱亦不思解脱的原因。他见江水而思朝廷“愁边有江水,焉得北之朝。”(《又雪》);谒诸葛庙而感慨“君臣当共济,圣贤亦同时”(《诸葛庙》);尽管身在江湖,却“尚思趋朝廷,毫发祥社稷”(《客堂》);他情切切地表示:“霜天到宫阙,恋主寸心明”(《柳司马玉》);他念念不忘“廷争酬造化,朴直乞江湖”(《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的仕途风云。杜甫自以为是在尽为臣之本分,实际上是在想象中重排参政议政的独角戏:一有风吹草动,他便本能地警觉起来,向朝廷发出警号(《绝句三首》);仅凭道听途说就认定河北诸道节度入朝②,立即赋诗作贺,赞美臣能尽职,君能修德,庆幸域内大定,妖氛扫清,并褒奖功臣,鼓励诸镇来归。(《承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夔州诗虽是针对现实而发,但由于远离朝廷,且为草野之民,其政治理想带有明显的主观性和空想性,它只能作为一种政治期待,以乌托邦式的幻影出现在诗的意象世界中:“一朝自罪己,万里车书通。锋镝共锄犁,征戍听所从。冗官各复业,土著还力农。君臣节俭足,朝野欢呼同。中兴似周初,继体同太宗。端拱纳诤谏,和风日冲融。”(《往在》)这种把中兴的希望寄托在君主的“罪己”、“纳谏”之上,幻想“结辈十数公”,“参错天下为邦伯”,即可“万物吐气,天下小安”(《同元使君舂陵行·序》)“纯是乱极思治之词”③。一个不再对现实的政治发生任何影响力的人的政治热情,总摆脱不了一厢情愿的执拗和无可奈何的悲怆,于是诗人情绪的这两个方面就汇聚交迸为孤愤。
通过张扬儒家社会政治理想而强化主体生命意识,延续并扩大生命意义,不过是夔州诗的表层形态。人们不难发现,夔州诗里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在激越的政治热情中潜涌着无所不在的丧痛;在急切的恋主思报的企盼中流露出时不我待的悲辛。夔州诗中不乏从亢奋的情绪顶峰,急剧跌落到失望的深渊的例证。这种乍热乍寒,忽喜忽悲,骤起骤落的心态,乃是主体生命生死搏斗的反映。杜甫晚年政治热情的高涨,乃是生命自身衰弱的反像,或者说是一种回光返照式的生命情态。
试看这样一些诗句:“时危思报主,衰谢不能休”。(《江上》)“心虽在朝谒,力与愿矛盾。抱病排金门,衰容岂为敏。”(《赠郑十八贲》)“我多长卿病,日夕思朝廷。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孙城。”(《同元使君舂陵行》)“壮年学书剑,他日委泥沙。事主非无禄,浮生即有涯。高斋依药饵,绝域改春华,丧乱丹心破,王臣未一家。”(《暮春题新赁草堂五首》)这些诗句在慷慨激昂的倾诉和剖心沥胆的表白之后,显得分外怆楚、凄凉和喑哑。主体生命的自我价值的张扬和失落、强化和虚化之间,儒家人生哲学的固有矛盾和阙失充分暴露了出来。
儒家学说是一种伦理化的人际关系学说。它非常重视“生”的意义,但这个“生”不是指生命的感性形态,而是指“生”者的社会责任。为了担当起这种社会责任,人应该克制自己的欲望,即所谓“克己复礼”。(《论语·颜渊》)对于“死”,儒家学说采取一种回避的态度,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儒家把死的本质完全归之于天命,宣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从而把死亡神秘化、宿命化。总之,儒家学说中的生死观是社会伦理功利体系,而不是生命本体的思辨论题,甚至也不是自然哲学或心理学的范畴;也就是说,生与死在儒学中不是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而是作为社会价值论而存在的。因此,它不能解决生与死在感性生命此在中的尖锐对立;它既不能推迟、更不能阻挡死的来临,甚至也不能消解人对死亡的畏惧。由于儒家人生哲学的严重阙失,它不能给人们提供一种直面死亡的精神武器,以至酿成杜甫晚年深刻的思想矛盾。作为现实主义的诗人,杜甫揭露了“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驱竖子摘苍耳》)的残酷现实,堪称“诗史”;作为人道主义的儒者,杜甫悲天悯人、推己及人的情志也同样是伟大的。但是“致君尧舜上”的儒家政治理想又使他陷入了“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自恋之中无以解脱。杜甫以诗人的气质和禀性来扮演政治家的角色,这就注定了他在面临生死大限之际,只能从儒家人生哲学的断层上跌落下来,陷入心理障碍和精神危机之中。在夔州诗里,政治忧患感与人生迟暮感是互相渗透融合的。不知是生命的最后余光照亮了杜甫的儒家社会理想,还是儒家社会理想耗尽了他生命的最后一点脂膏?总之,杜甫晚年的政治诗情是其生命情态的特殊表现形式。
向终结的存在:从生存状态上对死的领会
海德格尔指出:“死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种须从生存论上加以领会的现象”④,“死亡作为此在的终结在这一存在者向其终结的存在之中。”⑤向终结的存在是一种生存状态;而对死的体悟,在本质上也就是一种在生存状态上对此在终结的领会。面对死亡,杜甫的社会价值论人格,不能不还原为自然生命的生存状态,他以一个诗人特有的敏感,向我们展示了“向终结存在”的诸般情态。《寄薛三郎中璩》一诗就突出地表现了诗人对此终结的生存论思考:“人生无贤愚,飘飘若埃尘。自非得神仙,谁克免其身?……峡中一卧病,疟疠终冬春。春复加肺气,此病盖有因。早岁与苏郑,痛饮情相亲。二公化为土,嗜酒不失真。余今委修短,岂得恨命屯?……余病不能起,健者勿逡巡。”杜甫对死的必然性、先在性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对早岁嗜酒豪饮的反思,则是对生命衰竭的远因之追溯,从生存论哲学看来,这就是“向终结的存在”的本身,因为“死亡是一种刚一存在就承担起来的去存在的方式”⑥;而结句竟表现出一种参透生死的放达和超脱。然而这只不过是理性层面上的了悟,在情感世界里诗人却未能释然。当诗人的生命如风中残烛摇曳欲灭之际,生存状态的领会竟不能带给他古潭止水般的枯寂和平静:“故人忧见及,此别泪相望。”(《别常征君》)“尽哀知有处,为客恐长休。”(《承闻故房相公灵榇自阆州启殡归葬东都有此二首》)“他日一杯难强进,重嗟筋力故山违。”(《十二月一日三首》)“死为殊方鬼,头白免短促。”(《客堂》)“不可久留豺虎吼,南方实有未招魂。”(《返照》)以上诗句是诗人对死的预感,亦即对作为生存状态的“向终结存在”的领会。其哀惋凄绝,令人不忍卒读。另一些诗句表现较为隐晦,然而却更加沉重。如:“松柏邙山路,风光白帝城。汝曹催我老,回首泪纵横。”(《熟食日示宗文宗武》)此诗啁叹寒食难以再去祭奠祖茔,而自己不久也将为松柏中人。在《又示二儿》诗中,亦有“令节成吾老,他时见汝心”之句,诗人自悲自悼,竟揣测起死后儿女的孝心来了。又如:“北风黄叶下,南浦白头吟。十载江湖客,茫茫迟暮心”。(《凭孟仓曹将书觅土娄旧庄》)仇兆鳌引《杜臆》说:“末云‘迟暮心’,有首丘之思。”《礼·檀弓上》:“礼,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狐死正丘首,仁也。”《疏》曰:“丘是狐窟穴根本之处,虽狼狈而死,意犹向此丘。”首丘之思就是指死后归葬故土之意。
对作为生存状态的“向终结存在”的体验和领会,是夔州诗的重要内容,而这种体验和领会的集中表现则是对死的畏惧。
在生存论哲学看来,“畏死不是个别人的一种随便的和偶然的‘软弱’情绪,而是此在的基本现身情态,它展开了此在作为抛向其终结的存在而生存的情况。”⑦“在死亡之前畏,就是在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和超不过的能在‘之前’畏。”⑧面对死亡的悬临(Bevovstana),人之“畏”不仅是常情,而且是本能。海德格尔虽然把“畏”与“怕”加以区分,但他同时又说:“这两个现象多半总是不分的,而且是怕的东西被算成畏,而有畏的性质的东西则被称为怕”,“而畏……使怕成为可能的。”⑨在汉语中,“畏”与“怕”只有程度的差异而无本质的区别。《辞源》将“畏”、“怕”、“恐”、“惧”互训⑩。因此,如果不是胶柱鼓瑟,面对死亡的“畏”、“怕”、“恐”、“惧”都属于生存论“畏死”的现身情态。杜甫夔州诗中对死的畏惧表现得格外突出:“哀老自成病,郎官未为冗。凄其望吕葛,不复梦周孔。济世数向时,斯人各枯冢。楚星南天黑,蜀月西雾重。安得随鸟翎,迫此惧将恐。”(《晚登瀼上堂》)对此,陈贻焮先生写道:“这到底是种什么恐惧呢?杨伦答道:‘忧群盗也。’这固然不错。不过我认为这恐惧主要来自生怕客死他乡的担心。试将‘衰老自成病’,‘不复梦周孔’与……‘时危人事急’参读,可以看出,他近来确乎感到‘今时危而人事急,死期将至’的严重威胁啊!”(11)这是很中肯的见解。杜甫对死的恐惧,不是什么怯懦者的心态,而是对此在现身情态的自我领会。因为“向死亡存在本质上就是畏。”(12)这种人生的大恸巨怖震撼着古往今来的人们,使他们从夔州诗中感悟到畏死情结如何结胎于生命自身,从而深省到死之先在,生之须臾……
“惧”与“恐”引发的后果就是“逃遁”。因为死的阴影无处不在,而且步步紧逼而来,“连日常此在也已经向终结存在着,这就是说不断地即使以‘逃遁’的方式——理解它的死亡。”(13)这就是杜甫晚年宗教意识的深刻根源。在《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中就表现了一种强烈的皈依佛门的情绪:“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落帆追宿昔,衣褐向真诠。……本身依迦叶,何曾藉偓佺”一联,其意本是表白学佛不学仙,但是转眼之间却又与道士大谈其姹女丹砂修炼之术来了:“药囊亲道士,灰劫问胡僧。……姹女萦新裹,丹砂冷旧秤。”陈贻焮先生说:“挣扎于死生之际,依违于释道之间。此可见其内心的空虚与痛苦。”(14)此言不错,但似乎未透。人们对宗教的皈依固然是为了求得精神上的慰藉,但更深刻的原因在于求生本能。因为宗教世界观提供了人死后的世界图景和灵魂不灭、生死轮回的学说,这是世俗的人生哲学所没有的。因而杜甫一时依佛,一时求道,归根结蒂是对死亡的逃遁和以逃遁的方式所表现的对死亡的理解。
迟暮人的贪恋:在生与死之间寻找尽可能多的生活
朱熹说:“杜子美晚年诗都不可晓”,“夔州诗说得郑重烦絮”(15)。杨伦也认为:“杜公晚年五古,多有此蹇涩沉滞之笔,朱子比之扫残毫颖,如此种诚不可学。”(16)这主要是指夔州诗中那些以日常琐事为题材的篇什。这些诗中确有一部分写得琐琐碎碎,活画出一个垂暮老人絮絮叨叨的神情。但是我们对此似乎也应从生存状态的领会上来理解。
杜甫说:“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杜甫终身与诗结缘,诗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从生存论来看,这实在不是一个比喻而是一种陈述。到了晚年,更是如此:“他乡阅迟暮,未敢废诗篇。”(《归》)“此身未知归何处?呼儿觅诗一题诗。”(《立春》)“呼儿具纸笔,隐几临轩楹。作诗呻吟内,墨淡字欹倾。感彼危苦调,庶几知者听。”(《同元使君舂陵行》)“箧中有旧笔,情至时复援。”(《客居》)这充分证明,写诗不仅是杜甫晚年生活的重要内容,而且本身就是他残存生命的存在形式。上文所论杜甫的政治诗如此,其生活诗亦如此。而且后者甚至是在更本真的意义上贴近生活,呈现着生命。因为它是生命此在的自然情态而没有或少有儒学虚矫的人格面具。
“‘死亡过程’的心理学与其说提供了死本身的消息,倒不如说是提供了‘垂死者’的‘生’的消息。”(17)杜甫用诗“写日记、立遗嘱、志异俗、状物候、写游记、作素描”(18),无论是索寞枯寂中忽闻客至的喜悦之情(《过客相寻》),抑或是畦蔬朱果带来的盘飧自足之感(《园》);无论是园人送瓜引起的欣慰感念之意(《园人送瓜》),抑或是“苦苣马齿掩乎嘉蔬”触发的君子小人之慨(《园官送菜》);无论是畏虎为害课仆伐木的忧患之心(《课伐木》),抑或是“老于干戈际,宅幸蓬荜遮”的见险息机之思(《柴门》);无论是上后园思故土的萧瑟情怀(《上后园山脚》),抑或是水楼宴客,疏帘看棋的情境绮语(《七月一日题终明府水楼二首》)……无不给读者描绘出了他晚年的真实而生动的生活情态。而杜甫见萤火而伤羁旅(《见萤火》),听夜雨而动归思(《夜雨》);借鸡虫得失之喻以叹世风人心(《缚鸡行》),寄鱼水鸟林之情而悟浮生之理(《秋野五首》);瀼西悲秋(《复愁十二首》),东屯视园(《从驿次草堂复至东屯茅屋二首》),茅堂获稻(《茅堂检校收稻二首》),登台独酌(《九月五日》),孟冬惊雷(《雷》),岁暮怀人(《久雨期王将军不至》)……无不给我们提供了“生”的消息。苏珊·朗格认为,“最有启发性”的对生活历程的理解,那就是“在生与死之间尽量寻找尽可能多的生活。”(19)倘若我们把视角移到这样的基点上,定会从这些琐事诗中咂摸出另一番滋味来:诗人在死神的阴影下,那么专注地、一往情深地体验着人生,那么急切而匆忙地享受着生活,乃至不愿意放弃任何一点小小的苦涩的欢乐,执拗而又恍惚,孤僻而又随和,知足而又渴求,自怜而又怜人……唯有其人其事其诗其情融合混一,才能达到这种“简易纯熟,无斧凿痕”(20),“不烦绳削而自合”(21)的境界。那种过于苛严的指摘不仅少了点仁者之心,生者之情,而且也差了点智者之慧,学者之颖……
一个替代课题:死亡经验的象征性获得
读夔州诗,总有一种情感的激荡,灵魂的震动。究竟是什么神秘的力量使我们产生如此强烈的共鸣?社会学层面上的理解和认同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毋庸否认的是在深层心理中人所共有的那种潜在的死亡的诱惑。
死亡是一种不可剥夺的“特权”。每一个人都必须自己承受自己的死,“任谁也不能从他人那里取走他的死。”(22)然而,正因为如此,“他人的死亡却愈发触人心弦”,“在他人死去之际可以经验到一种引人注目的存在现象”;如果以他人的死亡作为“替代课题”,则“此在的某种了结‘在客观上’是可以通达的。此在能够获得某种死亡经验。”(23)从他人身上获得某种死亡经验,这是人们潜意识中的强烈冲动。这种心理现象不仅是生存论死亡哲学的研究对象,也是文艺美学的研究课题。生与死是文艺的母题之一。在艺术作品中对死亡的描绘即是一种替代性课题,人们从中获得某种死亡的经验。虽然艺术作品中的死并非本真的死,然而读者却能从这种替代的替代中获得某种象征性的满足。艺术中死亡的替代课题的典范形式是悲剧,而悲剧本身也是人们探索死亡的一种特殊形式。有研究者指出:“悲秋和悲亡成为中国固定的悲剧意识模式”(24),这不无道理。秋,是自然界向终结的存在;亡,是作为存在者的人的终结(国之亡是人之亡的历史化引伸)。悲秋的实质是悲亡,从生存论意义上说,悲剧意识的潜在本质也就是悲亡。写于杜甫去世之前不久的夔州诗,是他生命旅程的最后阶段的咏叹,是杜甫对自己唱出的挽歌,是生命向终结存在的艺术形式,它负载的正是生——死转化的生命信息。千载之下,人们把卷执读,这些信息即还原为杜甫当年生命体验的现身情态。因此,对于读者来说,夔州诗正是满足他们潜意识中死亡体验的替代性课题。人们从杜甫对生命意义的追求和幻灭以及面对死亡时的精神危机和逃遁中,感悟到人世的苍茫,生命的促迫,从而在更深的层次思考人生的目的及意义。
总之,夔州诗中那些身世之悲、家国之恨的忧时伤世的内容确实体现了杜甫的人格理想、价值取向和人生哲学。但是从艺术本体论的结构层次来看,它只是表层形态,它的深层内核则是此在的生命体验。“死者离弃了我们的‘世界’,把它留在身后。而在这个世界上遗留下来的人还能共他同在。”(25)当然这是一种精神“同在”,通过夔州诗的文本杜甫与人们在情感世界中相遇。这既是凝聚在诗中的生命符号的破译,也是一种死亡体验的艺术性替代课题的展开,这既是对死的超越,也是对生的回归。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个神话似的奇迹:在本真世界中,生者杜甫经由“向终结的存在”而走向死亡;在夔州诗里,逝者杜甫经由“向终结的存在”而复活。这就是夔州诗的生存论美学意蕴。
注释:
①参见邓乔彬:《黄庭坚何以赞赏杜甫的夔州诗》,《古典文学知识》1990年第6期。
②河北入朝事,史无记载,可能是杜甫听传闻而信实。
③杨伦:《杜诗镜铨》。
④⑤⑥⑦⑧⑨(12)(13)(17)(22)(23)(25)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89、310、294、301、301、224—225、318、310、288、288、286、287页。
⑩《辞源》修订版训“畏”为“害怕”;训“怕”为“畏惧”;训“恐”为“惧怕”;训“惧”为“恐惧”;训“恐惧”为“畏惧”。
(11)(14)(18)陈贻焮:《杜甫评传》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102、1151、1214页。
(15)见《朱子语类》。
(16)转引自陈贻焮《杜甫评传》下册,第1118页。
(19)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86页。
(20)陈善:《扪虱新话》。
(21)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
(24)张法:《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