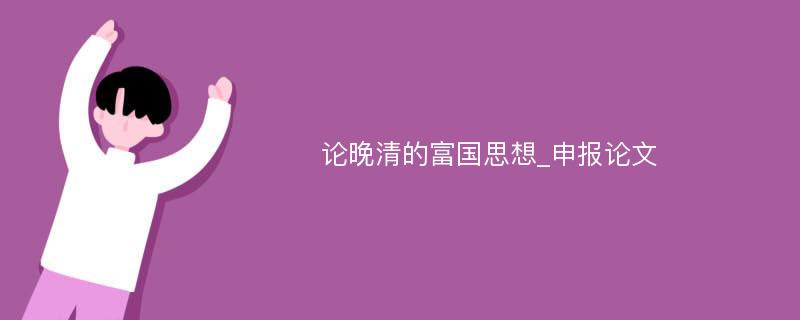
论清末的富国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末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14)05-0081-05 清末以降,特别是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富国成为摆在国人面前迫在眉睫的重大课题。各种富国主张、思想因之层出不穷,蔚为大观。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却着力不多,且多局限于个案,如张登德《论陈炽〈续富国策〉中的富国思想》[1]、张庆锋《盛宣怀的实业富国思想及实践》[2]、赵梦涵《薛福成“工商富国论”研究》[3]。不难看出,既往研究囿于个案,无法更加全面展示清末富国思想的内涵和外延,对于清末富国思想的现代启示更是少有触及。有鉴于此,笔者拟以清末的富国思想为视点,梳理史实,并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深入。 一、富国思想的多元内涵 清末富国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农业富国思想;其二,工业富国思想,体现为开矿富国和发展交通运输业;其三,商业富国思想,包含重商和金融、理财富国。此外,节俭富国亦是富国思想的重要内涵。 (一)农业富国论 农业富国论至清末已经有所弱化,但仍有一定的市场。1906年,商部即奏称:“富国之道首在重农,诚以农事为邦本所系,府库、度支、闾阎生计大都取给于斯。泰西各国罔不以农事为重,美利坚以农立国,富甲全球。日本维新以来农事改良,遂致物产繁兴、工艺发达。”[4]另外,开矿兴利在清末广受赞许,但有人却撰文反驳,“开矿则所费既巨,且矿苗之衰旺,矿质之精粗,苟非精于此学之人无由为之辨别”,并进而提出富国“何如种树一事,地无论南北,时无论冬夏,远则山巅水涯,近则墙阴屋角,无地不可种,无时不可栽”[5]。于此可见,由于树艺一项具有广泛的适应性,也受到一些人的青睐。 其实早在1875年,洋务派干将丁日昌就在著名的《海防条议》中提出丝茶富国的主张。他指出:“丝茶二者,中国大利之所归也,今仅浙闽数省种植得法,若能于地气不甚寒冷之省,一律劝植桑茶,多出一分之货,即可多增一分之税。洋人呢布皆从中国买丝棉而成之者也,往来越海洋十余万里,而犹有余息;若中国自行仿造耕织机器,则丝棉无自外求,深耕可尽地利,不惟百姓可免饥寒,而利权所入当益饶矣。”[6]可见,在丁日昌看来,丝茶具有足民、富国、争利权的三重功效。 (二)工业富国论 工业富国论,特别是其中的矿利富国之说在清末已经成为一种共识。1897年,《申报》载文指出,中国疆域辽阔,“为五洲万国冠,土壤之膏腴亦为五洲万国冠,其间若产金之矿、产银之矿、产铁之矿、产铜之矿、产煤之矿当不可以数计,取不禁、用不謁,足以富国,足以富民”[7]。1900年,《申报》载文再次指出开矿与富国的关系:“矿之为利大矣哉,盖矿中所产或金、或银、或铜、或锡、或铅、或铁、或煤,无一不适于民间日用之需,若采取日多金银,固可以充饷需济国用,自余各物除本国应用外,并可售之他国,以谋什一之利。中国自数十年来仿行西法,轮船铁路次第举行,制造局厂择地设立,无论铜铁铅锡煤炭等物皆须购自外洋,以致利源外溢。若自行开采,则种种大利非但可以自保,并能收回已失之利益,国不因之以富乎。”[8]“开矿一事为富国之本,朝廷深知其然,故叠谕疆臣实力兴办”[9]。就此来看,可以得出两点结论:其一,开矿富国论往往与富民相联系;其二,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社会舆论,开矿富国论都备受推崇,这很显然是与甲午战争后的中国局势息息相关。 清末维新派领袖康有为认为:“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变之之法,富国为先”,且指出富国之法有六个方面,即钞法、铁路、机器轮舟、开矿、铸银、邮政。并认为“行此六者,国不患贫矣。”[10]不难看出,六项富国之法中,四项涉及工业富国的思想。而其中的铁路一项更是被看做近代工业发展的先驱,清末史官恽毓鼎也特别强调筑路与富国的关系,他认为“铁路愈多,商货愈畅,而税则愈增,富国大端无逾此者。”[11]同时,他也是开矿富国论的重要支持者。[12] (三)商业富国论 清末内外交困的形势,使一些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兴商的重要性,并把兴商与富国联系起来。1909年,上海商务总会在欢迎海军大臣载洵致辞中言:“今中国当积弱之时,人人有自强之望。顾欲强国必先富国,欲富国必先兴商,农之所出,工之所成,必待商人以为之绍介而入于市,则其利乃溥。故商人者,实立国之要素也。”[13]从中可以看出商人作为联系农工产品和需求方的纽带,理应受到重视。此外,有论者甚至提出商业兴旺才是富国的根本的观点。[14] 1910年11月11日,中美商团在上海举行会议,华商公推张弼士为议长,美商公推穆尔为议长,其中一项重要的并得到双方赞成的议案是设立中美联合银行。“其性质系商业银行,兼可带做兴业银行生意。资本暂定现行墨银一千万元,中美各半,归两国商会担任,如数收足。设立银行总管理处于相宜之埠,仿照现行美国银行律订定章程,各举董事经理,并在北京注册。总行设于中国商务繁盛之埠,并在中美两国及南洋各处设立分行,其余支店,随时酌量情形随地添设”。[15]中外合资在今天看来,依然是发展包括商业在内的各类经济的重要方式。 开办中美合资银行之所以能够得到与会中国商界的一致认可,其实质性原因则是各国商业银行在我国不断增多,“吸收吾国资财,不知凡几,乃出入大权悉操之外人之手”,“若中美银行成立,庶与在沪各外国银行伯仲,而吾国商界既同处于主人之列,则周转市面、酌盈剂虚实为振兴商务莫大之利。况美国华侨汇归闽粤银款,据海关贸易册考之,每年平均约银七千余万两,其存款于外国银行者尤不可数计。华侨爱国之心最富,苟有中国自设之银行,当如百川之趋海,其存款汇款之利自不外溢矣”。“苟中美银行成立,于国家尤有种种之便利”,“此事上可富国,下可益民”。[16]不过,中美商界在清末帝制最后的日子里达成的共识,根本没有时间落实。另外,沈厚慈则提出了理财是富国的基础的论调。[17] 此外,时人还提出节俭富国的思想:“从来富国之道在乎足民,而足民之原在乎俗俭。俭者,美德也。君俭,则无好大喜功之举而府库自盈;臣俭,则无枉法贪贿之事而清廉自著;民俭,则无荡检逾闲之习而衣食可谋、室家可保。”[18]需要说明的是,清末的富国思想并非全部可取,清末报人汪大钧在其《保富篇上》中就提到,“于是有以富国之说进者,言富国之旨,大端有二:一开利源,一敛民财”。[19]很明显,此种主张把敛民财看作富国的手段实不可取。 二、富国思想的外部保障 富国思想的外部保障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其一,制度型组织保障,包括农会、商部、商会等;其二,教育型组织保障,涵盖各类学堂及讲习所等;其三,包括市场环境和军事保障。 (一)制度型组织 制度型组织之一是农官和农会。中国是传统农业大国,但缺乏管理农业的专门机构。1908年,广东试用直隶州州同张如翰条陈,拟请于各州县设立农官。[20]1910年,《申报》刊文《论苏省农务总会成立之关系》认为,“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欲富国先裕民,欲裕民先足食。盖农务者,衣食之源,生命所关,富国裕民胥于是赖”。基于此因,江苏省农务总会于是年在苏州成立,“刊有简章二十条,规划颇极周详。要其宗旨不外开通农民知识,因地制宜改良一切种植,冀农业之发达而已”。[21]总体而言,清末农业类组织在振兴农业方面起到了促进作用。 制度型组织之二是商部和商会。1903年,商部正式设立,其实早在1893年,就有论者著文提出应该设立商部,“惟商部一官,则尚无人焉奏请设立,是一缺陷事。外洋各国皆有商部之官,即东洋亦仿而行之,综商务之总纲为富国之张本,其意甚善”。文章进一步指出,“中国之商务广大,不亚于泰西各国。而所以治商务者则惟有税司榷员,此外无人焉。夫但收商人之税厘而不能为商人设一谋兴一利,则商人之出捐者未免心有所不服”。而“外洋商务皆统于商部大臣,商人有疑难莫决之事,商部为之剖决筹划疏通。商人有危险之情,商部为之保护。必思所以成全之,以故商人咸服而且上下一心、内外一德。夫是以商务蒸蒸日上而富国之道基于此,强兵之道亦根于此”。最后,文章提出“中国此时当仿其法而行之,亦设商部一官,其位与六部等,而各直省则皆有分司之员或即以藩司兼之”。[22]不能不认为,该论者有着超前的认识,以至于十年之后商部最终成立,向来被视为末业的商业也第一次有了直属的主管机构。 1905年,《申报》刊文《论内地宜广设商会》论述设立商会的必要性,“为今日中国商业计,则不可不急设商会。凡通商各埠商务荟萃之处,固宜急谋联合之法,即内地各都会及水陆交冲之处,亦宜仿照办理,一律设会”。文章认为商会的作用是,“无事则研究商情、联络生气,遇有关系公益之事,或有同业受亏之事,俱可由商会代表出而理论,或地方官吏讳盗为窃、延不破案或关卡司巡、罚捐勒索、黑无天日俱当群起争之。小者争于本省官吏或告知上海总商会公断,重大者或电禀本省督抚或电禀商部伸诉。一切通国之商,人人皆表同情,则势力既固、商业亦盛,商业盛则一国之中血脉贯通、手臂联属,农工之业亦可发达,而富国之策亦基于是矣,所以商会不可不设,而内地尤要”[23]。这表明时人开始把视角由沿海商会转移到内地商会,而这种视角的转变折射出时人对富国之学思考的深化,这本身亦是清末富国思想的一部分。 (二)教育类组织 1905年,商部就提出拟在北京西直门设农商中等学堂[24]。1907年,四川总督锡良奏称:“富国首在务农,阜民必先任土。”“东西各国有农学会以精研究,有农学堂以资讲求,物产繁兴工艺发达,故能竞致富强”。而“川省山河阻深、民勤土沃,只因乡墨守旧法、物理未明、绝少进步,即以夙称蚕国之美利亦复日就衰落,不获与江浙争衡。悯生计之将穷,惜地财之多弃,自非亟兴教育,无由开民智而拓利源”。因此,锡良请求设立农业学堂,“其学科系分为豫科、本科,俟普通农学讲习后,即授以蚕学新法,先得实验于固有之丝业,以次渐及于农田、树艺、畜牧诸科”[25]。作为清末重臣,锡良的奏请兴学在政府要员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1906年,御史叶芾棠“以富国利民端在实业,然非振兴教育终难收效”,“特奏请饬下各省督抚速设高等实业学堂,照奏定章程认真兴办,以发明新理、制物精工为主”[26]。 1907年,闽浙总督松寿奏请饬款兴办实业学堂。其奏称:“今日兴学,已注意于普通教育,尤贵养成实业人才。欲实业之发达,非研究工艺不可。南北洋地势适中,交通最便,可各设高等工艺学堂一所,每学堂至少须容学生千人,开办经费约需五六十万金,常年经费各学堂岁约二十万金可以敷用。虽近时财力窘迫,而各省通筹协解,大省或三数万金,小省或一二万金,众擎易举,自可观成。”[27]清末新政以来,清政府实行奖励实业的政策,而发展实业的前提,则是拥有充足的专门实业人才,因此各地纷纷奏请设立实业学堂。 (三)社会、军事保障 富国必先兴商,兴商的前提则是有一个良好的社会市场环境。1901年,两江总督刘坤一即奏称:“处今日之天下而欲国之强则非富不可,然处今日之天下而欲国之富则又非整顿商务不可。”而“欲整顿商务须先维持市面,欲维持市面须先戒虚务实,何谓戒虚务实,曰商务不外银钱往来、货物流通,而银钱往来、货物流通不外一信字,我之所以易彼者,信彼之银与货也,彼之所以易我者,亦信我之银与货也。使一旦我为彼疑,而我之货与银皆滞矣,彼为我疑而彼之货与银亦滞矣,一铺之货与银滞,则一铺之利必失,推而至于一国,则不几一国之利尽失耶”[28]。1902年,鉴于“崇文门税务及所属各口商税,每有吏员舞弊以致征数寥寥”的情况,肃亲王善耆“悉力稽查破除情面,遇有假托洋人货物者,即照会驻使协力拘惩,猾侩刁商无一漏网,诚富国之要图也”[29]。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刘坤一所谈的在市场交换中应当注重诚信的论点颇有现实意义。而整顿关税一项,其作用一方面在于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在于增加税收。 国防与经济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强大的国防能够为经济建设提供保障。特别是“交通時代之商务,不竞争于国内,而竞争于国外,故必恃国力以为之保护,仗军力以为之先驱”,“苏伊士开通以后,英国商业所以独霸东方者,其海军力足以睥睨一世也……列宾战争以后,美国商务所以突进千里者,其海军力亦有蒸蒸日上之势也。商业之盛衰,一视海军力之强弱以为衡”。因此,“故今日欲求富国必先兴商,欲求兴商必先厚其海军力,此必不可易之次序也”。“海军之成立早一日,即利权之保全早一日,国家奚患不能富强哉”[13]。 三、富国思想的现实启示 清末富国思想现实启示主要有三:一,坚持多方并举,共谋富国良策;二,坚持富国与富民的统一,而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三,不可盲目学习西方。 (一)坚持多方并举 1903年,唐文治借代载振拟《议复张振勋条陈商务折》言:“窃维近世之言理财者,莫不以振兴商务为急。而不知商之本在工,工之本又在农。何者?盖商必有其为商之品物,无上则无以为商也;工必有其为工之质料,无农则无以为工也。故欲求商务之兴盛,在先求工业之精进;欲求工业之精进,在先求农事之振新。”[30]由此可见,唐文治认为农业、工业、商业有着密切的关系,缺一不可,应该统筹协调,方可实现富国。 1904年,《申报》刊文提出了农工商并重的理论:“富国之道,开矿产以撷菁华,勤农务以广生殖,讲工业以精制造,鼓商情以利转输。必使地无遗利,国无游民,然后能财政丰盈、上下无匮乏之虑。”[31]显而易见,这里所谈的富国已经涉及国与民两个层面。 1907年,汪有龄撰文《今后振兴实业之方针》提到“通商劝农惠工之政,自古所重。积数千年,古意寖失,既贫且弱,亦固其所”。于是他提出刚成立的农工商部应该“遂举富国之术,兴利之事,而一以责之于本部,本部尽其责,则利由是兴,国由是富”[32]。1906年成立的农工商部本身就是农工商并重的绝佳例证。 (二)坚持富国与富民的统一 富国的基础在富民,民富则国富。清末以来,这种认识被更多的人所接受。1905年,《申报》即刊文指出:“欲求富国,当先富民。”[33] 1909年,都察院奏代递主事胡柏年条陈:“是故欲图强兵,必先富国,欲图富国,必先足民。民固国之根本,而生财之原动力也。”[34] 1910年,《申报》刊文《论国民担负之多寡与国势强弱之关系》指出:“吾民生计既窘,国力即不能发展,此盖理之出于自然者。何也。合民而成国,欲以富国,必先富民。国之所由立,出于国民所纳之租税,民贫而犹能负担莫大之经费,未之前闻也。语云藏富于民,惟富藏于民间。而民乃得以富自殖其力。直接以富民,间接以富国。欲求强大国力之策。第一当希望国民担负之减轻,百姓足君孰与不足。”[35] 1911年,《申报》发表时评:“欲强国,先富国,欲富国,先富民。”“所谓富国而富民者,将使大多数人生计日裕,则国力不患其不足”[36]。 以上论述都把富国和富民联系了起来,都提出了欲富国、先富民的论点。但是透过表象我们不难看出,以上论述提出富民的出发点是富国,仍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富国与富民的关系自古就是历来思想家论争的重点,其实早在先秦时期,荀子就提出“兼足天下”、“上下俱富”[37]的观点,一定程度上把富国与富民统一了起来。然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这种主张一直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清末亦然。 (三)不可盲目学习西方 1910年,邢宜良撰文《道德为富国强民之基础论》言:“近数年来国家锐意振兴、力图富强以御外侮,以复我国之光荣。于是开矿、练兵、筑路、制造、兴学校、造人才,凡此皆我政府诸公孜孜讲究者也。然学校虽兴,成效莫睹,而所谓人才者渺焉。查焉数年以来,官吏无道德如故,军商无道德又如故,此无他,为国家者舍本务末,舍道德而重虚浮之故。而夫在上位不重道德,故学校出游荡之士,行伍造无勇之军,廛市育无德之商。惟其不重道德,故开矿、筑路、制造皆归无济而无实效。嗟夫!舍泰西富强之秘诀(即基督教)而不求,唯知形下之道,是诚计之左矣。”[38]显而易见,邢氏所言道德富国,即所谓的基督教富国,显然并不适合清末中国,这反映了清末国人向西方学习的盲目性。 综上所述,清末富国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其中不乏闪光之处,并且一些主张颇具可操作性,这是中华民族经济思想中的宝贵遗产。至于其中的局限性,则在于清末富国思想对“富国”的阐释,一般仍是指保证国家财力充足,即在经济上有足够的支配力量,因而富国思想的立足点在于“国”,根本目的仍然是为了“治天下”,蕴含着浓厚的维护统治之利益驱动。另外,清末的富国主张也着意于思考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制约,以至于富国思想未能最终造成“国富”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