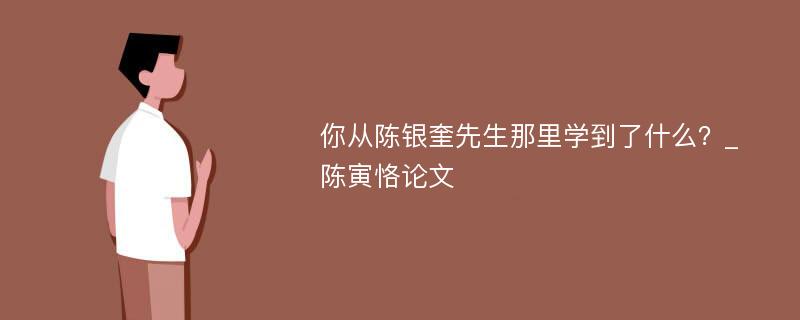
向陈寅恪先生学习什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陈寅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前些时候,在一些书刊中,讲堂上,以至大学生宿舍里,关于陈寅恪先生的思想、风骨、行止,一时似乎成了议论的热点。
无疑地, 作为一位有多方面重大成就的前辈史学大师, 陈寅恪(1890—1969)是值得人们纪念的。他在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特别是佛教史、西域各民族史、蒙古史、敦煌学、中国古典文学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建树。他“力求通过考证来发掘历史事实及其内在联系,从而展示出事物发展的全过程,其成就较乾嘉诸学者更上一层。为了提高史料的可靠程度和开拓史料来源,他倡导诗文证史,为史学研究另辟新途径。尤其是从两种不同观察的记载进行比较、分析的方法,是治史方法上的一大突破”(《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第一卷)。他所留下的这些思想、学术遗产,至今仍然需要我们很好地去发掘、研究、继承和发扬。
不过,对于有的论者来说,陈寅恪之所以值得推崇,不仅在于他的学术成就,尤其在于他的学人风骨、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而作为这种风骨、人格、精神的突出体现并被反复强调的,则是1953年中国科学院聘请他出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时,他复郭沫若、李四光函中所提出的两个条件。这就是:“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请毛公(毛泽东)、刘公(刘少奇)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有论者以为,当六十三岁的陈寅恪说出这句话时,他在那一刻正是表现了中国传统史学家某种秉笔直书的“壮烈情怀”!
陈寅恪曾自称“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曾国藩)、张南皮(张之洞)之间”。对于一位有着这样思想经历的老知识分子来说,主张不学习政治,不宗奉马列主义,是可以理解的。而且,马列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真理,它既不需要、也不应当强制人们去“宗奉”。这里的问题在于:陈寅恪之所以在学术上取得重大成就,是不是因为他不宗奉马列而争得重大成就,是不是因为他不宗奉马列而争得了独立思想、自由精神?不了解马列主义,究竟是他的长处还是弱点?主张不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史学研究,是表现了他的一种思想局限还是一种需要大力歌颂的英雄行为乃至壮烈情怀?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想引证一下周一良先生对陈先生的一些看法。
周先生也是一位在魏晋南北朝史等研究方面有重要成就的老一辈史学家。他早年曾师从陈寅恪,在历史语言研究所由陈先生任组长的历史组从事研究工作,并深受陈的影响;从哈佛留学归来后,又同陈先生在清华一起共过事,并给他译读过日文杂志的论文。他对陈寅恪的了解是很深的。正因为如此,他对陈先生的思想、学术的评价,也就应该有着特别的分量。
在《纪念陈寅恪先生》(1989)一文中,周一良先生提出了“陈先生何以能不断发前人未发之处”这个问题。为此,他讲述了陈寅恪具备的四个条件:非凡的天资,其中包括敏锐的观察力与惊人的记忆力;古今中外,博极群书;良好的训练,其中包括清代朴学的基础,古典诗文的修养,西方历史语言研究方面的训练,各种语言文字的掌握;勤奋刻苦。他说,在解放前卓然成一家的史学大师中,像陈寅恪那样,“完全地而不是部分地、充分地而不是稍稍地具备这四方面条件者,恐怕不多”。不过,他认为,这些还不是陈寅恪取得突出成就的主要原因。他写道:“解放以后,我粗学马列,感到陈先生虽不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治史之道却充满朴素的辩证法,善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这也许是陈先生在解放前的史学界能够冠绝群伦的主要原因吧?”他指出,陈先生论述历史现象时,经常注意区别共性与个性,研究二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看历史问题,很重视纵向观察,看源流和演变,能以几百年历史为背景来观察。“正由于如此,陈先生的论著大都视野广阔而辨析精深,符合于辩证法。”
以为“宗奉”马克思主义就会束缚研究者的思想,这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误解。诚然,“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是束缚思想的。但“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否定和歪曲。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所“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恩格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并不是由什么人发明出来,而后从外部强加给历史的僵化的原则;它本身正是从无数的历史现象中抽象出来的对于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的认识。而且,它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不是一种封闭的学说。它在发展中可以融合、吸纳一切对于历史的科学的观察方法和研究成果。正因为如此,以它作为指导去观察历史,将有助于人们透过历史的现象,把握历史的本质即内在的规律性。而一切对于历史科学的观察方法,也是可以而且一定会与它相通的。周一良先生对于陈寅恪学术成就所作的上述评析,不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吗?
几年前,在北京史学界的一次座谈会上,记得当金冲及教授称赞田余庆教授所著《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写得深刻、读来引人入胜时,周一良先生曾说:田先生这部书超过了陈寅恪。因为陈先生的方法,田先生都掌握了;而田先生掌握的方法,陈先生并不都掌握(大意如此)。周先生的这番话,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因为我在北大历史系上学时也读过陈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等书,从中受到过启发,而且听得人们议论,陈先生的学术成就几乎是无法超越的。不过,周先生当时并没有对这几句话作解释。后来,在1997年第三期的《北京大学学报》上,我读到了周先生对此所作的进一步的说明。他指出,田余庆教授“此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微观的历史考订与宏观的大势鸟瞰,对东晋一百年的政治、社会史作出不少富有创造性的解释,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上的一大突破。书中论点之新鲜,分析之透辟,不亚于陈寅恪先生之著作,而有些方面过之,其原因当归功于解放后不断学习唯物辩证法之赐”。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不仅不会限制、而且有助于推进历史科学的发展,这该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例证吧。
显然,周一良先生对陈寅恪、田余庆有关著作所作的上述评论是富于启发性的。事实很清楚:如果说陈寅恪的治学之道充满着朴素的唯物论、辩证法,是他在老史学家中冠绝群伦的主要原因,那么,不“宗奉”马列,就恰恰不是他的强点而是他的弱点,不是他的优胜处而是他的局限性了。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把陈先生的这种弱点和局限,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把它神圣化为崇高的风骨和壮烈的情怀呢?这究竟是对这位史学大师的尊崇还是讥讽?是对青年人的激励还是误导?是对社会科学的促进还是阻滞?这些问题,都该让我们深思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