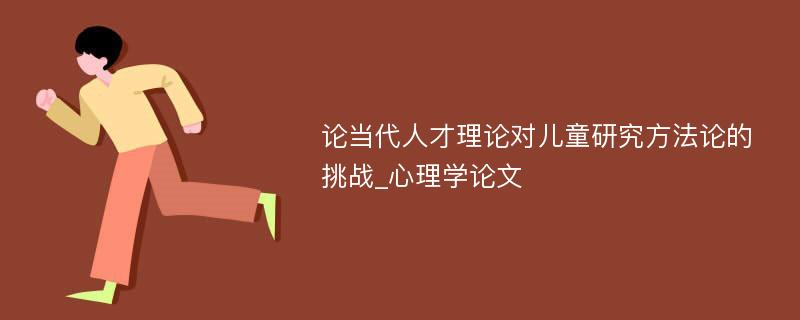
论当代“天赋论”对儿童研究方法学的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学论文,天赋论文,当代论文,儿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38(2002)03-0001-04
“天赋论”(Nativism)历来是儿童发展心理学中一个古老而常新的经典问题。近二十多年来,随着神经科学、认知神经科学、发展的认知神经科学、婴儿实时脑激活研究、神经语言学等突飞猛进的发展,使得人类对自身的“天赋”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并导致古老的天赋论在当代再次复兴。目前国外已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天赋论形式。本文试图对当代儿童发展心理学中“天赋论”的复兴及其研究方法问题作整体上的概览。我们首先综述一下当代各种天赋论的表现形式或类型,然后分析当代天赋论复兴的原因,最后就当代天赋论对儿童研究方法学的挑战及其启示进行讨论。
一、当代“天赋论”的各种类型或表观形式
众所周知,“天赋论”最早是一种古老的哲学观念。随着科学的发展对人自身认识的加深,它日益渗透到科学本身而成为一种科学观念。我们这里所考察的天赋论,显然是一种儿童发展心理学中的科学观念。这种观念在当代的复兴形式主要表现为以下4种:
1.模块天赋论。这种天赋论可以说是当代天赋论复兴的最典型的形态。其基本要义是:人的心理是由遗传上规定的、功能独立的单元即“模块”(module)所构成的。心理模块只能是天赋的,它是一种相对固定的、受到高度制约的天赋规定的组织。模块天赋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哲学家福多(J.Fodor),语言学家乔姆斯基,“进化心理学家”科斯米德斯和托比(Cosmides and Tooby)等。
福多1983年出版的《心理的模块性》首次提出了“模块”的天赋性概念。根据这一概念,作为功能独立的、目的特殊的单元即模块只能是天赋的。他宣称模块具有“固定的神经构架”(fixed neural architecture)。[1]这就意味着:模块被注定是“硬件化的”(即不是从更原始的过程所装配的),具有固定的神经构架(即遗传上规定了的)。福多把模块比作身体的器官。我们的身体是由许多功能独立的器官所组成的,通过各器官的相互作用,便形成我们身体的整体功能。当然模块并不像身体器官那样交换能量或液体,而只能交换信息。这表明模块是一个功能上的隐喻(你可以说是一个抽象的“器官”)。但它就像身体器官的成长一样,是受遗传控制的;它也不是遍布整个大脑的,它只在某个特定的神经结构或大脑皮质中存在(如语言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福多最近还进一步断定:“一个模块所专有的信息和操作或多或少无一例外地是‘遗传上预先编程的’(无能这准确地是指什么)。”[2]可以认为,福多所主张的模块天赋论是一种“纯粹的”或“强的”、“极端的”天赋论。
乔姆斯基晚期在其《关于心理研究的模块化方法》一书中,将他的语言模块的思想加以系统化。他认为:心理由“具有其自己特性的分离的系统(如语言官能、视觉系统、面孔识别模块等)所组成。”[3]乔姆斯基关注的是语言模块,更特别的是句法或“普遍语法”这样的模块。他确认,我们的“语言能力”是由对我们的自然语言进行内部表征的语法——普遍语法——所组成的。这样,乔姆斯基的模块实际上是—种在心理上表征的领域特殊的知识或信息实体。简单说,它是—种表征系统。这种表征系统当然是天赋的。
近期进化心理学家科斯米德斯和托比等提出了“达尔文模块”(Darwinian modules)的概念。这种模块是“天赋的”认知结构——其独特特性主要或完全由遗传因素所决定。此外,进化心理学家提出更强的观点:支配我们认知结构的许多达尔文模块是自然选择的产物。它们是在物种进化史期间由自然选择所发明的类型,以便在该物种的自然环境中产生适应目的。这样,不仅进化心理学家本身偏爱模块是天赋的这一观点,他们也偏爱于模块怎么样成为天赋的——即经由自然选择——种理论。虽然达尔文模块在现代环境中不必提高繁衍适应,但它们存在着,因为它们在我们“更新世”的祖先的环境中的确提高了适应性。换言之,虽然达尔文模块现在不必是适应性的,但它们是“适应器”(adaptations)。对模块的起源进行这样的说明,就是进化心理学家称为“达尔文式的”之理由。[4]
2.“初始天赋论”。这是指婴儿从出生时便表现出来的知识,或称“初始知识”(initiatknowledge)。其代表人物是发展心理学家戈普尼克(Gopnik,A.)和斯佩尔克(E.Spelke)。戈普尼克初始天赋论的要义是:“婴儿似乎具有天赋的心理知识,这种知识是似理论的,至少在它的确超出直接知觉经验这一意义上。它能产生真正的和富有创造的预测。它依进—步的证据而被修正。当我们说这种知识是天赋的时,我们不是在哲学意义上指这一点。它是指:既不是该哲学家也不是任何闲荡的家伙能想到一种学习它的方式。我们是指,它在42小时大的婴儿中显示出来。”[5]“我们支持的观点是,婴儿由于某种天赋结构在理解人方面被赋有一种跳跃性开始,但他们逐渐开始理解包括假装、意象、情绪、知觉、愿望、意向和信念在内的整个心理领域。新生儿尚不具有像这种充分的心理理论的任何东西,但他们的确具有理解他人和人的行动的富有优先权的方式。”我们可以认为,初始天赋论是—种比较“弱的”天赋论,因为它强调天赋的东西只是赋予一种“跳跃性的开始”。按照戈普尼克的说法,初始天赋论是一种“系统阐述关于早期发展的一种理论,这种早期发展严肃地呈现婴儿对人的理解的初始状态的丰富性,并仍然拥有发展的变化。我们提出我们称为‘初始状态天赋论’,它并不归结为福多的‘模块性或最终状态天赋论’——结果从一开始就是固定的,只是随年龄而成熟。恰恰相反,我们提出,发展是通过一种不断的修正过程而进行的,就像科学的理论变化过程。婴儿决不是面临从行为的粗陋事实引入心理的经验这一经验论困境。他们也不被一种简单地、生物学上固定地解释他人这一约束所诱惑。与科学相类比能使我们表明,4岁精致的心理生活在没有新生儿的心理中被预先安排程序的情况下而出现。西方成人的常识心理学框架既不是天赋的也不是成熟所决定的;它主要被儿童所塑造,以此来说明他与他人相处的经验。儿童——像研究他们的成人一样——是从某种强有力的假定——他们从事实验,他们构造的理论被他们所接受的证据深深地影响开始发展的。我们对儿童的理解以及他们对我们的理解本质上不是固定的,而是像我们彼此相互作用一样慢慢修补成形的。”[6]
3.“参数天赋论”。这种天赋论——以乔姆斯基为代麦——认为人类的“普遍语法”已经设置了有关环境输入的天赋规定之参数。婴儿为什么能学习不同的语言?根据乔姆斯基的观点,这是因为普遍语法有确定的参数,这些参数可以通过经验而固定下来。“语言能力”是一种错综复杂的网络,此网络与一个包含开关矩阵的“开关盒”相联系,这些开关可以在两种状态之间转换。除非开关以某种方式加以设置,系统就不会工作。当开关以某个允许的方式设置后,系统就按其自身的性质工作,但是不同的功能取决于所有开关的设置方式。这个固定的网络就是普遍语法的原理系统,开关就是由经验确定的参数。给正在学习语言的儿童呈现的数据必须能满足开关以某种方式进行设置的需要。而开关一旦设置,儿童就有了一个特定语言的命令,并了解了该语言的事实:一个确定的表达具有了确定的意义。这样,根据参数天赋论,所谓语言学习就是确定普遍语法尚未指定的参数值的过程,是设置开关使网络工作的过程。语言学习并不是儿童真正做什么事情,而是置于适当环境中的儿童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像儿童处于适宜的环境刺激和营养条件下,按预定的方式生长和成熟一样。总之,按照参数天赋论,儿童的语言获得能力是脑的固有机制的结果。婴儿的大脑可能天生就能分类接收刺激,如音位、词、句法类型和短语。这种天赋的机制使儿童能正确、快速地获得语言。
4.“素质天赋论”。这种天赋论认为人有天赋规定的“素质”(Predisposition)即注意偏向和原则倾向性等。这以卡米洛夫—史密斯(Karmiloff-Smith)为代表。她在1992年出版的《超越模块性——认知科学的发展观》中重新解释了“先天规定”一词的涵义。她说:“我在本书中用‘先天规定’这个术语,并不是说在出生时就存在预先规定的模块的遗传蓝图。我主张的先天规定的素质比福多的先天论所说的来得后成。贯穿本书的观点是天性(Nature)规定了最初的偏向或倾向,它把注意力引向有关的环境输入,而这又反过来影响随后的脑发育。”[6]卡米洛夫—史密斯认为,信息储存在儿童心理中有几种不同的方式。其中一种是通过作为进化过程之结果的“先天规定”。先天规定的素质可能是特殊的,也可能是非特殊的。无论是哪一种,环境的输入都是必须的。当先天成分被详细规定时——像福多和乔姆斯基那样,环境的作用可能只是触发有机体去选择一个参数或线路而不选其他。与此不同,当先天“素质”只是—种偏向或—个“概略”(a skeletal outline)时,那么环境的作用就不仅是—个触发器,它通过心理与物理/社会文化环境之间丰富的后成互动而实际影响大脑的随后结构。而所谓“概略”就只涉及到对特定输入的注意偏向,以及一些限制计算这些输入的原则倾向性。
此外,在当代天赋论的复兴中,还有所谓“领域特殊天赋论”、“成熟限制天赋论”、“机制天赋论”等。这几种往往只是提法上不同,或内容上大同小异,并不与上述四种典型天赋论形式有实质性区别,故从略。
二、当代天赋论复兴的原因分析
当代儿童发展研究领域天赋论的复兴,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实验研究技术方面的原因,也有纯粹理论上的原因。下面我们稍加具体分析:
从实验研究技术方面的原因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婴儿实验研究的方法和技术有了新的较大的突破,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婴儿实验研究的新范式。其中最有代表性的首先是“习惯化/去习惯化”技术。在这种技术中,向婴儿重复呈现同样的刺激,直到他们开始对它只注视比较短的时间,表现出对这个刺激不感兴趣。然后呈现不同的刺激。如果婴儿注视较长时间,表现出兴趣的重新产生,那就可以下结论说,婴儿认识(或知觉、理解)到新刺激与以前的刺激不同。婴儿对—个事件的兴趣(例如,在一系列各种大小和颜色不同的方块之后见到一个圆圈)一般表现为注意的延长。如果新生儿表现出对方块的兴趣降低,也不管它们的颜色和大小的改变,但是突然对第一次呈现的圆圈表现出兴趣的恢复,那么心理学家可以下结论说,新生儿出生时就存在着对“形状”的分辨能力,而不必经过学习。在这一技术中,婴儿的“兴趣”是通过吮吸的增强或观看的延长来加以测定的。这可以帮助我们探索环境的输入对婴儿先天素质的影响。例如,通过运用测定观看时间的技术便可发现,婴儿对一只没有支撑而停在半空中的球表现出惊讶(看的时间要长些),或者对一个物体似乎穿越一个坚固的表面而表现出惊讶(即他们也许对明显违反物理的规律具有特殊的敏感性)。
其次是“观看或倾听的偏爱”技术。在这一技术中,不测定习惯化和去习惯化,而是向婴儿同时呈现两个刺激,测量婴儿更喜欢哪一个。测量是由看不到婴儿能见到的刺激的观察者进行的。可利用这种技术测定婴儿把听觉刺激的数目(如3个鼓声)与两组视觉刺激中哪一个加以匹配的能力,其中一组包含两个物体,另一组包含三个。
近些年来,“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研究成为新的热点。心理学家发现,3岁儿童已处于理解“信念”的边缘状态。然而,在“不明的年龄”(a dark ages)期——从大约15个月到36个月,现已确立的婴儿研究技术——如偏爱新颖性的程序——不起作用,因为儿童太大以致不能坐着并被动地看;相反,要求健全的言语区分的测验(如指导语“当我第一次问你时,在我们做X之前,你相信的东西是……”)也不起作用,因为对于这种“言语体操”来说学步儿又太小。于是,最近又发展了几种专门测验不明年龄期儿童的心理理论的技术。其中一种技术是使用学步儿的语言能力。这种研究表明,18个月的儿童能理解:词指称客体,并能利用成人的注意线索(如凝视方向、姿态)来分辨一种新颖标记的所指物。在相似的年龄,儿童也以他们企图确定一个新颖词的所指物来说明他人的意向。而对早期谈话的自然主义研究的分析,也说明了儿童对心理的理解。
第二种新近发展的技术——被称为“行为再扮演程序(behavioral reenactment procedure)”——也探索儿童对心理的了解,但不依赖于语言。行为再扮演程序集中于儿童再扮演或模仿他们所看见的行为、但以更抽象的方式来进行这一自然倾向。大量研究表明,儿童——甚至更小婴儿——不是机械的模仿,他们不是直接模仿他们所看到的事件,反而是对它们进行解释。这意味着,如果我们正确地安排一种情境,我们就能利用他们再扮演成人行为的自然倾向作为他们怎么样理解世界的一种“解读”。这种方法被广泛用于通达儿童语言结构的心理语言学文献中。这种工作表明,要求模仿成人语言的句子的儿童,往往用相似的句子——常常是与将要被模仿的句子同义的——作出反应,但符合儿童自己的语言规则。行为再扮演程序使用指向目标的动作的模仿来考察儿童在解释人的行为时所使用的心理结构。[7]
第三种新技术关注的是儿童非常早地解读人的情绪表达的意义这—倾向。这构成了早期“社会参照”(social referencing)研究的基础。有证据表明,像幸福、悲哀和厌恶那样的基本情绪与早期婴儿的特殊面部表情相联系——并且是跨文化的普遍。在我们成人的心理理解中,情绪密切地和内在地与“意向”和“愿望”相联系。在日常成人框架中,我们假定,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或当我们意图时而行动,将导致幸福的情绪,而失败则导致消极的情绪。我们也假定,我们以将产生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情绪这样的方式进行行动。显然,这种新技术是利用解读情绪表达这一早期非言语能力作为探索儿童心理理解的方式。
除了实验技术变革的原因之外,当代天赋论的复兴还有深刻的理论原因。可以说是当代发展心理学理论演变的逻辑结果。这里不能不说到皮亚杰逝世后所谓“后皮亚杰时代”皮亚杰理论的状况。众所周知,皮亚杰是一个彻底的反“天赋论”者。他经常把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生态学家洛伦兹等作为批判的对象。在对婴儿天赋成分的估计上,他至多只承认“遗传格式”(genetic scheme,即注视、抓握和吮吸等)的存在及其对发展的意义。他的基本理论立场是:在包括感知运动格式在内的认知格式领域内,遗传与成熟的作用都限于:只能决定后天成就的不可能性或者说可能性的范围有多大。但是成就的实现,需要由经验从而也是由环境所给予的外界材料,以及由自我调节引起的逐步的内部组织化。要说明认知性行为,我们必须求助于“内源因素”,但是绝不能由此就说每一种内源的东西都是从一种遗传研究设计所派生出来的。但是,皮亚杰的这种过于“后成论”的建构主义观难以解释由婴儿研究新范式(新技术)所导致的新发现。可以说,皮亚杰的婴儿观——关于“感知运动期”婴儿的概念——已受到近期婴儿实验研究新技术的严重挑战。这就致使人们不得不重新考虑婴儿的天赋能力的问题。也就是说,古老的“先天”与“后天”的经典问题在新实验背景下再次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提了出来,迫使人们作出新的回答。这样,发展研究领域的天赋论的复兴就势所必然了。
三、对儿童研究方法学的挑战
最后我们需要从方法学的层面上反思一下,当代天赋论对我们的儿童研究提出了哪些挑战呢?这些挑战对我们又有什么深刻的启示呢?
无论我们直觉上或经验上是多么的不愿意,当代天赋论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科学精神——至少是心理科学中的一种普遍观念。那么我们所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关于婴儿心理的天赋性的科学确认。大量材料和实验数据表明:(1)婴儿具有先天规定的客体知觉的“原则”:婴儿来到这个世界时便能认识物体的“有界限性”、“凝聚性”、“坚硬性”和“没有接触就不会动”的特征;3-4个月的婴儿能在知觉输入的基础上推论某些物理学原理(如重力和惯性原则;物体不能穿越—个坚固的表面;不能同时占据同一空间),能认识到客体永久性或不变性。[8](2)婴儿具有先天规定的“计数原则”:——对应;稳定的排序;项目无关和次序无关;基数(只有最后的数词代表这组物体的总数)。(3)婴儿具有先天规定的语言素质和注意倾向:12小时的新生儿能区别语言输入与非语言的听觉输入;4天的婴儿已经对母语产生敏感。(4)婴儿具有先天规定的“常识心理学”:婴儿出生时喜欢注视人的面孔;婴儿用眼的相互注视和指向特定物体来进行非语言交流;对生物体和非生物体的运动的区别具有敏感性;18个月婴儿擅长“假装”。(5)成人脑的天赋特征:自闭病、威廉姆斯综合症、白痴专家等认知功能的特殊性;成人脑损伤表明认知系统的领域特殊性(如只影响面孔识别、数、语育等,但其他能力完好无损),等等。[9]对于发展心理学理论来说,一个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把婴儿心理的天赋性当作—个客观的事实加以确认。
紧接着的第二个挑战是:发展心理学理论必须严肃探讨关于儿童“天赋”概念的性质和内涵。根据我们目前的初浅的看法,“天赋性”不是指出生时就存在的预先规定的遗传蓝图(在这个意义上皮亚杰是对的);也不是遗传规定的不变的模块(因为这会导致一种静态的观点,而将“发展”完全排除在外)。合理的天赋概念也许是:一种相当有限的、与生俱来的素质。这样一种素质预先规定了婴儿最初的认识偏向或倾向;它能把婴儿的注意力引向特定的环境输入,而这又反过来影响随后的心理发展。我们认为,科学地限定“天赋”的性质和内涵将有助于我们不走向像福多那样的纯粹的天赋论。
由此便引出了第三个挑战:关于“先天”与“后天”的辩证关系。这是主张天赋因素的任何一种发展心理学理论不可避免的问题。从目前我们所达到的认识水平看,主张一种先天(天赋)与后天(后成)相互作用的动力论,也许是比较合理的解决方案。这主要是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丰富的可供选择的理论模型,如认知科学中的“联结主义模型”(人工神经网络),哈肯“协同学”中的“作为动力学系统的认知模型”等。这种相互作用动力论的主导思想是:(1)最初的天赋基础中详细规定的成分较少(而不至于像洛伦兹主张的那样,认知的范畴一如马的蹄和鱼的翅那样是作为遗传程序设计的结果而在胚胎发生中发展起来的),因而在天赋的相对固定性与后天发展的灵活性(可塑性)之间保持一个必要的张力;(2)若我们设想的天赋能力的图像越复杂,则解释后天认识发展的灵活性就更重要。因而我们的研究重点应该在后者;(3)天赋的因素或成分只有与环境发生相互作用,才能成为我们生物潜能的一部分;(4)相互作用的动力论强调的是认识的发展建构——皮亚杰的建构论将发挥更在的解释作用——而不是遗传规定好的程序的显露。
第四个、也是并非不重要的挑战是:关于当代天赋论对于发展心理学理论的价值。我们认为至少有这样两个大的方面的价值:(1)天赋因素的新发现使我们有可能重新探讨人类心智是如何在内部组织(建构)起来的,从而避免在纯粹的先天论与传统经验论之间作非此即彼的选择。天赋假设的一种优势是能阐明外界的“信息”是如何变成人类头脑中的“知识”的,从而也就有助于克服目前我国发展心理学界尚占主导地位的经验论倾向。(2)天赋论中的合理因素与马克思的实践观点并不是互不相容的,有可能在新的科学起点上将二者统一起来,从而将马克思主义实践论贯彻到底。
